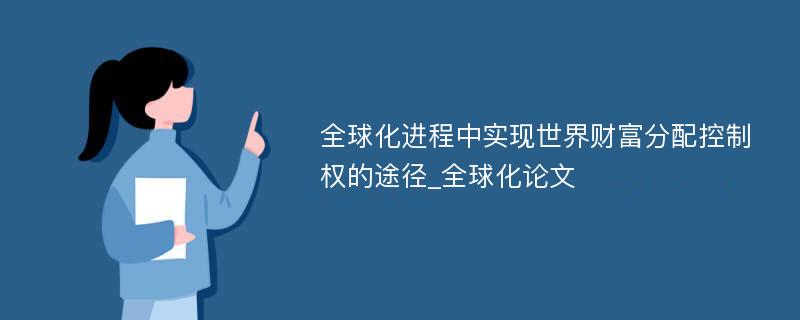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权论文,进程论文,分配论文,财富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尽管早在15世纪初,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开始七下西洋的远航,但启动近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却是欧洲的航海家。其原因在于,郑和以宣扬皇权和传播中华文明为主要目标的远洋①与欧洲追求资源与市场为目标的探险,其出发点截然不同,其结果亦大相径庭,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定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并且我们今天依然处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上升阶段,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由市场驱动的欧洲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价值更接近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引致了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就全球化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视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②还是自由主义将其理解为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③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④后发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⑤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⑥而“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⑦。由于权力资源是一种力量,或只是一种潜在权力,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力才能发挥作用。⑧权力的转化,就是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成以其他国家行为变化来衡量的得到实现的权力,即把国家的潜在权力转换为影响其他国家态度和行为的权力。现行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对权力资源转换的努力。例如,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投影”,因为国际秩序直接“约束行为体的价值分配活动”。⑨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和竞争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争夺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
传统意义上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的主要方式
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国家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是由一国的财富和军事能力来确定的,而军事能力通常与国家财富及技术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使得国家主动或被迫参与提升军事能力的世界竞争。历史地审视,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国家财富的殷实的重要来源,但并非是强国、进而巩固和拓展财富的必要因素;不仅如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囿于天赐的财富而疏于进取和武备,从而成为霸权国家仰仗军事力量攫取财富的“天堂”。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便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资源。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力,而逐渐衰微的强国会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的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战争并非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分配权的最有效的方式,⑩而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则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
1.倚重军事实力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
军事实力的运用是控制财富分配权的原始力量。霍布斯丛林法则所揭示的竞争方式及其结果,在近代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和依托的。汉斯·摩根索提出,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利益之根本,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实力的国家必然在国际上受制于强国。(11)通常而言,国家实力状况以及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力量的判断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尽管有学者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区分为领导者、追随者和边缘国家等多种类型,但凡是民族国家均会有其国家利益,无论处于哪种角色,“国家会致力于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这种努力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12)。尽管权力的资源来源广泛,但军事力量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随着国家的经济强盛和军事发展,不仅会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他国的领土和行为以及世界经济),也能够试图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彻底修正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对于既有霸权国家,“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13)而财富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维持军事强势需要巨额的政府支出与投资,这在客观上拉动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而又强化了军事实力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战争对工业生产能力扩张的显著的拉动作用,以近代钢铁工业为例,“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因此影响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4)。战争的目的是控制商业、贸易体系,获取经济利益。在戴维·希利看来,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5)
资本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要素和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霸权国家控制全球资本的最终目的,在于主导全球资本及其伴生的技术、信息的流向和流量,以低成本获取财富。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财富的分配权的控制从西班牙向荷兰转移进程中,尽管荷兰地理上相对较小,它却能赢得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势地位,在于荷兰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以显著的海上优势控制运输线与贸易,仅1644年,荷兰即拥有1000余艘战舰用来保护商业,其舰船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16)荷兰通过不断地骚扰西班牙的海运船只,打破了西班牙依赖于强大的海军和“炮舰政策”对美洲金银的垄断所形成的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加强对关键战争物资的争夺与控制,逐渐强化了波罗的海运输和贸易的控制,并且将这一海上优势转化为财富的来源。进而,财富的积聚促成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商业与金融重心,控制世界资本流动,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为其资本增值服务。
1688年荷兰总督威廉就任英国国王后,大力鼓励荷兰熟练工人去英国,加速了先进造船技术向英国的传播与扩散。到1780年,英国的商船队的运载量已经远远地超出荷兰的两倍多。(17)经过三次英荷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荷兰的贸易和海运力量,在英国的海上扩张与法国的大陆扩张夹攻下,荷兰被迫选择成为英国从属的军事伙伴,而英国则成为大西洋的领导力量,荷兰在海上和商业方面的地位迅速衰落。在与主要挑战者法国的竞争中,英国也是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控制欧洲的海上贸易来对抗大陆国家的军事影响,九年战争(1688-1697年)迫使法国陷入金融困境,连年裁减海军预算,无力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其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陷法国于困境。随着1793年英法战争中特拉法尔加之战使法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夺取大西洋的军事和商业控制权,战争的成果巩固了伦敦欧洲巨额融资的首要中心的地位和英国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
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国家的传播,对英国军事实力和以此控制的贸易体系的挑战不断出现,不仅动摇了英国的工业优势,更打击了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动摇了各国对其的依赖,引发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全球全方位地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业革命的传播与军备竞赛。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成为缩短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工业化差距的重要因素;美式制造系统代表了(军事)工业生产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被广泛引入了欧洲,显著地改进了大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工业化,一个有能力渴望大陆霸权、有能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国出现了,(18)英国已无法有效地控制世界贸易体系。
就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言,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始终是英国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的受益者,并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向海外传播的最大受益国。内战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的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技术被美国从英国引进后大规模用于工业。到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具备了与欧洲列强争夺市场的能力。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占世界总产出的40%强。2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海外资产翻了一番,并且在战争期间清偿了英国的债务,摧毁了英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巩固了美国的领先优势,全球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国家手中,在“恐怖均衡”推动的军备竞赛中,军事装备中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越来越高,只有控制全球金融资源的超级大国通过介入或威胁介入新武器开发领域,才可以把“恐怖均衡”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其他国家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投入。(19)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轮廓是部署于全球各战略要地的美国军事力量,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联系,强化、组织和支配西方阵营。相对于前苏联主要依赖军事政治资源控制东欧卫星国,冷战时期美国的准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众多的主权国家驻扎军队。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转为巩固其世界领导权霸权,军事力量仍然是美国依赖的重心。1996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触与扩大》里提出,“在海外保持美国的领导,我们可使美国更安全和更繁荣”。布什从2000年竞选总统起,就反复强调他的政策目标是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以加强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其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保障,倚重军事打击方法来解决国际冲突,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战争、1998年对阿富汗和苏丹的轰炸、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见一斑。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这一点。(20)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成为令全球瞩目的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而且东亚对全球政治秩序的作用日益重要。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的“权力场”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21),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全球战略部署,而战略重心东移或“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
2.依赖国际机制规导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
在全球化进程中,规范与规则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范式。(22)通常认为,国际机制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各行为主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3)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机制演变来看,现行规范各种国际经济行为和协调经济关系的国际规则与制度,主要是由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主导或推动建立的,反映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24)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反映着美国式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原则。美国按照其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力求他国遵循这些行为规范,(25)并谋求和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例如在吉登斯看来,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所有成员主权平等,即“特指法律主权而非事实主权。与拥有的实力相对应,大国有特殊的权力,也有特殊的责任”(26)。可见,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体现了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益和意志,成为其控制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方式。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方式,在国家间竞争与斗争过程中以条约或和约的方式明确了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条约作为正式的国际协议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成为“广泛的国际规制中的一个核心结构性元素”(27)。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不仅成功地牵制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力量,而且赢得了像直布罗陀等港口及沿海地区,从此以更强大的实力主宰海洋及海上贸易,为英国奠定一个比荷兰更广大、更密集的世界贸易体系创造了条件。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长达百年的“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意即英国是欧洲和平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维持这一和平秩序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力量均衡体系。在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协商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英国在欧洲主导和维护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样板效应”,即英国行使主导权(例如海上贸易保护)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利益,因而并没有其他国家去挑战英国的权威。于是英国在1848年废除《谷物法》,次年废除《航海法》,倡导在力量均势下的自由贸易,(28)牢牢掌握着全球近1/3的贸易,不仅降低了国内商品的价格,也为其他国家购买英国“世界工厂”的商品提供了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将大多数国家拉入英国主导的全球贸易网,强化每个国家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中的“共同利益”。这一体系日益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这种“共同利益”越是被各国所信奉,英国对这一体系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就越容易,代价也越低。马汉精辟地指出,英国不会把它的海上力量单纯地建筑在军事基地之上,也不会仅仅建筑在舰船之上,而是建筑在通过战争和和约获得的巨大的贸易优势上。(29)
梳理世界经济发展脉络可知,贸易协定和国际组织作为一个具有明确规范的、有目的的行为方式,对主权国家施加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改变国家的价值认同和利益目标,冲击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例如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全球贸易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与监督者于一身。据WTO官方网站显示,进入2013年,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已正式成为WTO成员方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9个。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制度化的框架并未解构,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内容,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控制的世界治理机构的重要性仍然无法取代,例如自1975年起,G7/8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机制;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始终占据着优势。(30)在这一国际机制框架内,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无法对现有国际机制施加有效影响而始终陷于两难困境:拒绝等同于被边缘化,遵从意味着被盘剥。
非物质性权力视域中的当代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对财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财富的主体要素也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部分代替各民族国家国内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加以利用,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是,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正如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31)霸权国家不再以占领殖民地为标志,而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软实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其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西方式尤其是美式民主,将其生活方式普世化。(32)长期以来,霸权国家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的变化,可归纳为如下若干方面:
1.文化价值观渗透:掌控财富分配权的灵魂
尽管文明冲突背后最重要的力量,在于非西方世界不断现代化必然带来的文明力量平衡的变化,部分是对于西方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滋生的不满和怨恨,但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出现,更多的则是由于西方的优势成为宣传西方利益、观念和价值的工具。(33)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一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有论者指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国化”;而“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缩影,他们把美国抬高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模式,系统地表述了旨在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政策”(34)。在基辛格看来,“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35)。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言论更是咄咄逼人:“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36)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因为信息网络技术飞跃的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各种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主流价值观,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37)。美国倡导的相互依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为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再以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张侵蚀为例,霸权国家通过消费文化的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消耗的泥潭和盲目追求炫耀性消费(38)漩涡中。
2.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强制:操纵国际财富分配的权杖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日益显著,成为开放条件下各国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准绳。同样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规定了活动或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全球产业链中标准权力与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导技术、产业领导权乃至世界经济霸权的兴替,成为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博弈(39)。技术标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权力和财富分配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些重要产业是否具有制定技术标准和推行技术标准的能力,决定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技术标准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决定了财富和物质权力汇聚的方式。(40)
历史地审视,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新的市场规则的制度前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降低贸易壁垒,使得商品与服务的国内市场拓展为全球市场;由于普遍性市场规则的形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全球生产与商品服务贸易呈现出体系化、专业化、交互式等特征,财富从后发国家向霸权国家流动的线路更加清晰、“合法”化。统一市场和普遍性市场规则的形成有助于技术进步的功效发挥,进而推动相应的产业技术标准建立与生产体制变革。(41)在模块化生产体制下,产业链往往纵向延伸,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具有兼容协议(界面、平台标准)的系统产品,(42)这个网络的标准也成为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准则。国际生产领域以微软和英特尔维代表的“温特制”(Wintelism)生产体制就是以模块化为基础,“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整合、控制全球资源”的。(43)
本质上,技术标准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控制力的编码规则或技术“契约”,有助于巩固霸权国家在于技术领域中的主导权和由此带来的财富分配权。在产业技术中取得标准制定权至关重要,技术先导性不仅关涉经济利益,而且关涉军事安全与政治利益;渗透性和网络效应则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可见标准的竞争对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国际政治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霸权国家和跨国垄断企业通过国家标准战略、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糅合在一起,占据了各个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体系,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标准竞争的网络结构中,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实际上为所有者建立了一个控制利益外溢的壁垒。由于标准的制定权通常受霸权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没有议价能力,从而沦为从属的模块生产者,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winners take all)的状态。由于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普遍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只有接受网络标准才能利用和享受网络带来的利益。标准作为共同的编码使无数一致化的单元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具有鲜明的正反馈机制,使得这个网络的标准具有通用准则,因而标准是网络系统的关键性节点,一旦控制关键标准模块,就能形成控制产业链、操纵和压制低层产业和整个网络的能力,进而影响到国家财富的流向。
由于通行的市场规则主要是由西方霸权国家所主导制定的,而标准制定者多属于在产业结构中处于顶层的西方跨国公司,因此在市场规则与产业标准所保护和实现的利益方面明显有利于霸权国家,后发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受挤压的境地。由于规则与标准的非对称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显著有利于制定者,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与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迫使后发国家接受和遵从设定的“游戏规则”,合法地控制的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标准竞争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后发国家企业发展、利益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3.生产体制牵引:跨国公司编织的“温柔陷阱”
全球化条件下,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不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受制于一定的生产体制,因而生产体制成为一种核心权力,既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也可以保障其他资源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整合生产要素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在于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44)被称为“美国式的法人经济”的大型纵向一体化生产体制是适应二战后企业竞争方式调整的一种新型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体制,直接推动了大型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巨大发展,成为各国企业效仿的标杆。正如杰夫·马德里克所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45)——新的标准化生产为企业赢得了新的规模经济。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世界贸易体系日渐演化为网络时代“全球化枢纽”的互动式分工结构,其最核心的力量在于使用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络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渗透到产业链或整个产业体系,能源互联网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新型材料制造技术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生产与服务日益标准化进而国际化,国际产业标准与产品标准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指挥棒”。新型的专业化分工协作被置于更高地位,例如半导体产业已趋向分裂为两类厂商:一类是只设计芯片、模块或电路板而并不亲自制造组装的“设计”厂商(feb-less firms),另一类是“制造”厂商(pure-play firms),只按照前一类公司的设计去制作芯片、模块或电路板。这种生产组织模式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发挥其核心竞争优势,而经济网络化使得设计、制造等不同生产环节灵捷地联系在一起。(46)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世界经济运行来看,基于模块化的新标准化产品生产平台与组织体制——“温特制”成为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体制。模块化是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过程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的行为,然后按照某种联系规则将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子系统(模块)统一起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的行为。(47)信息产品及网络设备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高度的标准化部件,能以较低成本便捷地整合为新的大规模标准化产品。不仅如此,通过这些标准化部件的不同组装方式,可以生成具有不同功能、满足不同需求、彰显个性的差异化产品。微软和英特尔共同构筑的“温特制”平台,即以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和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互相匹配依存,打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商业壁垒、闭合的盈利模式,通过短周期的产品、技术升级巩固其原有明显优势的领先者地位。美国的核心企业逐渐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最具备比较优势的价值节点或最能够创造利润的分工领域。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获得,主导企业出现“虚拟化”和产权控制一定程度的弱化。但由于“温特制”的作用,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规则和产品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48)“温特制”生产体制的成功,使得霸权国家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通过大型跨国公司将后发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国际分工体系变动的直接结果,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依赖于新的市场规则与产业产品标准,穿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和财富。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编织了一张张无形的和难以挣脱的生产、贸易、金融网络,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核心节点,在各自主导领域发起的产业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的制定,以公司内贸易的形式主导商品生产、贸易和投资,操纵全球产业链的构建,掌控着主要产品的定价权。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始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是霸权国家生产样式上的重大调整。其“再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修正制造业过度外包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虚拟化等缺陷,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继续把持重要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很可能出现一些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尽管各自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亦有低端循环延伸至高端循环,但从根本上来看,但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例如,例如美国凭借先进能源装备技术大力发展页岩气产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的报告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49),同时亦对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
4.货币汇率操纵:霸权国家发动的金融战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主宰着国际的资本市场作为西方国家成就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14个战略要点中的3项。其中货币汇率即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研究表明,汇率升贬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具有虹吸全球财富的惊人作用。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具有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功能,还能增强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意味着削减外部债务负担,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50)例如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中,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性财富,但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在全球财富分配控制权上始终未能获取议价权。
汇率变动,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的结果,但更是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利益斗争、博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确立了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但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同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优势被逐渐削弱,例如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制度优势造成重大打击,金砖国家的超常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采用非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也已经超越日元而被誉为“第二美元”。二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在相对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所支撑的,军事优势的削弱意味着政治地位和国际号召力的相对下降。第一次海湾爆发后,美国发现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地在世界任何地方开辟多个战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需要西方盟国的支持;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伊朗核危机上,需要看俄罗斯和中国的脸色,等等,这是一向自大的美国非常不情愿的。三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还在国际公开场合表示要借鉴和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从而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冠名为“输出模式”。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可知,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是美国惯用手法。各国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霸权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后发国家,并迫使后者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泄洪区。(51)从东亚、拉美等地区近年来发生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来看,汇率手段对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再如人民币被迫对美元的升值,意味着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国家财富巨额缩水,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剧,企业竞争优势大面积受到挤压。负利率造成的存款损失属于国内财富的再分配,美元储备的贬值属于国民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国家财富的流失。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从中国本土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的国际化转移,人民币加速升值实际上加速了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
全球化的深度发展,由霸权国家构建的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成为控制全球财富流动的主要方式。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依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加以利用,把领土征服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手段视为攫取世界财富的方根方式,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是,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并日益打上“合法性”的烙印。
在霸权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全球价值链和财富流动呈现出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尽管各自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亦有低端循环延伸至高端循环,但从根本上来看,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当下的国际体系显然由霸权国家所主导和控制,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追逐与控制也必然会侵蚀后发国家的国家利益,但接受现有的经济规则依然是后发国家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进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与其抱怨经济秩序的不合理、经济规则的不公平而简单拒绝排斥,还不如在接受游戏规则的同时,从中寻找有利的机会,通过发挥自身的区位竞争优势来增强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议价权,进而影响和改革这一规则。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有可能导致全球要素市场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引发全球财富的流动。中国如果能切实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生产方式,将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当代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的变化,已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后发国家的高度关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应当成为后发国家努力的方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都在经历着调整和变化,这对于中国更加积极、负责任地融入和影响国际社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①区别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利润和财富为目标的市场开拓。
②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100-101.
③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④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⑤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1页。
⑥Robot W.Cox,"State,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in R.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54.
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47页。
⑧David A.Baldwin,Paradoxes of Power,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p.132.
⑨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⑩例如依赖坚船利炮,葡萄牙对拉美国家300年的殖民扩张中,共运回黄金250万公斤,白银l亿公斤;西班牙在1521-1560年,共从美洲掠夺黄金16万公斤,白银445万公斤。这种掠夺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短期内成为欧洲的财富高地,但由于财富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繁荣的部门不是工业和制造业,而是印度香料的贸易和其他奢侈性消费的部门,并没有转换为产业技术革新的资本和增加军事力量的投资,因而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十分短暂。
(11)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
(12)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9-11.
(13)E.H.Carl,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London:Macmillan,1970,p.109.
(14)McNeill,William,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2.pp.211-212.
(15)转引自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16)丁一平等:《世界海军史》,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7页。
(17)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18)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1页。
(19)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2、102—103页。
(20)阎学通:《和平崛起与保障和平——简论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
(21)Sumit Ganguly,Andrew Scobell,Joseph Chinyong Liow,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 Handbook,2010.
(22)张明之:《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战略性发展机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审视》,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3)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1982,p.186.
(24)Robert Cox,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6.
(25)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26)Anthony 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266.
(27)Abram Chayes,Antonia Handler Chayes,"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2,Spring 1993,p.175.
(28)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原因,是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优势,因而成为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的外溢与传播,其他国家可能蚕食霸权国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而“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导致霸权国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由此,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霸权国家的重要选择。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24页。
(29)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289页。
(30)Saskia Sassen,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21.
(31)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2)朱世达:《“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33)Samuel Huntington,et al.,"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1993,Vol.73,No.3,pp.22-49.
(34)Christina Klein,Cold War Orientalism: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1945-1961,Ew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98.
(35)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36)David Rothkopf,"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No.107,Summer 1997,p.45.
(37)Mclsrael Maoz Azaryahu."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Vol.5,No.1,Spring 2000,pp.45,41-44.
(38)陈爱华:《解读“物”社会功能的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物社会功能”的伦理透视》,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9)毛丰付、张明之:《ICT产业标准竞争与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2期。
(40)杨剑:《技术标准竞争的权力结构限制与中国技术标准战略》,载《WTO经济导刊》2007年第6期。
(41)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
(42)Katz Farrell."Innovation,Rent Extraction,and Integration in Systerms Markert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0,Dec.
(43)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44)迈克尔·德托佐斯等:《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45)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46)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
(47)C.Y.Baldwin,K.B.Clark,"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Vol.75,No.5 pp.84-93.
(48)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49)杰夫·代尔:《亚洲崛起动摇“美国治下的和平”》,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12/c_124081495.htm.
(50)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伴随着弱势美元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和初级原材料价格的一路飙升、跨境投机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参见程实:《用货币统治世界》,载《中国经营报》2007年12月30日。
(51)何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因素及其影响》,载《中国外汇管理》2005年第6期。
标签:全球化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商业竞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