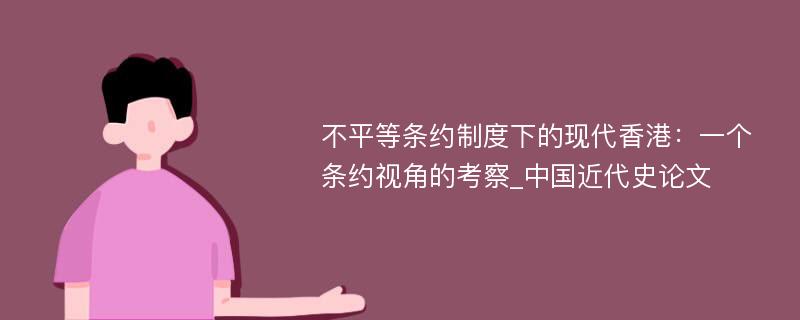
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近代香港——基于条约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条约论文,香港论文,条约论文,近代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4-0108-07
香港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在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地理名词的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与政治蕴含。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发展与终结都与香港紧密相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学界对近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虽然程度不同,重点不一,但都丰富了近代香港史的研究。从赋予香港以鲜明特征的条约出发,将其作为研究的视角,进而探求其在整个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本文的出发点之一。探讨不平等条约对近代香港社会的走向与影响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①。
一
不平等条约体系(学界亦有称条约制度者,其来源即是费正清教授的treaty system一词,本文称为条约体系)研究基本上包括以下几个方向: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内容与特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大的问题而进行,都属于他们下面的二级题目。探讨香港在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地位,也就难以避开上述问题。事实上,把涉及香港的不平等条约放到这四个大的方面中去考察,即是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近代香港。
依据严格的不平等条约概念,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直接涉及香港的不平等条约数量为17个②。这17个直接涉及香港的条约,可分为政治、租界、通商、鸦片贸易、邮政等6大类别。除去割让条款和划分租界的条约外,鸦片贸易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反映了香港作为向中国内地贩运鸦片自由港的事实,而组成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几大方面并未得到体现③。
毫无疑问,割让香港的《江宁条约》处于条约体系的开始位置。在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江宁条约》是一个标志,中国从此笼罩于不平等条约的罗网之中,自是之后,香港站在祖国的大门边,目睹与亲历了一部中国近代史。
学界一般认为,不平等条约特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与租界特权、协定关税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内地传教特权、驻军和使馆区特权、引水权。不平等条约体系亦即规定这些大大小小特权的具体约文,通过一个个具体条款,中国的主权受到限制。虽然割让领土与赔款并未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特权,但毫无疑问,二者均属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这是一个默认的事实。
由于割让条约的存在,使得香港岛内行政已经与内陆各省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即使与众多的租界和租借地相比,亦有显著区别:中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不论是名义上的主权还是租借出去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特点决定了此项事实: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施加的特权并未影响到香港。不但作为不平等条约特权标志的领裁权不存在于香港,同样地,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也不适用于香港,香港其实是游离于不平等条约之外的,但是,割让领土其实是最大的不平等。
《江宁条约》明确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与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④。这样的条款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不论是公共租界还是专管租界,中国仍然拥有租界名义上的主权,即使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主权。这是香港与租界之间所具有的本质不同。
中国虽然失去了租界的行政管理权,但租界仍然是中国领土,关税、国防、租界内中国人的管理等仍属中国,而且即使租期再长,仍然有一个收回的期限。威罗贝认为,“这些租界或居留地没有一个是脱离中国主权的。这些地区内居住的外人,只能享受他们在中国别处所能享有的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而居住在这些地区内的中国人,也决未脱离本国法院或其他中国政府机关的管辖”,因此居留地或租界仍属中国政治主权之下⑤。威罗贝接着引用了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的第一条,借以说明该问题。“大清国大皇帝按约准各国商民在指定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贸易行走之处,推原约内该款之意,并无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一并议给……再凡中国已经指准美国官民居住贸易之地,及续有指准之地,或别国人民在此地内有居住贸易等事,除有约各国款内指明归某国管辖之外,皆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⑥。
香港岛是通过条约割让,而九龙则是“永租”。“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永批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这里的永租实即割让⑦。巴夏礼在中国移交九龙时曾当场宣读了一份声明:“自此以后,大清文武大小官员以及差役人等,均不能在该地界内管理庶民。所有地界内一切政务,惟应归大英大君主所派官宪,遵照大英大君主会同内廷建议各大臣商定律例管辖办理。现在尚未奉到大英大君主谕旨。本大臣先将该地界,交与总督香港地方、水路军务男爵管理政治。其应别设派文武官弁,以及田土、民情、保安、地方、各等事务,均可操权办理”⑧。九龙的主权已经不属于清朝政府。
租界内的市政当局或工部局可以管理界内的警务、卫生、筑路等事项,但这只是行政机构,是为通商而建立的,他们不具有主权国家地方机构的地位。威罗贝特别指出,租界的治理机关虽有设置警察队的权力,警察人员并可执行逮捕,但他们不能设立法院以强制执行它们所发布的行政条例——一切司法诉讼必须在领事法庭进行⑨。香港则是英国直辖殖民地,拥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系统。通过1843年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英国政府确立了以香港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行政管辖系统,这与众多的租界、租借地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正如辅政司马撒尔所言“鉴于香港岛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受英国法律支配,……因此无论何国国民,凡胆敢以身试法者,必将受到英国法律的惩处”⑩。
协定关税是不平等条约体系中仅次于领裁权的另一重要特权,这里所谓的协定关税亦即进入除香港外的中国领土的关税,香港本身的关税已经不在清政府的掌控范围之内,是否收税,如何征收,清政府已力不能及。清政府要协定的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关税,在最初,主要是通过5个通商口岸实现的。关于香港的商埠地位,中英双方曾经有过争论。英国要求清政府对香港开放全部口岸以进行贸易,但清政府并未应允,双方最终达成了1843年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初步规定了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关税问题。内地居民入香港贸易,须通过《江宁条约》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发放牌证,“嗣后凡华民欲带货往香港销售者,先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关口,遵照新例,由海关将牌照发给,俾得前往无阻”(11)。这种状况到1858年的天津条约时得到改善。通过《天津条约》,外人可以深入长江各口,实现了“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的便利条件。
二
晚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直到收回香港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对香港的影响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外交途径。香港相比于其他租界或租借地所具有的这样一个特点,决定了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
香港近在咫尺,清政府却力不能及。随着香港本身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与内地交流的日渐频繁,种种问题开始显现。为了防范利用香港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以及鸦片走私等问题,清政府曾经设想在香港设立领事,其中以张之洞的奏折最具代表性。张之洞分析道,“窃维香港一岛,密连粤省,近年商务日盛,华民寄居益多,交涉案件无时无之,而该处尚未设有中国领事官,办理每形不便”,自香港归属英国后,“海外诸国讲好于英者,莫不各驻领事于彼,以治其本国之务,中国最为切近,转无驻扎之官”(12)。张之洞认为,清政府在香港设领,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需要:一曰通商;一曰保民;一曰逸犯;一曰巡缉;一曰海防。清政府在英属新加坡、美国旧金山以及西班牙古巴等处俱已设有领事,而“此等外埠,程途不若香港之近,华民不若香港之众,贸易不若香港之多,关系不若香港之要,彼皆设官,此何独缺”;内地人犯罪,逃往香港,“最为粤省吏治地方大患。照约本有逃犯查明交出之文,乃港官每事袒护,或交或否”等等,一一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利害关系(13)。虽然清政府通过种种外交努力,并未获得理想结果,最终未能在香港设立领事。
香港是向中国内地贩运鸦片的自由港,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为了治理鸦片泛滥之害,晚清政府屡次与英国交涉,约束香港的鸦片贸易。清政府已经认识到鸦片走私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李鸿章在《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中指出:“查洋药系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进中国各口。香港为英国属地,中外奸商即于该处私相授受。检阅总税务司呈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四年所到香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余箱至九万六千余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则止六万五千余箱至七万一千余箱。光绪五年所到香港洋药十万七千余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则止八万两千余箱,实计香港每年私销洋药二万数千箱,除分运新加坡,旧金山各埠外,余皆不经新关,不收厘税”(14)。经过清政府的外交努力,1886年9月11日中英双方订立《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其中第三款规定“鸦片运至香港,应即报知港长,非经港长允许并通知鸦片包商,不得转运,或存栈,或由此栈搬到彼栈,或再出口”,中国九龙方面在适宜地方“在税务司下设官一名,发卖中国鸦片税单”(15)。
新界不同于香港岛,亦异于九龙:取得方式不同,国际法属性不同。香港本岛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英国政府通过炮舰,强行从清政府手中取得,不是“租借”而是割让。九龙半岛南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属于“永租”,仍然是中英间战争的产物。新界的租让并不是由于中英之间的战争,至少可以说不是中英之间直接战争的产物,虽然新界的租让难免具有武力威胁的因素。新界属于“租借”性质,有固定的租借期限,“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99年期限的划定毕竟固定了租借期限,中国保有收回新界的条约依据(16)。
国际法学者公认,租借地主权仍然属于中国,王铁崖曾引用相关国际法学家的论述以为证明。举出克罗福特的论述,认为“主权”不应与“主权的行使”相混,而“一个国家可以继续是主权的,而由于条约或其他,重要的政府职能由另一个国家来行使”(17)。接着引用了德国法学家沙克对德国胶州湾租借地的评价,认为该评价恰当地说明了问题。“中国对主权的保留是法律上有效的。转移既不是永久割让,也不是若干年期限的割让。并不是领土被割让了,主权并未转移。德国对该地区行使主权的权利,但是所行使的主权是中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德国行使作为权力的委任的主权的权利”(18)。
之所以在这里要明确“主权”是不可分,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仍然拥有租借地的完全主权,为收回租借地奠定法理上的论据。在中国的租借地内,各国只是行使中国通过条约给予他们的权利。中国早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已经对与会各国明确了这一点,顾维钧在发言中指出:“各租借国控制租借地的办法和程度虽各不相同,但租约都有固定期限。租借权未经中国同意不得转让第三国,此层或明文规定,或含意如此。租借期间租借地行政权利的行使虽有中国放弃给予租借国,但中国对所有租借地保留了主权。租借权都是依条约而产生的,和割让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有所不同”(19)。顾维钧代表中国提出了收回租借地的要求,各国在事实和法理面前都予以承认。虽然租借地不一定能顺利收回,但是在法律上已经确认中国仍然拥有租借地完全的主权。
新界有固定的租借期限,这是其与其他租借地的共同之处,即使存在租借时间长短的区别,但毕竟属于同类性质。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规定中国可以在九龙城驻扎官员,保有对中国居民的行政权,但是,除此之外的新租之地清政府无权管辖。即使这样,清政府对九龙城的部分行政权也在1年后被英国剥夺,“1899年12月27日,英国修改1898年10月20日的枢密院令第4条,制定了新的枢密院令……‘见于九龙城内中国官员行使管辖权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上述枢密院令应予废除,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员应停止在城内各司其事”(20)。虽然如此,新界主权仍然归属中国。根据条约,新界是为保证香港的安全需要而“拓展”,虽然学者们认为这一借口并不成立,但是条约已经签订,新界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法律地位已成事实。在性质上,此一时期的租借地皆具军事用途,无不假军事借口而签订,比如俄国租借地旅大,比如威海卫租借地,比如胶州湾租借地,他们皆是因军事用途而强租。
有研究者认为,“较之租界,中国在租借地内丧失了更多的国家主权。租借地的殖民化程度更深。除了在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外,它们与被割让的领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租借地的特点,反映了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地位(21)。
三
香港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通过与条约特权的关系来体现,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来展现。《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存在,使得香港的收回是中国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后一个阶段,虽然澳门的收回要比香港晚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地位上,香港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中国政府不但收回了新界,还收回了被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香港与澳门的收回标志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最终结束。
历届政府从未放弃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关于香港的条约自然在撤废之列。但是,香港除新界外,均为割让出去的领土,并不为不平等条约特权所涵盖。民国时期的废约运动,无论是要取消治外法权,还是关税自主,均与香港无干。
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过香港问题,但均未获得通过。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中国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中提出了香港问题。顾维钧回忆道,“我到伦敦任职不久便接到训令,要我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训令不是直接要我谈判,只是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经过调查,顾维钧的结论是“英国——政府、金融巨头集团和普通老百姓——打算把香港全部归还给中国,不过人人认为当前应先解决当务之急”(22)。
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英美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权利,并与国民政府重订新约。在签订中英新约的谈判中,国民政府提出了香港问题。中国希望在新约中增加归还新界的条款,“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23)。为什么国民政府提出收回新界,而不是整个香港?既然要废除中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而割让香港的《江宁条约》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当然应在废除之列。王建朗研究员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政府考虑到谈判已割让领土一定非常困难,因而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容易的新界入手,因为这是租借地,即使根据不平等条约,主权仍归中国;二是新界占据了整个香港地区的90%以上,其他地区对新界有较大的依赖性,收回新界之后再图整个香港有很大的可能(24)。
英国政府内部对中国提出的收回新界,存在不同的意见。薛穆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他们就不大可能放弃,因为他们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范围”(25)。但是克拉克认为,“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并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拖延。副外交大臣则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在一项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中提出新界问题,但其仍然同意克拉克的主张。艾登认为,英国的答复应是:新界不属条约范围,但英国愿在战后讨论其未来(26)。香港问题最终未能在中英条约中体现出来,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未提及香港问题,“现本政府与美国及英国政府分别签订条约,废除英美在华之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之特权……同时英美两国宣布上海与厦门公共租界内指行政与管辖权应归还吾国,租借内之所有权利亦应放弃;其与英国签订之条约中,英国政府更放弃天津及广州租界内之各国权益”(27)。中华民国时期,香港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有不平等条约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28)。该规定考虑到条约的继承问题。虽然国民党政府与外国订立了大量条约,而且其中确有很多的不平等条约,但还有一种状况下的条约需要予以说明,即国民政府继承的晚清条约,主要是不平等的边界类条约。事实上,截止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已经从条文上废除了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晚清以来的许多条约特权已经不复存在(29)。其中,涉及到领土划分的边界类条约是个例外。晚清以来中国政府,主要是晚清政府,签订了很多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款,如何处置这些条款,共同纲领没有给出明确说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条约是晚清政府的遗产。虽然一直未予单方面废除,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其他的边界类条约。
新中国对旧有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时,关于香港的条约并不在废除之列,澳门也是这种情形。如果领土问题不算作不平等条约特权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认为此时新中国已经为不平等条约体系画了一个句号。但租借地依然存在,依据中英之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为租借给英国的领土。如果香港与不平等条约体系存在关联,那么主要是因新界问题而存在这种关联的。因不平等条约而割让的领土当然属于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领土主权,但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虑,新中国政府尊重既有的现状。1972年中国致函联合国,强调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归属问题,“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30)。
1951年春,周恩来更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策略,指出:“这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继续让英国占领香港“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31)。毛泽东在接见索马里总理谈话时指出:“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并解释说:“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32)。经过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同时将香港交还中国。至此,中英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遗留完全清除,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及其影响也得到彻底消除。
注释:
①本文所做的条约考察是基于王铁崖三卷本《中外旧约章汇编》而作出的。该三卷本汇编是目前公认的最为权威的编纂,虽不能收罗所有的约章,但重大约章均已收入。
②关于条约概念的讨论详见侯中军《不平等条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一——条约概念与近代中国的实践》,西安:《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不平等概念的论述,详见侯中军《不平等概念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这17个条约分别是:1842年8月29日《江宁条约》、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858年6月26日《天津条约》、1860年10月24日《续增条约》、1874年《轮船往来港澳章程》、1876年9月13日《烟台条约》、1885年7月18日《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86年9月11日《香港鸦片贸易协定》、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年3月19日《香港英新租界合同》、1901年5月31日《香港英新租界水面照会》、1902年9月15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4年12月29日《互寄邮件暂行章程》、1905年9月9日《香港政府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907年12月2日《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1911年5月8日《禁烟条件》、1917年9月《九龙分关章程》。
④⑦(11)(15)(1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1、145、37、488、769页。
⑤⑥⑨(19)[美]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与利益》,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09、262、310、299页。
⑧《额尔金晓谕》(中英文两种),1861年1月19日,英国殖民地档案,CO129/80,第49,50页。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6页。
⑩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04页。
(12)《粤督张之洞奏请催香港设领事以期安内驭外折》,《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六。
(13)《粤督张之洞奏请催香港设领事以期安内驭外折》,《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六,第9~12页。
(14)《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第17页。
(17)(18)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7、369页。
(20)《香港政府宪报》第46卷第9号(特刊),1900年2月20日。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71页。
(21)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22)《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第14~15页
(23)《外交部关于中英新约意见书》,1942年11月7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765页。
(24)王建朗著:《中国非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25)《薛穆致外交部》,1943年11月17日,FO371/31663。转引自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59页。
(26)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60页。
(2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533页。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章程》,1980年9月,第18页。
(29)关于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历史及抗战废约问题,请参见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一文,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30)吴学谦:《就提请审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香港问题文件选辑》,第17页。
(31)李育民著:《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64页。
(32)《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