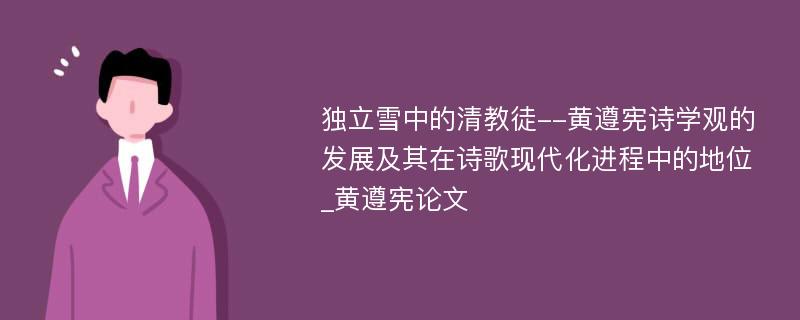
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黄遵宪诗学观的发展及其在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教徒论文,诗学论文,风雪论文,诗歌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275(2006)01-0016-06
黄遵宪一直被一些学者看作清末“诗界革命”的代表。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很可以算作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直到80、90年代,一些近代文学史仍沿袭此说,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诗界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1] (P731)。
然而,黄遵宪本人,在临终前不久,却有一段自我评价,和文学史家们的论断不同:
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2] (P440)
也许因为未曾留意北美大陆的开发史,这段话似乎没有引起很多人深究其意义。17世纪初,100多名英国清教徒登上北美洲东北海岸时,那片后来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土地几乎还是令人生畏的荒原。他们在那里开辟草莱,建立了第一片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大举殖民的历史。“清教徒的代表们在马萨诸塞建立了移民区,其影响却遍及其他移民区”,而早期清教徒文学也为后来的美国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3] (P1)。一个多世纪后,由清教徒首先开拓的这片大陆上才建立了那个“西半球新国”,而华盛顿、杰弗逊(哲非逊)和富兰克林,才是美利坚独立、开国的旗帜和代表。
黄遵宪的意思很清楚。这位了解美国历史的外交官,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自己在近代诗歌变革史上的地位:我只是一个开拓者,一个在荒原一般的旧诗领地上,在迷茫而寒冷的“尊古”风雪中艰难行进的、孤独的开拓者,还不是一场创建新诗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和代表,而且新诗国的建立也有待于未来。这位毕生致力于诗歌改革的诗人,对于一种能挣脱传统束缚(象北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新诗的追求,对于一个新诗国的瞩望,看来比同时代的人更为远大。因而他对于自己“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的评价,也可能比同时人以及许多后人更为准确。季镇淮先生《〈近代诗选〉前言》称黄遵宪“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先导人物”[4] (P325),是最符合黄遵宪自我评价的。
本文着重通过黄遵宪的诗歌理论,结合其创作,考察这位诗界革命前的“先导人物”,探索中国诗歌改革的历程。
在古代文学各体裁中,诗歌是成就最高、发展得最为成熟、形式体制也最为精致的。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却也构成一个能量巨大的引力场。所以,中国诗歌近代化变革的探索,进行得相当艰苦而缓慢,起步时往往只能借助前人经验和理论,加以变通。黄遵宪的早期诗论,就表现出这种特点。
黄遵宪说自己“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很多论者认同了这个说法。其实这是他晚年的语言。在他“少日”,“诗界”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他的“论”也没有那么明确。不过“别创”即改革思想确实出现得很早,这就是他21岁写的《杂感》: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这首诗的主要意义,是提出了诗歌的“今古”矛盾,这正是近代诗歌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他不像前人那样只是针对某些诗派,而是针对整个诗坛普遍存在的学古倾向,主张突破传统的“拘牵”,创造出与古人以及沿袭古人者不同的诗,确实表现了一种革新诗歌的自觉和勇气。
黄遵宪反对“尊古”的思想基础,是当时兴起的经世思潮。《人境庐诗草》第一篇就称:“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2] (P70)诗坛上“俗儒好尊古”,就是思想文化界“昂头道皇古”的表现。诚然,经世思潮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成为从传统转向近代的思想通道:由此出发,经世主张可能随着“世”即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随着经世救弊的需要而发展、变革。但经世救弊本身还不一定是一种近代思潮,当时提出的经世策略大都还没有越出传统范围。青年黄遵宪思想中最可贵的就是“知今”、“阅世”,所以此后几十年中,他对世界时代、对近代中国的认识日渐深化。但当时也还阅世未深,知今不足。他所能感受到的,主要是面对鸦片战争后时势变化,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失落,所谓“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换言之,他虽然提出了诗歌“今古”问题,但他所谓“今古”之别,还只是形势不同;他还没有也还不可能意识到“今古”的时代性区别。
因此,当他试图在创作中具体解决“今古”矛盾时,就遇到了困境。26岁左右写的《致周朗山函》[2] (P291),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困惑:
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
“其变极尽”,确是对古典诗歌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概括。以题材论,从自然千变到社会百态,几乎没有古典诗歌还没有写到的;以风格论,浪漫、现实、雄奇、平淡、晓畅、瘦硬、神韵、性灵……已经无体不备;以功用论,言志、抒情、叙事、议论,乃至赠友、悼亡、作序、代书、干谒、判案……凡是用文字的地方都可以用诗。“其变极尽”四字,道出了古典诗歌引力场的广阔和引力的巨大。要想挣脱这个引力场,哪怕跨出一步,都绝非易事。一方面豪迈地宣称“古岂能拘牵”,一方面却又深感“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这一矛盾,直到后来,仍长期困扰着这位先行者。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那时他只能提出两点:“有我”、“率真”。《致周朗山函》说:“虽然,诗固无古今也”,天地自然之日出其态而不穷,悲忧喜欣之出于人心者无尽,兴亡聚散生死贫富之出于我者不同,“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又说:“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有(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亡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也。”
有些论者把此信所论视为黄遵宪诗学基本观点且给予高度评价[1] (P749)[5] (P73),对此似可商榷。诚然,“有我”——表现独特个性,“率真”——抒写真实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但也是最一般的原则。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两点,并有许多论述。远的不说,稍前于黄遵宪的宋诗派诗人何绍基,就提出“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反对“或逐时好,或傍古人”[6] (卷三)。宋诗派是被今人视为学古诗派的,而何绍基的观点却和黄遵宪十分相近,这至少说明,黄遵宪这两个主张还不足以和他所反对的“尊古”派区分开来。以“我”、以“真”可以成一家之诗,却不足以对抗崇古诗风。关键在于“我”和“真”的内涵,在于“人”是否具有新的思想感情。黄遵宪当时对此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
他提出的另外两个设想,是“俗语”入诗和学习“民歌”。
对于“我手写我口”、“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后人评价都甚高。胡适说这“竟是主张用俗话做诗”,王瑶在建国后最早的一篇黄遵宪诗论中也说这是比诗界革命“更彻底的主张”[7]。钱萼孙(钱仲联)曾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黄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8] 这个意见却遭到一再反驳。诚然,“少年兴到之语”的论断确实轻率了,可是反驳者都没能解释钱仲联指出的一个事实:黄遵宪诗集中只有少数诗用了口语,绝大多数诗不仅用文言,而且用了很多典故,亦即他并非“我手写我口”,倒确实是“无一字无来历”,这是为什么?
这里首先涉及对《杂感》诗的理解。实际上,黄遵宪只是认为可以和要敢于以“流俗语”入诗,并非主张完全用口语做诗。而以俗语入诗也早有人提出,龚自珍就说过“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但这和五四以后完全用白话写诗,不是一回事。所以,说“这是我国语言文学史上关于言文合一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1] (P755),不准确。
更重要的是,在“俗语”即社会语言本身近代化之前,以俗语入诗并不能带来诗歌质变。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化,一是通俗化,这是相关但不同的两个问题。古代语言与近代(现代)语言,是两个时代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和表述方式都不相同。而俗语和文言,则是同一语言系统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吸收俗语,可以丰富书面语言,但不会改变语言的时代性。只有口语随时代变化以后,以近代的口语、白话写作,才可能创造新的文学。黄遵宪后来的创作,主要向着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思想发展。而在描写日本、欧美、南亚风光世态,表达民族自强、民主自由思想等等这些方面,“流俗语”是无能为力的。这才是黄遵宪并未把“我手写我口”贯彻于创作实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对这一主张,不应作过分夸大的估价。
其实,在那组《杂感》诗中,他还提出过另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今言”:“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若置重译,象胥通蛮语。”“今言”所涉及的,已不仅是“文”与“言”的对立,而且关系到“古”与“今”的差别,就是语言的时代性问题。不过这层意思想当时并未展开。
他的另一个设想是学习民歌。其《山歌题记》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正以人籁易学,天籁难成也。”① 后人对此也评价很高。然而这也是前人提出并实践过的。如明代李开先《词谑》云:“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冯梦龙辑《山歌》十卷,“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论更过之。而且同样,民歌也有个近代化问题。山歌、情歌给诗带来自然清新,却未必适应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意境,所以黄遵宪的多数诗并无民歌风,相反更长于以文为诗。对“我手写我口”和取法山歌的主张评价过高,其实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主导论”等偏颇观念所致。
青年黄遵宪主张“有我”、“率真”、“俗语”入诗和学习山歌,一方面反映出他为探索诗歌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变革意识,但如何变革,他还没有找到“出其范围”的途径,还只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诗歌的变革,还有待于时代变化、他本人思想变化和在创作实践中探索。
时代变化和人生机遇使黄遵宪踏上一条传统士大夫从没走过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之一,成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诗人。从光绪三年(1877)起,历任驻日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这十多年外交生涯的独特经历,改变了黄遵宪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正如他在政治上不断寻求救国道路,他在诗歌领域里也不断探索改革途径。在传统诗歌的巨大引力场中,这位诗歌改革先行者的探索显得非常艰难,也因而极其可贵。
黄遵宪初到日本时,他的诗学观变化还不大。观其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所论“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以学而至焉者。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云云[2] (P760),基本上是传统的作诗之道。他与冈千仞所论大体相同。其思想的重大变化,约在1880、1881年左右,他受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2] (P453)。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也发生重大变化,标志就是《明治名家诗选序》: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章,国必弱。故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文章之有诗,又等而下之矣。虽然,古者太史巡行群国,观风问俗,必采诗上陈,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春秋》为经世之书,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我朝大儒顾亭林之言曰:“自诗之亡,而斩木揭竿之变起。”盖诗也者,所以宣上德、达民隐者也。苟郁而不宣,防民之口,积久而溃,壅决四出,反或酿成巨患焉。然则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所以臻此极盛也。……其雍容揄扬,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固不待言;即偶尔有触忤时事,稍涉忿激,而其意本乎忠厚,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专集总集之编,相继出于世,是可以觇国运矣。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而其人能以诗鸣者,皆绝为当世所重。东西数万里,上下数千年,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安可以其无用弃之哉?②
据黄遵宪手迹稿,文末还有一段:
尚武者不能废文,强弱之故,得失之林,其果重在此欤?抑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而无用之用又自有故欤?[2] (P250)
这篇文字尚未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是黄遵宪诗歌改革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表明其诗歌改革理论的基础和方向转变。
首先,“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意味着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摇。价值观是任何一种形态文学生存的前提,因此这一判断,实际是对传统文学继续存在的否定。而更重要的是,关于“文章为无用之物”的判断,是以“今日之世”为参照系的。他不是一般地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而是认为过去曾经有用的文学到今日已为无用之物。这个“今日之世”不只是指中国社会,而是指“五洲万国”即世界时代。他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而且进一步思考:欧洲的强盛,真的只是他们一味尚武、讲求船坚炮利吗(“其果重在此欤”)?他从明治维新看到诗歌在维新运动中的舆论动员作用:“文章亦小技,能动处士议。武门两石弓,不若一丁字。”[2] (P99)青年时期就深知“识时贵知今”的黄遵宪,走入近代世界后,已开始意识到“今日之世”与古代的时代性区别。否定了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文学的追求,即他所说“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这成为其诗歌变革的动因。
其次,从过去责备俗儒尊古,到通过对明治维新前后诗歌的对比,揭示了诗歌衰落的深层原因——文化专制。“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岂止是对德川幕府时代的描绘,难道不包含对清朝文网繁密的联想吗?而明治诗歌“极盛”的原因,则是“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亦即创作自由。后来他在《日本国志》引进了西方“自由”观念:“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为人各有其身,身有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近代自由论,为诗歌改革、诗歌解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欧罗巴”,希望能像欧洲“以诗鸣者”那样,创造出“绝为当世所重”的诗。中国古代诗歌,以纵向继承为主,可以亲风雅,可以崇屈骚,可以尊李杜,可以学苏黄,从没有人提出学外国诗人的。在中国文论史上,黄遵宪是第一个把“欧罗巴”诗人树为师法对象的。它标志诗歌变革的新取向。当然,黄遵宪主要是看重欧洲诗歌能发挥社会作用,他还不懂“欧罗巴”的诗,在艺术上还无法借鉴。
此文作于1880年,当时可称空谷足音。
也是在这之后,黄遵宪在诗歌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逐步向着创造区别于传统诗派的“新派诗”方向努力。“海外偏留文字缘……吟到中华以外天。”[2] (P105)这位足遍东亚、北美、西欧、南洋的外交官的海外诗,为中国诗界开拓了一片新大陆,艺术地再现了海外世界之“新”,并且写出一个中国人走入近代世界后新的感受、新的认识和幻想。从他对《日本杂事诗》的修改可以看出,他不只着眼于奇景异态,开拓题材,更注重传播新的思想。③ 诚如康有为所说:“以其自有之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2] (P67)。
1891年他在伦敦自撰《人境庐诗草自序》[2] (P68),总结创作经验,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诗论开头再次申述了诗歌改革的艰难:
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
这段话和20多年前的《致周朗山函》意思相近。不过,可以看出一个微妙的变化:现在他虽然感慨“戛戛乎其难”,却不再认为“无能出其范围”了。换言之,诗歌改革诚然艰难,却并非不可能突破传统“拘牵”,创造出“新派诗”。因为他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篇《自序》标志他诗学基本观点已经形成,这就是“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诚然,这和他早年主张“有我”等观点有相承之处,前人诗论也有类似说法。但以此作为诗学核心观念,则是他独特的体会。所谓“诗外有事”,就创作论,可以理解为诗是外界事物、世事、人事的反映;就鉴赏论,又指诗可以具有比表面句意更深广的社会蕴含。所谓“诗中有人”,就创作而言,指诗歌应该抒写诗人的真实经历、内心感情;就鉴赏而言,则指诗可以使人观照到作者的思想倾向、人格个性。这两句话,涉及了诗歌理论中客体与主体、反映与表现、创作与鉴赏等诸多问题,已接近近代文艺观。可惜黄遵宪当时还缺乏近代理论意识,所以并没有展开。
不过,从诗歌变革的角度看,此文中最有价值的,还不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而是“今之世”和“今之人”。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创作方向:反映和表现今日时代和今人情思。
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何必与古人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乎为我之诗。
早年《致周朗山函》还说“诗固无古今”,而这篇《自序》则明确指出“今之世异于古”。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一种“近代”意识。“今之世”,就是“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也是“古学水风火,今学声气光”[2] (P120)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又处在“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2] (P123)的时世。因此,他谈到“述事”,强调的是“今日”官方和民间关注的国家大事、社会情状,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同时,《致周朗山函》中的“有我”,已经变为不同于“古之人”的“今之人”。所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是生活在“今之世”而且具有“今之人”意识的“我”。至此,黄遵宪基本明确了诗歌变革的主要方向:反映“今”之时世,表现“今”之人物。“新派诗”之“新”,就新在这个“今”字上。
再次,对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改革也做了多方面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一些设想。然而在这方面,仍明显表现出想挣脱“古人束缚”又难以挣脱的矛盾。
《人境庐诗草自序》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诗境”中除“述事”一项关系内容外,其他基本属于形式范围,可见他在这方面很费了一番心思。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艺术表现,在保持比兴、格律等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的前提下,注重以文为诗,即“复古人比兴之体”,又“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前人以文为诗,往往造成诗味减弱、破坏韵律,所以他把“比兴之体”和“古文之法”、“单行”和“排偶”结合起来。这样以文为诗,有利于扩大诗歌的表达和描写能力,有利于反映“今之世”复杂的事态和“今之人”广阔的视野,不失为古典诗歌适应近代社会的一种方式。但是黄遵宪所用的还是“古文家之法”,这个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只是古典格律诗范围内的一种变通。其二,诗歌语言,“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用语要“切于今”,是表现“今之世”、“今之人”的需要。然而语言素材仍只能从古籍中“采取而假借”。观其诗作,确很吻合,诚如钱仲联所说,“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9] (P162)。这个矛盾现象,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作过解释:“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其三,风格取范方面,“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即继承古典浪漫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博取众家之长以自铸风貌。从这几方面可以看出,虽然他旨在表现“异于古”的事和人,艺术上却还是只能基于古而扩展变化。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成熟和完美,使诗歌改革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极为艰难。“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确实是先行者深味个中甘苦之语。
需要指出,这篇自序虽然与其创作大体相符,但也存在实践已有更新创造而理论上尚未能总结出来的情况。例如《以莲桃菊杂供一瓶作歌》,就显出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化。古代诗歌中的艺术想象,主要借助神话传说和对自然变化的夸张。这首诗却是借助植物学、化学等科学新理展开想象。这种变化,黄遵宪自己还没能上升到理性。
1897年,他在《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正式张起“新派诗”旗帜。
1899年底,梁启超在总结黄遵宪探索“新派诗”、谭嗣同与夏曾佑尝试“新学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起“诗界革命”。在《夏威夷游记》中,他一方面肯定“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因为其诗能“以欧洲意境行之”;但同时指出黄诗的不足:“然新语句尚少。”而“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者,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但是这类诗“已渐成七字之语录”,“不备诗家之资格”。新派诗有新意境但少新语句,新学诗善用新语句但失去了诗的风韵格调,两者各有所不足,却恰成互补。于是他综合这两种方式之所长,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因此,可以说,没有黄遵宪此前30多年的艰苦探索,就没有“诗界革命”。黄遵宪确实“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先导人物”。
不过还不止此。诗界革命兴起后,黄遵宪立即成为诗界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参与者和重要的理论建设者。诗界革命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和探索精神,其诗论有更新的发展,虽所言不多,却从各个方面补充、发展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
其一,对诗歌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和改革方向,提出了更明确的新目标:
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2] (P440)
这是《明治名家诗选序》的进一步发展。他再次强调学习欧洲诗人。但《明治名家诗选序》只说欧洲诗人“为世所重”,却没能道出“为世所重”的原因。而这段话则明确指出:“左右世界之力”来自“鼓吹文明之笔”。实际上也道出了“新派诗”的基本特质:传播近代文明。
同时,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不但重视诗歌的社会内涵,也注意诗的艺术特性。晚年他概括自己论诗宗旨说:
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2] (P457)
他把古代“兴”的理论和近代自然科学“吸力”理论糅和起来,说明诗歌艺术功能的特性在于“感人”。尤其是拈出“移情”这一概念,虽出于“高山流水”的典故,却能与西方艺术论相通。而这方面,恰恰是梁启超诗论比较欠缺的。
其二,对诗界革命提出了更鲜明的要求,表明了更坚决的态度:
诗可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唯晋、宋以后,词人浅薄狭窄,失比兴之义,无兴观群怨之旨,均不足学。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2] (P1582)
“今人所见之理”就是民权、自由、国富、法治等近代观念。今人“所用之器”,就是近代科学技术创造的新事物。今人“所遭之时势”,就是列强凭凌、专制压迫、民智待开等现实。《人境庐诗草自序》还主张从“群经三史”“诸子之书”等等中“取材”,而这时他意识到,诗界革命的新诗,只能取材于这些新理、新物、新的现实。过去习用的语言,都无法表现这些新诗料,因此必须扫去一切陈陈相因之语。其基本观点仍是“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但在语言和内容上,都从兼取古籍转向弃古从今。
其三,更为突出的是,他在这一时期开始探索诗歌形式体制的改革。这是他此前还没有涉及,也是梁启超较少注意的,而又是诗歌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当时诗界革命参与者中,几乎只有黄遵宪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首先是改革古典诗歌形式体制的主要特征,即句式。1902年9月,他给梁启超的信中,先提出“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与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2] (P432)有些论者只注意他提到“弹词”“粤讴”,因此又主要肯定“他重视民间文学”,对其最重要的意义揭示不足。实际上,这一设想,是试图打破传统的五、七言格律体制。所以3个月后,他就致信梁启超,表示杂歌谣“非我所长”,“故不欲为”,而同时寄上《军歌》,恰恰就是“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并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虽然,愿公等拓充之,光大之。”[2] (P438)可见其设想意不在“歌谣”,而在句式。他还推测日本新体诗只是“于旧和歌更易其词理耳,未必创调也”。可以看出,他的“新体诗”不只要在“词理”即内容方面革新,而且要求“创调”即创造新的诗歌形式。新体诗比杂歌谣更进一步,不再借用民间歌谣,而是和近代音乐结合了。由这时开始,清末学堂乐歌和军队乐歌迅速发展,歌词日益通俗化。正是这种白话歌词,为五四白话新诗造成了氛围。
在提出改革句式的同时,他还有一句话,过去也注意不足:“弃史籍而采近事”。诗歌和“史籍”有什么关联?只有两种:一为咏史,黄遵宪显然不是对此而言;另一种,就是用典。我认为“弃史籍而采近事”,实际意思就是:“不用典”!
除改革格律、用典外,还有语言。黄遵宪早年萌芽的“今言”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他在《日本国志》中论证了言文合一的必然性,并提出了文体语言变革的两个基本要求:“适用于今”,即语言近代化;“通行于俗”,即文章语言社会化。这时尚未提到诗。1901年的《梅水诗传序》[2] (P287)则针对诗歌重申了《日本国志》中的观点:“语言者,文字之所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吾部洲文字,以中国最古。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或积世而变,或随地而变,而文字则亘古至今,一成而不易……语言与文字扞格不入,无怪乎通文字之难也。”他以丘逢甲所编嘉应州客家诗集《梅水诗传》证明“语言与文字合”就可“几于人人能为诗”,进而把这和“轰轰然以文化著于五洲如吾辈华夏之族,亦叹式微”联系起来,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行,种族之存亡,关系益大”联系起来,从时代要求、从中国近代化和文化复兴强调诗也应言文合一。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后来胡适“八不主义”中的几个要点,黄遵宪已经涉及了!可惜的是,他晚年的理论大都没有展开,而他本人,也在诗界革命兴起不久就去世了。
黄遵宪的诗论基本是他探索经验的总结和设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究。因此,其诗论的特殊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价值,而在于历史。它代表了古典诗学基本结束自我发展历程、现代诗学还没有诞生之间的一个阶段,反映了这个阶段中诗学努力挣脱传统的巨大引力场而仍受到“古风格”“拘牵”,新诗学观的因素在实践探索中生长的艰难历程。多数近代文学史,都把他放到后来20世纪初的“诗界革命”中评述,因而模糊了这一段诗歌逐步转型的轨迹。当然,他的探索直接影响了诗界革命,并在晚年以一些更新的设想丰富了诗界革命论。但黄遵宪主要是作为诗界革命先导人物而存在的。在戊戌变法前30多年中,在诗派争喧、诗人林立的诗坛上,艰难摸索和开拓中国诗歌近代化改革道路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
(本文原系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笔者作了删改。)
注释:
①《山歌》及《题记》为黄遵宪光绪十七年(1891)抄寄胡曦。但他自编《人境庐诗钞》,将《山歌》置于卷一同治七年《杂感》之后,同治九年《生女》之前,当系“少日”之作。
②《明治名家诗选序》,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七辑)据刊本,陈铮编《黄遵宪全集》据手稿,两者文字有所不同。本文此处引文依《人境庐杂文钞》。
③参见拙著《从〈日本杂事诗〉到〈日本国志〉》,《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标签:黄遵宪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教徒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读书论文; 杂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