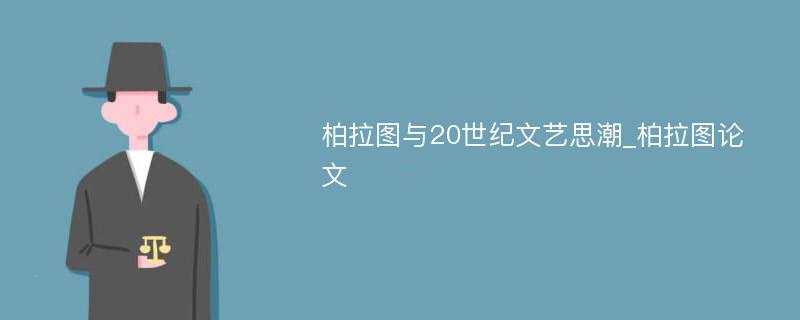
柏拉图与二十世纪文艺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思潮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柏拉图的复活
在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中,我以为有如下几篇(部)对20世纪思想影响深远:《会钦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巴门尼德篇》和《蒂迈欧篇》。柏拉图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见识,主要见诸于《蒂迈欧篇》,随着现代物理学的重大变革,其重大意义也已为人们所发现,怀特海把柏拉图与牛顿相提并论,认为这部著作与牛顿的Scholium一道,成为“统治西方思想的两种伟大的宇宙学文献”。当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堡和柏拉图学者弗利得兰德则把柏拉图提出的自然界的几何学视为当代量子论的先驱,弗利得兰德强调说:“如果认为德谟克利特是以伽俐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先驱,那么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在同样的意义上,也许可以把柏拉图看作是卢瑟福和玻尔的先驱。”[①]。
在人文科学领域,《巴门尼德篇》和《斐德若篇》与20世纪有着重要联系,但这两部著作是被现象学家和解构主义者在否定的意义上提及的,是在批判的意义上给以论述的。借助于《巴门尼德篇》和对巴门尼德的理解,海德格尔叙述了欧洲人的“在场形而上学”将“存在”的真理加以遗忘的故事。[②]《斐德若篇》则主要是在德里达著作中获得了反响,它被认为参予建构了欧洲“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受到非常激烈的批判。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哲学的边缘》等著述中多次提及《斐德若篇》,并对其进行拆析、解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中的对立系统进行颠覆、倒转,将其中诸如“文字”这样的下属概念进行涂抹和重新命名,赋予新含义。当德里达对《斐德若篇》中的文字起源说和功能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把胡塞尔、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卢梭、海德格尔等都划入《斐德若篇》所开启的传统中去了。20世纪对于柏拉图的批判的确非常广泛,除了以上的论述之外,《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隐喻、柏拉图著作中的视觉隐喻、所有的二项对立概念等,就像其文字起源传说一样,都受到了系统的批判。
但是,20世纪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许就是“重返柏拉图”。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理论总与柏拉图著作有关,它实际上还包括对于柏拉图著作进行理解并借鉴的重要方面。本文将从“苏格拉底对话体”、《会饮篇》和《理想国》在20世纪理论中的具体作用入手,审视20世纪理论对于柏拉图著作的复杂态度及一定程度上所作的借鉴。
二、“苏格拉底对话”体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强调并辨明柏拉图与巴赫金的理论联系:其一,对巴赫金产生了重要吸引力的柏拉图因素不是其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他赖以构建理念论哲学的艺术形式方面,这种艺术形式便是他的“对话”体裁,或称之为“苏格拉底对话”体。其二,在巴赫金看来,“苏格拉底对话”是欧洲艺术散文和小说史上狂欢体文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上的重要基础之一,由此我们认为,如果缺少了对“苏格拉底对话”体的研究,如果不指出复调小说乃是对于“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等狂欢体文学的“客观记忆”的结果,那么,复调小说理论则势必缺乏根基及历史渊源。
巴赫金所强调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的以下特征对于形成复调小说理论产生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对话”体现了苏格拉底关于“真理的对话本质”的见解。但后期柏拉图为了表现一种现成的思想,为了教育的目的,把苏格拉底变成了“导师”,让他附就于一种带有独自性质的表述格局。因此“苏格拉底对话”形式在柏拉图后期便解体了,这里巴赫金强调了柏拉图早期对话著作的重要性。(二)“对话”中对照法和引发法的使用。(三)“苏格拉底对话”的主人公都是思想家。巴赫金说,“‘苏格拉底对话’在欧洲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思想家式的主人公”。(四)“对话”中情节场景尤其是边沿场景的设置。如柏拉图在《赞扬篇》中设置了审判和苏格拉底等待宣布死刑的场景,苏格拉底在这种场景中的话语初步具备了“边沿上的对话”的特征。(五)“苏格拉底对话”塑造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的形象”。巴赫金认为,柏拉图让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对话关系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在对话中凑到了一起,已经非常接近了“死人的对话”。另外,巴赫金还认为,“苏格拉底对话”是一种狂欢化了的体裁,其基础便是狂欢式,对此他描述道:“柏拉图的某些对话,是按照狂欢节加冕脱冕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苏格拉底讽刺’是减弱了的狂欢节上的笑声”[③]。
从表面上看,巴赫金并没有在“苏格拉底对话”与复调小说之间一一作出类比,但若统观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全部,就会发现,上述特征已经融入他对于复调小说的分析之中。巴赫金对于复调小说的相应分析如下:(一)复调小说也把“对话”当作自身的创作原则,从而打破了由作者一人掌握固定真理、并采用独白表述格局传达这一真理的局面。巴赫金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按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原则,把惊险性、问题性、对话性、自白、生平录、说教等令人闻所未闻地组合起来(撮合),构筑了他的“巨型对话”,同时又在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在人物的自我意识内部,构筑了令人惊叹的“微型对话”,让艺术的真理、生存的真理在对话之中向外涌现(为真理接生),这样,在复调小说的内部,独白型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视觉便被否弃不用了。应该说,柏拉图的“对话”体从根本上在大的方面左右着复调小说的艺术思维。(二)复调小说也采用对照法和引发法。巴赫金通过作品的分析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使用对照法和引发法的巨匠。[④](三)复调小说中的每个重要人物也都是思想家。巴赫金认为,凡是走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视野中的人物,也都被迫变成了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⑤](四)“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场景,尤其是边沿场景,在复调小说中变成了根本性的普遍设置的场景。在这场景之中,生活中的一切都已被置之不顾了,于是发生了“边沿上的对话”。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边沿上的对话”是初步具有类似特征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成熟形态。(五)复调小说在更高的自由度上同样把“思想”当作一个独立的形象来塑造。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已经越出某人的大脑与另一人的思想发生了对话的交往,“拉斯科尔尼科夫孤身一人的意识,倒成了他人声音争斗的舞台”,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艺术发现使他成了伟大的思想艺术家”[⑥]。最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我们能看到整个狂欢体的典型成份:哄笑和悲剧、丑角、游艺场、假面人群”,还有更重要的,“狂欢式世界感受本身”[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狂欢化特点,据巴赫金看来,是以“苏格拉底对话”为历史源头的。
综上我们看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显然受到了柏拉图早、中期对话体著作的显著影响。巴赫金不是以拒斥的眼光来看待柏拉图的,他从柏拉图著作中抽引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特征,变成了自己复调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会饮篇》与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雅克·拉康是巴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他通过对弗洛伊德进行重新解释,在本世纪60年代的法国掀起了一场精神分析学的革命。据霍尔登介绍,在这一新的精神分析学的意识形态中,“拉康的Ecrits几乎变成了一部咖啡馆著作”[⑧]。这种盛行一时的精神分析文化是拉康著作的一种结果,他的天才使他能够采用所接触到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对弗洛伊德进行重新解释、借题发挥,拉康对于柏拉图《会饮篇》的改写或再写作(rewriting)就是其借题发挥的一个成功例子。
由于写作风格的特殊,拉康对于《会饮篇》的评论尽管很多,但都不太系统。在其著作集(Ecrits)、公开的讨论会和一些论文里,常常可以发现对于《会饮篇》或多或少的碎片式的评论。拉康之所以重视《会饮篇》,是因为《会饮篇》与精神分析学一样,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欲望理论,而如果能对《会饮篇》的欲望理论进行改写,那么对于拉康来说,就无异于在理论上走了一条捷径。
《会饮篇》的主题是“爱情颂”或“对于爱神的礼赞”,写悲剧家阿伽通因悲剧上演得奖邀请几位好友在家中会饮的事情,后来他们规定每个人都要对爱神颂扬一番以助兴,于是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欲望的理想主义话语,其中对拉康有着重要意义的是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两人的观点。他们二人均认识到“爱情或欲望起源于缺失,最终又趋向于寻求完整状态”。在苏格拉底那里,“缺失”(lack)是指一种“没有成为或者没有拥有(a failure-to-be or failure-to-have)”,而“趋向于寻求完整状态”则指源于缺失的欲望“以某种方式推动情人趋向于善”。其关于欲望源于缺失的观点,与拉康的欲望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拉康实质上又把苏格拉底的欲望理论从理论论的高处拖了下来,而且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写。
但相比之下,拉康似乎对阿里斯托芬的“背对背球形人神话”更感兴趣。按照这一神话,人类最初只有男人、女人和阴阳人三种,与现在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形体上“是一个园团,腰和背都是园的,每个人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园颈项上安着一个园头,头上有两副面孔,朝着前后相反的方向,可是形状完全一样,耳朵有四个,生殖器有一对,其它器官的数都依比例加倍”[⑨]。由于这种背对背园形人力量巨大,宙斯“象截青果做果脯和用头发截鸡蛋一样”,将他们全部一分为二,这样,对于由球形生物截开而成的人类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只是“一半”,他们总想与另一半重新合拢,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人类于是产生三种恋情:男性同性恋、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其中,异性恋是原阴阳人截开之后男女两半之间产生的恋情,也是现在较为常见的一种恋情。阿里斯托芬说,从此以后,“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医好从前截开的伤疼”。因之,爱情便被等同于一种希望恢复他所失去的整一态的期待,它起源于“整一体的缺失”,它要通过对于完整态的恢复来实现这种期待。从表面上看,这种神话和理论较之苏格拉底的更形象生动,但理论归宿实与后者基本一致,因为其中同样设定了男高于女、心灵高于肉体的二项对立图式。
拉康将上述理念论内核进行了删除,并且唯物主义地重写了阿里斯托芬的神话,“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依靠一个神话本身来说明人类曾经有过那样一种整一状态,这是不可信的,再者,从爱情的本身来考虑假若真曾有过那么一种整一态的话,那么,现在的每一种爱情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对于原始状态的替补,而肯定不是一种对于遗失了的整一状态的恢复”[⑩]。拉康沿用了阿里斯托芬的遗失(loss)和缺失(lack)的概念。“遗失”表示一个人在最初时失去了某物这一事件,而“缺失”则表示一个人在其关键性的遗失某物之后的匮乏状态,它们都是欲望产生的原因。对于阿里斯托芬来说,遗失的东西只是那种过去作为园形人存在的完整状态,对此,拉康在《演讲集》(Le Séminaire)中写道:“阿里斯托芬的神话通过一种生动的、但又是欺骗的方式揭示出:正是另一个人,他的性的一半,才是人在爱中所寻求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找完整态的意象,但这只是一种关于神秘之爱的神话描述。我们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入手,应当把主体的寻求对象界定为属于他自身的那部分,而不是性的完整态。本属于他自身的那部分将永远地失去了,因为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性的生物,而且不再是不朽的”。[(11)]既然人类的爱情源于他的失缺,那么他究竟失去了什么呢?拉康将这个失去之物称为“客体a”(意为“遗失的或不在场的客体”),在其Le Séminaire中,他继续写道:“可列举的客体a的各种形式,应当以乳房为代表或对等物,它表示本属于他自身的那一部分在个体出生时就失去了,并且能够使那些意义最深远的遗失了的客体象征化”[(12)]。拉康将需要和欲望作了区分,幼儿的需要可以满足,但是欲望却不可满足,因为他的欲望客体永远遗失了,这样,母亲只有通过喂奶把幼儿的欲望当作特殊的需要来满足,而乳房则只能作为“客体a”的一种象征而发挥作用。这种欲望的一般性和需要的特殊性的冲突,这种需要的临时满足和爱的一般要求之间的差数或分裂现象构成了拉康“欲望的辩证法”的重要内容,用“客体a”取代阿里斯托芬的“完整态”的意义即在此处。
在《无意识的位置》(Position de l'inconscient)中,拉康整理了阿里斯托芬的关于背对背园形人与鸡蛋之间的类比(宙斯就象用头发截鸡蛋一样把前者截开),并通过“鸡蛋”与子宫内的胎儿和煎蛋卷之间的联想,对于主体确立之前的“缺失”进行了既是充满诗意的又是科学的解释:“为了占有《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领地,让我们想一想他的原始的背对背园形物,它的两半结合得紧紧的,就象一个马德堡球体;后来它被宙斯切为两半,成为我们求爱时的这个样子,成为一种寻求那不可寻求到的完整态的存在。当我们想到这种球状的原初人及其分割的时候,我们想到了阿里斯托芬用的一个比喻——鸡蛋,……我们可以想想子宫内的卵子(egg),它还不需要一个外壳。我们再想想每一次卵细胞膜破裂时,一部分卵细胞受了损伤,在受精的卵细胞膜产生之后,婴儿带着他的胎衣出生。据专家们分析,随着脐带的切断,新生儿失去的不是他母亲,而是他的解剖学的完整态。婴儿出生后,助产士叫做接生婆。卵细胞的分裂创造了人(l'homme),但是也创造了l'hommelette”。[(13)]在这里,拉康通过联想对阿里斯托芬的神话进行了科学修改,使卵子与鸡蛋、卵子破裂或脐带切断与宙斯对背对背园形人的分割、解剖学完整态与原始完整态、医生的手术刀与宙斯的刀具、助产士或接生婆与真理的接生婆苏格拉底之间在联想层上构成对应关系。拉康认为新生儿失去的不是他母亲,同时不强调母亲与幼儿的性联系,这与阿里斯托芬强调性爱因素不同,同时也与弗洛伊德强调母亲在婴儿性欲中的重要作用不同。拉康强调幼儿失去的是属于自身的份额(它被标示为客体a),并把母亲划入到他者域(Other)中去,以充当他者的代表和第一位他者,而另一方面则把乳房当作“客体a”的一种象征来看。这样又触及到拉康以欲望理论为基础的主体理论,而且“主体的破灭”本身又构成了拉康“欲望辩证法”的另一重要内容。这里拉康通过考察主体与他者、主体与能指的关系,揭示了主体匮乏的真理:在无力支配他者,以及在能指的效应之下,主体欲望的客体因遗失了。于是主体的结构带来的缺失,加上他在出生时带来的缺失,使得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使其欲望的实现遥遥无期。拉康说:“这里有两种缺失交迭起来了。一种缺失来自于根本性的不足,主体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达于自身存在的辩证法就是围绕着这种不足而运转的。即是说,这种缺失来自于这个事实,即主体依赖于能指,而能指却首先出自他者域中。这种缺失终于再度巩固了另一种缺失,这另一种缺失是先在的,真实的缺失,它是人在性繁殖的过程中、在降生的时候已经设置下的”[(14)]。
从总体上看,拉康与《会饮篇》的联系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拉康沿用了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的“遗失”和“缺失”的概念,并在欲望源于缺失这一基本点上取得了共识。其次,拉康通过对于阿里斯托芬神话的再写作,以“客体a”概念为中心,建立了科学的欲望起源说。第三,拉康在阐述两种缺失理论的时候,引入了导致主体第二次缺失的他者概念,从而使欲望起源说冲出了《会饮篇》的理念论话语所设置的禁闭。以上表明,拉康对柏拉图著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与柏拉图之间所形成的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批判性的关系,因为这里面同时包含着拉康对于柏拉图的很重的依赖成份。拉康的写作方式决定了他不会对柏拉图进行正面的和单纯的攻击,他对柏拉图哲学的核心采取一种避而不谈的现象学态度,在这一前提下,他对柏拉图本文的空缺处或隐喻部位进行了阅读和再写作,并在其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路易·阿尔都塞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拉康“对于哲学所提供的安全的求助常常带有二律背反的性质”[(15)],这和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
四、《理想国》与热奈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
在结构主义阵营中,另有叙事话语理论的代表热拉尔·热奈特继承并翻新了柏拉图的叙事思想。热奈特的这一理论导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极力推重“叙述”的地位;第二,在理论上标举“摹仿说”的谬误。
柏拉图的“叙事”观点主要见于《理想国》第三章,热奈特曾在几个地方提醒我们注意,并对之作了阐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把文学作品分为纯叙事(diégésis)、纯摹仿(mimésis)和叙事摹仿兼用(如史诗)三类[(16)]。热奈特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个分类,并且转述了柏拉图关于叙事和摹仿的定义。柏拉图说,诗人“以自己的名义讲话,而不想使我们相信讲话的不是他”,这叫做纯叙事;而如果情况正相反,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在说话的错觉,并引入当事人自己出来说话,这便是纯摹仿。为了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差别,柏拉图把荷马用纯摹仿(戏剧体的直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克律塞斯与阿凯亚人之间的直接对话的戏,改写成了以叙事者为媒介的叙事,人物的对白变成了间接引语。热奈特认为,柏拉图的“纯叙事”与“纯摹仿”“唯一拿得出来的对等词是叙事/对话(叙述方式/戏剧方式)”,柏拉图的“摹仿”实际上指“对话”[(17)]。
在柏拉图看来,叙事和摹仿是有轻重之别与高低之分的。他极力推崇叙事,贬低摹仿。柏拉图认为,性格愈卑劣的人越喜用摹仿,而越喜用摹仿的人或诗人则愈卑劣,是故柏拉图严禁摹仿的诗人、尤其是戏剧诗人进入他所构想的理想国,而只接受那些朴实无华的不事摹仿而专叙事的理想诗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分类作了改变,热奈特写道:“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是非常不同的,因为这种分类把所有的诗歌都纳入摹仿,而只区分了两种摹仿模式,即直接摹仿(柏拉图称之为严格摹仿)和叙事摹仿(他和柏拉图一样称之为diégésis)”[(18)]。亚里士多德取消了柏拉图的关于摹仿和叙事的混合体这一类别,并把史诗这样的类别归入叙事摹仿一类。他认为,史诗中采用对话体的摹仿部分无论篇幅大小,都改变不了“史诗在本质上的叙事性”[(19)]。总的来说,柏拉图推崇叙事,贬低摹仿,并使二者相对立,亚里士多德则推崇摹仿,贬低叙事,并把二者统一于摹仿。按照这一逻辑,柏拉图认为酒神颂歌高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又高于悲剧,而亚里士多德却反其道而行,把悲剧置于史诗或其它一切体裁之上,他只“赞扬荷马作品中的一切与戏剧类似的特点”,即赞扬纯摹仿的部分。[(20)]
在对叙事的态度方面,热奈特是按照柏拉图的路子走的。但是,两千年来,欧洲人对于叙述的轻视以及对于纯摹仿(或者戏剧)的推崇的倾向却是来自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对此,热奈特写道:“柏拉图对纯叙述的辩护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反其道而行之,很快以人所共知的权威成功地支持了纯摹仿的优越地位”[(21)]。不仅“整个古典传统都抬高悲剧,把它奉为最高的艺术形式”,而且,戏剧模式、戏剧念白或纯摹仿还严重制约了叙述体裁的发展。比如,热奈特说,“用‘场景’一词来指小说叙述的基本形式便是极好的说明”。他认为,“直到十九世纪末,小说场景仍相当可悲地作为戏剧场景的平庸仿效来构思:这是二度摹仿,即对摹仿的摹仿”。[(22)]可见,热奈特对叙事采取的是柏拉图的态度,并沿用了柏拉图式的词汇。
20世纪文艺思想的主潮是反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的,而热奈特也加入了颠覆“摹仿说”的行列。但是,也有一些被热奈特称之为“新亚里士多德派”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实际上还在沿用《诗学》里的教条。热奈特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柏拉图的老问题,即纯叙事和纯摹仿的对立在英美的小说理论中,以亨利·詹姆斯及其弟子们几乎原封不动使用的讲述(telling)和展示(showing)的对立形式重新出现,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宗文艺理论的中心环节。亨利·詹姆斯等人以“展示法”对于小说写作的要求,实际上相当于重新标榜了摹仿说,这种写作倾向和理论的立足点受到了热奈特的批评。热奈特说,“展示这个概念与摹仿或叙事表现的概念一样是虚幻的:与戏剧的表现相反,任何叙事都不能‘展示’或‘摹仿’它讲的故事,而只能以详尽、准确、‘生动’的方式讲述它,并因此程度不同地造成摹仿错觉,这是唯一的叙述摹仿,理由只有一个,而且很充分:口头或书面叙述是一种言语行为,而言语则意味着不摹仿”。[(23)]热奈特把摹仿看成幻觉或错觉非常类同于柏拉图的摹仿是影子的说法,但与亚里士多德的“逼真”说截然不同。在《新叙事话语》里,热奈特重申他对摹仿或“展示”说的批判态度,他说道:“对语式距离的研究主要批评了完美摹仿(即mimesis)的古老概念,尤其是它的现代同义词展示的概念”[(24)]。
我认为,热拉尔·热奈特与柏拉图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遥远的同谋关系,但如果进一步看,则他实际上是以一个为柏拉图所未曾见识过的结构主义面孔出现在柏拉图面前的,这势必还要带来二者的交锋与歧异。当然,对于这一歧异,热奈特对柏拉图也进行了批判,例如,他指出无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多少不同,但在下面这一重要问题上观点仍是一致的,即“对于柏拉图正如对于亚里士多德一样,叙事是一种淡化和弱化了的文学表现模式,——暂时还很难发现有谁能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25)]或许热奈特以及其它结构主义者,与柏拉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完全把作品当成不再指物叙事的语言或文本,而柏拉图则出于治国的目的和道德方面的需要,过多强调了文艺的表现功能。
五、对抗还是同谋:舆论
罗素曾说,柏拉图对近代以前欧洲思想的影响,比起亚里士多德来要大得多[(26)]。同样,在20世纪,人们对于柏拉图哲学的注意也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主要表现在:其一,尼采以来的现代思想在对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首先提及的是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柏拉图主义的产儿;其二,就20世纪思想与柏拉图所形成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谋关系而言,柏拉图对于20世纪的影响更非亚里士多德所能比。本文仅从几个有限的方面论述了柏拉图与本世纪文艺思想的复杂关系。
但是,现代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批判本身也值得推敲。比如,尼采曾经声称他反对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海德格尔还说尼采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也决心克服形而上学,但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也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所以,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罗蒂耐人寻味地说,尽管“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对德里达的实用主义评论者如我本人,都在竞争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反柏拉图主义者的地位”,但这只是一个“多少有些可笑的企图”[(27)],以致于反柏拉图者反被柏拉图哲学所擒获,变成了柏拉图哲学的解说者和传人。这真是应验了怀特海说过的一句话:“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28)]。
注释:
① (28) 王宏文、宗洁人《柏拉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应、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87—188、197、131、132—133、226页。
⑧ Peregrine Horden,"Thoughts of Freud",in Freud and the Humanities,ed.,by Peregrine Horden,Gerald Duckworth & Co.Ltd,London,1985,p.7.
⑨ (16)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38-240、50页。
⑩ (11) (13) (13) (14) John Brenkman,"The Other and the One:Psychoanalysis,Reading,the Symposium",in Literature & Psychoanalysis,ed.,by Shoshana Felma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yty Press,1982,p.411、、p.419、p.419、p.420、p.422.
(15) Louis Althusser,"Freud and Lacan",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203.
(17) (21) (22) (23) (2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116—117、117、109、216页。
(18) (19) (20) (25) Gérard Genette,"Frontiers of Narrative",in Ut Figura Poiesis:The work of Gérard Genet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29、p.129、p.130、p.130.
(2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3页。
(27) 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389页。
标签:柏拉图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巴赫金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理想国论文; 阿里斯托芬论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会饮篇论文; 巴门尼德篇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