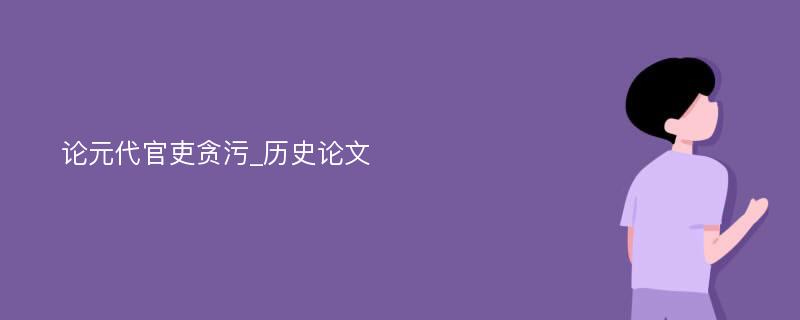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吏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5-0032-10
官吏贪赃,是古代政坛的宿弊之一。元代官吏贪赃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曾经从多方面探寻元帝国百年而亡的奥秘。笔者认为,在造成元帝国百年而亡的诸多因素中,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
元代官吏贪赃有哪些异乎寻常的表现?元朝统治者的惩治贪污政策有何特色?为什么官吏贪赃这一古代政坛宿弊,会在元代得到恶性发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1][2][3][4][5][6]的基础上就这几个问题试作如下探讨。
一
元代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7](卷—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肆虐始终,一批宰相也卷入贪赃浪潮。
有元一代,官场道德风气的败坏,备受注目。早在世祖朝前期,监察御史王恽已有过“仕途之间,廉耻道丧,赃滥公行”的说法。吴澄也指出:“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官经断罚事状》)[7](卷一四《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以上议论并非危言耸听,成宗初“京师犯赃罪”的官吏,就有300人,占当时“在京食禄者万人”的3%,大德七年(1335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黜的赃污官吏又多达18473人[9](p.383,P.388,p.456)。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元代官吏贪赃的确是流为风气和泛滥成灾了。
中央官吏的贪赃丑闻,络绎不绝。史称:“桑哥当国四年,诸臣多以贿进。”[9](p.347)前述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其中大部分当是中央省院台部寺监的官吏。可见,世祖朝中央官吏掌权者、晋升者行贿受贿大有人在。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札鲁忽赤脱而速受赂,为其奴所告,毒杀其奴,坐弃市”[9](p.410)。此为执法官员受贿而杀人灭口。武宗初,刑部尚书乌刺沙因贪赃受御史鞫问,英宗朝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相继因贪赃被杖免[9](p.501,P.625,p.627),也属于执法官员贪赃。它如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良“坐赃免”,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工部尚书苏炳因“贪邪”被御史台劾罢[9](p.672,p781),又是中央高级官员贪赃的较突出事例。中央官员贪赃一方面是侵欺官钱,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及其他下级官吏的贿赂。他们与平民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算多,并不意味着受贿贪赃机会和数额会少一些。相反,由于大权在握,他们比起地方官吏更容易因贪污受贿而积累巨额财富。
地方官吏贪赃因“天高皇帝远”的特殊条件,更是肆无忌惮,各显神通。如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因受财三万余锭,平章的里不花盗钞三十万锭,被纠弹;英宗初,江浙行省平章伯颜察儿、江西行省白撒都“并坐贪墨免官”[9](p427,p.609)。此为行省官员贪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真定路总管张宏“乘变盗用官物”被罢职;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因“奸赃”被按察司举劾;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福建宣慰副使哈只“贪污狼藉”被罢黜[9](p.774,p.105,p.197)。此为宣慰司和路府官员贪赃。据说,到松江府做官的“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阘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还流传着“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的诗谶,暗示松江府已成贪滥肮脏之地[10](卷三○,《诗谶》)(注:谷水和云间,均是松江府的别名。)。
地方官员因贪赃而骤成巨富者,为数不少。“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勤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11](卷六七,郑介夫《太平策》)。尹廷高《车中作古乐府》诗曰:“铃丁当,铃丁当,大车小车摆作行。问渠捆载有何物?云是官满非经商。蟠螭金函五色毯,钿螺椅子象牙床……人生富贵归故乡”[12](卷下)。这些财富“非取于民,何从而得?”至于获取手段,不是别的,正是官职和权力。《元曲》中常见的贪官“定场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13](第一卷,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第二折,p.276)就颇能说明官员职权在其贪赃暴虐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元朝灭亡南宋后,大量派遣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到江南去做官。这些人成分低俗冗杂,“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多数以征服者、占领者自诩,带着争相掠夺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欲望,“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对所辖编民毫无恻隐怜爱,并缘侵渔,豪横吞噬,无所不至[14](卷一○,《奏议存稿·通南北之选》)[15](卷二三,《民间疾苦状》[8](卷九二《特选行省官事状》)[7](卷三六,《故逸士游君建权墓表》)。元代官吏贪赃在江南地区最为猖獗,或许与这个背景大有关系。
另外,元代各级衙门中诸多吏员,其贪赃往往较长官正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视贿赂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祸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16](卷六,《送陈子嘉序》)。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已作详尽考察,这里恕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王朝的官员贪赃,大抵是在开国百十年后才较多出现的。元代则不然。不仅官员贪赃大量出现较早,肆虐始终,而且往往是以明火执仗的勒索出现,不予掩饰,不知廉耻。
《黑鞑事略》云:“见其物则欲,谓之撒花。”[17]汪元量《醉歌》诗曰:“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18](卷—)撒花,原意为赠物、礼品,后转意为强夺于人的财物。关于蒙古贵族官僚“撒花”与元官僚贪赃的联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初六的诏书说:“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吏,视此为例。”[l9](卷二,《圣政·止贡献·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诏书》)官吏受贿贪赃,虽然是汉地传统王朝官僚系统内违法蠹政的弊端,但在蒙古国官僚机构简单,“无俸禄以养廉”等条件下,与贪赃贿赂大体相同的“撒花”,又是贵族那颜经济收入的合理合法的重要来源。诏书中“纵贿赂而为蠹”,即谓此。元代官吏受贿贪赃最初即与蒙古国那颜取财于部属的“撒花”旧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王朝建立不久,忽必烈根据陆续设置和健全的汉地式官僚制法则,颁布上述诏书,以官吏俸禄取代和废止了旧有的“撒花”。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作为统治民族蒙古贵族的“撤花”旧俗,很难用一纸诏书立即予以彻底废除。它又融入汉地王朝官僚贪赃流弊,而以不合朝廷正规法制却又多少符合蒙古草原帝国旧俗的混合形态,顽强地存续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元代官吏贪赃明火执仗的勒索方式的由来。
在元代官吏贪赃习气的成长和膨胀过程中,一些色目贵族官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都拉合曼以扑买聚敛,乘机中饱私囊,开其先河。“唯事贿赂”的燕京断事官牙剌瓦赤和世祖初“盗国财物”的西域人,又“蹑迹而纂其后”[20](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色目权臣阿合马贪污受贿,再次领官场风气之先,“江南内外宝物,俱半匿聚其家”[21](《大义略叙》,P.178)。桑哥“继踵用事……居官为吏者,惟知贿赂关节,可以进身”[22](卷七,《奉使宣抚回奏疏》)。成宗朝,西京道宣慰使法忽鲁丁借运输军粮“侵匿官钱十三万余锭”,又鬻瑟瑟二千斤于宫廷,牟取暴利[9](P.453,p.454)。元末叶子奇云:“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此言或带有某些种族偏见,但也并非无根之说。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理财聚敛而贪赃的行径,的确与汉地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观念,相去甚远。
时至元末,形形色色的官吏贪赃,得到恶性发展。“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别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23](卷四下《杂俎篇》)。包括皇帝所遣宣布谕旨的使臣,也频繁向地方官“求贿”[9](p.3432)。于此,和历代王朝稍异的元代官吏贪赃方式及习气,与元帝国的腐朽败落同步,发展到顶点。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一批中书省宰相也卷入了官吏贪赃的浪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世祖朝阿合马和桑哥“奸赃暴著非一”[9](p.4576),已如前述。仁宗朝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毺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自福贿金一百五十两”。顺帝朝太师右丞相伯颜大肆聚敛,“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9](p.4579)[24]。它如英宗朝中书平章塔失海牙,文宗朝中书平章朵儿只、速速、均因贪墨劣迹被杖免和流窜[9](p.613,p.752,p.766)。更有甚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十一名正、副宰相中,就有右丞相完泽、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八人,因受朱清、张瑄贿赂而受劾或罢职。另有参政哈剌蛮子被罢黜,估计也与此受贿案有关系[9](P.448,P.450)。粗略计算,贪赃宰相占当时宰相班子人员总数的82%。秦汉以来,宰相贪赃间或有之,但数量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宰相权势颇重,又容易受皇帝猜疑和其他官员嫉恨。尤其是西汉尚书台多员宰相体制形成后,不乏正、副宰相内部相互监督牵制。故多数宰相常在关乎风化名节的贪赃事上不能不有所顾忌。元代却异乎寻常地冒出宰相班子内大多数受贿贪赃的恶性事件,的确发人深省。除了选相不精及朋党等因素,似乎还有更深的社会背景有待探寻。
二
针对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元朝统治者陆续制订并实施了一整套惩治贪赃的政策。即完备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官、奉使宣抚监治的双管齐下。遗憾的是,赃罪条例成效欠佳,监察、奉使屡治不止。这套惩贪政策基本上失败了。
最初的赃罪条例,是在世祖朝桑哥被诛后出台的。《元史·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丁未条云:“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人死者以闻。制曰:‘可”’。这就是有名的“赃罪十三等”。此赃罪条例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见到。仅在《元典章》大德七年以后的某些公文中略见其梗概。在世祖末和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的十余年间,它一直是元朝廷惩办官吏贪污的法律依据。如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帝命事无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决之”[9](p.388)。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成宗又正式颁布“官吏受赇条格,凡十有三等”[9](p.404)。此次颁布,显然意味着“赃罪十三等”的正规化、条格化及其全面推行于全国各地。
或许是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八名正、副宰相受贿事件,给元廷造成了颇大的震动。当年三月,在惟一没有卷入受贿丑闻的左丞相哈剌哈孙的主持下,又颁布了“官吏赃罪十二章”[9](p.449)[20](卷二五,《丞相顺德中献王碑》)。关于此次新颁布的“官吏赃罪十二章”,《元典章》留下了较完整的记载:
大德七年三月十六日,钦奉圣旨:……以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互有轻重,特敕中书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所定条格开列于后:
诸职官及出身人等,今后因事受财,依条断罪。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官,须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官,减一等。以至元钞为则。
枉法:
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
一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七十七下;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
二百贯之上,一百七下;
不枉法:
一贯至二十贯,四十七,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注边远一任;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降一等;
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降二等;
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降三等;
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降四等;
三百贯以上,一百七,除名不叙。[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
以上条例,也被收入《大元通制》和《元史·刑法志·职制上》,故是大德七年以后较为稳定和正规的赃罪条例。此条例,是中书省、御史台等奉成宗敕令“集议”修正“近年所定赃罪条例”而来的。所谓“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不是别的,正是前述至元二十九年拟定、元贞二年正式颁降的“赃罪十三等”。可以说世祖末所定“赃罪十三等”,是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的蓝本。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又是在世祖末“赃罪十三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处罚条例数看,“十三等”含“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十二章”则仅有枉法五章和不枉法七章。显然,不枉法条例减少了一章。前揭成宗圣旨还称,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互有轻重”,不尽恰当。那么,经过中书集议修订成的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整?它与“赃罪十三等”相比,在赃罪处罚上是加重,抑或减轻了呢?请看残留在现存元代公文中的“赃罪十三等”片断:“……依十三等不枉法例,笞决三十七下,解任,殿三年,别行求仕”。“……照依十三等不枉法例,一百贯以下,期年之后,注边远一任叙用”[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官典取受羊酒解任求仕》、《司吏犯赃经格告叙》)。
两相对照,在不枉法笞决三十七下等条上,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明显加重。唯不枉法一百贯条,稍有减轻。但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犯赃或致死罪的规定,大德七年已不复存在。总的来说,经修订的“十二章”处罚程度,较前加重减轻兼而有之。从一般处罚看,加重的稍多。而取消死罪,又是减轻处罚的表现。大德七年奉使宣抚罢黜赃官18000余人,却未见一人被杀,也反映了后一种变化。
元廷还对赃罪处罚的某些细节,作了补充性规定。如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御史台官员又奏请批准:官吏受贿,初已有伏罪之辞,而后审复,有司徇情致使翻异伏罪之辞的,要加等论罪。十月,又规定:职官坐赃,已经断罪后再犯者,加本罪三等。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御史台官员奏请皇帝批准:“官吏犯赃及盗官钱,事觉避罪逃匿者,宜同狱成”。即使经赦免而不治罪,也要降黜其官职[9](p.406,p.433)。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曾就枉法、不枉法的界定,赃物没官或给主等,加以详细的阐释[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此外,对受赃自首,家属受赃,吏员受赃,监察官受赃等,也作了一系列惩罚规定[9](p.2613)。一系列补充规定的面世,使元廷惩办官吏贪赃的法网更为严密了。
对官吏侵盗和侵用官钱者,元廷的惩办也格外严厉。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元贞元年(1295年)两项条例,均保留了钱谷官、仓库官监守自盗,重者处死的严酷处罚[19](卷四七,《刑部九·侵盗,仓官侵粮飞钞、《侵盗钱粮罪例》)。对挪用官府钱粮,也不惜以刑罚严格禁止:“诸职官侵用官钱者,以枉法论,虽会赦,仍除名不叙。”[9](P.2613)[19](卷四七,《刑部九·诸赃·侵使》)
上述赃罪条例,虽然颇为系统详密,但在实施中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第一,犯赃改注边远。“赃罪十二章”中,有“不枉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下,注边远一任”条。实际上,犯赃官员改注边远地区的做法,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已经开始推行[19](卷八,《史部二·选格》、《犯赃官员除授》)。时至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仍有“广海,古流放之地”,“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9](p.681)。此举虽然能够客观上暂时解决广海官员多缺的难题,对所注赃官也不乏惩戒寓意,但其负面效应又比较严重的。这些因犯赃改注边远地区的官员,其责任依旧是“宣明教化,礼义兴行”。然而,“彼身经断罚,处民之上,岂惟内怀惭德,先不自安,部内之民,将何化服?”王恽认为:“固非惩恶劝善之道,似不足取”[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经断罚事状》)。改注边远地区的政策,还进而形成了内地与边远官员之间的铨注壁垒,即仕于广海等边地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中州江淮吏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这批官员自暴自弃,继续肆虐于边地,致使“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堕而民益偷。甚则疾视其上,构结徼外蛮夷,凭陵郡县,贼杀长吏之祸成矣”。犯赃官员不仅不能幡然图新,反而助长了边远地区吏治的恶化。王恽和朱思本不约而同地抨击“见行降远格例”,指出它是“亡金弊法”,建议效法唐代“数年停勒之法”和赵宋“远近适均”之制[25](卷—,《广海选论》),是有道理的。
第二,惩贪措施,相对宽大。无论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抑或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比起唐、宋律令中“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之类的规定[26](卷一一)[27](卷一一,《枉法赃不枉法赃》),由六条增加到十二、三条,条例内容更为具体化了。但它取消了枉法重罪“绞”刑和不枉法重罪“役流”,最轻的杖数尚不及唐宋律的一半。若与明初“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和“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28](卷九三,《刑法志一》)[29](卷三三,《重惩贪吏》)相比,就显得宽疏多了。罪罚条例详细严密而相对宽大,也是元朝廷惩治贪赃措施的一个特色。
惩治贪赃措施的相对宽大,对制止贪赃的效用多半是负面的。元人郑介夫上疏说:“又见各处州县官不顾名节,纵意侵渔,大小民讼,商贾纳贿。不幸有因小赃告发,虽行定罪停罢,今在闲居,已成巨室。纵不再仕,亦可了终身之计也。似此之类,何可胜数?”[16](卷六七,《大德七年郑介夫妻》)[14](卷一○,《置贪赃籍》)。贪赃罪罚,在一定数量的杖责以外,只有除名和殿叙。这比起借贪赃而成“巨室”,了却“终身之计”的收益来,的确是判若云泥,悬殊很大。以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乃至死刑等方式,严惩贪赃,才能使贪赃者权衡利弊,有所畏惧,才能杜绝贪官不思悔改、蒙混过关和视贪赃为利薮的恶习。况且,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又是元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惩办犯罪官吏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者对郑介夫等有识之士的提议置若罔闻,始终未能改变其相对宽大的惩贪措施。
惩贪政策的失败,还表现为监察奉使,屡治不止。元代监察机构分为御史台、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三部分。御史台的32名监察御史,江南、陕西二行台48名监察御史,以及分隶三台的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均负责朝廷内外百官贪赃枉法的监察。台察官的监察活动,包括纠劾、刷卷、按问等内容。前面列举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贪赃案件,大多数也是由台察官检举揭露的。台察官的上述监察活动,虽然在遏制和减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元代台察官及其监察职能经常受到较大干扰,最终也给元廷惩治贪赃带来了消极影响。首先,台察官不断遭受阿合马、卢世荣、铁木迭儿、脱脱等权臣的压制、打击,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难以正常和有效地纠劾官吏贪赃[30]。其次,台察官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其全部监察活动必须在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由于怯薛等蒙古旧制的影响,台察官并非蒙古皇帝最信任、最亲近的臣属。许多情况下,皇帝不仅没有履行“朕当尔主”的许诺[9](p.118),反而会对监察官的举劾横加指责。如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御史台臣劾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曰:“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9](p.455)。皇帝把“朕所信任”当作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以此对台察官纠劾作出最高裁决。这种情况下的监察活动岂不是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吗?程钜夫所言:台察官“以征赃为急务,于按劾则具文”[14](卷一○,《置贪赃籍》),或许就是其按劾职能得不到朝廷支持的消极后果。再次,由于官场贪墨风气的濡染,不少监察官吏也利欲熏令,知法犯法,不顾台察官犯赃“加等断罪,虽不枉法,亦除名”的条例[9](P.2618),率先贪赃。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南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监察御史何守谦坐赃杖免”[9](P.427,p.621)。更有甚者,元末还出现了“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23](卷四下,《杂俎篇》)。台察官自身都陷入了贪赃泥潭,又如何能依法惩治一般赃官呢?
成宗朝开始,奉使宣抚也成为惩治地方官吏贪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奉使宣抚以“按问官吏不法”和“询民疾苦”为宗旨,由朝廷选派高级官员充钦差,佩二品印,巡行各道,对包括行省、廉访司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进行督责和惩治。元代共举行此类奉使宣抚六次,奉使宣抚“得专决,不惮大吏”,对五品以下官吏可全权处置,四品至五品,也有权停止其职务,审查其罪过,奏报朝廷发落[9](p.659)[31](卷一三,《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其权力明显超过御史台监察官。奉使宣抚作为蒙古汗廷使者旧制和汉唐金钦差巡行影响的混合产物,在元中后期惩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奉使宣抚同样不可能是医治元代贪赃等官场弊病的灵丹妙药。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贪赃成风的严重干扰。早在大德七年那场最成功的奉使宣抚中,就曾经发生江西福建道奉使官塔不带“坐赃”被罚,“终身不叙”的案件[9](p.468)。顺帝至正五年,政治和社会危机严峻,积重难返,“奉使者脂韦贪浊,多非其人”。主持者元顺帝乖戾多变,不能对奉使宣抚全过程进行明智而有力的控驭。所以,此次奉使宣抚基本以大贪官督责小贪官,“欺诈百端”,“政绩昭著者十不一二”的失败结局而告终。民间怨谣:“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10](卷—九《阑驾上书》)就是对元后期奉使宣抚的讥讽和鞭笞。
三
在考察过元代官吏贪赃异乎寻常的表现和惩贪政策的失败以后,人们自然希望进一步探寻元代官吏贪赃恶性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
元代官吏贪赃和惩贪政策,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条件下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除了汉地传统王朝造成官吏贪赃的共通原因外,还具有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面,我们从俸薄,选举不精,徇私曲赦,蒙古贵族旧制的渗透等方面,试作若干分析。
首先谈俸禄微薄。由于俸禄支付纸钞和官员冗滥,元代俸禄微薄甚为突出。据大岛立子教授的研究,月俸18贯和职田4顷的中县达鲁花赤和县尹的实际经济收入,只相当于腹里中等百姓的生活水平[32]。尤其是元后期“物日以重,币日以轻,而制禄如其旧”[7](卷一七,《赠张嘉符序》),俸禄微薄更为严重。
关于薄俸的危害及其对官吏贪赃的影响,世祖朝胡祇遹说:“近日,颁降条画,职事官、钱谷官犯赃者或杖死。诚为善政。然以月俸计之,府吏月俸六贯,年来米麦价直每石不下一十贯,日得二百文,可籴二升,仅充匹夫一日之食。衣服鞍马奴仆之费,必不可缺者,何从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蓄……况兼钱谷官无升斗之禄,无进身之阶。凡有失陷亏欠,则勒令合偿。职事官,则六品而下,不过二十贯,一身之费,亦不赡给。傥过官府勾唤,送往迎来,杯酒饮饭,必不能免者,又何从而出?饥寒切于身,勤劳苦其心,父母妻子,冻饿于其前,公私费用,逼迫于其后。身既从事,不敢朝夕去职,别营生业。今蒙禁止曰:勿取于民,勿枉法,勿妄求,勿盗窃官钱。虽饭蔬饮水,清苦廉介之士,亦不能堪,岂非强人以必不能者与?”[15](卷一二,《寄子方郎中书》)。
俸禄是职业官吏维持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养廉之具。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俸禄微薄引起的官吏相对贫困,呈现上升势头。两宋官吏中“多负人息钱”,“家食不给”,“无屋庐以居”的情况,已不乏见[33](卷三)[34](P.13132)。但是,像元代俸禄之薄,致使一般官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尚前所未有。这的确成为官吏贪赃恶性发展和屡禁不止的经济方面的根源。难怪陆文圭、程钜夫等说:“夫不足以养其身,而徒以禁其欲,欲无侵渔百姓,难矣!”“钞虚俸薄,若不渔取,何以自赡?”“官吏俸禄甚薄,不足以养廉,不得不贪墨以为家计”[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14](卷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不能自赡,故多贪残,宜于系官田地拨与职田》)。
元朝统治者的低俸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蒙古国草原官制比较简约,万户、千户和断事官只有部民、牧地的封赐及下属的贡献,根本没有汉地式的俸禄。这种草原旧俗对蒙古统治者长期不重视官吏俸禄,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兼之,元代冗官极为严重,支付诸多员额的官吏俸禄,已是不小的财政负担。增加官俸,也有一定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冗官制约着低俸,低俸维持着冗官,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循环机制。另外,官吏俸禄与钞值贬降挂钩,也加重了官吏低俸的危害。
其次谈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元代选官法比较特殊,大体有科举、荫叙、宿卫“别里哥”(蒙古语belge,符验之义)选、吏员出职等途径。其中,由令史、书吏入流出职者为数最多,宿卫出身者居官最显。因科举举行迟,取士少,授职低,“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9](p.4255)。
选官铨调时“不试贤能”、“阀阅是先”、“夤缘请托”等弊端,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北人世勋,皆居要津,贤能遭贬,奸贪恒多,“小大之职,颇稀清白之风”,严重败坏了官吏素质。官吏素质的降低,又直接导致腐败贪赃。于是,“官之失德,宠赂日章”,“营求之力既殚,取偿之意愈急,驱车在道,见物垂涎,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昼之攫”[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换言之,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是来自官吏队伍自身的直接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元代官吏素质低下,与儒士社会地位较低和官吏习儒者偏少,乃至官场风气的败坏,都有关系。
人们注意到,宋代吏治相对清明和官吏贪赃不十分严重的原因,不仅在于“严贪墨之罪”,还在于尊崇儒士和重视儒学道德规范的约束[6](第五章第五节)。元代的情况则与两宋形成较大的反差。儒士社会地位较低,甚至有“九儒十丐”等自嘲之说。相当多的儒士选择了远离官场的隐居和半隐居的道路,主要是追求“自立于己”,“而不敢求用于时”[7](卷一一,《复董中丞书》)。这样,儒士支配官场和儒学“仁义道德”规范约束官场风气的状态,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官吏素质低下和官场道德沦丧,难以遏止。
正如吴澄所云:“吏多贪残,而儒流知有仁义”[7](卷一八,《送彦文赞府序》)。儒士入官,多半讲究名节廉耻,即使为生活所迫,稍有额外不法收入,也懂得有所节制,适可而止。这可以算作一种来自道德伦常的自我制约。非儒士或不习儒之官吏则不然。他们不甚顾及礼义廉耻,容易“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元代官吏中儒士少,也是酿就贪赃成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有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史称,蒙古勋贵、答剌罕、中书左丞相“雅重儒术”,“闻儒者谈辄喜”,“惟不言利”,“一以节用爱民重民爵为务”。大德七年(1303年)一月,右丞相完泽等八名正、副宰相因受贿罢黜时,哈剌哈孙是惟一未染赃污而继续留任中书左丞相者[9](P.3291)[20](卷二五,《丞相顺德忠献王碑》)。
再谈最高统治者徇私曲赦。元朝皇帝经常朝令夕改,突然曲赦犯赃官吏,或对其罢而复用。如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因贪赃应该罢职,成宗以其是“故臣子”,特地减轻罪罚,让他依旧任职[9](P.414)。武宗初,一些因受贿被监察御史弹劾的官员请托入觐,以求免罪。武宗果然下令“曲赦”御史台逮系的犯赃官吏,罪罚仅限于征赃和罢职[9](p.482,p.493)。在曲赦犯赃官吏时,权相的斡旋作用颇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大都路判官萧仪收取贿赂,忽必烈欲断徒刑服淘金役。右丞相桑哥以萧仪“有追钱之能”为他开脱,忽必烈“曲从”,将徒刑减轻为杖[9](p.320)。成宗初奉使宣抚“纠治官吏贪邪”,有的宰相自己也“贪墨”,希望“因而肆赦”,后遭到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的阻拦,未能得逞[36](卷七,《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耶律文正公神道碑》)。吐蕃喇嘛帝师更充任曲赦犯赃官吏的积极怂恿和鼓吹者。“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9](P.4523)。
犯赃官员罢而复用的事例更多。成宗初,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弘吉烈带阿鲁灰受贿“遇赦免,复以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七年(1303年)“以贪贿罢黜”的洪君祥,又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前河间路达鲁花赤忽赛因“坐赃罢”,后“以献鹰犬,复除大宁路达鲁花赤”[9](p.385,p.449,P.453)。尤其是前揭大德七年三月成宗刚刚将“营私纳贿”的平章伯颜、暗都刺、右丞八都马辛等罢免,以圣旨告示天下。翌年九月,伯颜、八都马辛等三人又官复原职。文宗朝又有“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辽阳行省平章哈剌铁木儿尝坐赃被杖罪,今复任以宰执,控制东藩”[9](p.715,p.765)。
时至元末,曲赦和罢而复用,愈演愈烈。正如苏天爵所言:“近岁以来,赦宥太数……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岁,六年之中,肆赦者九。”[36](卷二六,《论不可数赦》)
频繁曲赦和罢而复用,直接带来了赃罪条例执行中的混乱,破坏了赃罪条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一部分赃官可以利用各种条件侥幸减轻或逃避处罚,甚至官复原职,依然如故。这不仅亵渎了朝廷法律的尊严,也使犯赃官员心存侥幸,台察和清廉官则蒙受打击。曲赦和罢而复用,表面上只涉及一小部分赃官,但对惩贪政策的贯彻执行,又带来了全局性的危害。
最后,谈谈蒙古草原旧俗的渗入。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在采用汉法之际,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蒙古旧俗长期保留下来。元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具体政策自始至终呈现蒙古法、汉法二元状态。我们注意到,有元一代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蒙古草原旧俗,同样地渗入了官吏贪赃,甚至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惩贪政策。我们前面提到的蒙古“撒花”俗对官吏贪赃的推波助澜,怯薛“别里哥”选与科举长期停废,视儒学为宗教而不当作治国修身之术等等,明显是蒙古旧俗因与汉法的抵牾而给元代官僚体制带来的不良影响。据初步考察,著名的成吉思汗“札撒”及宝训中,尚未见到惩办贪污的规则。蒙哥汗时期的“阿蓝答儿钩考”,也重在清查钱谷亏欠挪用和不上缴国库等事。而在《史集·窝阔台汗纪》中,我们偶尔检出一段与贪污相关的轶事:
合罕慷慨善良的名声四处传播,所以各国商人都争相来到他的宫廷。合罕吩咐收下他们的〈全部〉货物,不管好坏,全部如数付酬……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必阇赤们,有些开支。我这是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37](卷二,p.94)。
窝阔台明明知道,汗廷必阇赤等官在商人与官家的交易中因商人的额外“开支”而获取不少好处或礼品。这种好处或礼品,在蒙古俗看来就是所谓“撒花”,而从汉法观察,明显是贿赂。窝阔台不仅不予以责备惩治,反而下令高价支付商人货款,美其名曰替接受好处或礼品的必阇赤等官“付钱”。不难看出,窝阔台对官吏贪赃受贿,采取了明显的宽容放纵政策。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载,窝阔台批准了耶律楚材“便宜一十八事”中的十七件,惟独不批准禁止“贡献礼物”的“撒花”。足见,“撒花”旧俗在窝阔台等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尽管颇受窝阔台宠幸的耶律楚材竭力斥责其“蠹害”,也无法动摇窝阔台保留“撤花”俗的立场。此处的“贡献礼物”,与前揭商人的额外“开支”类似,都是所谓“撤花”。
上述放纵“撒花”贪赃的政策,像幽灵一样,长期困扰着元朝的多数皇帝,使他们在惩办官吏贪赃时往往干出前述频繁曲赦等荒唐事来。成宗大德七年取消赃罪十三等中的死刑条,估计与此不无联系。有一个现象比较清晰:元朝诸位皇帝中,像元世祖、英宗等采用汉法较多的皇帝,其惩治官吏贪赃相应地也比较严厉。而成宗、武宗、泰定帝即汗位前久居漠北,受蒙古旧俗熏染较深,其在徇私曲赦方面就似乎走的更远些。英宗朝惩办官吏贪赃最为坚决。见于《元史·英宗本纪》因贪赃被罢黜杖免的有: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班丹等多人。英宗终因“南坡之变”遭暗杀也表明:依蒙古旧俗对官吏贪赃持宽容放纵政策,在蒙古贵族官僚中颇有市场;而采用汉法和严惩贪赃,则在蒙古贵族官僚中受到孤立打击。
总之,蒙古旧俗的渗入,不仅影响了元代官吏贪赃活动本身,还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元代官吏的素质和统治者的惩贪政策。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且超越其他王朝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只要从蒙、汉二元体制和蒙古旧俗的渗入这一角度观察,元代异乎寻常的官吏贪赃及惩贪政策的失败,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收稿日期:2004-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