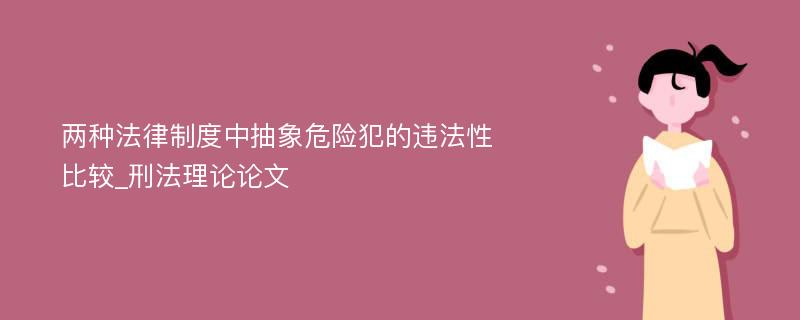
两大法系中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系论文,两大论文,抽象论文,危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3)03-0094-09
引言
将特定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刑事处罚,是主权国家在领土范围内的“垄断”行为。由于刑事处罚是一种剥夺性的强制措施,不加限制会任意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因此不管国家的刑事处罚权从何而来,立法者要制定刑法都必须遵守合理的界限。“任何人,包括国家,无正当理由不得强制他人。对人民行为的控制要求正当化根据,尤其是当这种控制伴随着对于不服从规范的人民采取严苛地、惩罚性的措施的时候。非有充分的正当化根据,立法者不得制定刑法。”①立法者制定刑法的正当化根据,就是宣布人民行为违法、给予人民以刑事处罚的违法性根据。对于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来说,刑法条文在规定上就将法益侵害的结果确定为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结果就是立法者规定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所要禁止的结果,因此,构成要件结果就是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对于抽象危险犯来说,刑法条文只是规定了行为,结果不是明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上的这一特征导致我国刑法理论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正当化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因此,如何在犯罪构成上找到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就成了研究抽象危险犯最重要的、也是更根本的理论问题。
一、大陆法系的做法
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益侵害性(法益保护原则)来构建的,法益概念和法益侵害性具有很深的理论基础。例如,许廼曼教授明确指出:“内容上绝对要坚持的是,法益保护原则(社会侵害原则)经由直接深植于社会契约,而成为每一种宪法理论的基础,不能因为宪法法院所发展出来脆弱的安全措施而被放弃,……而在方法论上,一旦刑法释义学放弃以法益保护原则(社会损害原则)作为它的基础——作为限制立法者恣意的基础,并因而在诠释时作为最高准则的基础——刑法释义学即再也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这种立场坚持以法益保护原则作为限制立法者和刑法解释论的基础,体现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基本立场。
(一)违法性的概念
在通行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违法性是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后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但是,违法性也可以同时包含两个阶层的判断,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而且缺乏违法阻却事由。“在违法性的标题下研究的却是排除违法性,乍一看,这是个令人迷惑的语言使用习惯。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构成要件该当性涉及的是违法性,是所有使得某一行为表现为违反了受刑法保护规范的行为的特征,只要允许性规定不介入,该行为就是违法的。因此,对于不法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将会在犯罪构造里的构成要件与‘违法性’这两个评价阶层进行分配。从某种程度上说,违法性本身只是构成要件该当性与缺乏阻却违法事由的结果”。③因此,本文所指的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指的就是对抽象危险行为的否定评价,同时包含了构成要件该当性与缺乏违法阻却事由,是与有责性相对应的违法概念。
由于在德国的三阶层体系中,将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情形,又称为“不法”,其中,“违法性概念强调的是行为的性质(价值判断),是对于对象的评价;由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评价对象,所以,不法概念包括了违法性的评价对象与对于对象的评价”。④因此,为了避免违法性这个用语本身所带来的困惑(两种含义),本文以下主要使用“不法”概念来代替符合构成要件,并且没有违法阻却事由的“违法”。
(二)自主的不法
在三阶层体系下,如何说明抽象危险行为对于法益的侵害性,是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法益的“侵害”具有比对法益的“危险”更大的不法,因此,作为法益侵害的前阶,所有的危险犯(包括抽象危险犯)都具有比实害犯更小的不法。同样,如果说实害犯的不法在于行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实现”,那么,危险犯的不法就在于行为具有产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因此,“危险犯的不法当且仅当是实害犯的不法的必要的前阶。因为危险犯的不法已经包含了重要的、自主的实害犯的不法内容,同样,危险犯也包含了危害性原则的所有内容,以及实害的不法结果之所以还未出现的具体情形”。⑤
按理说,抽象危险犯是危险犯,而危险犯的不法与实害犯的不法之间存在着自主的关联关系,所以,抽象危险犯也应该满足这种自主的关联关系,不然就会丧失其危险犯的属性。但是,在行为已经造成了客观的法益侵害的案件中,没有必要再去探求行为是否包含了危险的前阶;在行为尚未造成客观的法益侵害的案件中,因为无法从法益侵害中推导出客观的违法,也就没有办法推导出侵害的危险的前阶。易言之,在具体危险犯中,我们可以从具体危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中推导出客观的不法;在抽象危险犯中,由于构成要件中并未规定除行为之外的其他客观要素,因此我们很难从中推导出客观的不法。显然,抽象危险犯的不法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而是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危险犯的不法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而抽象危险犯的不法一直备受争议。
(三)两重的抽象化问题
抽象危险犯是刑法对法益实行前置保护的犯罪类型,国家不必等到法益侵害或者具体的危险结果发生,在此之前就可以动用刑罚进行规制,这是抽象危险犯的典型构造。但是,这样的刑事立法包含与原来的放火罪等传统的抽象危险犯不同的性质,尤其是在刑事立法采用抽象危险犯来保护新兴的集体法益的场合,产生了新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来的抽象的危险犯是以‘对可能把握的具体法益的抽象的危险’为基础,而现代的刑事立法中的抽象的危险犯是以‘对把握困难的抽象法益的抽象的危险’为基础。也就是说,现代的刑事立法中对于抽象的危险犯的处罚,具有通过对侵害和危及部分系统的平和来保护保全系统整体或者系统整体的顺利地运行的构造,可以说是处罚对于系统整体的普遍的法益来说的抽象的危险。由此,在这里就产生了保护法益的抽象化和危险的抽象化这两重的抽象化。”⑥这“两重的抽象化”被当作反对的理由,出现在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批评中。
本文认为,“保护法益的抽象化”并非反对抽象危险犯的理由。首先,虽然现代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多用来保护“整体的”、“普遍的”法益(理论上一般称为集体法益、集群法益或者超个人法益),而集体法益确实具有抽象化的特点,但法益概念的客观性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客观性,具有一定具体性的集体法益都可以成为抽象危险犯的保护对象。其次,对于刑法已经规定的抽象危险犯,解释论上可以通过具体化的方法来消解其保护法益的抽象性,亦即,对于每一种犯罪类型项下发生的每一起案件,都找到并具体说明其所保护的是何种法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将所有的集体法益都作为保护的对象,仅仅是少数的、重要的、具有保护必要性的集体法益才得以进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因此,抽象危险犯的保护法益可以被刑法上的法益概念所包含。
“危险的抽象化”这一批评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规定了危险与实害几乎同等程度(不具有抽象化)的抽象危险犯,如侮辱罪;刑法也规定了危险的具体化程度很高的抽象危险犯,如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只有在少量以集体法益为保护对象的抽象危险犯中,才可能存在危险的抽象化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地难以解决。
一方面从集体法益的性质上看,集体法益是全体的个人法益的集合,虽然集体法益具有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但集体法益并不高于个人法益,与之相反,集体法益是刑法对于个人法益的前置化保护,对于集体法益的损害必然会在将来危及个人法益,正是因为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这种关联关系,集体法益可以被具体化。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这种关联关系,可以认为,在保护集体法益的犯罪中,刑法既保护了集体法益,同时也间接地保护了个人法益。所以,“对集体法益的侵犯具有双重侵犯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双重包含性。这种最新的观点对于集体法益的代表(个人法益)来说也更加的适合,因此,双重侵犯性与被侵害法益的性质和类型联系在一起”。⑦易言之,在特定的抽象危险犯中,我们可以认为其存在“两重的抽象化”,这是一个缺点;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认为其具有“双重侵犯性”,因为其对法益具有双重侵犯性,所以抽象危险犯具有“两重的不法”,违法性根据更加的充分,这又是一个优点。所以,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化的批评并不能成立。
(四)抽象危险犯的法益侵害性
由于规定抽象危险犯的刑法条文只是规定了行为,“结果”不是抽象危险犯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依然是法益侵害,还是行为方式本身(而不是行为所引起的法益侵害结果)即具有刑事的可罚性,就成了争议的问题。
如果认为抽象危险犯的不法是行为的不法,就意味着只要实施刑法条文上规定的行为就可以成立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就变成了形式犯。但是,将抽象危险犯理解为形式犯是有问题的,“犯罪必须全部理解为实质犯,所谓的形式犯不过是以轻微的法益侵害为结果的结果犯或者是以轻微的危险为结果的抽象危险犯而已”。⑧如果认为抽象危险犯的不法仍是结果的不法,就必须论证“抽象的危险”是“结果”。对于直接侵犯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例如侮辱罪)来说,将抽象的危险看作是法益侵害的结果,不存在特别的困难。对于侵犯了集体法益的抽象危险犯来说,由于存在着两重的抽象化,要将抽象的危险看作是结果,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理论上对此提出了以下不同的解决路径。
1.累积的不法说
累积犯最初是由库伦(Kuhlen)在环境犯罪中创设出来的犯罪类型,指的是每一个行为单独来看都不能对集体法益造成现实的或者直接的损害,但是这些行为累积起来或者通过重复实施的累加最终会导致集体法益损害的犯罪。⑨库伦试图用“累积的不法”或者“重复的不法”来替代抽象危险犯的不法。但是,如果认为刑法应维持个人责任原则,累积犯的概念就没有存在的余地;而且,因为其他人的行为而处罚行为人,严重侵犯了行为人的利益。
2.规范的侵害说
由于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的法益侵害结果都具有现实化、具体化的特征;相比之下,抽象的危险是一种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并不存在真正的损害,是一种具有“推定”性质的危险,或者说是“危险的危险”,因此,应该将对法益的侵害结果区分为“现实的侵害”和“规范的侵害”两种,抽象危险犯的侵害是一种特别的侵害形式,无需现实化。⑩但是,这种规范的侵害概念,已经在实质上脱离了法益侵害的实质,反而靠近了规范违反说的立场。而且,这种方法直接在法益侵害结果之外,创设了另外一个概念,分化了法益侵害结果的内涵,可谓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了另一个问题。
3.功能的侵害说
这种观点从集体法益的性质出发,认为集体法益的性质决定了行为对集体法益的侵害具有独特性。集体法益是全体个人法益的集合,因此是个人法益的系统表达,直接关系到国家机构、公共职能的正常运作功能,是可以被具体确定的保护对象。因此,不应该将行为对集体法益的侵害限制理解为对经济制度的破坏或者严重威胁,而是应该将行为对集体法益的侵害从是否对公共职能的正常运转造成了障碍判断,(11)亦即,抽象的危险是侵害结果,但是,是一种功能的侵害结果。
本文认为,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对其法益侵害性作了过高的要求,要求抽象危险的法益侵害结果也达到实害犯、具体危险犯或者未遂犯的侵害结果的程度,但是,抽象危险犯的侵害结果不能与这些犯罪构成相比较。立法者规定特定类型的抽象危险犯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抽象的法益,抽象危险犯的侵害结果应该与立法者所意欲保护的对象相联系,亦即,在立法者通过刑法条文保护的是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在行为对经济系统造成了崩溃性的、毁灭性的损害或者严重性的威胁时,才能被看作是侵害结果。只要行为对于受保护的法益类别造成了立法者预期的一定程度的妨害,就是造成了侵害结果,所以,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仍在于其法益侵害性。
二、英美法系的路径
在构建抽象危险行为的违法性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大陆法系主要以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来构建犯罪论体系,而英美法系主要以危害性原则来作为犯罪化的主要核心。虽然从语言表述上看,社会危害性与危害性原则相差无几,但是二者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事实上,二者在理论的构建上具有一定的交叉,但是由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理论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刑法体系构造、不同的刑法思考方式,因此,二者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有学者试图揭示法益概念与英美刑法上的危害性原则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德国刑法学界的普遍怀疑。(12)
(一)危害性的概念
英美刑法理论上一般承认四个基本的犯罪化原则:危害性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父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13)其中,危害性原则是犯罪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亦即,要求拟被入罪的行为要对他人造成危害。因此,危害性原则可以被当作一味有效的解药,成为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过宽的手段。
从犯罪构成上来看,英美法系要求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犯行和犯意。其中,首先要有犯行,然后才能考虑行为人是否对此犯行具有犯意。犯行必须具有违法性,即不正当地侵害他人的权利;犯意必须是故意或者具有预见可能性,这是对行为人归责的基础。任何类型的犯罪行为都必须具备对他人造成危害的违法性,抽象危险犯等扩张处罚的犯罪构成也不例外。不过,有些严重的犯罪从犯罪构成上就符合危害性原则要求,因为该等犯罪被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犯罪构成上的结果,例如,杀人罪,如果杀人行为不会致人死亡——这一危害正好是杀人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行为就不成立杀人罪。但毫无疑问,有些犯罪也对他人造成了危害,但是这种危害并不是构成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上,刑法上规定了各种不同的犯罪。对于保护生命来说,除了杀人罪之外,刑法也规定了杀人未遂罪、危险驾驶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及其他保护个人生命和安全的措施。在这些(危害结果)并非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中,作为正当化根据的危害与犯罪行为本身距离较远。(14)根据这种分类,包括抽象危险犯在内的危险犯属于后者,即属于危害结果并非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
这种按照危害结果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来划分犯罪类别的方式,对于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来说也是最新的成果。一般而言,英美法系都将犯罪分为完成罪与未完成罪,其中完成罪指的是既遂模式的犯罪概念;未完成罪指的是预谋、未遂等犯罪形态。显而易见,不论危害结果属于构成要件的犯罪,还是危害结果不属于构成要件的犯罪,都可能是未完成罪。
(二)抽象危险行为的犯罪化
一般行为的犯罪化,在构成要件上就已经符合了危害性原则的规定;但是,抽象危险行为的犯罪化似乎与危害性原则相抵触,因为危害结果并不是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要素。有学者认为:“现在,刑法处罚范围的拓宽常常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正当化根据,这个根据是对危害性原则的增选:拟被入罪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远距离的危险。一系列禁止性规定(例如,与使用毒品相关的禁令)都通过行为导致最终的有害的社会结果来作为处罚的根据。将危害做这样的扩张,最终可能导致危害性原则是对国家惩罚权的限制这一有用性无法发挥。”(15)
可以说,抽象危险犯扩大了“危害”的概念,使其包含了距离危害结果比较遥远的侵害,这就使得“行为”与“危害结果”出现了分离,于是,刑法开始处罚不具有危害性的不法行为,“不法”与“不法的根据”相分离,危害性原则无法发挥其界限功能。而危害性原则的界限功能本来承担着双重任务:第一,划定处罚的范围,防止过分处罚;第二,设立处罚的边界,防止不当罚行为向当罚行为渗透,确保当罚行为与不当罚行为相比,具有统一的处罚性。一旦危害性原则无法发挥其界限功能,其作为犯罪化根据的功能就是不足的。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危害性原则遭到了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就是危害性原则的界限功能是模糊的、弹性的,也是有空隙的,已经无法发挥其限制国家惩罚权的作用。因此,“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以及“过度犯罪化”等问题开始出现。(16)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在这些扩张处罚的范围内,危害性原则具有矛盾的效果:其被作为对处罚的限制而引入,实际上却演变成一项对处罚的扩张起推动作用的机制。因此,要说明抽象危险与被禁止的行为之间的可罚性,仍然需要其他的根据。这并不是说危害性原则当然不适用于抽象危险犯,也不是说抽象危险犯颠覆了危害性原则,而只是意味着,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不法必须引入一定的限制机制,不能仅仅根据危害性原则就对刑事可罚性的范围进行无限制的扩张。
(三)四项限制机制
胡萨克提出了四项附加的限制原则,来作为抽象危险犯等危害结果并非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的犯罪化根据。
第一,重要性原则。这种犯罪构成必须是用来防止重要的风险:“如果这些犯罪被用来防止不重要的风险,就会导致处罚那些主观责任连过失犯的程度都不及的行为人,而且,法典也很少会对这些具有如此低的有责性的行为人实施刑罚。”(17)英美法系没有法益概念,因此,很难通过被侵害对象是否重要这一点来确定抽象危险犯等犯罪构成是否必要。而且风险是否重要,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即便能够认定风险是重要的,仍然不能确定抽象危险行为对这种风险的侵害是否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第一个原则并不能起到限制作用。
第二,有效性原则。这种犯罪构成必须“能够事实上降低最终会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性”(18)。但是,在立法上规定这种犯罪构成的时候,降低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只是立法上的推测或者立法者的目的,至于事实上是否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难以通过实证来证明。因此,第二个原则所能起到的限制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危害性要求。国家不得将减少某种危害的发生可能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除非国家将故意的、直接导致同样危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胡萨克提出这个要求的立论基础是:“在任何国家的责任体系中,过失犯罪都比故意犯罪更轻。如果一个故意地、并且直接地造成了危害结果的行为,都没有被规定为犯罪,那么,国家就没有理由将一个旨在于防止人们仅仅制造了同样的危害结果产生的可能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9)可以说,建立危险犯(主要是抽象危险犯)与实害犯之间的危害程度上的关联性,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理论尝试,笔者也赞同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但是,胡萨克的立论基础存在着问题:首先,并非在任何国家的责任体系中,过失犯罪都比故意犯罪更轻。这是只有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才能得出的结论。正如有批评者所指出的:“过失犯罪并不必然就比故意犯罪要轻,这取决于犯罪的性质而不是罪过的程度;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犯罪的轻重并不取决于可谴责性程度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行为的违法性。”(20)因此,第三个原则也是有问题的。
第四,有责性原则。胡萨克认为立法上出现了过度犯罪化的状况(基于理论上的假设),因此,应该通过有责性原则限制抽象危险犯等犯罪构成的处罚范围。“除非行为人对于行为最终产生的危害结果具有某种程度的有责性,不然不应为自己制造了危害的可能性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单纯地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可能引起最终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并不具有可罚性。”(21)这一原则要求抽象危险犯的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的结果,以避免客观归责。但是,危害性原则并不属于犯意的范畴,将属于可谴责性层面的判断前置到危害性的判断中来,反而会使得危害性的判断更加的主观化。可谴责性的判断属于事后判断,是如何对行为人归责的问题;危害性的判断是事前判断,是如何将抽象危险行为等犯罪化的问题。胡萨克混淆了这两个判断,因此,他提出的几个原则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危害性原则所遇到的问题。
(四)抽象危险犯的危害性
因为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就是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所以,危害结果没有实际发生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是“真正的危险”还是“不真正的危险”来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产生了真正的危险的行为,这种危险会在伴随的事实中体现。抽象危险犯是产生了不真正的危险的行为,由于这种危险需要伴随一定的事实才会发生,而立法者规定即便未出现这些伴随的事实,行为人对此也有认识,依然应受处罚。(22)
对于具体危险犯来说,由于法律同时规定了危险行为引起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危险在行为的伴随事实中真正的发生,危险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不存在违反危害性原则的问题。有问题的是抽象危险犯:“以粗心驾驶罪为例,英国公路的限速是每小时70公里。法律设定时速限制是为了保护人命免受危害,但是,行为人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行驶就构成本罪,即便前方道路空无一人,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危险。因此,70公里的限速规定就是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处罚的是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会产生危险的行为,但即便这些特定情形并不存在,行为人也认识到特定情形不存在的,仍然构成犯罪。”(23)因此,抽象危险犯的问题就是:既然未产生真正的危险,为什么要将抽象危险行为规定为犯罪?可以说,在抽象危险犯正当化的问题上,英美法系面临着与大陆法系同样的问题。
在注重实用主义的英美法系,设置抽象危险犯是实际的需要。首先,要证明危险行为事实上产生了真正的危险有时具有认定上的困难,会花费更高的执行成本,也不利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其次,作为提前处罚的措施,抽象危险犯比相应的具体危险犯更有利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因此,“抽象危险犯就成为避免处罚不足和过度犯罪化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24)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危险犯的犯罪化根据,就是为了填补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之间的处罚漏洞;同时又可以避免将危害过度延伸,处罚那些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造成国家对个人领域的过度干涉。而抽象危险犯既可以达到避免危险行为继续向前发展、以至于发生具体危险的效果,又可以通过行为与最后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找到危害性根据。但是,抽象危险犯的规定会包含危险行为与最后的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关联性的情形。例如,A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行驶,即便前方道路空无一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抽象危险犯。同样,B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行驶,前方道路也空无一人,但是,B是职业赛车手,即使开到200公里,他也有足够的把握不会对他人或者自己的生命、身体造成任何危害。B的行为构成抽象危险犯吗?对此有两种理论说明B的行为构成抽象危险犯。(25)
1.参与共同活动的合作义务
刑法将抽象危险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内向型保护。危险驾驶罪就是典型的内向型保护犯罪,因为立法者设定规范是为了禁止(所有的)危险驾驶行为,规范的保护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所有的)驾驶人。这种规范是一种互惠型的规范,行为人遵守规范不仅可以使他人免受自己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也可以使自己免受他人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二是外向型保护。例如环境污染罪,工厂非法排污的行为被禁止,是为了使他人免受污染的损害。这种理论能够说明为什么人们都要遵守抽象危险犯的规范,但是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特定行为人确信不会发生危险的行为也要受处罚,于是要引入社会连带理论。
2.社会连带理论
社会事务中的个人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行为人自身确信不会发生危险的行为,可能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说确实是没有危险,但是对于道路上的其他人来说仍然具有危险。所以,上例中的B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会产生危险,但是,他并不能控制道路上行驶的他人的行为,也无法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会对他人产生危险。事实上,一旦B开始实施超速行驶或者醉酒驾驶行为,他的行为就已经对他人产生了可能造成危害的危险了。而且,当他以其他的驾驶人员无法预料的方式驾驶时,他的行为已经因此对他人产生了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危险。
三、结论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都在于其法益侵害性或者危害性,这是各国对于抽象危险行为实行犯罪化的核心根据。在英美法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至少是可能产生危害的抽象危险,可以发展成具体危险,如果没有具体危险犯的规定,通过抽象危险行为造成了具体危险结果的,依然构成抽象危险犯,不然无法填补处罚的漏洞。相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抽象危险犯在成立上比大陆法系更加严格,一旦实施了刑事立法规定的抽象危险行为,几乎不具有排除抽象危险犯成立的限制机制,或者说,即便具有限制机制,也很少可以发挥限制作用。
我国刑法理论上必须肯定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是法益侵害,而不是行为方式本身即具有刑事的可罚性。作为刑事处罚的前置化类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抽象危险犯的违法性根据:一是双重的侵犯性,对于保护集体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而言,侵犯了集体法益的行为必然会间接地侵犯个人法益,因此具有双重侵犯性。二是功能的侵害性,抽象危险犯的侵害结果应该与立法者所意欲保护的对象相联系,只要行为对于其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立法者预期的功能上的妨害,就是造成了侵害结果。
注释:
①Simester and Sullivan,Criminal Law Theory and Doctrine,Oxford and Hart Publishing,2003,p.5.
②[德]许廼曼:《刑事不法之体系:以法益概念与被害者学作为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间的桥梁》[C],王玉全等译,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集贺许迺曼教授六轶寿辰》,春风煦日论坛2006年版,第203页。
③[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M],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④张明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J],《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第45页。
⑤Roland Hefendehl,Debe Ocuparse el Derecho Penal de Riesgos Futuros? Biens jurídico colectivos y 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Revista Electrónica de Ciencia Penal y Criminoligía,04-14 (2002),p.9.
⑥[日]関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C],王充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⑦Tatiana Vargas Pinto,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 y resultado,Editorial Aranzadi,SA,2007, p.119.
⑧[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M],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⑨参见钟宏彬:《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M],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91页。
⑩See Tatiana Vargas Pinto,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 y resultado,Editorial Aranzadi,SA,2007,p.142.
(11)同前注[10],p.137.
(12)参见[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C],樊文译,《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13)Nina Persak,Criminalising Harmful Conduct:The Harm Principle,Its Limits and Continental Counterparts,Springer,2007,p.13-22.
(14)See A.P.Simester and Andrew Von Hirsch,Remote Harms and Non-constitutive Crimes,Criminal Justice Ethics,Vol.28,No.1,2009,p.89.
(15)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 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Harm and Culpability,Oxford,1996,p.259.
(16)See Bernard E.Harcout,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in Vol.90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 Criminology,p.109-194.
(17)Doglas Husak,Overcriminalization:The Limites of the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62.
(18)同前注[17]。
(19)同前注[17]。
(20)See A.P.Simester and Andrew Von Hirsch,Remote Harms and Non-constitutive Crimes,Criminal Justice Ethics,Vol.28,No.1,2009,p.92.
(21)Doglas Husak,Overcriminalization:The Limites of the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74.
(22)See A.P.Simester and Andrew Von Hirsch,Remote Harms and Non-constitutive Crimes,Criminal Justice Ethics,Vol.28,No.1,2009,p.94.
(23)同前注[22],p.95.
(24)同前注[22],p.95.
(25)同前注[22],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