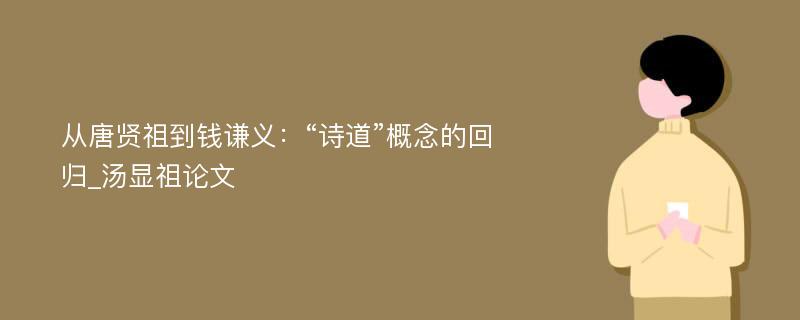
从汤显祖到钱谦益———种“诗道”观念的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汤显祖论文,到钱谦益论文,诗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3-0068-07
明末诗文大家汤显祖,晚年与钱谦益的一次短暂交往,在钱谦益学术生涯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① 但是就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历史意义,迄今仍未见有人详加论述。近来虽有一些学者提及此事,然尚欠进一步的描写与分析。本文欲以此事作为切入点,旨在通过对汤、钱二人交往的细致描写与分析,凸显出钱谦益诗学的路径、规模及特点,以期进一步把握其对虞山诗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另外,借此亦来考察明末儒学知识界内在结构的调整与变革的历史趋势。
关于汤、钱二人之交往,须先作史实上的清理。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对之所叙甚详,兹引书中最有关系的一段文字如下,再略加推论:
临川汤义仍文集若干卷,吴人许子洽生以万历乙卯谒义仍于玉茗堂,而手抄之以归者也。义仍告许生曰:“吾少学为文,已知訾謷王、李,搰搰然骈枝丽叶,从事于六朝。久而厌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泛滥词曲,荡涤放志者数年,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而吾年已往,学之而未就也。子归,以吾文视受之,不蕲其知吾之所就,而蕲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谓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兴乎?”余闻义仍之语,退而读其文,未尝不喟然太息也。[1] 905
这一段回忆对于了解汤、钱之关系以及明末文风之蜕变都极为重要,我们可以从历史和心理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从历史方面说,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几项事实:一、汤、钱二人的交往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此时,汤显祖已弃官归乡,以诗文自娱;而钱谦益则因丁父忧而尚未赴朝任职,至此已过五个年头。故这次交往发生在彼此较为闲暇的一段时期中。二、汤、钱之交往是通过吴人许子洽完成的。许子洽,又名许重熙,常熟人,与钱谦益相友善。万历四十三年曾拜见汤显祖于玉茗堂,手录其文以归,并向钱谦益转述汤显祖的郑重嘱托。其后不久,钱谦益为许子恰抄录回的《玉茗堂文集》作序,对汤氏诗文进行了简要评价,持论甚高。关于许重熙拜谒汤显祖一事,亦可参证于许重熙《文集原序》、汤显祖《答许子洽》及《答钱受之太史》等文。② 据史料推测,许子洽抄回的《玉茗堂文集》很可能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帅机等人选定并刊刻于南京文棐堂的《玉茗堂文集》,其中赋两卷、诗十三卷。故钱谦益所作文集序当包括对汤显祖诗文的总体评价。三、据引文推知,汤显祖极为推重钱谦益,并以复兴“古文之道”的重任相期许,这在钱谦益转述之言中灼然可见。汤显祖《答钱受之太史》云:“文章之道,有尽所托。旷世可以研心,异壤犹乎交臂。存来感往,咸效于斯。”[2] 1535其推重后学之意尤为显豁,换言之,他是将钱谦益视作自己学术事业的传承者而深以期许的。
从心理方面看,由于汤、钱二人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我们在分析两者交往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之前,必须先分别地对两人交往前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加以追溯。
汤显祖在《与陆景鄴》中对其学术历程追忆道:
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未知其法。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前以数不第,辗转顿挫,气力已灭,乃求为南署郎。得稍读二氏之书,从方外游。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赋。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犹未能忘情于所习也。[3] 1436
可见其对自身学术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用他的话可概括为“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赋。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以此可明其一生学术之演变是在“道”与“文”之间的往返游离,或者说,对“道”的体认与追寻始终是他诗文观念演变的一条主线。自年少起,汤显祖便以学“道”自居,汲取江西学风的理致之气,“公少时学道于盱江罗明德先生,有得于性命之旨。壮年成进士,锐然有志当世”[4] 1688。若观其学术起始之路径规模仍可归属传统儒学之界域。“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又决非自谦之词。就心性而言,他对诗文韵语喜爱有加,自称“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5] 1451,“不佞少颇能为偶语,长习声病之学,因学为诗,稍进而词赋”[6] 1516。特别在其登第之后,“翳迹仕途,播迁海滨”[7] 1638,传统儒者所企慕的致用之学已全无用武之地,故而逃遁于诗文韵语以潇洒自娱成为他最主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仆少于文章之道,颇亦耳剽前识,为时文字所系。弱冠乃幸一举,闭户阅经史几遍,急未能有所就。幸成进士,不能绝去杂情,理成前绪。亦以既不获在著作之庭,小文不足为也。因遂落拓为诗歌酬接,或以自娱,亦无取世修名之意。[8] 1398
在诗歌创作上,汤显祖是以反驳王、李俗学的姿态迈入诗坛的。③ 起初欲以六朝绮丽的诗风对抗七子粗陋鄙俗的诗体,这在他早年编撰的诗集《问棘邮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其后不久,因自省诗作“过耽绮语”[9] 1401,遂弃去六朝文风转向师法宋元诗的劲健直露之气。正如钱谦益所云:“四十年来,希风接响之流,汤临川亦从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10] 1359然汤显祖在晚年对自己向韵语讨生活的经历颇为不满,尤其是这种诗风间的对抗与替变本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诗坛痼疾的最佳途径——“久而厌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旧弊方除又会产生新的弊病。故其晚年的所有努力,便在于开辟出一条新路,“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旨在从根本上探求诗文的本真之“道”,以期从更高的层面解决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正可视作向其早期学术求“道”理路的回归。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汤显祖生命的最后六年中,其留下的大量诗文时常流露出一种悔过的心态,对其自身学术之发展(尤其是中年以诗文自娱的一段时期)更多地表现为惋惜和遗憾。汤显祖认为,其学不足行于世之因主要在于“乡举后乃工韵语,三变而力穷,诗赋外无追逐功”,大量精气耗费于诗文,而对于古人之“道”的探求则大有缺略。因此,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值他晚年反省一生学术的遗憾、困惑期,钱、汤二人之交往当与此期汤氏特殊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十年,在钱谦益的学术生涯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万历三十八年(1610),钱谦益高中榜眼,因丁父忧闲居在家,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段时间当中,其诗文造诣不断精进,对诗的理解也渐趋成熟。少年的钱谦益曾一度沉迷于王、李俗学,他说:“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摇笔自喜,欲为驱驾,以为莫己若也。”[11] 1347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左右,他入京赶考结交嘉定李长蘅。李氏的一番质疑方摇动其追随王、李之学的坚定信心。④ 之后不久便归乡闲居,一面恭孝侍母,一面研讨诗文,其对于自身学术拓展之方向与路径,必是反复思虑、举棋不定的一段艰苦时期。钱谦益回忆道:
仆狂易愚鲁,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李、王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瞌睡于梦呓之中,不觉汗流浃背。[12] 1306
另《复李叔则书》云:“仆年四十,始稍知讲求古昔,拔弃俗学。门弟子过听,诵说流传,遂有虞山之学。”[13] 1343可见四十岁是其学术的成熟期。若按年代推算,当在明天启元年(1621),正值他家居十年之后。据此不难推测,归宁十载正是钱谦益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说,钱谦益学术的成熟必源于这个时期的苦心沉潜。所以,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接受汤显祖嘱托之时,在学术上恰恰是处于徘徊抉择之际。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汤显祖结交钱谦益的动机以及在彼此之间产生的深刻影响。汤显祖的个性,内向而独拔,“达官贵人,辄干之不置,公亦不以屑意也”[4],不是慕名通好、结交权贵的那种人。他主动转托许子洽而嘱咐钱谦益一事,显然是为问学求道的意图所驱使。汤显祖在晚年对自己以往的治学途径感到困惑,尤其在如何处置“文”与“道”之关系上纠缠往复、纷扰不清。“诗赋外无追逐功”——在他看来,这根本算不上明体达用的通人硕学,以至“世之慕公者,类皆赏其清词丽句,仅在骚人墨客之间”,这对于胸怀儒者济世之心的汤显祖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震荡。故在其六十岁之后,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之加剧,由文返道、以儒者之志替换文人之心的自觉意识表现得越发强烈。正如钱谦益所述:“泛滥词曲,荡涤放志者数年,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这成为汤显祖晚年学术的主调,若循着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很可能走上一条讲究“文道合一”、“经世致用”的实学之路。然汤显祖毕竟已入风烛残年之时,不免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为所淹没。万历中,临川能讼言之,而穷老不能大振”[11],故时常也流露出一丝的无奈。因而,只有寄希望于后人,方能秉承绍继自己未竟的事业:“安得四出而望见其人,其人又安肯坐而为某来者”[3]、“吾衰且敝……以吾之情,不减昔人。将才与学,不能有加于今之人也多。托末契于后人,予将老而为客”[14] 1401。所以晚年的汤显祖寻求薪火传播者的意识颇为明显,此殆可断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汤显祖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主动结交钱谦益的,但就另一角度而言,钱谦益在吴中地区日益上涨的名气声望,也成为汤氏如此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钱谦益云:“自余通籍,以至于归田,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连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15] 961,足见其已自立一方,成为吴中诗酒风流的领袖,无论是古文或是诗歌之造诣,均精绝一时。汤显祖对之甚为企慕,曾道:“近吴之文得为龙者二。龙有醇灏丰烨,云气从滃郁而兴,幽毓横薄,不可穷施者,钱受之之文也。”[16] 1139其中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汤显祖对钱谦益的嘱托究竟涉及了怎样的问题?其对钱谦益学术发展之启示又在于何处呢?据钱谦益《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以及汤显祖六十岁之后的部分文章进行推测,大致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其一,源于诗坛变革所生出的困惑。就创作而言,汤显祖是一位极具天赋才情的诗人,其特立独行,绝不影从他人,业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因而,他对诗坛上流行的王、李诗风极为反感,并致力于清除抄袭盛唐格调而形成的流弊。在诗歌创作上,他首先标举六朝绮丽的诗风,此举不仅源于个人之喜好,更重要的是在于对抗王、李粗鄙诗风的一种手段。然而未久,他便体察出六朝诗风的新弊。其在《答罗匡湖》中道:“市中攒眉,忽得雅翰。读之,谓弟著作过耽绮语。但欲弟息念听于声元,倘有所遇,如秋波一转者。”[9] 汤显祖显然接受了朋友的规劝,遂将心思转出六朝“绮语”的园囿,进而推举宋诗径露充沛的体势与格调。然他心知肚明,虽其“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5],诗风间的对抗与替换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诗坛之积弊,故其一生的努力“三变而力穷,诗赋外无追逐功”,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那么应该如何改革诗坛,如何为诗坛规划出一条可行之路呢?对于这一点,汤显祖虽劳于所思,但终无所就。其晚年甚至弃绝诗赋一类的韵文:“时为小文,用以自喜……韵语行,无容兼取;不行,则故命也。故时有小文,辄不自惜,多随手散去。”[5] 所以说,汤显祖将自己的困惑转告钱谦益,实则期盼这个年轻人能够汲取自己“三变而力穷”的教训,探索一条改革诗坛的有效路径。
其二,在“道”与“文”之间游离的痛苦。汤显祖其人,始终具有济世救民的士大夫情怀,若论其思想世界的特性及归属,理应视作典型的儒家文人。秀琦称其“壮年成进士,锐然有志当世。为南祠部郎,抗疏列论时相,谪尉海南。既而量移平昌,即自投劾而归”[4],足见他干预世事的儒士之心。然其“名位沮落,坎壈百罹”[4],“冷局孤踪,不获展其志用”[17] 1688,因而不得不转“道”从“文”,驰骋于笔墨声韵之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举。然在汤显祖精神世界的深处,一直深藏着儒者关怀现实的影子,所以他在笔墨韵语的游戏之中,时常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谴责和痛楚,这种感觉至晚年愈来愈烈。他在与钱谦益的信中说:
不佞壮莫犹人,衰当复甚。世途瞆瞆,妄驰王霸之思;神理绵绵,长负师友之愧。赋学羞乎壮夫,曲度夸其下里。诸如零星小作,移时辄用投捐。盖亦存心所知,匪烦人定者也。又何足掩空虚而对问,侈怡悦以把似者哉?[2]
其意已被秀琦点透:“公之学以明体达用为归,非铮铮细响自鸣而已”[4],可见赋学曲度绝非他一生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其心思仍在匡时济世、明体达用的通人硕学。故汤显祖晚年,遂转向曾、王之学,“长行文字,深极名理,博尽事势,要非浅薄敢望”,这既能一展其文采之华,又可达其入世之志。因而可以说,在曾、王之学所构建的知识世界里,汤显祖所承受之“道”与“文”分裂的痛苦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与弥合。然他对曾、王之学仍处于“欿然不自有”[18] 906的阶段,而未能对之作理性自觉的把握。这一点,也正是他期盼钱谦益“精思而深造”[18] 之处。
从钱谦益一边推想,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后,他也正处于学术发展之关键期。此时,诗坛格局极为复杂。“七子”派诗风受到公安、竟陵的攻击,虽大势已去,然于士人中仍具一定影响力;竟陵反叛公安,自立门户,标举清新刻露之词,崇尚幽冷静僻的诗风,多少已显露出新弊。另外,钱谦益所在虞山一地,又承袭百年来吴中香艳绮靡的诗风,此与“七子”派、竟陵派诗风纠缠在一起,构成诗坛门户众多、派别林立的独特景观。⑤ 而对于刚刚归宁闲居的钱谦益而言,心中追随王、李“俗学”的信念方有所摇动,那么面对日益复杂的诗坛将何去何从,这必定会成为他深深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换言之,汤显祖变革诗坛的困惑可以成为钱谦益进一步思索的起点。就汤显祖终生的诗学路径而言,其反驳王、李一派的方式在于标举六朝绮丽的诗风,后又因自陷于“绮语”而转向师法宋元格调。经过这样的反复变易,非但没有解决诗坛之痼疾,反而引起一些新的流弊。汤显祖晚年对之深有参悟。他认为这种以诗风代替诗风的变革途径,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诗坛之颓势,其结果正可谓“王、李之朋徒耳”!或者可以说,他心中实已辨清诗歌风格层面的流动性和变易性以及诗风与“诗道”两者之间的距离,并力图将这种体悟辗转传述给钱谦益,以期他能透过诗坛的表面现象而直指问题的中心——“诗道”。
我们不禁要问,汤显祖期望钱谦益“精思而深造”的“古文之道”特指什么?这里的“道”与明末知识界的变化又有何种关系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儒者之“道”的问题即“道”的永恒性、历史性与现实性。⑥ 永恒性,是对“道”超越时空之本体品性的一种描述。“道”之本义是人走的道路,进而引申为不可易变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之道”就含有文章写作之本质规律的意味。历史性则表明“道”同时又是具体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传统之中,而非游离于历史之外,故文章之“道”则可以通过梳理历史的活动而得以探求。现实性指“道”的实践品格,儒家戍守之“道”并非仅仅局限于哲学层面的本体阐发,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对整个社会的一种秩序体认。循此三层含义来理解汤显祖所言之“道”,当是在不同层面给钱谦益以启示:
就“道”的永恒性而言,上面已约略谈及,其对钱谦益诗学变革的整体指向影响甚大。汤显祖晚年于曾、王之学体悟出的诗文之“道”,与其一生反复变易的诗文宗法主张密切相关。我们如果将诗风间的转变视作“诗艺”层面不断运动的表征,那么汤显祖晚年的文学活动可以视作从“诗艺”向更为深层、永久的“诗道”层面的回归。这种变化趋势,不仅表现着汤显祖诗文观念的演进轨迹,大而言之,亦可预示着一个新的诗学时代的到来。而对于汤显祖这一点深刻的体悟,钱谦益似是深有契合。他在《题怀麓堂诗钞》中云:
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剽唐《选》之余沈,生脱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穷,晦昧结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19] 1758
其实将汤显祖对个人诗风易变之深刻反思扩大到对明代几百年间诗学发展的宏观认识上。所不同的是,钱谦益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肯定了诗风交替代兴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导致的“传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之恶果,这又是对汤显祖晚年体悟的进一步推进。基于这种认识,钱谦益遂将革新的视野转出诗风层面的苑囿,进而直指问题的中心“诗道”,并以之作为毕生诗学活动的最终鹄的。如若检视其《初学集》、《有学集》之恢弘著述,自天启元年(1621)之后,对“诗道”的叙述与探讨业已成为钱谦益诗学的主旋律,甚至一直演奏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而可以说,汤显祖晚年以“道”之重任相托,对于钱谦益新型学术理想的确立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就“道”的历史性而言,“诗道”又需依存于连绵不绝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古人善于谈“道”,但总的特点是征史论“道”。数次以明“道”为职帜的学术变革,无不表现出托古立论的特点,即根据历史来言说现实,利用历史之渊源来强化变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因而,历史,始终成为“道”体的坚实依托。⑦ 同样,诗学的变革亦如此。“诗道”并非虚空之指,而是存在于诗歌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故而只有沿着诗歌演进之轨迹穷源溯流,原本雅故,方可推究其变化发展的本质规律。汤显祖晚年能够回溯于曾、王之学而顿悟诗文之“道”,关键之处便在其勇于摆脱明末俗学立坛树帜之困扰而返求古人,在历史的延续中寻找、探求诗文创作的精神脉理。正是这一点,直接给予钱谦益方法论层面的不少启示:“北地纡前辙,弇山定晚年。襟期同郑老,师匠并临川。”[20] 630钱谦益承汤显祖之衣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痛斥明末诗学割裂古今诗歌源流之弊。如他抨击“七子”派道:
嗟乎!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羃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沈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21] 709
“七子”派论诗之弊在于“支离割剥”、“限隔人代”,学术眼光极为狭小:“天地之大也,古今之远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广也,窃窃然戴一二人为巨子,仰而曰李、何,俯而曰钟、谭,乘车而如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22] 1344他们从盛唐诗歌的体制中抽象出一整套格调,并以之作为评判诗歌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用一种违背诗歌本质规律的外在尺度,来生硬地裁量历代各具特色的诗歌作品。其结果是割断时代与时代间的联系,把一个完整的诗歌发展脉络,截为价值不等的片断。钱谦益对此进一步批评道:“僻学为师,封己自是,限隔人代,揣摩声调,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为河汉,谬种流传,俗学沉锢,昧者视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剑于已逝,此可为叹息者也!”[23] 429故而冲破俗学之陋劣,恢复诗歌发展之原貌,在历史源流中把握诗歌最为根本的规律,这成为钱谦益学术革新的主旨之一。在学术取向上,汤显祖追慕曾、王,回溯古学的理路在钱谦益手中得以拓展,表现出直接古学灵魂血脉的显著特征:“先河后海,穷源溯流,而后伪体始穷,别裁能事始毕。”[24] 924这种考信古人、先河后海的方法,后来被钱谦益发展为“通经汲古”之学。
最后,就“道”之现实性而言,“文以载道”乃汤显祖与钱谦益共同信奉的永恒准则。汤显祖一生的遗憾与悔恨便在于被世人视作“欲以笔墨驰骋”的文人墨客,“诗赋外无追逐功”是对其“锐然有志当世”之心的无情折磨。钱谦益对其晚年遗憾痛楚的内心世界当是体会得十分真切。作为有经世理想的儒家士大夫,理应以国家民族的存亡复兴为己任,而不应将心思气力完全耗费在诗文韵语的研讨声中:“呜呼!诗道大矣,非端人正士不能为,非有关于忠孝节义纲常名教之大者,亦不必为。”[25] 831反之,诗文则须承受时代的使命,成为关怀现实、反应民情国势的重要手段。正如钱谦益所云:“文以足志,词以足言。托物连类,主文谲谏,其不独俪花斗叶,以词赋为君子而已也”[26] 955,“夫诗本以为正纲常、扶世运,岂区区雕绘声律、剽剥字句云而乎?”[27] 830可见钱谦益将诗文纳入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路昭然若揭,这也是汤显祖在晚年期望后人不断追求的诗文境界。
总结的说,汤、钱二人的交往,对钱谦益而言,具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是对诗坛革新模式的反思,一是“诗道”观念的复归。汤显祖改革诗坛之举,使钱谦益深切地体会到不能重蹈前人之覆辙,若以诗风之标举来引领诗坛之发展,只会流弊相生,落入门户间的争斗。所以,超越自立门户、独霸坛坫的恶习,反求诸更高层次的“诗道”,遂成为钱谦益心中的最高理想。特别是汤显祖晚年的所思所行,为其“诗道”观的确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后,钱谦益学术思想方面(尤其是诗文观念)的发展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他和汤显祖的这次交往。若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也正反映出明末传统儒学逐步复苏的内在趋势。
注释:
①就对钱谦益诗学之影响而言,学界比较关注程孟阳。一是因为钱谦益曾多次提到程孟阳对其学术的影响;二则在于他正是通过程孟阳这一途径而邮传震川(归有光)之学的。实际上,据金鹤冲年谱记载,钱谦益与程孟阳的首次深入交往在万历丁巳(1617):“程孟阳自嘉定来,居拂水山庄,留连旬月,相与讲诗论法,先生之诗遂大就。”(《钱牧斋先生年谱》,《牧斋杂著》,《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33页)而在此之前,钱谦益并未濡染嘉定学风。与之相比,钱谦益与汤显祖的交往则发生在万历乙卯(1615),恰在其与程孟阳第一次拂水唱和之前。因此,这次交往对于钱谦益学术发展的历史意义颇值得开掘。
②汤显祖《答许子洽》云:“僻在江外,子墨之游无几。幸如门下贲思,假以芳帙,渊云徐庾,舂容骈陛……挈此于吴中,如以残砾比海月耳。”(徐朔方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3页。)再如许重熙《文集原序》云:“熙于乙卯之夏,一登夫子之堂。谈筵穷莫,渺矣情飞;玄论辙幽,爽然骨解。是编也,虽咀我一脔,未窥鼎内。而珍兹尺锦,足祕帐中。”(徐朔方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0页)此均为确证。
③钱谦益《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云:“义仍官留都,王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尽出其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弇州没,义仍之名益高。海内訾謷王李者,无不望走临川,而义仍自守泊如也。”(《初学集》卷三十一)
④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云:“为举子,偕李长蘅上公车,长蘅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语未竟而散去。”(同上)但这次交谈并没有促成钱谦益学术的转向。他在《四书传火集序》中道:“忆往年与长蘅同上公车,时时谈古今文字。长蘅亟称归太仆,以为比肩曾、王,空同辈所不逮也。予心志其言而未敢信。”(《牧斋外集》卷三)
⑤“七子”派诗风影响至吴中地区可以追溯至黄勉之兄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涍”条云:“余观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就虞山而言,徐祯卿亦“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列朝代诗集小传·丙集》“徐博士祯卿”条),成为浸染“七子”诗风之确证。至万历中后期,据冯舒《怀旧集》所载,虞山徐济忠、孙朝肃、郭际南等人均是“七子”诗风的推崇者。(见冯舒《怀旧集》,《丛书集成新编》)可见,在明中后期,“七子”诗风在虞山占据一席。与此同时,竟陵派诗风对吴中(包括虞山)诗坛影响亦大。徐波(徐元叹)、沈春泽、葛一龙、吴鼎芳、张泽、华淑等人构成竟陵派一支。其中沈春泽,字雨若,号竹逸,虞山人。天启二年(1622),钟惺将自选诗文托其谋刻,可见其与竟陵派的密切关系。(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沈秀才春泽”条)至于吴中绮靡香艳的诗风,堪称诗坛传统。此点在后文阐释“二冯”诗歌审美观时将有所涉及,此处不再展开。
⑥余英时对“道”的中国特征论述甚为精辟。他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具备两种属性:一种是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种是“人间性”,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而这两种意义又是内在贯通的:“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人伦日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借鉴这种说法,进一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儒者之“道”。
⑦余英时曾以印度、以色列、希腊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道”的历史性:“我们都知道,古代印度人的历史观念极淡薄,这和他们把世界视为‘虚幻’的观念分不开的。古以色列的‘先知运动’一方面突出了‘超越创造主’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将耶和华从一位民族神转化为全人类的上帝。这样一来,以色列一族一地的历史自然不能在其教义中具有任何意义了。古希腊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和中国人大异其趣。整个古希腊思想中便存在着一种‘反历史的倾向’,西方史家之祖希罗多德的出现,有人甚至诧为意外。‘哲学的突破’给希腊人带来了追求普遍性规律和永恒性理念的要求,柏拉图在这一方面尤其具有代表性。从这个观点看,历史现象既是变动不居的又是独特而无从归类的,因此没有研究的价值。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的学术,但却不曾给史学留下任何地位。在他眼中,史学的重要性远在诗学之下。这和中国古代的学术总汇于‘史’的情形恰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