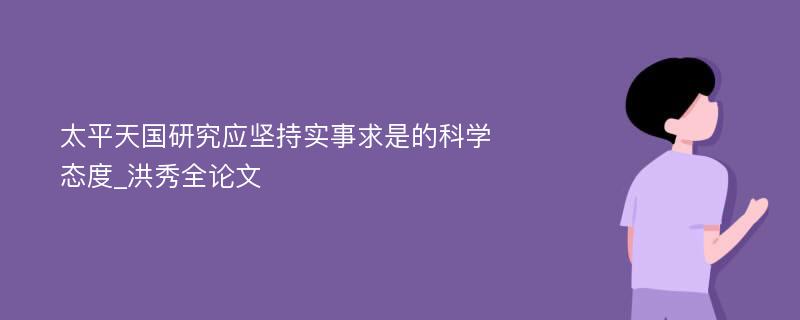
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态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025-008
(一)
太平天国研究,如从1856年(清咸丰六年)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算起,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注:《贼情汇纂》十二卷,张德坚总纂。所记起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秋,虽曰迄于1855年8月(咸丰五年七月),但实及于1856年。次年有节本付刻。全本迟至1932年由盋山精舍石印发行。在此书之前或与此书同时,已有若干种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如成书于1853年的陈徽言《武昌纪事》,成书于1854年的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汪堃《盾鼻随闻录》,周邦福《蒙难述钞》,成书于1856年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等。由洪仁玕口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著录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即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也在1854年于香港出版英文本。但这些记述,大都是作者的见闻或经历,虽有史料价值却不属于研究性的著述。《贼情汇纂》则受曾国藩之命、专为收集太平军情以供战争需要,编纂中又“广搜博采,多收而严覈之,闻自何人,见自何处,更一一详注之。删所诬,存其实”,作了一定程度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并采取按专题分类编排方法,条理清晰、检索便捷,成为一部具有初级研究性的资料汇编,开了清政府探索太平天国的先河。);如从20世纪初年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算起(注:《太平天国战史》,刘成禺(汉公)编著,1904年由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序文称其“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显然,此书成为革命派吹倡反清的宣传品。继此书之后,黄世仲(小配)撰《洪秀全演义》,摭拾太平天国遗事轶闻,仿《三国演义》体例,都三十万字,先后刊于香港出版之《有所谓报》及《少年报》,1908年出版单行本,书出后,风行海内外,对反清革命思想传播起过良好的作用。),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大体上看,20世纪以前是骂的多。这是因为清王朝把太平天国视为“犯上作乱”的“贼匪”,危及朝廷的“腹心大患”,所以一切公私著述、文书奏报,无不竭尽咒骂贬斥之能事。诚然,在有些外国传教士的著述、外国人写的游记、乃至一些地主文人的记述中,对太平军军纪、太平天国的若干措施或规定,说过好话、有过褒扬(注:外国传教士的著述,可参见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以上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太平天国》第六册),以及裨治文《太平天国的政治与宗教》(刊《大风》92期、另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外事考》第838-842页),艾约瑟、杨笃信、花牧师、赫威尔、慕维廉、麦都思、史美士、丁韪良等人的报告、评论、专著、通信等(均见《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宗教考》第1929-1973页)。 外国人写的游记,以吴士礼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及富礼赐《天京游记》为最著名(此两种均由简又文译成中文,刊于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第105-156页)此外还有英国翻译官麦迪乐访问天京后于1855年10月1日在《泰晤士报》发表对中国内战的意见以及所著《中国人及其革命》一书中论及太平天国对外人的态度;英人施嘉士《在华十二年》,麦高文在《华北先驱》1856年12月13日发表的通讯等(均见《典制通考》中册:《外事考》第842-848页;下册:《宗教考》第2000-2004页)。
地主文人记述中,对太平军多为贬斥咒骂,但也偶有对军纪赞扬的话,如陈徽言《武昌纪事》称太平军攻占武昌曾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又记太平军有人闯入女馆行奸,“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类似称颂太平军禁奸淫的还有汪士铎《乙丙日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周邦福《蒙难杂钞》等。而与各私家记载称太平军为粤匪、发逆、长毛之类不同,行文中始终称其为粤军、粤兵、太平军的,是李汝昭《镜山野史》,此书将洪杨起事,断为官吏贪暴“民冤莫伸”;上下相蒙,“理数应乱”;认为官兵尾随追堵外,“别无他策”,一套乖张举动,完全是“上讨朝庭封赏,下索百姓捐资,名为忠君,实以欺君,名为保民,实以虐民耳。”洪杨起事,“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但是“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但无论在数量上、影响上都不足以改变咒骂贬斥的主流。
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因反清需要,借助太平天国历史吹倡反满。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被视作种族革命的英雄人物,讴歌赞颂,甚至不惜伪造史料以“供激发民气之用”(注:见柳亚子批校《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此书为残山剩水楼主人著,1906年在上海出版。柳亚子称:“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25首。自答曾国藩5首见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20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时讲授沪上,天梅为予言,将撰写翼王诗膺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并及叙跋诸文。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感动。”柳亚子明指此书之20首为高天梅伪托石达开而作。另5首,经考证亦非石达开所作,系革命党人黄世仲所杜撰(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434页)。)。太平天国从此被肯定、张扬。民国时期,太平天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整理、考订、鉴别史料的工作上(注:参见祁龙威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又,祁教授此书中《简又文评传》、《郭廷以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贡献》、《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料学》、《罗先生赞》诸篇,均对民国时期太平天国在资料、著述方面的研究工作有详实的论述。其后,祁龙威教授又在茅家琦教授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三卷本,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导言》中,撰写了第二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概述》,从印书、文书、文物三方面,全面系统翔实地论述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140年间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的辑佚、鉴别、整理、出版情况。);从出版的论著看,褒扬的势头不减。
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进入崭新阶段,成绩斐然、专家辈出(注:50年来,太平天国研究的成绩不容抹杀,一是整理出版了大量资料,二是发表了大量研究专著,三是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四是建立了一批博物馆、展览中心和纪念馆所。所有这一切,不仅使近代中国这场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说家喻户晓,而且使太平天国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成为最为热门的一个分支领域,并且日益走出国门,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参见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导论》第一节《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概况》和第三节《太平天国遗迹遗址概况》)。)。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无可回避的。举其大要,一是预设了它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性质,由是出现了评价过高、歌颂过烈的趋向;二是把宗教神学政治化,由是导致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阐释。
前一点,涉及许多理论问题,诸如什么是封建?什么是反封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能不能反封建?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农民革命?暴力与革命是不是同义语?等等。正因为对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又以先验的预设结论为出发点与归宿,才出现对这场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意义、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过高的评价,对它的领导人大事歌颂。后一点则是前者制约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它的反封建革命的性质,必然要从洪秀全的宗教活动中挖掘出革命的内容,从他的宗教宣传品中引伸出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思想,并把这些望文生义的内容牵强附会地拼凑成农民革命的“理论纲领”。
几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规范性话语,扼要地说: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前后坚持14年,转战中国17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上百万农民参加了革命战争。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到底,宁死不屈。他们的革命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参见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具体地说: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性质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目标是反对封建剥削者和封建压迫者,由于革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除了担当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外,已经担当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革命理论是体现在洪秀全所写宗教作品中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思想;革命纲领是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天朝田亩制度》;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镇压,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注:这些规范性话语中的性质、目标、革命纲领、失败原因等内容,都可在上揭《人民日报》社论中看到。),如此等等。还可以列举一些已成共识的规范性话语,但仅上述所举就已不难体味出语境的要旨是什么了。如果把形成这种话语系统的历史背景即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考察,就更能理解太平天国何以被抬到空前高度讴歌颂扬的原因。
(二)
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研究,不是没有争论。争论些什么问题呢?从当时发表的“研究述评”来看,主要是关于革命性质的讨论。有十来种不同说法,有称之为“单纯农民革命”,有认为是“市民革命”,有的则主张“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革命”等等。虽然提法各有不同,但谁都没有对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之说提出疑问。正如述评所指出:“这些说法相互间有的名同实异,有的名异实同,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大异小同,彼此交错,情况极为复杂。但是,提法上尽管有很多出入,有一点基本上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太平天国首先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是一次尖锐的阶级搏斗。新中国的历史家们强调指出这一点,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中学家们的所谓太平天国不是阶级斗争等各色各样的诬蔑与歪曲。”(注:见靳一舟《太平天国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另见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上册,第144-145页。)很明显,阶级斗争的理论支配和影响着太平天国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当然还有其它问题的评论,例如关于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对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关于建都天京的战略得失、关于太平天国起义为何在广西爆发等等(注:参见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导言”:第一节《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概况》,上册第10-14页。),但基本上都围绕着反封建的革命这个性质展开论证,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制约下进行研究。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容置疑,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也自有传统。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用阶级分析代替一切,往往会忽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容易在研究中造成视野过窄、方法单一的缺陷。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不仅混淆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的区别,而且往往会异化研究者的学术良知和研究成果的学术品格。
即使象太平天国这样一种以阶级矛盾为主要动因的农民起义,在爆发原因方面仍有众多明显的非阶级矛盾的因素如宗教的、民俗的、文化心理的等等,起着程度不等的促媒作用。文革前的研究就是因为只注意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忽视其它原因而显得结论过于单薄枯瘦。太平军固然对地主豪绅无情打击,但同时也使社会其它阶层受到战火冲击。即使在打击地主土豪时,他们既非自觉地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也没有把地租剥削作为封建剥削加以否定,如早在1853年就实行过区域性的“计亩征粮”的政策,允许这一区域内的地主合法存在(注:所谓“计亩征粮”,是太平军西征军在江西时实行的赋税政策。江西南昌地主文人邹树荣在所作《蔼青诗草》中有一首诗提到了当时太平军征收粮食的情况:计亩征粮忧富室(原注: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得钱相搏快游民。吾村前后分三次(原注:吾家一回出谷五十余石,一回出谷三十余石,一回出谷廿石),此举难期苦乐均。见《太平天国史资料》第72页。)。1854年,又全面推行“照旧交粮纳税”(注:“照旧交粮纳税”是1854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上天王洪秀全的“本章”中提出,由洪秀全批准施行的。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式》,《太平天国》丛刊本,第三册,第203页。),在保存原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要地主按成例交纳赋税,即“佃户交租,业主完粮”。如果按规范话语称当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问题称为“农民的根本问题”,那么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难以体现“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更不要说太平军曾多次镇压过农民的抗租斗争了(注:太平军镇压农民抗租,大多出现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福省和安徽皖南地区。记载此事的史料有佚名《平贼纪略》、沈梓《避寇日记》、龚又村《自怡日记》等。)。
问题不是在于能不能把太平天国称之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怎么说都可以。问题在于把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那就成了预设的或先验的原则了。
过分强调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甚至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其负面效应,从“四人帮”利用太平天国研究以售其奸的历史中已昭然若揭,毋用深论。倒是产生这类丑类和亵渎人性的气候与土壤值得痛定思痛、认真分析。其中包括研究者自己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的过程中,不失落自我、不异化人格,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原则和独立的学术品格这样一类问题。这决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种成果的问题,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的普遍性问题。自我异化虽然出自“脱胎换骨”的良好愿望,但同时也是自我保护的实际需要。在一个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环境里,独立的学术研究乃至独立人格的生存空间实在太小,政治权威的意见也就更具有理论张力,更易于为人接受。“四人帮”就是利用毛泽东的片言只语,打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歪曲太平天国历史,大搞影射史学,以图实现他们纂党夺权的阴谋。当戚本禹抛出批判李秀成的所谓学术论文时,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完全不了解文章背后隐藏的杀机。因为他使用的话语、规范、理论和分析模式实在与当时学术界流行的一套有太多的相同。结果,真诚愿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研究工作指导思想的学者,一个个都遭到了“四人帮”的摧残;太平天国研究“走入了死胡同”。
(三)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对“四人帮”御用工具歪曲太平天国历史的种种伎俩,作了拨乱反正的批判,这对太平天国研究解放思想,冲破人为设置的禁区大有裨益。以1979年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为起点(注: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也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260位代表参加会议,英、美、日、加、比、西德、澳大利亚等7国学者参加。共提交论文217篇。会后由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选出45篇,编成《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1-3册出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盛会,对尔后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太平天国研究再度繁荣。与文革前研究工作分散而不聚合的状况迥异的是,新一轮的研究热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各地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为中心吸聚当地研究者,并逐步形成若干为学术界认同的区域研究中心(注:比较著名的有1978年成立的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79年成立的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80年成立的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84年成立的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除学会外,1978年南京大学成立了由茅家琦教授领衔的全国高校第一个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然后,江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也先后成立了研究室。北京、南京、广州、桂平、重庆等地日渐成为重要的研究中心。),既发挥研究者个人特长,又适当协调、组织研究课题;二是以若干研究会领衔发起纪念性学术讨论会,邀请海内外专家对会议设定的主题共同讨论,以促进和深化研究(注:自1979年南京会议后,每逢金田起义(1851)、建都南京(1853年)的纪念年份,都有大小不一的区域性或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其中1981年的两广会议、1983年的第二次南京会议、1986年第二次两广会议和1991年的茂名会议等均堪称规模盛大的全国性会议。此外,四川石棉、江苏苏州、河北石家庄、浙江金华等地都召开过区域性会议。详情可参见《1978-1985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概况》,陕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6页《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介绍》。)。这两个特点,特别是第二点,成为尔后太平天国研究的常态,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会议的与会论文或在会议中受到启发后再研究的结果(注:参见同上书第52-58页《太平天国史著作介绍》中的《论文集》项。)。
新一轮的太平天国研究热潮,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研究视野的拓展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都超越了文革前。从数量说,自1978-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总字数超过文革前17年的总和;发表论文2000余篇,比文革前超过一倍;出版著作70余种,超过文革前60余种的总和(注:见同上书第8页。)。
从研究视野说,这一期间的学术界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开掘了不少新课题,如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地区的土客关系研究、太平天国社会风情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研究、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研究、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太平天国钱币研究等等(注:参见夏春涛《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特别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丛书,在编委会确定的“编得全一点,新一点,深一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方针下,已经出版了《太平天国开国史》、《太平天国经济史》、《太平天国军事史》、《太平天国与列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太平天国职官志》、《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等专著,代表了20世纪各自研究领域的水平。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四卷本和同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茅家琦教授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三卷本,标志了太平天国历史整合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称得上是世纪之作。特别是罗先生的大著,时人誉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注:此语见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从研究方法说,新一轮的太平天国研究,在使用历史学方法作政治史研究的同时,还尝试采取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以及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钱币学、刑法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太平天国的不同侧面,从而使太平天国的历史内容日见丰满。
有关新一轮研究主要的争论问题和取得的成绩,时贤已有所评论(注:参见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导言”第一节第二目《建国以来国内研究述评》,上册,第19-30页;另见上揭《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发表的夏春涛述评文章。),无需再赘。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和洪秀全评价的讨论,表现了学术界在解放思想的鼓舞下,冲破研究禁区的最初尝试。一些学者根据确凿的史实,指出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实质,并描述了它的封建化表现,论述了它的封建化过程,对以往认为是革命政权的传统说法,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注:见孙祚民《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由此,对洪秀全的皇权思想和专制措施进行了剖析和重新评价(注:张寄谦《论洪秀全》,《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还是皇权主义?》,均见沈嘉荣著《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重庆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一场讨论,后因研究领域的扩大而趋于冷寂。其间,虽仍有人对美化洪秀全思想提出不同看法(注:王庆成《论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研究》1979年第8-9期;祁龙威《洪仁玕与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二册;孙祚民《批判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中州学刊》1981年第1期。),对太平天国战争后果作过不同于以往歌颂赞美的评估(注:《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但研究的主流仍是坚持阶级斗争、歌颂农民战争、美化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
一个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的现象是:为什么新一轮的太平天国研究热,在“一哄而起”之后冷寂了下来,连“原先主攻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者也纷纷转移方向了”(注:此话出自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这与太平天国史研究起点高、研究难度大固然有关,恐怕还和研究环境的变化和研究规范的老化更有关系。当一个社会处在经济、文化乃至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急遽转轨时,文化心态包括研究情趣也随之而发生重大改变。闲适的纯学术研究往往经不起功利式的社会效应冲击;而对研究规范陈旧、史学功能与社会现实需要脱节的学科或领域,势必为急速转轨的社会选择所冷漠、淡化乃至抛弃,这是被各类学术史、特别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要求生存要求发展只有从观念上、方法上加以变革。以史学领域为例,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冷落沉寂,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扩而大之,历史学当前的不景气,难道不是社会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研究情趣的变化表现出来)在起作用,不是学科自身存在问题(例如观念老化、方法落后、话语陈旧、功能薄弱等等)所致吗?太平天国研究如果仍是用那一套规范性的理念和话语翻来覆去地做文章,那么被社会冷漠自在情理之中。
(四)
过分地美化农民战争,美化农民领袖,势必导致丑化它的对立面。自从20世纪初年革命派肥太平天国作为反清武器以来,就一直没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清王朝和湘淮军。例如大力歌颂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措施,无视战乱造成中国社会特别是江南社会大破坏的严重后果,甚至以美化太平军纪来批判清军的烧杀抢掠,把社会破坏的责任完全推到清王朝身上;无根据地夸大这场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把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太平天国革命为资本主义产生扫平了道路的结果,完全否认清王朝同样具有求强求富的需求和应变能力;为了美化洪秀全的革命思想,无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摧残,反而把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军“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等的揭露,批为“封建卫道士”;把湘淮军及其统帅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概骂倒,忽视湘淮军对清军军制、饷制等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在近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忽视曾、李等人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此等等。结果,清王朝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不但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研究得十分肤浅、薄弱,整体上显得模糊不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清王朝和湘淮军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太平天国研究热点逐步转向这一薄弱方面,出版了一批有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传记资料、文集和研究著作,重版和新版了有关湘淮军的专著。但毋用讳言,由于主流思想没有太多的质的变化,研究中常可发现简单化、片面性的缺点。
由此可见,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了某种需要而歌颂农民战争、美化农民领袖,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新一轮的太平天国研究热中有了削弱,有所改观,但并没有消除,仍是研究中的主流理念。
令人感慨的是,对这种现象大声说“不”的,竟然不是同行学人,而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潘先生近年来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余篇有关太平天国的学术随笔,最近又以《太平杂说》为题,结集出版(注:《太平杂说》,潘旭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书收入作者历年发表的35篇“谈话太平军”的文章,书后附有王彬彬、杨乃济所写的两篇读后感和评论。)。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尖锐辛辣的文字,对太平天国若干重要人物和史事,作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成说的新解,读后感到耳目一新、心智开张。请看作者对太平宗教的分析:“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注:见《其兴也勃》,《太平杂说》第59页。又:以下所举略去篇名,仅注书名、页码。)作者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君权和神权相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体制(注:均见《太平杂说》,第11页。),这种“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注:均见《太平杂说》,第73页。)
对于洪秀全,作者评论说:“他不是‘匪’,不是‘贼’,而是一个造反得逞的农村小知识者,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目光短浅、胸襟偏狭、性格固执、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如果中国皇帝分上中下三品,这个准皇帝理所当然归于下品。然而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致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误。”(注:均见《太平杂说》,第74页。)
作者认为“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注:均见《太平杂说》,第14页。)据此,作者呼吁要对农民造反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认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注:均见《太平杂说》,第17页。)
我不敢说体现在《太平杂说》中的观点、见解、分析、评论,都能得到同行学者的认同;我个人对潘先生的若干见解如不应称太平天国而应称太平军的“正名”说等,也有不同看法。但是,只要不讳疾忌医、不固步自封,保持一种开放式的态度,把学术作为求真知的“天下之公器”,那么就会对原有的成说、结论有再思考、再研究的必要。看来,要改变目前太平天国研究萧条冷寂的局面,除了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研究课题要拓展、研究工作要精耕细作外,还真需要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史。潘先生说得好:“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欲说还休,胎死腹中。”(注:《太平杂说》:《前言》,见该书第3页。)中国有句老话:旁观者清。隔行论史的可贵,就在于有清醒的头脑和求真的执着。
结论是明摆着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使太平天国研究走出低谷。
[收稿日期] 2000-7-25
标签:洪秀全论文; 太平军论文; 农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太平军北伐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