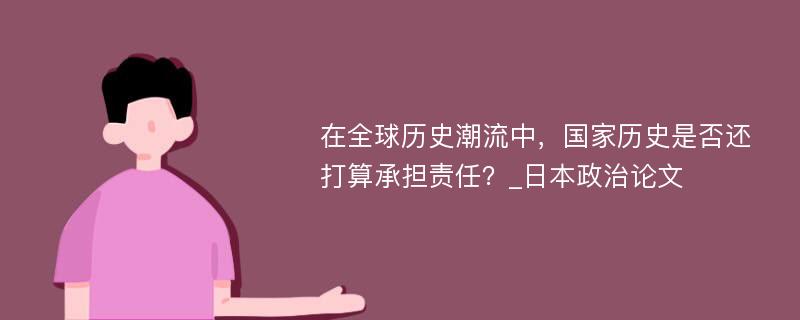
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别史還有意義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流论文,在全球论文,中國别史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2011)春天到美國,先是與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研究南美的教授Jeremy Adelman見面,他談到他們集體撰寫的全球史教科書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A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幾天後,又與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研究非洲的教授Jean M.Allman見面,她也談到從女性立場以及從非洲角度出發的全球史,她表示,現在撰寫全球史的一個目標是“去美國(歐洲)中心”。
全球史仿佛是歷史研究領域的大潮流①。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曾經指出,“1945年之後,世界已經進入了全球一體化的新階段”,因此他倡導一種“全球的歷史觀”②。這種注重全球視野的歷史觀念,一方面來自二戰以後西方歷史學的新思路,比如湯因比(Arnord J.Toynbee,1889-1975)《歷史研究》中觀察全球文明變遷的歷史觀念,這種文明史觀確立了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unit)應該是“文明”而不是“國家”,應該是各種文明在全球的盛衰與聯系③。另一方面來自近二三十年來風行世界的後殖民理論與現代性批判的推波助澜,這種新潮理論既批判近代殖民主義對民族國家的强行劃分,又關注全球化或者現代化之後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的負面影響,而且還批判歐洲中心(或者美國中心)的歷史觀念。因此,從學術與政治兩方面,把“全球史”推成大潮流。因此,在很多人看來,似乎“國别史”已經成爲陳舊的寫法,而“全球史”則不僅學術新穎,而且政治正確。有人甚至聲稱,全球史的意義是“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則表現爲“‘歷史’没有什麽重要與不重要的分别”④。
可是,我一直懷疑這種説法,歷史如果不能在意義上,區分什麽重要,什麽不重要,那麽,歷史就成爲毫無意義的事件堆垛和人物雜燴,這可能嗎?毫無疑問,當下的“全球史”乃是針對某種自我中心主義立場特别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而來的,其背景是“政治正確”與“後現代”理論,所以,常常樂於宣稱,自己是没有特定立場和特定位置的全球歷史觀察者,可是,這恰恰是把撰寫者放在普遍的“居高臨下”、“全知全覺”的位置,這樣没有“偏見”的全球史是否可能?這成了一個問題。所以,我向Jeremy Adelman教授提出一個問題説,是不是真的有“無偏無倚的全球史”?是否應當有一個“中國眼睛”的“全球史”(Maybe we have to write a New global history from China's eyes?)而我也回應Jean M.Allman教授,“也許美國學者的全球史撰寫,其意義是有意識的淡化美國(歐洲)中心,而中國學界如果要撰寫全球史,恐怕會有意識地把中國多放一些進去”。
其實,全球史的撰寫,由於顧及對“中心”與“邊緣”叙述比重的分配,會遇到一些非常麻煩的困難。困難之一是,全球史是否有很好的章節编排與貫穿脉絡,使它可以真正有效地“涵蓋”足够重大的全球性歷史事件?困難之二是,全球史真的能够做到“全知全能”和“不偏不倚”嗎,它以什麽價值標准來選擇全球史應當書寫的事件、人物、現象?困難之三是,全球史需要區域史和國别史的支持嗎,它如何與區域史、國别史相聯系與相區别?
很多問題真的是繞不過去的。很多力圖寫“全球史”的著作,都曾爲這種問題困惑,也許有人會説,這是因爲“全球史”涉及的人物、事件、現象過於複雜,任何歷史學家都無法全面把握。但更重要的是,這不僅僅是一個“能力”即兼顧各種複雜歷史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眼光”,即站在什麽立場觀看歷史變化的問題。比如,我比較熟悉的愛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名的三卷本《世界宗教理念史》(A Histoy of Religious Ideas),雖然他討論了“從石器時代到埃勒烏西斯神秘宗教”、“從釋迦牟尼到基督宗教的興起”,“從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這是三卷本的題目)這麽廣泛的宗教史現象,但是,却没有包括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的變遷,也没有涉及日本的神道教史與日本國家主義,甚至不涉及天主教的東漸史,這顯然不太吻合東亞歷史學家的看法,但其中却有頗長一章講“西藏宗教”,這顯然是愛里亞德個人的“立場”與“眼光”⑤。
美國近代世界史家L.S.Starvianos曾經提出,世界史要以歷史事件的“世界性”爲取舍標准,即有全球影響的(movements of world wide influence),才可以寫入歷史⑥。這當然很合理,可是,正如每個人觀察面前景物,都有一個立場、視角、背景,因此“遠近高低各不同”一樣,很多歷史撰寫者對同一個世界的歷史現象,都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意義尺度,那麽,什麽才是重要的“世界性的事件”呢?20l0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評論《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 the World)一書時説,如果中國取代美國,成爲世界的主宰力量,那麽,“鄭和下西洋”可能會取代達伽馬和哥倫布,在有關世界的歷史著作中占據重要篇章,一些中國學者爲此很受鼓舞。可是,歐洲的歷史學家對這種歷史論述能够接受嗎?
對於歐洲學者來説,“國别史”的寫作可能與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通過歷史撰寫來塑造國家認同有關,因此,對於他們來説,在後現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超越現代性歷史書寫”是很有颠覆意義的;對於非洲與印度等曾經有過被殖民歷史的國家來説,國别史的寫作無疑是在肯定殖民時代的“國家”,因此,對於他們來説,“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寫作當然天經地義。不過,對於東亞諸國特别是“中國”來説,在重視全球史的同時,也必須强調國别史似乎仍然必要,爲什麽?
原因很簡單,歷史不僅僅是文明史,也應當是政治史。在歷史上,文明之間的彼此聯系與互相影響,與國家之間的政治控制和疆域劃分,其實同時存在。從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來看,無論是國家形成的過程,還是國家對於文化的影響,東亞可能與歐洲很不一樣。第一,東亞缺乏一個可以超越“國家”和“皇權”的普遍宗教(如天主教),作爲共同體内互相溝通與認同的平臺或媒介,因此,分屬各個國家的民眾缺乏在文化上和信仰上互相認同的基礎;第二,雖然中國也曾有魏晋南北朝、蒙古時代、清朝時代的多民族融合,但由於在日本、朝鮮與中國之間,并無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族群遷徙和政權交錯,所以,三國之間疆界、民族、文化界限大體穩定與清晰,那些影響政治、形塑文化、構成認同的重大歷史事件,基本上是由“國家”/“王朝”主導的,國家在形塑政治、宗教、文化上的作用相當大;第三,由於19世紀之前,這一區域缺乏一個超越國家與民族,可以彼此聲氣相通、聯成一體的知識群體(士人),所以,彼此的國家立場相當强烈;第四,雖然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居於宗主國和大皇帝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對於周邊諸國并無全面支配的力量,彼此之間在觀念上有華夷界限(種族),近世以來,各自在漸漸建立思想傳統的主體性(如日本的“國學”、朝鮮的“朱子學”),又在漸漸强化語言的獨立性(諺文或假名),更在漸漸構造歷史的獨立性(神代史、萬世一系與檀君傳説),因此,很難簡單地成爲超越國家的“共同體”,國别對於歷史來説,依然重要。
在東亞歷史中,宋、元之後中國、日本、朝鮮其實已經漸行漸遠,特别是十六、十七世紀以後,三國之間的差異其實越來越大,政治、經濟、文化進程與結果,也相當不同。所以,即使是湯因比、亨廷頓這樣試圖超越“國家”而用“文明”爲歷史單位的學者,當他們討論東亞的時候,要麽看到“遠東文明”(Far Eastern Civilazation)有中國的主干(Main Body)和六世紀以後逐漸獨立的日本分支(Branch),要麽仍然會把東亞的中國和日本看成是兩個文明。
在全球或者東亞歷史叙述潮流中,爲什麽我要特别反過來强調國别史的重要性?
其實,這并不是民族(國家)主義史學的膨脹,而恰恰是對民族(國家)主義史學的警惕。因爲這一提倡中包含着一個意圖,那就是對東亞諸國尤其是古代中國歷史中,國家(政府)權力過度强大、國族(民族)意識過度膨脹的警惕。儘管我們説,這種警惕主要是針對現實中國而言,但是,現實中國的權力高度集中和當下政府過於龐大,自有它的歷史根源,這種歷史根源仍然需要對古代中國歷史進行追溯和清理。
在中國學界,近來曾經有過對“專制”、“王權”、“對建”等概念的討論,這些討論的目的是認識歷史上的“中國”/“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是否與其他“國家”存在差異?從錢穆和蕭公權在1940年代的争論開始,這一争論延續至今。可問題是,如果僅僅停留在“概念”層面進行“正名”,從“理論”上去“辯證”,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真正的結論。所以,我想,人們應當留心中國的這樣幾個歷史現象:
一是宗教與皇權的關係,自從東晋至唐代“沙門不敬王者論”的争論以皇權勝利告終,僧道逐漸由官方管理,儒家忠孝思想與佛教因果報應之説結合,中國宗教無論是佛教、道教還是其他各種宗教,基本上是在皇權控制下(這與日本、歐洲宗教的情况不同)。
二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自從秦代以來國家從封建制轉爲郡縣制,軍隊在唐代以後逐漸從藩鎮收歸中央,文化逐漸從地方差異轉爲同一取向,地方雖然有離心傾向,但是大體上仍然處在同一的狀態(這與日本諸藩與歐洲各國的情况也不同)。
三是中國對外的國際關係,華夷觀念影響的中國獨尊觀念與朝貢體制形塑的自大意識,使得“皇帝”不僅是中國臣民的天子,而且是萬國民衆的共主,這種“天下共主”的意識經由封禪祭天與汾陰祀地等形式,被不斷强化甚至神化。與西洋與東洋比起來,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的觀念,以及“天無二日,國無二主”這樣的傳統,中國的“皇權—國家”對於疆土與臣民的控制更是强大⑦。
四是中國對内的民族關係。歷史上,原本不同的各個種族逐漸混融,特别是到了清代逐漸把滿蒙回藏苗并入版圖,形成衆多民族共同的帝國,并且這個帝國延續到今,使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仍然延續着傳統中國的“帝國記憶”。
比起日本歷史中的“萬世一系”天皇傳説來,表面上,中國歷史并不能由各個王朝“一以貫之”,但是,雖然自古以來中國有分裂時期,但自從秦漢統一形成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權,到唐宋以後文化同一性漸漸確立,到明代重建漢族爲中心的統一王朝,再到大清帝國滿族入關、收编蒙古、改土歸流、平定回部、駐兵西藏定金瓶掣簽,把滿蒙回藏苗漢合爲一個大帝國,奠定現代中國版圖,這個“國家”似乎已經被一個“歷史”所叙述,它并不像後現代理論中説的那樣,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⑧。所以在中國,常常可以聽到“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和“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説起”這樣的話,我們當然覺得這個歷史過於單綫條,也過於漢族王朝中心,不過,是否需要考慮,爲什麽這個“國家”總是被一個“歷史”所叙述?
全球史寫作往往針對的是文明史而不是政治史。也許,很多學者覺得,由於文明與國家并不一定在空間上重叠,所以,不必固執於國别史的研究和寫作。可是,怎樣的一個“全球史”可以去除“國别”而聚焦於“文明”?這種去除了“國家”的“文明史”如何撰寫?有人説,全球史可以像滿天的星鬥或者撞擊的臺球。所謂“滿天的星斗”式的全球史,雖然去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弊病,但仍然是國别史的相加而已;所謂“撞擊的臺球”式的全球史,看起來强調了彼此的交錯與碰撞,但是這種交錯與碰撞中,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什麽産生了後果,什麽最終無聲無息?却很費躊躇。
我贊成全球史的寫作,但不必因噎廢食,把國别史看成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或者無用的歷史叙述方式,特别是在重寫政治史的時候。因爲下面三個原因需要格外重視。(一)在歷史上,由於有的區域,其疆域、民族、文化以及政治相對穩定在一個“國家”/“王朝”/“政府”之下,因此,它仍然是一個自足的“歷史世界”,國别史仍然較容易呈現其歷史狀况與現實特徵。(二)聯系的全球史,在交通阻隔、車馬不便的時代,人口、民族、宗教、文化没有太多聯系,歷史學家很難寫彼此關聯的歷史,只是到了海陸交通發展,文化交錯的空間越大,這種歷史書寫的可能性才會越大,不必一概而論地追逐全球史而忽略國别史。(三)當一個國家現在處在政府力量仍然强大、國家控制相當嚴密、意識形態依舊籠罩的時候,我們仍然要追溯這種傳統、這種觀念、這種制度的來源,這就要求歷史學家不能不注重彼此區别的“國别史”。
當然,我要鄭重説明的是,這個“國别史”的歷史叙述空間雖然是“國家”,但它并不按照現代民族國家來倒推“歷史”,因此,它不一定要像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説的那樣,需要“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⑨,只要這個國别史中的“國家”并不固守一個不變的邊界來叙述故事,也不把“歷史”限制在一個從現代國家逆向追溯出來的邊界之内。比如中國史中的“中國”,我在《宅兹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中已經指出:“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爲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⑩,更何况這個“中國”中的王朝、族群、邊界始終在歷史中交錯與融匯。
所以我想,如果國别史的撰寫者,看到“民族”和“國家”本身的歷史變遷,就不會落入後來的“國家”綁架原先的“歷史”的弊病之中。這樣,國别史的書寫就仍然有意義。
2012年6月修訂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東京召開的“世界史/全球史語境中的區域史”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注釋:
①關於全球史的一些論述,在最近的中國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如朱政惠、胡逢祥编《全球視野下的史學:區域性與國際性》(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中就收録了Hayden White、Georg G.Iggers、Frank Ankersmit、Edoardo Tortarolo等學者對於全球史的立場不盡一致的論文。不過,全球史仍然是最近的潮流,有人説到,美國大學歷史教學“對全球史的重視,可以説是一個特點。過去那種以歐洲史爲中心,以歐洲史代替整個世界歷史的教學方式受到了批評,從比較重視微觀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情况,回到研究世界歷史的軌道上。”(王晴佳《中美大學教育體驗與比較》6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②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势》(楊豫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243頁。参看張廣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論與實踐》,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導論》(張廣勇中譯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卷首,9-10頁。
③後來亨廷頓(Samuel P.He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即與這種文明史觀念有關。
④楊念群《從世界史到全球史》引述菲利普·費爾南德兹—阿邁斯托编《世界:一部歷史》(葉建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中語,《讀書》2011年4期,47頁。
⑤愛里亞德(Mircea Eliade)的三卷本《世界宗教理念史》(A Histoy of Religious Ideas,英文本,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日譯本《世界宗教史》,島田裕己、柴田史子譯,築摩書房,東京,1991,1992。中文本,吴静宜、陳錦書等譯,臺北:商周出版,2001。
⑥L.S.Starvianos:The World to 1500:A Globar History,New York,1975; 2nd ed,PP4-5.
⑦這些歷史現象均可以與歐洲和東亞之日本、朝鮮對比,顯然情况與中國不同,宗教(如天主教、佛教)在古代日本或歐洲的地位較古代中國要高,地方(或諸侯、國王、将軍)的力量在古代歐洲或日本也比中國要强,官員或豪强對國王(或皇帝)的制約,古代歐洲與日本也較中國爲大。
⑧關於想象的共同體,参看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中譯本,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9)。
⑨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憲明中譯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⑩《宅兹中國》31頁,中華書局,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