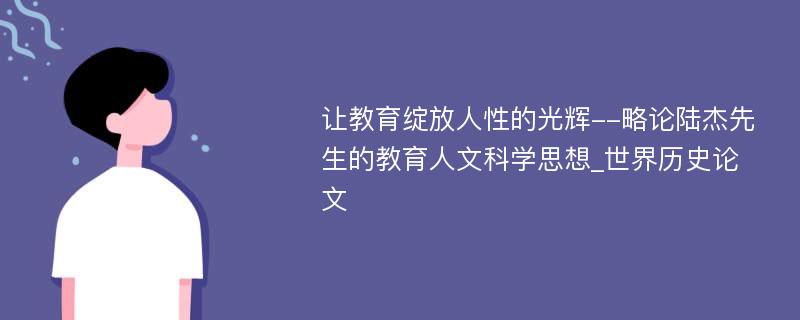
让教育绽放人性的光辉——鲁洁先生教育人学思想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辉论文,人学论文,人性论文,思想论文,鲁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2-0017-07
鲁洁先生是国内教育理论界既具有思想睿智、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理论家。理解“人”,从“人”出发,认识教育,实践教育,构成了鲁洁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的中轴。“教育就要使人成为人”,这是先生最常说的话,在我看来也是先生思想的核心和根基。
在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时,先生回顾自己在南京师范大学55载的工作和生活,深有感慨地说:“对于一个从事教育学专业的人来说,真正让我体悟到教育真义的,也许不是书本,而是她(他)们这些萦绕于心的生命。”[1]。
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的是,鲁洁先生对人的关注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因此她被国际知名比较教育学家、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先生誉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她站在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人学,并在21世纪中国学校的道德教育中加以实践。
理解鲁洁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首先要理解她的人学思想,理解她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认识。因为在她看来,教育面对的是人,教育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教育学是成人之学。人是教育的核心,是构建教育理论的关键点。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学思想
1.基于实践唯物主义对人性的解读
“人是什么?”是哲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其认识各不相同。但大致看来,有两种思路:一是从神的观点理解“人”,把人看作一个充满自由的绝对精神,成为一个“神人”。另一种思路则相反,它以物的观点来看待人,驱逐神圣性,还原人的自然性。
鲁洁先生批判了“神化”和“物化”的人性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看待人。[2]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实践性。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对象化的实践看作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生活方式。人通过实践展现和丰富其人性,实践的方式就是对于给定性(包括自然和自身)的否定与扬弃,在于对人自身和人的世界的创造和再创造。
鲁洁先生接受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认为人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不断地变革世界,进而也变革自身。变革自身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应然”对“实然”的否定。她进而揭示了人的双重性:实然与应然。她指出,“承认人是一种实然的存在,也即是承认人是现实的,可感的对象,他不是虚幻的,超验的,一切对人的认识都必须从这里出发。但是,我们对人性的把握却又不能到此止步,还必须承认,作为人,他总是要不断地从这种可感的现实中‘腾飞’,超越种种给定性,实现自己所追寻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确证。人总是存在于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否定性的动态过程之中。”[3]
对于人的两重性,鲁洁先生更强调在实然性基础上的应然性。因为应然代表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代表着人的价值追求和意义,意味着一个人要不断地超越。她的许多教育论述,尤其她强调要教育成为“一个意义的世界”、“行走在意义之中”,走向“超越性的存在”,实现“人的自我超越”,这些都是基于她提出的人的超越性。
2.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认识
鲁洁先生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分析,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的历史发展观。鲁洁先生认为,社会条件构成了人生存的历史依据。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增加了各种信息知识与文化共享的可能。再次,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把人们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4]
鲁洁先生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尤其是以广泛的交往为特征的社会条件的出现,要求我们将“世界历史的个人”的生长发展作为发展目标,努力促进当代人的转型。她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认为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格转型中尤为重要。[4]
在思维方式方面,鲁洁先生指出,当今的实践活动决不是单凭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所能把握得了的,只有通过共同主体的共同认识活动才得以比较充分地把握。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个体的认知思维能力,充分挖掘他们认知思维的潜能;另一方面,要增加思维的开放性,每个个体要善于使自己向他人、向社会、向整个人类开放,通过多极、多重主体之间认识上的互动,自主地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的认知结构。这个时代的思维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在价值取向方面,鲁洁先生站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她认为,个体固然有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但人作为社会的生物,其内存于社会之中,因此,他必须有与对他人共在的价值的肯定,个体的生活必然具有社会生活的特征。“双重规定性是价值主体的存在形式”。必须辩证地看待个体和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既强调个体的价值,也强调社会的、类的生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的价值分析,也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的本性不是固定的、抽象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历史的实践赋予当代人“共在”、“共生”的人格,这种人格建立在自我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但又超越了单子式的个人,它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完整人格、人性,赋予独立人格以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我们的教育考察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时代需要的发展中的人,在当代就表现为——世界历史的人。这是鲁洁先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人的当代阐释。
3.立足于教育视界的人性观:现实的人
鲁洁先生秉承她对于人性的分析,明确地提出教育所面对的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具体的、通过知觉实际被给予的,能够在经验中观察到的‘现实的人’”[5]。教育所面对的不是由符号、图像、逻辑所构成的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现实的、丰富的、具体的存在;不是反映着固定不变的共同人性的“类存在物”,也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现实的“唯一者”。教育所面对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但又是具有共同性、社会性的人。鲁洁先生指出了“现实的人”的两个重要特质:[5]
第一,现实的人表现为“承载生命的个体存在”。他不仅有着个体的可感的肉体生命,而且有着个性化生命。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我”,都与众不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化的个体”。相对于“类”的普遍存在和整体化的社会而言,每个个性化的个体都可以理解为一种“例外”。
第二,现实的人表现为“现实单个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特征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是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中的人,也即社会的人,是和社会、他人不能须臾相分离的人。社会关系不只是一个人生活的外在环境,人还要把他人、社会纳入于自己的本质之中,作为孕育、生成他的特定社会关系也就构成了他的人格要素。
这就是现实的人,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既具有丰富的个性,又有着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统一关系的人。
二、对教育无“人”的深层揭示与反思
正是因为鲁洁先生坚持教育是“人”的教育,当代教育是“现实人”的教育,因此,她从多个角度反思和批判了现实中无“人”的教育。
在《教育的原点:育人》中,她以“改嫁了的教育”揭示了教育的工具化现象。她结合中国教育的发展,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的“政治化”和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经济化”现象——教育在迎合政治斗争、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中丧失了自身,忘掉了它本来的对象“人”,教育成为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工具,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被无限放大,超越了它合理的边界。教育所要满足的不是人之发展需要,所遵行的不是教育自身的规律,而只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市场功利的需要,在较多的情况下,人们是在用政治和市场的逻辑来操纵教育。
在《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中,她批判了当代教育在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只教人去追逐、适应、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给人“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却放弃了“为何而生”思考,不能让人从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6]这种人沉迷于物质生活之中而丧失精神生活,只有现实的打算与计较而缺乏人生的追求与彻悟,失去生活的理想与意义。人性为技术与物质所吞没,成为物质的贪婪狂和技术的奴隶,忘却了自己的灵魂,成为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只有理性而无人性的“单向度”的人,使当代人发展出“物质巨子、精神侏儒”的畸形人格。
鲁洁先生指出,现存教育的悲剧是它从根本上放弃了培养超越性存在的期待,它只是把学生紧紧地捆绑在“应试教育”、“升学教育”等等的现存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行为之中,迫使他们去“适应”种种不合理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病态的教育。因为真正的教育是启蒙人的意识,启明人的心智,“教育的精神就是超越,就是创造,而现在的教育却正反其道而行之。”[7]鲁洁先生对适应性教育的批判,是因为她坚信,人应该成为一种超越性存在,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断地进行创造,过上更好、更值得过的善的生活。
在鲁洁先生看来,人是应然的存在,他应该追求意义和价值,但我们的教育过于追求理性,因而“失掉了一半的人性,也失掉了一半的教育”。鲁洁先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实证思维的作用下,现代人成为“被自然情欲所操纵的人,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人,丧失了生命激情的人。”[3]建立在这种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教育实践,也只能将人培养成为整个自然、社会因果链条中的一个被动的环节。
鲁洁先生深刻反思了教育中根深蒂固却不以为然的培养“知识人”的信念。她说,这一信条的人性设定是把知识、求知看作是人的惟一规定性,它颠倒了知识与生活的关系。由此,知识人的知识也就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知识观的主宰下,知识人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缺失的世界。这种教育同样是不完全的教育,它使人失去了意义。而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的生活是寻求意义的生活,他总要对他的现实生活做出反思,去追寻现实存在的各种意义。而知识的教育,尤其是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上的知识教育,其实早已将意义排除在外。这就是鲁洁先生所说的,“在一个科学知识称霸的世界中,各种意义的追寻都会成为无意义。”[8]
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的是,鲁洁先生对教育无“人”的分析并不是在一种抽象的人性观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和历史立场上。
第一,从社会发展来看,无“人”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鲁洁先生称之为“世纪的分裂症”。她说,既要看到20世纪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但还必须看到20世纪存在的问题:战争频繁、人类家园破坏、腐败堕落泛滥、人类精神颓废。“20世纪的一切都说明人类患下了‘分裂症’。在物质方面人类已达到造物主的水平,几乎已经无所不能,可以无所不为;但是在精神和道德发育方面,在自我认识、自我把握等方面,却是如此的发育不良,水平低劣。”[9]鲁洁先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揭示了人类无视生命意义和价值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唤醒人类对人自身的重视,对人类价值的重视。
第二,从价值取向上反思机械的社会哲学观。社会如此无视人的价值,除了时代发展的外在使然,还有更深刻的思想渊源。鲁洁先生指出,“从思想观念上来考察,则可以从中发现:一种建立在抽象社会观基础之上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5]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实践的观点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看作外在于人的实体存在,它只能塑造人,而人不能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因此也就成为无人的自然运动,其发展只是由机械因果决定的自然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在这种社会哲学看来,只有社会的存在,没有个人的存在,个人是社会的附属物,而不是社会的主体。
第三,从教育自身来反思,主要是科学的知识观,使教育驻足于抽象的理性世界,远离人的意义和生活。无可否认,知识在当今学校教育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离开知识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固然主要,但知识不是唯一的。当今的教育,一方面把知识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成为教育的唯一追求而失去了其他;另一方面,更在于其知识观上,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排斥了意义的价值。因为在科学的视野中,只有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知识才是知识,知识是由客观事物本身决定的,与认识主体无关,因此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价值无涉的。
人是一种意义的存在,意义是人的本质规定,但知识恰恰排斥了意义,因此,也分裂了人性,排斥了饱含意义的人的生活。科学知识的教学成为外在于人的理性的抽象,也必然脱离于生活。维特根斯坦早已说过,即使一切科学问题都能解答,但依然触及不到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意义的存在,而不是理性的抽象。
三、回归人性的教育理念
学习鲁洁先生的论著,可以看出,先生一直把人作为教育的核心,坚持教育的人本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场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中,鲁洁先生就提出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人性,认识教育,构建回归人性的教育理论。
传统社会哲学中无“人”,要回归人的教育,社会哲学的转变是前提,这就是要从机械的、无人的社会观转变到“人的在场”。鲁洁先生借助马克思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体人存在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0]24这句话,指出“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本身就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切社会的变化不是社会规律的自行运动,它只能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和动力,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一切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在:它为人的活动的开展,为人的生活的提高和完善,为人的生命潜能充分展现,为人的诸种特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等的普遍发挥提供条件。它以人的生成和完善为其使命和目的。”[5]只有社会哲学的转变,使社会成为“人在场”的社会,人创造的社会,讨论教育才不至于走西方抽象人性观的老路,也才能使教育真正归属于人,使“育人”真正成为教育的原点。
1.教育的本质:人的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
虽然鲁洁先生198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活动”,但如何培养,在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一书中,她把教育定义为“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这一定义后来一度成为“经典”的教育定义,但这一定义最大问题是把受教育者看作被动的客体,教育过程成为教育者施加外部影响、受教育者被动接受的过程。鲁洁先生在学术上勇于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他在1998年发表的《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从实践论的角度,站在受教育者是主体的立场上,重新阐述了她对教育的新认识。
鲁洁先生区分了两种实践活动,即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后者决不能还原为前者。只有承认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才能够真正把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依附于社会改造的实践。
2.教育目的:培养世界历史的人
鲁洁先生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当代人的“新”观念——世界历史的人。世界历史的人是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恐怖问题等的要求,使人类走出了单子式的“小我”,也放弃了整体的“大我”,力求平衡“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他既是个体,又是社会的;既是国家的公民、民族的一员,又是世界的公民、人类的一员。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既与时代同步,又落后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历时态的矛盾,在当今中国社会却以共时态的形式呈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既要培育个人的独立人格,又要看到西方国家过分张扬的个人主体性所出现的恶果,所以,中国的教育要超越个人主义,培养共生的理念,引导个人主义走向成熟和完善。鲁洁先生在《转型期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选择》中明确提出,转型期的中国道德教育要培养独立人格。“这种独立人格超越了个人主义的单子式独立人格,是一种共在型独立人格。”这种共在型独立人格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它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其二,这种独立性是以承认他人的独立性,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为其规定性的,正是在这种普遍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其三,共生性是一种新的人的结合关系,它既内含着独特性、多样性的个体价值,同样也显示当代人在价值上的普遍相关性;其四,这种共生性也不是追求完全的同质性,它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11]
培养共生性人格,使个体成为一种共生性存在,是当代教育的目的。鲁洁先生站在教育的立场,认为教育首先要使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要使学生明确当今的世界和社会又存在着多极主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追求,要承认“自我”和“他者”共在一个“生态圈”之中,其中每一个人既是独特的,对另一个人又是不可或缺的。
共生性人格是世界历史的人的重要人格特质。当今的教育必须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全球的视野,着力培养一代具有共生性人格、能够走进世界历史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
3.教育就是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回归生活”是鲁洁先生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想,她对“为什么回归”、“回归什么样的生活”有不同于前贤的认识。
鲁洁先生对于教育为何回归生活,是基于她对人的意义世界的认识和对当今知识教育、唯理性教育的批判。人的生活不仅需要物质的寄养,更需要意义的追求。因此,人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也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物质世界是客观的、看得见、摸得着,意义世界是主观的、理想的、对美好的生活善的向往和追求。意义世界是人所特有的生活世界,因为人是追寻意义的存在者。失去了意义追求的人,成为只有物质欲求的动物,而非真正的人。人不是不需要物质世界,而是要以意义世界去引导物质世界。教育既以完善人性为己职,就决不可忽视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
但是,当今教育的理性化、知识化倾向,使教育丧失了它的完整性。只教人“何以为生”不教人“为何而生”;只教人去征服自然、占有财富,不教人去敬畏自然、关怀他人。
鲁洁先生在《生活、道德、道德教育》中进而深入地论证到,“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实践性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属性”。[12]教育要走出“知识人”局限,走出唯理性教育的局限,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必须使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使教育成为一个人生活的过程,受教育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过一种更好、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善的生活。
四、鲁洁先生教育人学思想的特点
1.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鲁洁先生在教育人学方面的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哲学。
她说: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13]337因此,她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实践性,是人自己造就了自己,在历史的实践中发展了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完善自身。她纠正对实践的错误理解,提出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区别于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另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把教育的本质归结为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归结为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内核的独立实践活动。
鲁洁先生虽然把人性定位于实践性,但由于实践性是“实践”的,是不断展现的,不是空洞的、固定的,这就使得其区别于很多人本主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立足于历史的实践,她考察当代人的生存条件,揭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世界历史的人,把人置于时代的发展中,而不至于使人变得空洞,缺少时代的内涵,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发展的观点。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魂。鲁洁先生的思想中充满着辩证的思想,例如她对人性的认识,“人性的本质既在现存的实然中,又在超越现存的应然中。存在于上述两重性的否定性的统一之中。”从人的这种实然与应然的两重性结构中,衍生出了一系列相互否定的人性特征,如预成与生成、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等等。但辩证法并不是“中庸”的综合,而是在否定中发展。她说,“人总是存在于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否定性的动态过程之中”,“也正是在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张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3]
2.具有高度的人类的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鲁洁先生的文章多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她对现实的批判,不是拘泥于细节,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人类发展中的问题。如世纪的“精神分裂症”问题、无主体的社会哲学问题、教育的功利化、外在化问题,不仅深刻,而且有气魄、有胆识、有力量。其实,这种反思背后,更是她高度的人类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回顾20世纪的发展历程后,她指出,20世纪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世纪,是一个人类力量无限张扬的世纪,是值得人类自己为之骄傲的世纪。但是,另一方面,20世纪又是一个蒙受不幸和耻辱的世纪,是让人类感到不堪回首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生存家园的惨遭破坏、腐败堕落现象的空前泛滥。她不无忧虑地指出,20世纪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分裂症”,如果人们不把握好自身,没有对世界、对人类的深远智慧和德性的锤炼,那么人们所面临的可能是较物质匮乏更为严重的灭顶之灾。[14]153这种担心是先生研究的动力所在。所以,她是在研究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谈到西方教育的功利化之后,她感叹到“既然历史把一个充满物质主义的世界交给了我们,德育的任务也只能是去超越它!不管这个超越任务是如何艰巨,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个既有先进物质文明又有崇高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5]其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学者,鲁洁先生通常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中国的问题,做出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回答。例如,在回答人的转型时,她指出,处在“人的革命”时代的中国教育必以人的转型为己任。但是,这种转型,特别是价值取向的转型,却处于双重矛盾之中,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很不相同的特殊性。“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个体价值的确认和个体独立人格的培养是我国教育的一项至今远未完成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我们是在整个世界人类发展背景下完成这项任务的。……因而,中国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不可能游离于整个人类发展的逻辑之外,它也必定面临着把人推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使命,这是人类发展的使命。”[4]
3.“人是主体”的核心思想
“人是主体”的内涵,在鲁洁先生的学术思想中主要体现为:
第一,个体发展的主体。她以人的“实然”与“应然”两重性,揭示人的发展过程。人的发展就是要突破它的实然性存在,在他的生存活动中要成为一种自由的存在,要创造出有别于既有的实然的新的实然,要超越其对象物和各种对象性关系,要生产出新的对象物和对象。
第二,社会发展的主体。鲁洁先生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纯自然历史过程,它不是预成的,也不是按照某种单一线路向前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自觉选择和历史创造性构成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人是社会的创造者、历史的剧作者,是人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社会的自然运动。她认为,当今的中国教育之所以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根本的思想渊源就在于无“人”的社会哲学,因此,她强调树立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人是社会的主体。
第三,从主体的角度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人性是实然与应然的否定性统一,是应然对实然的超越,这就从根本上赋予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主体性。教育不仅要向受教育者传授已拥有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具有时代的历史规定性,还要使他们学会不断地超越现实的种种规定性,去追求新的自我、新的世界。
第四,当代教育要培养具有共生性人格的主体。鲁洁先生立足于交往日益充分的当代社会,提出了从单子式的、孤独的个人转向培养具有共生人格的世界历史的人。她强调当代人应该成为共生性存在,“一方面,共生性存在以个体生命存在为其前提,只有结合于个体生命才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存在,才赋予生命以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作为关系性的存在又是诸多个体生命的凝聚,他内在地统整了自我与他我、小我与大我、内在与外在等等人的存在形态。”[16]。
4.生活中人学思想的实践者
鲁洁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她的身上,体现着对学生的爱、对同事的关怀、对集体的热爱。正如先生在2005年辞去全国德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时对国内研究道德教育的同行所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在一个平台上沟通交流不同的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收获。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因为爱。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上,参加这样的团体是很幸运的。在每次会议上都会得到一种推动、鼓励。在道德教育事业的艰难跋涉中,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时常记住先生的话,“教育需要高深的学问、渊博的知识,教育更需要对人的生命真切的关怀,无穷的挚爱!”[1]让先生的人性关怀,在我们的事业中延续吧!
收稿日期:2009-10-12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人性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共生关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