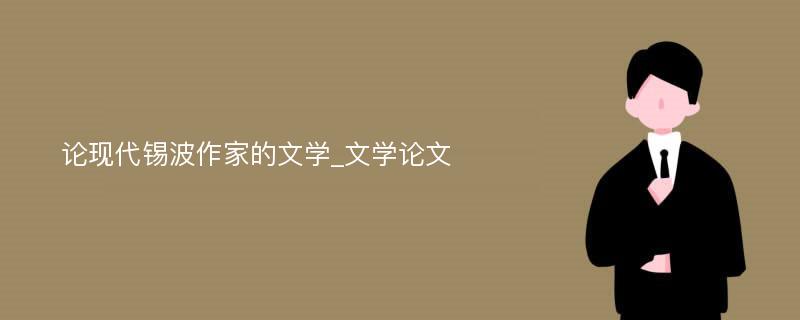
近代锡伯族作家文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锡伯族论文,近代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0)03-0098-06
锡伯族作家文学(亦称创作文学)的发端,因资料所限,只能追溯到清代中后期。清代以前,锡伯族处在蒙古科尔沁、女真统治之下,长期的封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不仅使他们处在极度贫困落后状态,而且抑制了其民族文化的发展。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4千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新疆伊犁,在长期的屯垦戍边、反对分裂、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条件下,以及在偏处一隅的封闭环境中,其创作文学开始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从整体而言,锡伯族创作文学呈现“留守型”文学特点,即其文学创作与民族命运和祖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文学发展史就是民族和边疆的兴衰史。从发展阶段而言,近代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可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第二阶段,民国初年至30年代;第三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锡伯族历史特点是:4千余名锡伯族军民移驻伊犁察布查尔地区,组成军政合一的组织——伊犁锡伯营,全体军民开始肩负屯垦自养、保卫边疆、反对国内分裂势力、抵抗外国殖民侵略的历史重任。因此,这一阶段的创作文学,表现出很浓厚的“留守型”文学特点,即主要表现屯垦戍边、平定国内分裂叛乱、抵抗外来侵略以及对西迁壮举的追忆上,充分表现了锡伯族勇于牺牲民族利益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阶段,有三部作品可资介绍。其一,《辉番卡伦来信》,系书信体散文,用满文创作,译成汉文2500字。作者沃克津,又作倭克津,锡伯营镶白旗(五牛录)人。1824年(18岁)入伍披甲。1849年补放骁骑校拟陪一次,此前,曾巡查边界等出差八次。1851年升任镶白旗骁骑校。1859年任镶白旗防御,此前,巡查边界等又出差两次。1862年补放佐领拟陪一次。《来信》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从信的历史背景分析,反映了锡伯族官兵戍边卫疆的历史活动,其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众所周知,清政府调遣锡伯军民移驻伊犁,主要是从戍边的目的考虑的。锡伯军民立足伊犁伊始,就投入驻守固尔班托海等18处卡伦。此外,由于索伦营官兵不敷调遣,伊犁将军又决定定期自锡伯营调遣官兵,协助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沃克津就是在被调换辉番卡伦一任时写这封信的。《来信》用优美顺畅的文学语言,细致描写了自锡伯营至辉番卡伦沿途自然景致、地理风貌、村落人情,每到一处,对所见所闻又发表议论,畅抒自己的见解。他面对卡伦官兵的恋乡心态和日益松驰的卡伦现状,出于保家卫国的高度责任心,郑重阐述了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敌加强防守卡伦的重要性,并记述了他以身作则整顿辉番卡伦秩序的情况。《来信》是历史的见证。在信中记述的辉番卡伦、齐齐罕、策济等地,在1864年以前均为中国领土,1864年沙俄通过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包括辉番卡伦在内的我国西北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来信》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艺术上也很成功,在锡伯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二,《喀什噶尔之歌》,满文,佚名之作,全诗近千行,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是锡伯族文学史上首部战争叙事长诗。清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张格尔之乱。清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先后调遣伊犁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满等营官兵以及关内增援兵数万人平乱。在战争中,锡伯营数百官兵,在总管额尔古伦
的指挥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喀什噶尔之歌》就是用诗的语言较详细记述了这次平乱战役的全过程,展现了伊犁各营尤其是锡伯营官兵在战争中的进退、胜败、兴奋与苦闷、胆怯与勇敢等等复杂的场面。诗作记述了许多在史料中阙载的史实,因此,其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长期以来,其史料价值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歌》中记述的人物如额尔古伦等生动形象,有血有肉,他们的内心活动如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记述的南疆地名均如实确切,与史料记载无二致。长期以来,《喀什噶尔之歌》被锡伯族群众广为传抄,并当作民间作品来吟唱。其三,《离乡曲》,汉文,诗作,120行,创作于1884年以后,作者锡济尔珲,字笔臣,民间尊称为“锡老大人”,锡伯营正红旗人。1879年由正蓝旗骁骑校升任正黄旗防御。次年,补放佐领拟陪一次。1881年,升任正蓝旗佐领,此前已食俸22年。1883年,被调补伊犁新满营。锡氏自幼好学,到他晚年,更是埋头书斋,博览群籍,潜心修学。他处身清末社会动荡之世,能够适应近代新思想的要求,积极主张发展社会文化事业,提倡接受汉文化,注重新式教育,在他任伊犁将军衙署文案处文案总办期间,招收锡伯族有志青年在身边,教授汉文化,传播其新教育思想。他培养的徒弟,在为发展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传播反封建思想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离乡曲》疑在其任文案总办期间所创作。锡笔臣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秋,他经历了阿古柏之乱、伊犁农民起义以及伊犁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伊犁10年外患、清政府清除内忧外患及新疆建省等历史事件。在伊犁恢复旧秩序的过程中他被任命文案总办,他“居高临下”,忆身后,想未来,强烈的忧国忧族的思想促使他创作了《离乡曲》。诗人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诗中告诫人们:“沧海桑田时变迁,人生不可忘艰难;水有源来木有本,忠孝相传万万年。自从盛京往西移,百有余年到此时;作此一种离乡曲,辛勤传与后人知”。西迁,对锡伯族来说,是改变锡伯族军民命运的事件;西迁之后,锡伯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与新疆的历史更加紧密,国兴我兴,国辱我辱。锡笔臣充分领略这一民族与祖国荣辱与共的现实含义,出于对本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锡伯族西迁的壮举,用诗的语言展现在人们面前,并阐述他的思想认识。因此,《离乡曲》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上述三部作品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特点,也代表和反映了锡伯族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特点。总起来讲,爱国主义是三部作品的主题,也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从这一点讲,这一阶段的锡伯族创作文学,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播和讴歌的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第二阶段,民国初年至30年代。这一阶段的锡伯族文学是由一批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直接推动发展的,而且,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是和本族的民族教育同时发展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曾一度推行“新政”。在新疆,把“兴学”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伊犁,先后设立了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初两等公校、满营义学和女子琼玉学校、武备学堂等。还将伊犁兴文学校改为驻防高初两等学堂。在上述学校,先后有不少锡伯子弟求学。尤其是在武备学堂和驻防高初两等学堂求学者不下数十名。另外,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两批近10名锡伯族青年去俄国托木斯克和阿拉木图留学,眼界得以开阔。这些青年与求学武备学堂、驻防高初两等学堂等学校的青年在锡伯营形成为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新生力量,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次变改。1912年初,在全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推翻清在伊犁的统治,伊犁地区民主主义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在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锡伯营上述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在锡伯营首先掀起了重教育、兴文化的改良运动。约民国二三年间(1913或1914),由常广斋、博孝昌、佟精阿、穆精阿、元宝春、萨拉春、广普、寿林等发起,在伊犁成立了群众性文化团体——“尚学会”。随后锡伯营一、三牛录成立了分会,发展会员。在尚学会的影响下,锡伯营四牛录又成立了“兴学会”。两会的宗旨是开办学校,提倡新教育,鼓励文学创作,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中文学创作作为反封建、争民主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继教育之后活跃起来,相继涌现出了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反对封建愚昧,鼓励青少年入学受教育,提倡禁毒,反对八旗习气,提高妇女地位等。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为:诗歌(含歌谣)、散文、小说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设的学校普遍都采用了新式课本,而这些课本都是锡伯营文人志士自己所编,其内容主要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及译文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已经绝世,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其中《劝学歌》和《别再吸食鸦片烟》等作品,几十年来一直为群众传唱不断。《劝学歌》由锡伯族著名教育家色普希贤于1919年创作。他从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出发,以朗朗上口的歌谣形式,劝诫青少年:“少年时光不再来,努力求学实紧要,只要牢树真决心,任何事情难不倒!”《别再吸
食鸦片烟》由萨拉春创作。他目睹杨增新统治时期锡伯族不少群众沉溺于吸食鸦片的泥坑,生产荒废,精神萎靡不振的惨状,大声疾呼:“家破人亡已够悲惨,亡亲灭族也在眼前。兄弟们呀姐妹们,别再吸食鸦片烟!”30年代他又创作了小说《真正的金子》,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起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适应社会教育客观要求的同时,深深印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在变革社会生活,唤醒人们思想意识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一时期,新疆的社会局势比较复杂,呈现瞬息万变的状态。1928年迪化(今乌鲁木齐)发生“七七政变”,金树仁接替杨增新任新疆省主席,然而面对新疆多事的局面他无能力“扭转乾坤”,经过几年从政,碌碌无功,于1933年被盛世才推翻。盛世才执政初期几年,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颁布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整饬社会、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育的方针,使新疆社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1937年底开始,他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与苏联反目,逐步投靠国民党,数年中新疆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44年随着他的倒台,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目的的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伊犁处在了民族军及其临时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持续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锡伯族创作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锡伯族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爱国主义、唤醒全社会的主题得到高扬,而且知识分子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后第二代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创作队伍的主力,第一代知识分子随着时代的进步,适应客观世界的要求,更新观念,从广泛的角度参与社会生活,其创作领域更加拓宽,思想认识越益深入,作品更是丰富多彩,使锡伯族文化生活呈现多样化。40年代末,第三代知识分子开始成熟起来,在文学创作领域初露锋芒。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不同程度地受到进步文化的熏陶,表现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善于探索的特点,在以后的锡伯族文学艺术领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盛世才主政前期,迪化等地掀起抗日文化宣传,锡伯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点顺应当时的客观要求,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民族口号下,表现出了鲜明的各民族共同性。当时,在迪化各类学校求学的数十名锡伯族学生,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并不断把信息传递到家乡——察布查尔等地。一批热血青年如进太、兴福、荣林、多隆额、德清、佟金昌、吉成、图奇春、仲谦、庆常等发起,在迪化创办了《暑光》期刊,并作为锡伯族进步文化团体“锡(伯)索(伦)满文化促进会”会刊,成为锡伯族师生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园地。安子瑛、图奇春、柏雪木、仲谦、吉成等人创作诗歌、散文、小说、翻译苏联小说、诗歌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值得一提的是,郭基南从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1939年10月安子瑛以“反帝会”的名义推荐他到迪化进茅盾领导的文化干部训练班(简称文干班)学习,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当年底,他开始在《新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一天的生活》、《黄老木匠》、《李掌柜买公债》、《满天星》、《太行山下》、《一场激烈的球战》等散文、小说、话剧、速写。话剧《满天星》不久被察布查尔各校师生排练,在各牛录巡回演出,受到良好的抗日宣传效果。总结这一时期锡伯族的文学创作形式,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锡伯族知识分子充分吸收汉文化以及苏联文学营养,“移植”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而且,文学创作的中心在迪化。从1937年盛世才借所谓“阴谋暴动案”,对异已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清洗。1940-1942年间,其清洗活动变本加厉,先后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留苏学生、知名人士、资产者及共产党人数百名,其中也有锡伯族知识分子、学生如萨拉春、伊敏政、广禄、穆精阿、安子瑛、仲棣华、通宝、图奇春、巴吐沁等数十人,新疆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这时,锡伯族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全疆形势一样,已经全面停止。随着形势的逐渐恶化,迪化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和学生纷纷返回家乡,被盛氏关押的知识分子出狱后也都返回家乡,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心转移到伊犁。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国民党完全控制新疆,三区革命爆发。1945年以后,察布查尔地区出现了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为锡伯族文学艺术创作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迎来了解放前锡伯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
三区革命中后期,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革命领导人,纠正艾力汗吐烈等人的错误路线,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三区革命运动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三区各族文化活动也开始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不仅第二代知识分子仍活跃于文学创作领域,而且第三代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创作中坚,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很多艺术性和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如萨拉春的诗作《明媚的春色》、《老年人和青年人》、《清晨》等;柏雪木的诗作《送瘟神》、《共享园中菜》、《羊拐骨的胜利》、《铜刀行》、《汗腾格里颂》、《素花之歌》、《老妇泪》等;管兴才的诗作《狩猎歌》、《接新娘》、《十二月歌》、《婚礼歌》、《吸大烟的婆娘》等;玖善的诗作《锡伯人的狩猎》、《察布查尔母亲对我们叹息》、《二月初二——初春之夜》、《柯吉阿拜》等;赵令福的叙事长诗《沙枣树下》等。其中《送瘟神》、《汗腾格里颂》、《素花之歌》、《狩猎歌》、《婚礼歌》、《吸大烟的婆娘》等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思想性也很深刻,在锡伯族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此需特别提出的是,1941年郭基南被迫由迪化返回家乡后,开始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创作活动,近10年间,先后创作诗歌、散文、特写、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多部。如诗歌《野火》、《车夫怨》、《祖母泪》、《新生》、《春望》、《同情》、《五一之歌》、《致友人》、《我要弹奏》、《飘扬吧,五星红旗》等;1949年又编选两部锡伯文《诗集》,收入20多位锡伯诗人的作品40余首,由伊犁锡索文化协会出版;散文和杂文《月下闲谈》、《妇女的呼声》、《夜鼠》、《深夜杂感》、《匆匆》等;小说《母亲》、《醉汉》、《委员——选举谁》、《羊的故事》、《唠叨大妈的牛犊》、《鼻子的纠纷》等;报告文学《军民一条心》等;剧本《察布查尔》、《继母》等。在扶持这支创作队伍方面,《伊犁日报》、三区《民主报》、《新生活报》(《察布查尔报》前身)、锡索文化协会等报刊和组织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锡索文化协会是锡伯、索伦(达斡尔族)文化团体,1947年在伊宁成立,萨拉春任会长,在察布查尔、霍城、塔城等地设有分会。其宗旨为发展民族文化。主要活动有:编印锡伯文课本,创办锡伯文《新路报》,鼓励知识分子搞文学艺术创作,帮助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锡伯族的文学创作,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作者队伍基本成熟。在这支队伍中新老结合,新人向老作者吸取营养,继承他们的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老作者随着时代更替,思想更加成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民众的关系更为接近,不断从民间吸收营养,更新观念,基本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其次,新老作家队伍在更加贴近贫苦群众的同时,其作品各有基点。老作家因社会阅历广,作品多从历史的角度挖掘题材,借古喻今、以史讽今、借物喻今成为一大特色。而新作者因从小遭受社会的压迫,理想受到人为抑制,因此,1945年以后在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思想得以解放,思路得到拓宽,深感有了“用武之地”,其作品多从现实角度挖掘题材,单刀直入、活泼明快、题材多样化是其特色。再次,汉族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对新老作者普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作品更加贴近了社会,贴近了贫苦阶层,贴近了现实,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主题更加鲜明。第四,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反映群众生活,反映现实,反映本民族的习俗文化,广泛被群众所接受,很多诗作被谱成曲,在民间广泛传唱,成为男女老幼喜闻爱唱的“民歌”。又如一些移植的剧作,不断被编排演出,成为家喻户晓的精神食粮。这一点是文学作品得以传播、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支点。
新疆锡伯族人创作文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随着锡伯族西迁后屯垦戍边历史的开始而发端。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以其特具的功能发挥了鼓舞人的作用,尤其是在旧中国文化生活及其单调的漫长历史时期,更成为广大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从宏观上考查,各个时期的文学虽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状况,但它们之间承前启后的发展主线是显而易见的。综观三个时期,锡伯族的创作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三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始终体现出锡伯族军民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三爱”精神主题。这是几百年来它始终能够鼓舞锡伯族军民克服因难、奋发向上的魅力所在,也是这些精神产品代代相传的原因所在。(二)三个时期有文学作品,以其浓缩性特点较深刻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现状。从思想性来讲,讴歌什么、鞭挞什么,界限很清楚,旗帜很鲜明,充分反映了锡伯族人民善良憨厚、爱憎分明、精诚如一的民族性格。(三)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均表现出其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正是这一点,才使锡伯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艺苑中放出异彩。(四)锡伯族创作文学越到后期越体现出大众化特色,而其大众化特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得到加强的。大众化是文学艺术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五)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充分吸收了锡伯族民间文学的营养,有时两种文学形式结合得极其紧密,甚至难分难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其一大特色。正是这一点,才使创作文学成为培养其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的关键因素。(六)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充分吸收了汉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后期阶段,吸收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从整体上分析,锡伯族创作文学也有其缺憾,一是绝大部分作品均用锡伯文创作,因此,流传范围狭窄,不少作品因而失传。不少作品译成其他语种需要很大程度的再创作,难以保持其民族特点。二是创作队伍始终不够壮大,各个时期只有少数人在创作舞台上,这一点是锡伯族文学领域很少涌现优秀作品的根源。三是少数人由于缺乏理论修养和社会实践,其作品不仅缺少民族和地方特点,而且模仿别人,也没有自己的个性。四是作品多表现为诗歌形式,这是锡伯族创作文学脆弱性的重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