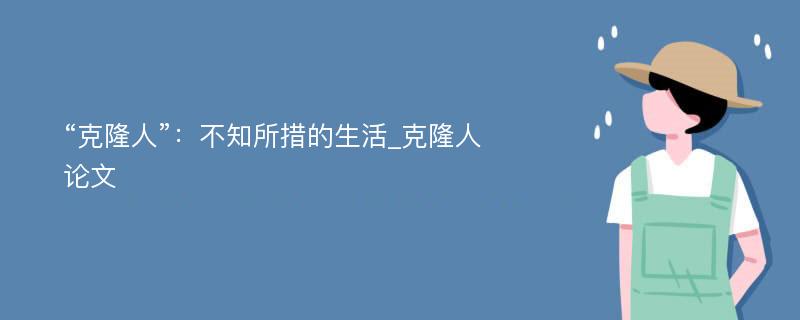
“克隆人”:无所适从的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所适从论文,克隆人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克隆人真的从理论变为现实,第一个“克隆人”的第一声啼哭将真正震惊全人类:其一举一动将挑战人类现有的社会规范,其所思所想将冲击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喜怒哀乐将触及我们的良知和灵魂。暂且撇开克隆人带给现有人类社会的诸多冲击(科技的、法律的、医学的、伦理的、家庭的等等)不论,单从人生价值观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将受到根本性挑战:
挑战之一:“我”的意识——我是谁?
古希腊特尔斐神庙的古老神谕——“认识你自己”,使苏格拉底将哲学方向由自然界努力引向人生伦理。“认识你自己”的巨大召唤亦促使古今中外的无数大哲大智们殚精竭虑。由“人是什么?”到“我是谁?”,这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直到海德格尔仍使其执着不已。他针对康德为解决哲学主要课题而提出的三个问题——如何能知?认识论问题;如何能行?伦理学问题;有何希望?神学问题——认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未为康德所提出,即:何为人?20世纪后期,很多学者认为,在伦理学中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主体性的消失,没有所谓的自我。所以,重新建构主体性则成为20世纪末期的主要任务。可是,当此困难性极大的任务尚未完成之时,“克隆人”的不期而至使“人是什么?”和“我是谁?”得旧疑又添新问。
“人是什么?”的疑问使人类跟自然界相揖别;“我是谁?”的思索使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我”的意识使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性的人,是一个有别于外物、有别于他人的富有鲜明个性的“我”。“我就是我”的意识使人的个性得以张扬。可是,若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克隆人”,他会怎样思索这个问题?当他面对他的原型,他的“上帝”,他不禁会发出疑问:“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我’还是‘他’?”这跟双胞胎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根本不同:双胞胎是父母(他)生的,而“克隆人”是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我)生的。“克隆人”不管在后天环境里如何被塑,但他在心理上永远都逃不出那个“前我”的巨大阴影笼罩,他将被本来尚未彻底解决的“我是谁?”的人生疑问愈益困扰,痛苦不堪。
挑战之二:生死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趋乐避苦,求生畏死是人的天性,所以,生死观成为千百年来人类所苦苦探索的重中之重。中国传统人生观理论,除了佛教比较特殊以外,都是重生轻死的。季路问孔子生死问题,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对死采取了避而不答的态度。自其而后的儒者们都一以贯之地保持重生轻死,乐生入世,视死如视生,生当载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态度,即:生要堂堂正正,死要气概非凡——这已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而道家对生死问题则采取了另一种重生轻死、顺应自然的态度。庄子妻亡,他却鼓盆而歌,成为道家生死观的最佳注脚:以乐观、旷达、幽默的态度力争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和艺术中,人类对生死的态度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现,那就是在风和日丽中歌舞吟咏、赞美人生。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从“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出发,认为人生就是赎罪、净化灵魂、接近上帝、获得永生的过程。而处于上升时期的近代资产阶级朝气蓬勃,在不断的探索和冒险中寻求幸福和快乐,探寻生的意义和人生价值。时至二十世纪,当悲观主义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领域之时,处于迷途的痛苦中的西方人对生死问题格外关注,于是出现了卡谬的“荒诞”,萨特的“晕眩”、“恶心”,海德格尔的“畏”、“烦”、“死”,开始从死的角度去思考生的意义。
由上可以看出,重生轻死乃是诸多生死观中的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而人类为什么如此重生轻死,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人皆有一死,并且人死不能复生。与这种生命有限的悲剧感相对应的,是在生命价值体认方面由悲其无常、短促,辛酸、多挫而进于积极增促生命的价值体现和人生意义的崇高追求。当人类通过各种方式探求长生不死的企图告以失败以后,便发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无奈感叹;“好死不如赖活着”,道出了人类对一次短暂生命的无限依恋和珍爱。这种对有且仅只有一次生命体验和对生命崇高价值性的追求,成为人类积极作为的内在源泉。可是,当你面对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不掺杂任何外人遗传因素的克隆“你”来,你不禁会发出疑问:这是“轮回”呢还是再生?而且,当你或克隆“你”认为生不逢时、命运多难之时,克隆技术的强大背景使选择轻生的困难已不那么困难了:再来一次又如何!?“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曾经豪言今已成真。生(再生)如此容易,死又有何难?——“克隆人”没理由不对世人所谓的“生死大事”淡然处之。
挑战之三:命运观——扼住命运的咽喉?
个人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和社会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微不足道,因此,对冥冥之中支配一生贫富贤愚的神秘力量——命运,真可谓是敬畏交加,心情复杂。自古至今,人类对命运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的,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不可勉,时不可力”,“万事皆由天注定”,宿命论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另一类是积极的,要么“尽人事,听天命”,即承认命运是人力无法抗争的必然趋势,但反对因命运而放弃努力;要么“制天命而用之”,“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屈服”,洋溢着人类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表达了人类战胜命运的自信。而且,此精神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高扬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自信也不断高涨,对命运的藐视和挑战几乎成了现代人的主流命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古人疑问已不成疑问,而成为今人的信条。放牛娃成将军,演员成总统,乳臭小子成世界首富等等诸多事实,使人们对出身命运的看重转向了个人奋斗和自我创造。
可是,此观念对“克隆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在艰难困苦之时仍对未来充满信心,在风雨飘摇之中仍不息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其原因正在于人生的不可预测性。人生的不可预测使人们执着于一条信念:人只要活着,未来就有转机和希望。支撑着我们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传统命运观对“克隆人”意味着的却是无尽的疑虑和困惑:“我的‘前我’为什么要复制我呢?他考虑过会不会使我的人生幸福呢?我的‘前我’会不会前定我的一生呢?面对我的‘前我’,我有可能或者怎样表现我的鲜明个性和创造性呢?为什么我就不能象别人一样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我’呢?这是命吗?”面对诸多困惑,“克隆人”置身于受传统人生价值观支配的主流社会,真可谓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当然,仅从人生价值观来看,克隆人发出的挑战不仅仅只此三类。爱,责任,荣辱,处世,苦乐等等观念都将受到冲击,但上述三类受到的冲击则是内在的并且带有根本性。因为人作为主体,是有思想、意志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存在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能够发挥主体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安排自己的活动,追逐一定的目标,进行改变环境、创造历史的活动。可以说人生既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完全被自然生理规律决定的生存过程,也不是纯精神的、绝对自由的自我实现过程,当然更不是宗教神灵或者拥有造物技术的造物者的创造和恩赐,而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基础上能动的生活过程,所以,人生就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的统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惟其因为是主体,人才不是消极被动的动物,而是积极能动的创造者,是“万物之灵”。正因为如此,才使人拥有尊严,人生富有价值,生活更有意义。
可是,如我们在以上所分析的,“克隆人”的出现却极有可能使人生单调而生活缺乏意义,使人类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对人类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提出严重挑战。克隆人的问题既是一个科技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生命伦理问题,而“克隆人”的身份出现将会引起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创造文明,但也可以十分轻易地毁灭文明,所以,发展某项科学技术不仅仅只是满足人的好奇感,也不能“为了科技而科技”,而要看是不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价值。不然,“克隆人”就会极有可能象核武器一样成为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另一把头悬之剑。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只限于此,对核武器的问题我们可以(最起码在思想上)达成共识:这个东西很坏,我们不想要,我们销毁它吧。可是,我们能对“克隆人”采取这样的行动吗?因为“克隆人”是人不是物,其也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对其就象长期以往对待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讲义务不讲权利:你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我利用,你的价值取决于我的需要。“克隆人”已经赋有人的生命和尊严并且给人的生命感和尊严感带来严重冲击,其一旦引发危害就是覆水难收。正因为如此,当克隆人的技术在理论上成为可能时,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这既是人类出于对自己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直觉维护,也因为人类已经饱受某些科技成果之害而不得不慎之又慎。惟有敬重生命,才能延续生命;惟有热爱人生,才能得到幸福;惟有用理性和审慎战胜狂热和偏执,人类的前景才会光明。
标签:克隆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