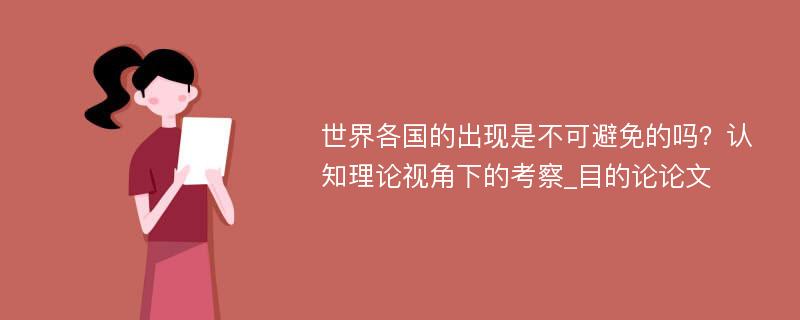
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重新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下称“世界国家观”)的热潮。世界国家观在西方学术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国家的研究更是蔚然成风。①冷战结束后,主要受到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和现有国际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两方面因素的刺激,世界国家成为一种可能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和世界秩序方案,重新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这也意味着世界国家观的研究重新兴起。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已有世界国家观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评介,而是集中考察亚历山大·温特有关“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观点能否成立。考虑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政治和哲学研究领域的承认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把这一考察纳入到承认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尝试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首先,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尤其是温特受到启发的霍纳特承认理论进行评介;其次,在比较温特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承认理论间异同的基础上,就两者共享及温特世界国家观独有的问题进行研究,就世界国家不可避免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做出判断。
一、世界国家观的经验研究成果及其面临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世界国家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验研究取向的成果,它们通过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来推论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并论证世界国家必然性的几率,亚历山大·温特的研究属于这一类;②第二类可以称之为安全关切,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安全威胁的存在,让世界国家的出现成为必须,这是一种实用性的考虑,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的研究属于此类;③第三类是规范性的研究,认为全球贫困和政治人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类型,这种治理类型不一定非得世界国家,但应是某种形式的超国家机构,它不但能制衡国家权力,而且还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龙尼·利普许茨(Ronnie Lipschutz)④和查尔斯·贝茨(Charles R.Beitz)⑤的观点属于这一类型。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国家研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更为连贯和系统,相关观点的构建也更为精致有力。考虑到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将持续存在,因此可以推断,这波研究世界国家的热潮还将会持续下去,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浪潮那样短命。⑦在上述三类研究取向中,经验取向的研究成果最值得关注。除了温特的《世界国家为什么不可避免?》(下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另外还有两篇有关世界国家的经验研究论文——《世界国家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和《运用考古学的数据预测世界的未来状态》。这两篇论文运用数学方法预测世界的未来状态,前者根据人口压力模型预测单一的世界国家可能不会出现,但当人口达到100亿的时候会出现342个国家和6个类似目前联合国的国家联邦;而后者首先通过历史分析,判断在过去的12000年间世界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然后运用二次曲线推断大约到公元5000年左右,地球上将出现一个世界国家。⑧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纳入其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国际体系中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个人与群体为承认斗争与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无政府结构的建构作用,以及一个目的因——世界国家——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将引导世界经过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最后达到世界国家的阶段。
在经验研究取向的成果中,温特的世界国家观最为精致,论证最为严谨,“无疑是最具想象力的成果之一”,因此产生的影响也最大。⑨本文将集中分析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在展开分析前,有必要简单讨论世界国家观经验研究成果共享的一个难题,即在缺乏外部他者情况下,世界国家如何维持自身身份的稳定。之所以出现这一难题,是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等行为体,都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其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对内管理内部事务和控制边界,对外与其他行为体进行沟通与协调。这些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其他外部单位的存在。当世界以一个世界国家的形式得以组织,因为缺乏外部他者,它将无法维持自身。因此,世界的发展即使按照温特等经验研究者们的逻辑展开,结果也只能是囊括了全世界所有政治行为体的两个超大集团,但不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⑩对于这一难题,温特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一,通过世界国家的整体与其部分(包括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建构来维持世界国家身份;其二,将空间区分转化为时间区分,即通过回顾历史来维持稳定。(11)然而,这样一来,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如果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互构与历史性的他者在世界国家出现以后能够维持身份的稳定,那在世界国家形成之前这两种身份构建方式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世界各国和谐相处而不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对于这一问题,温特及其他世界国家观的经验研究成果并未给出有效的回答。
除了上述问题,对温特世界国家必然性的批判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切入。已有研究指出了以下批判路径:其一,温特有关“世界也是人”的假定与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温特将国家拟人化,(12)认为国家和个人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将导致世界国家不可避免会形成。批判意见指出,国家是否真如温特所说那样为了承认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并不明确;(13)其二,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温特虽然强调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互构,但当世界国家的形成成为一个不可避免、无法逃脱的宿命,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中就出现了一个自然法则,行为体的能动性也因此被否定;(14)其三,温特的目的论实际上不是真的目的论,仅仅是个概率问题。除非接受国家也是人的机体隐喻并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一旦达到世界国家的阶段并停留于此,而且除非这种发展是基于国际体系自身的特征,否则,温特所谓的目的论就不是真正的目的论;其四,温特并没有告诉人们,他是何以确定世界国家是世界的终极状态的,能否将他所说的目的因置换为其他世界秩序状态,如和谐世界,等等。(15)既然已有上述批评意见,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对世界国家的必然性进行分析?路易斯·卡布雷拉(Luis Cabrera)认为,对其批评可能来自三个方向,除了前述的对国家拟人化与将目的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质疑,还存在另一条批判路径,即追问黑格尔承认理论对国内范围里的承认斗争所做的说明是否准确,以及温特是否正确地解读了承认理论?(16)在已有成果中,布里安·格林希尔(Brian Greenhill)的《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与集体身份形成》一文,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该角度切入的。(17)但其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失:其一,未考察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承认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其二,因此也未对温特世界国家观对承认理论的偏离展开讨论。因此,本文将温特的世界国家观纳入到承认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考察其有关世界国家必然会形成的观点能否成立。
二、承认理论的近期发展
承认理论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承认理论一般都将其理论鼻祖追溯到黑格尔,认为他在《精神现象学》、《伦理体系》、《法哲学》、《思辨哲学体系》、《耶拿实在哲学》(I、II)等著作中,都提到过相互承认的思想。(18)然而,由于黑格尔在不同著作中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因此后人对其相互承认理论的解读,就出现用不同的方式而得出不同的结论。长期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学者,重视的是《精神现象学》中以主人—奴隶辩证法形式体现出来的承认思想,而对《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等黑格尔早期文本中论述的承认观点,理论界长期未予应有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阐发和重新解读,也就出现了关注黑格尔不同文本的现象。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俄裔法国思想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ejev)、(20)中国哲学研究者高全喜等人,(21)主要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汲取养分;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新代表人物阿克塞尔·霍纳特(Axel Honneth),则主要根据《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等较少得到关注的文本来阐发和重构黑格尔的承认思想。(22)当然,除了上述人物,还有其他许多人参与到承认理论的研究当中,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23)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24)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等。(25)在对黑格尔承认思想的重构和阐发者当中,泰勒、霍纳特与弗雷泽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他们较早地参与到这一理论的发展当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从哲学角度构想了一种如何应对当代承认问题——包括政治承认、社会承认、文化(差异)承认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方案。(26)他们三人在发展各自承认理论的过程中,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两位学者的影响,或在通过与对方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因此,他们的承认理论有相似之处。不过,由于关注的现实问题与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有所区别,他们在承认问题上的具体观点和对于美好社会规范内涵的看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差异。考虑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从霍纳特承认理论中汲取了很多的思想资源,本文着重讨论霍纳特的承认理论。
霍纳特是如何重建黑格尔的承认思想的呢?尽管在不同阶段,霍纳特在承认问题上的观点发生过比较明显的变化,(27)不过自其博士论文开始到现在,霍纳特始终保持着对承认问题的关注。(28)他关于承认问题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1992年出版的《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一书中。书中,霍纳特区分了西方思想史中解释社会冲突的两种逻辑,即以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代表的“为自我持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self-preservation)的逻辑(29)和黑格尔等人最初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的逻辑。长期以来,“为自我持存而斗争”主导着政治哲学对社会冲突问题的解释,这种对人类冲突解释逻辑的单一性,不仅遮蔽了人类具有追求承认的社会性动机,而且忽视了社会冲突的规范和道德内涵。强调“为自我持存而斗争”逻辑的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极大地塑造了国内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而且还影响到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等现象的解释。直到现在,现实主义仍然坚持“为自我持存而斗争”逻辑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有效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也无意否认这一逻辑在解释国际关系现象中的意义。霍纳特希望建立的是一种能够说明社会冲突的道德内涵理论,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逻辑刚好符合这一标准。鉴于此,霍纳特对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理论作出了系统重构。不过,霍纳特认为,黑格尔对承认问题的说明存在“受制于理性的客观运动”,保留了“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等缺陷。(30)为了实现承认理论“经验的转向”,霍纳特重构黑格尔承认理论的途径就是利用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乔治·米德(George H.Mead)的象征互动论,来对社会冲突的道德内涵进行经验研究。霍纳特对黑格尔的这种重构,与他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经验理论,以实现法兰克福学派从一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规范理论向经验研究转向的目标是吻合的。
霍纳特建立了一种用以说明蔑视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道德动因的承认理论。霍纳特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自我追求承认的斗争是在主体间展开的观点,同样认为承认目标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冲突过程才能实现。黑格尔与霍纳特的主要分歧在于:黑格尔主要关注自我在与他者进行承认斗争中确立起“自我意识”(31)或主体性;而霍纳特更加强调承认斗争带来的行为体对自身特殊性的觉醒或坚持这一结果。对霍纳特来说,自我认同的不同维度表现为不同的承认形式。对这些承认形式进行区分,并且对这些承认形式进行经验验证,也就构成了其承认理论的核心内容。为此,霍纳特构想了由三种承认形式组成的“关于承认形式的经验现象学”,并认为这些承认形式对于行为体的“实践自我关系”,即“肯定性的自我关联”有着重要的意义。(32)根据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与《伦理体系》中提出的观点,黑格尔认为,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爱情”、“权利”、“伦理”三个承认阶段,它们是通过承认斗争而渐次得以实现的。在黑格尔三个承认阶段的基础上,霍纳特利用米德的象征互动论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情感关怀”、“法权承认”与“社会尊重”这三种攸关行为体实践自我关系的承认形式。他认为,这三种承认形式分别体现在家庭关系、法权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它们对于行为体实践自我关系的意义在于:它们分别有助于维持和增强行为体的“自信”、“自尊”、“自重”的情感需要。如果在不同的承认领域中,行为体不能获得相应的承认,那么行为体就遭到了“蔑视”(misrespect或misrecognition)。既然承认可以有不同的体现形式,那么蔑视形式也可以进行区分。霍纳特认为,蔑视形式包括:可能对行为体自信构成损害的虐待、强奸等现象;对行为体自尊造成打击的权利剥夺、法律排斥等现象;影响到行为体追求和维护自尊的侮辱、诽谤、心理伤害等现象。霍纳特认为,各种不同的蔑视体验,严重损害了行为体积极自我认同的发展,导致行为体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实践和伦理问题,并产生消极的情感反应。在他看来,这些情感反应构成受到蔑视的行为体从事“为承认而斗争”的动力。这种为了反抗蔑视、争取承认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也就是霍纳特所谓的“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将使社会达到一个承认要求得到平等、全面实现的终极状态。
三、世界国家观与承认理论之间的关系
霍纳特承认理论日益得到国际关系研究界的关注,(33)而温特对霍纳特承认理论的运用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温特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承认理论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一)霍纳特承认理论与温特世界国家观在“四因说”上的同构
承认理论在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动力因、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来论证世界国家必然会生成的过程中,(34)温特区分了导致世界国家形成的三种因果关系,即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个人或国家等行为体为争取承认而进行的斗争,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无政府状态的结构建构作用,以及终极性因果关系——前两种因果关系的互动带来向终极状态的演进。在这三种因果关系中,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其主要功能在于说明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为承认而斗争构成温特世界国家观的动力因。由此可见,霍纳特承认理论构成温特世界国家观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理论资源。因此,自下而上因果关系的论述是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决定温特世界国家必然性这一结论能否成立。
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的承认理论首要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将目的论引入自身的研究之中,温特明确指出自己尝试用目的论来分析世界国家生成的必然性。(35)他认为“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倾向于保持稳定,无法说明变化;而自组织理论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关注非线性动力,无法解释变化的方向”,为了展望国际体系“进化”的方向,就有必要构想一种终极状态。(36)显然,温特有关世界国家构成世界进化的终极状态的设想具有任意性,他没有给出规定世界的终极状态为什么就是世界国家的任何理由。(37)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世界国家而不是别的状态构成温特所说的引力场(attractor),或者为什么国际体系的演进路径不能在两个或更多的引力场之间移动?(38)这种目的因设定的任意性,严重削弱了世界国家必然性的可信性。
与温特相似,霍纳特同样有目的论倾向,只不过他没有像温特那样明确将其理论导向目的论的轨道。霍纳特将三种承认形式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内)社会是否取得规范进步的标准,认为“基本个体权利的连续开展以某种方式和规范原则(即社会成员被承认的程度——引者注)相联系,这种规范原则从一开始就引导观念”。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目的论特征,似乎承认斗争的开展,将自动引导社会趋向完满承认。霍纳特还直接将“终极状态”的概念纳入到其承认理论的框架中,他指出,“为了区分进步与反动,就必须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根据对终极状态的假设和把握,这一规范标准可以指出一条发展方向”。(39)霍纳特所谓的终极状态,与温特所说的世界国家一样,是指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得到全面和平等承认的状态。从上述论断中可以发现,霍纳特对终极状态的表述,与温特将目的因引入世界国家观的原因完全一致。我们无法确定温特是否因为受到霍纳特上述论断的影响,才运用承认理论来论证世界国家的不可避免性,但两者之间的目的论取向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两人在对待目的论的态度上有差异?答案在于霍纳特与温特的研究目的有所不同:与温特试图运用目的论来论证世界国家的必然性这种经验研究取向的研究不同,霍纳特试图建立一种具有经验内涵但以规范为导向的承认理论。前者的经验取向使其将目的论作为一个解释因素来论证世界国家生成的必然性,而后者的规范取向使霍纳特在目的论仍然受到很多质疑的今天不得不谨慎从事,避免直接运用目的论来论证其承认理论。
除了目的因上的相似之处,霍纳特的承认理论与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在其余三因方面也几乎同构。首先,在动力因方面,两者完全一致,即都将为承认而斗争视为社会(一个是国内社会,一个着重研究的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次,在质料因上,温特认为他已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对观念在世界构成中的核心作用做了充分说明,他认为没有必要对世界国家观的质料因进行专门讨论,由此可以判断温特世界国家观的质料因是观念。(40)霍纳特承认理论在质料因的问题上比较含糊:一方面,他希望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范式”的改造和对霍布斯“为生存而斗争”逻辑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黑格尔承认思想中具有的德国唯心主义成分,此外,他还借鉴米德的象征互动论思想来完成承认理论的经验转向,再考虑到他对弗雷泽再分配范式的批判,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霍纳特与温特一样,强调主体间观念的“建构主义者”。不仅如此,鉴于象征互动论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41)而且考虑到承认斗争所争取的目标无论是情感关怀、法权承认还是社会团结,均属于精神和观念层面的因素,因此,将霍纳特承认理论的质料因归结为观念应该不成问题。至于形式因,温特世界国家观中的形式因即他的无政府状态观念结构具有的建构作用;至于霍纳特承认理论,其形式因同样是社会结构,因为在他构想的承认斗争中,“人们似乎由一个独立于他们意图的力量裹挟着趋向某个目标,该目标编码于他们互动的结构之中”。(42)如果对霍纳特承认理论质料因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其形式因同样是温特所说的观念结构。
(二)温特世界国家观对霍纳特承认形式的选择性强调和弱化
温特是如何借鉴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来论证其世界国家的必然性的呢?在温特世界国家观中,承认斗争带来行为体集体身份的扩大,构成最核心的理论逻辑。他认为,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学说的目的,仅仅在于为人们心甘情愿保留在利维坦中进行合法性论证。通过展示自然状态中“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这一可能,霍布斯警示人们从利维坦退回到自然状态的危险。(43)就此而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没有为利维坦或世界国家的“出现”提供充分条件,为此,温特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世界)国家的身份边界可以扩大到包括所有人,而不仅仅只是国家的原初成员”。(44)为了回答这一难题,温特认为有必要借鉴承认理论的思想资源。因为他认为在承认斗争中,不对称承认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即使通过运用霸权或错误意识,让未被承认行为体处于顺从或未反抗的状态,这种状态从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为了保持系统的稳定,使非对称承认状态向相互承认的状态转化,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45)这种转化的动力,就在于行为体为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而开展的承认斗争。一旦达到相互承认的状态,就会“形成集体身份和团结”。温特的逻辑是:一旦承认他者的地位和接受由此对自我构成的规范限制,那么“他者就构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两个自我实际上就合二为一,一种‘我们感’和集体身份就由此而生”。(46)可以将温特的这种逻辑概括如下:相互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感”或集体身份。
显然,上述等式有明显的逻辑跳跃:前一个等式与后一个等式能够成立,(47)但中间的等式显然有问题。即使根据常识,相互承认或者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并不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彼此消融。正如对一个国家主权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该国的认同一样,相互承认并不等于彼此认同。但正是根据上述等式,温特认为自己完成了个人层面上的承认斗争导致集体身份的扩大、国际关系层面上承认斗争导致世界国家不可避免会生成的论证。由此可见,承认斗争构成驱动国际体系最终趋向世界国家的关键动力。
需要追问的是,温特是否对承认理论作了正确的解读?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在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中,行为体追求承认的具体内容是否与霍纳特的三种承认形式相符?在论文中,温特对承认作了如下界定:“承认是一种赋予差异以特定意义的社会行为,这就意味着其他行为体(他者)被视为主体;相对于自我来说,他者主体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48)温特明确提出,承认行为的前提条件在于具有差异或他性的事实,这种差异或他性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国家。个人之间的差异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生理身体”,而国家的差异则是基于“各国之间划定的边界”。在此基础上,温特区分了两种承认形式,即“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49)“薄的承认”的承认对象是大同主义意义上的“普世的人”,即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往往是指司法意义上的人权,它不关心主体的特殊要求。而与此相对的“厚的承认”,承认主体不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国家。这种承认在“普世的人”的基础上,承认行为体的特殊要求,如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对自身特性的维护等;而当行为体是国家时,承认斗争的追求目标包括大国地位、荣誉和威望、成为上帝选民等等内容。(50)温特将“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都纳入到其世界国家观中,认为它们在世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均发挥了作用。
温特对“厚的承认”与“薄的承认”所持立场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反映了温特试图融合国际关系伦理研究中大同主义(或称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倾向;其次,两种承认形式试图对应和囊括霍纳特的三种承认形式:“薄的承认”对应霍纳特的法权承认,而“厚的承认”则试图包容霍纳特的情感关怀和社会团结。
在借鉴霍纳特承认理论的同时,温特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温特强化了“薄的承认”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他将个人的被承认程度视为趋向世界国家不同阶段的衡量标准,也反映在以下论断中:“对于世界国家的形成而言,重要的是‘厚的承认’将会逐渐被‘驯化’——也就是采用非暴力手段追求承认并且接受(世界国家的)国家权威——不管其追求的内容是什么。”(51)如此一来,为“厚的承认”而开展的斗争,在世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被视为无足轻重。其二,考虑到国家等行为体对国内承认斗争的限制作用,温特拒绝探讨国内范围内个人或群体追求薄与厚这两种承认形式对世界国家形成可能带来的影响,他的理由是:“体系的目的在微观层面上是多层因素决定的,国内斗争的细节并不会影响到终极状态。”(52)这两点修正让温特的两种承认形式几乎缩减为“薄的承认”一种承认形式,而厚的承认形式成为一个摆设和背景。尽管在论证过程中,温特也提到国家在向世界国家演变的各个阶段可以保留自己的差异,如在集体安全阶段可以“在认同全球整体命运的同时维持自己的差异”,甚至在世界国家阶段还可以“保留一定的个体性”,甚至引用社群主义者米歇尔·沃尔泽(Miachel Walzer)的观点来强调“只有承认差异,一个大的身份才能保持稳定”。(53)然而,在温特那里,承认目标的界定性特征,始终是法权和主体性,而不是差异与个性。如此一来,温特在对霍纳特承认理论进行借鉴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后者的修正。其中最突出的修正,就是突出法权承认这一承认形式,以此论证世界国家的不可避免。温特虽然致力于在社群主义和大同主义之间进行调和,但他对“薄的承认”或法权承认的突出强调,使其滑入大同主义的阵营。(54)世界国家观与大同主义的联姻,使个人、社会群体、国家等行为体具有的特殊性无栖身之所。温特的这种立场,与其建构主义理论追求的理论目标息息相关。温特认为,他的建构主义是一种体系理论,而且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是一种普适性理论。(55)既然建构主义是普适性理论,温特自然不会赋予标识国家独特性的各种因素——如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等——以重要意义。(56)
四、承认理论面临的批判与世界国家观的非必然性
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的承认理论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对它们的分析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两者在“四因说”上几乎同构,于是对霍纳特承认理论的某些批评同样适用于温特的世界国家观,所以有必要考察学术界对霍纳特承认理论的反应;另一方面,温特世界国家观对承认理论作了关键性的改造,从而导致其与霍纳特承认理论有显著差异,这就需要分析这种改造是否给其世界国家观的必然性带来某些特殊的困难。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57)
(一)承认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与对黑格尔承认思想进行乐观理解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许多承认理论家——如霍纳特、泰勒、雷蒙德·威廉斯(Robert Williams)、(58)温特——都倾向于从乐观和目的论的角度解读承认斗争的结果,认为承认斗争会带来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批评者一方面承认这种研究有助于人们揭示和矫正社会的不正义,同时也指出,对承认斗争的乐观解读,既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相互承认思想,也与承认斗争的经验结果不相吻合。帕特奇·马克尔(Pattchen Markell)在重新阐释黑格尔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基础上,对承认斗争的后果提供一种非乐观、非目的论的解读。在《承认之限》一书中,马克尔在对泰勒、霍纳特及威廉斯等人承认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得出承认斗争是一场悲剧的结论。(59)在他看来,承认斗争的结果既不是某种集体身份的形成,也不会带来某种纯粹的社会正义状态。与此相反,承认斗争在带来某种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新的社会不正义现象。因为承认斗争并不是将平等的权利和独立地位在斗争各方进行平等的分配,而是其中一方独立性的取得往往导致另一方“独立性的放弃”。马克尔将承认斗争带来的这种结果,称为“悖论”(irony)。(60)
为什么承认斗争会带来承认悖论?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群体、国家的身份是在与他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得到维持的,这构成一个人存在的本体论条件。如此一来,身份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他者“不可预知的回应和反应”,因此身份就具有明显的“社会脆弱性”。另一方面,虽然笛卡尔式的孤立、自主、自由的主体概念已不适用,但追求“主权”即身份的自主性是行为体近乎本能的反应,而落实到行动中往往让行为体意识不到身份的“社会脆弱性”,不愿承认自身身份依赖于他者承认这一本体性的有限性。(61)于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承认斗争在带来某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不避免地产生某些新的蔑视。在该书中,无论是希腊悲剧《第欧根尼》中角色对身份的确认、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还是19世纪德国对犹太人的解放、著名自由民族主义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多元文化主义治理方案,都产生了这种悖论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尔认为:“就论述行为与身份或习性(ethos)之间的关系而言,悲剧既有助于理解一个完美的承认机制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这种不可能性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惋惜的制约,而且也是能动性之为可能的一个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所说的自由。”(62)马克尔的结论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确注意到了承认斗争的主体试图掌控身份自主性的内在冲动,这往往是人们下意识的反应,超出他们知识掌控的范围。这样一来,承认斗争是一场悲剧而不会带来承认要求得到完满实现的结论,这不仅给霍纳特与温特的目的论取向当头棒喝,而且重新为承认斗争中人的能动性开辟了空间。
导致承认悖论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在承认斗争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63)在承认斗争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参与承认斗争的行为体在权力分配上是不平等的。这种现象在霍纳特的三种承认形式中有鲜明的体现。就国内层面的承认斗争而言,在情感关怀领域,不考虑道德争议,父母是居于强势的一方,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给予孩子充分的关怀与爱护;在法律承认领域,国家或其他权威机构往往构成决定是否给予行为体平等法权的仲裁者或垄断者;在社会尊重领域,行为体之间在社会地位与权力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某些人在是否给予其他行为体同等尊重的问题上处于优势。如此一来,争取承认的斗争者就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选择:要么为了满足自身的承认要求而反抗强势方的压制、要么为了取得强势方的承认而顺应后者的要求。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将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概念称为“承认困境”。承认困境具有自身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可概括为:如果某一行为体感到自己受到蔑视,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他将通过言辞、象征、行动(包括战争)来表达对蔑视者的不满,或者要求后者道歉,或者要求后者对其给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然而,被蔑视者的承认要求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蔑视者的态度。因为被蔑视者旨在追求承认,这种追求让蔑视者感到反感与厌恶,往往带来对被蔑视者的进一步蔑视。当双方都不愿让步时,就有可能爆发严重的冲突。这种过程就像“安全困境”一样,让处于承认困境中的行为体陷入到“自动毁灭性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恶性循环过程”中。(64)简言之,无论是蔑视与反抗之间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双方的实力对比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社会中的“承认困境”更加明显。毕竟在国内社会中,还有获得大家认可的权威机构或道德惯例对这种困境进行干预,以纾缓这种困境。然而,在国际社会中,屡见不鲜的是,同盟之间的情感支持不能保持稳定和持久,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又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至于在国际关系文化与价值观等领域中出现的承认要求,更取决于互动各方的态度。因此,承认困境在承认斗争中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温特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提到,在世界国家形成之前,美国等强国可以凭借实力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甚至采取发动战争等手段,侵犯如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其他主权国家。对于这些现象,国际关系中却没有有效的力量对其进行制衡,更不用说由某种国际行为体来追究其责任。(65)即使在世界国家形成以后,权力在承认斗争中的显著性仍将存在。如果世界国家的确形成了,那么由谁来制衡世界国家的暴政?由于垄断了对其他行为体的承认权,世界国家既可以给予成员要求获得的承认,也可以拒绝赋予这种承认,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杀死各种亚群体。(66)实际上,温特认识到,在缓解承认困境的能力上,无政府状态与世界国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别。例如,他承认,“对于解决承认问题,世界国家比起无政府状态显然要强。”(67)也就是说,温特本人对于世界国家能否真正解决承认问题,是抱有疑惑的。即使追求承认的行为体对世界国家抱乐观态度,并如温特所说的那样积极参与到促进世界国家形成的事业中去,然而受制于自身的权力资源,它们收获的可能不是承认,而是被奉行现实主义政策的大国利用,使它们陷入比此前更深刻的承认困境中。马克尔对于承认斗争必定会带来使所有承认要求得以实现的终极状态的批判,不仅适用霍纳特等人的承认理论,同样适用于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如威根·P.香农(Vaughn P.Shannon)指出,温特对于世界政治经过渐次发展的四个阶段最后达到世界国家状态的论证,不仅极其粗略,以致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更重要的是,温特关于国际体系变化的线性发展观,“并没有为人类历史是由非线性变化的循环构成的观点留有余地。这种非线性的变化是由变化的无目的性、主权的推力与其他难以计数的各种政治力量共同造成的,它们使得(世界国家——笔者注)‘不可避免性’存在问题”。(68)不管对世界历史持一种进化论还是循环论的观点,根据对承认斗争的过程及其后果进行重新审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斗争不会带来某种终极状态,不会导致世界国家的形成。
(二)温特世界国家观必然性的软肋
温特强化法权承认这一承认形式,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后果,而且与经验事实不符。笔者首先考察这种取向的理论含义,然后根据经验研究成果对温特世界国家观的必然性进行审视。
1.淡化“厚的承认”的理论效应
温特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在世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包括个人、国家等群体进行承认斗争的目的,仅在于追求自身的平等法权和使自身的主体性得到承认。按照这种推理,似乎行为体一旦获得了平等、全面的法权或主体性,它将无意反对那些忽视或消除其个性的举动。这同样可以从温特论述建构主义有关集体身份形成的条件中得到验证。在考察集体身份形成的条件时,一方面,温特认为行为体之间的同质性有助于集体身份的形成,因为“客观同质性的增大可以使行为体重新认定其他行为体是自己的同类。把其他行为体归为同类不等于与他们认同,但是以两种方式促使认同的产生”;另一方面,温特也强调国家自我约束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温特虽然将这两者都列为有利于促进集体身份形成的条件,但同质性与尊重差异这两种明显冲突的条件在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如何协调,温特语焉不详。事实上,温特甚至注意到在历史上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国家——如欧洲君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国家——曾发生过严重冲突的历史事实。鉴于此,温特不得不承认,“我们几乎没有理论上的证据可以说明团体身份甚至类别身份自身能够产生亲社会的安全政策,并因之造就集体身份”。(69)既然这些国家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为什么依然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温特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在这一问题上,只能再次说明温特对强调普适人权和“薄的承认”形式的大同主义的皈依,即突出人权,同时低估群体、国家等对行为体身份认同的意义,也就忽视了各种差异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将温特的这一立场放在霍纳特的承认理论框架中,温特的选择性借鉴将更为明显。
霍纳特承认理论明确提出,对个性与差异的尊重是承认斗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维度。霍纳特认为,承认带来的集体自尊或团结,是以尊重行为体的特质和个性为前提的。对于两者间的关系,他指出:“‘团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主体彼此对等重视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70)也就是说,团结的形成或巩固,不是以消除行为体之间的差异或生活方式为代价,而是以尊重后者为前提。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各种反抗的原因时,霍纳特认为:“在动机问题上,比物质上的窘境远为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与成就,因为在无产阶级眼中,这些东西是应该受到尊重的,然而,它们却没有被社会上其他人承认。”(71)在霍纳特看来,团结的前提是尊重行为体的差异、生活方式、社会成就等,而对这些行为体珍视的事物的蔑视或否定,往往带来反抗与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情况同样如此。对他国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习惯、发展道路、主权等方面的尊重,是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开展合作的前提;相反,对他国特质与差异的蔑视,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原因。无论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以及伊朗、朝鲜对核武器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坚持自己的差异和追求“厚的承认”。(72)国家之间的蔑视,即使不采取暴力和流血冲突的方式,但常见的如以羞辱、诬蔑、冷战等妖魔化与去人性化对手体现出来的蔑视现象,也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甚至让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解决的矛盾,最后演变成“难解难分的冲突”(intractable conflict)。(73)就此而言,霍纳特将对差异与特质的维护作为承认斗争的一个独立领域,并把它作为其承认理论的第三种承认形式,是具有独特眼光的。
温特强化法权承认这一承认形式,具有消除国际关系中差异的理论效应。诚如马克尔所言,承认斗争或许的确让社会中的某些不平等承认现象得以消除,从而产生了某种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很有可能是以其他人丧失主体性或独特性,或者蒙受物质上的损失和遭受文化上的同一为代价。如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世界国家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自由主义虽然表面上鼓吹自由、多元,但实际上却有消除差异的倾向。如同温特强调“普世的人”或“薄的承认”的优先性,自由主义同样基于人的概念的“单一普世性”来思考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抽象的个人主义,不以某个具体敌人的存在为目标,而只有存在差异,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的可能。(74)事实上,对差异的敌对态度,构成西方文化的一种底色。无论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宗教战争,还是在西方发现新大陆后对印第安人的征服,还是在现代化学者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线性研究模式,甚至在主张竞争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将差异建构视为威胁,要么对其进行同化,要么将其消灭的倾向。(75)对于温特世界国家观中对待差异的态度,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指出,温特世界国家的必然性“将自由主义的‘和平工程’作为其逻辑结论:政治敌手的消灭,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权威结构才能实现,这样就没有给全球政治空间留下任何外部性,同时也就取消了国际关系”。(76)如此一来,因为没有任何外部敌人可以用来消灭,“冲突将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将切切实实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者无疑会以暴力抵制这种尝试——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概念将他们纳入到(全球性的)祖国中去”。(77)尽管温特强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将有效地防止人们通过暴力手段争取承认,然而当自身的(身份、文化等)的差异受到严重的威胁,铤而走险的行为体很有可能通过运用核武器来争取承认,彻底实现国际体系的“终结”,而不是形成一个世界国家。
2.承认斗争的经验事实
在理论上强化法权承认,不仅有严重的理论后果,而且与行为体突出追求其他两种承认形式——尤其是第三种即自身的差异和贡献——的经验事实不符。正是这一经验事实,能对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必然性予以致命打击,因为它们否定温特有关承认斗争带来集体身份扩大这一世界国家观的核心逻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支持温特有关自我的形成有赖于他者的存在这一象征互动论的观点,然而并不能论证他有关承认斗争导致形成集体身份扩大和世界国家必然会生成的结论。根据由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与约翰·特纳(John Turner)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对他者的承认并不一定带来对他者的友好情感,相反,更多地是以对内外群体的区别对待为特征的,而且经常体现为对内群体的偏爱与对外群体的歧视。(78)即使这些群体在接触前没有互动或利益冲突的历史,这种对内外群体的区分,并由此带来对不同群体的成员采用不同态度的模式总会出现。(79)早在1995年,通过利用社会认同理论与泰菲尔后来提出的最小群体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80)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追求自尊的动机和行为,就足以使国家间爆发冲突,(81)从而对霍纳特根据象征互动论提出的互动过程有助于超越无政府状态中自助逻辑的观点进行质疑。(82)不仅如此,对于温特认为已经进入康德文化状态的欧盟国家,默瑟承认,虽然在欧盟国家内部的确形成了某种集体身份,然而这种内部团结却是以对欧盟外国家的排斥和歧视为代价的。(83)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即使形成了集体身份的某一群体,仍然有对外群体排斥的倾向,根据霍纳特的承认理论,这仍然是一种不正义。(84)对于默瑟的批判,温特曾经做出过回应。姑且不论两人之间的分歧是否得到解决,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群际交往与互动,不管是否带来竞争或冲突,如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征服,经常出现的结果不是温特认为的那样趋向同质化,相反是彼此对自身差异和特性的坚持。
更明确地从这一角度分析世界国家必然性的是格林希尔。(85)如前所述,在温特的承认逻辑中,行为体之间彼此承认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意味着集体身份的形成。然而,这里存在逻辑上的跳跃。这种跳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温特低估了行为体对自身差异的坚持。格林希尔正是瞄准此点,从而从根本上否认承认斗争带来集体身份的扩大这一温特世界国家观的核心逻辑。格林希尔指出,即使温特强调的行为体对平等法权或主体性的追求这一承认要求得以实现,行为体也只是承诺与其他行为体和平相处,而没有承诺除此之外的更多东西。也就是说,法权或主体性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承认者向被承认者抱有友好情感,更不意味着前者在与后者的互动中采取利他逻辑。(86)而这是温特集体身份概念的基本内涵。为了证明这一至关重要的论点,除了上文提到的社会认同理论,格林希尔还借鉴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Marilynn Brewer)的“最优独特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与比尔·麦克古尔(Bill McGuire)的“自发自我概念”(spontaneous self-concept),来对集体身份不能产生的深层缘由进行考察。格林希尔得出结论:“对他者的承认可被视为确认一种属于共同身份的感觉,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过程强调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因此进而强调他们之间的特质,而不必然涉及共享身份任何有意义的感受。”(87)将这一结论运用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上,格林希尔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对温特的观点提供支持,反而证明了承认斗争不必然带来集体身份的扩大。当温特世界国家的这一核心逻辑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世界国家必然会形成的结论也就不能成立。鉴于此,格林希尔建议温特等建构主义者,不要对在国际体系中产生一个根据黑格尔逻辑衍生出来的世界国家抱有太多的期待,而要满足于“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承认仅仅意味着,‘他者’有权以已经存在的方式继续存在”。(88)
从承认理论的框架中来对温特的世界国家观进行考察,无论温特赖以论证其世界国家观的重要理论资源——霍纳特承认理论,还是他基于对自由主义或大同主义伦理价值的认同而对后者进行的改造,都不能为其承认斗争必然驱动国际体系最终达到世界国家这一终极状态的观点提供充分的支持。因此,温特有关世界国家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温特将世界国家观学理化的努力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西方学术界热衷提出不同的世界秩序方案,例如,冷战后就曾出现过“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诸多世界秩序方案。这些世界秩序方案不仅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世界秩序方案的构建,虽然首先是一种理论探索,但其一旦产生广泛影响,就很有可能引导甚至塑造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89)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有关世界国家或世界政府的研究成果。在现有关于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的三种研究取向(经验取向、实用取向与规范取向)中,经验取向的成果最值得关注,其中又以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影响最大。温特在其无政府状态的视野中,看到了国际关系的“终极”发展方向,为国际政治最终可能达到的状态——世界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温特这种对人类发展方向的展望和关切,在当前“问题解决理论”盛行的国际关系学界是比较鲜见的。(90)后者往往对理论或观点中的规范内涵或价值取向避而不谈,而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并不讳言自身的价值追求——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发展,并通过运用耳熟能详的术语、概念或假定,对世界国家这一看似“乌托邦”的世界秩序前景作出学术论证。即使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尝试仍然值得赞赏。(91)这种将某一世界秩序方案学理化的努力,能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提供重要启示。我们有必要思考,在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观等世界秩序方案后,学术界如何才能将其学理化,而这正是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在《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一文提出的问题。(92)
在赞赏温特将世界国家这一世界秩序方案学理化的同时,还有必要对其世界国家观隐含的价值取向保持必要的警惕。温特的世界国家观虽然试图包容大同主义与社群主义,但他的世界国家观与其建构主义一样,都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或大同主义色彩。温特突出强调的是“薄的承认”,即抽象的个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对国家、个人等行为体致力于维护的特殊身份、独特的文化、习俗等属于“厚的承认”范畴,以及它们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温特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这种态度,实际上与基于抽象的个人概念克服或消除差异的自由主义或大同主义倾向大同小异。因此,温特的世界国家观虽然精致和复杂,但同样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具有一些隐而不彰的价值目标。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的匿名审稿专家所提供的建设性修改建议。另外,曹伟、沈晓晨、宛程、王静、周明等人阅读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中的不当之处概由作者承担。)
①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的研究历史可参考Derek Heater,World Citizenship and Government:Cosmopolitan Idea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6; Tomas G.Weiss,"What Happened to the Idea of World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3,No.2,2009,pp.260-261; Campbell Craig,"The Resurgent Idea of World Government,"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2,No.2,2008,pp.133-134;柴宇平:《“世界国家观”考评》,载《福建论坛》1999年第1期;以及斯坦福大学编写的有关世界国家观演变过程的条目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world-government/,2011-04-11,等等。
②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2003,pp.491-542,中文删节版见[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秦亚青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ll期,第57-62页。
③Daniel Deudney,Bounding Power: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Ronnie Lipschutz and James K.Rowe,Regulation for the Rest of Us? Globalization,Governmentality and Glob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5.
⑤Charles R.Beitz,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Charles R.Beitz,The Idea of Human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⑥Luis Cabrera,"World Government:Renewed Debate,Persistent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3,2010,p.513.
⑦Ibid.,pp.525-526.
⑧Peter N.Peregrine,"Is a World State Just a Matter of Time? A Population-Pressure Alternative," Cross-Cultural Research,Vol.38 No.2,2004,pp.147-161; Melvin Ember and Carol R.Ember,"Predicting the Future State of the World Using Archaeological Data:An Exercise in Archaeomancy," Cross-Cultural Research,Vol.38,No.2,2004,pp.133-146.
⑨Luis Cabrera,"World Government," p.514.
⑩参考Amber Lynn Johnson,"Why Not to Expect a 'World State'," Cross-Culture Research,Vol.38,No.2,2004,pp.119-132;冷晓玲、李开盛:《论世界国家生成的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5、117页。
(11)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527-528.
(1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76—281页;学者们对温特这一命题的争论集中在《国际研究评论》2004年第2期上,参见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2,2004,pp.255-316.
(13)Iver B.Neumann,"Beware of Organicism:The Narrative Self of the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2,2004,p.266.
(14)Vaughn P.Shannon,"Wendt's Viol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Project:Agency and Why a World State Is No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4,2005,pp.581-587.温特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回应,参见Alexander Wendt,"Agency,Teleology and the World State:A Reply to Shann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4,2005,pp.589-598.
(15)这些观点可参考James F.Keeley,"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2,2007,pp.421-422,尤见第422页的脚注。我国学者唐世平根据其支持的国际关系社会进化模式同样认为,温特所说的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的,可参考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29页脚注③。
(16)Cabrera,"World Government," p.517.
(17)Brian Greenhill,"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14,No.2,2008,pp.343-368.
(18)王凤才:《霍纳特承认理论思想渊源探析》,《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第58-59页;也可参考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纳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学转向”》,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5页。
(19)[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226-261页;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陈燕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337页。
(20)[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另参阅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页。
(21)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霍纳特关于承认问题的代表作可参见[德]阿克塞尔·霍纳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除此之外,霍纳特还有一系列关于承认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下文将有所涉及。
(23)沃尔泽关于承认问题的论述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376页。
(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法制国家的承认斗争》,曹卫东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338-375页;另参阅Jürgen Haacke,"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 the Centrality of Recogni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1,2005,pp.181-194.
(25)[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纳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美]凯文·奥尔森主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Barbara Hobson,Recognition Struggles and Social Movements:Contested Identities,Agency and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Nancy Fraser,"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 Terry Lovell ed.,(Mis)recognition,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Nancy Fraser and Pierre Bourdieu,London:Rutledge,2007,pp.1-16.
(26)Simon Thomp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ecogni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3.
(27)相关讨论可参考王凤才:《霍纳特承认理论发生学探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54-59页;王凤才:《“社会病理学”:霍纳特视阈中的社会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5-28页。
(28)近年来,国内逐渐兴起对霍纳特的研究,其中尤以王凤才的努力最为突出,他已出版一本专著和数篇论文。此外,国内已有一篇专文研究霍纳特承认理论的博士论文,参见胡云峰:《霍纳特承认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
(29))霍纳特:《为承认而斗争》,第11-15页。
(30)同上书,第72页。
(3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尤见第126页。
(32)同上书,第149页。
(33)如Erik Ringmar,"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A Hegelian Interpretation of a Peculiar Seventeenth-Century Preoccu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1,No.1,1995,pp.87-113,Erik Ringmar,"The Recognition Game: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7,No.2,2002,pp.115-136; Jürgen Haacke,"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81-194; Philip Nel,"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4,2010,pp.951-974; Michelle K.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curity,Identity and The Quest for Power,Ph.D.dissertation,The Chicago of University,2008;[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238页。
(34)受到温特的启发,米利亚·库尔基(Milja Kurki)主张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系统地引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参阅Milja Kurki,"Causes of a Divided Discipline: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Cau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No.2,2006,pp.189-216.
(35)温特知道,在盛行单一因果性解释模式的国际关系学界,运用已受到批评的目的论来对世界国家的前景进行论证,可能会遭遇到质疑。为此,他曾在文中做了大量的辩解工作。参阅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494-499.后来的事实证明,温特预料中的质疑并未出现,可参考Keeley, "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p.419.
(36)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01.
(37)在另一处地方,温特认为这种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和平联邦”、“政体”、“新中世纪”体系,但他认为,无论如何称呼,世界的终极状态始终是所有个人或群体都被一个“全球韦伯式的国家”所承认和保护,请参阅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06.
(38)Keeley,"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p.422,No.16.
(39)引言分别见霍纳特:《为承认而斗争》,第123、175页。
(40)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03.
(41)温特在想象两个独立主体(自我与他者)的首次相遇时,最为典型地采用了象征互动论思想,可参考Alexander Wendt,"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Boulder & Colorado,Lynne Rienner,1996,pp.47-64.
(42)Thomp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ecognition,p.164.
(43)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09,温特的这一观点与政治哲学家们的理解是一致的,请参考William E.Connoly,Political Theory and 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p.28-29; Louiza Odysseos,"Dangerous Ontologies:The Ethos of Survival and Ethical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8,No.2,2002,pp.408-409.
(44)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0.
(45)Ibid.,p.514.
(46)Ibid.,p.512.
(47)前一个等式之所以能够成立,请参阅Louiza Odysseos,The Subject of Coexistence: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3—84页。后一个等式能够成立,请参阅温特有关共同命运、同质性、相互依存、自我约束有利于集体身份形成的观点,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第423—454页。中间的两个等式之所以不能成立,请参阅秦亚青有关冲突辩证法与“互补辩证法”之间差异的精彩论述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2010,pp.129-153.
(48)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1.
(49)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511-512.温特对承认内容的这两种区分或许从米歇尔·沃尔泽那里受到了启发,因为沃尔泽早在1994年就区分了“薄的德性”与“厚的德性”,参见Miachel Walzer,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Notre Dame,IN: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4;不过沃尔泽明确反对成立世界国家,参见Briend Orend,"Considering Globalism,Proposing Pluralism:Michael Walz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2,2000,pp.411-425.
(50)这两种承认因素与国际关系伦理学研究中大同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观点相互对应,关于这种争论可参考Molly Cochran,Normativ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Pragmatic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李开盛:《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两种思想传统及其争鸣》,《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第54-59页。
(51)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2.
(52)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16.
(53)引言分别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p.521,525,527.
(54)这一结论并不奇怪,温特建构主义一开始就有自由主义的气质。这一点可参考萨缪尔·巴尔金:《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641页;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石之瑜、殷玮、郭铭杰:《原子论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社会建构”与“民主和平论”的共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29-38页。
(55)温特提到:“我希望我的模式的适用范畴是跨历史和跨文化的”,参见温特:《国家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5页。
(56)有关建构主义如何忽视世界不同世界观和文化间差异的讨论,可参阅曾向红:《“世界观问题”为什么没有成为问题: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欧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8-22页。
(57)需要说明的是,在阐述承认理论面临的困难时,本文没有涉及霍纳特与弗雷泽之间有关承认与再分配这两种社会规范要求之间关系的争论。这是因为:尽管弗雷泽对霍纳特将承认要求的实现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决定性衡量标准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但考虑到温特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的成果认为,即使基于弗雷泽的再分配逻辑(温特称“资本的逻辑”),世界国家的形成也会不可避免,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基于“为承认而斗争”导致世界国家必然性的趋势。然而,温特没有就此展开讨论,笔者因而不对再分配与承认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世界国家形成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温特的相关说明见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494.
(58)参阅Robert Williams,Recognition: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Alban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2; Robert 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温特在其世界国家观中也借鉴了威廉斯的观点。
(59)Patchen Markell,Bound by Recognition,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60)Ibid.,p.5.
(61)Ibid.,pp.57,58,86,102,103.
(62)Patchen Markell,Bound by Recognition,p.88.
(63)就如何看待承认斗争中出现的权力现象,霍纳特与其批评者展开了一次直接的对话,请参考Bert Van Ben Brink,David Owen,Recognition and Power:Axel Honneth an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64)John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2,No.2,1950,pp.157-180.
(65)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26.
(66)Shannon,"Wendt's Viol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Proje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84;冷晓玲、李开盛:《论世界国家生成的不可能》,第121页。
(67)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524.
(68)Shannon,"Wendt's Viol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Project," p.583.
(69)引言分别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2、448、445页。
(70)霍纳特:《为承认而斗争》,第13页。
(71)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eds.,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3,p.131.
(72)Michael C.Williams and Iver B.Neumann,"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NATO,Russia,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2,2000,pp.357-387; Iver B.Neumann and Jennifer M.Welsh,"The Other in European Self-definition:An Addendum to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27-246.
(73)对于冷战中苏美两方与巴以之间妖魔化对方的情况,可分别参考[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Daniel Bar-Tal,Yona Teichman,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in Conflict:Representations of Arab in Israeli Jewish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74)Sergei Prozorov,"Liberal Enmity:The Figure of the Foe in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Liberalism,"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1,2006,pp.75-99.
(75)Naeem Inayatullah,and David L.Blane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New York:Routledge,2004.
(76)Prozorov,"Liberal Enmity," p.87.
(77)Ibid.,p.90.
(78)[美]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载周晓红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方文、李康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Henri Tajfel,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79)Heri Tajfel,"Soci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33,1982,pp.1-39; Miachael A.Hogg and Dominic Abrams,Social Identifications: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p.43-47.
(80)Hogg and Abrams,Social Identifications,pp.41-43.
(81)笔者并不认同默瑟的宿命论或结构决定论观。事实上,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群体之间的比较,并不一定会带来冲突与侵略。参见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2,2005,pp.235-265.
(82)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2,1995,pp.229-252;温特对于默瑟批评所做的回应参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01-302、346-347页。在《为什么世界国家不可避免?》一文中,温特预设了“冲突”是承认斗争的唯一形式。参见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p.493.
(83)李明明:《国际关系集体认同形成的欧洲社会心理学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68页。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权力,请参阅Thomas Diez and Ian Manners,"Reflecting on 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J.Williams,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7,pp.173-188.
(84)对于国际社会中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涉及对他者的排斥与歧视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含义,参见Bahar Rumelili,"Interstate Community-Building and the Identity/Difference Predicament," in Richard M.Price,ed.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2008,pp.253-280.
(85)Greenhill,"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43-368.
(86)Greenhill,"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356.
(87)Ibid.,p.352.
(88)Ibid.,p.363.
(89)国际关系学者论提供世界秩序方案的重要性,参见Jenny Edkins and Maja Zehfuss,"General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3,2005,p.454.
(90)[加]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美]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3页。
(91)这种赞赏态度也可见冷晓玲、李开盛:《论世界国家生成的不可能》,第115、117页。
(92)[加]罗伯特·考克斯:《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10-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