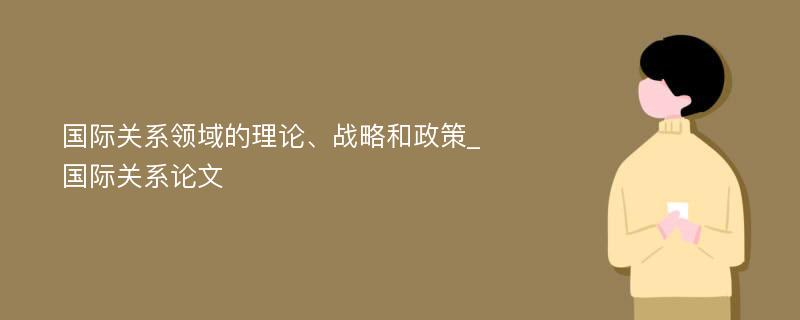
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领域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恩格斯
国际关系学界正在进行一场反思。这场反思的起因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自己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感到不满。②虽然一些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坚持理论发展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不得不面对他们在政策领域日益被边缘化和许多学者主动远离政策领域的现实。③约瑟夫·奈和约翰·伊肯伯里等人提供的证据是学者担任高级决策职务的减少、学者们实证研究偏向国际体系本身而不是具体问题,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理论或者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也在下降。④例如,为了促使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现实主义者专门成立了“促成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Realistic Foreign Policy)。⑤不过,一度在美国政坛得势的新保守主义学者自然会对国际关系学者在政策制定方面影响力下降这一论断不以为然。而且,在近期的美国政界,许多优秀的学者继续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或担纲时政评论,例如约瑟夫·奈、杰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斯蒂芬·克拉斯纳(2005-2007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和鲜明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柯庆生(2006-2008年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以及《新闻周刊》的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
对于学者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一些较为清高的学者例如肯尼思·华尔兹采取了比较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而不在于政策意义,虽然他们自己也发表政策意见。另外一些学者试图做一些辩护,毕竟学者的影响力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参与到具体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他们认为,学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思想和战略。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主张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经验的或实际的分析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⑥斯蒂芬·克拉斯纳明确地指出,“制定外交政策是极为困难的,比火箭科学还要难很多。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而学术界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思想。”⑦既然如此,为什么提供思想及具体理论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在政策领域——起码在常见的舆论中——却很少得到认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成果很少应用于具体政策,以及会出现约瑟夫·奈等很多学者所担心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现象?本文将主要结合现实主义来回答这些问题,并努力澄清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决策领域的必要性、途径和努力方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根源
学术界的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力较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但对于其根源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虽然类似,但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总结起来,大体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较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过于细致具体
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学者)认为,现有的理论过于抽象宏观、范式之间互相排斥,一些理论甚至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无法有效地用来制定(以及解释和预测)具体的外交政策。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华尔兹提出了一个可能让许多人不解的看法,即理论要肯定会远离现实,“一个模型飞机应该看上去像一架真的飞机,然而解释力量的获得却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而不是与之保持接近。一个完整的描述最缺乏解释力。”⑧既然理论远离现实,那么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研究者来说,自然会觉得理论往往过于抽象、甚至是偏颇,重视一些因素而忽视另外一些因素。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说明战争为什么反复出现、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最为稳定这样的“少数重大事件,”但却没有发展出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得心应手的具体外交政策模式。华尔兹强调说,这种宏观的、针对国际体系总体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关于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⑨其他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自由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国际制度很重要,但政策制定者并不能依据这种理论来明白国家应该在什么时候参与国际制度、在国际制度内如何斗争。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谈到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不同感受时指出,“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有或多或少的充分信息和大量时间来做一些回顾性研究。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你没有时间,信息也很有限”。⑩赖斯也指出,学者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论立场,而政治家却不得不兼顾各方面的影响。事实上,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尤其是涉及外交政策的领域还包含着很多普通学者无法了解到的信息,而理论本身由于关注的是最重要的因素,自然会忽略这些信息。因此,学者们难以运用宏观理论来较好地适应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斯蒂芬·克拉斯纳也认同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直接服务于具体政策的看法。他倾向认为,学者可以为宏观的战略提供思想,但可能难以为现实问题提供特别准确的答案。(11)当然,无论是赖斯还是克拉斯纳,他们都不否认理论本身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领域发挥作用。如果政策制定者一开始就不认为现有的理论可以发挥作用,那么他们的战略制定大多肯定会倾向于直觉的判断,或者就是没有战略。19世纪后期,从俾斯麦时代向威廉二世时代转变的德国外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不知道俾斯麦是否精通现实主义理论,但他显然具有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俾斯麦清楚地知道当时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国,从而努力与英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尤其避免与英国争夺殖民霸权。而在威廉二世时代,受到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德国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向,制定了太多不明智的、四处扩张的世界政策(包括海军军备竞赛),使得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大陆联盟体系不到20年间就瓦解了。如果威廉二世能够多一点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和理论指导,他的灾难性的“世界政策”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12)
(二)政治家和学者对理论本身存在误解,或者说并不真正了解
这是造成国际关系学界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不断辩论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即使在同一个理论阵营内部,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分支。因此,要准确的把握某个理论阵营的核心(理论硬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例,一些学者把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确定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就是一个常见的误解。(13)从理论上说,小布什政府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单边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或者称为“进攻性理想主义”),与米尔斯海默的强调国际体系制约、伺机而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小布什政府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反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米尔斯海默鼓吹的把中国作为主要遏制对象有着明显的不同。
类似地,许多人一谈到现实主义,就会把它与强硬、扩张、冲突和战争等联系起来,认为它已经远离了经济全球化、各国间高度相互依赖的现实,因此无法运用现实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台湾问题、贸易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不了解理论本身所造成的误解。这些误解的核心在于把现实主义当成了一种万能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因果关系,为分析其他问题提供了背景,虽然它总有用,并且常常很重要,但在具体条件下,其解释力或大或小。不能把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某一支流极端化,将其视作整个现实主义的代表。因此,如果想要用现实主义来分析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首先要真正深入了解这一理论的硬核,然后再全面把握它的发展流派。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往往缺乏相当专业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想要达到一个准确、熟练运用理论的境界自然是很困难的。
(三)国际关系学者不热心外交政策领域,希望保持研究的价值中立
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就曾批评国际关系学界缺少“与政策相关”(policy-relevance)的研究。但实际上,即使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大师如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等也都曾做过大量的政策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结论与迷惑于诸多细节的常识性结论往往是不一致的,却抓住了现实世界的本质,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对20世纪70年代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趋势的认识。(14)应该说,这样一种局面正在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的现实主义学者不仅开始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外交政策理论,他们的研究也紧紧联系现实,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从财富到权力》、杰克·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斯蒂芬·沃尔特的《联盟的起源》、柯庆生的《有用的敌手》等。(15)
在回顾了国际关系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三方面根源之后,可以看出,对理论家们的真正挑战在于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究竟应该如何应用于现实?那些致力于解释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理论能不能用来分析和制定外交的战略与政策?第二和第三方面原因在于不熟悉理论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自身:他们或者无力从理论出发结合现实,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或者相信那些直觉的理论指导政策选择更为可靠,而根本不愿意关注理论家们提供的种种政策建议。(16)这样一种状况是理论家所无法改变的。如果想要把国际关系理论较好地运用于实践,那么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澄清国际关系理论运用现实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和结构;其次,完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是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政策理论,使之自身能更好、更顺畅地运用于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因此,接下来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什么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对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17)本文仅涉及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界定的国际关系理论。笔者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和华尔兹、斯蒂芬·范埃弗拉等政治学家的论述基础之上。基欧汉曾经指出,“即使人们想从大脑中摈弃理论,这也会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某些暗含假设、命题——虽然它们只是理论的粗陋替代品——的帮助,人们根本无法处理世界政治的复杂现实。”“甚至一个有限的、部分的理论——仅仅包含少量命题和一些指导性说明——也是有用的。”(18)简单地说,理论就是告诉我们,在某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内部,什么因素或者说哪些因素更为重要。这些因素经过锤炼之后成为核心概念,而它对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的理解就成为理论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主要逻辑。(19)对于一个理论来说,它的核心概念和主要逻辑就组成了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而理论硬核所依赖的一系列基本前提实际上就构成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笔者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例,来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与结构。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
1.解释性
按照华尔兹的界定,“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20)换句话说,理论不能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也不能止步于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现象,因为这些都还没有向人们说明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因素和主要矛盾(因果关系)。用戴维·辛格的话来说,“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当描述性要求和解释性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即使这是以牺牲某些描述上的准确为代价的”。(21)那么,理论是如何解释现实世界某领域的重大事件和现象的呢?简单地说,理论是通过发现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一些因素,然后将其概念化而实现的。这些因素就成为分析该领域内核心问题的自变量。这个概念化的过程是理论家们最艰苦的工作。他们需要保证自变量的客观实在性、相对独立稳定和特别的严谨;如果是几个因素的话,还需要阐明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例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肯尼思·华尔兹所提出的“国际结构”变量(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可以用来解释诸多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包括了相互依赖、联盟形成、国家之间向强者学习、均势总会出现等等。解释性理论是规范性理论的基础。一旦我们了解导致某个国际政治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制定出解决的战略和政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涉及变量越少(符合简约性标准)、解释力越强的理论,对于政策制定也会是最有用的。
2.可证伪性
笔者在这里所谈的可证伪性是基于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也就是说,由于理论本身是一个普遍的论断,而现实中我们永远无法穷尽所有的证据,因此也就不可能证实理论。(22)因此,从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说,不存在不可证伪的理论或者说绝对真理。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只能解释部分的现实,都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成立,都不是绝对正确的普遍真理。因此,我们在评价国际关系理论时,只能以“好的理论”(解释力强)或者“坏的理论”(解释力弱)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以“正确的理论”或者“错误的理论”下结论。进一步说,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基本前提是否成立,而这些基本前提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23)既然理论是通过发现本领域内的重要因素(有可能是领域的组织结构如实力对比,也可能是领域内的规范机制如国际制度),持不同范式(世界观、方法论和对该领域的基本判断)的理论家们就可能找到不同的核心因素。举例来说,如果无政府状态、高度相互依赖、国家主体地位的这些基本前提不存在的话,就不可能会有以国际结构作为核心概念的结构现实主义,也不会有以国际制度作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制度主义。(24)因此,我们在使用理论来解释现实、制定政策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厘清理论使用的范围,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理论所强调的核心因素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
前面我们提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性和可证伪性,这两种性质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结构由两部分所构成:作为理论范式的基本前提与作为理论硬核的核心概念、主要逻辑。
所谓范式,托马斯·库恩指出,“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举例说,看一张等高线地图,学生看到的是纸上的线条,制图学家看到的是一张地形图。看一张气泡室照片,学生看到的是混乱而曲折的线条,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熟悉的亚核事件的记录。(25)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一般指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和基本价值观的判断,例如结构现实主义秉持物质主义的本体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国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基本假设、国家利益先于意识形态和普遍正义的价值判断等等;而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的是理念主义的本体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国家中心主义基本假设等等。范式的特征决定了理论阵营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也就是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性”。学者们从不同的范式出发观察国际关系,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和某些因素。因此,很自然地,结构现实主义从无政府状态出发,会关注体系之中的实力对比状况,而建构主义从文化认同的观念本体论出发,会关注国家对彼此的身份认知。
除了范式(基本前提)的差异外,理论硬核的不同是另外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所谓理论硬核的概念是拉卡托斯提出来的,指的是核心概念和主要因果关系,例如牛顿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与库恩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了解范式的革命不同,拉卡托斯详细分析了在一定范式内理论不断发展进步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在拉卡托斯看来,理论的发展是围绕理论的内核不断扩展保护带、解决难题的过程。(26)因此,即使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范式上已经逐步趋同,它们在核心概念和主要因果关系的差异也使得它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27)所谓的主要因果关系,用斯蒂芬·范埃弗拉的话来说,就是主假设——理论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核心假设。(28)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结构,所建立的主假设是国际结构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际制度,所建立的主假设是国际制度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如果结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冲突与合作时抛弃了国际结构,或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抛弃了国际制度,甚至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是“核心的”,那么这两种理论就面临着变质或者说退化的危险。
在理论硬核的基础上,如果是一种如拉卡托斯所说的“成熟科学”,那么就会出现更多辅助假设,也可以称之为推论。一般来说,这些推论是相当具体的,很多也是直接的政策推论。例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的基础上,华尔兹推断说,两极结构是最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政治家们就应该致力于实现体系的两极化。另外的一个推论是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大国的自由度。在单极体系之下,霸权国具有相当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使国际社会有着强烈反对的情绪,美国敢于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29)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确实预言到了新的重大事实。因此,总起来说,可以把理论分解为如下的结构“基本前提→核心概念→主假设(主要因果关系)→推论(辅助假设)”。推论的不同可能导致理论内部出现不同的流派,例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分析外交政策时,出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不同分支,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基于基本假设和理论硬核的统一性。
三、如何将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
从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老百姓所感受到的丰富多彩的现实,以及蕴藏于其间的无穷的内部联系,在理论家那里进行的是有意识的简化。只有通过简化,找到某个领域内最重要的因素、最主要的矛盾(因果关系),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领域内的现象,这样做必然会省略掉许多因素。这一点,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理论家无疑深受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后者曾指出,“在追求作为可满足一定目的的有力工具的理论时,理论往往为我们服务得很好,虽然明明知道它是假的”。(30)华尔兹也认为,理论只是一个智力工具,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对于同一个事实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的。用华尔兹的话来说,“一种理论是对某种行为领域的组织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一种理论要说明某些要素比另外一些要素更为重要,并且要详细阐明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31)波普尔还深刻地指出,理论的内容越丰富,为真的概率就越低。理论之所以必须远离现实、具有简约性,原因在于,针对太多细节情况、要素而建立起来的具体假设,往往会不太稳定、只能解释非常狭窄的领域。(32)而普遍性的理论,因为仅仅关注领域内最重要的因素,就可以具有更广泛的解释能力,并在相当长时间发挥作用。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家来说,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不但可以解释1648年以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可以解释古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内部政治。现实主义总结出来的法则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其他因素影响力的消长而发生太大的变化。理论家们并不是对丰富多彩的世界视而不见,相反他们试图抓住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与其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宏观和普遍性的,不如说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是普遍性的,但同时是关注重点的。
如果回过头来看赖斯和克拉斯纳的评论,我们会发现,赖斯之所以所谈到学者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与政治家相比,学者思考时间充裕自不待言),是因为学者们掌握了关于问题的更全面的知识——这些理论和历史知识同样是重要的信息,可以进行战略性地思考,而政策制定者们则会纠缠于太多具体事务之中,并不一定能从全局的、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许多当前的细节。对于克拉斯纳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理论家,他认识到具体事件的处理需要许多学者们所有意忽略的信息(偶然因素)和和无法获得的信息(机密情报),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家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具体的决策事务。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具有清晰战略思维的人才能更合理地处理具体的环节,因为他们知道各个因素的内在关系、在国家总体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一旦他们有能力获得足够的内部信息,那么他们将有可能制定出更好的宏观战略和具体政策。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战略应用
既然理论的本质是抓住一个领域内的重要因素,那么理论与战略之间就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战略问题就是那些影响全局的、长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3)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基本前提下,国家的对外战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在充满了复杂的利益矛盾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朋友与对手的问题。既然是战略,就应该具有一定稳定性”。(34)国际关系理论从关于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论断、核心因素和主要因果关系等诸多方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例如,现实主义认为,在分析和制定外交政策时,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应该询问国际体系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有力的、可归纳的特征就是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35)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国际战略的东西。首先,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现实主义强调物质性的国家利益,反对以意识形态和抽象道德来指导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依据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确定国家利益,那么所有的外交政策——从敌友的认定到问题的重要性——都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外交从以意识形态画线向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转变看得很清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重点、对外贸易重点、参与国际组织的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次,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前提告诉政策制定者,最终维护自己利益的办法是不断增强实力,而不是诉诸国际法、世界舆论或者是“寄希望于下一代”、“寄希望于某国人民”的做法。再次,以国家为主体的基本前提也提醒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领导人必须要代表国家利益,因此,“交朋友”的方式只是开展外交的途径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方面,可以从伊拉克战争美国毫不讳言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中看得很清楚:在关键时刻的盟友只会是利益一致的愿意者,对霸权国来说尚且如此。(36)
同样,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因果关系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建议。首先,实力对比结构这样一个核心概念为决策者对自己国家的战略定位提供了分析依据:国家应该通过分析体系内单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来确定自己的相对实力位置。其次,这个核心概念告诉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国际结构之下是否处于有利地位,关键在于它自己的相对实力位置,以及与结构中强国的关系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吉田主义”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现实主义大战略,通过与美国的结盟减少了安全负担、减少了领土和战争债务的麻烦、带来了经济复兴等等。(37)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它选择与最强者结盟。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告诉政策制定者,哪些国家是更重要的、需要作为外交政策主轴的、付出最多资源甚至果断与之结盟的。再次,实力结构的概念告诉政策制定者要时刻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依据结构状态来制定其他诸多的具体外交政策,不要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这个核心概念还告诉政策制定者,“多极化”不是可以轻易促成的,因为单极、还是多极的界定是依据单个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变化无常的联盟或者集团。
可能其他现实主义者还可以梳理出别的许许多多的战略建议。但总而言之,理论家给政策制定者的忠告是:任何时刻都要保持一个清晰的战略思维,意识到哪些因素是不可超越的结构性限制,意识到自己的战略定位。
(二)国际关系的政策应用
如何将精炼的理论运用于具体政策的制定,这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笔者仍然认为,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罪责主要并不在于理论自身,而在于实践者。换句话说,抓住核心因素、关注主要矛盾、明确战略定位,是一切具体外交政策的基础。事实上,理论家提醒说,“分析家如果不从一开始就仔细考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就可能会错误地归因于那些虽然可见但只具有附属意义的因素”。(38)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已经确定的战略定位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在具体问题、事件中国家可以利用哪些机会、采取哪些策略来解决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就如前面提到的,即使是面临特别具体的问题,情报机关的信息也未必就是全面的;相反,可能涉及更多、更广泛的宗教、历史、哲学、心理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如赖斯所说,学者未必在信息方面就居于劣势。一旦参与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去,有理由相信优秀的理论家也会成为优秀的政策制定者。
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应用潜力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第一,许多普遍性国际关系理论能推出相对具体的推论(辅助假设)。如前所述,这些辅助假设很多是直接和政策相关的。例如,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前提、国际结构的核心概念,可以得出推论说,国家必须向体系中的最强者学习,否则就不能增强实力、实现自助。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政策推论。如果决策者关注自由制度主义,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本身强调了多边国际制度对霸权的制约、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自然也就会接受自由制度主义的政策推论: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的理论因为核心概念和主假设的不同存在不可通约性,但是从它们所推导出来的政策推论却未必一定是相互冲突的。例如,国家向最强者学习和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本身是不矛盾的。即使有些政策推论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例如日本追随美国和积极参与联合国),一般来说也有相当的回旋空间。第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前文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围绕着如何分析外交政策的问题,发展出了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的许多新流派,把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39)这些新的理论发展着眼于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在结合了体系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实力、观念和政府结构等因素之间在决策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对于理解国家具体外交政策(相对于国际环境要求)的偏差或者说非理性、促进外交决策过程的理性化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四、结论
总结起来,本文谈到了如下观点:(1)虽然学者们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有所降低,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国际关系学界、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理论本身对于决策的作用就一定在削弱;(2)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重要因素、主要因果关系,具有简约性、解释性和可证伪性等特征;(3)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直接地运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对于了解国家的战略定位、利益目标、敌友选择等都具有指导意义;(4)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可以运用于具体的政策研究,不管是提供清晰的战略底线还是提供具体的推论;(5)理论家们和具有理论思维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从事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时,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不是劣势。
当然,以上所说的理论和理论家在政策领域的优势,要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理论家自己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理论的本质;另一方面,理论家要学会在实际的运作中整合本理论核心因素与其他诸多因素的关系,明智地利用国际体系所给予的各种机会,通过许许多多的政策细节,推动国家实现总体战略目标。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对理论的学习、对理论思维的培养无疑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384页。
②Joseph S.Nye,"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4/12/AR2009041202260.html.
③安德鲁·贝内特和约翰·伊肯伯里在回溯了100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研究趋势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见Andrew Bennett and G.John Ikenberry,"The Review's Evolving Relevance for U.S.Foreign Policy 1906-200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November 2006,pp.656-657.
④事实上,要证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政策影响力在下降,我们起码要一对一地访谈高级决策者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运作,判断其政策的制定是仅仅以情报和信息为主,还是结合了相当的理论和历史认识,但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⑤具体情况参见该联盟的网址:http://www.realisticforeignpolicy.org/.
⑥〔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林茂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⑦"Does the Academ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tter in the Real World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http://news.stanford.edu/pr/03/krasner129.html.
⑧〔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⑨See Kenneth N.Waltz,"Neorealism: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XV,Spring 2004,http://www.columbia.edu/cu/helvidius/archives/2004_waltz.pdf.
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赖斯对于信息获取的认识,与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所指的缺乏信息,往往是指缺乏有关内参、内部机密、即时的信息,而赖斯指的是全面的、背景性的知识。参见该讨论会的新闻简报:http://news.stanford.edu/pr/03/krasner129.html.
(11)参见该讨论的会议简报:http://news.stanford.edu/pr/03/krasner129.html.
(12)一个非常好的网络评论参见:http://www.riwh.org/bbs/redirect.php? tid=326&goto=lastpost&highlight.
(13)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李永成对此做了的探讨。参见李永成:《被误读的米尔斯海默:也谈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第66-71页。
(14)在有关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程度方面,华尔兹和吉尔平持有相同的看法,即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使得当前的国家间相互依赖高于19世纪末期;在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之下,大国的行动自由度反而增加了。这与许多人从繁忙的航线、港口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不同。See Kenneth 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http://www.irchina.org/xueren/foreign/view.asp? id=13;〔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四章“全球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Stephen M.Walt,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1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7)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一些探讨,可以参考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1期,第19-25页。
(18)Robert Keohane,"Realism,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
(19)秦亚青把波普尔的问题意识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69页。
(2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6-7页。
(21)J.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Vol.14,No.1,Oct.,1961,p.79.
(22)〔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9-63页。
(23)关于范式的介绍,参见徐明明:《论社会科学范式的结构》,《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53-56页;郑杭生、李霞:《关于库恩的“范式”:一种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19-125页。
(24)如果我们考察罗伯特·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到《霸权之后》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建立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基础之上。相互依赖理论阐明了世界政治的新范式(经济相互依赖、军事力量的有效性下降、联系渠道的多样化等等),为国际制度成为核心自变量奠定了基础。
(25)Thomas S.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11.
(26)〔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2页。
(27)在批判所谓的“新—新合成”的时候,需要对理论硬核的差异及其带来其他效应需要给予更深层次的评估。毕竟,由于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从国际政治理论向外交政策理论转变)就会呈现出相当的不同。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趋同的批判,参见秦亚青:《译者前沿》,〔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5页。
(28)〔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29)华尔兹曾指出,“作为冷战的胜者和唯一的大国,美国的行为和其他不受制约的大国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缺少制衡的力量,该国就会依据自己的国内冲动——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其他的——来行事。”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24.
(30)〔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3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1页。
(32)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的中文版序言中认为的关于他的理论仅仅只能解释“少数重大事件”的说法,其实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理论广泛的解释力。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构现实主义只能独自充分解释少数重大事件,但可以有效地用来解释很多的问题。
(3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页。
(34)宋伟:《浅说国际战略与中国的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6页。
(35)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197.
(36)相关介绍和报道参见《纽约时报》、CNN等网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Coalition-of-the-willing; http://www.nytimes.com/2003/02/19/opinion/the-coalition-of-the-willing.html; http://edition.cnn.com/2002/WORLD/europe/11/20/prague.bush.nato/.
(37)Richard J.Samuels,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p.36-37.
(38)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No.1,October 1998,p.151.
(39)宋伟:《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25-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