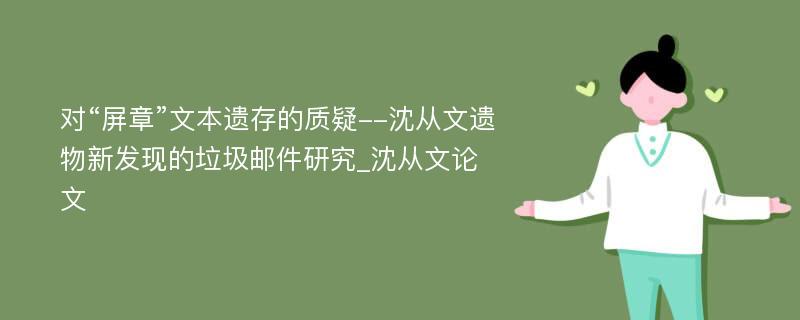
遗文疑问待平章——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废邮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文论文,新发现论文,疑问论文,从文论文,平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集在这里的沈从文佚文废邮十四篇,是我和裴春芳、陈越两位同学近两年来陆续发现的。其中《废邮存底·致丁玲》、《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敌与我》、《新废邮存底·关于〈长河〉问题,答复一个生长于吕家坪的军官(残)》、《致莫千(残)》、《给一个出国的朋友》、《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胜利》、《诗人节题词》八篇由我辑录,《读书随笔》、《梦和呓》、《文字》三篇由裴春芳辑录,《旱的来临》、《新书业和作家》、《纪念诗人节》三篇则由陈越辑录。这些长长短短的佚文废邮诚然零碎不成系统,不能与重要的创作相比,但其中一些篇什也包含着相当重要的信息,或许为沈从文研究者所乐见,所以我又对辑录稿通校一过,并酌加注释,集中刊布于此。坦率地说,由于个人闻见有限,有些篇什或已被人发现在先也未可知,倘如是,则理当以先发者为准,我们的后发自然作废。关于一些文本的考辨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的介绍,说来颇为繁琐,不便夹杂于校注之中,所以在这里归总交代一下。
友谊与爱情的遗迹——沈从文致丁玲的信和给张兆和的情书
前面的《废邮存底·致丁玲》、《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旱的来临》三篇,都是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作的,均刊载于杭州发行的《西湖文苑》杂志上。
刊载于《西湖文苑》第1卷第3期上的那封《废邮存底》,目录页署名“甲辰编”、正文里又署名“甲辰”,而“甲辰”乃是沈从文的笔名之一,并且这封《废邮存底》末尾的附识——“这是我一九三○年在武昌时写给最近失踪的丁玲女士若干信中的一封信从文识”——已完全点明了写信者和收信者的真实身份;复查沈从文1930年9月16日至12月下旬在武汉大学任教,则此函当写于这一时期。为示区别以便于研究者援引,我在整理时酌改为《废邮存底·致丁玲》。刊载于《西湖文苑》第2卷第6期上的诗作《旱的来临》,不论在目录页还是正文里,作者都署名“岳焕”,而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岳焕”也是他的笔名之一。按,《西湖文苑》虽然是个地方性的小刊物,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在那上面假冒沈从文之名与笔名发表作品,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惟其是个地方性的小刊物,研究者一向不大注意,而沈从文当年身在异地并且辗转不定,这个刊物他未必期期都能收到,纵然收到,也由于战乱迁徙而未必能够一一保留下来,这或者就是这些文字长期散佚在集外的原因吧。
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的诗,多为情歌、拟情歌和情诗,像《旱的来临》这样咏叹乡村旱灾、农民艰辛的诗篇,是颇为少见的。《废邮存底·致丁玲》则尤为珍贵。近年来,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已成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涌现出了《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题研究著作,该书并附录了相关的讨论文章和参考文献,但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却未见涉及。研究者们利用较多的还是沈从文的《记丁玲》及其续篇等,在这些著作中沈从文也摘引了他与丁玲之间的多封往来信函,可惜大都不完整。比较而言,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可能是现存最长也最为完整的沈从文致丁玲书信,从中可以推知,丁玲曾经写信与沈从文讨论妇女问题,所以沈从文便复函给她,非常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得出来,两位好朋友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分歧显然无碍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时当丁玲遭难之际,沈从文特地发表这封致丁玲的旧函,并加附识点出丁玲的“失踪”,这无疑有声援友人、问难当局之意。所以,不论对研究沈、丁的关系还是探讨沈从文的妇女观,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颇为有趣也颇难辨识的,是发表在《西湖文苑》第1卷第4期上的那封《废邮存底》。
在该期目录页和正文里,这封《废邮存底》都署名“甲辰编”,信前并有编者“甲辰”的一段题识云:“辛·第廿九号·从一个海边寄到另一个海边。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她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末尾有写信时间“二十年、十一月”。为示区别并便于研究者引用,我在整理时改题为《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这显然是一封情书,写得颇有情趣,可究竟是谁写给谁的呢?不待说,“甲辰”自然是沈从文,但既作 “甲辰编”,则他或许只是这封信的编发者也未可知,何况“甲辰”又特别加上那么一段题识,径直告诉读者该信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的呢!但问题是,不论那个“三十岁的女人”抑或那个“十九岁的男子”,都无名无姓,难以稽查。当然,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初期)沈从文的交往圈子里,也颇有几个年近“三十”而仍然热情敢爱的知识女性,可要说她们竟然会爱上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男子,那也似乎太超前了些,几近于不可能。即使在沈从文的朋友圈里确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信,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也更加难解——事关年龄如此悬殊的一对男女私情(几近于今日所谓“姐弟恋”)的情书,又怎么会落到沈从文的手里、并且任他拿来公开发表呢?倘说是沈从文无意中得睹一位30岁的女性的情书,也很难设想她或她的年轻情人会同意沈从文把如此“出格”的情书拿去发表呀!然则,难不成沈从文是偷窥、偷抄出来抑或是胁迫别人同意他拿来发表的吗?虽然在绯闻满天飞以至人们已经不以绯闻为非反以为荣的今日,情书的公开被“晒”已是稀松平常之事,但我们恐怕很难设想为人正直善良的沈从文在当年会如此不负责任地行事吧!
既然按照“甲辰”即沈从文的“题识”之提示去看,这封私密的情书的被发表反倒成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也就只好返回到“甲辰”即沈从文自己那里——或许他才是这封情书的真正“编写者”,而他所谓“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的说法,也可能是小说家惯用的有意诱导读者的障眼法,旨在掩饰一个暂时不愿被人知晓的真实: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女子”的情书,而那“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那“一个十九岁的女子”,则很可能就是当时正在恋爱中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但窃以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按,沈从文自1929年9月起在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也就在这年冬天他爱上了该校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张兆和。次年2月新学期开学,沈从文也开始了对张兆和的辛苦追求,中间颇多曲折而锲而不舍,至1931年前半年渐有转机——张兆和不再拒绝他的爱情了。欣喜若狂的沈从文在1931年6月某日写信给张兆和,随后并将这封信以《废邮存底(一)》的题目,发表在该年6月底出版的《文艺月刊》第2卷第5-6号合刊上,现改题为《由达园给张兆和》,收入《全集》第11卷——据说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数百封情书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件”,①可见其珍贵。从此之后,二人的感情发展就比较顺利了。1931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其九妹岳萌也跟随他到青岛读书,而张兆和则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学习,到次年7月张兆和毕业,沈从文则乘暑假之机到苏州张家看望她。……这封编号为“辛·第廿九号”的《废邮存底》,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在1931年11月的某一天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算法,1931年的沈从文恰值三十而立之年,而张兆和也正当19、20岁的花季,并且他们也恰好各在一个海边——沈从文在青岛而张兆和在吴淞,这正与“甲辰”即沈从文在这封《废邮存底》前面的题识里所提示的情况——“从一个海边寄到另一个海边”——的情况相合。至于题识里所谓“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她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的说法,虽以无名无姓并且性别颠倒的障眼法掩饰了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却也真实地表达了三十而立的沈从文对年轻的张兆和的深情和隐忧。那深情与隐忧正可与半年前的《由达园给张兆和》相校读。由于来自湘西那样一个颇有些神秘的地方再加上受“五四”以来流行的爱情神圣观念之感染,沈从文很喜欢把男女爱欲作泛神论的理解。即如他在前一封信中就对张兆和说“我赞美你,上帝!”并谦卑地自称为她的“奴隶”,在这封信里又以一个爱情迟到的盛年女性自喻,情不自禁地向对方倾诉自己的崇拜与感激之情,一如题识所言“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然而由于二人的年龄差距不小,沈从文也不免有些担忧和忧郁,所以他在上封信里乃以诗人自喻,以为“‘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而在这封信里,作为沈从文化身的那位年长的女性也同样对其年轻的爱人感叹道:“我知道我老了,若是我聪明一点,就是我在这时能有一种决然的打算。我死了比我活下还好。我可并不想死。我将尽这件事成为一个传奇,一个悲剧,把我这种荒唐的热情,作为对这个新旧不接榫的时代,集揉凑成的文明,投给一种极深的讽刺。”……不难理解,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既让年纪不小的沈从文倍感幸福,但两人在年龄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差距,也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沈从文同时不无自卑和忧郁,如此矛盾的情结在两封《废邮存底》中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连表达爱情的比喻——如把心爱的人比作“上帝”和“月亮”——也如出一口。
此外,这两封《废邮存底》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关联。那半年,正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取得可喜进展之际,却又是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最感孤苦无助之时,作为好友的沈从文对丁玲自然特别关心,但无奈自己身在异地,于是他寄望于与丁玲就近的张兆和,所以在给张兆和的第一封《废邮存底》里探问道:“听说×女士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②这“×女士”即曾到中国公学讲演的丁玲;无独有偶,在《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里,写信者也殷勤询问丁玲的情况,并殷切期望收信者能与丁玲成为好朋友:“丁玲女士你见到了没有?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朋友,你们值得互相尊敬。”……诸如此类的关联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顺便说一句,《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一开头提到寄给对方的“真珠螺,××妹一个人在海滩上寻找了多久日子才得到。有种黑水晶,不从海边得来,(它们是乡巴老,)它的生长地方,在有仙人来去的劳山”,也正暗示着沈从文当时的所在地青岛,“××妹”当指跟随着沈从文一起生活在青岛的妹妹沈岳萌。
如果我的推测和考证多少有点道理,则沈从文对他的这封情书做如此特别的处理,也应该有点特别的考虑才是。这或者与张兆和同是《西湖文苑》的作者有关。按,发表在《西湖文苑》第1卷第3期上的兰姆作品《水手舅舅》及第1卷第4期上的托尔斯泰作品《苏拉脱的咖啡店》,都是张兆和翻译的。她的这些译作很可能是沈从文拿去发表的,而《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也发表在第1卷第4期上。不难推想,这样一封热烈的情书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一定会把年轻的张兆和暴露在读者的视野之下,而让她感到难堪的,所以沈从文不得不对这封情书做改头换面、颠倒性别的处理,即以障眼法保护年轻的爱人也。
复检《全集》第15卷收有沈从文的诗作《微倦》,编者并于诗后注明“本篇发表于1933年5月14日《西湖文苑》第1期,署名季蕤。”可知《全集》编者是知道《西湖文苑》这个刊物曾经发表过沈从文的作品,但又为何不收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的其他几篇文字呢?这些文字在今天看来也毫无违碍之处呀。推想起来,编者也许只是依据沈从文的存件编入《微倦》的,而未及翻检原刊吧,所以才把其他几篇遗漏在《全集》之外了。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全集》附卷里的《沈从文年表简编》,以及吴世勇所著《沈从文年谱》,也都没有著录《微倦》之外的其他几篇发表在《西湖文苑》上的沈从文文字。这自然不足怪,因为不论《全集》还是年表、年谱都属草创,任谁也难以遍检群刊,有所疏忽其实是难免的。说来可笑而又侥幸的乃是我自己。其实,《西湖文苑》乃是我此前亲眼看过的刊物——我整理的《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中收录的一篇沈从文佚文《〈三秋草〉》,就是从《西湖文苑》第1卷第2期上辑录的,其他如《废邮存底·致丁玲》、《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我当时也翻阅过,并有简单的记录,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我误以为这两篇可能已经收入《全集》了,因而也就没有翻检《全集》进行核对,遂与这两篇重要的沈从文废邮失之交臂。直到最近,为了整理下面的另一些沈从文佚文废邮,而重新翻查自己阅读旧书报刊的笔记本,又一次看到了几年前关于《西湖文苑》的记录,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许有失误——既然《〈三秋草〉》是佚文,则同一刊物上的两封《废邮存底》,也很有可能被《全集》漏收了啊!于是托陈越同学去把这两篇复制回来,而陈越是个仔细的人,他翻检该刊还发现了我疏忽未记的沈从文诗作《旱的来临》以及张兆和的译文,这才使得这几篇长期遗漏在外的沈从文佚文废邮得以重新捡拾回来。虽然“楚弓楚得”的豁达是自古相传的美谈,但文献的拾遗补缺所要求于我们的,不是豁达与随便,而是细心和耐心,像我这样与沈从文的佚文废邮交臂失之而又居然复得之,真是侥幸得让自己惭愧不已。
爱国与爱欲的焦虑——沈从文抗战及40年代的佚文废邮
其余十一篇佚文废邮都写于抗战及40年代,其中有些篇什之出于沈从文之手,应无庸议。如《敌与我》、《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胜利》、《诗人节题词》、《新书业和作家》、《纪念诗人节》五篇,在原刊或原报上都署名“沈从文”或“从文”,这些充满了感时忧国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文字,多可与沈从文已经人集的某些作品相参证,并且发表它们的刊物也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他或是其编者或曾为其特约撰述人等等,所以在那些报刊上冒名顶替沈从文发表文字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排除的。诗作《文字》的作者署名“雍羽”,这是沈从文40年代发表诗作时比较常用的一个笔名。至于《新废邮存底·关于〈长河〉问题,答复一个生长于吕家坪的军官(残)》、《致莫千(残)》两封废邮,则是从许杰先生的批评文章《论沈从文的写作目的》(该文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时原题《沈从文论写作目的》)里转辑出来的。从许文中不难推知,沈从文的这两封信曾在当年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可惜许先生在引用时没有注明原信发表的出处,所以这里转辑的乃是不完整的残篇,完整的信函应该还存在于世,希望大家帮助找到它们。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有些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和书札,也不乏改题入集者,所以此次我也尽可能地把上述文字与《全集》进行了核对,但《全集》卷帙浩繁,我实在不敢保证自己就没有疏漏或误断之处。例如《新废邮存底·关于〈长河〉问题,答复一个生长于吕家坪的军官(残)》、《新书业和作家》和《纪念诗人节》三篇,我读着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可是怎么翻检也查不出它们曾经改题入集。这或许因为同样的意思,沈从文也曾在别的文章中多次申述过,因而难免出现言近似而文不同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排除我的翻检还不够彻底、核对还不够细心,所以倘有失检与误断之处,还请读者和研究者指正。
需要考定归属的,是《读书随笔》、《梦和呓》和《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三篇。
《读书随笔》与《梦和呓》两篇,分别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57期(1938年9月26日)和香港《大公报·文艺》第417期(1938年9月29日)。两文发表的时间如此接近,而且都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则它们的作者“朱张”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这个“朱张”显然不大像一个人的真名,而更像是某个作家的笔名。然则“朱张”到底是谁呢?从他接连写作的这两篇文章来看,其时的“朱张”似乎在感情生活中深有感触而不能自已,于是埋首读书、借以遣怀,而他读的书中恰有法国现代作家法郎士的爱欲小说《红百合》,这让他颇有会心,遂萌生了也创作一部类似的小说《绿百合》的想法——
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
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弱颈长蒂,无语如语,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挡。
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事情和意思也出现在沈从文同一时期的文字《生命》里。按,《生命》一文已经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编者在该文末尾附注云:“本篇前三个自然段曾于1940年8月1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5期发表,署名雍羽。1941年8月以全文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烛虚》集。”应该说,《生命》与上述两文的相同并非偶然的巧合。事实上,读者只要把《梦和呓》与《生命》略作校读,就不难发现前文乃是后文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梦和呓》已不能说是一篇佚文了,而之所以仍然把它作为佚文,一则因为沈从文曾经单独发表过它,所以单篇辑录在此,以存其旧,二则由此可知“朱张”乃是沈从文的笔名之一,据此则同样署名“朱张”的《读书随笔》也当出于沈从文之手,并且《读书随笔》也在谈论着《红百合》和男女问题,所以它属于沈从文的佚文,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较难辨别的,是那封《给一个出国的朋友》的信。这封信写于1945年9月29日、发表于同年10月20日出版的《自由导报》周刊第3期,作者署名“章翥”。几年前我就碰到过这封信,但由于对“章翥”实在陌生得很,误以为他是一个无名作者、他的信也无关紧要,所以就没有细看。幸而因为要校录《自由导报》上的冰心佚文《请客》和沈从文佚文《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胜利》(二文均载该刊第5期),我不得不反复翻检该刊,也就不免与《给一个出国的朋友》多次碰面了。去年春天又一次碰到这封长信,心想何妨看看呢。这一看,才感觉到它很可能是沈从文写给即将出国的卞之琳的一封长信,大概因为信中涉及到卞之琳和张充和之间曲折而无果的恋爱等私密问题吧,所以沈从文不得不隐去自己的和卞之琳的真名。
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猜想”,要证明这个猜想,自然还需要一点考证。
按,《自由导报》周刊创刊于1945年9月29日,乃是西南联大文科师生的一个小园地,先在昆明、后在上海出版,沈从文和卞之琳都是该刊的特约撰述人。按理说,发表在该刊上的《给一个出国的朋友》,其写信人和收信人很有可能就在西南联大的文人学者圈中。而我之所以判断这封长信是沈从文写给卞之琳的,大体有以下三方面的理据。
最为显然的一面是,这封信的笔调实在很像沈从文的。即如开首的“我因答应好家中人今天下乡,回去作火头军,所以来不及送你了”几句,就是典型的沈从文口吻。这在沈从文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他少年从军,与司务长、火头军之类中下层军人混得很熟、感情很深,他早期的小说《会明》、《灯》就表现了对这类人物的“温爱”。应该说,这种感情已转化为沈从文的生活情趣,所以成家后的他是很乐意为妻子儿女“作火头军”的,以至于为妻子儿女“作火头军”成了他颇喜欢说的口头禅。直到晚年,沈从文在致一位老友的信中说到两个业已成家、在外工作的儿子,他仍欣然表示:“我们可能将来要去那边作‘婆婆’和‘火头军’的!”③沈从文的这种生活情趣,如今在他的家乡凤凰县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即如“凤凰旅游网”上最近的一篇文章说到沈从文等凤凰名人的爱情时,就有这样的称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让女人管家理财,而且常常自愿做火头军煮饭、炒菜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孩子们吃,并以能炒两三个好菜而自豪,亲情盎然。”④诸如此类沈从文式的语句,在这封长信中还有不少,熟悉沈从文作品的人读后便知,无烦列举了。
不过,仅从语言风格来判定文章的归属,是未免冒失的。更足资参考的,也许是人、事、情的关联。就此而言,也确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线索。即如从这封信的上下文可以看出,收信者过去曾为诗人而今身为教师,他刚刚幸运地获得出国的机会,却因为与女友的关系不顺而苦恼殊甚,而在那时的西南联大里,能够同时遭遇这等幸运和如此不顺的教师兼为诗人者,几乎可以说是非卞之琳莫属了;并且特别巧合的是,在当时的文坛和学院圈子里,最了解卞之琳多年来“为情所困”(恕我用了这个有点庸俗的套语)之底细的人,也同样可以说是非沈从文莫属——他既是卞之琳的好友又是张充和的姐夫呀。据卞之琳先生晚年回忆——
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文化委员会新任驻华总代表罗思培教授(Prof·Roxby)前往重庆赴任,路过昆明,经西南联大同事英国作家白英(Robert Payne)为我介绍与罗思培及其夫人晤谈,并找我的英文著作译稿向他们吹嘘,提供审阅,当年冬天我从重庆英国文化委员会总代表处接到通知,邀请我次年去牛津大学拜里奥(Balliol)学院作客一年。……⑤
卞之琳说自己在1945年冬天接到了出游英伦的通知,这当是指英国文化委员会正式发来的邀请函件。实际上,由于有西南联大的英国同事白英的居间介绍与沟通,卞之琳稍前些时候就已得到了将被邀请出国的讯息,并有可能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最知心的前辈兼同事沈从文。得知这个消息,沈从文自然很为卞之琳高兴,然而以他对卞之琳感情隐秘和优柔个性的了解,又不禁担心卞之琳会因为感情的原因而恋恋不舍、裹足不前。于是沈从文便写了这封长信给卞之琳,既中肯地分析了卞之琳恋爱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劝他接受无情的现实,同时也鼓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眼光应该远大点,不要恋恋于诗和情,还要有更大的文学抱负以至政治抱负——“也许反而可从国外广泛的学来一些知识,成为一种坚强结实单纯的信念,准备明日为××××的愚顽势力与堕落风气而长久对峙!”
诚然,这些关联乃是我根据相关情况分析和推测出来的。即使我的分析和推测合乎实际,也难向沈从文和卞之琳两先生求证了,所以临了我们还得求证于文本深层关联的校读,即把这封信与沈从文的其他文字相参校,看看能否在它们之间寻找出一些共有的而又只属于沈从文的元素——他所独有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及其修辞策略等。这样的元素似乎不难寻找。尤其是这封信所表达的爱欲观和文学观,与沈从文的观点非常契合。譬如,沈从文在小说《梦与现实》(此篇后来被沈从文用以代替真正的《摘星录》)中,反复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及相近的语词“古典”与“现代”,来标示笔下人物在个人情感生活中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之两极,这可以说是沈从文特有的观念和修辞。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封《给一个出国的朋友》的信中,写信人也对收信人在爱情上的矛盾态度作了同样的分析——
由于你生命中包含有十九世纪中国人情的传统,与廿世纪中国诗人的抒情,两种气质的融会,加上个机缘二字,本性的必然或命运的必然都可见出悲剧的无可避免。
正因为洞察到收信人情感气质的矛盾而使他在爱情上难免失意,所以写信人便敦劝收信人干脆潇洒放手,并激励他到了国外正好可用文学来转化其被压抑的爱欲——
你正不妨将写诗的笔重用,用到这个更壮丽的题目上,一面可使这些行将消失净尽而又无秩序的生命推广,能重新得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一面也可以消耗你一部分被压抑无可使用的热情,将一个“爱”字重作解释,重作运用。
这些话不仅像沈从文的口吻,而且径可说是其生活与创作的经验之谈。如所周知,用文学留住行将消失的生命之根、为人情人性尤其是人的爱欲做写照,并以此促进民族品德的重造,正是沈从文反复表达的审美理想。即如在《〈长河〉题记》里他就再三致意:“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⑥在《〈习作选集〉代序》里,沈从文更坦承他之所以创作《边城》——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⑦
两相校读,从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到用语修辞都契合到难分彼此。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良有以也”。
倘说单一层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想把上述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则似乎可以证明《给一个出国的朋友》确是沈从文写给卞之琳的一封谈爱情和促远行的长信,其中贯穿着沈从文式的用文艺来发挥个人受压抑的爱欲情热以促进国家民族重建之大业的旨趣——
这是你热情的尾闾。工作的成果中将永远保存有你对于人生热忱的反光,也还可望从另一世纪另一类人生命中燃起熊熊的大火!……我们从这一点看去,用历史,文学,和美术,来重新燃起后一代人的心,再来期望这个民主政治罢。也让我们从工作的试验中,消耗自己至于倒下,却从工作成就中,实证生命的可能罢。熟人关心你生活的,常以一个合理幸福的家庭,在一种新的情绪意境中,得到一点休息,更得到接受明日更大的勇气。事实上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生命热忱的充沛,又那是一个女孩子能消耗,能归纳,能稳定?热情的挹注,对女人,将是一种母性正常发育与使用,对男子,怕还是需用长久耐心和深致析剖并重新组合的艰难工作,方始有望!对另一具体国家,我们的战争已结束了,对抽象人生,我们的战争将从生命接近中的今日起始。你和我都知道,这正是一种完全孤立绝望无助的战争,不能退后也不应当退后,因为生命本身即有进无退,接受它时,虽不免稍感悲伤,然而都无所用悲观。
劝人亦所以自劝。把这些新发现的和我们此前两次公布的另一些沈从文佚文废邮,⑧与《全集》中的其他文本相校读,不难发现其间许许多多的“问题”之关联,最终都指向沈从文40年代以来特别焦虑的国家重建和个人爱欲两大问题。满怀热忱的沈从文在此力劝朋友努力奋斗、不要悲观、抽象抒情、不计功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沈从文对自己的勉励。只是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此所以由于国家政治和个人爱欲两方面都不尽如意的压抑之交攻,还是在40年代末把沈从文逼入到“疯与死”的绝境中不能自拔。
对这些问题,此前我和裴春芳也各从或一方面做过初步的探究,但限于能力和文献的不足,那些探究未能深入且不无疏漏。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自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接近问题,但要真正弄清问题的症结,无疑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校读相关文献、在更大的视野里梳理问题的来龙与去脉,并且需要更仔细地倾听作家话里话外的心声,才有可能。而要把可能变为现实,自然有待于花更大的功夫和篇幅去作仔细地平章分析,那就需要另文专论了。而本文只是一篇介绍文献的考证小文,已唠叨词费而不免破费刊物的篇幅了,且就此打住吧。
注释:
①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沈从文:《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③沈从文1970年9月22日复萧乾,《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④“凤凰古城”:《凤凰名人与爱情》,文章来源:凤凰旅游网(http://www.fhmjy.com)。
⑤卞之琳:《赤子之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⑥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⑦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⑧解志熙辑校:《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裴春芳辑校:《沈从文集外诗文四篇》,并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又,裴春芳辑校:《沈从文小说拾遗——〈梦与现实〉、〈摘星录〉》,载《十月》2009年第2期。
⑨解志熙:《“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裴春芳:《“看虹摘星复论政”——沈从文集外诗文四篇校读札记》,以上并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又,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载《十月》2009年第2期。商榷意见请参阅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