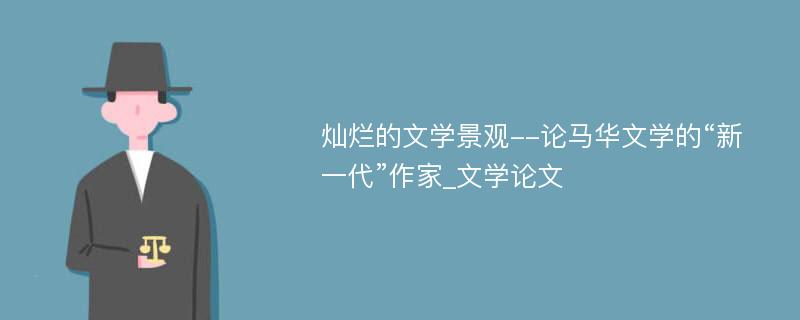
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关于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新生代论文,亮丽论文,作家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这是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我指的是近年来出现于马华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如钟怡雯、辛金顺、陈大为、林幸谦、褶素菜、寒黎、吕育陶、陈强华、黄锦树、林惠洲、许裕全等。他们出生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又大多曾经留学于台湾,被称为马华文学的“新生代”。
他们的出现,犹如马华文学园地上新栽种的奇花异卉,虽然还显得稚嫩,却生机盎然,英姿勃发,把马华文学这块园地装点得更加艳丽多姿,充满着活力和希望,格外耀人眼目……
这群“新生代”作家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他们出生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投身文学,这段时间,正是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转型期。由于结束了多年的政治动乱,又处于战后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当政者实行民族和睦的政策,使这个由多元种族组成的国家,政局稳定,民主化进程加快,自主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和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文教育事业也较前受到重视。
“新生代”作家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长的。因此,他们自小便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免除了“前行代”和“中生代”作家们都曾经有过的对生存的忧虑。他们都目睹或亲身感受到社会进步对社会生活及人们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变化。
但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异化作用,使人们更多地重物质而轻精神,重经济而轻文化,文学创作也日渐式微,后继乏人,只能在艰难中求生存。正如作家林云龙说:“物质文明也影响马华文学的创作风气,现在马华文坛没有多少支‘健笔’,社会也不鼓励作家,连展示马华文学的橱窗也不多了。”这种状况对于他们成长,又起着“刺激”和“催生”的作用。钟怡雯说:“某些前辈作家没有意识到语言技巧提升的必要,而不断以较粗糙的语言模式实践其写实主义的圣旨。忽略了语言技巧和内容必须相辅才能相成。某些优秀的中生代作家,被昔日稿酬微薄、风气低迷的文学环境磨掉了壮志,而销声匿迹。才情不足的、封笔休耕的、加上惜墨如金的,以致马华散文以新生代为创作主干,这也许是时势使然吧。”(注: 钟怡雯:《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 —1995)·序》。)她说的是散文创作的情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它方面(诗、小说等)的情况也大多类此。诚然,她对老一辈和中年一辈作家的分析与评价或许不够准确,但“时势使然”这四个字,则是符合马华文学的实际情况的,也可以说,“新生代”作家群的出现正是“时势使然”的结果。
二
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带有某些群体性特征。他们被称为“六字辈”、“七字辈”,即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年龄在三十岁上下,人数不止一个两个,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群体。所谓“无形”,是说他们并未成立有组织的团体,也谈不上同一个创作流派,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之所以把他们看成“群体”,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他们大多留学台湾。他们在国内时,便已接受了华文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华文基础,也培养了对华文的浓厚兴趣。例如钟怡雯,“自小受传统的学院训练,熟读古诗文”,“一直接受华校的华文教育”(注:赖佳琪:《钟怡雯:写作和真实应该分开》,《文讯》第137期。) 。但由于当地“华人社会虽然有很强劲的经济能力,却一向不注重人文的发展”(注:《蕉风》第474期《编辑人语·期待》。),因此, 他们便纷纷留学海外,而且主要是台湾。
他们为什么大都选择到台湾去留学呢?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而外,最重要的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一点也与在他们之前去台湾留学的人相似:“他们在马时奉为大家的一线现代文学作者(如余光中、叶珊、叶维廉),评论者(如颜元叔)也都在台湾发表作品。相对于老一辈马华作家之拥抱五四与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所谓的‘现实主义’)”他们“拥抱的都是台湾的现代文学”(注:黄锦树:《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误把台湾的现代文学取代了或等同于中国文学;二是对台湾文学的某种偏好,使他们认为与台湾文学容易沟通。
值得注意或指出的是,他们在台湾留学期间的台湾文坛,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传统、现代和本土这三种文学思潮重迭、并存与整合,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催生了大众消费文化,使文学出现了雅与俗的两极分化。在文化形态上,由于大众消费文化的刺激,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后现代文学也给台湾文坛带来了新的特异成分。与此同时,台湾文学也加强了对外国文学的吸纳,为台湾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文学经验,成为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一环。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作家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省思和发掘,使得感时忧国、爱乡爱民的人文传统在作品中得以充分显现,包括重视亲情和融洽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勤奋俭朴、坚韧耐苦、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刚强人格等也得到张扬……。
所有这一切,都对他们产生着影响,也使“他们在更多层面上实实在在也接触到中华文化”(注:岳玉杰:《椰风蕉雨化诗坛——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蕉风》第470期。)。
可以说,这些马华“新生代”正是通过留学台湾,走进并深入到中国文学的堂奥,获得并掌握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丰富知识,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从而建构起他们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
其次,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有着某些相近或相似的特点。他们都是文学创作上的多面手,既写诗,也写散文,有的还写小说,同时还兼具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特长,是很有见识的文学批评家和鉴赏家,学者和作家。这固然表明他们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但他们在创作时选择运用何种形式,又并非完全随心所欲,而主要是出于对如何更好地表达情感的考虑。辛金顺既写诗又写散文,“他曾有过理想,狂飙式的少年岁月,常被他用充满激情的笔援引入诗……他企图以诗的悲凉征服生命的悲凉,以散文的沧桑解剖岁月的沧桑。”(注:刘梦溪:《独行的旅客——侧写辛金顺》,《文讯》第138期。)钟怡雯最初是写诗的, 后来“发现还是写散文快乐”,“尽管她的散文有点诗化,文字意象也有丰富的诗意,还是被她自己定义为散文。”她还表示“将来有一天也要写小说……她将致力于开发小说的无限可能性。”(注:赖佳琪:《钟怡雯:写作和真实应该分开》,《文讯》第137期。) 这似乎可以认为是他们创作上的相似点之一。
在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内涵方面,他们也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譬如,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关怀。这里的所谓“历史”,又有着多重的性质和意义:既可能是指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能是指他们国家及各自生活的所在地区的历史,又可能是家族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还可能是整个华人先辈的移民史和创业史……。他们把这些“历史”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去思考、去阐释、去重构,甚至去颠复,试图以现代人的意识和观念,去解读历史的现代意义。辛金顺在他的散文《历史窗前》中写道:“唯有把个人的生命安放在历史之上,才能成其源远流长的承替,能大、能深、能沉……”,“唯有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才真正感悟到个人的渺小,生命也只能成其孤灯独照的苍茫。尤其在这片土地上,历史的内省和反观都很重要……未来我们仍有长路待行。”可以看出,他正是要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从回忆历史中引出对个人生命和未来前途的反省。
同样,陈大为的诗,或者是写他“读史,并重新融铸历史的精采过程”,“他常能读出前所未有的意义来”(如《风云》);或者“能在深入体会后利用历史条件来隐喻、抨击当今社会现象”(如《封禅》);或者“以历史变化为经线,并以华人在茶楼里的活动为纬线,交织烘托出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来”(如《茶楼》)……,诸如此类,都表明“他对历史与情节似乎有一份特别的嗜好。任何读者只要拜读过他的一两首诗作,就会感觉到诗人的创作方针一直是‘以古喻今’……他常常能入乎其内并出乎其外,经过一番重组与解构过程,结果他写出的诗当然已对历史做了改写以及再诠释”(注:陈慧桦:《擅长叙事等策略的诗人——论陈大为的〈治洪前〉与〈再鸿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997年2月23日。)。
看得出来,他们的历史意识是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并无永远恒定的客体,他们所表现的是主观世界中的历史真实,因此他们笔下的历史是过去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相互沟通的,并不是历史的还原与对历史的客观真实的把握。他们走向历史而又走出历史,从历史的偶发事件、破碎的史实中重构历史,抒发主观历史情绪,从而超越了历史。
这种对历史的深刻关怀,又不谋而合地使他们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学者化倾向,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达到较高道德文化品味和学术品味。正如钟怡雯在评论林幸谦的散文创作时说的:“学术思考的锻炼扩大了林幸谦的取材层面,从更深粹的角度,融合学术的思维与散文的语言艺术,探讨马华的文化位址,以及心理层面的挖掘”(注:9)。我以为, 这话也适用于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此前许多作家的作品所欠缺的。
再如,他们的作品中大多含有浓得化不开的“思乡情结”。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思,因而这种“思乡情结”也就具有文化的内涵,或者就是一种文化乡愁。他们原本都是远离故乡负笈海外的游子,思恋故乡实在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感情。但是,在他们笔下,这种感情又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因而也就具有了多元的价值:或者是寻根意识的自然流露,或者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或者是对故乡记忆的还原与复制,或者是对“原乡神话”的诠释和解构……。
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祖辈们的故乡成了“原乡”,祖辈们当年离乡背井和日后期盼还乡的故事便成了“原乡神话”;而祖辈们视为“异乡”的地方,却成了他们的家乡或故乡。于是,他们便“介于故乡与异乡之间”,力图“找到自己在这世界的位置”,也“更急于解构内心道德乡愁。”(注: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原乡神话·我及其他》。)我想,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海外华人普遍具有的心态和感情。因而,他们作品中的“思乡情结”就成了他们作品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而也相应地成了他们和其作品的鲜明标志。
又如,他们都置身在现代社会,时时刻刻都经历着、感受着、面临着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所加诸于人们的种种压力、引诱、喜悦、悲哀和困惑。于是,他们的作品中也有着他们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及现代生活的种种体悟和思索。褶素菜并非留台学生,但她却在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和生活过。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本质便看得更加深刻透彻: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以它对古老文明传统的破坏为代价的。于是,在她的笔下,“当年的吉山河,引人们都贴近大地”,而现在,“靠河而立的野新小镇”上,那“渐渐擎天而立的楼宇,把原是淳朴的乡民越加推离了与土地的相依”,河上,“窄窄的木桥已换上铺着柏油的石桥,路面是容许两辆车子并排而过的宽度。桥旁的车站依旧喧嚣它的热闹,使人常常忘了桥下还有吉山河的水流声……”(《吉山河水去无声》)
在寒黎的笔下,更充满了对现代都市的诅咒:“这里处处充满了功利社会的虚以委蛇、锱铢必较道德人际操作术。并且,贪婪、暗斗、残暴无时无刻潜藏在人心的拐弯角落,随时随地可以耍出几招以作个人防卫。这个地方,只允许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尘事浮想》);生活在这样的现代都市中,有些人的生活便如吕育陶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如今我准时上班、写情信、翻阅早报/以石英钟的频率生活/小心地避开各类思想的戒严区/在口号与等号间走钢索/趁经济的暖阳未凉前多摘几颗水果/(且努力地和钱币造爱)”(《存在的国度》)。人变成了没有思想、情感、灵魂的机械,冷酷、刻板、平淡,没有人的气息,没有生命的活力。
说到他们的艺术风格,总体上介于“五字辈”(出生于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与“七字辈”(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彼此间难免有相互渗透之处”(注: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序》。)。相对于“五字辈”的陈旧老化与“七字辈”的肤浅稚嫩,他们在艺术上显得比较成熟。
诚然,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实际上,即使在他们当中,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实践经验也还是有所区别的。同样是写诗,陈强华的诗,一方面既“形近五字辈”(注:陈大为:《对〈“诗选”扫描〉的几点说明》,《蕉风》第473 期。),另一方面,又“深受台湾新生代诗人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色彩较浓”(注:岳玉杰:《椰风蕉雨化诗坛——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蕉风》第470期。)。 林幸谦的诗“以隐喻修辞和结构思维见长”,陈大为的诗“语言风格卓赋特色,修辞造句层叠架用喻拟,并以辞类功能转换造就特异语码,语言空间布满文化意象”,其“晚近诗篇适度融入口语句型,语言作为工具性与音乐性得到交糅协调,情感负载与意义探索期以平衡”(注:费梁:《马华新诗的新形象——〈马华当代诗选〉扫描》,《蕉风》第473期。)。
在散文创作方面,正如钟怡雯所说:“辛金顺对台湾文学养份的吸收,转化了他的语言风格,对古典文学得到糅合也日益圆融”。而对于黄锦树、钟怡雯、林惠洲、许裕全等人来说,“散文语言的艺术性和叙述结构才是他们的经营点。换言之,他们企图以更大的叙述架构和更精湛、更有魅力的语言来铺展素材,拓宽散文的格局”。又因为他们同时是诗人,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出现诗化的画面,语言的诗质美化了叙述的魅力”或者“经诗化而趋向朦胧淡雅”。总之,“经由文类的互相渗透而达到的美学效果,正是旅台散文的一个特色”(注:钟怡雯:《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序》。)。
凡此种种。使我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们是一个群体,但并不构成一个流派;他们的创作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色彩,但又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分开来看是独特的心灵图像,合拢来则是互补的断代绘画;他们的作品属于马华文学,但又突破和超越了地域和疆界……。
三
毫无疑问,这道亮丽的风景,为马华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已经并且还将为马华文学增色添辉。它使我联想到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周作人、田汉、夏衍等一大批作家,都先后留学日本,并在那里投身于文学活动,然后又从那里将其他民族的文学介绍到中国,促成了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他们自身则无一例外地成了推动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繁荣发展的主力和干将。当然,我并无意将他们与上述中国现代作家作简单的类比。我由此而想到的是,如果说过去马华文学的发展空间比较狭窄,因而其对外的交流受到某些局限的话,那么,通过这群“新生代”作家们的负笈海外,便有助于扩大马华文学的影响,也增强了马华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与沟通。即此而言,他们所处的中介的位置及所起的桥梁作用,正与上述中国现代作家们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另一方面,或者正因为他们是后起的年轻一代,便容易犯一种年轻人都有的“通病”:他们对马华文学的历史和传统,以及老一辈作家的创作,时常取一种“冷眼”相待的态度,而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尊重。例如黄锦树便认为:“(马华文学)贫乏的语言反映了文化上的贫血,语言的困境是文化困境的表象”。他还认为,“假如马华文学一直停留在现实主义的时空,那就没有经典文学可言。”(注:《亚洲周刊》1996年第28期。)换言之,他认为现实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经典文学”,过去的马华文学因为是现实主义的,所以也“没有经典文学”。我以为,这种看法至少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是片面的。因为“经典文学”与创作方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必然关系。我们不能说,只有某种创作方法才可能出现“经典文学”,别的创作方法就不可能出现“经典文学”,事实是,大凡称得上“经典文学”的,必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似乎不能过早地说马华文学“没有经典文学”。尽管如此,我认为黄锦树的观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经典缺席”的争论,对马华文学的发展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至少表明这群“新生代”作家的不安于现状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或者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们才寄予厚望。例如作家小黑“希望他们多读书、多思考,表达的层面要广而深”。作家孟沙则认为“新生代”作家只要虚怀若谷,视野宽阔,他们肯定会超越前代。(注:《亚洲周刊》1996年第28期。)
令人可喜的是,这群“新生代”作家中,已经有人在创作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接并延续着前辈作家的传统。许裕全的散文《梦过飞鱼》便给人这一印象。读这篇散文,令人联想起韦晕早期小说《乌鸦港上黄昏》。从散文中那位以捕鱼为生的爷爷道德身上,分明看到老渔夫伙金的影子。他们同属于老一辈离乡背井的华人,有着相似的命运和遭遇,虽然最后的结局不尽相同,但都共同演绎了一个关于生命的哲学主题:“为了生存必须挣扎和抗争,以不屈的生命力,顽强苦斗,去追逐一个难圆的梦想。”他们可谓老一辈华人的缩影和写照。而许裕全和韦晕之间的艺术视角及审美视点竟如此相近,正表明了两代作家之间的某种承传关系。他们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是由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伦理道德观念所组成的民族血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