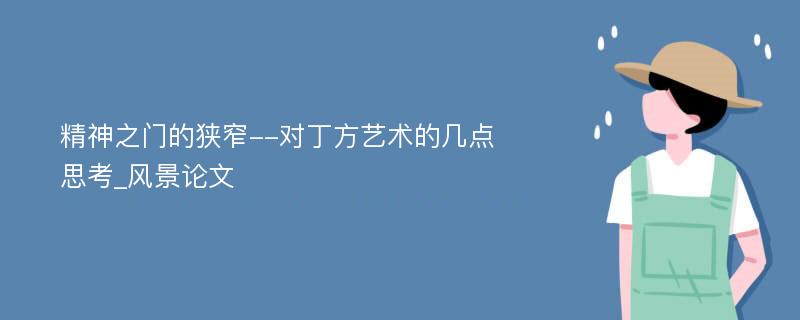
精神的窄门——丁方艺术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窄门论文,丁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受苦受难,也无法到达彼岸;每天我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我离幸福的路程还很漫长。
——彼特拉克
丁方是当代极少数视笔触、肌理、色彩为抽象的形而上学之物,持久地进行精神探索的画家。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形体、光影以惊人的强度扭结在一起,摔打出意义。它们偶尔有不同的名字:意志,救赎,希望,悲剧,苦难,历史……凭着这些记号,丁方的艺术被“主体”的时代拥抱,又被今天的时代遗忘和缅怀。
大约从2002年起,丁方有意避开先前流溢、扩张的造型样式,大量使用水性综合材料厚涂基底,再以油性薄透画法自由渲染,使画面呈现一种生涩的质态。新的构成形式源于对西北大地独有的雅丹地貌和风蚀地表的朴素直观,这是在自然视觉被形式化冲动长久压抑和磨砺之后浮现的自然主义模态,它维系着丁方反复咀嚼的“说不出的历史苦味”。在“为大地吟颂”题下的多个系列作品中,尽管时时回响着丁方式的精神主题,但是,裸露的山体,水性材料堆积产生的凝性,秩序和凌乱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这些压迫视觉的元素挤破了作者的意图。那种曾经被形式化(戏剧化)效果掩饰的二元性,在此以悖谬的方式直接呈示出来。这种异质力量为重新理解丁方的自我教化史提供了可能。
丁方的艺术从黄土高原起步:
这一切开端干一九八○年。那一年的春天,我重返黄土高原。蛰伏于童年记忆深处的某种奇异的力量,蓦地为我洞开了一扇通向一个未知境界的大门……①
多年来丁方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因为其中包含着只有他自己才能接近和理解的原初经验。这种经验甚至对于他也是一个谜,驱使他一次次重返高原。每一次重复与其说是为了理解,不如说是为了重温理解的难度。
《西北的回忆》(1983)是比文字更具体的记录。如此柔和、暧昧的情景只出现在失眠之夜,从剪开的裂口流出踏月而归的人群,诡谲的光随意闪动,而后是凝视者木然的背影。这是一种类似启示的经验,直到今天丁方仍然以凝视的姿态面对它,保持着它的陌生性,从而使每一次进入都变成自我放逐,变成对“他者”——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意义上的维持着差异的不可还原性而自身决不屈从于同一性诱惑的“绝对他者”② 的寻求。
在探索的早期,丁方邂逅了两位愤世嫉俗的现代主义者:卢奥(Georges Rouault)和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他们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卢奥把现世苦难和基督之死联系起来的质朴方式,偏执、狂热的宗教情绪,粗犷而近乎暴虐的线、色,浸透了丁方。卢奥指示了一条把苦难意识升华为普遍的怜悯和爱的道路,不过当时丁方还只能从形式的力度上来挥霍这份财产,这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油画和素描(尤其是那些用毛笔焦墨画的素描)中留下了痕迹。艾略特的意义要更曲折一些。《荒原》里的废城,鱼贯地流过伦敦桥和威廉王大街被死亡毁掉的人群,“伦敦桥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塌下来了”,这些意象是丁方反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隐秘来源和基本支撑。而那个在煤气厂背后的死水里垂钓的倒错的历史主义者(《荒原》),和不停地喊着“烧啊烧啊”要将“烈火和玫瑰化为一体”的声音(《荒原》、《四首四重奏·小吉丁》),构成丁方关于“自我”的双重幻觉。丁方后来的油画中反复出现的等待毁灭或燃烧着的无数个索多玛城,还有那股咆哮着穿过城市和荒野混合了泥浆、金属和垃圾质感(有时也沐浴着光辉)的巨流,实际上也来自艾略特这个母体。
丁方艺术的转折出现在90年代初。“走向信仰系列”中含混不清的挣扎主题,在“实在”的坚壳里遇到了真实的生命经验和历史意识。丁方的画面从此凝重起来。《悼歌》(1992—1993)把历史记忆和基督受难的场景有意叠合在一起,冷峻的基调、严整的结构与造型,特别是表达上的极度克制,透出令人窒息的气氛。压抑源于作者新近才有的孤独感,它既包含对刚刚消失的年代的反省,对扑面而来的新的时代精神的不知所措,也包含对自己此前艺术方式的怀疑。《大地系列·为晨曦而流泪》(1992—1993)是丁方的自我治疗之作。这是像惠特曼一样强健的体魄和人格才能切割出的风景,泪痕似的沟壑借助准确、有力的语言自然铺展,象征、隐喻在此简化为直陈。“大地系列”是丁方逐渐摆脱对文学叙事的依附,构造纯粹风景的开始。此种以形式语言的辩证方式来呈现的史诗性风景构成,在《悲风》(2002—2003)、《灵魂之光照耀的山峰》(2003—2004)、《咏叹回荡在云天》(2008)等晚近作品中,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在“大地系列”前后,丁方的叙事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叙事的视角从历史转向个人(此在)。主题的连续性、大叙事的一贯追求和构成样式的反复,使这个变化不易察觉。动荡和焦虑,逼迫他从历史之城退回内在之城,在生存论意义上重新思考“苦难”与“获救”的悖谬关系:“生命的意义只向站立在生存临界点上的灵魂敞开,唯此时他才能既俯身看到从深渊中逼近上来的死神的步履,又仰首瞻瞩到从天空上传来的神圣呼召。”③ 希望与绝望、“至高的荣耀”与“深渊的体验”的紧张对立,成为丁方持续探索的主题,催生出他艺术的多重面相。在这条道路上,丁方努力锤炼一种能够和精神的难度相匹配的造型语言,构成一个与平庸、卑琐的日常生活平行和对抗的形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声称风景是“人格的宣示”,是“精神的景观”。
丁方的圣像画很少受到注意,大概是因为题材太“西化”了。其实,这些圣像本质上是非宗教的,就像他宣称一切伟大的艺术本质上都是宗教的一样。《基督诞生》(1993—2005)这幅小画断断续续画了十二年,是丁方圣像中基督教味最浓的作品。然而,耶稣诞生在马厩里的场景被嵌在羊皮书页中,四周粗重的页边也是画框,这个意外的间离之举是耐人寻味的。另一种间离出现在《童贞女》(1997)中,金色的粗框沿头巾和衣领的边缘环绕,面部厚涂产生的琉璃效果和玛丽亚木然斜视的目光阻断了交流的通道,使这幅图像成为一个现代灵魂照不见自己本质的镜子,或者一个映射着现代灵魂反面的阴影。丁方基本上把圣像当作一种体裁来处理,藉此探究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经验空间与超验空间的跨度、紧张和视觉表现问题。他认为,基督教圣像艺术的成就,在于不使用三维透视,以单纯的平涂手法解决了这两种灵性空间的对立与沟通的难题④。《圣母颂》(2004—2005)通过对三维空间的否定,仅仅依靠笔触、肌理和光的辩证关系来呈现纯粹的音乐主题。面部受光部分的平滑处理和四周剥离质感的强调,在平面化的视觉空间里愈显凝结,圣母玛丽亚悲伤的表情和眼泪此刻被永恒化了;而发梢和衣纹处金属般的褶皱,以及背景的微光,则暗示着苦难的深度和意义。《下十字架》(1995—2005)凭借简单的对比把绝对的痛苦和忧伤封闭起来。《冥想》(1998—2005)也是用剥离效果的材质形塑圣者的面部和衣纹,而后罩以金色为主调的油彩,通过基底和表层的对比凸显不朽的意味,特别是,在圣者鼻尖的高光部位意外地出现一个弹坑似的凹陷,形成向内溃缩的肌理,这是缜密无缝的时间留下的印痕。在《凝思》(2004—2005)中,时间剥蚀了圣者的双眼和头骨,只留下永远冥想的姿势。
《死亡无法拒绝》丁方至少画过三次,一幅画于1995年,另两幅画于2004—2005年。他为此写下了题记:“这幅画是根据巴赫的一首同名《康塔塔》而创作的,它表达了我对‘时空无限’的悲剧性感受。”⑤ 这个感受和艾略特《荒原》题记里的女先知西比尔求死不得的感受是同一性质的,只不过对于西比尔没有青春的永生比死亡更可怕。这件作品里,剥蚀、溃缩的形式在本质上属于此岸的时间性感受中找到了更恰当的表现,尽管画面构成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尽管有死者干枯的面孔令人惊悚,但它还是可以直达我们存在的经验。
丁方是一直对绝对主义抱有信心的人。早些年他想通过对民族历史的回溯进入这块领地,而后又借基督教乃至一般神圣文化的形式探索心性之上的精神可能性。这条道路在20世纪中国油画中是绝无仅有的。重要的是,经历这样的探索,他为自己的造型确立了一个内在维度,一种时间性结构。
在犹太—基督教文化内,此种结构和等待末世救主(弥赛亚)到来的记忆有关,牵涉历史与个人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谜一样的联系,而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经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现代”命名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历史意识。黑格尔把“现代”叫做“新时代”。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是即将来临的未来时代,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出现;而世俗的现代性概念则确信未来已经开始,“现代”是为未来而存在、向未来开放的“新时期”(Epoche)。这个现代性时间意识催生出两种历史观念:社会进化论和历史主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哲学论纲》从一个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有关的“当下”(Jetztzeit)概念出发,对这两种历史观念进行批判。被社会进化论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使进步变成一种历史常态,把弥赛亚现身之际造成的断裂(革命契机)排除在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之外。历史主义用“同情和理解”编排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来填充“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满足于在理想的共时性中把握永恒的过去图景,剥去了现在与未来关系中对理解过去至关重要的一切东西。而“当下”这个具有革新意义的真实的现在瞬间,打断了历史的连续体,从历史的同质之流中逃离出来。“本雅明以‘当下’为轴心,把构成现代特征的激进的未来取向扭转过来,代之以更加激进的过去取向。对未来的期待只有靠对被压制的过去的回忆来实现。”⑥ 本雅明提到一种“弱弥赛亚力量”:“在过去世代和现在这一代之间有一个秘密约定。我们来到世上都是如期而至。如同我们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样,我们被赋予了一种弱弥赛亚力量,这种力量是过去所要求的。”而要解开这个世代“约定”的秘密,就必须把“现在”理解为透入弥赛亚时间的无数个“当下”的“碎片”(Splitter),对于每一代人来说,弥赛亚期待并不指向同一个“未来”时间,每一次期待都是把弥赛亚铭写在“当下”的肉体中。尽管犹太人被禁止探索未来,摩西五经和祷告剥去了未来的魔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来说,未来就变成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因为每一秒钟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⑦。
这种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现代性时间意识,对于汉语思想传统是一个异数,却在中国现代性历史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在此,并不存在汉语文化该不该、能不能接纳之的问题(那是意识形态专家和魔术师考虑的事情),只存在它能否在汉语思想里取得确当论述的问题,对艺术而言,就是能否找到基于生命经验的审美表现的问题。在这方面,丁方的实践常常是被低估的。
丁方超验维度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并非直接来自本雅明,虽然他很早就被本雅明的忧郁气质浸染;除去晚期艾略特,在这个影响史上还有一长串名字: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布洛赫(Ernst Bloch)、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以及基督教音乐。《言成肉身》、《升腾与下降》(1991)、《各各他》(1992)稍稍偏离他熟悉的戏剧性结构,在平凡的风景中追溯圣言的踪迹。这一次,他在西部的高原、雪山间经历了精神拷问。以前他潜心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历史记忆,而现在他发现,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同时也是阻碍我们与神圣相遇的屏障。一个艺术家如果还要探究这片土地的秘密,他就必须有能力突入此一悲剧性的悖谬结构中,在“悲剧性的深渊处境”里,他会看到,灵魂的救赎更艰难、更惊心动魄⑧。从“走向信仰”和“悲剧的力量”系列开始。衍生出他作品里那些标记性的符号:十字架、受刑的基督、使徒、高原与肉体、旷野上呼号的面孔、放逐之城……有时是以暴虐的方式出现的。其间,偶尔也有《请退让吧,忧郁的阴影》(1997)、《消逝着,荡漾的波涛》(1998)这样的无意识浮现,它们灵歌般朴素、安详和感伤。《艰途》(1994)、《荒野》(1995)、《罪灵们》(1998)、《苦阶》(1999—2000)、《时代的面相》(2003—2004)、《冷辉月下的城》(2004—2005)述说的是在被圣灵遗弃之地精神毁灭和生长的故事,这里,作者甚至有一种卸下十字架重负之后的兴奋和快意。怀抱基督受难的秘密在绝望的土地上行走,让时间在无尽的跋涉中消耗、磨蚀,这是丁方的艺术想象中令人激动的部分。重要的是审美表现问题,即如何使深度的精神暗示经由空间转换重现于平面。面对八个世纪以前俄罗斯圣像画,丁方领略了把线、形、色等物理要素神奇地整合在某种神圣场景中的方式。虔敬的画师们用代表大地生灵沉睡性质的冷褐色横扫在木板上,接着,生命的成长因素以富于表现力的笔触从远处背景中凸显出来,逐渐凝固成清晰的形象。丰富的笔触一般都经过细心的打磨,其神学—形而上学意义在于:必须有一只先于光出场的隐秘之手,对生存的痛苦进行抚慰。如此,粗砺的笔触、肌理才在承受光照之后变得温顺,化为感激的嗫嚅隐退到幽暗中。这时,薄敷的暖褐色或幽蓝色开始显示其精神魅力,以投影来烘托光耀,以低音轰鸣来呈显高光音色。最后,多层次的薄敷、刮沥让整个过程愈加具有历史感。“正是上述历史感使我们的灵魂在返回遥远过去的途中,有福禀受到未来希望之光的朗照。”⑨
有一天,丁方再次重返西北大地,高原、流沙、荒野和故城在光的辉映下骤然化作艰涩而愉悦的生命瞬间,这是卢奥和基弗尔(Anselm Kiefer)的瞬间,是土地上漫长苦旅的馈赠。正如十多年前丁方在等待这一刻到来时写下的:
……一种沉凝有力的挚着之光,它从另一个世界突入此世,温厚地漫溢在坚实的躯体上;而天际尽头沿着地平线那一缕将升未升之光,把神圣之光君临此世带来的希望,呈示给我们。
我自己深知这一希望的价值。有了这一希望,我便不再祈求任何了。⑩
凭着这个希望,丁方浸透了无名伤痛的悲剧情怀羽化为苍凉、辽阔的普世景象。
在丁方的风景中,有几个基本意象:光、玫瑰色天空、山峰、旷野和城。
光作为一个意义符号,最早出现在“城系列”中。此时,它既暗示着某种未知的启示,也被当作画面构成必需的戏剧性要素来使用。这种戏剧化的处理,在随后的“剑形的意志”和“悲剧的力量”系列中达到了极致。也是在这两个系列中,光的精神蕴涵日渐丰盈。《孤寂中的祈祷》(1991—1992)把光和个体获救的艰途与希望联系起来。当他带着这样的眼光重返高原,干枯的土地与河流沐浴了光辉。而在《光辉深处的灵魂》(1996)、《希望的微光》(2002)、《圣母颂》(2004—2005)中,光显现出纯粹的音乐本质,它以不同的调性和表情出没于“城市系列”和“圣风景系列”。特别是在《大地之歌之一》(1993—1994)、《精神的景观》(2003—2004)、《神界的黄昏》(2008)等作品中,远处的微光如音乐动机般凝缩,成为丁方风景里最感人的部分。
《圣灵的火焰》(2007)以高贵、单纯的色彩、笔触和肌理,呈现了一个绝对超验的风景:
哦,仰望灿烂的葱岭,神奇的山峰正被天堂之光所辉耀,玫瑰色和紫罗兰色的阴影,叠合出深沉而婉约的和声,构成了我人生经验中最壮丽的咏唱。(11)
玫瑰色和紫罗兰色的阴影,是荷马的有玫瑰手指的曙光女神从黑暗中走出的时刻,也是但丁和维吉尔告别的时刻。在近年的风景中,它作为超验的符号被嵌入远景,又映照在近景的边缘和缝隙间,使画面成为两种灵性空间永远争执和不断僭越的场所。丁方长久追寻的历史感和时间意识,借助这个高度形式化的结构,获得了抽象的表现。
《敞开的胸膛》(2007)通过远景与近景、色与光、粗砺与柔美之间复杂的对比与融合,展示不同灵性空间错综暧昧的关系,成为丁方塑造此岸风景的无意识图式。《叙事诗三首》(2003—2005)是元语言的切片:凝聚、风化、剥蚀,其间还穿插着另一个要素——书写,它是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抽象。对这些要素相互越界的可能性的探索则构成丁方风景语言的修辞部分。
《葱岭流沙》(2007)用沉闷的色调叙述佛教圣人传道之途的艰困,披着铅白的粗重笔触和黑色油彩相映衬,透着无言的苦味。《山峰的精神素描》(2006)把厚重的肌理、飞白的笔法置于同样幽暗的色调中,记录生命、历史凝固和被封存时刻的涌动。《生命与岁月的纠缠》和《大地跟随闪电》(2006—2008)是这个“无穷动”主题更富表现意味的扩展。
《大悲剧》、《天堂有多远》、《时代的尽头》、《旷野呼告》(2008)浓缩了80年代以来多个系列的母题,但去掉了先前的戏剧性成分,以质朴、洗练、灵动的语言,呈示现代生存根本的悖谬性质。而其间大量以雅丹山峰为题材的风景,则通过坚实、凝重的构成,展现精神再生的多重可能,尤其在《玫瑰双峰》(2007)和《神鹰的故乡》(2007—2008)中,黄、白、古铜、玫瑰和紫罗兰扭结成一体,摔打在布面上,铺叙成无声的大地颂歌。
我宁愿把丁方的教化史想象成一个现代个体自我治疗的故事。某一天,他意外地成了历史精神和个人记忆的交汇点,感觉受到某个神秘事物的触动。这是每一个对哲学和艺术抱期望的人多少都有过的经历。就像罗蒂(Richard Rorty)十二岁那年同时被真理之书和乡间的野兰花吸引,梦想找到某个思想框架或审美框架来调和它们,让他如叶芝说的那样“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正义”。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明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正义”的想法原来是一个错误,是把柏拉图领入歧途的东西,“实在”和“正义”、野兰花和救赎真理,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他转而关心另一类问题:假如一个人能够抛弃这个柏拉图式的企图,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生活?(12) 丁方的道路有点近似。早年他凭着朴素的文化意识,寻找个人与历史沟通的符号,唤起埋没在“历史之梦”中的生命形象。随后,一场自我意识的危机,把他推到个体生存的基点,重新考虑生命、艺术与永恒的关系,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开始从不断分裂又不断弥合的冲突中生长出来,此时他大概和罗蒂感受一样,自己并不比多年前更接近那个“单纯的一瞥”。不同的是,丁方的探索始终基于一个坚实的视觉原型——西北高原,自他踏上那里的一刻起就再没有离开。这种持续紧张的实践,使他碰巧被80年代接纳,又让他侥幸地避开了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几十年西西弗斯式的苦役,终于成就了一个炼金术的奇迹,丁方收获了诸神隐匿之际的风景的元形式,一种可以在任何空间中展现精神冲突的造型力量。与此相比,那些旅途留下的尘土,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变得不大重要了。
这样的理解是以放弃作者的“意图”为代价的,因为我相信,当代艺术最好的部分是可以不靠伦理架势和意识形态标签得到充分理解的,虽然它们的起源往往离不开这些东西。相反,如果执迷于此,我们可能要冒失去艺术和生活政治的危险。就像“反讽”这个了不起的艺术样式唤起过我们的政治直觉,等到它变成一种要挟的姿态到处复制、泛滥成灾的时候,它的革命性(反讽本身包含了对反讽的反讽)就丧失殆尽,而沦为意识形态偏见的俘虏和侏儒的傻笑。
注释:
① 丁方:《山魂与人灵》,《丁方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② Cf.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trans.Alphonso Lingis,The Hague,Boston & 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
③ 丁方:《现时代艺术的境况与希望》,《丁方文集》,第177页。
④ 参见丁方《俄罗斯精神艺术札记》,《丁方文集》,第153页。
⑤ 《中国油画二十家·丁方》,北京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⑥ 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引文按英译本略有改动(Cf.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UK:Polity Press,pp.1-16)。
⑦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耀平译,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15页;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8页。引文按英译本略有改动(Cf.Walter Benjamin,“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ed.Hannah Arendt,trans.Harry Zohn,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pp.253-264; 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trans.Peggy Kamuf,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4,pp.180-181)。
⑧ 参见丁方《山魂与人灵》,《丁方文集》,第144—145页。
⑨ 参见丁方《俄罗斯精神艺术札记》,《丁方文集》,第157页。
⑩ 丁方:《山魂与人灵》,《丁方文集》,第145页。
(11) 《中国当代名家系列·丁方——为大地吟咏》,藏新艺术有限公司(台北)2008年版,第49页。
(12) 参见理查德·罗蒂《托洛茨基和野兰花》,《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411页。引文按原文略有改动(Cf.Richard Rorty,“Trotsky and Wild Orchid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enguin Books,1999,pp.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