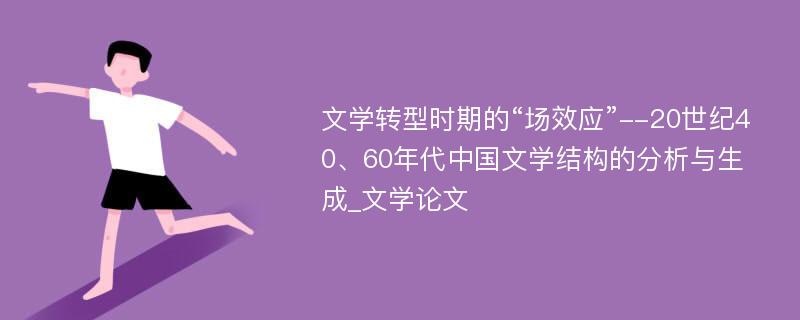
一个文学过渡期的“场效应”——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结构分析和生成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渡期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效应论文,年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40年代政治划分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区域文学研究,50、60年代称谓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以及传统现代、当代文学的历史分界线,这一文学史格局已成为了约定俗成的定论。回到了历史本身的情境,文学史的特殊性并没有由此呈现清楚的原貌。文学演变不是简单社会历史的新、旧断代,更不是政治势力范围的鲜明两两相对。文学的生成往往是在一个多元交错的文化场中的整合。就文学整体而言,20世纪40~60年代更有着在文学史形态、文学结构、文学史意义等方面自己的构成。这是一个“五四”启蒙时代文学的转折期,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过渡期。文学表现出更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场效应”。而对此“文化场”,我们文学史的工作重要的是清理其中的诸多关系,任何操之过急的结论都可能会淡化历史的本真和原味。在新近不少学者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中,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文学史的认知已经得到了重新的改写。最突出的是,他们在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较过往有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辨析,对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中“人”的多层次多视角反映、表现、揭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这段文学史的特殊,值得我们重评。可能恰恰不是在文学本身,而是在于一个特定的过渡时代的复杂“场效应”。这不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观念能够解释的,也不是文学“断裂”或“多元”可以说明的。有研究者提出的“转折的研究”,要全面清理“这一时期作家流动情况、作家生存状况、创作状况的变化,以至于物质生活的变化”(注:赵园:《研究现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4年第2期。)。这对文学史时间与空间的认识有启发性。我理解“转折”的文学史调查和清理工作,不能离开“文化场域”。作家的一切活动和创作现象是“过渡”或“转折”过程中的关系互动。于是,我对40~60年代中国文学有了以下的想法。
“场效应”中的40~60年代文学史
作为“场效应”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这30年总体表现为民族的、国内的战争与阶级斗争为纲背景下的特殊政治形态之产物。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统一性和对抗性,为了战争,为国家独立后的生存;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又表现出无序性和多元性,为了战争中的偷生,为了适应和平时代的新形势斗争与建设。文学更多是走进了这样的“文化场域”,寻求自身的生存形态。这里不只是条理清晰的对立或并立,也不是绝对的时间分界和空间独立,而是文学与社会场、政治场、经济场构成了多重交叉的运动和互动的“场效应”。
40年代初,政治上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分裂,并不表示文学上立刻有明显的阶级、党派对立。同样,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旧制度的解体,但是,也不是说文学在这一刻有了明显的分界线。1941年1月出版的《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首篇《1941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一文是当时文艺界座谈会的综述。文章中的记录表明政治的“皖南事变”并没有马上改变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同人格局,国民党文人王平陵依然到场并发言。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与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状况实际并没有多大变化。在1948年的《文艺丛刊》第6集上刊发杜霞的《北平的文艺界》一文,称“北平的文艺界和出版界是非常荒凉的”,把沦陷区的作家袁犀、梅娘、张爱玲等称为“一群人渣”;说北平是“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之流的教授所把持”。这与建国初(1951、1952年)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文艺观点等批判的口吻何等相似!显然,文学场不能够简单等同政治权利场的紧张对垒。文学场应该属于文学自身活动和实践的场所,更是一种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中进行的主观选择。同时,与其它场域一样,文学场域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它也处在与政治权力场域的关系之中。文学场域本身则是由文学创作领域中客观存在的可能位置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
回到文学的现场,4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历史战争状态的划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足鼎立格局,自然也能够说明清楚各自政治环境的不同所表现的文学不同。但是,就文学的文化结构分析,重要的还在于从他们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找寻各自文学生成取向的不同内容。40年代初,在延安的丁玲对作家是这样引导的:“作品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它一定是属于大众的,能结合、提高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那么他必须首先取得大众能理解而爱好”(注:丁玲:《作家与大众》,《大众文艺》1940年5月15日,第1卷第2期。)。这与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也是解放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和生成条件。国统区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更多是作家如何适应战时需要、如何与人民结合的积极探索。杨晦说:“抗战初期作家们的情绪是高扬的,而对于事件不十分把握得住,但大的前提是与人民结合,如文章入伍,文章下乡,通俗化等。以后的‘民族形式’的讨论,是一大的转变,成为争取主流的一种运动。”(注:梅林记录《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记一个文艺座谈会》,《文艺复兴》1946年6月1日,第1卷第5期。)而处于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作家境况,显然高谈“大众”、“人民”、“形式”是奢侈的,文学表现正义,文学解决生计似乎是更为实际而具体的话题。“我们对于正义的信念应始终不变,但应该如何树立正义,我们不能不从现实的种种变化中,重新考虑我们的方法问题,现在多数文化人的沉默,也许正在对于时代的变异作着深刻的考虑”(注:哲非:《文化人何处去》,上海《杂志》1942年8月10日,第9卷第5期。);张爱玲说:“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注:张爱玲:《必也正名乎》,上海《杂志》1944年1月,第12卷第4期。)大时代有生存区域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经历生活、体验人生、理解生命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构筑大时代文学形态的丰富性。同样,50、60年代中国的新政权建设时期,文学的“歌颂和斗争”的双重主题变奏也并不就是唯一的。当我们读到“三红一创”文学作品时,既是受革命历史宏大叙事和新时代农民创业的鼓舞,又是发现文学作家自觉与不自觉的精神裂变。从1951年4月《文艺报》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开始,一个接一个文艺界的思想大批判,实际也并不代表文学的全部。除主流的《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文学期刊之外,还有先后创刊的《民间文学》、《剧本》、《说说唱唱》、《译文》、《文学研究》刊物杂志,以及各地的报纸杂志、文艺副刊;还有许多作家因为“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以及农民的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的表现相当娴熟,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得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曲折地传达出真实的社会信息,体现了富于生命力的艺术特色”(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除上述之外,作为文化场的文学史应该正视放大的文学整体性,在完整的社会文化进程中观照文学。40~60年代中国文学是立足于极其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建设初期的特殊历史。40年代的战争环境,处于被封锁的延安地区,客观的贫瘠地理环境和经济落后,所形成的统一领导下的大生产运动和思想整风运动,确立了这一区域基本的文化和社会形态高度自治性。而战争环境下处于国民党统治和日伪占领的中国广大的农村和都市,民众在饥寒交迫中的生存抗争和秉烛待旦的期盼,蔓延于这些城市的是物价飞涨的恐慌,或商业大减价的喧嚣,或百无聊赖的筹划生计;而“在冰雪凝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艾青《手推车》),更多乡民、市民终日相伴的是凄惨和贫困,漂泊不定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调。
进入50、60年代,告别了战争的灾难,这是一个新的社会初创时期。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农村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三反”“五反”等重大社会政治运动。这些既是在社会建设、调整中的政治需求和历史必然,又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自己独立的路,建构一个自主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历史探索过程。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的跨越期、社会形态多样的复杂期中生成和发展。《洼地里的“战役”》、《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年早知道》、《山乡巨变》、《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等作品正是建国初期社会历史生活的“文本”。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建国初期的真正经济建设的场面和完全生活化的内容并不是主要,而宏大的政治场面的渲染和人物的成长、转变、改造过程,及其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其身份的立场认同与区别,却构成了“文本”世界的中心位置。当然,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经济文化的社会图景还是可见一斑的。所以,他们的“文本”作为历史与文学的整合概念,可能较之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准确一些。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单纯从一个方面、一种关系中叙述和判断,就可能遮蔽许多东西。文学历史的复合性、场域性,也很难得到充分完整的体现。同时,文学自身的内在形态在特殊时期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个性和价值,也会受到社会文化不完整的把握而缺失,掩盖了文学史某些鲜活的原态面貌。
“场效应”形成的特殊文学结构和生成走向
对这段文学史在做出这样的清理之后,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设问:这一时期文学自身与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场效应”下的特殊文学形态和生成方式究竟应如何对待呢?已经有的文学史说法,40年代文学:延安文学、都市文学、乡村文学三大战时区域,分别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统一;文化边缘生成的反省;民众悲壮苍凉的生与死三大生成形态。
50~6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以一体化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文学特殊现象和主题内容:思想改造、歌颂与暴露、干预生活、革命历史、政治抒情……显然,这些历史的叙述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致辨析,“文化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具体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连理关系,更代表着文学自身的结构系统和生成走向。
40~60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场”的关系,总体概况就是一切处于“特殊状态”:在一场特殊的民族战争和阶级对立,一个过渡时代国家新政权巩固和建设中,文学因此自然而成了一种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境自觉与不自觉的运作载体。文学自身的内容和结构形式也带着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可以说它们并非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文学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的简单历史延续、递进,或者说转折,我们更不认为文学此时发生了某种精神“断裂”。这一特殊时段的作家整体处在一种非常态下的写作,文学在战争背景下区域分割的多元与隔膜,文学顺应新国家新政权需要的歌颂与抒情,这些还是十分表层的现象。所以,我们不可能以文学史常态的演变进化寻求其规律,以文学一般普遍的功能观和取向标准衡量其价值和辨析其形态。
翻阅历史的记录,关于抗战无关论、关于暴露与讽刺、关于民族形式与大众化、关于延安文艺整风、关于战国策派、关于现实主义及主观论、关于文艺自由、关于萧军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关于文艺界反右、关于文艺政策的调整等,构筑了这一特殊文学运动的走向和文学思潮的内容。
作为文学思想和观念性的理论现象问题,他们往往是随历史的重大变革而提出。夏衍在抗战初期说:“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不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注:夏衍:《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自由中国》1938年5月第2号。)80年代末王瑶回顾这一时期文学时有同样的观点:“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面,文学必须为抗战服务,成为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的武器。”(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同样,建国后的文学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新社会里书写的。从各种文艺思想的批判、批评到保卫“社会主义文学”,关于现实主义典型性、真实性、人民性的讨论,并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目标的最终确立。这也就是40年代毛泽东“讲话”文艺精神、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6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文艺思想最终形成的过程。这其中还有胡风、冯雪峰、王任叔(巴人)、钱谷融和秦兆阳、邵荃麟等对主流文艺的质疑和补充,还有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传统艰难行进中的徘徊、矛盾、困惑中的创作实践。这些构成了文学史在特殊时段的特殊文学演变形态:特殊环境下必须保持的战争临界状态,对抗、对立的革命思维方式;一体化下的文学服务意识,反映再现原则;作家世界观意识指导下的中心是“写什么”;时代主流的歌颂与抒情,人民大众的喜闻乐见,成为首要的审美标准。
再梳理文学创作实践的生态和结构:整体文学史宏大叙事的主导地位呈现文学演变的特殊性。不仅以文学思潮烘托了历史的轮廓,而且还以不同创作个案的书写实践涂抹了文学的多色天空。如,长篇小说从个人历史向着家庭历史转移,再到国家民族的叙事(历史的传奇);个人化的主观抒情诗转向社会、政治的讽刺诗,长篇叙事诗与政治抒情的革命的诗史(组诗);现代戏剧也以社会讽喻剧和历史剧的基本体式潜在隐喻历史与现实话语。但是这些还只是40~60年代文学史一方面传统认知的“贴近主流转型”生成的结构形态。文学史另一角度是否还存在行进中的“空间”和“过程”现象呢?40年代战争环境下的文学特殊情景,很大程度是由巨大的特殊“空间”所构成。比如不同地域的沦陷区类似“南玲北梅现象”、“徐訏、无名氏现象”,特殊的大后方文学,边缘的跨文化的南洋、东亚华文文学,等等。他们既在政治势力分割的三大区域之内又超然于政治之外。50~60年代的社会革命的重大变革,“一体化”的文学机制实际运作过程,文学在历史意识形态化的背后,作家主体世界丰富复杂而隐现“生产”历史的另一过程。如,现代作家进入“共和国”后自觉与不自觉困惑和“检讨”的精神裂变,文学作品歌颂的主旋律,传达出丰富复杂的“国家想像”、“农民想像”、知识分子的成长之歌、革命人生的狂欢体验等各色现代性“自我”。
同样,文学话语形态:战争主体的农民中心,民间市井的边缘;革命斗争话语,生活真实的故事、人物、抒情;知识者的改造,心灵选择、焦虑、直言。这些也主要是在文学史自足状态下的文学审美方式的考察。这一特殊时段文学的现代性“空间”和“过程”的形式特质,应该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形态:“对立”、“二元”模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与潜在精神取向的现代叙事逻辑相交织,即文学与历史在共生共存下想像、记忆的建构和营造。《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既是“文本”中的历史,想像的中国,又是“历史”中的作品,现代中国的注释(教科书)。而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陈翔鹤等一批“五四”文学精神承传的老作家,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选择。在《蔡文姬》、《关汉卿》、《胆剑篇》、《茶馆》等作品的背后,联系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多重话语,不约而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代言,彰显出创作主体和文学环境的紧张、矛盾的关系。这也使得40~60年代文学整体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成走向:革命战争与思想斗争主控了文学生态,但来自作家群体年龄的差异,身份、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五四”以来的老作家经历记述“成长历程”到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反省,再到徘徊于羁绊焦虑中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思想改造。崛起的青年作家不是生存困惑,就是不满现实的暴露和干预。革命的工农作家则是统一的自觉讴歌和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典型塑造,及其民间革命传奇故事的编织。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冯至、孙犁、王蒙、流沙河等作家的自我言说,潜在写作的民间立场,是文学史的另一线索。同时,也真正呈现了富有张力的“场效应”下,广阔的创作视域和多元的文学世界。
“场效应”视域中的文学史意义重估
40~60年代中国文学在“场效应”中多重叠加现象整合了过渡期社会复杂形态,使得文学史有了特殊历史时期丰富性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的40年代延安文学和由红色经典组织的50、60年代“十七年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一体化、工农兵主流化的文学,这些并非完全是文学精神的失落。他们在理想高扬和激情澎湃的讴歌中,最大限度地书写着作家与大众密切联系的生命形式,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存状态。丁玲在《作家与大众》文章中,表述作家为何而创作是这样说的,“对环绕在他周围的一切,有过思索、观察、有爱、有憎,下过判断,存过理想。这感情在他身上滋生、酝酿,发酵、爆发,他精神上、肉体上都需要把自己意见传达出去,他要争取大多数人是与他一致:感情的一致,意志的一致,努力的方向一致。于是他找着,摸索着,结果他找到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工具,他写起文章来了。”“文艺便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便不是有价值的文艺,没有价值的东西,还能说是艺术吗?当然不是。”(注:丁玲:《作家与大众》,《大众文艺》1940年5月15日,第1卷第2期。)这是刚来延安没有多久的丁玲的创作态度,与两年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十分贴近,与建国后许多作家的创作动机相同。由此,与大众密切联系的追求,文学现实感的强化,使得文学“场效应”生成了新质和变异的多重组合。一些文学审美理想突出和艺术个性强烈的作家作品,往往受到排斥、挤压,或者有意识的疏离。同时,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化又将社会生活反映的历史真实发挥到极致。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整体高扬的社会、民众、政治的理想精神,也是文学必需的,文学能够给予的。英雄的“神话”和典型的期待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需求。战争状态下被封锁的延安,需要调动最广大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国初期,文学“场效应”做出了一定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能够否认延安文艺、“三红一创”经典作品对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必须对文学“场效应”整体复杂关系做深入的清理,历史是客观也是主观的复合体,文学史的体验和理解比纯粹历史更加重要。
其次,40~60年代特殊情境下的文学场倾斜,从文学世界本身观照整体性的另一突出现象,是文学的创作主体比任何时候都受到生活本身的挑战和制约,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突起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上述我们对此段文学史结构和生成的梳理已经说明了诸多作家生成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历史的合理性的本身,正是来自现实、生活、大众的需求,文学的独特风貌正是由作家直接感受生活获得。这一点对在最强调生活与现实的主流文学之外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在宏大的革命战争生活、农村生活、农民解放生活、知识分子的成长生活等之外,理想的田园生活(沈从文)、漂泊的流浪生活(萧红、钱锺书)、没落贵族和市民人生的生活(张爱玲、梅娘)、中间状态的问题生活(赵树理)、普通人和“小人物”的生活(孙犁、茹志鹃)等作家的追求,同样是忠实于生活和忠实于自己生活的感受,烘托了文学史的丰富多彩。40~60年代中国文学中,“五四”的一代作家不是在奋起抗争中生存,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困惑。新作家的激情和主体政治附庸构成了政治文化的文学理想。真实的历史再现与再现生活的理想之梦,成为一个独特的既充满矛盾又充满理想的相互交织的文学场。文学场即是生活场,它不是单一的主体或客体,而是由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关系网络。我们旨在寻求特殊的过渡期的关系网络的丰富线条。
再次,在“场效应”的视域里,40~60年代文学史、文学本体世界的建构和解构,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悖论现象,恰恰呈现了转折与过渡期的历史真实。例如,工农兵和知识者之间的距离感形成身份的明显错位,文学创作中心与边缘的紧张对立,并且彼此的差异感从必须克服到人为消解的路向,也是有迹可察的。丁玲一度在延安的另类言行和文本创作,以及从《在医院中》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调整和转变;张爱玲的世俗的“传奇”和“流言”的人生,曾经如流星划过“孤岛上海”寂寞的天空,但是很快便销声匿迹;赵树理的农民与大众化的“方向”,也很快成为赵树理本人的精神负担和始终解不开的“谜底”。“‘五四’的作家纷纷检讨自己的过去创作的失误:‘贸然以所谓的‘正义感’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是非常幼稚的、非常荒谬的’(曹禺);‘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茅盾);‘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冯至);‘我几乎不敢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老舍)”(注:洪子诚:《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文学过渡时代一方面是必然性叙事和理想的极度张扬,另一方面是主体的焦虑和矛盾。既是历史对现代性话语范式的覆盖,又是过渡转型中文学新的生长点,是对历史的积极应对,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充实。显然,“场效应”集中聚合了革命时代精神现象的许多复杂因素,也提供了最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文学特殊案例。
最后,这段文学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场效应”使得创作主体的重塑与历史记忆的重叠,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史的思路。这三个十年的文学是多种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文学,更是政治意识形态逐渐借助文学归化(改造)创作主体,或者再造创作主体的文学。因此,三个十年文学史每一个十年的演变,并非一定是因果关系的流变。主体的重塑和历史记忆的叠加形成了特殊性文学“场效应”,也必然推动“场效应”中文学主体世界复杂因素的互动关系的检视,使得这一段文学史被真正还原到造成文学生成蜕变的具体意识形态生长过程中关系网络的考察。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清理文学史的一切相关材料(出版、期刊杂志、党派文件、商业广告、经济报道等);重读文学作品(作品概念也不仅仅包括战争、革命、农民、知识分子、都市、乡村等题材,而且要扩展到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学,如日记等潜在写作)。而“场效应”作用于创作主体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生成和确定。如40年代的文学“漂泊”、“流亡”、“人在旅途”、“故乡童年”、“土地”、“家园”;50、60年代的文学“歌颂”、“抒情”、“暴露”、“成长”、“英雄”、“诗史”、“香花毒草”等创作现象和主题意象,将成为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和其研究的重要工作对象。关注作家的文学思想的变化、复杂多样的生存状态比起作品本身的研究,更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武训传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