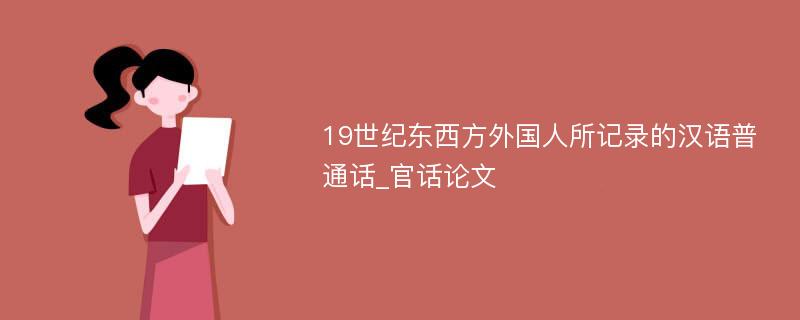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话论文,汉语论文,士人论文,东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交往来极少,所以除朝鲜司译院以外,欧洲的传教士和日本的商贸通事从实际需要出发,关注的汉语口语主要是南京官话,对通行于朝廷的北京官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和通商交涉逐渐增多,促使他们的外交人员和传教人员开始将目光从南京官话转向通行于朝廷的北京官话;而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传统华夷观的改变,也使北京官话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取代南京官话,获得正统地位,成为清末学堂官话教本的标准。此时期欧美与日本学人所编撰的汉语辞书和教材以及相关的国内文献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官话嬗变轨迹。
一、新教传教士所认知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等新教传教士随欧洲的殖民者东来亚洲传播“福音”。由于当时的中日朝东亚三国禁教和闭关锁国,这些传教士只好滞留在巴达维亚、澳门等地,通过文献资料等途径学习和研究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化,伺机进入东亚地区传教。此间,马礼逊耗时十数年编写了多卷本汉英辞典《三部汇编汉英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三部分分别于1815年、1822年和1823年在澳门正式出版。
马礼逊的这部汉英辞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完全按《康熙字典》部首顺序排列汉字,编译汉字词汇。辞典的开篇有一个长达16页的关于汉语言文字的导言,对汉语、汉字及其音韵和训诂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说:
官话(Kwanhwa)广泛使用于江南和河南的省份,因为两地都曾建有朝廷,所以那里的语言赢得了支配地位,优于其他省份的语言,成为宫廷语言的规范,是受教育者的标准语。现在,一种鞑靼汉语(Tartar-Chinese Dialect)正逐渐赢得地盘,如果这个朝代长久持续的话,它终将取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么一句话:“皇家语言是专为区别于平民语言而特定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4册第52页),语言间逐渐出现差别与技术或发明无关。[1]x
根据马礼逊《汉英辞典》的解释,“Tartar Chinese”指的是“满洲人”,“the Tartar language”指的是“清话”,所以,马礼逊这里所言的“鞑靼汉语”指的应该就是通行于清朝朝廷的北京官话。他以《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皇家语言”的定义为理据,预言“鞑靼汉语”终将取代其他官话成为官话标准是有现实依据的,清人高静亭《正音撮要》的序言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礼逊预言的合理性。1810年,高静亭应乡邻亲友学官话之需,编就官话教材《正音撮要》,于1834年付梓。此书序曰:“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语音不但南北相殊,即同郡亦各有别。故趋逐语音者,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内又以皇都为则。故凡搢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2]1361不过,这段话中的“趋逐”和“趋仰”两词表明,京话在当时也只是时髦而已,并未成为朝廷正式颁布的官话标准,高静亭自己在《正音撮要》卷四《千字文切字》所采用的注音也并没有依据京话京音。正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所言:“实际上,该千字文的音系存在入声,并不能视为单纯地依据了所谓的北京音。”[3]781
19世纪30年代,新教传教士终于进入广东等地传教。1832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介绍中国及东南亚等地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历史地理等方面信息的文章。1834年5月,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汉话》("The Chinese language")和《汉文》("TheChinese written language")两篇长论,详细介绍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发展历史和学习方法,内中对官话(the mandarin dialect)的介绍如下
在帝国的北方省份,广泛通行纯正的汉语,这种汉语一般被称为官话。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如果不用当地的词汇,也不会被听懂。在中国北方与鞑靼接壤的地区,满洲人统治所导致的语言变化非常明显。毫无疑问,此种影响遍及整个帝国的边境地区。在浙江和江南,纯正的汉语(那里大部分人所说的语言)与当地方言间的差别非常明显。在福建省及其东部地区这种差别更加显著,对于一个只会标准汉语的人而言,当地常用的福建方言是非常难懂的。在帝国的西南省份,较少偏离纯正的汉语,这些城市通用的语言非常类同于政府朝廷所通行的语言,一个人如果懂得其中一种,只要稍稍留意一下交谈的主题,就大致能听懂另一种。[4]3
从裨治文的介绍看,当时浙江省和江南省(今江苏和安徽)虽有地方方言,但大部人在说“纯正的汉语”,即官话;西南省份的汉语比较接近于官话;北方省份虽通行官话,但间杂有当地乡言俚语,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密集的地区,汉语已经因清朝的统治而大为改变。
1842年,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lams,1812-1884)分别编撰出版了汉语语法书《汉语语法指南》(Noticeson Chinese Grammar)和汉语教科书《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这两本书在介绍汉语音韵特点时虽然没有特别强调官话,但他们都引用了马礼逊对汉语音韵的论述,说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之分。有人声的存在,说明他们介绍的汉语并不是以北京音为基准的。因为当时来华的西方土人已经非常清楚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无入声调。1840年,英国人罗伯聃(Roberr Thom)和被他称为蒙昧先生的中国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晚清第一个《伊索寓言》汉译本《意拾喻言》,[5]64-67,罗伯聃在这本《意拾喻言》的英文前言中对汉语有一个概论性的介绍,他在其中称汉语的口语为“言语”(yén yü,or Spoken Language),并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即“官话”(kwan-hwa,or Mandarin Language)与“乡谈”(Heang-tan,or local dialects)。他说:
“官话”又可以分为:
第一类:“北官话”,也被称为“京话”或“京腔”,简言之就是北京城的语言。这种带有大量粗俗俚语的方言(idiom)在以前首都还在南京的时候,被认为是非常低俗的土话(patois),就犹如现今的广东话,然而当朝皇帝们一直住在北京,他们说话都带有北方口音,以至于那些不敢落伍时代的年轻人尽可能像北京那样说话。依他们的话说:那是皇帝的嘴巴,圣上难道还会有错吗?(这是一个中国人几乎无法辩驳的理据。)而且,由于北京人很少参与贸易,他们主要跟随整个帝国的官吏们,这些官吏随处可见,所以所有官府都使用他们的语言。当普通百姓听到说话者的口音,他们立即会作出判断,言者是否为政府的雇员,是否需要敬畏地面对这些人。我们可以从《红楼梦》(24卷)、《金瓶梅》(20卷)、《正音撮要》(4卷)和《圣谕》(2卷)中找到最佳的北京方言的语料。
第二类:“南官话”,又被称为“正音”(true pronunciation)和“通行的话”(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严格说来,这才是官话,或者说是南京城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人将“正音”这个词用来专指他们的方言,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想发“入声”或者说“短促声”,然而又当然性地无法正确地发这种音。要求这个国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说好官话,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意大利的一句谚语:“像一个土生的罗马人一样说托斯卡纳语”。南京话(The Nanking language)被用于舞台并或多或少地出现于他们所有的小说之中。[6]vii
罗伯聃对于汉语官话的介绍显然肯定了南京话的正统性,但也指出了北京话在中国官场所呈现的强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马礼逊在《汉英辞典》中的预言。
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礼逊的后继者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迪谨(Joseph Edkins,1823-1905)则明确指出了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有无入声。1857年,他在上海出版《汉语口语(官话)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Core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7]190,1864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在修订本的第二章中分8个条目详细介绍了官话的发音系统。其中指出:“官话”通行于三分之二的中国,范围包括长江以北的各省、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广西的一部分。由于地域广阔,各地的官话往往混杂着一些“乡谈”,带一些本土腔,所以“官话”又有不同的地域名称,如“山东官话”,就是山东通行的官话。“官话”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南京、北京和北方各省以及西部省份,其中南京官话有五个声调;北京官话也就是“京话”,只有四个声调,第四个声调分流至其他四个声调之中①;西部官话的范围至少有南京和北京官话那么广,它以四川的首府成都府为标准,也是四个声调,如果尾音“ng”跟在“i”后面,就变音为“n”,如“sing”(姓)就与“sin”(信)发同一个音;区分这些官话的主要依据就是有“四个声调”还是“五个声调”,是否只有“n”和“ng”的尾辅音,以及在其声母中是否有g、d、b、z、v等这些字母的语音特征;外国人记汉语的音通常依据中国各种辞典的正字法,混合了南京和北京的发音[8]7-10。在谈及北京官话时,艾约瑟专门作了一个注释说:北京本地的学者认为首都方言有别于官话,例如,“I”、“you”的发音ngo、ni是官话,发音wo和nin、na则是京话。另外,艾约瑟还特别指出:从政治性考量,因首都是北京,所以暂且将北京话作为官话的标准,但作为真实的语言学,必须对包含整个领土范围内的语言进行研究,包括它们的特征、流行的口语等;而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必须学习北京话,这种北京话已经净化了土音,被公认为“帝国官话”,不过,目前还没被选作拼写的唯一标准,因为它与这个国家南半部的同类语言差别较大;北京话虽然时髦,但南京话使用范围更广。
以艾约瑟的这本《汉语口语(官话)语法》为契机,来华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和通商人员开始将学习官话的重心由南京官话逐渐转向了北京官话。
二、西方外交官员开始重视北京官话
艾约瑟在《汉语口语(官话)语法》中对官话现状的介绍首先引起了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的强烈共鸣。他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北京官话,终于在1867年出版刊印了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迩集》。在其序言中,威妥玛引用艾约瑟关于官话的论述说:
……然而,“dielect”这个词是令人误解的。“官话”(kuan‘hua)不只是官吏和知识界层的,而且还是近五分之四的帝国百姓的口语媒介。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势必有各种各样的语言(dialects)。艾约瑟先生,没有人像他那样努力去探究过这些不同方言的规则与界限,他将官话划分为三个主要系统:南方的(the southern)、北方的(the northern)和西部的(the western),并将南京、北京和四川省省会成都分别定为各个官话系统的标准。他认为南京官话(Nanking mandarin)比北京官话在更大的范围被理解,尽管后者更为时髦。不过他承认,“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必须学习北京话,这种北京话已经净化了土音,被公认为‘帝国官话’(kuan‘hua of the Empire)。”[9]vi
威妥玛不仅对艾约瑟的观点作了介绍,而且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在这里引用这种观点是为了证实我自己很久以前的一个结论,即北京话(Pekingese)
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dielect)……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在逐渐侵入所有另外的官话语言……
这一点,即选择并确定一种语言(a dialect)为对象,大约是20年前的事,接下来就是建立表音法。那时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表记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表记的是南方官话(the southern mandarin)——诸如马礼逊博士(Dr.Morrison),即第一部汉英辞典的编纂者,麦都思博士(Dr.Medhurst)和卫三畏博士(Dr.Wells Williams)等人——他们对于土著话语系统的描写,远不是无懈可击的。有人认为马礼逊的表音法是官话表音法,但艾约瑟先生否定了这种观点。[9]vi
此前,马礼逊、麦都思和卫三畏等传教士将南京官话视为汉语官话的正统,并以南京音为基准、用罗马字注音建立了汉字声韵表。但作为外交官的威妥玛自“大约是20年前”的19世纪40年代起,独树一帜地将北京官话视为外国人应该首选学习的官话,而艾约瑟的“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必须学习北京话”的论断给了威妥玛强有力的支持。自此,西方传教士与外交和商贸人员对于官话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从事外交和商贸的人员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更多地与来自北京朝廷的官员打交道,所以尤其倾向于将北京官话视为“帝国官话”。
那么,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于官话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规范呢?当代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对清代官话的相关史料进行过梳理,发表有《关于清代官话的资料》一文,文中引用了《东华录》雍正六年(1728)七月上谕广东、福建两地籍贯的官员必须学会使用官话的记录②,并指出:以此为契机,中国陆续出现了各种官话教科书,但由于是局限于广东、福建两地,所以无论是诏令学官话的效果,还是在那里诞生的官话教科书的质量都不尽如人意[3]771-784。在这些官话教科书中,莎彝尊的《正音咀华》当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他不仅在该书中给“正音”下了一个定义:“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而且还对官话南北音作了解释:“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10]1。这说明无论南京话还是北京话,虽然都属官话,但都不等同于“正音”。不过,莎彝尊在卷一列了一张《正北音异表》,用45个汉字举例说明了“正音”与“北音”的读音之别。“北、百、白、薄”等其中37个字实际上就是有无人声的区别,在“正音”为入声,在“北音”人声消失。莎彝尊在其另一本著作《正音切韵》中同样也附了《正北音异表》,然而,此两部书都没有列《正南音异表》,可见,当时的“南音”与“正音”的差别并不像“北音”较于“正音”那么明显,这大概也正是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和罗伯聃等人将南京官话当做官话正统的原因之所在。不过,莎彝尊毕竟也没有下结论说南京话更接近于官话“正音”。如此,所谓“正音”实际上成了一种既没有实际参照语言,又没有具体到音素的拼音体系可据,更没有声音媒质可资鉴别的模糊性概念。难怪熟习音素文字的西方士人在以罗马字对汉字读音进行注音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学习汉语官话究竟应该选择北京话还是南京话,争议不断。
19世纪中叶,艾约瑟和威妥玛的“必须学习北京话”的观点似乎占了上峰,威妥玛编写的《语言自迩集》不仅深受欧美人士欢迎,于1886年出了第二版,而且还受到了日本外交人员的热捧,被东京外语学校等日本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机构采用为汉语教科书,以应付由传统的教授南京话向教授北京官话的急速转变[11]88-92。不过这个时候南京话并没有被轻视,仍然被认为是官话的正统。1872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卢公明神父(Rev.Justus Doolittle)在福州、伦敦、纽约和旧金山同时出版《英华萃林韵府》(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他在该书的前言第三段中如此写道:
汉字已经依照威妥玛先生拼写北京官话(Peking Mandarin)音的系统进行罗马字转写。如此,书中的汉字究竟应该依据北方还是南方官话进行罗马字转写,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我曾被认真地建议应该用南方官话转写,但由于我住在天津时已经学了北方官话,所以无法采纳和实施这个建议,从而导致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少的错误。那些喜好南方官话的读者,我建议你们参看第二册中以那种语言(that dialect)写就的汉字音节,内中的介绍性评述指出了北方官话与南方官话最大的区别,熟悉一种官话的人有必要了解另一种官话的特性。[12]1美国传教土卫三畏于同治甲戌年(1874)以《五方元音》为蓝本编写出版了汉英字典《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该书的导言中,他也引述了艾约瑟关于官话的三大分类说:
在此广阔的区域,大概被称为“南官话”和“正音”或“正确的发音”的“南京(话)”使用最广,它被描述为“通行的话”,或“到处都明白的话”。然而,作为“北官话”或“京话”为众人所知的“北京(话)”现在最为时髦,最具宫廷色彩,就好像伦敦的英语,或者巴黎的法语,被看做是公认的帝国的宫廷语言。[13]xxxii
话虽如此,不过卫三畏还是将北京音与汉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东方言音排列在一起,作为八种方音与官话音列表进行具体比较。他还特别指出:“在上海、宁波以及整个江苏和浙江所听到的语言在语言风格和发音上更接近于官话。”[13]xviii而且,在他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dom)修订本中,对“宫廷语言”还作了另一番介绍。《中国总论》初版于1847年,35年后,鉴于“这一段岁月里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可能超过先前历史的任何一个世纪”,作者对该书作了修订,于1883年再次出版。修订版中,作者对“语言和文学两章作了大量改进”[14]1-2。语言这一章指的是第十章“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他在其中这样介绍:“宫廷语言(the court language),也即官话(Kwan hwa),或‘曼达林’语(mandarin dialect),与其说是一种方言(a dialect),还不如说是国家正式语言——即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15]613。接着,他阐述了在华欧美语言学家对汉语的研究成果,其中也论及了马礼逊和威妥玛。在这里,他还是认为马礼逊的汉语罗马字所转写的是“宫廷语言”,而威妥玛的则是“北京话”。他说:“在马礼逊的《字典》里,宫廷语言(the court dialect)中不同音的字有411个,若将送气音的字区别开,则有533个。在该作者的《音节字典》中,是532个。威妥玛的北京话(Peking dialect)表中只有397个,另一张表则增至420个。”[15]611
由此看来,虽如威妥玛所言,北京话在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知识分子间的语言生活中已经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并没有被公认为官话之标准,它仍然只是一种“dialect”而已,并不等同于“the court dialect”。卫三畏自1833年起在中国的广州、北京等地居住长达43年,一度曾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1874年还曾随美国公使觐见了同治皇帝。应该说,他亲历了当时近半个世纪的汉语官话的实际变迁。他对官话略显矛盾的介绍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语言生活中南北官话并存通用的实际状况,而他个人从传教士到外交人员的角色转变也决定了他取舍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的态度,传教更需要使用范围较广的南京官话,外交则更需要朝廷流行的北京官话。
三、北京官话上升为清朝的国语
用途的不同使西方来华人士在对汉语官话的取舍上有所侧重,传教士往往选取使用范围较广且他们认为是“正音”的南京官话,而外交通商人员则往往选取通行于朝廷的、更具实用价值的北京官话。此种情况也反映在日本的汉语教育中。
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中日两国都处于闭关锁国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多的是局限于长崎与中国南方的贸易往来以及由此顺带的文化交流,所以当时日本的汉语教育是“唐话教育”,教授的是南京话[11]264-292。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主体意识增强,开始重视与清政府的外交往来,于是,汉语学所等日本的汉语教学机构便将汉语教育的重心由南京官话转向了北京官话。日本现代学者六角恒广对日本的近代汉语教育史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日本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国语教育应从明治九年(1876)9月北京官话教育的实行算起。所谓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国语教育并不是指由语言学的汉语发展历史规定的近代汉语,而是指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起了作用的中国语教育。在19世纪70年代,为了适应外交的实际需要,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数年后便从南京官话转变为北京官话教育。同时他还认为:“进入明治后,中国语教育之所以被重视,是外交上的需要,而带来向北京官话转变的契机,也是外交上的需要。”[11]77-87为适应急速转变的形势,日本一方面只好使用当时仅有的北京官话教科书——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另一方面分批向驻北京公使馆派驻专门学习北京官话的留学生。明治十四年(1881),长崎人吴启太和东京人郑永邦驻北京三年后,总结自己学习北京官话的经验,合作编就了实用性北京官话教本《官话指南》。在此书的凡例中,作者明确该书所指的官话是分“上平、下平、上声和去声”四声的北京官话。但他们还特别强调说:“京话有二:一谓俗话;一谓官话。其词气之不容相混,犹泾渭之不容并流。是编分门别类,令学者视之井井有条,厘然不紊,庶因人因地而施之,可以知所适从。”[16]1这说明当时的北京官话除语音外,遣词用句与北京方言是有很大区别的,延续了传统的官话语汇。
其实,用途的不同不仅对外国人取舍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文人自己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卢戆章(1854-1928),青年时期赴新加坡学习英文,回国后帮助英国传教士麦嘉湖(John MacGowan?-1922)编译《英华字典》,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一套拼读汉字用的切音字母,编成书刊印出版,取名《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提出:欧美文明之国之所以文盲极少,文风极盛,是因为“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划简易故也”;日本也以47个简易字划的切音字(假名)兴盛文风。中国有切法,但无切音字,所以创制了这套切音字母,以帮助国人识读汉文。他还认为官话应以“南京腔为各腔主脑”,理由如下:
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17]6
以上这段文字表明,直到19世纪末,中国大部分地区最为通行的仍然是南京官话,与17、18世纪时的状况并无多大改变。日本江户时代教授南京话的唐话教科书《小孩儿》就有类似的说明:
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通得了,苏州、宁波、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那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11]270
当卢戆章从中国当时语言的实际通行状况出发提出“字话一律”方案时,认为应该用南京话为正字、正音,然而当他的切音字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维新者们所采用时,他又转而改用了北京音,以京音官话设计了第二套切音字方案,著成《中国切音字母》。而且,为配合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学务纲要》第24条,即:“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卢戆章又于1906年付梓《北京切音教科书》(首集、二集)。他提出:“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京音官话为通行国语,以统一天下之语言也”;如果能通过切音字让全国百姓学得京话,识得汉文,那么,“全国都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弱?人民何致鱼肉”[18]2-3此时的卢戆章一改原本提倡用最通行的南京话为正音的主张,接受张之洞等洋务运动领导人的近代教育思想,以京音官话为通行国语。可见,立场的不同同样也左右了卢戆章对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取舍。而张之洞等人拟就的《学务纲要》终于让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赢得了汉语的正统地位,且以朝廷典章制度形式得以确认,成为具有法律效用的语言规范。
北京官话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最终超越南京官话而获得清朝的国语地位,笔者以为与当时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改变有很大关系。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的半个多世纪里,由于不断遭受帝国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洋务派、维新派等上层士人对传统的华夷观展开了反思。到了19世纪中后期,夷夏之辨的演变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在维新派收拾西方学理构建民族主义理论后,无论主张学习西方者,还是反侵略者,都不再在‘夷夏之辨’上做文章。”[19]62近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以及维新派强调满汉民族之间的融合与趋同,反对排满的思想等政治环境,促成了语言学家改变了对北京话的偏见③。换言之,正是此种传统华夷观的改变,为北京官话获得正统地位提供了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从19世纪中外士人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记载看,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朝廷强调官员必须学会使用官话,但官话实际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各地通行的大抵只是“蓝青官话”,其中最主要的有北京官话、南京官话和西南官话三种。从使用范围看,南京官话最广,最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甚至被认同为“正音”。但由于北京的京城地位,北京官话越来越受士大夫们的青睐,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洞开,北京官话也日益受到西方及日本外交官员们的重视,外交事务的需要促使他们纷纷由原本学习南京官话改为学习北京官话。传统华夷观的改变以及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也使经历洋务维新运动后的清朝政府实施近代化办学方针,在官学中开始推行以京音官话为标准的国语,北京官话终于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超越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汉语口语之规范。至于清朝灭亡、民国初期重新陷入国语国音的纷争,则又当别论。
注释:
①在艾约瑟的这本《汉语口语(官话)语法》中,汉语声调的排列顺序为“上平”、“上声”、“去声”、“入声”和“下平”。第四个声调指的就是“入声”。
②《东华录》雍正六年七月条曰:“甲申谕: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例,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扦隔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言,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晓矣。”参见《东华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③当时中国人对于北京话的偏见最大的莫过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1852年,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发布了一道《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内曰:“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州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页)。此与明代王世贞等人提出的“大江以北渐染胡语”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标签:官话论文; 北京话论文; 马礼逊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南京话论文; 威妥玛论文; 艾约瑟论文; 威妥玛拼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