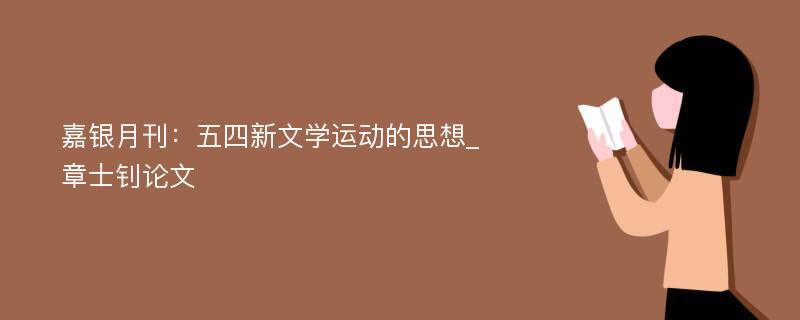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寅论文,先声论文,月刊论文,思想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著里,章士钊、《甲寅》杂志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是逆向意义 的,即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主义的代表,《甲寅》杂志就是保守主义的大本 营。这些结论显然主要是根据章士钊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职、《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 刊以后的种种表现,它基本上忽略了章士钊这样的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的实际的体验、 表现与影响,毕竟,此时此刻的章士钊并不是反对文学变革的守旧形象,当然更不是后 来压制学生运动的“老虎总长”。他在日本创办的《甲寅》月刊杂志所刊登的文学作品 虽然属于旧体,但当时也不存在与新文学对抗的问题,何况文学并非它讨论的重点,政 治文化才是它检讨的目标,而就是在对近代至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的反思当中,章士钊 和《甲寅》月刊同人实际上重新调整了个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架构,从而为确立未来五 四新文学的基础立场——个人主体立场从现实政治思想的意义上打开了通道。本文意在 通过对于《甲寅》月刊及其代表人物的简要追述,提醒学界注意到其作为五四新文学运 动“先声”的重要事实。
一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史上,章士钊与《甲寅》月刊的价值得追溯到中 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民族观念的重要嬗变之中。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鲁迅兄弟出现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理想还是固守在民 族国家建设的层次上,尽管这样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出现了从“维新”到“革命”的发展 演变。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根本改变这一顽固的国家主义的人生与文化的认知方式,还 得重新返回到民族国家建设所依据的社会政治思想本身,只有在这一层次上发生了思想 的裂变,只有新的社会政治观念得以进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思想认知的方式,最 终形成中国文学现代转换所需要的“立场”与“格局”。
于是,我们看到,进一步的嬗变还是首先出现在社会政治的观念上。回顾近现代中国 的历史,尽管政治给文学的损害十分明显,但也必须注意到,在从封建专制主义向现代 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如果没有社会政治观念的变迁,没有文化专制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削 弱,一个普遍的广泛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影响中国学界革新意识的主流政治理念来自维新派与革命 派,他们虽然也各有不同,但却常常又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是从族群的社会的与国家 的角度来思考现实,他们相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根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问题, 而整体目标的解决也就是个人的现实要求的达成。我们说过,正是这样一个排斥了个人 的立场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浓厚的政治功利性,又是这样的政治功利性妨碍着中国文学在 通达个体精神的道路上完成根本性的历史转折。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观念在辛亥革命 之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推翻封建王朝、完成民族国家的“整体”革命以后,一个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新 中国并没有降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专制政治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的自由与幸福 ,“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7年的时间里 ,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70年的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面对这样 的政治乱局,一批遭遇了变乱又敏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那种将个人幸福寄托 于国家政治整体追求的理想无疑是失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个民族与群体 的笼统问题,它必须要切实地返回到对个人权、地位与民主自由的现实中去。
同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者而流亡日本一样,一批因为政治失败而 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又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因为政治理想的不同他们成了新专制主义的 反对派,又因为国内专制统治的残酷而不得不充当亡日人士,像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 为、梁启超那样避祸东瀛,暂借日本的自由空间来反思过去、设计未来。只是,在历经 了近代政治的风云变幻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将个人的命运简单交 付给空洞的国家主义理想,现实的深刻教训迫使他们必须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作重新的 思考和定义,这批知识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流亡者章士钊与陈独秀 。
章士钊先后留学日本与英国,系统考察学习了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 ,受辛亥革命感召归国,1912年在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宣传以英国为 典范的政党模式与政治制度。早在1902年春,当时尚在南京陆师学堂求学的章士钊就结 识了从日本回国演讲的陈独秀。1903年,上海《苏报》被封,章、陈等人创办《国民日 日报》,以承接其批评时政之理想,由此而友谊笃深。辛亥革命以后,两人都投入到反 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他们先后又都流亡日本。此时的日本,又如同百 日维新失败之后一样,再次成了中国政治家的流亡之所与反思之地。逐渐地,在原本就 声威卓著的章士钊、陈独秀周围,汇集了一大批的思想者,他们或者是流亡的知识分子 ,或者就是留日或曾经留日的学生与学者,前者如易白沙、刘文典,后者如李大钊、高 一涵、吴虞、吴稚晖、杨昌济、张东荪等等,因为章士钊1914年4月主编《甲寅》杂志 的关系,他们都有了思考与表达的机会。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等应邀参加编辑工作 ,李大钊也在后来一度参加了上海《甲寅》日刊的编辑。
二
章士钊一度也是国权论的阐述者,他以边沁的法定民权说为根据,质疑卢梭的天赋人 权论,对民权的“幼稚叫嚣”担心不已,以为国人因此而“笃为玄想,习为放纵”。( 注:行严:《平民政治之真诠》,《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然而,正是民国以后的 专制复辟给了他深刻的教训,《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完成了从早年倡导国权到倡导 民权的重要转变。
因为与同盟会政治主张的分歧,章士钊最初是在国内自办《独立周报》,表达了他对 当时政治的失望,“人心不革,则无论何种政治,不能救我中华”。反袁革命失败,章 士钊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主编出版了《甲寅》杂志,成为《新青年》杂志问世以前 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一个主要传播阵地。民主政治是章士钊这一时期探讨的基本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此刻对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已经与一般的革命人士大有不 同,“同盟会——国民党在民初号称‘民权党’,但它所指的‘民权’实际是人民的公 权,即人民的参政权,并且将参政权简化为议会的权力;而人民的私权,实际并未纳入 其视野。”(注:邹小站:《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近代史研 究》2000年1期。)章士钊一度也曾经是“国权高于民权”的国权主义者,但就是经过这 个时期对国内乱局的反省,他认识到在中国,恰恰是“行私者每得托为公名以相号召, 抹杀民意以行己奸,毁弃民益以崇己利”,(注: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存稿 》卷上,商务印书馆1922年,313页。)“中国之大患在不识国家为何物,以为国家神圣 不可渎”。(注: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杂志存稿》卷上,商务印书馆1922年 ,340页。)于是他一改前议而成为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凡关于权利欲望 之种种主张,直主张之,无所容其嗫嚅,无所容其消阻。”(注:章士钊:《自觉》, 《甲寅杂志存稿》卷上,商务印书馆1922年,320页。)《国家与责任》、《复辟评议》 、《爱国储金》、《国民心理之反常》是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发表的重要论著。在这里, 颇有象征意味的是章士钊一出手就将严复选作了自己的理论对手。《民立报》时期的章 士钊对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还颇有疑虑,而现在,当他读到严复对卢梭人权思想的指 责时,却挺身而出予以辩驳,这就是他发表在《甲寅》创刊号上那篇著名的《读严几道 民约平议》。严复的原文《民约平议》发表在梁启超新办的杂志《庸言》上,严复、梁 启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具影响的启蒙先驱,章士钊《甲寅》创刊号上的这一公开的辩 驳可以说就是一种标志: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从自己的现实体验出发划开了与前 一代思想家的距离,由此,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如果说关于 “个人”本位的思考能够在六七年前出现在鲁迅等人那里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 ,今天,在现实政治的教训之下则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共识,这就是推动中国现代文 化形成、灌注于现代文学内核的理性精神,也是六七年前试图超越政治小说而起的中国 本土的文学创作所欠缺的新的思想能量。
章士钊和他的《甲寅》杂志就是在这一思想层面上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的。 例如李大钊曾经以热切的目光关注着章士钊和他的杂志,在1914年致章士钊的信中,他 写道:“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所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 “得《甲寅》出版之告,知为足下所作,则更喜,喜今后有质疑匡谬之所也。”(注: 李大钊:《物价与货币购买力》,《甲寅》月刊1卷3号。)李大钊后来成了《甲寅》月 刊的重要作者。据《甲寅》月刊发行人、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日记记载,《甲寅》杂 志的单行本与合刊在上海购者甚众,供不应求。(注: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29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吴虞日记》告诉我们,即便是当时成都这样的内陆 城市也有许多读者争相阅读《甲寅》月刊,吴虞也成了杂志的作者,(注:吴虞:《吴 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时间,《甲寅》月刊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 检讨近代以来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目标,重新判定个人与国家、民族相互关系的思想策 源地。
杂志每期的重头戏由论著、时评、评论之评论、论坛、通信等几个部分组成,既有个 人的政治立论,又有对当前国家政治形势与方针政策的评价,也有对西方政治制度、政 治理论的介绍,在所有这些内容之中,都贯穿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与人权 的呼唤。高一涵提出“国家者建筑于人民权利之上”,(注:高一涵:《民福》,《甲 寅》月刊1卷4号,1914年11月。)张东荪将“人民独立自强”作为“第一问题”,(注: 张东荪:《行政与政治》,《甲寅》月刊1卷6号,1915年6月。)吴虞反孔非儒的诗歌《 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发表在《甲寅》月刊1卷8号。其他作者的代表作如白沙《广尚同》 、渐生《爱兰国民党》(1卷3号)、汪馥炎《舆论与社会》(1卷4号)、劳勉《论国家与国 民性之关系》、CCY生《改良家族制度札记》(1卷6号)、运甓《人患》(1卷8、9期)、无 涯《道德进化论》(1卷10期)等。
章士钊当时主张政治应当“有容”,“有容”的政治思想也形成了他“有容”的办刊 宗旨,这在当时也的确鼓励了像陈独秀等人比较激进的捍卫个人自由权利的思想主张。 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也曾是梁启超学说的受惠者:“读康先生及其徒梁 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注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新青年》2卷2号。)但在日本留学又流亡的经历 、继而辅佐章士钊编辑《甲寅》的他却终于有了新的思想认识,《甲寅》1卷4期推出了 陈独秀著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激进地高举个人的权利,与曾经盛行一时的国 家主义思想形成尖锐的对抗:“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甚至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 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就是这篇论文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决定着五四 思想主潮的论说实际上是借着日本这一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完成着与传统思想的一次至关 重要的交锋。当许多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来信斥责陈独秀的言论时,作为主编的章士钊亲 自撰文予以辩护,他发表《国家与我》一文将陈独秀的合理性归结为“解散国家”、“ 重建国家”的爱国意识,是对于“伪国家主义”的自觉,同时主张发扬人格独立精神, “颠覆本族之僭暴者”,建立可爱的新国家。(注:秋桐:《国家与我》,《甲寅》月 刊1卷8号。)李大钊在《厌世心与爱国心》中虽然不同意陈独秀“恶国家不如无国家” 的消极情绪,但也表示:“我需国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则国家者,方为可爱。” 李大钊还根据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提出,人生主要的价值在于一种创造力,这种创 造力也是他作为宇宙主宰的独立的人所必备的品格。“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 ,自我主宰。”
五四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日本这一言论空间,展开了关于个人与国家、民族发展 的新的考察和论战。考察与论战的成果完善了以个人独立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思想方 案,正是这些方案成为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基本思想资源,也正是这样的考察与论 战催生了像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新文化大将。《青年杂志》评述《甲寅杂志 》是“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注:《通讯》,《新青年 》1916年10月2卷2号。)
三
陈独秀是在反袁革命失败后不得不流寓域外的,据说他一度“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 有无数虱子”。(注: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我以为,恐怕也 就是这样的体验提醒着人的“个体”生存的事实,从而为陈独秀和他的流亡同志重新定 位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以真切的启示。于是,我们这里特意提醒大家留心一下《甲寅》月 刊的文学动向,尽管在此时文学并非杂志关注的要点。但是,新的思想理当为文学的感 悟场域开辟新的空间,何况此刻的新思想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它本身就是现实人生 的经验小结。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就是从《甲寅》月刊时期开始,陈独秀对苏曼殊的爱 情小说大加褒奖。《甲寅》1卷7期发表苏曼殊的新作《绛纱记》,1卷8期又发表了《焚 剑记》,在同时发表的评论文字之中,陈独秀着重突出的是文学的人生况味,从而与前 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观划开了界限。例如他对苏曼殊的小说爱与死的主题 有相当深入而细致的感悟:“知人生之真,使不即得,不死何待?”这番语言大约能证 明他就是苏曼殊的知音,“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死,曰爱。”他还引王尔德的剧 本《萨尔美》为例,表达了对以死为结局这一爱情至上观念的赞赏。(注:陈独秀:《< 绛纱记>序》,《甲寅》1卷7期。)面对近代中国文学政治压倒私情的传统,面对梁启超 一代人“勿为情欲之奴隶”的谆谆教诲,陈独秀的这番感慨已经透露出了基于个人主体 立场的新的文学意识,他对于苏曼殊文学价值的发现也是颇有远见的。
过去我们往往将善于“言情”的苏曼殊作品归入鸳鸯蝴蝶派,近些年来又注意到了他 所揭示的“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证的困惑体验”,(注: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性 体验的发生》第八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如果放在我们这里所追 述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角度,苏曼殊作品的独特意义同样十分的显赫:显然,苏曼殊 在亦革命家亦僧人亦多情才子“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很 难再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色与传统之中了——“言情”是他飘零人生的叹息而非 生命的质地,鸳鸯蝴蝶派“言情之正”的“正”对于苏曼殊而言完全是不伦不类,在革 命家慷慨激昂的呐喊与佛家的离尘出世之间,是一个苦苦追问“自我”存在秘密的生命 ,就像近代中国的革命志士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屈挣扎的现实关怀,近代中国的佛学思潮 流泻着一种自我再认的“反传统”追求一样,这样的生命的自觉也正是挣脱传统主流人 生哲学,渡向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留日学界、佛门高僧、南社同人、异域亲友与风尘 女子,苏曼殊穿梭于各种阶层各种角色之间却又傲然独立;言情、漂流与迷惑,苏曼殊 作品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学所没有的“个人本位”立场,体现了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 对现实人生意义的探询和求证。后来钱玄同也认为:“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 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注:见戴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97页,新 华出版社1987年版。)
章士钊也在《甲寅》上发表了小说《双秤记》,用作者的说法就是“今所得刺取入吾 书者,仅于身历耳闻而止。”强调“身历耳闻”的人生体验,这当然就与空洞的政治小 说不同了,作者接下来还进一步表示:“然小说者,人生之镜也,使其镜忠于写照,则 留人间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价,吾书所记,直吾国婚制新旧之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 为忠实之镜与否,一任读者评之。”(注:见《甲寅杂志》1卷4期。)
探讨中国文学的新路并非《甲寅》杂志的主旨,但由思想的更新而带来文学趣味的变 迁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前述陈独秀、章士钊对于苏曼殊的推重以及他们本人的文 学片论都是证明。有意思的是,1915年10月,《甲寅》杂志的停刊号上登载了《申报》 驻京记者黄远庸致编者章士钊的信,似乎正是洞见了《甲寅》杂志以“政论”为主体的 思想文化过渡,预言了《新青年》在未来的选择,在信中,黄远庸提出:“愚以为居今 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注:黄远庸 :《释言》,《甲寅杂志》1卷10号。)
标签:章士钊论文; 陈独秀论文; 苏曼殊论文; 甲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新青年论文; 李大钊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