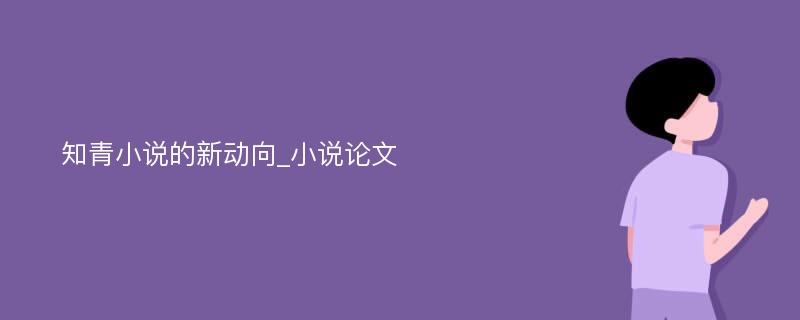
知青小说新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走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新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知青”生活,恐怕要成为本世纪末知青作家和非知青作家们关注的最后一道文学创作风景线。
最近由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所引发的对一代知青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的不同看法,显然会成为各种不同作家的诠释自己主体意识的焦点。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它是被绑缚在“伤痕文学”的祭坛上,用悲剧的手法抒尽了一代知青的苦难和悲情;尔后,它又被凌架于“英雄主义”的战车上,以悲壮的美学情调净化和圣化了那一段“苦难的历程”;九十年代,随着矫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溃灭,“知青题材”作为一个过去时态的历史而被封存起来。如今,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重新返观这段历史,其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那种“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应该早已淡化了,在磨出了老茧的心灵上,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我想以历史和人性的名义来冷峻地考量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动人和并不动人的故事。
无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动机,而就其客观效果来看,它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城乡大交流,是包括生活观念、思想观念、生存观念、人生观念等在内的两种思想和世界观的对撞、交锋、融合、排斥的历史过程,动态的城市文明和静态的农业文明之间冲撞所产生的那种很难区分的美丑、善恶、真假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区域中的判别,更会使我们的作家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案头放着两种不同的文本:一份是《上海文学》今年第1期, 上面有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另一本是王明皓的中短篇小说集《快刀》。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我想在玄思中找到一条回答今天,也回答明天的答案,虽然我知道这对作家来说是并不重要的。
在《大树还小》这部作品中,刘醒龙是以一个现代农村少年的视角(亦即知青的下一代人)来窥探那一段历史并作出人生的价值判断的。显然,这篇小说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以往“知青小说”的各种主题模式:知青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形象的瓦解;知青作为英雄形象的化身的溃灭;知青作为田园诗人的形象的崩坍,在《大树还小》中得以淋漓的体现。卢新华、孔捷生们“在小河那边”的“伤痕”变成了痞子们的自作自受;梁晓声们在“暴风雪”中的英雄气慨化作一团鱼肉乡里的匪气;就连史铁生、朱晓平们与农民的和谐田园牧笛也变成了毒蛇的诱惑,“青春祭”实乃一文不值的丑恶生活历史的写照。
说实话,刘醒龙对知青题材的重写是有着更深的历史内涵的,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女,大树就清楚地看到了这场运动最终是给一代知识青年带来了幸福,而把历史深深的遗憾以及它所遗留下的罪孽留给了最终尚挣扎在那祖祖辈辈厮守耕耘于土地上的农民。这种历史的不公,当然要激起两代农民的愤怒,正如农民看到知青们重演拿到招工表格时又笑又哭的情景时所说的那样:“怎么走不了就像是在地狱受罪,那我们前几辈子没有走,后几辈子也没走,钉在这儿就是理所当然的吗?”亦如大树用老师的话来说的那样:“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立场位移,形成了小说的另一种全新的审美价值判断。作为上山下乡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人的存在,知青在刘醒龙的笔下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蒙难者受害者到英雄末路再到普通人,这条线索在此全然崩溃,知青作为一种丑类的存在,仿佛完全是由于那次历史的错位,将两种生存状态尖锐地突现于历史的地表。
我以为刘醒龙的反省是有历史新意的,他起码从人性和人道的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最广大的农民所处的生存状态问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诚然是给农民带来了城市的现代文明,包括那份浪漫主义的悲情。我们看到了《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洗衣歌》给一代青年农民捎来的浪漫精神的诱惑和愉悦。小说所竭力营造的两组城乡青年恋爱者的悲剧,将知识青年和农村青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推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刘醒龙却没有把这种尖锐的历史矛盾向更深的“历史必然”去质询,而这样的“停顿”,只能造成更深的历史创伤,而不能形成历史的和谐。因此,刘醒龙在这种执着的信念下愈走愈远,以至将上一代人之间的纠葛与仇恨深深根植在下一代人心灵深处中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窥见到大树那双充满着仇恨烈火的眼睛。甚至让大树那犹如电影明星的姐姐因在都市里打工而遭到白狗子的糟蹋,二代人的恩怨岂是一笑可以泯灭的吗?正是为此,小说就更充满着火药味。
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主体的知青,在那个动荡时代里,在精神无所皈依的情况下,其所作所为固然有许多不合人性与人道之处,有的甚至干了些偷鸡摸狗的苟且之事,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甚至也就是极少一部分人所为,将此夸张上升为一种普遍,那是极不公平的。就我的体验,在那漫长的插队岁月中,虽然整天沉浸在悲观主义的情绪中,但在劳动中与农民结成的那种难以诉状的友谊却是终生难忘的,所以在读《那遥远的清平湾》时的和谐使我感到亲近。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的反思者,刘醒龙用血泪所塑造的文艺形象是令人深思的,这位被城/乡对立的世欲观念所戕害的女知青,最后终于在郁郁寡寡欢中投江而死,回到了她心灵的栖居地,亦证明了作者所阐释的意念,城市的知青可以抛弃乡下女子,而乡下的男人却为什么不能堂而皇之地娶一位女知青,即使是娶了女知青,也是别人扔下的破货。这种历史的不公还将延续下去,所以秦四爹要大树“治好了病再好好读书,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知青。”头顶青天面朝黄土的农民的唯一出路至今仍是“唯有读书高”这条道。
面对着许多知青回到当年落户的村庄去重新与昔日的农民叙旧,去重新体味一下那种生存环境。我们在电视纪实片中看到的是那种使人潸然泪下的动人情景;而在《大树还小》中却看到的是白狗子们“为了精神的需要”“回来感受一下,找一些灵感。”也就是寻找“人的历史对自身的重要性。”当然,像白狗子这样“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来寻开心的大款不是没有,但是,更为复杂的是,知青在寻觅“旧我”的过程中,其心境是难以描述的,面对昨日、今日和明日,他们是因人而异的,绝不可能只是白狗子一种心态,尤其是面对昨天,仅仅用忏悔是不够的,因为有些知青在回首往事时是无愧的,只有白狗子那种愧对乡里的知青才有权力忏悔。正如刘醒龙在《小说选刊》1998年第3 期的《书信208号》中所言:“忏悔不一定是为了改过, 真正的意义是重新支撑起一个人的精神天国。生命发展的残酷性同样也在忏悔上体现出来,有资格忏悔的人总是将忏悔发生在自己的成功之后,而失败者是没有这样的资格。”刘醒龙要求的知青忏悔无疑是“寻求苦难与幸福的和谐”,而在其具体的创作中,作者之所以陷入偏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忽略了知识青年们生存的那个严酷的历史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统治思想给知青和农民所带来的共同历史压迫,乃至这种历史压迫中更深的现实和传统的政治因素。任何丑化和美化知青和农民的创作,都很难真实地刻划出历史的原貌和人性的本真。
反思近二十年来的知青题材小说,像阿城那样较为冷峻客观,保持中性的作家作品不多,可是,阿城的作品却很少介入农民内部,也就是说,阿城的小说基本不去描写知青与农民之间的感情纠葛,尤其是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情关系。因此,作者的那份热情就可很潇洒地隐匿于不悲不喜、不温不火的情节之中,缺少冲突正是阿城知青小说的特色。阿城的知青小说在人性思考和生存思考方面是突破了以往知青小说的模式,然而,它们在历史思考的层面似乎还欠深邃。
当我读完了王明皓的知青小说集《快刀》后,就非常惊异作者的另一种写法和他所获得的另一种视角。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大陆的杂志不吃王明皓这一类的知青小说,除了少数篇什在《雨花》上发表外,绝大部分却是先在台湾《联合文学》等杂志上发表,甚至出了集子后,才转而由大陆一些杂志所发表认可。除了小说本身写法上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外,除了许多篇什弥漫着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怪诞和鲍照诗中的鬼气外,我以为,作品所透露出的那种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的人性审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曾经是知识青年的作家,王明皓摈弃了自我角色的情感介入,试图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性视角来解剖那一段历史和一段历史中的人,尤其是“知青”这个上山下乡的主体。
我以为王明皓的知青小说写得太“酷”,所谓“酷”并非是悲剧美学中那种惨烈之美,而是一种鲁迅笔端之下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阴冷之中透出的那份洞悉无常人生的喟叹。亦如作者在《快刀》集序言中所说:“我的知青小说,在大陆被称之为‘后知青文学’,所谓后,是为了和以前相区分。前十年,写知青的作家很多,而今早已寥若晨星了,当年我没赶上‘潮头’,如今却获得了一个视野,一个冷静,一个特定的视角,倒也平心静气的了。”这一份冷静视角的获得,固然是因了许多“前知青小说”的铺陈,否则是很难来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和刘醒龙不同,作为一个曾经沧海的知青,王明皓不带任何激情(起码是不着任何情感痕迹)地去剥离那一段瘆人的历史,以及在这瘆人的历史中活动着的人,乃至他们的“死魂灵”。这些,固然不能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手笔,但“大音稀声”,“大智若愚”的道理,作者还是彻悟的。因此,在那近似于自然主义的中性客观的描写中,我们仍能谛听到遥远的历史深处所发出的悲悯的人性呼喊,以及对历史的叩问与凝思。
“寺背村”是王明皓小说的一个不可逃离的历史性境遇,像“我”这一群知青在这块土地上演绎出的一幕幕悲喜剧却是令人深思的。木纳中透着灵动,呆板中露出睿智,这在王明皓的小说知青人物中成为一个贯常。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对知青这个“自我的严肃解剖,“解剖自我”一旦成为王明皓知青小说的一个固定视角,它的历史意义就不同了,整个小说的意象构成既然推翻了原有知青小说的意义范畴,那么,作者笔下的人物当然就赋有了另一种鲜活的意义。由此,我们才读出了王明皓知青小说的全新意义。
《快刀》真是一把解剖知青灵魂的“快刀”!那种在逆境生存环境下用尽了心机的冷酷体现在一个愚钝的知青身上,而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兽类中的优生劣汰、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法则。同时,也使我们想到工于心机的人类格斗中,取胜的一方却往往是用最简单的思维和手段而获得的真谛,掩卷细想,又觉得脑后冷飕飕的生风。那声“快刀,好快刀!”的呐喊,如其说是在赞扬刀,倒不如说是这位绰号叫“快刀”的知青所发出的绝死的讯号。听不出其中奥妙的农民邻居们自然是欢天喜地,而意会到个中隐情的大队书记当然在这一幕严酷的斗争中取了退守之道。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说了刀的快,也描摹出了被刀者对于死的那么一种精神境界。头二百个字,读了叫人毛发悚然,却又淋淳尽致,很觉着有一番余味的。我的《快刀》绝没有类比先贤的意思,只不过描摹了一种往事。通篇小说如同一刀砍下去,却连一滴血也没流得出来,冤哉!”不管有无类比先贤,我反正读出了《药》的韵味,读到了《阿Q正传》的余绪, 这种对知青生活的勾勒和解剖,也体现出作者的气度。
《那年我们十八岁》最使我感动,作为一个好小说,作品能在不露声色中把十八岁的“我们”写得灵魂出窍、血肉淋漓,可谓不同凡响,确是上乘之作。小说也是写“我们”在饥饿中的失节,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偷吃了邻村农民赖以生存的鸡,致使一位大嫂喝了农药自尽。作者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是非的价值判断上,而是更加深入人性的内部,延展了小说更为广阔的描写疆域。农民大嫂死后,两位知青已然是迈不过这道德心灵的门槛的,于是他们自动跪去吊孝、投案,引来了一顿绝死的老拳痛击,其中,寥寥几笔,又描写了那位深明大义的驼子——死者的家属——穿透历史的义举。从驼子保护两位知青的义举来看,作家要表达的无非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的意蕴。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和农民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知青落入苦境,农民被瓜分口粮。而在这历史的阵痛中,作家不能沉缅于相互的怪罪而分清谁是谁非,而是要从中发掘出人性的内涵,以抨击那一切不合人性和人道的罪恶机制。
在《荒年》、《地灯》、《如梦令》、《大寺墩情话》、《夏天的轶闻》等篇什中,王明皓的知青小说充分描写了知青灵魂的锈蚀和堕落,当然,也描写了农民们的愚昧和自私,但其主要笔触还能停滞在他所亲历过的那场震撼人心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人的灵魂的剖析上。
作为小说的两种写法,我似乎更欣赏后者,我佩服王明皓的自我解剖气度,这种忏悔绝无丝毫矫揉造作;我也欣赏刘醒龙以新的反思来颠覆以往知青小说的思维模式,但我对《大树还小》中所流露出的逆向思维所产生的偏执不以为然。作为一个同样亲历了这场运动的刘醒龙,尽管那时他还是个少年(1968年),但审视这一历史事件的眼光却不能永远凝固在十二岁的少年的心灵上。也许,对于那种一味陷入苦难之美、英雄情操中的知青情结的反拨,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不失为一贴苦药,但是作为一个超越历史,超越阶级本位,超越自我的现实文本,作家不能不面对已然逝去的历史作出更高一畴的审美价值判断。作为交往很深的朋友,我想告诉刘醒龙的是,创作往往只有在超越了自我情感的时候,才能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