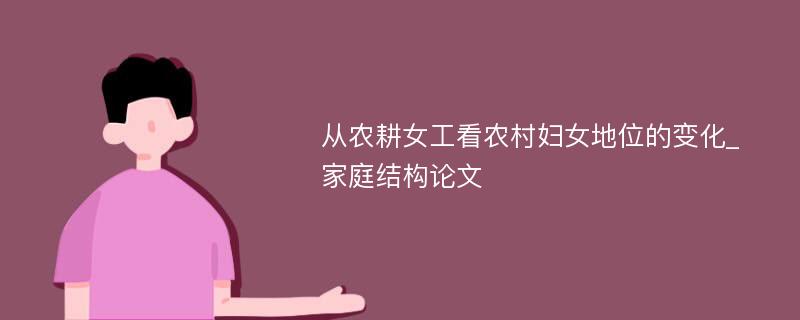
从男耕女工看农村女性地位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工论文,地位论文,农村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悄然兴起,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一般的观点是,外出打工者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城市中“农民工”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他们;在家中留守的多为女性,农村中出现一种“农业女性化”的趋势且日益显著。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女性外出打工者的比例一直持明显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的调查,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为21.8%,而90年代中后期达到34.8%。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则显示在跨省流动的4000多万人中,女性已占48.2%,基本和男性持平,而且将会持续下去并保持着平稳上升的势头。因此在考察当前农村女性地位及其变迁的时候,我们则不能忽视“打工”这一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能不思考“打工”对于农村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打工”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使得她们能够重回公共领域,提升在经济上的优势。女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女性地位的构成要素之一,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其他子地位获得的首要因素和物质基础。基于1990年我国首次大规模女性地位调查的各种相关学术成果,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地位的核心作用,而且引用大量数据验证了经济指标对于女性地位的正向效应,认为经济地位的获得是享有和行使各种权力的基础,多元回归分析证明,女性的经济收入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在广西的一些村镇中出现了一种较为明显的男性赋闲在家、种地赌博,女性外出打工赚钱的“男耕女工”现象,而且无论未婚、已婚都是如此,没有明显的差异。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村作为调查对象。
女性地位研究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女性外出工作成为和男性一样的“挣面包的人”时,也就意味着女性在经济上独立的到来,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然而这在有着以家庭为重的利他主义传统的中国,却并不符合现实。该村中女性外出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个体打工所得自然地转化为家庭收入,以供全家人开销。家庭的供养者虽悄然地转化为女性,但是资源分配的格局却是基本未变,首先是孩子念书和未来的发展,其次是老人的供养,再次是丈夫拿去赌钱,然后还有农业和家庭的其他花费,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女性自己的需要。
主体意识的变化和自主性的匮乏
女性地位的变迁,主体意识的增强无疑是最显著的表现。女性外出打工,成为家庭主要供养者,拥有资源的日益增多,都促使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警醒。这在年纪较长的女性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受害人”意识。
“在家里,做完事(农活)回来还要煮吃的,伺候家里的老老小小,还要管理菜地,还要喂猪和鸡。女人家啊,命不好,就是难哪!”
“他那么喜欢赌,我看见就心烦,还像个家吗?一桌人在打牌,屋里头乱七八糟的,我当时就想回广东做事,女人就是苦啊。”
“平时我不在家,他就要什么都做,我一回来,就什么都丢给我了,就管点田里的事。我回来就苦啊,什么都要做:煮饭、喂猪、种菜,什么都要我去做。比在厂里干活还要累。女的就是女的,苦命啊。”
较年轻的女性则更多地表现出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公平意识的萌芽和主体性的增强。
“不公平,可她们都不计较的。你看那些婶婶们,成天地劳累也不嫌烦的,我看到就受不了了。”
“当然不公平。这里本来就不公平的,我们村里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男尊女卑’。”
“当然不公平了。出去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在家庭内部,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表现为家务应该共同商量。
“不过他还是和我商量一下的,在一些事情上,不管怎么来说,还是从我这里拿的钱嘛。”
“钱是我们一起的啊。他要买什么都和我讲的,春季的时候买化肥也要讲一声的。”
“家里的钱都是我拿的,说话当然算数。什么事我们都要商量的。”
但是妇女们在村务也就是公共事务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不是说“晓不得”就是“我不懂”。而问及女性是否应该参加村务和祭祀等活动时,一致的反应是“不是女人家的事”。
“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哪轮到我们管。我们就管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村里的事女人家都不出头的,那些事我从来不管的。”
“没有。从来就没有参加过。我们这里女的是不参加村里的什么事的。”
“那些事我不晓得,不是女人家的事”。
显然该村中女性的主体意识仍处于模糊的状态之下,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就是矛盾、茫然和无所谓的态度。而且经济状况越是不好的家庭中,女性的责任感就表现得越明显,自主性就越差,男性就更容易掌控和坐享其成。首先的表现就是生孩子意愿的矛盾。
“这么多个孩子读书,我们也蛮辛苦的,那时侯要是没生那么多就好了,是婆婆和他的意思啊,他们说劳动力多一点好。”
“家里那么多小鬼也难养啊,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孩子多了。婆婆和他要啊,我也没办法。”
“计划生育抓得也严,可不都是这样,好几个小鬼,都是他们的意思。”
其次是对这种“男耕女工”表现出的不满与无可奈何。
“怎么没有想过他出去,我们还吵了架,他不愿意去,就是想在家里赌呗。我也不计较那么多了,他不去我去,总得让这个家过下去吧。”
“我们吵了几次,后来他不去我也懒得和他争了,我自己去。要不家里真的就没有钱了。”
“都是这样的,吵也没用,我不出去这个家怎么过啊?”
再次就是公共事务中女性声音的缺失和女性对这种排斥表现出的认同和内化。由于主体意识的薄弱和自主性的匮乏,对于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女性就缺乏必要的兴趣和认知。在涉及到相关问题时,被调查者的答案都是“不去的,没女人家什么事”,或者说“去问他”,而且没有年龄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在这种以男性为主的社区结构和社区文化中,女性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渺小与无所谓。通过“局外人”的身份把自己固定在被支配状况上,通过承认社区文化去接受同化似乎成了她们惟一合理的选择。
“男性支配”下的个体经历
“外出打工”对个体经历的丰富、女性地位的变迁起着一定积极的作用。它为农村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使得她们可以接触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她们摆脱社区传统文化的束缚,接受现代文明,主体意识的萌发,自主性的增强,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些原子化的个体日常生活经历甚至是经济上优势的获得,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女性弱势地位的根本性改变。许多学者也从多方面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论证经济因素不能解释一切,对性别歧视的思考应该既注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靠关系,又能充分认识其中任何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的全部意义。认为是更宏观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和男性统治造成了女性相对的弱势地位。
在该村,打工虽使女性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但并没有动摇主导产业——农业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男性仍是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家庭经营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女性仅仅是帮手和补充。在家庭中,主体意识的增强虽然使女性具备一定的自主性,但显然并未拥有和男性同样的话语权,家庭资源的控制权和家庭事务的决定权,女性拥有的只是在男性同意下的使用权而已。而且经济上的优势和外出的经历既没有增加女性对政治的关注,也没有提高对自己应有权利的意识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村里的事依然是男的商量着办,哪怕男的都是靠女的养活着。文化方面,所接触的各种新思想和生活方式也没有影响到女性在村中的日常生活,没有改变对自己角色和功能的定位,结构性的、传统的、文化的因素作为习惯仍然深植于女性的思想之中。
在“男性的支配”一文中,布迪厄指出,性别支配构成了所有支配的范例,而且可能还是最为顽固的一种形式。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是中性的东西被继承下来,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该村中的“男耕女工”显然是“男权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合力的产物。它不证自明并从头脑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两性关系微妙的互动,社区中两性各自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女性的弱势地位与被支配的状况就是这样通过女性自身的误识与同化被维护着,仅靠经济因素一方面的变化是不能必然带来女性地位全面和本质性的变化的。
在该村,这种“男性的支配”首先是男性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为基础。男性自一出生就享有绝对的资源优先权,尤其是教育。无论家庭情况如何男孩一般都会念到初中,对于女孩来说这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男孩没有必要出去打工,他有权利享有家中的一切资源,包括姐妹们寄回来的“血汗钱”并视之为天经地义。正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匮乏,使得女性丧失了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女性先天就弱于男性的因果颠倒的逻辑,使女性陷入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家庭和村庄结构通过自身的运行,把这种支配关系纳入到一种生物学的自然解释中,将其合法化,并成功地转化成为一种自然化的新结构,使这种天赋性的弱势地位得到了再生产。面对这样强大而合法的结构逻辑和文化传统,女性自然就会作为被支配者按照支配者——男性的视角来定义自己的角色与功能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这无疑会导致女性系统的自我贬低甚至是自我诋毁。由此可见,在“男权制”结构下,女性的弱势是天赋性的和必然的。经济因素的改变虽然能够带来一些改变,但无法撼动整个结构的根基,不能改变这种先天性的不平等,自然也不会带来女性地位的根本变化。
其次,打工领域与生活社区的隔离,闭塞的环境、落后的经济也是造成这种“男耕女工”的主因。许多学者认为重返公共领域是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前提是“公共领域”与女性生活的“私人领域”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而在该村,女性打工所处的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打工只是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在更高产业结构中劳动和在城市文明中生活的机会,所能够带来的变化也只是个人的变化,并没有可能改变女性日常的生存环境。该村地理环境封闭,经济条件落后,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的经营方式,必然造成村庄结构的僵化,传统文化的强大,这从家家虔诚的祖先崇拜中就可以看到。而这又都与男性为核心的“男权制”互相嵌入影响,自然将女性置于金字塔的最低层,使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弱势的状态。这种“男性的支配”允许男性合法地享有女性所提供的一切劳动与服务,在各方面给予男性占有绝对的优先权和控制力。年轻一辈中,家务看似是二人商量有平等的意向,实际在本质上仍脱不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工作,女性就能解放的观点,在这里未免显得有些幼稚,对女性而言,工作有时意味着更沉重的双重枷锁。在村庄结构和传统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个体的改变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女性地位的变迁、主体意识的恢复和自主性的加强等,都与宏观的结构紧紧相扣,单从个体角度谈女性地位提高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综上所述,女性地位的变迁是个体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微妙地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依赖的基础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日趋平等、女性控制各种资源的能力和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和自主性的加强。经济因素的变动只是提高女性地位的一个必要前提,并不是充分条件;外出打工也只是为女性改变命运提供了一个机遇,并不能够必然导致整个女性地位的改变。从根本上讲我们所需要改变的,还在于“男权制”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男权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