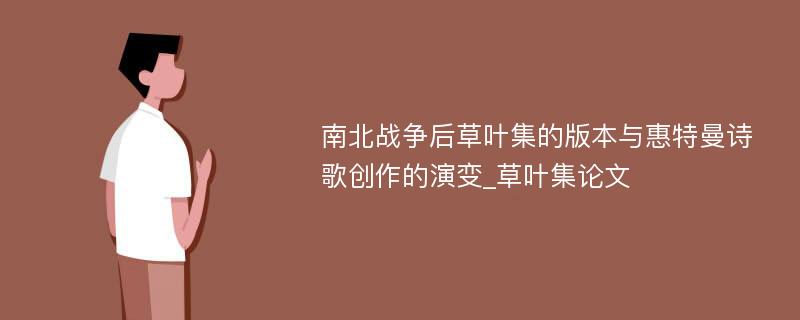
内战后《草叶集》的版本与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草叶论文,战后论文,版本论文,惠特曼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惠特曼一生只创作了《草叶集》这一部诗集,在36年的创作生涯中持续增删修改其中的诗作,总共出版了六个版本,构成其别具一格的创作特征之一。《草叶集》犹如一个勃然萌动的生命实体循序渐进地衍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和风格。国外已有学者关注“《草叶集》的成长”,并侧重从量变与技巧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注: G.W.Allen. The New
Walt Whitman Handbook.New York:New YorkUniversity Press.1986,pp67—159.)在惠特曼看来,《草叶集》既是领略与衡量他的创作成就的凭证,也是他藉以再现自我和整个世界的一个弹性载体:
我自己创作使我能够为人欣赏的唯一不断成长的作品,
我无所拒斥, 接受一切, 而后以我自己的形式再现一切。(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 and Sculley Bradley,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Inc.,1968.pp340.)
创作民族诗歌的宏愿,要求惠特曼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维系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可能像约翰·班扬或者埃米莉·狄更生那样在与世隔绝的情形下从事创作。自《草叶集》问世以后,社会反应便介入惠特曼的创作,对其思想意识、创作理论、心理状态、创作计划、主题与风格等方面产生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干预,而诗集版本的陆续更迭既可以印证社会干预对诗人所产生的影响,反之又导致社会产生新的干预。《草叶集》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出版了三个版本,另外三个则于战后问世。至于前三个版本与惠特曼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笔者已另文论述。(注:参见刘树森:《〈草叶集〉的前三个版本与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7)。)本文拟从内战后的三个版本入手,通过从多重视角分析不同文本的主题内容,结构,语言风格,以及版本外在形式的文化内涵等等,探讨诗人创作的发展变化。
1
如果说,报刊舆论的压力,爱默生和出版商的劝阻和干涉,以及一般读者对于《草叶集》的漠视,构成内战前干预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外在因素,那么内战爆发后整个民族的存亡危机对他的创作则产生了重要的内在影响。内战使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除了1861年发表了鼓动人民参战的《敲吧!敲吧!鼓啊!》一诗之外,他的诗歌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其它体裁的文章也寥寥无几。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种体裁的文字,从1855年至1860年的六年间多达665篇,但1861至1865 年的五年间仅有57篇。(注:有关这一组统计数字,可参见Joel Myerson.ed.,Walt Whitman: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Pittsburgh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3,pp661—775.)1862年底,由于要探望参战负伤的弟弟乔治,他自纽约赴华盛顿。战争的惨烈景象与他在战前憧憬并讴歌的民主前景形成强烈的反差,灵魂深感震撼。战前,惠特曼赋予美国民族诗人以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他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维持平衡的人,
他供给所有需要供给的——他抑制所有需要抑制的,
在和平时期,他讲述和平的精神,博大,富有,节俭, 建设人口众多的城市,鼓励发展农业,艺术,商业,启发人研究自己,灵魂,健康,不朽,政府,
在战时, 他是战争的最佳支持者——他带来的大炮如同工程师制造的一样,他能够使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人热血沸腾。(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Blodgett,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pp198—199,liv.)
诗中对于诗人使命的界定,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和平时期的幻想。一旦战争来临,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惠特曼只写出了一首“使人热血沸腾”的诗,而乏力创作其威力“如同工程师制造的一样”的作品。但他并没有消沉无为,而是作为“战争的最佳支持者”在战地医院充当志愿救护人员达三年之久。据他自己回忆,曾经“照料了8万至10 万名受伤、患病与垂死的军人”,(注:转引自 Besty Erkkila.Whitman the Political Poet.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sity
Press,1989,p200.)后因健康受损,体力不支,才返回家乡修养。 在战前已经闻名的美国诗人中,惟有他直接为战事服务,身体力行自己的理论。
按照惠特曼战前的构想,《草叶集》第三版出版以后,他作为民族诗人的使命随即完成。因此,他以《再见!》一诗作为诗集的结语,憧憬在不远的将来:“他的国家深情地吸收他,就像他深情地吸收了自己的国家一样。”(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 Blodgett and 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68.pp 729.)1863年,他仍在战地医院服务,便致函爱默生,称计划写“一本小册子,有关目前这一阶段的美国,她具有阳刚之气的青壮年时期,及其在最难于忍受、最严重的危机状态下的行为”,展示“一个充满分离行动、游戏和暗示意义的世界”。 (注:Edwin H. Mill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 Whitma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1—1967,vol.1,p69.)这便是1865 年出版的《桴鼓集》以及次年出版的《续篇》,分别收入53首和18首诗,绝大多数以战争经历与感受为题材。社会对此反应良好,至少没有像战前的《草叶集》那样招惹訾议,反映了社会舆论对诗人创作的外在负面影响逐渐消减。这些诗如《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和《啊,船长!我的船长!》,在形式上愈来愈多地采用传统的段落形式和格律,其内容没有直接勾画战斗场面,而是将笔墨集中用于描写战后尸首遍野的惨景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生死离别的感受。诗中描摹的每一幅景象,每一种情感,都是诗人亲身感受的记录,有别于《草叶集》中着力铺陈乌托邦式前景想象的诗篇。这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放弃建设“《新圣经》的伟大工程”, (注: Edward F.Grier.Walt Whitman:Notebooks and Unpublished Prose Manuscripts,6 vol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vol.1,p353.)不再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而专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现实题材。
致你,古老的事业!
………………
这些叙事的诗篇是献给你的,——我的书和战争是一个整体,
我和我的书都浸透着这种精神,如同竞争是以你为中心,
就像车轮围绕轴心而转动,这本书虽然不知不觉,
却是围绕你的理念而创作。(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 and 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68.pp4—5.)
然而内战后《草叶集》的第一个版本,即总第四版1867年问世,标志着惠特曼又试图回归战前的创作主旨。该版由纽约的印刷商W·E·查频承印,在同一标题下按三种模式分别装订:其一为《草叶集》,共计338页;其二又收入作为“附录”的组诗“桴鼓集”及其“续篇”, 共计434页;其三又添加作为“附录”的组诗“离别之歌”,共计470页。在《草叶集》六个版本中,此版最为杂乱,反映了诗人创作转折时期的矛盾心态。通常所说的第四版指上述第三种模式,由三个部分构成:其一是原《桴鼓集》及其《续篇》中的诗作;其二是《我的歌的主题很小》(《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等6首新诗;(注: 自《草叶集》的第二版开始,惠特曼不断在新的版本中变换诗歌原有的标题,以期在诗集的整体结构中更好地表现各种主题与创作意图。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至1891年的“临终版”为止。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中凡与“临终版”的标题相异的诗歌,均在其后附注“临终版”中相对应的标题。)其三是第三版中原有166首诗中的160首,剔除了《忆旧的诗》等6首。 与前三版不同,此版没有使用惠特曼的任何肖像。
就艺术风格而言,惠特曼力图更加贴近传统模式。在1855年的第一版中,他主要尝试以一种全新的诗歌话语塑造主人公“我”的个性化形象,而从第二版开始,便愈来愈多地考虑如何适度消释诗歌形式方面过于反传统的因素,使“我”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所认同。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民族文学迅速萌生的时期。除霍桑的《红字》(1850)与梅尔维尔的《白鲸》(1851)之外,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也采用欧洲小说的传统形式,出版后均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朗费罗1855年出版的史诗《哈依瓦撒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全然是欧洲文学传统的临摹版本,也拥有惠特曼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庞大的读者群。这些成功的范例都对惠特曼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这一时期,他在经历了挫折之后研究了朗费罗的诗歌的整体艺术效果,在一则笔记中写道:
朗费罗创作的《哈依瓦撒之歌》——一首娓娓动听的诗歌——有韵律,缺少观点,印地安人的思维程序,单调乏味的格律,感觉迟钝、愚昧无知、 木头似的人物, 形形色色的传统,但使我大为开心。(注:Edward F.Grier.Walt Whitman:Notebooks and Unpublished Prose Manuscripts,6 vol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vol.5,p1730.)
因此,惠特曼适度调整其艺术风格,对新版中的一百余首诗作了不同程度的增删修改,有些诗的改动之大是先前所没有的,例如,《神话是伟大的》一诗由71行删至49行。修改涉及词汇,意象,标点符号,格律,标题,诗行的节奏与长度,诗节的构造等诸多方面,尽力剔除抽象的内容与艰涩的表达方式,使诗歌话语更为清新直白,开始具有易于读者接受的表现力。以此版的第一首诗为例,从头至尾每一段落内都留下了推敲的痕迹。下面的引文是该诗第一节在第三版与第四版中的不同文本。
(一)自由,生机勃勃,粗野,
优美,丰满,自满自足,喜爱形形色色的人和地方,
喜爱鱼形的鲍玛诺克,那儿是我出生的地方,
喜爱海洋——水产丰盛,品种繁多,
来自曼纳哈塔的男孩,那座由船只构成的城市,我的城市,
或者在内地被抚养成人,或者来自于南方的草原,
或者始终在加利福尼亚的空气, 或者得克萨斯州或者古巴的空气中生存,
记录并歌唱一切——颂扬尼亚加拉——颂扬密苏里,
或者在克纳克森林我的家中过着原始的生活,
或者漫游与狩猎,喝的是水,吃的是肉,
或者躲避到密林深处冥思苦索,
远离大众的喧嚣,度过一段欣喜若狂的时光,
星辰,雾霭,风雪,山脉,岩石,五月的鲜花,我的惊奇,我的爱人,
觉察到水牛,安静的牛群,那头胸部肥壮、毛茸茸的公牛,
觉察到拂晓时荒野中的模仿鸟,
我独自一人,在西方歌唱,为新世界引吭高歌。(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1860 Tex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p5—6。)
(二)从鱼形的鲍玛诺克开始,那儿是我出生的地方,
生就的健壮,由一位完美的母亲所抚养;
游历过许多地方——喜欢行人拥挤的道路;
曾居住在曼纳哈塔,由船只构成的城市, 我的城市——或者南方的草原;
或者曾是宿营的士兵, 或者携带着背包和枪支——或者曾是加利福尼亚的矿工;
或者在达科他森林我的家中过着原始的生活,吃的是肉, 喝的取自泉水;
或者躲避到密林深处冥思苦索,
远离大众的喧嚣,度过很多欣喜若狂的时光;
觉察到生机勃勃而自由的施与者, 连绵流淌的密苏里河——觉察到巨大的尼亚加拉瀑布;
觉察到成群的水牛,在草原上吃草——那头绒毛浓密、 胸部肥壮的公牛;
还有许多地球,岩石,五月的鲜花,经历过——星辰,暴雨,风雪,我的惊奇;
已经研究过模仿鸟的音调和山鹰的音调,
黄昏时听到过一只鸣叫无比动听的鸟,来自沼泽杉林中的隐居鸫,
我独自一人,在西方歌唱,为新世界引吭高歌。(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New York:Wm.E.Chapin & Co,Printer,1867,pp7,V,118.)
作为“纲领诗篇”之一,此诗浓缩了惠特曼的诗歌理论,初次发表于第三版时原题为《原始的草叶》,此次易名为《从鲍玛诺克开始》,突出了主人公“我”成长的背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上文为一个冗长但并不复杂的句子,主语和谓语动词直到最后一行才出现,此前的部分由形容词、分词、介词短语和名词构成,详细叙写“我”漫长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与社会文化基础。第三版文本中的前两行诗,描述“我”的内在个性与外在体格特征,但位于句首,且以形容词为主,难免使人感到突兀费解,在第四版中被删除。第四行“喜爱海洋……”也被剔除,第三行则改为“从鱼形的鲍玛诺克开始……”从而直截了当地描摹“我”的经历。“记录并歌唱一切……”一句,也因上述原因被删除。新增加的“或者曾是宿营的士兵……”一句,显示了内战对于“我”的影响。其它诗行几乎都有所改动,使文字更为具体和形象,更为接近符合传统诗歌的范式。例如,将“尼亚加拉”润色为“巨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将“密苏里”具体化为“连绵流淌的密苏里河”;“星辰,雾霭……”一行完全由名词构成,寓意零落,也被删掉。对于内涵较为抽象或者使用不当的意象,要么剪除,如“或者始终在加利福尼亚的空气……”一行,要么重构意象,例如以“荒野中的模仿鸟”反衬鸣叫响彻天穹的“山鹰”,并与“山鹰”和“鸣叫无比动听的”“隐居鸫”一道衬托“我”出世之前的个性特征以及出世后的命运。此外,该版还沿袭传统诗歌,间或以分号代替逗号,使内容在叠加的描述过程中呈露出错落有致的层次。至于诗句的语法结构,艾伦注意到后者更多地使用过去分词,表明“诗人试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现在已经将他1860年表述的诗歌理论付诸实践了”(注:G.W.Allen.The New Walt Whitman Handbook.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0.)。
诗集的主题结构也清晰地表明惠特曼试图回归到战前弘扬民主理想与个性的创作主旨。在新收入的6首诗中, 唯一重要的作品是位于卷首的《题词》(《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在此诗中,惠特曼第一次从《草叶集》貌似庞杂的诗歌内容中梳理出核心主题。
下面这支歌的主题,然而也是最伟大的——即,——那个奇妙的事物,一个普通而单独的人。为了,我歌唱那个事物。
人从头到脚的全部生理结构,我都歌唱。不只是相貌, 也不只是大脑,才值得歌唱;我说整个更有价值。女性与男性, 我同样歌唱。
也并非终止于这一主题。我还说出这个词,这个词。
我歌唱我的和 ——在间歇期间我了解了不幸的。
啊,朋友,不论你是谁,终于来到这里上路, 我可以透过每一张书页感受到你的手的压力,我也以同样的压力回敬。因此,让我们手挽手踏上共同的征程。(注: 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New York:Wm.E.Chapin & Co,Printer,1867,pp7,V,118.)
诗作均围绕上述主题而重新安排,不再沿用第三版的组合方式。《从鲍玛诺克开始》和《沃尔特·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从不同侧面全面表现“我”的个性特征。《亚当的子孙》和《菖蒲集》两部组诗侧重赞美人的“形体”与生理机能;介于两者之间的《奋发向上》一诗,一方面提示创作主题的开拓,由描写异性间的爱情发展到赞美男性之间的情感,此外也宣泄了贯穿诗人整个创作生涯的不断探索、“奋发向上”的精神。
谁走得最远?因为我发誓要走得更远;
……………………………
谁具有最渊博的思想?因为我要包揽那些思想;
谁创作出了适合于地球的赞歌? 因为我如痴如醉地为整个人类创作欢乐的赞歌!(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New York:Wm.E.Chapin & Co,Printer,1867,pp7,V,118.)
其它诗篇均安排在题为《草叶集》的四部组诗之中,只有《向世界致敬》和《什么地方被包围了?》两首除外。这四部组诗的主题似乎较为凌乱,不如前两部组诗那样单一整齐,但基本上是以烘托“我”与“全体”之间的关系为主,而并非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这种组合在于“惠特曼显然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诗歌”。(注: G.W.Allen.The New Walt Whitman Handbook.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3.)作为“附录”,《桴鼓集》及其《续编》和《离别前的歌》等三部组诗,被置于诗集的尾部。《离别前的歌》仅包括14首诗,但除开篇的《当我独自坐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的时候》(《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之外,其余的13首又分为三部组诗。在这些诗中,核心之作为《当我独自坐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的时候》。作为“纲领诗篇”之一,此诗在前三版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此次却被置于诗集的“正文”之外,仿佛是创作完成后追忆往事。余下的诗篇多为辅弼之作,鲜有新意。
早在内战之前,惠特曼已经认识到,他的诗歌尽管在形式上不断向传统的规范靠近,但毕竟以独特的话语宣扬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形态,难以见容于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只能是属于未来的作品。内战后,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诗集此版的上述特征来看,他极力保持讴歌前景想象与塑造“我”这一理想人物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有历史使命感和超前思想的民族诗人,他并非无视内战后日益严重的社会弊病,只是没有在诗歌中直接表现而已,以维持其诗歌艺术的特色。对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他在内战后则犹如内战前一样,在其散文体的著作中发表见解深邃、文笔犀利的评论。应当说,他的散文作品也是一份重要遗产。
2
1868年,英国诗人威廉·罗塞蒂编辑的《惠特曼诗选》在英国出版,为惠特曼赢得了国际声誉,有助于这位尚未得到本国读者认同的美国诗人摆脱备受误读与指摘的窘境。这本诗选以《草叶集》的第四版为蓝本,删除了其中一半的作品,主要是描写性主题的作品。惠特曼原本难以容忍罗塞蒂的“阉割”,后来出于较为实际的考虑才予以认可,但坚持要求诗选采用《草叶集》初版中自己那幅工人模样、放荡不羁的肖像。他认为,它以非文字的方式彰明一种性格,犹如《我自己的歌》以文字和意象对“我”的塑造一样,是“作为整个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置的”。(注:转引自Walt Whitman Quarterly Review,vol.4,no.2—3,1986—1987,vol.4,nos.2—3,pp44.)显然, 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第四版缺少肖像所构成的缺憾。自内战结束后直至他1892年去世,面对追求艺术的终极价值与现实社会所认同这两种选择,惠特曼时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第四版出版以后,惠特曼主要致力于修改已有的诗歌,调整诗集的内部结构,而以创作新诗为辅。1870年,他出版了《草叶集》的一部“分集”,题为《向印度行进》,但将出版时间注为1871。其中共收入73首诗,49首为旧作,包括《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与《来自永远摇动的摇篮》等重要诗歌;24首为新作,除了《向印度行进》等4首之外,其余的作品均无显著特色与价值。正如首页的题诗所言, 该诗集的核心主题是关于死亡的思考,即诗人在内战后对于人与自然平衡发展的哲理性思考。
掠过一切,穿过一切,
穿过,和,
犹如一艘航船在水面上前行,
的——并非只有,
还有——众多的 ,我来歌唱。(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Blodgett, 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3,ppi,571.)
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之下,惠特曼在战前便以对称的方式表现主题,诸如个人与群体,灵魂与肉体,以及生命与死亡。战争的浩劫,使他愈来愈关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永恒演进的方式,关注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精神驱动力和人的终极归宿。战前,他侧重抽象地认识生与死,强调二者是永恒的辩证存在,并构成一切事物存在与沿革的基本原理;战后则倾向于具体地思索生与死在人与社会的本质层面的意义,并将视野转到东方。认为以印度为象征的理想而古老的泛东方文化,即主要指古印度与中国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强调以心灵为本,崇尚直觉,追求相对的完美,更接近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想,应当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则,人与社会的发展注定会失衡,人类必将面对悲剧的命运。因此,对于一味青睐物质发展及其享受的美国社会而言,转而“向印度行进”势在必行。
对于人类,这是心灵返航的征程,
回归到理性早期的天国,
回归,回归到智慧的起源,回归到单纯的直觉,
重新与美好的在一起。(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 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 Blodgett,Arthur Golden,
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3.ppi,663—664.)
《草叶集》第五版1871年出版,因是匆忙编撰而成,版本的情况也较为复杂。主要原因之一是惠特曼出现了中风瘫痪的先兆,自觉身体每况愈下,担心能够从事创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第四版中的组诗《离别前的歌》,现在更名为《离别之歌》,一字之差便使作品宛若绝唱。该版由纽约的印刷商J·S·莱德菲尔德承印,在华盛顿发行,初次印刷时收入诗歌180首,其中10首为新作,共计383页;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将所谓“分集”《向印度行进》作为“附录”收入;1872年,第三次印刷时,又将1871年以单行册出版的《毕竟不只是为了创造》(《展览会之歌》)一诗作为“附录”收入。一般而言,第五版是指上述第三次印刷的文本。
这一版也以调整诗歌的内在结构为主要特征。第四版中的《题词》一诗,经过大幅度删改后改称《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自此以后一直用作整个诗集的起首之作,画龙点睛。
我歌唱,一个普通而单独的人,
而又说出这个词,这个词。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结构,
不只是相貌也不只是大脑才值得歌唱,我说整个更有价值,
和我同样歌唱。
具有巨大的激情、冲动和力量的,
心情愉快,支持按照神圣的法律所采取的最自由的行动,
我来歌唱。(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Blodgett,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2.pp558.)
该诗的内容与形式进一步表明惠特曼在经历了内战前后的矛盾与彷徨之后,又回归到事业起初的创作主旨。然而这并非简单的复归,而是社会生活与创作实践使他对自己的使命具有了比先前更为深刻的认识。该版中的诗歌,包括“附录”部分,大致按上述诗中的主题序列重新组合,形成了诗集问世以来最为明达的主题结构。至此,《草叶集》的内在结构基本上确定下来。居诗集之首的组诗《铭言集》除《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之外,另外还有8首短诗, 从不同侧面陈说诗人的创作主题与特征。随后的《从鲍玛诺克开始》和《沃尔特·惠特曼》等7首诗,则形象而具体地塑造主人公“我”的个性。《亚当的子孙》和《桴鼓集》两部组诗仍旧集中表现人的肉体与性的主题。其余的部分包括13部组诗,《向世界致敬》和《跨过布鲁克林渡口》等各自为单位的26首诗歌,以及两组“附录”,分别表现相对集中的主题。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原本作为“附录”的组诗《桴鼓集》及其“续编”中的71首诗经过删改后,有48首首次纳入诗集的正文,分别组成《桴鼓集》等三部组诗。有关内战的诗歌是惠特曼真实经历的写照,而此次收入诗集的正文,表明他试图将“我”这一理想化的主人公塑造得更为真实完满。内战前,他强调“我”的个性化与理想化;在经历了民族危机之后,则意识到,若要将“我”塑造成为一个史诗般的人物,还必须使其凝聚鲜明的社会现实感。将《桴鼓集》收入《草叶集》的正文,透射出这种创作意图。
编织进去!将我坚毅的生命编织进去!
编织吧,编织一个强壮而经历丰富的战士,迎接未来伟大的战役;
将鲜红的血液编织进去!将肌肉编织进去,犹如绳索拧在一起! 五官,见解也编织进去!
编织得坚实耐久!昼夜编织,经纬交织! 不停地编织! 毫不疲倦!(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 Blodgett,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2,pp524.)
此外,这一版在形式结构方面也较为冗杂,使诗集整体的主题结构在直观上晦涩费解。例如,包括“附录”部分在内的21部组诗中, 有8部取名为《草叶集》,混淆了主题内容的层次。其中一部名为《草叶集》的组诗只收入《致你》一首诗歌,即使希望以此突出诗中内容的重要性,但冠其以“组诗”之名,毕竟有名无实。
1873年2月,惠特曼因中风不治而偏瘫;同年5月,与他在感情上至近的母亲也因病去世。这些变故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后直至1892年谢世,他创作并收入《草叶集》的150余首诗歌, 均为短篇之作,内容多为忆旧,玄想,借景抒情,抑或阐释其思想与诗歌主题,再也无力创作出可以与内战前的诗歌媲美的作品。在1874年发表的《哥伦布的祈祷》一诗中,他对于志向高远、命运不济、暮年落魄的哥伦布的描述,仿佛是一幅维妙维肖的自画像,使其晚年的身心状况跃然纸上。
我的大限临近了,
乌云已经将我笼罩起来,
航行蒙受挫折——航线受到质疑,失败了,
我把我的船队交给。
我的双手,我的四肢变得麻木无力;
我的大脑受到煎熬,神志不清;
让这些朽木分离吧——但我不愿离去!
我要紧紧地拥抱你,啊,上帝,尽管海浪轮番冲击我;
啊, , 至少我是理解的。(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Blodgett,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3,ppi,665.)
1876年为美国建国100周年, 惠特曼为此自己在坎姆登出版了《草叶集》的所谓“作者的版本”。以往有些研究者倾向于将该版视为诗集的第六版, 但现在公认它只是第五版的一个“变体” (注: Walt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Harold W.Blodgett,Arthur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pp198—199,liv.)。这一“变体”数次印刷,内容各异,难以确切描述。一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卷。第一卷是以第五版为蓝本的诗集,用烫金字样在书脊标明“百年纪念版”,新增添的内容包括两幅肖像和四首新诗。他重新使用其肖像表现自己的创作内容与特征。一幅肖像曾用于初版与第二版,作为诗人的形象置于诗集之首,而现在则作为诗中主人公“我”的形象置于第29页,位于《沃尔特·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之前。另一幅为惠特曼1871年拍摄的侧身头像照片,此时52岁的诗人仿佛已经72岁开外,额头皱纹深陷,蓬松的须发皆白,连成一片,将消瘦的脸庞掩映在其中;他目光斜视,表情凝重,似乎在沉思,抑或疑问,但整洁的呢子大衣和白色的衬衣说明生活状况尚且稳定。这幅肖像显示出他内战后的身心境遇。他曾以它为题材,写了一首题为《出自这张面具的背后》的短诗,描述自己外在形象的文化心理内涵。
出自这张扭曲、皱纹深陷的面具背后,
这些或明或暗的地方,整体上的这种戏剧性效果,
脸庞的这幅普通帷幕包含的我代表我,包含的你代表你, 包含的每个人代表每个人的,
………………………………………………………
这幅人心的地理的绘图,这窄小而又浩瀚无垠的大陆, 这无声无息的海洋。(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Edited by Sculley Bradley, Harold
W.Blodgett,Arthur Golden,and William Whit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vol.3,ppi,665.)
上述肖像置于第235页, 位于组诗《桴鼓集》中的《包扎者》(《裹伤者》)一诗之前,旨在显示内战在“这幅人心的地理的绘图”上留下的烙印。此外,《当成熟的诗人到来的时候》等四首新收入的诗,分别单页印刷,并用浆糊分别贴在第207、247,359及369页的空白处。上述处理方式,加之其中的三首被从后来的版本中删除,一首收入“附录”,足以表明诗人勉为其难的创作状况。作为配伍的姊妹卷,第二卷为诗与散文合集,题为《双溪集》,收入《哥伦布的祈祷》等14首新诗,以及《民主展望》等9组散文。
3
1881年,《草叶集》的第六版由詹姆斯·R ·奥斯古德出版公司在波士顿出版。此版以第五版为底本,共计384页, 删除了《想一想灵魂》等16首诗,并对其余的大部分诗歌予以修改,但没有再像第三、四版那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新增加的部分包括《双鹰的嬉戏》等17首篇幅短小的诗歌。这些新作的题材多与日常生活内容有关,字里行间虽然再也寻觅不到以往那种开卷便荡涤人的心灵的激情与思想,却犹如在轮椅中生存的诗人一样,以有限的观察空间和心静如水的思考见长,只言片语中还不时折射出理性与艺术的光辉。
在沉思中漫游整个宇宙,我看到渺小的从容奔赴不朽的境地,
我也看到那统称为的庞然大物匆忙地吞没自身,消失并死亡。
上文即《在沉思中漫游》一诗,是惠特曼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后有感而作,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上述17首作品的风格。此外,他还利用其它方式弥补活动受限、创造力萎谢造成的欠缺,如《双鹰的嬉戏》是依据朋友转述的见闻创作而成。(注:G.W.Allen.The New Walt Whitman Handbook.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8.)大体而言,与从前的作品相比,这些诗歌没有鲜明的特色与重要的价值。
此版也不以增添新作为主,仍旧通过借鉴传统的诗歌形式修改已有的诗歌,重新调整内容和主题结构,并最终确定了诗集正文的文本。此后,在他的有生之年,《草叶集》虽数次印刷,但始终使用该版本的印版,增添的部分均作为“附录”缀辑在正文之后。这一版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变化。其一,惠特曼将作为第五版“附录”的三部组诗以及1871年单册出版的《向印度行进》中的诗歌,除删除几首之外,均收入诗集的正文,使其中的诗歌从初版时的12首增至284首。 诗歌数量的递增使诗集的内容结构变得更为丰满,主人公“我”也呈现出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自然发展过程。“我”以“歌唱一个人的自我”拉开了诗集的序幕,在吟唱了成功与坎坷,喜悦与悲伤,青年与暮年之后,最终以“我仿佛是一个脱离了躯壳的人,成功了,死了”作为诗集的尾声。(注:Walt Whitman. 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 and 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68.pp 506.)其二,组诗的数量由第五版的21部减少到12部,与一年中月份的数量相吻合。12部组诗在数量上象征一年的周期,以四季的更迭比照《草叶集》的生长周期,而作为核心意象的“草叶”的一枯一荣,衬托出“我”的发展过程。这种结构也赋予《草叶集》编年记事体的特征,成为记述主人公“我”的自传体史诗。其三,诗人再一次为部分诗歌与组诗更名,以便更为清楚醒目地宣示其内容。例如,贯穿诗集各版的压卷之作,即初版中的第一首诗,定名为《我自己的歌》。追溯此诗标题的变化,从初版时的无标题到第二版的《一个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再到以后的《沃尔特·惠特曼》,最终改称《我自己的歌》,也可以从中品味诗人创作艺术的流变。另外,这一版不再以“草叶集”用作组诗的标题。有关内战的诗篇大多收入《桴鼓集》与《林肯总统纪念集》。
位于卷首的“铭言集”等三部组诗主题未变,但增加了诗歌的数量。其后,《向世界致敬》与《跨过布鲁克林渡口》等8 首“歌”汇集在一起,组成一个雄厚而多元的主题板块,着重刻画主人公“我”的社会本质。组诗《候鸟集》也倾向于探讨人类的某些共性,以迁徙的“候鸟”象征人类必然要永远发展和演变。其后的组诗《海流集》与《路边集》中大多为短诗。前者主要赞颂母亲一般的大海是诗人创作的摇篮,并侧重描述了“我”经历的一段精神危机。后者突出“我”广泛的生活阅历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
惠特曼还借鉴了交响乐的结构特征,在组诗之间插入“纲领诗篇”,使核心主题在诗集中反复呈现,通过回旋达到提示与强化的目的。“铭言集”之后的《从鲍玛诺克开始》,“林肯总统纪念集”之后的《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以及“神圣的死亡的低语”之后的《你啊,拥有平等儿女的母亲》,均为此类“纲领诗篇”。《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以内战为主题,其后的《秋溪集》均为短诗,表现多重辅助性的主题,但诗歌的序次采取了回顾往事的视角,由步入人生暮秋的“我”诉说其身心的经历。其余的组诗以及《暴风雨雄壮的音乐》等单独排列的八首诗,主要表现有关人类精神价值的主题,其中的组诗“离别之歌”又与“铭言集”中的《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遥相呼应,完整地记录了“我”的生命轨迹。
J·卡泰尔和M·考雷等学者认为,《草叶集》第一版出版后,惠特曼的创作风格便发生变异;迨至第三版面世后,其创作激情与能力已经穷竭,此后的诗歌虽然数量不菲,但多为平庸之作,无法与其早期诗歌相提并论。(注:对于文中涉及到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Jean Catel:Walt Whitman:La Naissance du Poete.Paris:Editions Rieder,1929.) 应当说,他们漠视惠特曼内战后的成就,实质上是轻视或者忽略惠特曼作为民族诗人的使命及其创作宗旨。这与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不承认惠特曼拥有自己系统化的诗歌理论不无关系。在创作之初,惠特曼便阐明他之所以致力于诗歌创作,并非为了创造超脱社会现实的艺术,而是力图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干预美国人民及其社会的发展。大致而言,他内战后的努力与成就,主要在于成功地使其诗歌在建构超越现实的意识形态并基本保持反传统的艺术风格的同时,适当贴近传统的诗歌范式,促使《草叶集》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强劲地向主流文化圈渗透。
惠特曼在去世前一年出版了《草叶集》的“临终版”,即在第六版的基础上添补“七十生涯”与“再见吧,我的想象力”两部组诗以及散文回忆录《回顾走过的道路》作为“附录”,并声明以此作为诗集的标准版本。他的遗嘱得到了后人的尊重,但一般认为此版“附录”中的诗歌只具有象征意义,表明诗人的创作生涯持续到生命的尽头。对于理解与研究他的诗歌,特别是探讨其创作流变,《草叶集》的六个版本,尤其第一、二、六版,则是必不可少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