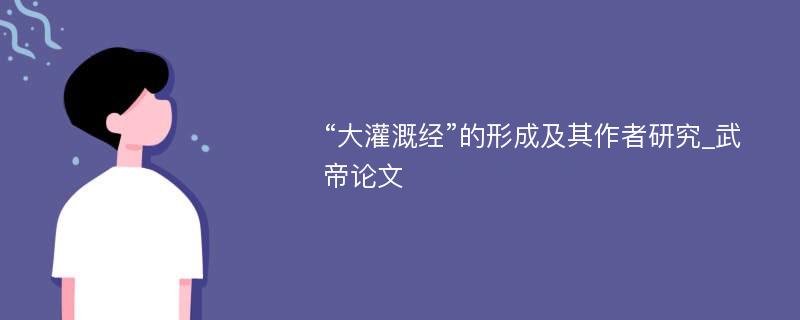
《大灌顶经》形成及其作者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二卷《大灌顶经》在中古中国影响较大,其中的第十一卷《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和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影响尤其广泛,从敦煌写卷中可以看出,这两部经在中古中国很流行。特别是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作为药师信仰的源头,影响尤其深远。但关于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自古有种种异说,本人的博士论文对《大灌顶经》进行了专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在这个基础上,笔者对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作一专门讨论,以期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 形成诸说
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说,第一种说法是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的记载,因为这是十二卷《大灌顶经》首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所以非常值得重视,《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载:
《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一卷,《灌顶十二万神王护比丘尼咒经》一卷,《灌顶三归五戒带配护身咒经》一卷,《灌顶百结神王护身咒经》一卷,《灌顶宫宅神王守镇左右咒经》一卷,《灌顶塚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一卷,《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一卷,《灌顶摩尼罗亶大神咒经》一卷,《灌顶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经》一卷,《灌顶梵天神策经》一卷,《灌顶普广经》一卷。本名《普广菩萨经》,或名《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凡十一经。
从《七万二千神王咒》至《召五方龙王咒》凡九经,是旧集《灌顶》,总名《大灌顶经》。从《梵天神策》及《普广经》、《拔除过罪经》,凡三卷,是后人所集,足《大灌顶》为十二卷。其《拔除过罪经》一卷已摘入《疑经录》中,故不两载。①
在《出三藏记集》卷第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僧祐针对《灌顶拔除过罪经》记载道:
《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秣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遍行于世。②
按照这种说法,从《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尼咒经》到《灌顶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经》九卷是旧集《灌顶》,总名《大灌顶经》,也就是说,现今《大灌顶经》中的前九卷在某一个时间被编集成《大灌顶经》,这是旧集《灌顶经》。而从《灌顶梵天神策经》到《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三卷,也就是现今《大灌顶经》中的后三卷在某一个时间被编集到旧集《灌顶经》中,成为现今藏经中的十二卷《大灌顶经》之规模。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认识,一是先有九卷本的《大灌顶经》,之后经人编集,才有十二卷本的《大灌顶经》;二是虽然僧祐说先有九卷本,后有十二卷本,但并未说十二卷本的后三卷是在九卷本《大灌顶经》之后所作,只是说在九卷本《大灌顶经》之后才被后人编集到十二卷本中;三是僧祐确定《大灌顶经》第十二卷为刘宋秣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并将之判为疑伪经。其他十一卷的作者并未提及,这也意味着僧祐并不清楚其余经典的编撰情况。
第二种说法是智昇的总结,他在《开元录》卷三《总括群经录》说:
《大灌顶经》十二卷。或无“大”字,《录》云“九卷”未详。房云:见《杂录》。《大孔雀王神咒经》一卷。见《竺道祖录》及《僧祐录》,初出。《孔雀王杂神咒经》一卷。见《竺道祖录》及《僧祐录》,第二出。
右三部一十四卷。初一部十二卷见在,后二部二卷阙本。③
接下来在《开元录》卷二十《入藏录下》说:“《大灌顶经》十二卷。一帙,或无“大”字,《录》云“九卷”,未详。一百一十八纸。东晋西域三藏帛尸梨蜜多罗译。”④智昇在《开元录》卷三中上举三部经判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接下来又把《大灌顶经》十二卷看成是帛尸梨蜜多罗译,将之列入《入藏录》。实际上智昇的这个看法是承继了费长房的意见,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七依据《杂录》把《灌顶经》九卷判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又在《历代三宝记》卷十《译经宋》中说:
《药师瑠璃光经》一卷。大明元年出,一名《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一名《灌顶经》,出《大灌顶经》。《祐录》注为疑,房勘婆罗门合有梵本,神言小异耳。……右二十五部合二十五卷,孝武帝世沙门释慧简于鹿野寺出。⑤
费长房在这里说,他根据梵本对勘,认为《药师瑠璃光经》,也就是《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梵本只有很小的不同。进而认为此经为刘宋沙门慧简所译出。接着在卷十三《入藏录》中的《大乘修多罗有译第一》中把《大灌顶经》十二卷列入有译。很明显,智昇采取了费长房的看法。但是因为智昇的《开元录》在后世影响很大,并成为后代刻本藏经的目录基础,因此进入到刻本时代后,诸藏都题《大灌顶经》十二卷为帛尸梨密多罗译。
第三种说法是现代学者的意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司马虚考察经文内容,认为《大灌顶经》为慧简所作,⑥但是他没有提出过硬的证据。日本学者阿纯章受司马虚的影响,接受《大灌顶经》十二卷为慧简所作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证据,即《大灌顶经》十二卷都有共同的主题,每卷都以末法时救济处于危难的众生为目的,提供名为“灌顶章句”的咒语和它的使用方法。他进而认为前九卷灭法观非常普遍,有着紧迫的气氛,应是出自同一个人或是同一集团之手;后三卷没有看到灭法的紧迫气氛,但也有着相同的结构,可以看出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集团撰出。他倾向于认为十二卷的编撰者就是慧简或以慧简为中心的集团。另外阿纯章还认为在僧祐的时代,《大灌顶经》不是以十二卷的形态流传,而是各卷作为一卷本流传。在《大灌顶经》的流传中,除了十二卷本的完整形态外,可能还存在九卷本的形态。⑦阿纯章的研究较司马虚的看法有所发展,也是目前关于《大灌顶经》形成的最新成果,但是这个看法在某些环节上解释不足,尚有扞格难通之处。
二 诸说批判与再研究
上面所列诸说中,僧祐的记载和看法非常重要。因为首先他生活的时代离他所记载中出现的年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很接近;再者,僧祐是一个律学大师,一个严肃的学者。但是当时信息不便,虽然僧祐和刘宋中期时间接近,实际上我们看到僧祐的记载模糊和破碎。因此,对他的记载我们应该既要充分尊重,又要有所拣择。第二种说法中,智昇的说法没有对《大灌顶经》的形成作出说明,只是根据费长房的记载和自己的判断把《大灌顶经》十二卷都归为东晋的帛尸梨蜜多罗译。这种看法实际上并不可靠,通过简单的考察即可知道,费长房只是说《大灌顶经》十二卷中的前九卷为帛尸梨蜜多罗译,第十二卷为慧简所译,十二卷中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他并没有考订出译者,费长房就径直把《大灌顶经》十二卷列入有译中,这是以偏概全的说法。智昇继承并发展了费长房的错误,进而把十二卷的译者都定为帛尸梨蜜多罗译,他的这个错误说法流传至今。
日本学者远藤祐介也主张《大灌顶经》前九卷译者为帛尸梨蜜多罗,他支持费长房依据《杂录》认定《大灌顶经》前九卷为帛尸梨蜜多罗的说法,而现在流传的十二卷为帛尸梨蜜多罗译是《大唐内典录》以后的经录弄混淆的结果。⑧关于远藤的说法,有必要加以论证。首先,正如我们如前所说,费长房虽然依据《杂录》认定《大灌顶经》九卷为帛尸梨蜜多罗译,但又在有译中将十二卷判为有译,自己记载就混乱,并非从《大唐内典录》才开始。其次,关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的可信性没有做出说明,而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历代三宝记》记载混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远藤认为费长房依据的《杂录》即竺道祖《晋世杂录》,而《晋世杂录》是可信的,并因此对望月信亨批判的《晋世杂录》进行可信性论证。费长房相关记载如下,《历代三宝记》卷七“译经东晋”说:“(东晋)《灌顶经》九卷,见《杂录》;《大孔雀王神咒经》一卷,见竺道祖《晋世杂录》及《三藏记》;《孔雀王杂神咒经》一卷,亦见《竺道祖录》。”⑨并将这些经典的翻译归之为帛尸梨蜜多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费长房的所谓《杂录》前并没有加“竺道祖”等形容词,这已经表明《杂录》和《晋世杂录》不同,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历代三宝记》其他记载中找到这个《杂录》,这个《杂录》便和《晋世杂录》不同。更重要的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大灌顶经》不是翻译经典,而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自己编撰的经典,这个《杂录》的记载可靠性不足。
第三种说法分别是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最近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视。司马虚认为十二卷《大灌顶经》有一种很强的逻辑关系,他倾向于《大灌顶经》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集团所创作的,或即是慧简。然而司马虚没有给出论证过程,仅是猜测。阿纯章在司马虚的基础上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证,指出十二卷《大灌顶经》十二卷中前九卷和后三卷的主题和气氛有所不同,虽然如此,他仍认为创作十二卷《大灌顶经》的作者即是慧简,关于这一点,阿纯章同样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我们知道,关于《大灌顶经》的形成,历史上僧祐记载最早。僧祐主张第十二卷的作者是刘宋秣陵鹿野寺慧简,但对这个慧简,缺乏相关记载。这是我们对这部有名的经典形成缺乏了解的原因,也导致学者们在讨论它的形成时容易陷入猜测。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改变这一局面,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关注经文本身提供的证据。细读经文本身,我们可发现《大灌顶经》形成的若干资料,进而可作出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十二卷《大灌顶经》应是一部伪经,具体论证可参考笔者的博士论文。⑩确定了这一点,才可能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上述司马虚和阿纯章两位学者的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缺失点是怎么去解释《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问题,这部经是《大灌顶经》的第十二卷,是药师经的第一个本子,是药师信仰的源头,后世又有三个译本。如果按照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大灌顶经》为中土编撰,那么如何解释后世译本频出的现象呢?两位学者并没有给出说明,这个问题和本文问题有关,但和讨论主题有所偏离,但因为笔者已在专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11)下文不再对此进行讨论,而是直接去探讨设定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转向具体的探讨,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十二卷《大灌顶经》为某人或某集团有目的的编撰,经文之中多处有说明,卷一《七十二神王护比丘咒经》说:
先当洗浴身体著鲜洁之衣,于高山上以香汁涂地,纵广七尺名之为坛,当从此上度是灌顶十二部微妙经典,当受之日思念十方诸佛菩萨应真圣僧,归诚作礼及度经师。(12)
天尊演说无上真妙之法灌顶章句十二部妙典,我当于佛灭度之后广宣流布此深妙典。若有国土遭疾恶者,县官所呼召,万疾流行,我当于中诵读此经,百毒万恶莫不消散。说此语已便讽诵宣传说是十二部妙典。(13)
是故吾今为其演说灌顶章句十二部要藏,拔除邪恶,令得长生。(14)
佛言:“我经中说诸禁咒术不应行者,谓诸异道邪见法术惑乱于万姓,但为利养以活身命,我所不许。今吾所演灌顶章句十二部真实咒术,《阿含》所出诸经杂咒,尽欲化导诸众生故,不如异道为利养也。”(15)
第一卷《七万二千神王度比丘咒经》实际上是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序章,说明了创作经典的原因,是因为有恶王灭法,世界已进入末世之中,人民信异道邪见师。虽然佛所说法中不允许行禁咒术,但是作者在这里对自己编撰经典行禁咒术进行了辩解,作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使人民得“长生”,是为了化导众生,而不是如异道邪师一样为利养。从经中记载恶王灭法,破塔灭僧的现象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灭法活动。笔者认为从经文多处记载“灌顶十二部章句”的事实可以推断,十二卷《大灌顶经》应是经过了一个有目的的编撰过程,这一事实还可在经文的其他几经中可以看出,卷六《塚墓因缘四方神咒经》说:
若人面值于我,以种种供养无所乏少,不如有人于我灭后以此灌顶十二部鬼神神咒总持之王示于人民,令其读诵,其福胜彼百千万分不及一也。我结是灌顶无上章句十二部要虽不同时,然欲利益无量无边,邪见众生学习之者舍诸邪见,积功累德渐得至佛。(16)
卷七《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也载:“若有男子女人等辈行此灌顶十二部封印大神咒经时,香汁涂地圆如车轮。”(17)卷八《摩尼罗亶大神咒经》也说:“我既说是《摩尼罗亶大神咒经》甚深微妙灌顶章句十二部典,不可妄授持与人也。”(18)从上述叙述看,十二卷《大灌顶经》确实经过了一个明显的编撰过程,笔者对照过经文的敦煌本,没有发现异本出现,因而上述推论可以成立。
在上述引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卷六《塚墓因缘四方神咒经》这一段,经文明确说“我结是灌顶无上章句十二部要虽不同时”,也就是意味着十二卷《大灌顶经》不是同时产生的,那么如何来看待结《大灌顶经》不同时的问题呢?十二部经不是一下子就编撰完成的,这个事实显而易见,笔者认为这句话指的不是这个层面,如果仅仅指这个层面,经文作者没必要单独提出来。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在提示十二部经为分成不同时间段形成的,具体地说,是《大灌顶经》后三卷先形成,前九卷后形成。
十二卷《大灌顶经》中,明确提到灌顶十二部经的,最多只到卷八《摩尼罗亶大神咒经》,卷九、十、十一和十二都没有提及,我们注意到卷九《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经》中说:
今佛世尊说是《灌顶召龙神咒》,不但为今维耶离也,标心乃在像法之中,千岁之末,佛法欲灭,魔道兴盛,当有恶王断灭三宝,使法言不通,破塔灭僧,五浊乱时,为是当来诸众生辈演说此法,示于未闻,普使宣传流布世间,人民受者不遭患难,众病除愈,死得升天。(19)
经文中提到了恶王断灭三宝和破塔灭僧的事实,这和卷一内容相同,都充满了灭法的危机感,气氛非常紧迫,日本学者阿纯章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种气氛在《大灌顶经》后三卷中是找不到的。前九卷为同一个时期产生,还有经文本文为证,卷二末尾说:“阿难叉手白佛言:‘设有诸比丘尼若欲受者,云何授与?’佛言:‘当如大比丘受七万二千神王灌顶大法无有异也。’”(20)所谓七万二千神王灌顶大法,即卷一《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卷二明显是接着卷一来讲的。卷三说三归五戒二十五神,在说了三自归后,卷四则说“有受三自归者,尽带持此百大神王名”(21),然后就说百神王名字,经文应是卷三的发展。卷五说:“诸比丘辈不解我意,见有书持读诵之者,谓此法言非佛真说,起邪见想,诽谤不信。我先于《比丘护身》说诸诽谤愆咎之过,若见闻者唯应专修,勿生不信。”(22)显然,这里的《比丘护身》即卷一《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卷五为卷一之后编撰的。卷五到卷九说的都是“杂法”,取自于道教和民间巫道,为的是拯救末世下的人民。而卷十到卷十二中,看不到末世和恶王灭法的影响,这三卷应该在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产生,前九卷则在此之后产生。如前所述,前九卷多处提到灌顶十二部法要,则经文作者在编撰前九卷的时候就已经计划把后三卷纳入到《大灌顶经》中,编成十二卷,以符合佛教“十二部经”的传统说法。因为后三卷先产生,而且后三卷很可能在世已经流传,所以作者在编撰前九卷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修改,这也是为什么后三卷没有出现“灌顶十二部法要”这种词句的原因,同时,这也能够解释经文作者在卷六《塚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中说“我结是灌顶无上章句十二部要虽不同时”这句话,这里作者是在强调前九卷和后三卷不是同时形成,实际上在确立了前九卷在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后三卷先形成。
从“我结是灌顶无上章句十二部要虽不同时”这句话中我们还可确定一点,《大灌顶经》十二卷是同一个人编撰完成的,虽然作者强调了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经文中找到其他例证。卷十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经文中详细叙述了“九横”,九横的内容与安世高译《佛说九横经》等佛教传统的九横内容不同,藏经中也只有这一处有这个说法,应是作者自己从道经中借鉴来的。而我们在卷一《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中却可以找到相应的九横,经文说:“佛法既灭,出千岁时灾变如是。诸佛菩萨应真圣僧,天龙八部一切鬼神,见此灾怪愍念众生于末世中受诸苦恼,使是比丘出现于世,救度危厄苦患众生,不为九横之所得便。”(23)从经文内容看,九横的内容是关于横厄灾害的,与安世高译《佛说九横经》中的佛教戒律截然不同,我们认为从逻辑上讲,这里没有具体解说九横的内容,是因为作者认为已经在别的经典中已经解释过,因此在这里不需要再加说明,而且所谓“别的经典”,应即是此前所作经典,如果是后面的经典,则应在此处加以说明。总之,无论从经文本文还是从内容上看,《大灌顶经》十二卷应为一人创作编撰。
三《大灌顶经》的创作者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说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慧简依经抄撰《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我们认为,僧祐与慧简年代相去不远,本人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佛教学者。他的上述记录言之凿凿,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是关于《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最早记录,没有充分的依据,不能轻易否定。依据这个记载和上文论述,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又在北魏灭法之后,我们可以确定慧简在这一年集中编撰了《大灌顶经》十二卷,其中后三卷在北魏灭法之前形成,前九卷在公元457年前后编撰,在编撰前九卷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将之前形成的后三卷纳入到自己的编撰体系中。僧祐之所以只记载了慧简依经抄撰《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应是《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在当时影响较大,他依据某种渠道获得了这条信息。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记载慧简在秣陵鹿野寺,通过CBETA查询,除了慧简这一处记载外,不见其他任何一处有秣陵鹿野寺的记载。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记载了包括《药师琉璃光经》在内的慧简译经二十五部,但没有说明依据。在这些译经中,有的经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已经记录,但为失译。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对这些经典不予讨论。有关工作拟在将来进行。
日本学者新井慧誉曾经撰文讨论过慧简的问题,他找出大体同时代的三位叫慧简的僧人,分别是《出三藏记集》记载的鹿野寺比丘慧简,《法显传》中的慧简,以及刘宋张演著《续光世音应验记》中提到的慧简(24)。刘宋张演著《续光世音应验记》在中国早已经散失,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日本又发现了此书,近年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整理,现把其中涉及慧简的段落移文如下:
荆州厅事东有别斋三间,由来多鬼,恒恼人。至王建武时,犹无能住者。唯王周旋惠简道人素有胆识,独就居之。以二间施置经像,自住一间。既涉七日,因夜座,忽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便来喷简上。简目开心了,唯口不得语。独专念光世音。良久,鬼来谓道人曰:“闻君精进,故来相试。神色不动,岂久相逼?”豁然还入壁中。简起澡漱,礼拜讽诵,然后还眠。忽梦向人谓之曰:“仆以汉末居此,数百年矣。为性刚直,多所不堪。君有净行,特相容耳。”于此遂绝。简住弥年安稳,余人犹无能住者。(25)
《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与之基本相同,文载:
释慧简,不知何许人,梁初在道。戒业弘峻,殊奇胆勇。荆州厅事东,先有三间别斋,由来屡多鬼怪。时王建武临治,犹无有能住者,惟简是王君门师,专任居之,自住一间,余安经像。俄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便倚简门上。时简目开心了,但口不得语。意念观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进,故来相试,今神色不动,岂复逼耶。”欻然还入壁中。简徐起澡漱礼诵讫,还如常眠,寐梦向人曰:“仆以汉末居此数百年,为性刚直,多所刚直,多所不堪。君诚净行好人,特相容耳。”于此遂绝,简住积载,安隐如初。若经他行,犹无有人能住之者。(26)
比较道宣《续高僧传》与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故事基本一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续高僧传》中添加了“释慧简,不知何许人,梁初在道。戒业弘峻,殊奇胆勇”这两句。我们认为,道宣添加的这一段不合事实。张演生活在刘宋初年,他所记载的故事至少为刘宋初年,道宣说这个慧简还一直生活到梁(502—557)初,恐怕是道宣所臆加。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五说:
忱字元达。弱冠知名,与王恭、王珣举流誉一时。历位骠骑长史。尝造其舅范宁,与张玄相遇,宁使与玄语。玄正坐敛袵,待其有发,忱竟不与言,玄失望便去。宁让忱曰:“张玄,吴中之秀,何不与语?”忱笑曰:“张祖希欲相识,自可见诣。”宁谓曰:“卿风流隽望,真俊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宁使报玄,玄束带造之,始为宾主。
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27)
刘义庆《世说新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其书《方正篇》说: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熟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28)
刘义庆是刘宋时人,他称呼王忱为王建武,而据《晋书》记载,王忱也曾镇荆州,那么这个王忱很可能就是《续光世音应验记》中的王建武,董志翘也持这个看法(29)。如果是这样,太元中(381—396)王忱任荆州刺史,我们把《续光世音应验记》中的故事场景放在太元中的最后一年396年,慧简当时二十岁,到萧梁的第一年(502),慧简也已经126岁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们把所有的年代都往道宣的记载推迟或尽量提前。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中并没有说慧简梁初仍在,显然,道宣记载慧简在梁初活动,明显是臆测,看来,《续光世音应验记》中的慧简应生活在东晋末年。
在《法显传》中,一名叫慧简的僧人也出现了两次,相关文字如下:
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30)
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焉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法显得苻行堂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遂与宝云等共。为焉夷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31)
《法显传》中慧简出现了上举两次,慧简等人去了高昌,后面没有再提及。新井慧誉对这里出现的慧简进行了考察,考察的做法是先考证了几位重要僧人的年龄,接着说《法显传》中所有僧人出现有一定顺序和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严格按照年龄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他据此断定此慧简不可能为编撰《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慧简(32)。对此,笔者心存疑虑。首先,新井把法显六十岁左右的高龄(33)去印度作为标杆就很不妥,法显去印度时六十岁左右,不能据此判断其他几位僧人去印度时年龄也大到法显这个地步;再者,新井实际上考察出具体年龄的只有法显和宝云两人,其他几位僧人的年龄并没有得出具体结论,这样的话,就不能很好地确立标杆。换句话说,即使《法显传》中僧人的出现是按照年龄来排列的,也不能得出《法显传》中的慧简不是编撰《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的慧简这个结论。
可以先来看关于宝云的生卒年月,《高僧传》卷三“宋六合山释宝云”条载:
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更,礼事供养,十室而八。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几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游履外国别有记传。(34)
《高僧传》中载宝云元嘉二十六年终亡,各家记载一致。但是关于宝云的年龄,诸家记载略有不同,《出三藏记集》中作“七十有余”。汤用彤引《名僧传抄》说宝云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为十八岁,至元嘉二十六年应为七十八岁(35)。元嘉二十六年(449)距宋明帝大明元年(457)八年,《法显传》中的慧简和宝云无疑是同时代人,即使假设慧简和宝云同时或稍大,活到457年也是完全可能的。从时间序列上看,笔者推测《续光世音应验记》中的慧简也极有可能就是《法显传》中的慧简,也不排除为抄撰《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慧简。这一点在经文本文中也能得到一些支持,卷七《伏魔封印大神咒经》说:“当如前法存思三想及五方之神形色像类,使一一分明如对目前,如人照镜,表里尽见。如此成就,无余分散,专心一意,病者除愈,恐者安隐,邪神恶鬼无不辟除(胡言文头娄者,晋言神印也)。”(36)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晋言”一词,按照这个词,则应该判定作者是晋时人,但如我们上文考证,卷七中出现了“行此灌顶十二部封印大神咒时”这样的句子,而经文的编撰应为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后,那么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作者活动时代经历了东晋,并进入了南北朝。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这三个慧简很可能是同一人,他经历东晋末年,并和法显等人西行求法,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又集中编撰修订了十二卷《大灌顶经》。
注释:
①②(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6—177、225页。
③④《大正藏》第55册,第503页上;第705页中。
⑤《大正藏》第49册,第93页中至下。
⑥Michel Strickmann,The Consecration Sutra: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Edited by Robert Buswell,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75—118.
⑦阿纯章:《关于灌顶经的成书》,《华林》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
⑧远藤祐介:《关于灌顶经的译者》,《密教学研究》第36号,2004年,第45—64页。
⑨《大正藏》第49册,第69页上。
⑩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待刊。
(11)参见拙文《〈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文化汇流”》,《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12)(13)(14)(15)《大正藏》第21册,第497页中;第497页下;第498页上;第498页下。
(16)(17)(18)(19)(20)《大正藏》第21册,第514页下;第517页上;第520页下;第523页中;第501页中。
(21)(22)(23)《大正藏》第21册,第505页上;第511页下;第497页下。
(24)新井慧誉:《沙门慧简》,《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38号,1971年,第275—281页。
(25)(29)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9、37—38页。
(26)《大正藏》第50册,第646页中及下。
(27)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2—1973页。
(28)刘义庆著:《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153页。
(30)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31)《法显传校注》,2008年,第8页。
(32)新井慧誉:《沙门慧简》,《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38号,1971年,第275—281页。
(33)章巽在《法显传校注》序言中引各家记载,说法显从长安出发去天竺时,他的年龄无论如何已经在五十八岁以上了。见其书序言第2页。
(34)(35)(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3、104—105页。
(36)《大正藏》第21册,第515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