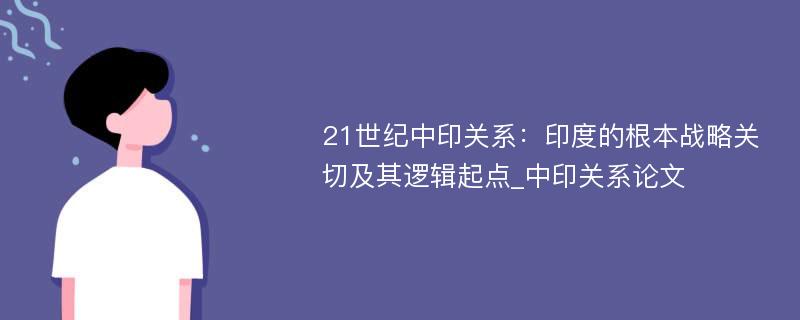
21世纪的中印关系:印度的根本战略关切及其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关切论文,中印论文,逻辑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是:在全球惟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是如此。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颇有影响力、政治上成熟、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上升的地区核心国家,印度因其一以贯之的大国抱负及曾经有过的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经历,使人们不再质疑印度的世纪性崛起。
具体到中印关系上,对印度来说,最具根本性的战略关切显然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而且关键不仅仅是有些学者或政界人士担忧中印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国竞争态势,还因为国务家们和国际政治理论界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世界头等强国地位是一项极其稀有的宝贵财富,历史上往往只有少数一两个国家能抓住机遇乘势占据这种地位,进而引领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方向。而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落败的国家,往往会招致更大的体系压力甚或有挫败感,并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丧失这种机遇,从而不得不继续屈居于二流国家地位甚或更惨。正是这种理论假设,使得世界强国竞争具有无情的非此即彼的特性,并多少得到了历史的佐证。基于上述假设不难看出,就中印两国而言,根本的战略关切在于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以及与这种大国地位追求相伴随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实力较量与战略警觉。为此,本文并不细究中印关系的发展演进脉络和其间的重大外交事态,而是主要侧重于从印度方面来考察21世纪的中印关系,重点阐释在印度的世纪性战略追求中中国因素的重要地位,以及在致力于中印之间的“稳定的平衡”过程中,印度的主流中国形象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进而指出印度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与其大众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自信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印度对华政策新的逻辑起点,而正是这一根本变化,决定着新世纪里中印两国将能够为克服相互关系中的种种困难寻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使和平与合作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流。
一、新世纪印度的根本战略追求及其中国因素
显然,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始终未失大国抱负。无论是独立前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发出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豪言壮语,①还是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印度人民党领袖鼓吹要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抑或是现政府大力宣扬的“印度世纪”,无不揭示了印度的世纪梦想: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国。应当承认,独立后的印度尽管满怀大国理想,并力图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按照大国的方式行事,但印度始终没能得到其他大国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可以说,在冷战背景下,印度的对华政策根本上讲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也就是安全追求。尼赫鲁曾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地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边界。如果我们是朋友,即使是那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争论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1959年12月9日,尼赫鲁在议会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表示了对“中国威胁”的强烈担心:“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我们的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②所以不难看出,冷战时期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界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不断取得渐进式的进展。
当然,与边界安全问题紧密关联但却更加影响深远的是,印度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接受在与中国的实力对比中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论及中印关系时,印度著名国务家迪克西特曾告诫说:“我们必须记住,最大的现实是中印之间的不对称。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更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印度警觉到,中印关系完全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对华关系的)目的应是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以改变上述不平衡,以及减轻中国政策中的这部分内容,这就是印度政策和战略的关注点。”③印度著名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亚姆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印度)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和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这就是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抗衡的一个途径。”④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印度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因为中印两国实在太相像了。但是,与中国频繁地被提及相比,“印度战略家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⑤。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也曾抱怨说:“每一个印度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⑥
在对其他大国感到不满的同时,印度很自然地也对中国感到些许嫉妒甚至怨恨。苏布拉马尼亚姆就指出:“如果历史是未来的指针,那么便可以认为竞争源于它们致力于恢复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在欧洲国家到来之前这种地位和影响力在亚洲是压倒性的)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决心(多数原因是印度自己造成的)拒不承认印度应拥有与其规模、人口、军事实力、经济潜力和文明成就相一致的世界地位。”⑦所以,与中国进行不言自明的实力竞赛,从而确保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便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其中,在印度看来,1998年的核试验至少是改变了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局面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纪的亚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将能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对此,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学者指出:“如果说1962年的战争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及改变了次大陆的权势结构,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则是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效果。”⑧正因为如此,曾出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亚什万特·辛哈才会有下述自信:印度的对华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⑨换言之,它基于新的势力均衡这一现实。
毫无疑问,在印度看来,首要的追求便是中印之间的所谓“稳定的平衡”。但印度同时也认识到,“印度的崛起不仅有赖于印度的行动,而且有赖于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进展的反应,以及今后几十年的客观环境。”⑩
二、印度四种主流中国形象及其政策选择
一国关于另一国形象的认识,除了取决于历史交往过程中的观念互动与观念建构外,还基于现实利益碰撞和未来构想。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极为复杂:“怀疑、神往、震惊、团结、竞争、友好、焦虑、恐惧、愤怒、畏惧、敬重、轻视,而首要的是迷惑不解。”(11)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印关系的起起伏伏直接影响着印度的中国观。正如一项研究所指出的,“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既重要又微妙的因素是,一代人如何评价给本国造成心灵创伤的近期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战败是一国最痛苦的经历。(12)显然,在最近时期的中印关系上,印度既有中印是兄弟的友好记忆,更多的则是1962年战败的耻辱。正是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过程中,在爱恨情仇的驱动下,在当代印度,形成了一位印度学者所说的四种主流中国形象:(13)
第一,视中国为印度古时的朋友和现今的盟友。这一认识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这一认识主要基于反殖民主义和反西方的历史经历,要求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现状,建立更加人性和正义的世界秩序。其次,这种认识对未来中国在国际体系及邻国中的作用持一种相当温和的观点,认为没有来自中国的真正的威胁。再次,便是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发挥一种稳定作用,认为中国的权势大体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颠覆和进攻性的。
第二,视中国为印度学习的榜样。这又包括:视中国为近乎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赞赏中国敢于抵制西方的压力,冷静地做出相关的决策;认为中国正崛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其行为方式值得印度学习和效仿。
第三,视中国为不可预测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这一观点在印度军队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同时持这一立场的还有一些战略分析人士,如印度学者J.M.马立克(J.Mohan Malik)。他说:“中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一个同等的竞争对手的崛起。一个真正的亚洲对手将挑战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中央王国’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北京要推行一项遏制印度的政策,以及通过代理人战争包围印度。”(14)还有的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政府外交政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试图打破那种将印度的眼界局限于南亚的思想倾向。显然,这种努力并不为其他几个世界大国所容忍,它们错误地认为,像印度这样一个觉醒的巨人必将对其利益构成威胁。在这些对印度满腹怀疑的国家中,中国名列榜首。(15)
第四,视中国为不可理解和过于诡秘。在印度,大多数公众舆论持这种看法。其中,积极的一方面是视中国为一个富饶神秘的国度,而消极的部分则是视中国为一个搞阴谋诡计的国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指出,随着中国在21世纪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注定要受到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巨大变革的影响。中国用以对付印度的可能正是孙子教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中国将核导弹技术转让给巴基斯坦,它也就能监控印度,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威胁印度了。中国可能继续与印度友好,但同时通过维持印巴核平衡来遏制印度。中国的野心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要霸权国家。据此,中国视印度为一个可以被巴基斯坦牵制的地区国家。这正是高深莫测的中国对印度的挑战——一种并非残酷的军事威胁。(16)
从根本上讲,21世纪中国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印度自己也无法给出定论。正是由于观念上的巨大分歧,导致印度的中国政策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使是在今天,在与中国接触的目标上仍没有明显的共识,国内战略界也没能提出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结果,尽管对华政策受实用主义指导,却仍然是两方面的折中,即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设想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尼赫鲁式的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折中。“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多数是在军队和战略研究界,以及与西藏运动有着紧密联系的部分政党人物。这部分人急切地希望与美国结盟来反对中国。而合作论者主要是理性的中国问题学者、前外交官和一些左翼政党人士。他们认为中印两国都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深受冷战之害,主张应在冷战背景下认识1962年的战争,认为两国之间尽管有突出的领土争端,但仍可以发展互利合作关系。(17)
印度前政府部长、人民党主席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也认为:“今天,印度的中国观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她是一个具有侵略和扩张主义性质的威胁,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姐妹性质的古老文明。”(18)所以,斯瓦米认为,一个有效的对华政策首先要求建立全国共识:自1962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印度该怎样界定与中国的复杂的利益关系。(19)尽管对中国的认识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认识,但普遍认为中国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20)中国为什么对印度特别重要呢?一位印度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1962年与中国的边界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成为印度自信的一大障碍,并一直延续至今。可见,印度的国民情绪和普遍的对华大众舆论,在今天仍然塑造着印度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这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取向及其关键点
美国著名南亚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曾写道,“印度独立(分治)50多年来,一直在这样两种前途之间挣扎着:或者崛起成为大国,或者由于分裂而崩溃。”显然,在追求上述第一种前途——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中,印度的战略表现至少招致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即认为体现出了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或比较理性的现实主义。
实际上,印度并不乏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21)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Kutaniti,the law of crookedness),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尽管当今印度政界人士很少宣扬考底利耶的思想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有任何降低。主要是因为考底利耶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此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公开提及他的名讳。(22)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之外,印度所有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新建构考底利耶的传统罢了。(23)
具体到中印关系,印度的对华政策无疑是基于坚定的现实主义,尽管其国内有着不同的中国观和相应的政策选择。但也应该看到,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地催生出一项理性的现实主义政策,究其原因,在于大众政治时代舆论对决策的干扰和影响。
在论及外交决策时,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曾指出:“在国际事务中,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似乎是:公众的声音既没有影响力,也往往是错误的。”(24)但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自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就已进入大众政治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大众在国家事务中拥有重大的发言权,国家能否推行理智的国家政策与舆论息息相关。(25)尽管如此,普通大众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国家事务,而且他们对于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观点往往来自“早晨同咖啡一起匆忙吞下的报纸头条”。更为严重的是,在生活的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验证他们的观念,结果往往不假思索地赞成报纸上的那些观点。由此而来的是大众观念可能导致最大的危险:由于舆论的干扰,特别是由于决策者有意错误操纵舆论并深陷舆论的泥潭之中,导致当事实最清楚不过时,决策却是最错误和最具灾难性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一国内部激进的集体情绪使人们对各自的性命攸关的利益视而不见,并招致严重的后果。这在1962年的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上就有典型的表现。
尽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26)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但1962年边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相当一部分印度公众,所谓“中国威胁论”还不时冲击中印双边关系。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敌对心态的作用下,印度政府怎么可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新的战略目标来理性地推行一项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呢?换言之,印度对华现实主义政策取向首先必须重视并解决好国内的舆论问题,特别是要正确审视和评判1962年的边界战争及中印边界争端。所以,1998年6月,在印度联邦院发表讲话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特别强调指出:“印度人民必须确实感到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将是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一大要素,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安全”,尽管他也呼吁中国方面应当注意印度在边界和巴基斯坦防务问题上的沉重感情。(27)
正是意识到舆论对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印度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大众。例如,在瓦杰帕伊政府时期,印度官方就鼓励当年的官员、退休将领和知情人士,在边界问题上大胆发表不同于昔日官方的言论,允许出版论述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学术著作,默许杂志发表以批评尼赫鲁错误对华政策著称的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40周年之际,印度最大的网站rediff.com特地就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问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并特地邀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和前官员参与。这种引导舆论的做法,非正式地为中国正了名,也为印度政府推进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国内舆论氛围。(28)
实际上,在新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印度正确引导国内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为发展与印度的新型关系,中国的南亚政策出现了印度学者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更加“平衡”;其次,视克什米尔问题为印巴之间必须用非武力方式加以解决的双边问题;再次,在印巴冲突中保持“中立”。(29)第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超越,即成功地超越了冷战,成功地超越了印度核试验危机,成功地超越了边界争端,不使之影响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第三,双方致力于互信机制建设的努力取得积极进展。继1993年9月7日两国签署了意义深远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之后,1996年又签署了《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6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第四,经济合作与依存度不断加深。尽管中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两国经贸总量也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但正如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阿尔卡·阿查里雅所说:“竞争必然会出现,尤其是因为我们面对同样的市场,寻求同样的技术和能源资源。不过,为什么说中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潜在伙伴,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果不与中国合作,你就可能因能源问题发生冲突。如果在美国市场不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两国在那里就可能产生矛盾。我们都太大,不能同时在同一地区争夺相同的东西。”(30)
四、战略自信——中印关系新的逻辑起点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的谈话中论述了中印发展起来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强调指出:“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目标下,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31)这里,邓小平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战略自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方面的战略信心却显然不足。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当数印度前外长J.N.迪克西特下述一连串发人深省的提问:“(中印两国)能否避免竞争的潜流和处于萌芽状态的怀疑,建立起持久的、积极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国是否会鼓励支持在其南部边陲出现一个强大的印度?印度是否能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在战略上主导印度洋地区的东南亚?”(32)
显然,印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基础,是力量平衡,更需要的是战略自信心。
2003年1月27日,印度外长在第五届亚洲安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亚洲安全与中国》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有些分析家认为印中之间将有一场争夺亚洲霸权的战斗,他们谈论印中之间由于势力范围的重叠和两国决心要成为世界大国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彻底揭穿这些理论。这位外长还充满信心地说,印度不会追求、也不会制定基于两国冲突不可避免的政策。他特别强调指出:“我向在座的各位保证,印度对待与中国的关系的态度是向前看的,并且持乐观态度。印度的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嫉妒。她是基于印度必然走向繁荣和中国必然走向繁荣和强大的信念。因此,为了双方的利益,两国不仅要学习共存,而且要学习解决分歧并建立共同点,这才是合乎逻辑和合理的。”(33)在这里,印度似乎重新找回了邓小平所论说过的两国关系的逻辑起点,虽然时间晚了15年。
毫无疑问,不仅印度需要用这种新的逻辑来看待中国和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而且国际社会也需要像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从亚洲崛起的高度去观察中印两国的崛起。这方面,新加坡交通部长林双吉就做出了呼应:“在新世纪,更重要的不仅是中印崛起,还有整个亚洲的崛起。同样重要的是,亚洲崛起不会导致惟我独尊的亚洲或太平洋世纪,而是产生一个动态进程和全球化的亚洲共同体,从而通过贸易和投资网络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得好,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两国共同发展,中国的崛起正在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提供难得的机遇,中国应该成为印度的伙伴而不是对手。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远见和新的逻辑,2005年中印两国确立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和平与合作将成为新世纪中印关系的主流。
注释:
①[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②《国际问题译丛》1959年第22期,第11页。
③J.N.Dixit,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New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2001,p.248.
④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电。
⑤[美]斯蒂芬·科恩著:《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⑥[印]瓦杰帕伊:《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载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⑦K.Subrahmanyam,"Understanding China:Sun Tzu and Shakti",The Times of India,June 5,1998,p.7.
⑧Alka Acharya,"India—China Relations:An Overview",in Surjit Mansingh,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98,p.190.
⑨Inaugural Address by Mr.Yashwant Sinha,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organi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New Delhi,February 4,2003.
⑩[印]亚什万特·辛哈:《地缘政治: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载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11)Amitabh Mattoo,"Imaging China",in Kanti Bajpai and Amitabh Mattoo,eds.,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New Delhi:Har-Anand Publications,2000,p.14.
(12)[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3)Amitabh Mattoo,"Imaging China",in Bajpai and Mattoo,eds.,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pp.13-25.
(14)J.Mohan Malik,"India Goes Nuclear:Relations,Benefits,Costs and Implic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0,August 1998,pp.194-195.
(15)M.L.Sondhi and Prakash Nanda,Vajpayee's Foreign Policy:Daring the Irreversible,New Delhi:Har-Anand Publications,1999,p.98.
(16)转引自Sondhi and Nanda,Vajpayee's Foreign Policy,pp.143-144.
(17)Wahegura Pal Singh Sidhu,Jing-dong Yuan,China and India:Cooperation or Conflict ? 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p.114-151.
(18)Subramaniam Swamy,India' s China Perspectives,New Delhi:Konark Publishers,2001,p.Ⅶ.
(19)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s,p.143.
(20)Suriji Mansingh,"Why China Matters to India",in Mansingh,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159.
(21)本节有关考底利耶地缘政治思想和策略主张的论述均源自Kautilya,The Arthasastra,edited,rearrang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N.Rangarajan,New Delhi:Penguin Books,1992.特别见Part X:"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l:"Defence and War",pp.541-579.另外还可参见Giri Deshingkar,"Strategic Thinking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Kautilya and Sunzi",and V.R.Ragavan,"Arthashastra and Sunzi Bingfa",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New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1998,pp.357-366;晋劼:《〈政事论〉思想与策略》,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
(22)Imtiaz 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93,p.223.
(23)Ahmed,State and Foreign Policy,pp.217-218.
(24)[英]爱德华·卡尔著:《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25)Norman Angell,The Public Mind—Its Disorder and Its Exploitation,London:Noel Douglas,1926,p.15.
(26)《〈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国政府网,2005年12月22日。www.gov.cn
(27)关于中巴关系特别是双方的防务合作关系,中国外长唐家璇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享有包括军火贸易关系的主权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印度享有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印度外长辛格2001年12月在议会说:“我们已与中国讨论了有关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的导弹发展计划问题。中国坚持说它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遵从了现有的不扩散国际体制。”见Prakash Nanda,Rediscovering Asia:Evolution of India' s Look-East Policy,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2003,p.414.
(28)这方面的论述主要引自王宏纬、朱晓军:《印度对华政策转变的背景浅析》,中国与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昆明,2003年9月23日至24日。
(29)Bharant Karnad,Nuclear Weapons & Indian Security:The Realist Foundations of Strategy,London:Macmillan,2002,p.544.
(30)麦马克、亨利·朱:《印中关系解冻》,原载《洛杉矶时报》2006年8月25日,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6年9月12日。
(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32)Dixit,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p.219.
(33)Inaugural Address by Mr.Yashwant Singh,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标签:中印关系论文; 中印战争论文; 中印冲突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印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印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