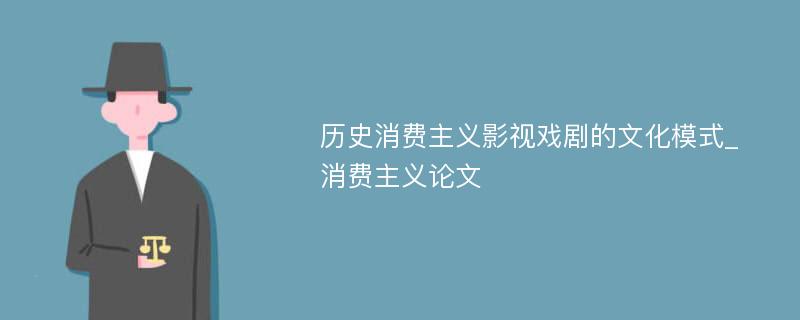
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剧论文,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市场转型,“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相互策应,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在这个大背景下孕育而生。所谓历史消费,也即消费历史,把历史史实、历史言说进行各种形式的“戏仿”、“歪说”,并夹杂各种文化消闲的噱头于这些“戏仿”、“歪说”之中。中国当下,伴随着消费对象的不断“越界”,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呈现出日渐明显的泛化态势。消费历史的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消费主义特点之所以“风行”,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的易操作性、易模仿性。它遵循一套简便易行的文化模式,只要严格遵守,就能适应社会大众的欣赏心理,就能创造票房,产生“晕眩”效应。鉴于这种形势,本文针对中国当下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主要文化模式进行剖析与批判,以资对思潮研究与文艺创作有所借鉴。
一、“配方”化与“怀旧情绪”
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好莱坞电影的“配方”化生产所造出的种种流行的电影类型片系列。其实任何流行的文化思潮,都有其固定的“配方”模式。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也有自己的程式化配方。好莱坞的“配方”化生产常常选择被广泛接受的题材作摹本,抽取其中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核心要素(例如,传奇主人公、有波折而完美结局的爱情、些微的暴力、色情成分等等)重新搭配组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予以再现。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依然如此。但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主要的摹本从“历史”与“消费”这两大母题出发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个顺序,即先选择比较有广泛影响、有大众接受基础的历史题材,再结合消费类型题材要素与之进行组合。这样,历史消费主义的“配方”就是历时性与现时性相结合的流行“配方”了。例如电影《英雄》选择的是大众熟知的“刺秦”历史故事,却改编成现代的武侠类型,几个刺客之间演绎了几段多角恋关系——尽管最后被自反性拆解为凭空虚构,但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偶像明星的客串,加重了“言情”的渲染。又如电视剧《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于感动中国大众的历史故事,先占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心理优势。然后结合当下大众“看热闹”的消费需求,让温文尔雅的梁祝有了一套花拳绣腿,一出经典的文戏硬塞进了武打暴力的“佐料”。这样的历史传奇故事,既煽情,又好看。尤为甚者,近来国内大兴“经典”的消费戏说“热”。《沙家浜》、《红岩》、《潘金莲》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性的经典,都在历史消费的思路下,被改编成“配方”式类型。这些历史消费主义“配方”,遵循着比好莱坞“配方”还低俗的模式化。有人曾对此类“配方”予以经典的概括:“不过,看了几例,便知道了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一是内容泛性化,二是性爱多角化,三是人物粗鄙化。把握了这几点,特别是‘泛性’加‘多角’,只要这么一‘化’,无论什么经典都可以胡来,可以戏说、新编。”[1] (P435)也正是这种吸引人“眼球”、赚人“眼泪”、讨人“开心”的消费主义“配方”,把历史题材改编成一种“历史背景”,进而成为一种虚拟历史——力图唤起的不是观众的“历史感”,而是对不可再度追寻的过去的“怀旧情绪”。
怀旧是一种人们对逝去时光的共有情绪,但这种共有情绪却极具个人化色彩,因为它不需要遵循什么真实的逻辑,因而也可以任意曲解、消费,只要似曾相识。例如新近上映的电影《美人依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都截取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场景作为“怀旧”的参照背景,虽然演绎的不是“历史”,但却始终有一种历史中个体无奈的淡淡忧愁弥漫其中,让观众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对旧时代的“感伤”。这种感伤的怀旧情绪,和我们时代今天进入新世纪、社会转型为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势又极为契合,似乎有“共通之情”。当然,只要这种“怀旧”不触及作为宏大叙事的“正史”,一般都无可厚非。可是,事实上,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侵袭之下,“怀旧”正和怀旧式演绎历史纠缠在一起,人们很难分清是在书写历史,还是在抒发一种历史感伤情绪。由湖南卫视与上海嘉禾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唐情史》,融合古装历史与现代言情于一体,以唐代历史上一系列名人间的“男女之情”为主线串联历史。“情”,尤其是“令人感伤之爱情”在这部连续剧中成为历史演义的主动力。这部让你大为惊奇的“皇室家庭戏”最为吸引人的固然是无中生有的名人感情的野史,但是如果没有正史的搭配组合,也唤不起人们对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感叹与感伤。“怀旧”在这里又悄然转换成“怀情”。但这毕竟是在演绎历史,历史可以解说,却不可重组,尤其是不可貌似严肃地以消费式组合历史。
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曾说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取代丹东,路易勃朗取代罗伯斯比尔,1849—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2] (P603)马克思的话是针对历史上切实发生的事实而言的。第二次历史事件模仿第一次历史事件之所以看起来“搞笑”,在于第二次发生事故之时,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同于第一次的改变,貌似事件的历史本质已经有了天地之别。就影视艺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而言,也存在着第一次与第二次之别。影视剧作所谓的“第一次”再现,是紧扣第一次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历史条件表现切实的历史本质真实;影视剧作所谓的“第二次”再现,则仅仅是对事件形式的简单模仿,无视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本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无疑属于“第二次”再现,因为它将“第一次”历史事件的历史条件已经更改为消费时代下的历史环境,将“第一次”的历史本质已经借消费的噱头化为虚空——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给人的审美效果只能是历史的笑剧。鲍德里亚在评说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一次,他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回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3] (P99)这种回忆,确切说是一种丧失了历史根据的情绪上的“怀旧”。据于此,鲍德里亚认为:“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成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3] (P100)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正是秉承这一主旨,将历史当下化、生活化、消费化,最终使人们沉湎于历史消费的消费迷局之中,而忘却了现实性的基础,“从中我们不应只简单地看到对过去的怀念: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即在否认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3] (P100)
二、“噱头”与“小历史”
无论是“配方”还是“怀旧”,都是在针对接受者的内在情感需要进行材料的编排设定。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配方”特征除了套用传统的接受模式,还擅长设定能够激发接受者的感观欲望的各种“噱头”。这些“噱头”并不止于传统戏剧那样的插科打诨,而是集中于和人们的生理欲望密切相关的东西,例如“性”和“暴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刚刚从封闭的传统社会开始向开放的消费社会转型,一系列艺术与内容乏味,以半遮半掩的“性”为卖点的影视剧大量出现。《欲望歌女》、《寡妇村》等影视作品甚至标出“儿童不宜”字样来哗众取宠,港台的一些经过删减的“三级片”可以在电影院“午夜场”放映,各种海关走私的“色情”(有些仅仅是“露点”)录像片以“夫妻教学片”的名义充斥中国内地地下音像市场。这些充满“性”意味的影视作品的泛滥,固然和中国社会中长期被封闭、被压抑的大众欲望躁动不止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消费社会的金钱本位与欲望消费的关联,刺激了消费直接联系于生理欲望。在消费主义的伦理观念里,只有欲望能最大限度地带动消费,任何传统的节制禁欲都会破坏消费圈的加速循环。“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的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的暴露癖。当然同时,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3] (P158)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在进行历史消费中,几乎没有一部作品忽略了“性”问题。这种历史消费剧作,或通过裸露的“交媾”场面“吊”人胃口(如以《大唐情史》为代表的“情史”系列),或通过历史人物的野史绯闻惹人遐想(如以《皇太后密史》为代表的“秘史”),或把“性”(包括“情”)改写为历史的“主旋律”(如以《至尊红颜》为代表的“伪史”系列)。总而言之,无“性”几乎就没有今天的消费历史片。
作为“噱头”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则是“暴力”,确切说是无对象、无因由的“暴力”。消费主义影视剧中的暴力内容宽泛,既包括各种犯罪暴力,也包括无因由的展示性暴力(例如武打片的暴力展示),还包括作为参照背景的暴力掠影(例如影视中与主题无关系的街头巷尾的暴力场面)。消费主义影视片喜欢展示暴力场面,似乎血腥和打斗更能激起消费者本能的欲望。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主义的暴力展示的是一种消费主义式的自我陶醉,消费者在观看这些虚拟的却被当作现实的暴力场面时,对自身所生活的没有如此暴力的消费主义社会便充满认同感,充满超越其他不安全民族和地区的优越感,同时,出现这些暴力,“从破坏性(暴力、轻罪)到可传染的压抑性(疲劳、自杀、神经症)以及集体逃避现实的行为(吸毒、嬉皮士、非暴力)等多种形式”,[3] (P199)也是消费社会中人们在盲目迷失自我的情况下,对付各种社会消费压抑而不得不进行内心宣泄的需要。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处理“暴力”问题和消费社会的暴力渲染并无区别。陈凯歌为完成影视消费题材转型所拍摄的《蝶舞天涯》,一开始的本名是《吕布与貂蝉》,这段表现三国历史的艺术片,充斥着消费主义式的血腥与暴力场面,最后鉴于广电局的压力不得不删减、更名。历史影视片所涉及的历史一般都比较久远,而且一般说来,人们常常会认为越是久远的历史社会越是充满暴力与野蛮。历史消费主义影视片从迎合观众、激发观众猎奇心理出发,往往会加重渲染这种社会历史的暴力,这种渲染也衬托了当下消费社会的文明与安全,给予了消费者对于久远时空的不可再来场面的无限玄想。就如同每个人都有可能幻想犯罪一样,“恶”的本能也可以借助历史暴力予以宣泄、予以消费。
除了“性”与“暴力”,如果说“噱头”还有第三个突出特征,那就是“搞笑”。但是消费主义搞笑不同于莎士比亚式戏剧的搞笑——一种对历史旧事物的嘲弄、对历史新事物的欢庆。有时候,消费主义“搞笑”所嘲弄的恰恰是合乎历史存在价值的合理的东西。“笑”自身在文化意义上有种“否定”意味,[4] (P9)所以“笑”在严肃的题材(如历史题材)中更适合用于作为颠覆的手段。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作中“搞笑”的内容很多,无论是《新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涉及历史内容的《梁祝》、《梁祝笑传》、《水浒笑传》(港)、《还珠格格》……都秉承一个“搞笑”的传统,历史文化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中常常作为“搞笑”的对象,只要有趣,惹人发笑,可以任意歪曲历史事实。乾隆皇帝也可以成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搞笑”父亲,梁山伯、祝英台可以成为插科打诨的高手,水浒英雄个个是“无厘头”。这种“搞笑”本身要颠覆一种历史传统,颠覆一种在文化中和当下消费主义原则相冲突的种种原则。要想肆无忌惮地搞笑历史,这个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中的“历史”就不能容许“宏大叙事”,只有通过个人化、“小历史”化,历史才能贴近当下个人,才能为当下的消费受众理解、接受。
“小历史”(民间、私人的历史)相对于宏大叙事的“大历史”(官方、主流的历史)而言,“宏大叙事”是正史、按照社会科学规律可证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的非正史、私人史并不是为官方承认的历史,有时候却更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为此,可以说“小历史”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但是当下历史消费主义所主唱的“小历史”显然不是可证、可靠的真实历史,而是源于个人主义想象的主观杜撰的“小历史”——这一点也许正是鉴于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的否定而滋生。《大明宫词》能让诗人王维飞跃37年的时空距离,把《红豆》一诗演绎成对太平公主的爱情表白;《还珠格格》能借着历史上某位公主的名字遐想出一曲感天动地的爱情、亲情的畅想曲;《康熙微服私访》能让皇帝每次私访“艳遇”不断;《铁齿铜牙纪晓岚》能让纪晓岚插科打诨,智斗和绅几十集……这些都依靠编者纵横想象的“小历史”——说白了,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小历史”更像当下消费社会中的私人生活的历史化,更像当下日韩言情剧的中国化。“噱头”的演绎依靠历史的演绎。
三、“游戏性”与“反历史”
历史消费主义有时打着“历史”的旗号,有时打着“消费”的旗号,有时在适应“传统”,有时在适应“当下”,最终历史消费指向了一种对历史的远远背离,对金钱本位的现实贴近。历史消费主义的“反历史”本质由此体现。
历史消费主义如果不颠覆历史,就无法进行历史消费。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起着规范传统的作用,而消费主义取得本位的社会所要建立的规范恰恰是和历史传统所树立的规范在众多方面相抵触的。消费历史,就是清除掉历史的权威,而换之以消费的权威。消费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中,确切地说,是一种“游戏”的别名。通过消费(游戏),消费者体验了游戏本能的快感,释放了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消耗了闲暇的时间,最终满足了暂时的生理或心理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消费成为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的手段,就如同笑的意义是空无所有一样,[5](P60)消费的意义也在于无意义的消耗——一种游戏,“在一个项和另一个项之间、在符号和另一个符号之间‘玩耍’其个性。在符号之间,没有矛盾,就像孩子与其影像之间没有矛盾一样,也没有排斥性的对立:秩序化的勾结和蕴涵”。[3] (P226)这种消费(游戏)瓦解一切确定不变的、同一的东西。历史的同一性、确定性、严肃性,正是这种消费(游戏)所首先要瓦解的对象。“消费者受到一种模型‘游戏’和其选择的规定,就是说受到他在此游戏中的组合蕴涵的规定。正是在此意义上消费是游戏式的,而消费游戏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3] (P227)中国当下正进入消费时代,影视的历史消费题材的转向,正反映了消费游戏历史的真实。在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中,赵姬变成了秦始皇的母亲,还当上了吕不韦的情人。饰演赵姬的女演员,袒胸露乳、性感十足,活跃于各色男人之间,极尽“肉欲”之能事,历史仿佛变成了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游戏。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人们对于情感趣味的追逐远远超出了对史实的精确要求,徐志摩、梁思成与林徽音的三角关系,一个诗人与三个女人的故事,现代流行都市小说中的香艳奇遇,一时间都借历史真实的名义集结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即使徐志摩、梁思成的后代不断提出异议的佐证,也丝毫不能改变观众对历史就是如此的认同……类似的历史影视题材比比皆是,观众真的在寻找历史真实么?更确切的答案也许是——观众在寻找一种消费游戏的“真实”肯定,为当下的消费寻找历史就是如此的意义肯定。
现实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受着现实社会的“意义”、“价值”、“道德”之类的限制,要进行肆无忌惮的游戏,就要首先在理念上解除这些观念上的重压,而历史消费主义所虚拟的供给消费的“历史真实”正可以达到这种虚拟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是短暂的,在此之后,接受者很快就又会进入空虚、虚无的循环,因为历史在消费中被“反掉”,而恰恰是历史铸成了我们生命的真实感、存在的具体感。虚无与真实在消费中易位。“反历史”源于对历史的“游戏”,“游戏”提供了一种“反历史”的策略。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历史的——当然,这个历史是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作为传统的历史与作为正史的历史。“反历史”是在反一种确定无疑的历史潮流,欲确立的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新的权威。这种新的消费权威,是“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3] (P90)这种消费主义符号秩序,是购物的秩序,是消闲的秩序,是游戏的秩序,也是金钱本位的秩序。商品社会消费主义思潮是人自身物化的一种极端表现,人自身开始由被物质的商品控制,发展到被代表物质性商品的符号所控制。人们在进行许多消费之时,所意识到的不是对自身发展的满足,不是对物质商品使用价值的汲取,而是对所消费的物质性商品在整个商品社会符号秩序中所代表的地位秩序的沉迷。“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6] (P147)在对待历史的符号游戏中,迷失自我的人们,不再需要在历史中体味自我存在的历史价值,而是被消费符号所操纵,按照消费的意图消费一切——从物质到精神,从他人到自我,没有终极的指向,只有过程的消耗。历史消费主义所代表的消费主义权威意义正是在这种“反历史”中体现无疑。
“配方”、“怀旧”、“噱头”、“小历史”、“游戏”、“反历史”……甚至还可以归纳出更多的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文化模式。但无论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走着怎样的路线,始终不变的是“消解—确立”模式。在这种抽象中,虽然呈现更多的是“消解”,但隐藏在背后的“确立”及所要“确立”的东西更耐人寻味。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只是一面镜子,它关联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刻的矛盾,而这些深刻矛盾又关联着不同时代的利益人群,这些利益人群又会推波助澜,使这种矛盾深化,从而走向历史的辩证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