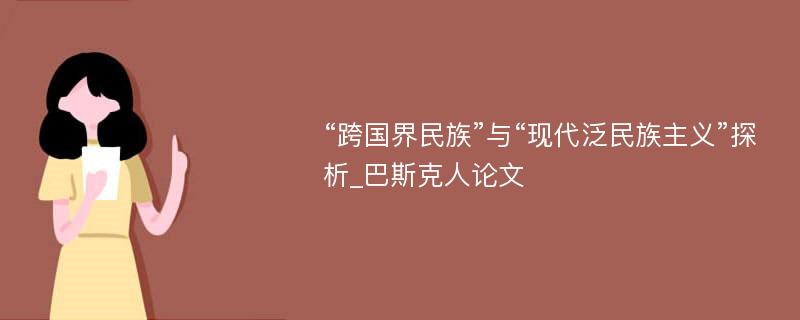
“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民族研究界及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中,“跨界民族”似乎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没有人对它产生疑问。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跨界民族”说是不能成立的。在理论上,“跨界民族”说有概念不清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它经不起民族现实状况的检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易于被现代泛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不利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巩固和地区安全。在现代泛民族主义者试图重建“历史民族”的政治统一与独立建国的活动中,“跨界民族”说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否定“跨界民族”说,代之以正确的概念——“跨界人民”,不仅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一、“民族”与“跨界民族”
国人现已习以为常的“跨界民族”说,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汉语“民族”一词的概念及使用情况谈起。
古代汉语中没有“民族”一词。据专家考证,此词是近代从日语中引进的,(注:参见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并且与西方语言如英语nation的概念是一致的。在实际使用中,远的不说,从1905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起,国人皆知的“民族主义”之“民族”就是nation之义,此义一直沿用至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除极少数台独分子外,皆知“中华民族”之所指,对它的概念与内涵确认无疑。因此,汉语“民族”一词具有英语nation的含义,当无争议。那么,在西方人的语言和概念中,nation是什么意思呢?
《牛津辞典》(1976年第6 版)的解释是:“居住在有固定边界约束的一块领土上,在一个政府之下形成一个社会,具有共同血统、语言、历史等主要特征的人口众多的人民(eole)。”
《麦克米伦当代辞典》(1979年纽约——伦敦版)的解释是:“占有一块固定领土,在一种政治制度下团结起来的具有共同的族源(ethnic origin)和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人民(eole)。”
《插图本西班牙语大辞典Vox》的解释是:“领土、起源、历史、 文化、习惯或语言同一的具有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意识的人们的自然社会。”
斯大林的著名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比较一下上述定义,虽然措词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强调了“nation”的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而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正是“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把英语中的nation译为“国家”或“国民”是适当的,而译为“民族”则不甚达意。
确定了汉语“民族”的前述概念,“跨界民族”说也就不能成立了。“跨界民族”,有的学者亦称“跨境民族”,(注:赵廷光、刘达成:《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界”和“境”是指“国界”和“国境”,二者是有区别的,但都与国家领土相联系。外国语言中也有“跨界”的概念,如英语transnational 就是“超越国界”(即“跨界”)的意思。根据汉语“民族”有nation之义,若把“跨界民族”译为transnational nation,这就令人费解了, 因为nation意义上的“民族”不可能、也不允许是“跨界的”。 也许有的论者会说,“跨界民族”之“民族”不是英语nation的概念,而是其他人们共同体。但这种争辩是无力的。汉语“民族”一词最早产生的时候,完全是与nation一致的,而且至今仍保留这种一致,并经常被运用。既如此,“跨界民族”就是一个有问题、有争议的术语,至少是一个容易产生问题和引起争议的术语。
证明了“民族”的nation之义而否定“跨界民族”说之后,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概念的困扰, 这就是“民族”还具有英语中的nationality之义。什么是nationality呢?
在欧洲人的语言和观念中,nationality与nation 都是一个常用的人们共同体概念。早在19世纪,欧洲人就对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认为后者比前者所指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如有人说:“我的共同体是一个nation,你的共同体是一个nationality。”(注: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Wanshington-Camb ridge,1972,.4.)这种层次差别在哪里呢?西欧的“民族—国家”过程表明,nation指的是有自己统一国家的人民,而nationality 则是指没有建立或失去独立国家形式的人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承认这两类人们共同体的区别,因为人类社会的民族发展过程产生了这种区别。
关于nationality的政治前途, 早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认为,它有独立建国的权利和可能性;共和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则认为,它可以与其他nation一起建立共同的国家,而非一定走向独立。(注:参见Jordi Solé Tura,Nacionalidades y Nacionalismos en Esafia:Autonomias,Federalismo y Autodeterminación,caitulo 1,1985,Editonal Aliana,Esana。)实践表明,后一种认识是正确的,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建立多民族的主权国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并且,随着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关于nation和nationality 的层次目前已抛弃了传统的解释。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内部关系中,不再分谁是nation , 谁是nationality,而是说大家都是nationality,大家共同构成一个nation。例如1978年西班牙宪法就认为,西班牙这个nation 是由不同的nationalities组成的,各个nationality都有权利实行自治, 都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统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建立在对不同的nationalities 的承认基础之上的,也认为“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是由56个民族(nationalities)包括汉民族组成的。应当说, 这是人类社会在民族关系与民族政治理论上取得的一大突破性成果,它否定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唯一真理的教条,这一教条认为,凡是不同的人民,都有权利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民族,进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当然,世界上现有许多国家不承认国内有不同的nationalities,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上存在nationalities。所谓nationality, 它与nation一样,也是一种具有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的人们共同体, 只不过这种统一性与一体性在现实中不是以国家形式,而是以某种内结构性的(西班牙文为inestructural )政治单位如自治区的形式来体现的。当然,由于在同一主权国家内存在民族杂居的情况,nationality 的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着部分成员和部分地区的分化。但是,这种部分分化与“跨界”毫无关系,在同一国家内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同一国家内,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政治机制保证每个nationality的同一性。因此, 作为一种存在于现代主权国家内部的内结构性的政治—地域共同体,nationality同样具有不可跨界性。 法国和西班牙两边的巴斯克人都不可能再视双方为一个整体。有此想法的只是一些泛巴斯克主义者,他们认为,法、西两国的巴斯克人仍是同一个民族,并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不能达此目的,也应组成一个联盟。 (注:参见 Juan Pablo Fusi, El Pais Vasco:Pluralismo y Nacion alidad,Editorial Alianza,Madrid,1990。)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我国有的论者认为, 把“民族”一词与nation或nationality对应起来是不对的。他们说,前者是指国家,后者是指国籍,并建议把“民族”与西方流行的术语ethnicgrou对应起来。 (注:参见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商讨:
第一,在西方世界,nation不仅具有“国家”的概念,也具有“人们共同体”的概念。当指人们共同体时,应有相应的汉语来表述,而不可一概理解为“国家”。如前文所引的著作Nations and States,若译为《国家与国家》,就很难理解了。西班牙学术界对nation一词的使用也可证明,它不只具有“国家”的概念。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先生认为:“1930年的情况如同现在一样,不仅要解决西班牙人组织成一个君主制或共和制国家(estado,同英语state)的能力问题, 而且要解决西班牙人组织成为国民(nación)的能力问题。”(注: 朱伦译:《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在指称人们共同体时,国内现通常将nation译为“民族”。有的学者主张将其译为“国族”,(注: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示它的本质特征。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国民”。(注:参见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载《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这一译名比较普遍, 如我们常说“国民生产”、“国民收入”等。一个“国”字,恰如其分地界定了nation这种人们共同体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的政治本质规定。
第二,nationality也不只具有“国籍”的概念, 还具有“人们共同体”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前述作者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讲得非常明白。他在自己的论述中特意指出, citizenshi指“国籍”,以此提醒读者,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的nationality 应作“人们共同体”来理解,或作nation属性来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欧洲人至今仍使用nationality的概念指称国内的少数“民族”, 如西班牙人便是如此。美洲国家的各族土著印第安人也使用nationality 来自称,并要求主体社会及国家承认这一点。因此, 我国长期用“民族”与nationality对应,并无什么不妥,而且应当坚持下去,因为这是合乎民族政治的现实要求的。 西方一些国家借用本是文化人类学学科用语的ethnic grou来界定国内不同的人们共同体, 目的恰恰在于从政治上否定不同的nationalities的存在。有些群体可以用ethnic grou来界定;有些群体则不能。如西班牙的各类外来移民可以接受ethnic grou;而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等就不能接受。
第三,主张“民族”与ethnic grou概念相对应,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学科的界限。“民族”是政治学上的“人们共同体”;ethnic grou是文化人类学上的“人们群体”,二者是有区别的。 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都是从政治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 并把它与西方的nation或nationality概念联系起来。混乱来自另一学科——“族类学”(ethnology)在我国的传播。我国最早引入这一学科时, 将其译为“人种学”或“民种学”。自蔡元培先生将其译为“民族学”并沿用下来后,(注: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84年,第3页。 )汉语“民族”一词在其使用过程中就开始发生了不应有的混乱,造成了“一女二嫁”的局面。作为ethnology 研究对象的ethnic grou,本可以用不同的汉语词汇来表述,不一定非使用“民族”一词不可。现常见的译名有“族群”、“族体”、“族团”、“族类”等。如果我们承认西方语言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在指称人们共同体时的差别(人类社会中也的确存在这种差别),我们就不应仅以“民族”一词笼统称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汉语中的“民族”与英语中的ethnic grou对应起来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按自己的观点把西方一些国家中的某些ethnic grou看成是“民族”,但就ethnic grou的词义来说,它不是汉语“民族”的意思。国外使用ethnic grou这个词,正是为了从形式上到内容上与nationality相区别。退一步说, 即使我们从文化人类学或族类学的角度看问题,像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译为“跨界族群”比较恰当)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ethnic grou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所指范围可大可小。汉族可以分为不同的ethnic grou;拉美各国的移民在美国可以统称为一个ethnic grou;拉美各国内部的居民亦可分为几十种、上百种ethnic grous, 这完全取决于研究者以什么标准来划分。对于没有政治含义的ethnic grou这一概念,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跨界”来修饰,这未免有点不伦不类。也许有人认为,当代国家中的ethnic grous亦有政治追求, 国外现也承认了ethnic grous 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 但我们应该看到, ethnic grou的政治行为与nationality 的政治行为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
前者不可能涉及领土自治的问题。
美洲土著人不接受ethnicgrous,而力争nationalities的称谓,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当人们用“跨界”这一概念来修饰某种人们共同体时,目的在于指出这个共同体有怎样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而在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政治和领土分野。国际上习惯用“跨界人民”(eole across the boundaries 或 transnational eole)来界定这类共同体。
“人民”(eole)是一个中性概念,是历史学术语。它可以用来指称一些不宜用ethnic grou 或 nation 和 nationality 来指称的文化与地域群体,如“阿拉伯人民”、“伊比利亚人民”、“蒙古人民”、“犹太人民”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此处不妨引述西班牙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先生的一段论述和他的基本观点:“西班牙作为人民(ueblo )的分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重于它作为国民 (nacion)的分量,而作为国民的分量又重于它作为国家(estado)的分量。”(注:朱伦译:《西班牙现代史论》,第362页。 )作者对西班牙“人民”的分析是从种族、语言和文化上进行的;而对西班牙“国民”的分析则主要是从国家、领土和政治的角度进行的。无论是作为“人民”还是作为“国民”,又都包括不同的民族(nacionalidades)。(注:参见朱伦译:《西班牙现代史论》,第14~17章。)“人民”与“国民”或“民族”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一定具有后者必备的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由此,“跨界人民”也就有了具体的学术含义和实际意义。“人民”者,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同一个ethnic grou;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同一个nation或nationality。但是,由于汉语中存在着“民族”与eole对应的用法, 于是就有了“跨界民族”的说法,实际上应把它作“跨界人民”来理解。
汉语是一种词汇极其丰富的语言。前述nation、nationality 、ethnic grou和eole等四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完全可以有相应的汉语词汇与之对应。这四种人们共同体是具有不同的特征,按照学术用语一词一义的要求,我们应赋予它们不同的符号,不能都以“民族”冠之。笔者在上文中分别以“国民”、“民族”、“族群”和“人民”与之对应,并对它们的本质特征作出初步界定,旨在论述汉语“跨界民族”这一概念的不确切性,以及可能由此而产生的歧义与危害。至于这种对应是否规范和贴切,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无论如何,汉语“民族”概念的混乱这个在本世纪初产生的问题,到本世纪末应该加以解决,以便与国际学术界的用法相统一。
二、“跨界人民”、“历史民族”与“现代泛民族主义”
“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是具有经济、语言、 文化等共同性的人民(eole)在实现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后形成的利益单位。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人民”都能成为“民族”的。在相邻的人民实现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些弱小的“人民”不可避免地或被肢解,或被分化,由此形成了“跨界人民”。“跨界人民”不是同一个民族。但从文化和历史方面看,“跨界人民”又曾是同一个民族。 对于这样一种人们共同体, 国外有人用“历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ity)称之;(注:西班牙从官方到学界的普遍用语。)也有人用“文化民族”(cultural nation)称之。 (注:参见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4。)笔者倾向于用“历史民族”来界定。所谓“历史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具有政治统一性或最终未形成统一的“国民—国家”(注:鉴于nation与nationality 的差别,笔者主张把nation—state译为“国民—国家”;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亦可称“国民主义”。)(nation—state),而在现实中被分成了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跨界人民”。 如中世纪时代的加泰罗尼亚人,最终未能像卡斯蒂利亚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一样建立起自己的“国民—国家”,而是被分解了,成为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少数民族,现在以“跨界人民”的形式存在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跨界人民”与“历史民族”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历史民族”是“跨界人民”的过去形式,而“跨界人民”则是“历史民族”的现时状态。从“历史民族”到“跨界人民”,其间有一个分化过程,各部分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历史民族”的分化归因于民族发展不平衡;归因于强势民族的国民—国家运动。所谓国民—国家运动,从政治上看就是已凝聚为民族(nationality)的人民(eole)独立建国的运动。 每个民族都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并非每一个民族都能达到这种愿望,只有少数强势民族能够把别人的地盘纳入本国的版图,弱小民族则无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或被包裹在某一强势民族的国家之中;或被相邻的某个或几个强势民族分化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部分。“历史民族”的分化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
1.分割或肢解。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对某个民族进行分化。如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更准确地说,是西班牙的主体民族卡斯蒂利亚人)南、北对进,毫不留情地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历史地域一部分归入法国的版图,一部分归入西班牙的领土。
2.切割。即由某一民族对另一民族进行部分分化。例如,英格兰人的势力侵入爱尔兰人的地域,结果把北爱尔兰地区从爱尔兰切割出来,使之成为英国的领土。
3.进占或迁移。即由于某一民族的部分成员迁居他民族地域而发生的自行分化。如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是从阿尔巴尼亚迁移过去的,而不是由于塞尔维亚人切割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固有领土。尽管不是塞尔维亚人主动去分化阿尔巴尼亚人,但结果这部分自行分化出来的阿尔巴尼亚人还是被塞尔维亚人包裹在自己的国家中了。
4.殖民混血。这在拉丁美洲比较普遍。其特征是欧洲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人混血后形成一批新兴的民族,并建立不同的国家,导致一些未被混血的土著民族发生分化。例如,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中部,西班牙移民的后裔与部分克丘亚人混血,形成厄瓜多尔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等新兴民族,并建立了三个国家,那些未被混血的克丘亚人便自然分属这三个国家。
5.殖民瓜分。这在非洲特别突出。欧洲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制造了许多与原来的民族分布不一致的人为的政治疆界。这些疆界后来又成了非洲各独立国的国界,由此造成了许多非洲民族的分化。非洲跨界人民的产生表面上看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实际上还是当地强势民族的核心作用造成的。无论是历史上作为欧洲人的殖民地,还是后来作为独立的国家,既然是一个政治单位,就总该有一个或几个较为强大的民族作基础。当代非洲国家的民族结构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核心民族的国家只是少数。(注:参见李毅夫等:《世界各国民族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从道义上说,除个别情形外,“历史民族”的分化是不公正的,但这种不公正已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民族”之间的分野愈来愈大。考察一下由“历史民族”演化而来的当今世界的“跨界人民”,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其主要表现是各自不断接受了所在国家的主体民族的影响,彼此之间的同一性不断减少,共同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他们已经或正在向着不同民族的方向演化。基于共同的社会经济生活而形成的政治统一性和领土一体性在“跨界人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跨界人民”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某些共性特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化等,也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活而发生质变。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人,其语言、文化已大不相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更多地接受了卡斯蒂利亚语言、文化的影响;而法国的巴斯克人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兰西语言、文化的熏陶。这种影响或熏陶甚至导致了人们的性格的变化。西班牙人的性格是“火多于水”,在行动上常受理想主义的支配,时常勉为其难地为所不能为。(注:参见朱伦译:《西班牙现代史论》,上卷,第2、14章;下卷,第3~6章。 )在西班牙人的影响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不能不表现出西班牙人的性格。50年代末,在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中产生了恐怖主义组织“埃斯卡迪与自由”(ETA)。该组织起初试图以暴力手段使法、 西两国的巴斯克人建立统一的独立国家,受挫后它又转入地下搞暗杀,坚持不放弃极端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注:参见Salvador Giner Esafia,Sociedad y Politica ,caítulo 12,Esasa -Cale,Madrid,1990。)然而,受法兰西社会、文化影响的法国巴斯克人已变得现实主义多而理想主义少。他们不仅本身缺乏西班牙巴斯克人的那种政治激情,而且对来自另一国度的“同胞”的鼓动亦很少响应,至多在对方遭到缉捕时给予一点亲戚般的同情和庇护。法国的巴斯克人不为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动,原因何在呢?答案只能是:法、西两国的巴斯克人已不再是同一个民族,他们已经分化为两个民族了。
民族分化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人们对待民族分化的态度却不一样。有一种态度是不承认或不甘心接受民族分化现象,并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力图再造“跨界人民”的统一。对这种思想、态度和行动,可称之为“现代泛民族主义”。所谓“现代泛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以“跨界人民”为基础、以建立新的“国民—国家”为目标的非现实的和反历史的政治民族主义。
“现代泛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泛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历史上的泛民族主义首推19世纪初产生于奥地利、19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于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其具体内容是“梦想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此外,还有19 世纪中叶以后产生的泛伊斯兰主义,它“主张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再后来,到20世纪初, 面对巴尔干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青年土耳其党”提出了泛突厥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之下的、包括从博斯普鲁斯到阿尔泰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实际上, 这种旧泛民族主义还可追溯到更早,至少可追溯到16世纪初欧洲人向海外殖民的时代。无论是英吉利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曾把美洲殖民地人民视为自己的臣民,以至后来竭尽全力地阻止美国和拉美西班牙语各国的民族独立。
关于历史上的泛民族主义的本质,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下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3页。 )历史上的泛民族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没有“民族”的基础,它所维护的是“帝国”这种过时的民族政治形式。泛斯拉夫主义者所说的“斯拉夫人”并非某个民族实体,而是包括十几个民族在内,其语言、文化同源,体质特征相近,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可以走向政治统一的同一个民族。在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历史潮流推动下,他们纷纷走上了独立建国的道路。泛伊斯兰主义以宗教文化和历史渊源相同为旗帜,但最终未能阻止阿拉伯世界建立二十多个国家。泛突厥主义也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阻止巴尔干各族人民的独立。
与历史上的泛民族主义不同,现代泛民族主义有“历史民族”作基础。目前,这种泛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泛民族主义问题在各种民族问题中显得特别突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前文提到的西班牙恐怖主义组织“埃斯卡迪与自由”一直坚持泛巴斯克主义,主张法、西两国的巴斯克人统一,建立埃斯卡迪国。(注:参见Juan Pablo Fusi,El Pa ís Vasco:Pluralismo y Nacionalidad。 )在南美洲古代印加帝国的后裔——克丘亚人中间,存在着以印加国为旗号,试图统一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克丘亚人重建印加国的泛民族主义活动。(注:参见朱伦、马莉:《印第安世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目前成为世界热点问题的北爱尔兰问题、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也都因为带有泛民族主义的性质而变得十分棘手。在中亚、南亚以及非洲,也存在着泛民族主义的组织与活动。所有这些泛民族主义的组织与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借用现代国际政治所承认的民族权利原则,追求“跨界人民”的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然而,现代国际政治秩序同样承认现代国家主权原则。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以现有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以破坏现有主权国家的界线为代价的现代泛民族主义不仅要遭到有关主权国家的反对,而且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当今世界的民族与国家格局使现代泛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只能被看成是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的一个例外。
现代泛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是自19世纪以来席卷世界五大洲的“国民—国家”运动。因此,怎样正确地看待“国民—国家”运动,便成了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泛民族主义的关键问题。归根到底,“国民—国家”运动是大民族的运动,或者说是以大民族为核心的现代主权国家运动,而不是单纯以民族为界线的国家的建立过程。由于大民族的发展使小民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化,致使现代主权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被分化的“历史民族”或曰“跨界人民”如想再造统一,势必要对使自己分化的强势民族进行分化,而这一点是任何强势民族绝对不能接受的。“国民—国家”运动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现在的时代已不是增生新国家的时代,而是以现有国家为基础,各民族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民族繁荣和民族差别继续存在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伴随着政治分离。现代泛民族主义者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追求“跨界人民”的政治统一的同时,妄图对现代主权国家进行政治分离,难免不归于失败。
从“跨界人民”的内部来看,现代泛民族主义亦无多大市场,因为“跨界人民”业已分化,他们不再是一个整体。
如果从理论上寻找现代泛民族主义失败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指出,它在有关民族和民族权利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它像游侠骑士唐吉诃德那样把自己的瘦马当成“冲锋陷阵”的坐骑,把客栈当成敌堡,焉能不失败、不碰壁?“跨界人民”不是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现代主权国家也不是具有民族监狱性质的帝国。游侠骑士最终被关进了铁笼子。但关住泛民族主义者的铁笼子是什么呢?理论问题还要靠理论来解决。现代泛民族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是人们对“跨界人民”的错误认识。因此,准确界定“跨界人民”这一概念,指出对于“跨界人民”的认识上的误区,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现代泛民族主义的虚幻性和危害性的认识,从而使现代泛民族主义失去市场。当然,如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泛民族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渐趋消失一样,现代泛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从人们的观念中消除的。目前,影响人们清醒认识现代泛民族主义之虚幻性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对什么是“民族”的认识落后于民族分化的现实。因此,从理论上界定“跨界人民”已不再是同一个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地克服现代泛民族主义思想,使泛民族主义活动失去群众基础和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