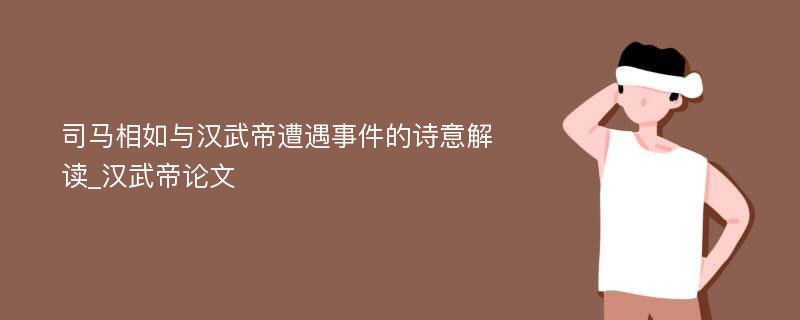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事件的诗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相如论文,诗学论文,汉武帝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4)03-0082-05
汉大赋奠基者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遭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广为知晓的事件。但这一历史事件迄今还只是在“知人论世”的最肤浅的层次上著名于世的,在众多的文学史、汉赋汉文的研究著作中,这一事件仅作为司马相如的生平之重要部分而被学者重复地叙述。它的基本框架(司马相如在梁孝王处写《子虚赋》,汉武帝读后,叹恨不能与作者同时,适逢相如老乡狗监杨得意在旁,遂荐相如。相如见汉武帝而作《上林赋》,任为郎)被从这一著述搬到那一著述。因此,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的事件与其说是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如说是人们感觉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反复地重述这一事件并没有产生解构主义意义上的“互文性”,最新的文本与以前的叙事文本相较并无意义的层进,这样的重述使事件变得不平凡起来,但事件被感觉重要者始终停留在感觉开始的地方。就是说,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是重要的,而且只对相如来说是重要的(在以汉武帝为主旨的著述中这一事件通常不会被提及)虽然在学术界成为普遍的感觉,但其重要性究竟为何一直未被真正提问。至于汉武帝作为遭遇之文学接受主体一方面被忽略,也使仅有的对事件的文学史立场的关注处于在作家神圣原则下的盲区。
当我们说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遭遇这一重要性未被真正提问时,意味着我们并不把这次遭遇理解为一次单纯的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由于关涉着汉代文化、汉代诗学的一次重大转向,其重要性比它表面被感觉到的那种重要性要大得多。
本文追问:二者在西汉初期相遭遇的历史事件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在何种层面上它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文化、一代诗学和一代文学,它是在历史的延续性的惯性驱使下创建着民族的诗性,还是以非连续性的方式参与着民族性格的命名。以这样的追问,笔者希望能赋予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一个具有空间性结构的坚实地基。
一、事件发生的主体意向性解读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围绕赋文本相遭遇的历史事件,从其最显豁的性质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的主动式遭遇,尤其是遭遇双方都具体到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此之前,这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遭遇还是不曾有过的。在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相遭遇的事件中,我们可以,也需要弄清楚,汉武帝和司马相如何以要在阅读之外,彼此寻求更进一步的遭遇。尤其是汉武帝恨不能与作者同时的意向究竟只是纯文学性的呢?还是指向着另外的超出了文学范围的东西?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究竟只是对帝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呢?还是一种寻求到文学知音之际的答谢?
首先的问题是,汉武帝何以在阅读了《子虚赋》之后如此激动难安。因为,这表明汉武帝在阅读时对作品获得了震撼性的审美感受。而当代的一般读者面对《子虚赋》这样缺乏人的个体性生存处境、徒有华丽辞藻的文本,能感到它是美的已属不易,更遑论为它的巨大的美所震撼了(注:汉大赋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知识性语言,人们之讥评汉大赋作品为“字林”、“字窟”,感受到的正是其语言的知识性。这种由赋家卖弄其同时作为文字小学专家之学问而建构出来的知识性语言,与诗性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常常是美的反面。)。汉武帝在一般读者无能为力的地方,却真实地读出了《子虚赋》的巨大的美。造成这一悖论式阅读情景的原因何在呢?说到寻找原因,在此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指责一般读者的文学修养水平比汉武帝的要低,这里的真实原因乃在于汉武帝作为一个体之文学接受主体是一个独特的人,当他阅读《子虚赋》时,他始终怀有仅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的意向。以此意向,他既不同于一般读者,甚至在汉代帝王这一群体中也属于一个具有惟一性的自我。至少在他之前的汉代帝王还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倾情于文学活动,还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违背高祖刘邦坚守的南方文学精神。
汉武帝在《子虚赋》的阅读上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阅读意向究竟指向着什么呢?
第一,作为文学主体,汉武帝的阅读心理是追新求异的,他事实上把文学的阅读也当成了一次人生的历险。这种心理是由他政治、军事上好大喜功的心理裹挟而来的,好大喜功显然不仅仅是汉武帝面对自己的文治武功伟绩时的沾沾自喜、亟欲表现的冲动,而且还是对建功立业过程中的历险期待与偏好。《子虚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诗学精神上,都正好适合武帝用来作他的文学的历险。因为,武帝此前熟悉的是骚体赋文的创作与接受,如他创作《瓠子歌》,命刘安写的《离骚经章句》。《子虚赋》这样的汉大赋因此引诱他进入的完全是一片陌生之地,其中每一块陌生的林地都既对他的阅读习惯与经验来说是一个陷阱,又同时都是对他的把阅读作为历险的心理期待的强化。与在骚体赋那里仅能获得常态的,因而也是温吞水式的愉悦不同,汉武帝在《子虚赋》中的心灵之旅不断得到的是意料之外的狂喜。
历险式的文学阅读心理是不追求文学对阅读主体的精神的升华的,它追求的是文学形式的创新带来的感官刺激,它过于迷恋外在的华丽辞藻闪烁的耀眼光芒,以致于在生命的外面就眩晕了。所以,尽管《子虚赋》的写作深度远不如《惜誓》、《鵩鸟赋》这样的骚体赋文,但汉武帝却惟独为它迷狂。
第二,汉武帝政治、军事上的好大喜功心理是汉武帝阅读《子虚赋》时的深层的、主导性的意向性结构,这一心理同时产生的是汉武帝亟欲与相如晤面的渴念。
汉武帝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实践着他弱枝强干的强国大业和开疆拓土的进取方略,他作为一个赋文学主体,则希望文学能将他的伟大事功对象化,以供他自观自娱。这样的自恋情结,难道不正是文学主体的普遍性心结吗?服从于这一普遍法则,汉武帝的希望显然是有正当的合法性依据的。
从《子虚》、《上林》的表面文字看,诸侯、帝王的狩猎、宴乐生活最终都被归列到讽谏对象一边,被批评为“大奢侈”,天子对这样的生活始乐而终悔。但是,这样的描写至少在汉代就被人理解成司马相如的一种写作策略了。扬雄在《法言·吾子》中不就说大赋的社会效用是“劝百讽一”吗?百分之九十九的“劝”和百分之一的“讽”,这个算式中的比例关系是开启汉武帝特殊的阅读意向的金钥匙。这一比例关系隐喻着赋中帝王狩猎和宴乐生活的“大奢侈”意义层之外的意义。即是被赋家称为“大奢侈”的意义所在,武帝读出的感受却是“奢侈不是奢侈”,“奢侈”实质上是他的伟大的文治武功业绩的物化形式。
《子虚》、《上林》赋的一大价值,就是它们在汉代首次以歌颂的基调,把君王的伟大事功和日常生活联为一体,赋予文学以对象化形式,实现了帝王对自身生活的审美性自观,为汉代帝王创构了一种富丽堂皇的文学庆典。汉大赋这样的庆典因为一开始是帝王的,所以它最终一定会是国家的,这一点,在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那里被勾勒得既鲜明又完满。它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在绝大多数接受主体那里,它将难被青睐。毕竟,更多的人不是帝王,他们的生活与国家重大政治内容也基本不沾边。
司马相如创作《子虑》、《上林》二赋的心理意向性若给予价值评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子虚》、《上林》的夸饰意向性客观上与汉武帝多欲好利的心理欲求是重合的,这种意向性重合上升为帝国时代的整体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最终共有“非常”的英雄人格和价值渴求。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一文中以天子使者的口吻答蜀中父老对汉军数年征讨西南的责难时说: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非常”在“黎民”的眼中是他们恐怖的原野,只会令他们产生某种痛感,但对于伟大的君王、英勇的使者而言,“非常”的一切陷阱、陌生都不过是确证他们的“非常”生命、智能的绝佳战场,都不过是崇高的对象和使他们自身生成为崇高者的推动力。非常,即崇高本身。
司马相如以天子的代言人说: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悦云尔哉!
他宣告伟大的君王既不会拘守成法,也不会媚俗,他所追求的是以响彻宇宙、绵延于历史的宏大声音,为天下立法:
(贤君)必将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
贤君的胸怀因此“兼容并包”,能统各种异态文化于区内,所运思者亦以“参天贰地”为主要对象。其胸怀与思,均是涵摄宇宙万象,返虚入浑式的。
把司马相如的这段话与他的“赋家之心,苞括宇宙,综览人物”[1]的赋论相比较,可知后者可归类于前者“崇论宏议,创业垂统”的观点。后一观点虽晚于《子虚赋》产生,但却因与司马相如的“赋家之心”重合而可一并用来阐释其创作《子虚赋》的心理意向性。因此,在与汉武帝谋面之前,司马相如就已经与汉武帝心灵相通。
总之,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以大赋为中介的遭遇是两个“好大喜功”之人的历史交接,是渴求崇高、实践伟业并热衷于自我表现的两个天才的人生轨道的交叉,是汉代时代精神的政治代表与文学代表的亲密交往,是一个自恋的文学接受主体对一个同样自恋的文学创作主体的发现。因此,对司马相如以赋取悦君王的心理意向的第二种价值判断,即认为相如的以赋悦君是功利的、庸俗的、丧失文学家品格的,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犹如当时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守望着他们创造并表现的英雄时代。
二、遭遇与诗学转向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相遭遇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汉代诗学的转向。这一巨大的转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汉赋文学的语言、句式的改变。《子虚赋》、《上林赋》以去掉骚体赋的“兮”(些)字而令整篇句式与骚体赋相区别。就当时的文学背景来看,“兮”(些)字句属于南方诗赋,而无“兮”(些)字句通常属于北方诗赋。因此,《子虚》、《上林》的去掉“兮”(些)字在诗学的转向上至少有两层意思:首先,由骚体赋转向汉大赋写照的是汉代政治价值中枢的中心转移,由此转移直接带来的是汉代文化格局的重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反拨的是此前的黄老治术。黄老从总体上讲是南方的文化,充满自由、散漫、无为、自在和神秘主义的思想话语。汉初刘邦喜楚憎儒,是导致汉代开国选择黄老以为治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儒术,则是北方的文化,充满规训、惩罚、秩序、理性和伦理主义精神。黄老文化对应着汉初的大诸侯、小天下的政治格局,儒术之兴,则意在小诸侯而大中央。从黄老转向儒术,同时也就是汉代文化中心从南方转向北方。在政治、文化之重心从南向北的转移之际,汉大赋句式之去掉“兮”(些)这一南方文学话语标志,当然是被前者裹挟所致。
其次,“兮”(些)字句式在汉大赋文本中的消失,带走的是汉代骚赋文本中最为南方化的深层灵魂的诗性精神。“兮”(些)字是南方诗性的语言标志,是南方方言,而“方言是每一成熟语言的神秘源泉,一种语言的精神中所蕴涵着的那些东西,都是从方言那里来的”[2]。《吕氏春秋·音初》以涂山氏之女所作“候人兮猗”歌为“南音之始”,以有娀氏二佚女所作“燕燕于飞”为“北音”之始,比较此“南音”“北音”,内容均为女子怀念爱人,惟句式上“兮猗”确属南方独有。所以,丢掉了“兮”(些)字成为汉赋之诗学精神向北倾斜的历史拐点。因为,“兮”(些)比较其他南方方言来说,是最鲜明也是最本己的南方诗学旗帜。任何本文只要被带上这“兮”(些)字,就意味着它被打上了南方诗学鲜明的烙印。而一旦文本丢掉了“兮”(些)字,即使它仍然是南方的,但它的南方身份也一下子变得晦暗不明,模糊不清起来。汉大赋的南方诗性蚀没之处,也就是汉赋向北方诗性倾斜之处。中国北方文化语境中的诗歌虽然也有类似于“兮”(些)这样的虚词,但这些语气虚词一则更为变动不居,不能固定为一个两个虚词以作为代表,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之“矣”,“今我来思”之“思”,虚词两句一变;二则北方诗赋的语气虚词并不像在楚歌诗赋中那样固定化为相对不变的句式。
赋文主要以实词命名“针”(箴)和引说缝针隐喻的治术之理。汉大赋自《子虚》、《上林》二赋弃“兮”(些)字句不用,因此是把此前空灵缥缈的南方诗学,转到浊实坚硬的北方诗学。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汉大赋写的弘大时空,基本上是由物的填满(注:万光治在《汉赋通论》中说:扬雄《蜀都赋》铺陈树木名称近二十种,水草名称十余种,禽鸟名称十种,水兽名称十五种。此种写法,自《上林赋》以来,成为汉大赋作家通用的模式。由此可见物之填塞之为赋家所热衷,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中,物之实挤走了情之虚。)来作的叙事。以汉大赋去掉“兮”(些)字句为标志的汉赋领域的诗学转向,一方面拆除了楚辞、骚赋原有的虚实关系,另一方面在向北方诗学倾斜的这一次转向中又并未将北方诗学原有的虚实相生结构拿过来,造成的结果,就是汉大赋走向物化极端。此处所谓“物化”,指的是文本时空被美石、奇兽、珍树、骏马、妙乐和丽人等“物”完全塞满,几乎没有给人的情灵留下多少呼吸舒卷的空间。此正是汉大赋在今日读来难以令人产生美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这是倾诉个体性之人的哀情之诗学向国家、权力诗语的转向。汉初的骚体赋文语境应是由贾谊贬谪长沙时发现屈原其人、其文,并立即摹仿屈骚创作《惜誓》等作品而始创构出来的(注:万光治先生所辑《汉赋今存篇目》,贾谊之前赋家仅有虞公、陆贾。但二人作品《丽人歌赋》和《孟春赋》均已佚。所以,汉代的赋家,实自贾谊始。)。贾谊的创作忠实于楚辞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惜誓》、《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等作品都是赋家发自个体性人生处境的哀情诉说。这种创作倾向在汉初蔓延为骚体赋文的普遍的、主要的语境。除了枚乘的《七发》是一个例外之外,像庄忌的《哀时命》、武帝的《李夫人赋》、东方朔的《七谏》和《客难》,都无一不是赋家切己的生命私语。这些作品要么宣言着文人对沦丧的政治伦理原则的诉求(《客难》),要么在死亡的逼迫下守望自己危若游丝的生命。(《鵩鸟赋》),要么寄此岸之深爱至彼域亡魂(《李夫人赋》),要么拒绝着屈原式的诗人之死。
骚体赋家所代表之汉初诗学精神,因此是反思、恐惧、焦虑、愤怨和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悲剧精神,对于赋家来说,骚体赋在总体上被吟唱为汉代文人的命运急剧下沉到极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战国之崇高地位,至汉代沦落为俳优之列)的无尽挽歌。
《子虚》、《上林》创起的汉大赋展现的则是另一番诗学境象。汉大赋对人和物的个体性以及作为文学形象的掏空、取消,都表明汉大赋纯然是一种文学符号化的天下,国家之政治权力话语。对文人自我生命的沉思完全让位于对人的外在事功的夸饰和炫耀。文人对自身生命的镜映与投射终止,代之而起的是汉大赋在好大喜功的时代心理躁动下掀起的帝王话语的喧哗与狂欢。可以总括地说,从个体转向群体,从私人转向公共,从文人转向帝王,从批判转向颂美,从哀诉转向欢呼,这就是司马相如与武帝遭遇之历史事件给汉代诗学带来巨大转向的具体内涵。
上述汉赋诗学的转向,如按文学自身的艺术与美的尺度来衡量,它的负面性远大于它的正面性,因为屈骚所开启的是文学自觉的审美创作道路,本来,如果两汉对这一道路坚执并拓展,则两汉即可成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然而,汉大赋之经由汉武帝的推崇而迅速成为汉代新的代表性的赋文范式,这就掐断了骚体赋所秉承的楚骚的文学自觉精神,汉代诗学的向北方倾斜,结果使它在很大程度上重归先秦那种文学不自觉的诗学道路,中国文学审美自觉的进程被延宕,至魏晋南北朝才重见曙光。
三、结论
司马相如遭遇汉武帝事件对于汉代诗学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
首先,这次遭遇重构了汉代诗学在赋文领域里的格局,为汉代寻找到了自身的代表性的文学范式。事件之后,虽然文人继续在写骚体赋,但汉代文学的重心已然转移到汉大赋的创作与欣赏了。汉代文学因此与战国之屈骚划清了界限,有了自身独立的家园。
其次,事件为汉代诗学带来了崇高、神圣和英雄崇拜等诗意内涵,这些构成了汉代诗学精神中最基本、也是主要的部分。这种向外扩张、大肆铺陈、炫耀巨美的诗学气性使汉代在整个中国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世界诗学史上,也只有古罗马的诗学风格与之差堪相近。
其次,汉大赋一方面延宕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它却确立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语言美的价值的认可,如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就为魏晋文论的自觉扫清了思想的迷雾。
最后,事件对中国古代作家的身份是一个宿命般的隐喻,指涉的是古代作家总是以政治主体——文学主体身份在场的,而且在作家的自我意识里,政治总是他的第一生命。汉大赋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无非是在赋家这样的生命结构的功能驱动下,总体上成了一种帝王文学罢了。由此生发出去,人们因此也可以把这一事件阐释为君臣之间的知遇与被知遇。
有了上述重要性,汉大赋、司马相如和汉武帝便都在诗学的视界内步入永恒。
收稿日期:2003-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