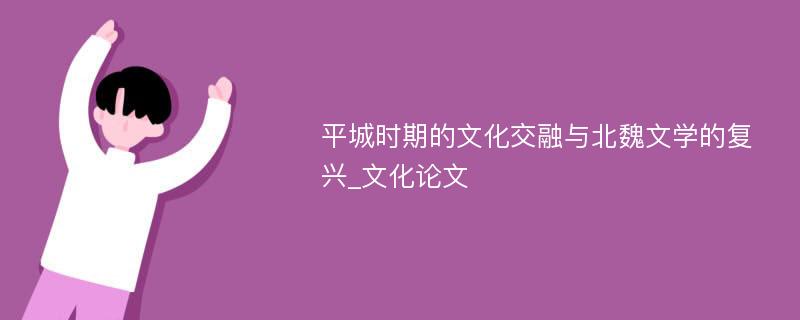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时期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3-0137-05 天兴元年(402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拓跋氏迁都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战乱频仍,经济发展滞后。可喜的是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出现端倪,北魏经济呈现复苏景象。在文化上,北魏皇族虽固守拓跋民族相对落后的文化传统,但试图接受多种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政策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了北魏文学的复苏。目前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较少,故撰此文试论之。 一、平城时期的多种文化融合 宋代叶适云:“刘、石、符、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1]以胡变华,这是北魏初期拓跋氏推行的文化政策。到平城时期,这一政策并未改变,占主体的仍然是鲜卑因素。从统治阶层的任职情况来看,宗室贵族168人,代性贵族103人,汉族地主153人,汉族人是拓跋氏的57%,仅半数略强。若从高级文武官员的任职人数来看,宗室贵族111人,代性贵族59人,汉族地主71人,汉族仅占42%。就官员任职来说,鲜卑人占绝对的优势,而且多官居高位。在法律政策上,一直沿用严刑峻法。太武帝拓跋煮令崔浩定律时,腰斩、宫刑等酷刑比比皆是,甚至到了太和五年(481年),法律仍有“门房之诛十有六”,死刑达二百三十五条。虽经世祖拓跋焘两次、冯太后与孝文帝三次修订律例,略有改变,但主体未有太大变化。这种法律体制仍然是鲜卑贵族体系,与南朝法律迥异。但魏都平城毕竟是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贸易日滋,各种思想涌入,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北魏平城时期出现了以鲜卑为主的多种文化交融情形。 与初期对汉族文化惧怕的心理相比,平城时期北魏王朝对汉族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北魏王朝先后派遣32次使节出使南朝,南朝宋、齐先后派遣35次使节出使北魏,南北交流频繁。在行人的往来中,北魏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始元年(396年),北魏夺取后燕并州后,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兴安元年(452年),宗爱杀死太武帝后为宰相,录三省。胡三省指出:“魏盖以尚书、侍中、中秘书为三省,亦犹今以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也。”[2]在魏都平城的建设上,更能体现北魏对汉文化的渴慕。《魏书·李冲传》云:“诏曰: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3]1181-1182可知,在平城的修建中,主要参与者为蒋少游、李冲和穆亮。蒋少游曾出使南齐,“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4],蒋少游在修建明堂、太庙时肯定采纳了金陵的模式与风格。李冲与穆亮是受儒学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由他们建设的魏都平城,势必融入汉文化因子。另外,在北魏平城时期,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像崔浩、李冲、李彪和穆亮走向了北魏政治的最前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学习汉文化相关联的,平城时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在戎马倥偬之际已非常注重儒学,迁都平城始祭孔子。史称太宗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3]64。世祖拓跋焘时以皇权的威力把儒学推广到整个统治集团,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诏曰:“今制自王公己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3]97从此,胡汉高级官吏子弟一律要入太学学习儒学。拓跋焘时令州、镇长官辟举当地人士为属官,指明将卢玄等40多位大族人士召入平城,又令地方官举荐人才,大批世族人士应召入平城,使平城一时出现济济多士的局面。经过几代帝王的提倡,学业始兴,经术弥显。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平城时期颇受青睐。太祖拓跋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道教始播。太宗拓跋嗣、世祖拓跋焘亦喜好道教。太武帝拓跋焘“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3]3053。同时,接受道士寇谦之建议,以太平真君自居,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3]3053。自此,道教压倒儒佛,成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道教内部还发生了变革,陆修静“改革原始的五斗米道,使民间道教变成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称为南天师道”[5]。寇谦之则依照北方的特点,适应拓跋氏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3]3051,建立了北天师道。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使道教在世祖朝达到极盛。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平城时期也艰难地发展着。文帝在洛阳,昭成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迁都平城的同年,太祖造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极力推崇佛教。太宗、世祖亦崇佛法,佛教与儒、道一样得到健康发展。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后,以僧尼人数众多,劳动力减少为由,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年五十已下者”[3]3032,这是太武帝初次抑佛。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又下诏曰:“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3]97此次抑佛把畜养沙门的人资格限定在王公大人以上,极大地减少了僧尼数量。佛教在太武帝朝受到重创,发展势头一度减少。高宗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不久便下诏恢复佛法,佛教的发展从此不可遏制。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拓跋濬接受沙门统昙曜的建议,在京城西武州塞凿云冈石窟。北魏后期佛教寺庙达3万所,僧侣达200万人。 魏都平城是座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各种域外文化输入平城,对北魏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北史·西域传》云:“太武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6]大月氏国的琉璃技术传人北魏平城。《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欧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7]波斯的玛瑙制艺传入平城。1970年,大同市轴承厂在位于市区城南工农路(现改称迎宾东路)北侧的厂区内动土时发现一处北魏遗址,并出土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八曲银洗1件,此后该厂区陆续又出土石雕方砚1件,石雕柱础以及多件铜鎏金铺首衔环。这6件文物经后人研究是孝文帝时期从中亚细亚传入平城金银器艺。这些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汉文化一样,都对魏都平城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 由此来看,北魏平城时期各种文化输入,相互影响,给鲜卑文化带来冲击。平城时期的多文化融合,势必对其文学艺术产生很大的作用,促使鲜卑皇族在文化领域变革。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载,平城时期的文学作品约有诗歌18首,散文210余篇。若与北魏(包括东、西魏)诗歌159首,散文1367篇的总数相比,显然少得可怜;若与迁都平城之前相比,其文学作品的总数超过了十倍以上。因此,平城时期是北魏文学复苏之时。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主要与该时期多种文化交融分不开。为了便于讨论,笔者拟根据作者身份将平城时期文学分为皇室文学和士人文学两类。 二、平城时期皇室文学始盛 北魏皇室是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代表者,研究这个群体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可以了解北魏文学如何一步步更新民族文学观念,向先进的中原汉族文明靠拢。平城时期的皇室文学作者主要包括明元帝拓跋嗣在内的6帝,以及东平王翰和广陵王羽8人,散文88篇。文明太后胡氏的《杨白花》诗歌创作,给皇室文学带来新的契机。史载明元帝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3]64,儒学修养超过汉代大儒刘向。孝文帝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3]187,文学成就在北魏皇室罕莫能比。明元帝嗣和孝文帝宏在向汉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其文学创作也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平城时期皇室文学主要可分为书信体和诏书二类,均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信体文章是太武帝拓跋焘的五份书信,分别写给崔浩、臧质、王慧龙和宋文帝刘义隆。这些书信要么是写给文化程度很高的汉族知识分子,要么是南朝刘宋的皇帝,感情淡漠,文辞质朴,风格稚嫩,是典型的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大破焉耆,赐崔浩书云:“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余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8]字里行间显现出世祖的英雄豪气,得意神气。但一个帝王写出这样的书信,充分暴露出其文化底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二月,宋魏交兵40余日,北魏大败而归,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与宋文帝刘义隆书,有云: 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9] 这是最高级别的国书,理应写得典雅华丽,文采十足,但这个国书全部是口语化、通俗的文字,它反映了北魏拓跋民族的文学现状。 诏书是平城皇室文学中所占数量最多的文体,约占94%。这些诏书都是应用性文体,关乎国家大事,是历来最受关注的文本。其风格一如前所论及的书信体文章一样,以简洁质朴的文风为主。如神瑞二年(415年)《敕有司劝课》有云: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 这是北魏前期写得最具文采的诏书。文章多用排偶句,显得非常有气势。这种公告全国的文书,理应写得典雅与隆重些,但实际上却写得洗练,风格完全雷同于当时的军国文书,缺少帝王之气,这正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审美倾向。到太和二年(478年)的《明功罪诏》,风格也没有变化。此诏距《敕有司劝课》已将近70年,风格一如既往,这说明平城时期的诏书风格相同,都是拓跋民族所固有的传统文学风格。 平城时期皇室文学简洁质朴的风格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价值审美趣味,是北魏前期文学的主流。《魏书·李先传》有云:“太祖曰:‘卿既宿士,屡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长?’先对曰:‘臣才识愚暗,少习经史,年荒废忘,十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卿用兵不?’先曰:‘臣时蒙显任,实参兵事。’”[3]789这一段对话颇值得玩味,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对经学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军事谋略。因此可以说,兵法权谋之士才是北魏朝廷重用之人,其他一切活动都得为此服务,文学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3]154,故风格简洁质朴。然平城时期的多文化交融势必对皇室文学产生影响,文学风格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迹象在胡太后的《杨白花》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10]这首诗的作者《乐府诗集》题为无名氏,然后代学者据《梁书》考证,确信作者为北魏文明皇后冯氏。《梁书·杨华传》云:“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惋焉。”[11]这首《杨白花》乃宫廷淫秽之作,但颇受后人赞誉,就在于它情景交融,情感真挚,发自肺腑,很好地刻画了胡太后对杨白花的相思之情,“音韵缠绵,……令读者忘其秽亵”[12]。这首情调缠绵,音韵协谐的诗歌与鲜卑民族文学风格不相类,显然是受南朝文学的影响。 三、平城时期士人文学兴盛 平城时期的士人文学创作可分为归附士人文学和本土士人文学两大类。 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平城时期北魏先后灭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将河西纳入北魏版图。同时,平定青、齐,将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今山东地区的士人收入囊中。平凉户、平齐民,以及以其他方式归附的士人,他们的文学创作,给平城时期北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促使北魏文学发生变化。归附士人既有诗歌创作,又有散文创作,试分两类详论之。 归附士人的诗歌可分为酬答诗和述志诗二类。酬答诗以韩延之《赠中尉李彪诗》、宗钦《赠高允诗》、段成根《赠李宝诗》和游雅《诗》四首为代表,多采用四言长篇的形式,赠与北魏朝廷重臣,表达自己初入新朝的不安以及对前途的担忧。如宗钦《赠高允诗》第十一章云:“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蒨。”宗钦是河西著名的儒学家,世祖平凉州后归附北魏,《赠高允诗》大约就是他初入魏时所作。全诗十二章,既有对高允的赞许,又有期盼,更多的是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忧虑。第十一章写自己年老华发,进退维谷的处境。诗歌虽然采用了板滞的四言诗的形式,但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比同时期的北魏诗歌成就略高。述志诗以刘昶《断句诗》、王肃《悲平城诗》和胡叟《示程伯达诗》为代表,多采用四言形式,抒写自己的怀抱,是平城时期难得的上乘之作,如王肃《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王肃为六朝著名的大家族琅邪王氏,因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于太和十七年(493年)奔魏,先后任平南将军、镇南将军、车骑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等职。《魏书·祖莹传》云:“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3]1799据此,王肃《悲平城诗》作于其任尚书令之时。其实不然。王肃任尚书令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其时北魏已迁都洛阳,那么王肃作此诗何意?是对平城的眷恋,还是唾弃,笔者认为都不是。这首诗当作于王肃初到平城之时,后来常常吟咏而已。这首诗写一个南方人初到北方时的切身感受,颇具苍凉之气。但这首诗绝不是写平城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是一首述志诗,抒写自己志向不得舒展之苦闷。艺术上成功之处正如彭城王元勰所评“声律殊佳”,采用“三、五、五、五”的格律句式,显现了汉文化较高的素养,艺术成就明显高于同时期北魏文人。 归附士人的散文主要以奏疏和赋颂为主,当他们多被北魏委以新职,就有机会给皇帝上奏疏。这些文章是应用性文体,缺乏真挚的情感,但在艺术上较同时期北魏文学略高。如刘昶《乞停更与宋主书表》: 臣殖根南伪,托体不殊,秉旄作牧,职班台位。天厌子业,夷戮同体,背本归朝,事舍簪笏。臣弟彧废侄自立,彰于遐迩。孔怀之义难夺,为臣之典靡经,棠棣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伏望圣慈,停臣今答。 刘昶是宋文帝刘义隆之第九子,和平六年(465年)奔魏,被封为宋王。此文作于宋泰始三年(北魏皇兴元年,467年)。文章的内容姑且不论,行文流畅,属对精切,文辞典雅,明显高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艺术水准。归附士人的赋颂以程骏《庆国颂》最为有名,如其中的一段: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程骏本河西儒生,世祖平凉州后归附北魏。据《魏书·程骏传》云:“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曰:‘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文明太后令曰:‘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3]1348-1349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在太和五年(481年)二月,本文当作于此时。其内容为歌功颂德之作,连文明太后都觉得“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可见其颂圣之竭尽全力。文章辞藻华美,纯用四言,显示了河西士人深厚的文学素养。 东晋南播,大批士人随之南下,也有部分仍留在北方,这些人就是北魏的本土作家。他们的文学素养本来甚高,但摄于拓跋鲜卑忌汉文化的心理,其心迹颇为隐晦。平城时期多种文化的交流,文化政治略为宽松,他们的才华便显现出来。平城时期本土士人诗歌有高允《罗敷行》、《王子乔》、《答宗钦诗》和《咏贞妇彭城刘氏诗》四首,既有向拓跋鲜卑文化靠拢的一面,又有与南朝诗风相近的一面。平城时期本土文学数量最多的是奏疏和赋颂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显现出受多种文化交融影响的特点,缓慢地向先进的汉民族文化靠近。如崔浩《上五寅元历表》: 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干三、皇五帝矣。 崔浩是太武帝最为信任的汉族政治家,是六朝时期著名的世族大家——清河崔氏,家学渊源,文学艺术水准很高,但这篇《上五寅元历表》却写得很通俗。原因是本文写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1年),是北魏政治比较严酷之时,崔浩的文学创作只能符合拓跋鲜卑的审美情趣,以朴实无华为主。此外如崔光《临广川王谐丧议》、古弼《乞停发车牛表》、尉元《求运粟济彭城表》、高允《谏文成帝不厘改风俗》、高祐《上疏论选举》、韩麒麟《推用新附》等风格均如此类。这说明在平城时期本土作家文学风格以拓跋鲜卑的文风为主,朴实无华。然此时多种文化交流,文风模拟南朝亦成为时尚,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如高允《鹿苑赋》:“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夫道化之难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开,遘长夜之始曙。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敢布心以陈诚,效鄙言以自著”。歌颂献文帝高蹈出世、冲妙无为的闲散生活。用词典雅,属对精整,文辞华丽,句式以四、六骈句为主,很明显是受南朝文学影响的结果。又如高闾《至得颂》称赞献文帝敏悟有识鉴,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家强盛、兴旺,其功德可与先王、往圣相媲美,必将流芳后世,功业不朽。文章的语言无深奥冷僻之处,故读来琅琅上口,节奏感极强。尤其“嘉谷秀町,素文表石。玄鸟呈皓,醴泉流液。黄龙蜿蜿,游鳞奕奕。冲训既布,率土咸宁。穆穆四门,灼灼典刑。胜残岂远,期月有成。翘翘东岳,庶见翠旌”数句,色彩鲜艳、华丽流动,充分显示出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和民众蓬勃向上的气势和风貌。虽然全文用了四言句,但文辞华茂,排偶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与南朝文风类似。此外,如崔浩《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安原《临刑上疏》、刘洁《奏恤南州灾民》、许钟《上言庙祭有神异》、源贺《上书请入死者恕死徙边》、卢渊《议亲伐江南表》、李彪《表上封事七条》等风格均如此。 综上所述,平城时期北魏文学出现了复苏的景象,数量增多,质量略有提升。特别是此时期的多种文化融合,给北魏文学带来生机,部分作家自觉向南朝文学学习,给文学带来生机,北魏文学繁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