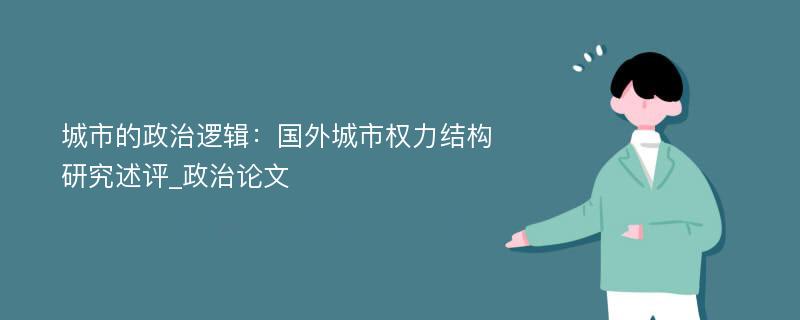
城市的政治逻辑:国外城市权力结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述评论文,逻辑论文,权力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5-0182-10
权力及其结构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等有关学科研究的“大问题”。权力结构是指决策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态,具体表现为决策者的阶层构成及组织形式。城市权力结构研究将国家层面的权威性价值分配问题置于城市层次,与国家权力结构研究类似,对于城市中的权力运作,通常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城市权力掌握在谁手上(Who)?这些权力是如何取得的(How)?权力运作的机制与结果是什么(What)?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城市的政治逻辑。本文目的在于梳理近年来国外城市权力结构的不同理论与流派,分析其理论内涵与传承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政治与行政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提出建议。
一、精英还是多元: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两大传统
从理论脉络上来看,传统城市权力结构研究有两大流派:一是以亨特为代表的精英论(elite theory),二是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论(pluralism)。精英论与多元论的争辩,奠定了此后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基本模式。
(一)精英论
精英论认为,城市决策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决策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重大的政治方案通常是由这些精英起决定作用,城市各级官员予以配合来实现少数人的意志。具体而言,精英论的观点包括:(1)上层少数人构成单一的“权力精英”;(2)该“权力精英”阶层统治社区生活;(3)政治领导与社区领导是该阶层的执行者;(4)该阶层与下层市民之间存在冲突;(5)地方精英与国家精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精英论的代表人物亨特(Hunter)以美国的亚特兰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决策层级与权力运行的过程,并于1953年出版了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奠基之作——《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在亨特看来,研究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要找出城市中的主要领袖。亨特设计了“声望法”① 来识别这些领袖,发现城市权力通常由不超过40人的集团行使,其中工商界的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亚特兰大市的城市权力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亨特还指出,这些精英大多相互认识、经常来往、互相磋商公共事务,从而结成密切的权势群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一些人在公共部门供职,在社会上引人注目、声名显赫;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人行使权力,其活动和影响一般不为常人所知。
亨特的研究所采用的结构功能分析、非正式因素(工商界精英)支配城市发展的命题,开启了后来成长机器论、城市体制论以及相关的城市权力结构经验研究传统。
(二)多元论
对于精英论的观点,多元论者提出了质疑。多元论者认为,城市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官员要向选民负责,所以选民也有权力,他们以投票来控制政治家。
多元论的代表人物达尔(Dahl)不同意用“声望法”来进行权力研究。他指出:任何人拥有权力资源而不去使用的话,不能算是权力;权力不仅仅是声望,还要有行动的实权,因此,应当用“决策法”来考察谁在重大的城市政策上参与实际决策。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Who C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the American City)。该书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城市重建、教育政策和政治任命等三个问题进行分析。达尔发现,有不同的团体和个人参与了这三个方面的决策,个人或团体都拥有各种资源,有其在特定专属领域的影响力,但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足以垄断城市的决策过程②,城市权力显得很分散,城市的决策总是倾向于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将纽黑文市的城市权力格局定义为以“分散的不对等性”(dispersed inequalities)为主要特征的多元政体(Polyarchy)。
达尔的著作与波尔斯比(Polsby)的《社区权力和政治理论》(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沃芬格(Wolfinger)的《声望与社区权力研究中的现实》(Reputation and Reality 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Power),共同构成了多元论的核心。不过,多元论的观点也遭到了广泛批评。
首先,达尔的研究选择了纽黑文市的城市重建、教育政策和政治任命等三个领域进行研究,那么,怎样才能确定这部分决策的结构能代表城市整体的权力结构?事实上,决策议题不同,往往会影响利益相关人投入的强度与时间,因而所呈现出来的决策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其次,巴克拉科(Bachrach)和巴拉兹(Baratz)在《权力与贫穷:理论与实践》(Power and Poverty:Theory,and Practice)中提出了“权力的两面性”理论,认为:权力不但能决定某一事件或提案进入政策议程,也可以扼杀某一重要事件进入政策议程。达尔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已经得到允许的提案,但却没有研究那些尚在构想或酝酿阶段就已被否决的提案。获得允许的提案,也许可能是无法真正威胁城市资源分配和既定权力结构的琐碎事情。所以,多元论者研究的只是部分的权力运作和权力集团,而不是全部。
二、增长机器还是城市体制:城市权力结构的模型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权力结构的争论一直被精英论与多元论所垄断。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国家开始面临普遍的政治经济再结构问题:在生产领域,从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向特殊化的弹性生产模式;运输通讯科技的发展,使跨国公司兴起,资本更易于流动到其他国家。在政治上,为解决凯恩斯主义而导致政府失灵的财政危机,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崛起,自由市场被当作最有效率的调节社会生产与分配的机制,私有化、去管制化、自由贸易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在这种大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面对有限的资源与多变的环境,更多的组织(包括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工会、社区团体)被引入到城市系统中,新的非阶层化谈判系统开始浮现。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城市权力研究理论开始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增长机器论(grow machine)与城市体制论(urban regime),这两种理论都致力于将城市权力结构模型化。
(一)增长机器论
增长机器论基本上同意“精英论”的观点,认为在城市中的确存在利益一致的精英团体,但增长机器论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群精英有相同的利益?增长机器论认为,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一问题在经验层面的答案都是“增长的议题”。增长机器论的代表人物莫罗奇(Molotch)认为,城市就是一部增长机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体(Locality)的本质就在于增长③。动用资源,追求增长是地方精英,尤其是地方工商精英的共识。增长精英所组成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包含了经济利益团体、土地开发商与房产经纪商、银行、律师等关键行动者,这一联盟不是直接参与城市决策,但企图影响决策,或者提出地方发展的意识形态。增长机器的成本常常需要所有居民承担,比如增税与环境成本,但其所促成的地方经济发展利益却并非均衡分配给居民,而是由地方精英所享用,城市遭遇“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由于经济发展能够为政治人物带来选举利益,因此城市政府也会支持“亲增长”政策,并利用公权力达成私部门的目标,而媒体也会支持“亲增长”取向,以增加销售量和广告量。
罗根(Logan)认为,增长机器论提出了许多可以揭示城市发展的有价值命题,但问题在于,相比较城市增长联盟,劳工、工会等也并非是局外人,他们也应该纳入到增长机器的分析。1987年,罗根和莫罗奇合作的《城市财富:地方的政治经济学》(Urban Fortun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在“地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框架上进一步阐述了增长机器命题,并专门分析了城市中存在的“反增长”力量④。
增长机器论的贡献在于,它将1950年代以来多元论与精英论关于“谁统治城市”的辩论导向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增长机器论将土地开发等重大的政治经济议题带入了研究之中,为城市权力结构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架构。同时,在“谁统治”以外,增长机器论还回答了在城市决策中“谁得到了什么”等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其理论也因而显示出了较强的批判色彩。
然而,批评者认为,增长机器论将城市发展过于窄化为土地开发,忽视了其他维度的考察。而且,增长机器论的分析焦点往往局限于一个城市或地方,并没有考察城市所属区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更没有考虑跨国区域与全球分工,这些都是增长机器论的局限⑤。
(二)城市体制论
将城市权力结构模型化的工作仍然在继续。1980年代以来,费因斯坦夫妇(Norman & Su- san Fainstein)、埃尔金(Elkin)与斯通(Stone)等学者相继以城市体制论来解析城市权力结构。城市体制论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城市体制中的成员有哪些?这些成员如何运用权力与发挥影响力?
立足于对亚特兰大市的研究,斯通指出,城市体制是为城市公私部门合作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informal governing alliance)⑥。在城市权力结构上,城市体制论既不偏向于精英论,也不偏向于多元论。城市体制论认为,在城市体制模式下,政府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来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同样,私部门也不能独立制定政策来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决策是复杂的关系与互动网络。
基于斯通的研究成果,墨斯伯格和斯托克(Mossberget & Stoker)对其描述的城市体制的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⑦:(1)体制是一个非正式的但相对稳定的,能够对城市发展政策发挥持续控制作用的制度性资源。它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或者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来完成。(2)体制旨在掌控公共资源的政府和控制经济资源的私部门之间建立沟通。除此之外,其他的社区组织(例如美籍非裔的中产阶级团体)也参与其中。(3)合作不是上天的恩赐,需要努力去争取,而且城市体制不是存在于所有城市。(4)体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随着行政管理者的更换而变化。(5)体制的性质是由参与者所控制的资源,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6)体制可以通过“选择性诱因”⑧ (selective incentive)达成一致意见。(7)体制并不表明行动者在价值观和信仰上完全一致,但合作将使他们在政策上趋于一致。
城市体制论对多元论、精英论的挑战首先在于对“权力”理解的不同。在多元论和精英论那里,权力是一种“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模型,因此其理论强调支配和抵抗;但与此不同的是,城市体制论认为权力应该是一种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的权力或能力,而不是一种高于他人的特权或社会控制权。因此,城市体制论将关于城市权力设问由“谁统治”转向了“如何统治”,强调赋予某方权力(power to),关切权力如何被产生以达到特定结果,而非权力如何限制社会行动(power over)。换言之,城市体制论的重点在于如何获致行动能量以创造特定政策结果,而不是控制社会行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赋予某方权力”(power to),斯通将城市权力细分为四种类型:(1)系统型权力(systemic power):企业立场出发的权力,内涵于资本的社会关系。(2)命令性权力(command power):冲突时能够对对方施展的支配性能力,内涵于国家机器的社会关系。(3)协议性权力(bargaining power):建立暂时联盟(coalition),塑造新的集体权力基础,使得参与者的作用能力有所增加。(4)先发性权力(preemptive power):占有、保持和利用策略性位置的能力,能够设定共同的目标与议程,并动员组织资源以达成目的。
其次,传统多元论认为,在多元民主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团体可以在多数议题上主导整个社会。斯通则认为,像战后亚特兰大这样的城市,固然有联盟在经济发展政策与族群政策上主导整个城市,但其权力形式并不像精英论那样的全面主导,由上而下控制;其他不在体制中的团体,只要能够掌握议题,有效动员,也有相当宽广的空间可通过投票、选举来反制联盟。
总体来看,城市体制论对权力赋予了新的认识,并企图超越精英论与多元论的对立,以理论结合历史研究与经验研究。城市体制模型提出以后,其实用价值和洞察力受到了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与城市规划学界的一致关注。除了解释美国城市内部关系以外,城市体制论更被延伸至解释区域关系、次级城市体系甚至社区关系,城市体制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的支配性典范(dominant paradigm)⑨。
不过,到了199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对城市体制论提出修正。普遍的批评是,城市体制理论非常重视“中层”(middle range)研究,过于关注城市内部联盟的结构与体制维系,却忽略了由宏观层次如国家与全球化趋势(national and global)等外在结构性因素来了解城市体制的发展。道丁(Dowding)更是指出,因为城市体制论在解释、预测不同的体制模式、体制的维系与改变上有着相当的限制,因此城市体制论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不如说是一个概念模型⑩。
三、城市治理与伙伴制:这是城市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吗
城市体制是否可以解释所有城市中的所有决策模式呢?或者说,城市体制是否就是适合于所有城市的权力结构呢?许多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指出,城市体制论存在一定的“美国偏差”,因为在美国,城市具有自主性,城市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自己的财产、税金或是来自其他部分的收入;同时,城市政府资源有限,必须寻求私部门支持;城市从政者仰赖私人的选举联盟,不受政党政治的任期所束缚等等,这些结构要素,可以让民选官员与企业分享彼此共同的利益来确保经济的发展(11)。这是城市体制比较容易出现的条件,但这些结构性条件,在其他国家却不一定具备。比如在英国,中央政府比较集权,也仍然支付着城市绝大多数的财政需求,因此,城市体制论必须做出修正,要在更广阔的脉络下超越地域化倾向的理论局限(12)。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更具有解释力的范式。
(一)治理与城市治理
显然,治理并不是一个新造的名词,传统的“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几乎没有区别,它们所指的都是一种正式并制度化的过程,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运作,其目的在于维持公共秩序和便于处理集体行动上的问题。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政府管理大变革中,“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成为一套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思想体系(13)。
在许多关于治理的定义中,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义最受到关注。该委员会在其1995年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报告中,对治理做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斯茂思(Smouts)认为,这个定义明确并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显示了治理的四项重要特征:(1)治理既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process);(2)治理的基础是协调(accommodation),而不是支配;(3)治理同时涉及到公部门与私部门的行动者;(4)治理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而是有赖于持续的互动(14)。从中可以看出,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体制论的延续与深化。
在可操作的层面,治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罗茨(Rhodes)在《理解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就是管理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15)。根据罗茨的界定,政策网络是“相对稳定与前进的关系网,动员与汇集广泛分布的资源,使得集合的行动得以协调迈向共同政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治理模式下并非没有政府,政府一定会存在,而且其地位并非与其他行动者完全一致;治理模式下的政策网络不是自治、独立、自由的网络,而是由政府指导与推动的组织网络;治理的焦点就是政府如何有效地与政府内及政府外的组织互动,最终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因此,虽然罗茨的名作“The New C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通常被翻译成“新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但其真正的意思恐怕是“新治理:没有统治的治理”。
政府如何指导和推动网络呢?科科特等人(Kirkert,Klijn & Koppenjan)区分了政府管理网络的两大战略,即网络经营与网络构建(16) 。网络的经营是指对现有网络结构内的关系进行管理,这常常需要政府为妥协创造出共同决策的环境,比如一个政府机构可以为一项新规制的通过,召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由此产生一个被认为是有益于所有人利益的结果。网络构建是指改变或参与网络结构的努力,要求改变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资源分配方式,寻求政治方向的变动。
丹麦学者索仑森(Sorensen)则提供了一个更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分析框架,她界定了四种网络管理的方式:参与式的介入方式、支持与促进式的介入方式、自我构建式的不介入方式以及故事叙述式的不介入方式(17)。前两种都与大多数网络管理著作所讨论的直接干预类似,后两种方式却显得很有新意。“自我构建式的不介入方式”指政府通过推动立法为网络的发展指明大致方向,达成目标的路径和机制则留给授权的组织自由定义和细化;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激励性措施鼓励组织通过特定方式互相合作。关于“故事叙述式的不介入方式”,索仑森给了这样的描述:通过讲故事,可以建构利益关系,树立敌-友形象,为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描绘过去和未来的景象,从而塑造理性行为的形象。由此,“讲故事”代表了一种不通过直接干预而影响自治主体政治战略的不介入方式。
(二)伙伴制:城市治理的具体实践形态
伙伴制(18) 是“为重整一个特定区域而制定和监督一个共同的战略所结成的利益联盟”(19)。最初,伙伴制被英国保守党政府在重振城市计划中当作一种手段来重构公共和私营经济的界限;后来,这一概念被逐渐运用到重振城市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领域。作为一种“利益联盟”,伙伴制一般具有四个维度:中央政府与城市政府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与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在属性上,前两者是政府间的府际关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IGR),后两者属于公、私部门协力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在很多文献中,很多时候伙伴制即指公私伙伴制。
为什么城市中的不同组织会倾向于缔结伙伴关系呢?罗茨认为关键在于“资源”,也就是说,城市的行动者会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或劣势,进行各类资源的动态交易。罗茨将这些资源分为五种:宪法及法定职权、政治正当性、资金和财源、组织能力与信息。罗茨指出,城市中的行动者具有权力依赖(power- dependence)的关系,任何治理结果的产出都必须借助行动者之间的磋商和交易才能完成(20)。
此后,里奇与珀西-史密斯(Leach & Percy- Smith)对罗茨的观点作了修正,他们在罗茨五项资源的基础上增列了土地、人力以及社会资本等三项资源,以此构成了城市中可竞争的八项资源(21):(1)土地(1and)。这是指天然和人造的有形资源,例如住宅、公园、学校、医院及公共开放空间等。通过伙伴制可以进行城市更新;在伙伴制的开展过程中,强调私人土地运用于公共目的,闲置公共空间的再利用,以及其他土地资源的再生及可持续使用。(2)人力(people)。强调公、私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的整合运用;为了应对全球化对城市产业经济的冲击,城市政府间也可以通过区域治理的原则,合作解决产业经济失衡所造成的失业或劳动力不足问题。(3)财力(money)。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其行政职能的发挥依赖于充足的财力。为了提升城市伙伴制的绩效,城市政府必须强调施政的成本效益、引进民间资金和财力,整合城市政府间平行预算的运用,充分发挥综合效益。(4)权威(authority)。权威是城市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资源,特别是在公私伙伴制建立的时候,权威是保证公共利益的重要支柱;在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府际关系中,权威则是奠定资源分配、分担,以及共同或个别承担责任的重要基础。(5)正当性(legitimacy)。这里指的是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的正当性,正当性作为一种资源,可增进地方政府运用其他类资源的合法性。(6)信息(information)。在公私伙伴制的开展过程中,强调信息的公开化以增进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度;在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府际关系上,则强调信息的分享来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7)组织(organization)。城市政府的组织能力也是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资源,除了传统的科层体制,网络型组织等新的领航(steering)机制越来越被广泛运用。(8)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城市治理过程是一种复杂且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资源,可被界定为主要根植于团体成员间的互信关系。在有效规范约束之下,成员彼此具有对等互惠的信念,因而有助于整体目标的达成。
可以肯定的是,治理、网络、伙伴制越来越成为流行语言;而且,治理在实践中也发挥了成效。比如伙伴制,它似乎已经变成“告诉我们城市的问题和正确的解决办法的方式之一”(22)。朱森和麦格雷戈(Jewson & MacGregor)认为,伙伴制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因为它“分散了成败的责任,并保证相对低一级的公共开支能被用来调节大量的私人投资”(23)。不过,在分散责任的时候,它也有助于那些对已经是社会上的赢家有利的政策合法化,并常常会排除城市中的非精英群体。这样的结果,似乎又背离了城市治理论企图超越精英论等传统观点的初衷。
因此,朱森和麦格雷戈随即指出,关于目前如此流行的伙伴制,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伙伴制应该包括哪一种利益和当事人,又应该排除哪一种利益和当事人?谁应该在伙伴制中充当领导?在伙伴制中谁的任务应该优先?事实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城市决策将在治理、网络、伙伴制等新招牌下演绎出我们一直想要摆脱的东西,比如社会不公、边缘群体、社会排斥,等等。
四、城市社会运动:城市中的权力冲突
城市体制论和城市治理论对于城市权力以及公私部门合作打造联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它们共同的问题是都致力于描述城市权力中的合作,对权力中的冲突却着墨不多。当然,也可以说这并不是城市体制论与城市治理论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但是为了对城市中的权力结构有全面的、立体的了解,还需要增加关于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s)的讨论。城市社会运动并不与前述讨论具有直线的理论传承关系,它们也许并行发展,但城市社会运动理论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城市权力结构的景观。
(一)空间与集体消费:城市社会运动的目标
卡斯特尔对城市社会运动给了一个描述性的界定:“由于社会支配利益的制度化,城市的角色、意义及结构的主要变革,通常是由大众动员所要求的结果;当这些动员造成城市结构转化时,我们称之为城市社会运动。”(24) 简言之,城市社会运动是一种造成城市结构转化的大众动员,是城市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城市矛盾的直接反应。
显然,城市与乡村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对城市来说无比重要,因此,城市社会运动的目标一定与空间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体制论还是城市治理论在讨论城市权力结构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维度,或至少没有给这一维度以足够的重视。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经典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描述一般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上,空间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不引人注目的(25)。
自1970年代以来,空间开始逐步进入社会理论论域。列菲弗尔(Lefebvre)是最早系统阐述空间概念的学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并系统阐述了空间概念。列菲弗尔认为,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空间的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经由占有空间并将其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而维持与延续。“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26),占有并生产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空间的再生产”化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少矛盾;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
列菲伏尔极富创意的空间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城市研究,我们从索雅(Soja)和哈维(Harvey)等城市研究者身上可以经常看到他的影响。索雅解释了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营造积累环境的缘由,提出国家本身也是社会生产的空间,反过来积极致力于特定社会空间化的再生产(27)。不过,政策是经过权力折衷后的结果,尤其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化与自由化的趋势中,这些政策的决定过程越来越倾向企业化经营,以及和资本家磋商。
哈维(Harvey)使用了“垄断地租”(monopoly rant)(28) 来分析资本主义与土地间的关系。他认为,垄断地租源于社会行动者专断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间接可交易的项目,此时不只土地、资源或区位与资本积累紧紧相关;通过使用而输出商品或服务,或者借此创造出稀有性,也是“垄断地租”的相关生产方式。在垄断地租的吸引下,体现使用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消解成为商品化的交易空间。
在将城市空间做了如此社会化、政治化的解读以后,一个必然的焦点就是通过城市空间生产或传递的各类商品与服务。住宅、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通过空间得以生产或者传递的产品或者服务,它们构成了市民生活的核心部分并成为支撑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物品,即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卡斯特尔对集体消费的定义是“问题的特点和规模使得消费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人”(29)。换言之,集体消费(30) 是指消费过程在其性质、规模、组织、管理上都采取集体供给的形式,也就是指以国家为中介的消费过程。在集体消费的视角下,城市被看作是一个组织起来以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指导或控制;城市成为“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民众自主性之间的冲突与焦点”。
随着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中的集体消费供给,集体消费成为城市中的核心问题,集体消费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具体表现,表现为住房供给短缺、医疗健康保护不够、社会设施缺乏等方面。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不再只是沿着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展开,还围绕着集体消费的供给差异而展开,市民日常生活政治化,消费成为城市政治动员的基础。
政府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足够商品化的空间来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却要反市场、反商品化地供应廉价城市空间。如此,围绕着集体消费而出现的矛盾,城市社会运动成了与阶级斗争不一样的权力冲突。
(二)文化意象:对城市社会运动的形上解读
哈维在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解读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时空压缩”的概念,以此说明运输与交通的强化,实际上是缩短时间来取消空间阻碍。在全球化的趋势中,许多产业和服务由于“时空压缩”而失去了其优势。不过,哈维紧接着指出,虽然很多传统的产业和服务由于时空压缩失去了其优势,但是“文化”却可塑造独特性与真实性,其无法复制性将造就垄断。
于是,同样在“垄断地租”的诱惑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中成长最快且产值最高的活动之一。服务业、金融业、高科技研发设计,以及时尚设计、媒体、文艺、娱乐、购物餐饮、会议、观光等产业,都特别要求塑造具有地域风味的文化意象,以保持其特色和吸引力。与此类似,朱肯(Zukin)将空间的生产、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工业及资本主义发展等范畴串联在一起,并着重分析了城市中的文化消费。朱肯观察到,美国在1970、1980年代城市向郊区扩张引发了市中心衰败,许多城市借助历史保存、文化设施补助来增加地产价值;这一措施同时也意味着对艺术工作的鼓励,于是,市中心“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开始了。由移民带来的差异文化所挑战、塑造的城市公共空间,各地对于“认同政治”的推销(marketing),也伴随文化消费而助长了城市象征经济(31)。
城市文化意象再现了支配的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导权,更说明了大型企业的垄断与国家政策对城市的控制。文化的使用创造了文化政治上的新紧张关系,它有时是民主的,可以合并而非分隔社会与族裔(ethnic)群体,帮助协商新的群体认同;但有时又被用来合法化(legitimize)经济成长的不平等获利。因此,城市的文化总是政治性与社会性地构成的,它是隐含了权力的协商过程与网络。
文化为城市社会运动界定了新的动机与目标。城市中心性的象征、公共空间意义的塑造,以及替空间形式提供象征意义的纪念性等,这些涉及庞大公共资源配置,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不同市民群体的权利的新城市文化工程,必定会成为城市社会运动和市民集动行动的关键场域。由此我们也看到,即使空间与集体消费问题得以解决,但无论如何,城市社会运动也都不会消失。
五、小结
从多元论到精英论、从城市体制论到城市治理论,再到城市社会运动,谁在统治城市?在用什么方式统治城市?应该由谁来统治城市?应该用什么方式统治城市?这一系列有关城市权力结构的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富有创意而且深刻的描述。
但是,这并不是城市权力及其运作的全部细节。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城市体制论还没有“形成可以解释或者预测城市体制如何形成的理论”(32);而从城市治理理论开始,关于城市权力的研究似乎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在“后现代理论的文字游戏下产生的解构跟重构的实验”,研究者在想像着城市的想像,却难以判定这是否真的是城市行动者的真正想像。
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样,关于城市决策的新模式,比如治理、伙伴制、网络等等,这些概念看起来能用来放在很多场合,但又似乎只是给了人们一种舒服的感受而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这似乎意味着,新的城市研究需要再发展新的概念工具。要做到这一点,按照卡斯特尔的主张,从方法上必须注意:“我们必须在田野研究中,在新信息的收集中,在发现社会隐藏的领域里,以及在所有迷人与悲惨的城市生活销魂魅力中回归它的源头。我们不需要新的城市意识形态或善意的乌托邦——我们应该让人们想像他们自己的神话。”(33)
卡斯特尔的这一警告,如果放到我国城市政治与行政研究的场域中则显得更有意义。近年来,我国农村政治研究引起了空前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城市政治与行政学研究却一直没有能够及时回应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更遑论对这些变化给以细微的关注与精确的解释。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34) 基于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城市权力结构研究迫切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我国城市决策过程是怎样的?这一决策过程的参加者是谁?哪些是进行实质决策的人?哪些是影响决策的人?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他们各自在城市权力分配中的地位?哪些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决策议题?不同的城市决策议题是否有不同的参与者?全球化以及城市政府主动推进的城市化(比如城中村改造)对于城市决策有没有影响?尤其在土地开发与利用上,这些影响可能是什么?城市决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集体消费品的供给与分配?城市中是否存在城市治理所指向的网络?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目前的城市权力结构与单位制时期相比较是否有了不同?如果有,是什么?在城市决策过程中有没有冲突?这些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更多具有问题意识的研究者来参与,通过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建构本土解释,并与国外有关研究展开有质量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8-03-21
注释:
① 声望法的核心就是“列出有声望的人,然后访谈并证实这一列表”。具体包括:(1)通过与居民交谈和其他一些调查,列出被认为是当地社区工商业、政府、市民或社交圈中有实际影响的所有人,在亚特兰大案例中是开列了这些人的名单。(2)询问社区中了解该社区的人们或对地方政治熟悉的专家的代表性看法,把上表中人物按顺序排列,在适当的时候增加或删除某个人。(3)把表中的人物数量由175人缩小到40人。接着,对这40人进行访谈,请他们指出其中被认为此区中最有领袖地位的人。最后,从中得到了一个中选率最高的12人名单。具体论述参见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② 例如,工商组织对城市重建较有发言权,但是对教育的影响较小。
③ Molotch,H.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2 :pp.309-332.
④ Logan,J.& Molotch,H.Urban Fortun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⑤ 参见Stoker,G.Regime Theory and Urban Polities,In Judge,D.,Stoker,G.and Wolman,H.(eds.) Theories of Urban Polities. London:Sage,1995 ; Lauria,M. (Ed.).Introduction:Reconstructing urban regime theory.Thousand Oaks :Sage,1997.
⑥ Stone,N.Regime Politics:Governing Atlanta,1946-1988.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
⑦ Mossberger,K.and Stoker,G.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gime Theory:The Challenge of Conceptualization.Urban Affairs Reviews,2001,36(6) :pp.810-835.
⑧ 实际的选择性诱因包括:信用资金、捐款、专业知识与技术、组织支持、人脉接触、媒体宣传以及对问题的深入分析等。见Stone,N.Regime Politics:Governing Atlanta,1946-1988.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
⑨ Lauria,M.(Ed.).Introduction:Reconstructing urban regime theory.Thousand Oaks:Sage,1997.
⑩ Dowding,K.et al.Regime Politics in London Local Government.Urban Affairs Review,1999,34 (4) :pp.515-545.
(11) 参见Elkin,L.City and Regime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7.
(12) 参见Stoker,G.Regime Theory and Urban Politics,In Judge,D.,Stoker,G.and Wolman,H.(eds.) Theories of Urban Politics.London:Sage,1995.
(13) 有学者就认为,强调治理不仅是要提供关于政府变革的新策略与思维,更要与从1980年代就开始兴起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相区别,因此在现在的背景下,关于“治理”最准确的叫法是“新治理”(new governance)。参见Reddel ,T.Beyond Participation,Hierarchies,Management and Markets:New Governance and Place Policies.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61 (1) :pp.50-63.
(14) Smouts,C.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50(1) :pp.81-89.
(15) Rhodes,W.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Political Studies,1996,44 :pp.652-667.
(16) Kirkert,W.,Klijn,E-H & Koppenjan,J.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Sage,1999.
(17) Sorensen,E.Metagovernance:the Changing Role of Politicians in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36(1) :98-114.有关评论也可参见斯托克:《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8) 事实上,治理、伙伴制、网络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人混为一谈。从其内涵和争论的焦点来看,这几个概念也没有太大区别。不过,仔细辨查,还是可以看出这几个概念在使用上的细微区别:治理意味着在整体上的城市权力结构模式,其核心是构建与经营网络;而伙伴制,则可以说是治理的某种具体实践形态。
(19) Bailey,N.,Barker,A.and MacDonald,K.Partnership Agencies in British Urban Policy.London:UCL Press,1995,p.27.
(20) Rhodes,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Policy Networks,Governance,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pp.36-38.
(21) Leach,R.and Percy-Smith,J.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New York:Palgrave,2001 ,pp.130-154.
(22) Clarke,E.Economic development roles in American citie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shifting partnership arrangements,in Wlazer,N.and Jacobs,B.D. (E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8,p,36.
(23) Jewson,N.and Macgregor,S.(Eds).Transforming Cities ? Contested Governance and New Spatial Divisions.London:Routledge,1997.
(24) Castells,M.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5) Harvey,D.The Right to the 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 (4) :pp.939-941.
(26)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
(27) Soja,W.Postmodern Geographies.London:Vcrso,1989,p.35.
(28) Harvey,D.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in Panitch,L.& Leys,C.(eds.),A World of Contradictions.Socialist Register,2002.
(29) Castells,M.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in C.Pickvance (Eds),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London :Tavistock,1976,p.75.
(30) 有关论述参见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1期。
(31) Zukin,S .The Cultures of Cities.Oxford:Blackwell,1995.
(32) Mossberger,K.and Stoker,G.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gime Theory:The Challenge of Conceptualization.Urban Affairs Reviews,2001,36(6):pp.810-835.
(33) Castells,M.Urban Soc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Susser,I.(ed.).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Oxford :Blackwell,2000.中文版本《二十一世纪的都市社会学》,载思与文网站,http ://chinese-thought.org/shll/002259_2.htm。
(3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
标签:政治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权力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