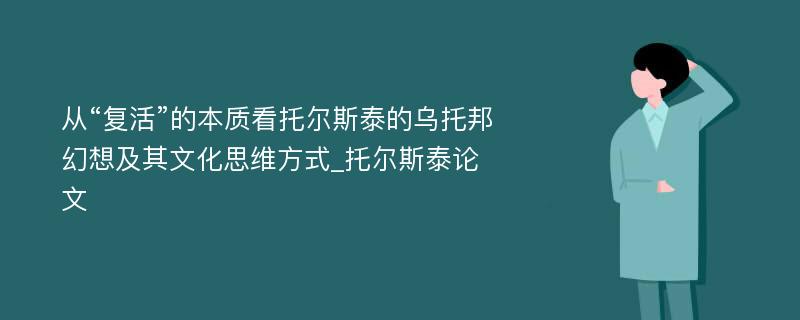
从“复活”实质看托尔斯泰的乌托邦幻想及其文化思维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乌托邦论文,实质论文,思维模式论文,幻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艺术创造,在俄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的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不倦地探索改良社会的方案。托尔斯泰的方案,就其实 质而言,是乌托邦主义的,在其代表作之一的《复活》中有着较为系统的体现,而这又集中地体现在“复活”思想上。可是,过去在论及《复活》中的“复活”时,几乎都一致认为:聂赫留道夫的“复活”,主要表现在他道德的自我完善,体现了托尔斯泰的荒谬说教;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复活”,则认为是卡秋莎回到人民队伍中。笔者认为,从《复活》原作的具体描写来看,其实不是如此。①为此,笔者拟从《复活》原作出发,先就男女主人公的“复活”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殊途同归的“复活”所体现的乌托邦幻想,再进而挖掘根源于作者思维中的宗法制农民的文化模式。
一、殊途回归的“复活”
《复活》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和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复活”思想的载体。
聂赫留道夫的“复活”,笔者完全赞同他的“复活”主要表现在他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体现了托尔斯泰的荒谬说教。恕不在此赘言。
而玛丝洛娃的“复活”,我以为并不是卡秋莎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这种说法与《复活》原作的具体描写是不相符的。
原作是如此描写的: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妇的私生女,由于母亲早死,被女主人收养,成为主人家里的婢女兼养女。十六岁,她与女主人的侄子聂赫留道夫真诚相爱,卡秋莎热情地憧憬着未来,幻想着幸福。然而,她的憧憬与幻想被阶级的壁垒撞了个粉碎。当聂赫留道夫成为近卫军之后,卑鄙地占有了她,又无情地抛弃了她,塞给她的一百个卢布就算是她的身价。由于不明不白地怀了孕,她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在经历了说不清的凌辱与痛苦之后,她最终走上了那个罪恶的社会为她这样的弱女子安排的唯一道路——沦落为娼。八年地狱般的生活,她的身心受尽了摧残,灵魂也遭到了腐蚀,她沾染上了诸如吸烟喝酒,卖弄风情等恶习。
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使她对聂赫留道夫以及整个黑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仇恨。所以当聂赫留道夫怀着悔罪的心情到监狱看望她,并表示要以同她结婚的实际行动赎罪时,她面对这个把自己推入火坑的仇人,禁不住发泄出满腔的愤怒,大为恼火地叫道:“我是苦役犯,是窑姐儿,……您是老爷,是公爵,你用不着跟我打交道,免得惹一身脏。你去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红钞票。”还说“……你在尘世的生活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肥脸!你走开,走开!”③。同时宣布:“你说您要结婚,那万万办不到。我宁可去见上帝!”④这种发自内心的控诉与谴责,是对贵族老爷居高临下的施舍行为的反抗,更是对自己作为人应有尊严的卫护。托尔斯泰紧接着刻画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的心理活动,“她明白他是个什么人,决不会对他让步,决不容许他象从前在肉体上使用她那样现在又在精神上使用她,她不容许他把她变成他表现宽宏大量的对象。”⑤这种想法,一方面道破了聂赫留道夫的用心,另一方面表明了玛丝洛娃从过去自暴自弃、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真正觉醒了,是应该积极肯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住这一点,停留于此,并把它当成玛丝洛娃的终极认识和态度,笔者以为失之偏颇。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这只是而且仅仅只是玛丝洛娃八年后首次见到聂赫留道夫时的认识及感情,因此我们还不能、也不应该如此就对玛丝洛娃“盖棺论定”。
以后,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的推移,玛丝洛娃最初对聂赫留道夫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是起了本质上的变化。
玛丝洛娃由于对少年时代美好生活的回忆,更加之因为聂赫留道夫悔改的诚意,玛丝洛娃深深地被感动了,于是不仅和聂赫留道夫和解了,而且她竟然再一次又爱上了他。当聂赫留道夫后来又去探望玛丝洛娃时,玛丝洛娃竟然“文静而胆怯”地请求聂赫留道夫原谅前天“说了不中听的话”,而且玛丝洛娃再次拒绝聂赫留道夫关于结婚的请求时,除了痛恨之情外,“还有点别的东西,有点又好又重大的东西”,以致聂赫留道夫谈到让她去医院工作时,“她的眼睛含着笑意”⑥,欣然同意了。明显地让人感到,玛丝洛娃的态度与她在狱中初见聂赫留道夫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再往后,当聂赫留道夫去看望已作了女助理护士的玛丝洛娃时,“她见到聂赫留道夫,就涨红了脸,……可是今天她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有那么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再次证明玛丝洛娃态度的变化。后来,“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赶出医院,这在她是特别痛苦的”,因为“这个罪名是冤枉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为此而被聂赫留道夫误解,她感到很伤心,“眼眶里满是泪水”⑦。可见,玛丝洛娃非常看重聂赫留道夫对她的印象,在意他对自己的看法,……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玛丝洛娃确实觉醒了,她对聂赫留道夫的爱的确复活了,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所写的一样,“其实她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戒掉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她所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⑧。由此观之,玛丝洛娃并没有把她最初的认识和态度坚持下去,而是依照她变化了的认识和态度,与聂赫留道夫的感情走到一块儿去了。
有的人认为,玛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的“复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倘若本质真是不同的话,那么,玛丝洛娃就应该把她最初的认识和态度坚持到底,只有那样方能体现他们两人“复活”的本质是不同的,归宿是不同的,人生选择亦是不同的。当然,这也是大家情感上所希望的。可是,事实上玛丝洛娃她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在思索,在行动。而恰好相反,玛丝洛娃按照她自己的认识和情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最初的认识和态度。
既然如此,玛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在情感上产生了共振,可是,玛丝洛娃又为何不答应聂赫留道夫赎罪的请求,干脆和他结婚呢?这“主要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她爱他,认为同他结合在一起,就会破坏他的生活,而她跟西蒙松一块走掉,就会使他自由”,于是玛丝洛娃“下定决心不 接受他的牺牲”⑨。不难看出,玛丝洛娃爱聂赫留道夫,却又拒绝他的求婚,这完全是为聂赫留道夫着想。关于这一点,聂赫留道夫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在动身到彼得堡去以前的日记里写道:“卡秋莎不接受我的牺牲,她要牺牲她自己……,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她在复活了”⑩。这既是聂赫留道夫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作者托尔斯泰“复活”思想的表白。玛丝洛娃不仅为聂赫留道夫的幸福、自由、生活考虑,而决意牺牲自己,同时,她对同聂赫留道夫结婚有了她自己崭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告诉了聂赫留道夫:“她爱您,而且爱得很深,只要能为您做一件哪怕是消极的好事,使得您不致再受到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幸福,对她来说,跟您结婚是可怕的堕落,比以往的一切堕落都要坏,因此她绝不会同意这件事。”(11)这里所说的堕落,是指玛丝洛娃认为,如果她答应同聂赫留道夫结婚,这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聂赫留道夫的牺牲之上的,是对他的拖累甚至毁灭。由此可以看出,玛丝洛娃对聂赫留道夫的爱是真诚的,玛丝洛娃的感情是多么高尚啊!
基于这些,所以当玛丝洛娃最后与聂赫留道夫告别时,她“没有说一般的告别辞”,而是“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地说“那我们就分手了”。此时的矛盾心境,在这简寥的话语和那“凄凉的笑容”中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一方面,玛丝洛娃为自己终于克制住了对聂赫留道夫的爱,没有拖累他,自己此时没有因为爱而“堕落”,而是“办成了她所要办的事,不由得暗暗高兴”;另一方面,玛丝洛娃为自己马上就要与聂赫留道夫分手别离,要割舍对聂赫留道夫的爱而“又不免心里难过”(12)。这就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玛丝洛娃的“复活”的内核——完全为别人着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感情、个人幸福,从而求得道德和自我完善。所以我们认为,玛丝洛娃的“复活”与聂赫留道夫由悔罪到为玛丝洛娃的幸福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复活”,其实质是毫无二致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殊途同归,实现了同一人生归宿——最终双双在精神上得到了“复活”。
玛丝洛娃和聂赫留道夫的“复活”本质是一致的,那么,又怎样解释玛丝洛娃跟西蒙松走了呢?从作品看出,玛丝洛娃只是从理智上敬慕西蒙松之流,但从情感上并不真正爱他。而西蒙松一类的政治犯,虽然冠以“革命者”之称谓,但是他们仅仅只是一些以柔弱反对粗硬,以谦恭与仁爱反对权势者的骄横与暴力,他们本身是反对暴力革命的,只是托尔斯泰式的信徒,实质上并不属于革命者。换言之,他们和聂赫留道无,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的主张,本质上是同性的,仅仅只是体现托尔斯泰说教的方式有异而已。既然,西蒙松是托尔斯泰式的信徒,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荒谬说教的体现者,那么玛丝洛娃最终放弃了聂赫留道夫而选择了西蒙松,就不能充分说明她是走向了革命,更不能证明玛丝洛娃不爱聂赫留道夫。
玛丝洛娃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怕托累、毁灭聂赫留道夫,才忍痛割爱,放弃了同他结合的幸福,恰如聂赫留道夫推想的那样:玛丝洛娃是“为我好而拒绝我,索性毁掉了她的船。”(13)玛丝洛娃的这种选择,在形态上、外表上确实是远离了聂赫留道夫,但是在精神上、内心上却是更加靠近了聂赫留道夫,也就进一步证明了玛丝洛娃完全为别人着想的“复活”,同聂赫留道夫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复活”,实质上具有一致性,真可谓殊途同归的“复活”。
二、乌托邦式的幻想
《复活》完成于1888~1899年,而作者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八十年代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变后的世界观、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主张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则自觉而充分地把这一思想赋予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的“复活”中。
《复活》中所塑造的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在出身、地位、教养、经历等方面是迥然不同的。托尔斯泰把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作为小说主人公,通过他们二人精神上的“复活”来体现作者的主旨,艺术地阐述其改良社会的理想,决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深刻的寓意的。卡秋莎·玛丝洛娃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聂赫留道夫则是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过去,后者侮辱、损害过前者,而前者也曾对后者刻骨仇恨。可是,到后来这两个起先相互对立的人,由于各自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彼此为对方着想,于是乎他们二人终于消除了怨恨,走到一起,同归于好了。倘使人人都能如此,那么俄罗斯的社会矛盾、不合理现象也就解决了,俄罗斯也就成为天堂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而又令人向往的社会改良方案啊!托尔斯泰正是把这个方案献给俄罗斯,期望人人遵守实行。这一点可谓全书关键,把握住了这一点,就不难准确理解整个作品了。
小说中描写了玛丝洛娃在狱中对前来探望她的聂赫留道夫的痛斥和玛丝洛娃所沾染的种种恶习,托尔斯泰是把这些描写作为一个铺垫、伏笔,其目的是以此来展示、衬托玛丝洛娃后来改变初衷,弃却前嫌,为他人考虑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复活”;而写聂赫留道夫早年对玛丝洛娃的诱骗、侮辱、损害,聂赫留道夫庄园里农民的贫穷、破产,客观上对贵族阶级对农奴的压迫剥削有所暴露和批判,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却在于以此展示、衬托聂赫留道夫后来的悔罪——赎罪——道德自我完善的精神“复活”。对于类似这种描写,我们不否认它们客观上的暴露性,深刻的批判性,但是也应予以清醒的认识,不然的话,就会过高估计作者的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头脑中,只有一个“复活”,而《复活》的男女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则是这唯一的“复活”的两个侧面,彼此不能割舍,更不能或缺任何一方。假如代表贵族阶级的聂赫留道夫“复活”了,而玛丝洛娃这个农奴的代表依然如故;或者是农奴代表玛丝洛娃“复活”了,而聂赫留道夫这个贵族阶级的代表却一如既往,那都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复活”。既然是那样的话,整个社会的“复活”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矛盾、不合理现象也就照旧而不能解决了。只有两个侧面——玛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都“复活”了,才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复活”。这样,整个俄罗斯就能依靠博大的“爱”而进入大同世界。
《复活》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期间多次修改,如小说结局,作者曾写成玛丝洛娃同聂赫留道夫结了婚,移居国外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只说明了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复活”,这从根本上讲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他构想的“复活”是不相符的。后来,托尔斯泰又把结局改成玛丝洛娃跟西蒙松走了,写出了玛丝洛娃为别人着想的精神“复活”,从而完整地构建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思想体系。这种结局充分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也更加自觉地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社会改良方案。
纵观托尔斯泰一生的艺术创作,早年的托尔斯泰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并孜孜不倦地探求解决这一社会矛盾的出路,“深深地思索着俄国的历史命运问题”。(14)他企图通过贵族的“平民化”,实现他们道德上的弃恶从善,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为此托尔斯泰赋予“爱”以神秘的力量,如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的尼古连卡、《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涅赫留多夫伯爵,等等。托尔斯泰在中期的艺术实践中,宣扬道德自我完善,不抵抗主义更浓了,社会改良方案也具备了雏形,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康斯坦丁·列文,面对着新的社会灾难,农村破产,冥思苦想而得出的理想方案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一定会得到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15)。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晚年的托尔斯泰思想系统才成熟,创作于晚年的《复活》就是托尔斯泰思想探索、艺术实践的总结,是他对俄国社会出路所提供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理想方案,象小说中的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那样,“要永远宽恕一切人”,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趋善避恶,或改恶从善,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病,“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16)。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玛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复活”,所展现的社会图景,实质上就是乌托邦主义的幻想,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托尔斯泰的乌托邦式幻想,反映了俄国农民“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17),这是作者的不足,是时代所决定的。作为伟大的文化创造者的托尔斯泰,是历史与现实的产儿,他的这种乌托邦幻想,与他的思维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宗法制农民的思维模式
历史孕育了伟大的托尔斯泰,现实造就了伟大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思维模式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列夫·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与时代的紧密关系,列宁曾这样论述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时代,在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里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一八六一年以后到一九○五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以前开始,在这个时期结束以后结束的,但是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列夫·托尔斯泰,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18)。托尔斯泰的精神特质、理想方案和思维模式都产生和形成于这一过渡时期。而这个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农民资产阶级革命”(19)时期,也是俄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过渡、转折时期。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使农奴制解体,从而造成了新的经济形态,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城市经济、商业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孕育了无产阶级,形成了新的历史形势和发展趋向。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既与地主土地占有制、农奴制残余相冲突,又互相统一,这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势态,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化意识呈现为多样化的混杂交融的格局。
虽然托尔斯泰赖以生成的这一时期文化意识是复杂的,但这个时期整体文化的主调或基础,却是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文化意识、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
那么,居于时代主调的俄国农民的思想和心态又如何呢?列宁对此作过精辟的论断,“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了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在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20)。可见,俄国广大宗法制农民的文化心理也是复杂的。尽管宗法制农民在政治上的追求是一致的,也有相同的经济期待,然而实现总目标的途径与手段却明显地呈现出差异性。而且,当时俄国宗法制农民大部分是渴望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与目的。列宁因此说宗法制农民的这种文化意识,这种心态,这种思维模式……,“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21),换言之,托尔斯泰的文化意识、思维模式,是根植于宗法制农民心态和思维模式之上的。
列宁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22)。高尔基在回忆录里又说,列宁赞誉托尔斯泰时常说:“在这位伯爵以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23)。为了塑造出真正的俄罗斯农民,托尔斯泰于是经常深入农民当中。他常常出入农民的茅舍,与农民们促膝谈心,为他们诉说、办事、教书识字、医病议事,等等(24)。而且,终身定居在乡间,和农民们一起体味耕耘的艰辛,共享收获的喜悦,《安娜·卡列尼娜》中康斯坦丁·列文在庄园与农民收割时的情景,正是作者托尔斯泰生活的艺术再现。托尔斯泰尤其熟悉自己庄园的所有农民。所以,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农民的心态、思维模式,有自己深切的认识,并且这些成为他的文化知识框架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也如真正的俄罗斯农民一样,对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有着独特的爱好和诗意的情绪,他儿子谢尔盖在《往事随笔》里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象父亲那样爱好和善于领会树林、田野、草原、天空的美”(25)。托尔斯泰这种领悟和感受大自然美的思维和情绪,与地道的俄罗斯农民的情绪和思维是没有二样的。
托尔斯泰正是由于与农民的长久而深切的交往,使他对于广大农民的非人 处境和不幸的命运,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较为深刻的认识,加之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促使他更加自觉地关心农民的生活和处境。为此,他曾担任过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尽力维护农民的利益(26)。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深入农民,了解了农民,靠近了农民,从而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思维模式方面来了。为此,托尔斯泰常以俄罗斯农民的生活水准来“匡正”自己的生活。晚年的托尔斯泰,愈来愈感到自己所过的优裕生活违背了自己的学说。他在1907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不平等,由于我们在贫困现象的环绕中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我越来越感到痛苦,这就是我生活中隐藏着的悲剧因素”。于是托尔斯泰公开宣布放弃贵族的权利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决心过简朴清淡的平民生活,最后为了彻底摆脱贵族化的生活而毅然弃家出走。
正如列宁分析的那样,俄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是复杂的,尽管他们的心态、思维模式呈交融混杂的局面,大多数宗法制农民表现出忍受、顺从、安于天命、虔信宗教的心态,但是这并非宗法制农民的本质。可是,这种非本质的文化心态却又是当时文化心态的主流。托尔斯泰熟悉宗法制农民,贴近农民,对宗法制农民的这种非本质却又是主流的文化心态,当然也是有切身的感受的。这种忍耐顺从,对宗教的膜拜,本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心态,是畸形文化心理的显示,可是托尔斯泰却把它承继了下来。
当然,如果仅止于此,托尔斯泰就不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了。作为第一流的文学大家的托尔斯泰,其知识文化素养毕竟又不等同于地道的宗法制农民。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知识养育了列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传统、文化心理因素的无比熟悉,也是托尔斯泰本人引以为自豪的。同时,处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托尔斯泰,虽然对西方文化抱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并不一概否定现代文化科学的成就。换言之,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化知识结构,具有明显的传统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即:托尔斯泰承继了宗法制农民的思维模式,又饰之以当代文明。
托尔斯泰对正在变革的社会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他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却无视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意义。他认为农民的非人处境,既受害于农奴制的野蛮残暴,也受害于资本主义的无情贪婪,于是经济更加破产,生活更加赤贫化。托尔斯泰认为,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自然,净化精神,完美道德,皈依宗教——多么象“一个真正的农民”啊!于是就有了《复活》中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双双在精神上“复活”了。可见,托尔斯泰的精神“复活”,改良社会的乌托邦幻想,根源在于他以宗法制农民思维模式为主导的思维模式。
托尔斯泰宣扬的道德自我完善,精神“复活”,是以个别人自身的改造为对象和出发点的。从个别到整体,人人道德净化,完善自我,不仅个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而且整个社会也就随之进化了,社会矛盾也就解决了,俄罗斯也就能建立人间天国了。这种以个别为前提的思维模式,与宗法制农民的文化心态是一致的。
可贵的在于,托尔斯泰的乌托邦幻想,虽然是从个人、家庭、宗族等个体观念出发的,然而终极却是社会整体。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宗法制农民思维模式、文化心态的突破和升华。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宗法制农民思维模式的承继、突破、升华,再加之“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27)。
总之,此文探讨托尔斯泰《复活》中“复活”的实质,辨析其乌托邦幻想的本质,追寻其宗法制农民思维模式的根源,丝毫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恰恰相反,我们期望以此更真切地认识、了解托尔斯泰的伟大,肯定他把“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载入艺术史册的史无前例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是为了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以助于建设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注释:
①拙作《托尔斯泰与乌托邦主义——对复活的再思考》,《达县师专学报》1992年1期。
②~(13)(16)托尔斯泰《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贝奇柯夫《托尔斯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15)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506页。
(17)~(22)(27)《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233页、211页、204页、205页、201页、210页。
(23)《高尔基选读·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24)(26)见《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译传》、《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
(25)谢·托尔斯泰《往事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