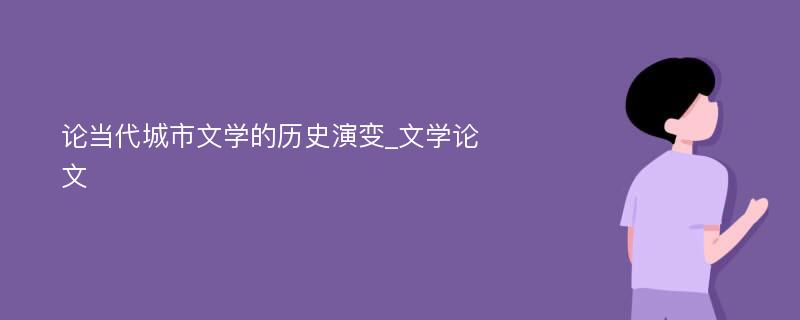
论当代都市文学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历史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农村文学、城市文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划分。在近百年多的西方文学史上,早已没有了这种基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文学划分。例如在美国文学中,曾有过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的称谓,但绝然不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对立;也曾出现寻根文学,但所谓寻根,是一个历史观念,而并非题材的选择。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地道的本土文化产物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因为它们身上负载了太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就都市文学而言,我们也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才能看清它独特的演变轨迹及艺术特色。
一、意识形态化的都市文学
都市是一个国家中最具现代性特征的文化景观。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相对于农村文学的常盛不衰,都市文学的发展道路却是非常的坎坷,尤其是建国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较为优秀的都市文学出现,当然,这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首先是晚生和缓慢的都市化进程使都市文学先天不足。中国作为几千年的农业国,农业文化底蕴异常深厚,而且一直到清末,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都是“以农为本”的国策,重农轻商,总是在压制工商业的发展,这就使以商品经济和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发展非常缓慢。相对于西方几百年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不到一百年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太短了,这样,现代都市所应具有的文化底蕴就非常的薄弱。其次,近现代的历史原因又使都市文学后天失调。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是基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策略进行的,战争所依据的最主要力量是农民,这样,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批判农村中与革命相悖的封建思想、为农民展示幸福美好的未来、争取更多的农民参加革命便成了延安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而当代文学所延续的主要是延安文学的传统,所以它也就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创作。同时,由于农村一直是作为革命的根据地而存在,其思想的纯洁性也就比城市优越得多。而城市是主导意识形态相对薄弱的地区,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思想观念要相对驳杂得多。这样就使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难以用传统的写作思维来应对,当他们根据文艺政策来表现农村生活时,自然是游刃有余,但用同一支笔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现代都市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而正是他们却是当代文坛最初的唯一正统的写作队伍。至于那些原来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当时正面临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他们所要做的正是放弃原有的创作方式,努力地向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学习。所以,虽然他们对现代都市的了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时却不得不夹起尾巴,从头开始重新做人了。
在当代文学之初,由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所以当时的都市文学都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即使一些较优秀的都市小说也是如此。例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部作品在五、六十年代的都市小说中,无论是叙事规模还是艺术特色在当时无疑是非常突出的,文革前出版的前两卷近八十万字甚至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史诗的特点。但其强烈的解释意识形态的目的使作者无法更为完整、全方位地展示上海这一当时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风貌,以致于严重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这部长篇小说所力图表现的是建国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为了表现这一主题,作者使小说中的几乎所有场景都赋予了政治意识形态性。对于以徐义德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来讲,他们整日所作的,就是如何摆脱共产党对工厂的控制和攫取最大的利润,而工人们所作的则是如何在斗争中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之所以说这些情节是意识形态化的产物,是因为它们不仅是工人或资本家工作时间内的活动,而且贯穿、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些公共性的政治生活之外,是没有任何私人性的个体生活的,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是如此。这样,在作品中,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被蒙上了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于是都市生活便被简化为一种斗争场所,人物也都为斗争而生活,不过这时所表现的斗争及人物的性格还都较为复杂,不像以后的作品那样只剩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虽然作家们都在努力使文学为政治服务,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使主导意识形态满意。例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篇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它恐怕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最早的都市题材小说了。小说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和贫农出身的妻子随革命大军进北京后的不同的生活感受和生活态度以及后来彼此的改变。“我”进城后,对一切都感到特别的亲切,“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象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但妻子却显得处处与这个城市不合拍,当“我”让她改一改时,她却说:“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改造我们?”(注: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一语道破了小说的主题,也就是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像“我”那样丢弃解放区的革命传统被城市所同化呢?还是像妻子那样用革命传统来改造城市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终于,“我”慢慢地理解了妻子,“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个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这正是我所没有的!……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象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注: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而妻子也慢慢地改变了自己急躁、固执、狭隘的毛病。这篇情节单纯,人物生动的小说的确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人们进城后的不同的感受和心态,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正是用艺术的形式阐释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讲的那段有名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显然,作品所要描写的是革命队伍如何面对城市这一新战场的现实问题。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这篇在政治上非常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作品,不久即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批判的主要是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作者在写完小说后曾说,他是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注: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第9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我想,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同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左之处了。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是不允许存在“日常生活琐事”这一私人化生存空间的,在一种即将消除生活的私人属性并使之融为公共属性的话语中,仍试图保留一种私人化的“日常生活琐事”自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了。
也正是在这些令人防不胜防的制约的存在,使当代都市文学从一开始就受到重创,作家们无所适从、如履薄冰,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都市文学问世了。此外,文革前涉及都市生活的小说多是一些工业题材小说,如艾芜的《百炼成钢》等,但严格地说,这些作品都只能算是准都市文学,都市文学的真正勃兴要到新时期以后了。
二、冲出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都市终于出了农村的包围,走向了自我成熟,处于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都市的现代化特征也日渐明显,城市化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都市文明的高速发展,成了促成都市文学勃兴的主要因素。而这时的都市文学也终于逐渐成熟起来。出现了诸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程乃珊的《蓝屋》、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夜与昼》、《衰与容》、刘心武的《钟鼓楼》、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等许多较为成功的小说。
成熟的主要标志就在于都市文学正在逐步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的制约,力图真实地展示都市多元的文化态势。在当代都市中,再也没有哪一种话语可以占据文化的中心位置而左右一切,中心的消失使各种话语平起平坐,谁也无法轻视谁。
刘心武的《钟鼓楼》所着力描写的就是八十年代初期都市里的人们面对改革开放大潮的种种复杂心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的那种困惑感。例如书中的老编辑韩一潭,一生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不知怎么搞得,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应接不暇,难以评论,而又无从遵循……”。(注:刘心武:《钟鼓楼》。)这可以说是当时几乎所有人的心声。随着历史的飞速发展,原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它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完整地控制人们的思维与日常生活了,多元的价值观念已展现在人们面前。
而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则更具有现代的都市意识。它全景式地描绘出了上海这一国际大都会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作品连接了城市与农村,商场与情场,企业与银行,人心与世态等各个方面,在广阔的场面与背境及纷繁的线索穿插与撞击中,把大上海复杂变幻、光怪陆离的风貌展示了出来,紧紧地扣住了时代的脉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中揭示了当下上海人那种退化的文化心态。时代正走向现代化,而人们的心态却远远落后于此。小说中符老先生最能说明这一点,他认为:“我发现大上海患的是‘衰弱巨人综合症’!到处以老大自居,自满自傲,在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里,却弥漫着各种各样封闭到水泼不进的心里状态!……可怕的不是落后,却是这种死不接受事实的态度,到处依然是狂妄自大……我看今天的上海人哪,多是愚蠢过头的聪明,或是聪明过头的愚蠢!”(注:俞天白:《大上海沉没》。)当年东方第一大都市的开放、气魄、灵活、精明等优点已所剩无几。冒险精神变成了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吸收融合变成了惟我独尊的排外心理;精明能干变成了斤斤计较,这都完全失去了国际大都市应有的气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上海的主要危机,告诉人们“大上海沉没”并非危言耸听,这样下去被历史所淘汰将会成为必然。
从八十年代的都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作家们已不再以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为创作目的。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层面。同时,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衰弱,知识分子叙事话语得到了最为有力地展示,现实批判性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历史代言人的自信使他们自觉地融入社会变革之中,“穷”、“达”都要兼济天下的豪情使他们坚信自己能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启蒙者的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八十年代成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最为风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作家在创作都市文学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全知”的叙事模式、“全景式”的描绘方式,力图“全方位”地展示变革的时代与变革的都市。这正是知识分子自信心及其精英叙事话语发挥到极至的表现。但是这种自信心在八十年代末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文学内部的自我瓦解,先锋作家们消解了过去的一切价值观念,理想的乌托邦仿佛离人们越来越远;无尚的崇高精神在王朔等人的谈笑间灰飞烟灭。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击更使他们一蹶不振。同时,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商品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精神价值走向文化的边缘,人文知识分子随之从启蒙导师沦为了没有观众的演员。凡此种种,也都促成了都市文学在世纪末的新转化。
三、都市民间叙事话语的浮出水面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当代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精英文化那种一呼百应的地位被追求感官愉悦、日常生活和商品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所代替,随着不同层次和利益集团、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同时共存、多元共生时代的到来,文学叙事话语多元呈现的时代也随之到来了。那种在八十年代由“大写的人”所营造的乐观、亮丽的“宏大叙事”已逐渐被灰暗、沉闷的氛围所取代。一股强烈的虚无主义气息弥漫于社会,弥漫于精神的旷野。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迅速解体,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确立,于是,无主流、无中心、多元共生便成为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都市文学也是如此。
在世纪末都市文学的多元话语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市民叙事话语的崛起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衰落。市民阶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一直是处于边缘的状态。或者基于阶级对立的观念而漠视其存在;或者基于塑造所谓“新人”形象使其始终处于受改造、被批判的地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衷情的是呼唤“卡里斯玛”人物的出现,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从来都不被认可,但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加强而国家直接干预减弱,便自然地削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民间各种经济机构的大量繁殖更使都市出现了意识形态暂时无法涵盖的新的空间,“在经济改革的促动下而繁荣发达起来的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谋求解脱它们只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解脱与国家的行政联系。由于它们获得了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主性,经济经营组织越来越多地在没有官僚行政渠道的垂直性居间调停下进行相互间的交换往来。这样,市民社会基面的整合在经济领域得到了促进而且开始与国家相分离。”(注: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见邓正业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正是市民社会的崛起带来了市民叙事话语在世纪末都市文学中的兴盛。
池莉在她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有这样一段寓言式情节,写的是一个被称为作家的“四”和一市民“猫子”之间的对话:
猫子说:“他妈的四,你发表作品用什么名字?”
四唱起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猫子说:“你真过瘾,四。”
四将大背头往天一甩,高深莫测仰望星空说:“你就叫猫子吗?”
猫子说:“我有学名,郑志恒。”
四说:“不,你的名字叫做人!”
猫子说:“当然”
然后,四给猫子聊他的一个构思,四说准把猫子聊得痛哭流涕。四讲到一半的时候,猫子睡着了,四放低了声音,坚持讲完。
这段对话揭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某种程度的隔阂与对立,二者无法沟通,它展示出知识分子试图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来唤醒大众的失败,那种以拯救的欲望来重建启蒙话语的激情并未得到回应,显示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
相对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衰落,市民阶层叙事话语的崛起更引人注目,这种民间话语的精神取向可以用何顿的一篇小说的题目来概括,那就是“生活无罪”。在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中,往往表现出生存大于一切的新的价值观念,为生存而采取的各种行为,哪怕为传统伦理道德所不齿,为现代法律所不容,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九十年代的都市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城市,金钱成了支配一切的杠杆,清高、道义、爱情、坚忍等传统价值所肯定的品格,在它的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所以,固守这些传统无疑是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面对的将是一无所有。而把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踩在脚下并闯入这一欲望化的世界去进行搏杀时,人们似乎不必有什么可耻、自卑的感觉。原因就在于“生活无罪”。这就是当下都市民间话语的精髓之所在。
在何顿的《生活无罪》中,眼望成为画家的“我”在朋友奢华的生活面前被彻底震撼住了,于是跻身商海,从倒电影票到成为公司经理,他的奋斗经历正是一个放弃理想而转向世俗的过程,因为“我感到这根精神支柱是那么稚嫩,象森林中的幼苗,禁不起脚一踩。”他的放弃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因为用金钱编织的世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这篇作品及他的《我们像葵花》、《就那么回事》等作品,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市民社会由其最初的朦胧的文化要求而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粗鄙的价值理论,由于它来自社会实践,所以具有一种使人无法回避的残酷性。
张欣无疑敏锐地感到了都市民间这一新的话语形态,在她的《爱又如何》中,尽管通篇充满了对可馨与沈伟在贫困中能相濡以沫的希望,但又无可奈何地让可馨说出了“人不可能活的纯粹”这句内心的感触。人不可能在幻想中生存,你想过自尊、清闲的远离经济大潮的生活,但外面的世界不会忘记你。可馨的清高与坚忍根本不能同大趋势相抗衡,以致于连爱情这一最后的避风港也难以守住。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权威的承认,既是一种无奈,又是唯一的出路。在《此情不再》中,朱婴的先与冯滨分手,后与思浩永别,同样是由于两个男人无法抵抗金钱的诱惑,冯滨得到了钱而失去了幸福,思浩为了金钱而落得身首异处,但他们同样是自觉自愿。他们并非没有看到前途的难测,但又同样知道钱在生活中的地位,于是只能拿生命或幸福去赌一下。作者很少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谴责或批判,而只是发出淡淡的叹息,因为在作者看来,他们只是在商品大潮的裹挟中身不由己而已。这正表明了作品的市民化的叙事倾向。
除张欣、何顿外,邱华栋、钟道新、唐颖等人的许多小说也都从各个侧面对当代大都市的变幻莫测、物欲横流作了多方位的描述,但对都市民间叙事话语有着明显展示。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作品虽然还是很明显地采用知识分子话语进行叙事,但对都市民间的世俗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训话或批判,而是一种饱含深情的体味。王安忆的《长恨歌》这部把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城市的历史交融在一起描写的长篇小说,叙述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物对话的减少,代之以作者的间接叙述,以及对语言的刻意雕琢、大段的抽象思辨和对人物情感的透彻理解、对人生悲观的深刻体味等,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叙事话语。但对王琦遥等人那种典型的小市民生活方式,作者已不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我们无法苛求每个人都能站出来与时代和环境相抗争,而且他们本身虽历经坎坷但毕竟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相对于历次战争、政治风浪中的那些凄惨的人间悲剧,他们处于始终是政治风浪旋涡中心的上海而能保留少许平静的生活,已是很值得让人庆幸了。这种过去一向受到指责的小市民文化,在作者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这就让人想起了张爱玲的那句话:“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注: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认识到这一点看来真是不容易,直到世纪末的今天,才真正让人体会到:“人们用极其崇高的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代进步或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注: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见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恐怕也正说出了都市民间叙事话语在当下中国的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