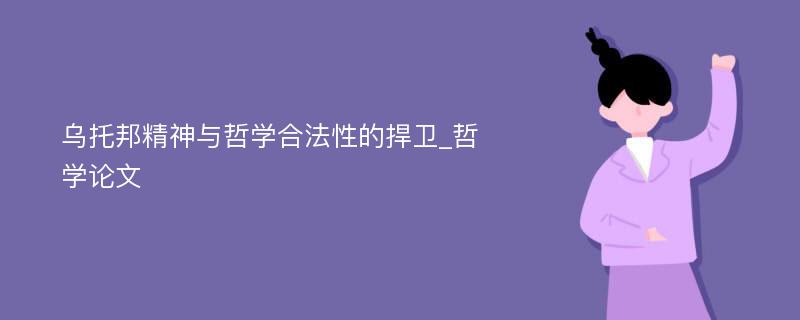
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合法性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大不同在于,它总是需要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①进行辩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的终结”成为不少流派和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主张,“虽然哲学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在20世纪,哲学却受到了来自哲学家的一连串史无前例的指责”。②在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或诉诸无反思的常识,或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对哲学的存在价值同样提出了种种质疑和否定。这使得为哲学的存在合法性进行自我申辩,已成为“哲学家所遇到的最尖锐、最有意义、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问题”。③要为哲学的当代合法性进行有力的辩护,基本前提在于拯救哲学所特有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④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是事关哲学存在合法性的性命攸关之处,同时也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本文将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语境中,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围绕着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当代合法性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对哲学的当代合法性进行专门的探讨。
一、乌托邦精神的危机:哲学的当代合法性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笔者所使用的“乌托邦精神”从“乌托邦”这一概念引申凝练而来。文中不对乌托邦思想进行具体探讨,更不涉及“乌托邦”设计的种种具体细节,而是从中提炼出“乌托邦精神”这一概念,特指哲学之为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
对于“乌托邦”一词,人们经常从常识和科学的观点出发,把它斥为“虚幻”和“空想”。常识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从它的观点看,“乌托邦”无异于是没有经验根据,也无实际用途的“幻想”或“幻觉”的代名词;而从科学主义的观点看,由于“乌托邦”无法被实证方法和经验手段予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属于“无意义”的“胡说”。在思想史上,曼海姆重新阐释“乌托邦”的含义,使之摆脱上述常识和科学主义理解,并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概念。他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区分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把“乌托邦”规定为“超越现实,同时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结合力”的精神取向。乌托邦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的消失,将“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⑤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学者,例如布洛赫、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詹姆逊、哈维等人,从不同视角对“乌托邦”所包含的重要的哲学内涵和意义进行了阐发。⑥他们的工作启示我们:超越常识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从一种哲学价值论的视角来理解“乌托邦”,人们将发现,在被常识和实证科学认为“不切实际”和“虚幻”之处,恰恰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真实”与“价值的真实”。在种种乌托邦设想和想象中,贯穿着一种不断超越现存状态,追求更美好生存样态的精神,一种立足于可感现实并不断超越当下境况的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追求,一种“相信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信念”。⑦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现状保持永不停止的反省和批判态度,并向其敞开另一种“更值得生活”的希望空间,不断呼唤和引导人们追求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由于这种乌托邦精神,我们就“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⑧
本文所指的“乌托邦精神”,正是在上述区别于常识和科学主义立场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在哲学发展过程中,以一种理论思维和反思意识的方式表达和显示这种乌托邦精神,构成哲学的一种重要品格。纵观哲学史,超越可感的当下存在,指向无限性的终极眷注,成为贯穿于其中最为强劲的精神定势。哲学家们虽然具体观点不同,但都努力在最深层面和最根本意义上去把握世界、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生活的价值,并由此表现出一种对于“终极性”的渴求。该渴求在“存在论”上追求“终极存在”,在“认识论”上追问“认识何以可能”的终极基础,在“价值论”上则探寻人的“终极意义”。在这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中,哲学向人们彰显出一种既立足于现实同时又否定现实的超越性理想,它要求人们克服自身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存事实的消极默认,避免人的思想在非批判和质疑中陷入僵化和教条,呼唤和推动人们从当下有限的现实中跃起,永远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在此意义上,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说道:“乌托邦精神是所有真正哲学的灵魂,并且,哲学不仅是乌托邦式的,而且要为一种理性的乌托邦辩护。”⑨
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其独特的追问和思考方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哲学家面对眼前的现象世界,却要否定它,以理性的方式去寻求和建构更为“本真”的“存在”。对此,马尔库塞概括道:“哲学按照真理来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义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了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找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⑩这表明,哲学的追问和思考不同于日常意识与实证科学。常识安居于自在自发的世界,对于现存状态持“习惯”和“接受”的基本态度;实证科学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以“客观性”与“可验证性”为最高标准。与它们不同,哲学不仅不以接受、肯定现存状态为满足,恰恰相反,它以否定和超越现存状态、追求比现存状态更美好的状态为己任。这种独特思维方式所体现的乌托邦精神,使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一个特殊维度的存在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确证。
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长期以来是哲学家们十分自觉的理论意识和精神支柱。对此,伯恩斯坦的论述颇为中肯:“贯穿形而上学传统的冲动是乌托邦冲动,在这种活动中,我们进行的怀疑保有了活生生的灵魂,并对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从不停止质疑。……形而上学的怀疑要求我们揭示并探究批评所包含的理想”。(11)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经典的乌托邦精神的诞生地,成为后人乌托邦想象的重要思想源泉。康德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带有转折性的重要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展现,这尤其体现在其对“目的王国”和人的“价值主体性”的论证中,康德深知“人的确是足够罪恶的”,但在任何时候都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并由此建立的目的王国中,人真正超越它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污浊”本性,并使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得以确立。(12)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清醒地看到了“人们的目光过分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为此,人们必须在精神力量的激励下,不断否定和克服一切“不合理”的障碍和“僵硬的事实”,在精神力量的激励下,建立起“新世界的形象”。(13)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概念为核心的辩证法理论所体现的正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
然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对哲学乌托邦精神的批判、否定和质疑,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而引人注目的现象,并因此构成了对哲学合法性最具根本性的挑战。
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乌托邦精神的批判、否定和质疑,关涉到20世纪以来许多重要的哲学运动,如语言分析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具体分析。概括而言,其内在逻辑表现如下。第一,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和教条等同起来,在批判和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一同冷落与抛弃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传统形而上学迷恋于超感性的终极存在,这使得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贯注着一种“绝对意识”,即总是设定无限完美的“另一个世界”作为“现存世界”的替代物,并设定了绝对的、无条件的“终极存在”作为“另一个世界”真理性的根据和保证,在此意义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原则和思维方式一样体现出独断性和教条性,宣告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也必然随之宣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终结。在这点上,尼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道:“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因此,“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14)第二,揭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虚无主义本性。以“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二元对立为基础,通过前者对后者的贬低和否定来显现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这是长期以来哲学的思维定势。但这是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此岸现实生活的否定与瓦解为代价的,而现实生活的瓦解,实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否定和瓦解,这表明,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虽然以超越性的价值理想为追求目标,但在根底上却恰恰具有价值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此而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自我挫败与自相矛盾的。海德格尔无疑是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代表者,他通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的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15)第三,揭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非批判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意志。哲学对现存世界的否定和超越以彼岸世界的终极存在为根据,而彼岸世界的终极存在是由哲学家的理性慧眼所“发现”的,因此,哲学代表着凌驾于一切生活领域和具体知识之上的超级话语,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完全由这种“超级话语”所规定和支配,在此意义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不过是自诩为人与社会历史的立法者、预言者和裁判者的哲学家的“思想自恋”,表达着自身企图占据话语权力中心,体现着哲学的学科帝国主义倾向。在这种企图与倾向的支配之下,极易助长一种自命掌握开启未来之谜钥匙的幻象,以及以真理为名塑造未来的野心,并对现实的社会历史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福柯对“总体性话语压迫”的解析、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暴力”的反思、拉康对“主人话语”的批判,等等,即是从不同视角对此所作的揭示。
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对乌托邦精神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根源。美国学者雅各比曾用“乌托邦之死”来概括当代盛行的文化气氛,其根本特征是“相信未来将比现在更加美好的这种信念已经消失”。(16)这体现在当代文化的诸多层面和领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针对苏联所代表的教条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已取得了最终胜利,“历史终结论”更进一步认为,随着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理性已获得了一劳永逸的确证,人类历史已经达到了至终究极的圆满状态。很显然,按照这种观点,“未来”不过是“现在”的同质延伸,人类超越性的乌托邦精神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社会层面上看,哲学对待乌托邦精神的这种态度与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功利主义成为最为强大的价值观密切相关。社会理论家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韦伯的“世界的理性化”、卢卡奇的“物化”、哈贝马斯的“劳动乌托邦”等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功利主义“代表着最为典型的现代性伦理——如果现代性有伦理的话”。(17)在这种世俗化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人们宁愿沉溺于“贪婪攫取欲”的满足而对不能带来现世“实惠”的乌托邦精神采取一种冷漠、厌恶和无视的态度。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中乌托邦精神的衰竭,哈贝马斯说道:“如果乌托邦这块沙漠绿洲枯干,展现出的将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沙漠”。(18)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反思、批判和否定,既是从根基处对哲学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了当代文化和当代人对于超越性价值理想的冷漠和怀疑。因此,捍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既是对哲学当代合法性,也是对当代文化和当代人的价值理想进行辩护。
要捍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需要直面并回答三个前提性问题:第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当代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第二,以往哲学的自我理解及其所体现的乌托邦精神究竟存在什么深层理论困境?第三,在当代理论语境中,应如何重新理解和阐发哲学的乌托邦精神?
二、人的现实生命存在: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的深层根据
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我们认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人的生命存在中有着深刻根据,它根植于人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凝聚着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体现着人们对于自身生存需要和发展的觉解与憧憬,是推动人不断走向自由与解放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力量。可以说,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人生命存在的乌托邦精神的自觉理论表达。正是在这里,哲学的存在合法性获得了最为坚实的根据。
“认识你自己”,自古以来是哲学最高的主题。但另一方面,人又是所有存在中最难把握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根源于人的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
人生命存在方式的特殊性,最根本的在于他不是单一和单重性的存在,而是处于“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物性”与“神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矛盾性的两极所形成的“张力”之中,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两极”之间的否定统一,同时又不断地打破这种“张力”,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的空间,构成了人特殊的生存方式。
人来源于自然,这一点决定了“自然性”构成了人的重要性质,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9)但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分别在于,动物完全从属于其本能生命,“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20)而人却从不满足于自然生命存在,而是要以自然生命为基础同时又突破自然的主宰,通过实践活动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成“属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环境,对此,马克思说道:“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21)这表明,人的生命存在又具有自为、自主和自由的本性。
人的自为、自主和自由本性,决定了人摆脱了一切“前定本质”的规定而具有了面向未来的“生成”品格。动物的存在遵循单一的“自然”尺度,因此,它的“存在”被其“本质”(即“自然”)所预先规定。但是,人不是自然现成的、被“完成”的作品,而是需要通过自主性创造、自为性活动和自由性追求而成就自身。因此,不断面向未来的“自我超越”,成为人的生命的根本特征。布洛赫把人规定为“希望的主体”,海德格尔把人理解为以“将来时间”为导向的生存活动,舍勒把人界定为“超越的意向和姿态”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这一独特生命存在本性的阐明。
人的自我超越本性是人区别于自然物的根本特征,但这种“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人能达到“无限”。人总是居于“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之中,并不断地从“有限”向“无限”敞开。这里所说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指人作为自由的超越者,其超越的前提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无论是人的理性能力、实践能力乃至个体的生命,都具有“有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才为人的自我超越和创造提供了基础和空间,如果人彻底摆脱了“有限性”,也就失去了超越和创造的驱动力。二是指人的自我超越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圆满的结局,不可能达到只有神才能达到的摆脱一切矛盾、绝对自由的理想状态,否则人也将同样失去超越和创造的必要性。在此意义上,人又区别于“神”的存在。
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处于“自然性”与“神性”这两极之间,同时又通过实践活动否定性地统一该两极。一方面,人天生具有“自然性”与“神性”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区别于单纯的“自然存在物”与“神性存在物”,前者是孤立、静止和封闭的,后者是极端完美和理想化的。只有在人特殊的生命本性中,贯穿着一种不断超越现存状态,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渴求,一种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并不断向未来可能性自我超越的冲动,它表明:乌托邦精神是人的生命所特有的“生命精神”。
人特殊的生命存在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解方式,以一种反思意识的理论思维方式对人独特的生存方式进行自觉理解,正是哲学的重大功能。如果说乌托邦精神是人特有的“生命精神”,那么,哲学因其对人的这种独特生存方式和生存本性的自觉理解,使得乌托邦精神成为哲学不可消解的重要精神品格。
要自觉理解人特殊的生命存在,首要前提是克服从“两极对立”观点去寻求人的单极本性,由于人生命存在所具有的“双重”和“矛盾”本性,使得无论是从“自然物质”一极,还是从“神性”(指极端的自由性与无限性)一极出发,都将导致人的生命存在抽象化,这是哲学在把握人的存在问题上的最大困难。在哲学史上,康德和黑格尔对此问题作出了特殊贡献。
康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通过“理性”批判,自觉地揭示了人的“理论理性”的有限性,并以这种“有限性”为基础,论证了人在实践领域所具有的自由超越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理论理性在把握“无条件总体”时必然陷入“先验幻象”,因而必须限制思辨理性的使用。但康德揭示“理论理性”的有限性,并不是要限制人的自由超越性,相反,他恰恰要为后者提供广阔的空间。如果说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我们必须依赖经验,但道德法则的根据不能到经验中寻找,只有超越经验对象的限制,才能确立道德法则的根据:“这正好就是使人超越自己(作为感觉世界的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将他与只有知性才能思想的事物秩序联结起来的东西,而这种秩序同时凌驾于整个感觉世界之上,凌驾于那与感觉世界一起可以在时间里被经验地决定的人的此在以及所有目的的整体(只有它才切合于作为道德法则的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之上。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只是人格而已,亦即超脱了整个自然的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性,而这种自由与独立性同时还被看作是存在者委身于特殊的、即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给予的纯粹实践法则的能力”,(22)超越经验世界中感性事物的诱惑和束缚,遵循理念这一“无条件的总体”所提示的“至善”方向,使道德法则的力量在人不断自我改善、自我提升和超越的实践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康德的上述思想,显示了他对于人生命存在中“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张力的深刻理解以及以澄清人的“有限性”为前提而对人的自由超越性的憧憬。正是在此意义上,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把康德引为自己的同道,认为康德哲学中所贯彻的正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
黑格尔的重大贡献则在于,他的精神辩证法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并生成自身的自由和自为本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精神作为“实体”之所以同时又是“主体”,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自由能动精神,精神从其直接性出发,自己规定和展开自己,不断地否定自身又不断扬弃这种否定性而返回自身,这是一个不断否定自身的抽象性、并不断达到具体性、丰富性和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但是,黑格尔对人自我超越的自由创造本性的理解是以否定人的自然物质本质为前提的,“人”被异化为抽象的精神存在而成为了“上帝”的代码,他通过凸显精神的能动性和自由性否定和超越了“物化的人”,但与此同时却又把人抽象化为“神化的人”。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为人的发展历史“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23)
马克思对该问题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把感性的生活实践活动确立为人根本本性的生存方式,既克服了康德把实践仅局限于道德领域的局限性,同时也克服了黑格尔把实践理解为“精神劳动”的抽象性,并以此为根据,对人特殊的生存本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以实践观点为根据,哲学将真正贯彻“矛盾”、“辩证否定”和“历史发展”的观点,以一种符合人本性的方式实现对人的把握。
首先,在实践观点的视野里,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活动在本性上就是“对立统一”的或“矛盾”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物性与神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矛盾关系在人的生命存在中内在统一,使之既不像在纯粹自然世界一样,受纯粹自然因果性支配,也不像在纯粹神性世界一样,受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和目的性所支配,而是处于二者的辩证张力之中。要理解人的这一本性,就不能运用知性思维方式,该方式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24)以之来把握人,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生命存在的瓦解、分裂与抽象化。辩证法的“矛盾”观点正是克服了“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在“两极对立”的否定性统一中把握人的“矛盾”本性。黑格尔说道:“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25)在黑格尔那里,“矛盾进展”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这实质上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矛盾本性,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活动性置换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即感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从而使“矛盾性”和“对立统一性”自觉成为把握人的理论观点。
其次,在实践观点的视野里,“否定”和“超越”是人的存在的固有本性。要理解人的这一生存性质,就不能运用把握物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物的存在完全是由自然赋予的前定性质所规定的,具有“本质前定”的性质,因此,“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物的存在方式正相适应。但如果运用它来把握人的存在,就会窒息人的自我否定性和超越性。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点正是对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克服。马克思说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6)马克思明确把“作为推动原则与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视为辩证法的最重大成果,并认为它的伟大贡献在于描述和表达了人的自我产生和创造过程,从而使辩证否定观点成为把握人的自我否定性和超越性的自觉的理论观点。
最后,在实践观点的视野里,任何声称历史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教条主义和独断论都与人的生存本性相违背。物的存在是给定的和自在的,被自然界规定其存在界限,因而它在本性上是“非历史”的;上帝是“永恒常在”的,它已经自足圆满,无需向未来敞开。与此不同,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历史”中寻求“超越”,“成为其所是”同时又不断地“否定其所是”。这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没有“历史的终结”,没有“完美的历史终极状态”,只有面向未来的不懈追求和创造。由此,马克思才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8)
在矛盾性中不断自我否定和超越,向未来更为美好的世界敞开,这是在人的生命存在中所体现的乌托邦精神;而贯彻矛盾观点、辩证否定观点、历史和发展观点的哲学真正以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思维方式,自觉实现了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理论表达和理解,在这种自觉表达和理解中,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哲学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运用其辩证法理论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它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承认深植于人的生命本性中的乌托邦精神,也就难以否认,乌托邦精神是哲学不可消解的理论精神,哲学也因此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圆周中不可终结的重要扇面之一。
三、乌托邦精神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内在冲突
现代西方哲学对乌托邦精神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深入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对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理解和表达中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即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里所谓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特指贯穿在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现代西方哲学家用种种不同的提法予以指称,例如“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基础主义”、“客观主义”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共同分享着如下重要特征。
第一,它以对“无条件的总体”的把握为最终目的,或者说,它的根本目标是获得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高原理和终极根据。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过十分深刻的分析: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哲学的“先验理性”具有“原理的能力”,其旨趣在于“把理性看作在原理之下获得知性的规则的统一性之一种能力。据此,理性就绝不直接致力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是致力于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而给知性的杂多知识以一种验前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29)这即是说,哲学理性的根本功能是寻求绝对的“无条件者”,并以之为根据,来实现知性知识的统一性。这种“无条件者”包括“我思主体”、“世界总体”与“上帝”等,康德把它们称为“先验理念”。哲学把握了这种“无条件者”,也即获得了可囊括和统领一切现象和领域的“最高真理”。
第二,与上述内在相关,它所追求的最高原理和终极根据,必然以超越历史的“永恒在场”为根本特征。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无条件的总体”,代表着“永久地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30)在它看来,“变化”和“生灭”是缺乏真实性和实在性的标志,同时也是产生一切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根源,因此,只有逃避时间性和历史性,进入固定不变和绝对确定的实在领域,才能使人的认识乃至人的整个生命脚踏大地、获得坚实的根基。消灭时间、进入永恒,克服历史,实现终极的“现时性”,这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的固有之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形而上学所坚持的时间观概括为“现在性时间观”,并指出历史性之遗忘乃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质。
第三,它必然是一种瓦解和抹杀矛盾的思维方式。为了把握“存在”,形而上学把世界分裂为“存在”与“存在者”、“本质”与“现象”、“真理”与“幻象”、“必然”与“偶然”、“永恒”与“生灭”等“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双向度的领域。然而,形而上学确立这些矛盾关系,最终目的却是要消解和终结它们。在这众多双向的矛盾关系中,前一项居于主宰性的地位,形而上学要求以前者为基础,来“统一”和“吞噬”后者,从而实现矛盾的“和解”。因此,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矛盾关系的双方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交互关系,而是等级制的统治和控制关系,它最终追求的是消解矛盾关系的单极统一性。
第四,它必然是一种把理论神圣化并因此轻视和贬低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理性所要把握的是一个超感性的永恒常驻的、普遍性的实在领域,与之相比,人的现实生活领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生成性”的领域,而“生成性”意味着转瞬即逝、崩溃毁灭,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它无论在认识还是价值等级上都居于“低贱”的地位。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通过抽象,把一切都置换成逻辑范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31)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代表的必然是一种颠倒逻辑范畴与现实生活、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以前者来压抑后者的理论逻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传统哲学对超历史的、无条件的、终极的、神圣存在的追求,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否定和批判现存世界、追求更完美世界的超越精神,这表明,西方传统哲学内在地体现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这是它所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但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对乌托邦精神的表达,始终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原则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形而上学的理论方式和理论原则与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冲突和矛盾,它使得后者无法真正得以彻底地体现,并最终成为其桎梏。
首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无条件总体”的迷恋将最终窒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表征着人在其历史有限性中不断面向未来生成的可能性。它自觉地承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32)因此,永保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不停息地“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哲学永远不会终结的任务。与此不同,传统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对“最高原理”和“最终统一性”的追求,去获得具有终极权威性和最后确定性的至上真理与绝对知识,这表明,它最终寻求的不是“超越性”而是“绝对性”,不是向“未来敞开”,而是“永恒在场”,不是“批判”与“否定”而是“同一性”与“肯定性”。然而,倘若哲学掌握了“绝对”和“终极”,那也就意味着它不再需要否定和超越自身,也无需想象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马克思曾这样论述道:“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33)很显然,如果哲学已经掌握了“一切谜语的答案”,也就无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视野就被关闭,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也因此而遭到窒息。
其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人的“矛盾性”的消解瓦解了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动力源泉。在生活实践观点的视野里,人是一种矛盾性、双重性的存在,它决定了人必须在历史中寻求超越,在有限性中寻求无限性,在束缚中寻求解放。离开了这种张力,人就失去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可能,也失去了面向未来的真实渴求和驱动力。然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否定矛盾为归宿,人由此成为只按照单一尺度存在的存在者,人或者被“物化”成自然存在物,或者被“神化”为虚幻的幽灵,这实际上瓦解了人生命存在中的“内在张力”,消解了人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真实动力,因而,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无法得到充分彰显。
再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人的历史性的消解,必然窒息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维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总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开展其生活,这种历史性规定了人的“有限性”或“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表明人的消极无为。恰恰相反,历史性和有限性为人面向未来进行自我否定和超越提供了真实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说:“永恒满足的死敌是‘时间’,即内在的有限性,即所有条件的根本。因而,完整的人类解放概念,就必然包含与时间斗争的前景。”(34)如果消灭“时间”并达至“永恒满足”,那么,也就失去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消解人的历史性而追求“永恒在场”,实质上等于要求哲学寻求“永恒的满足”,去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35)失去了“历史意识”,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不可能得到彻底体现。
最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现实生活实践的漠视,消解了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现实根基。现实生活实践是乌托邦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植根于对人独特的生命精神的自觉理解。但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以哲学思辨消解了生活实践,这种颠倒使得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失去了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而成为了“无根”的浮萍。
以上四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表明:传统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对最高原理和终极统一性的追求,为人的生存发展确立永恒的、超历史的“最高支点”,但这与人通过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在“矛盾”中自我超越和否定,向未来敞开和生成的生命存在特性是相冲突的。传统形而上学追求最高原理和终极统一性,并以它们作为无条件的根据,来规范和要求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但由此却使哲学对超越性价值理想的追求,异化为外在于现实生活并束缚人历史发展的僵化教条与虚假偶像。由于这种矛盾和冲突,哲学窒息了人生命存在的乌托邦精神,同时使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陷入扭曲、教条和独断。这正是导致现代西方哲学对它采取激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并使哲学的合法性陷入危机的深刻理论根源。
四、乌托邦精神的当代内涵与哲学不可消解的合法性
如何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拯救和重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要回答这一问题,根本前提是重建哲学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重建,我们将自觉认识到,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不是哲学悬空思辨的结果,而是在对人独特的生命存在的理解中,以一种反思意识的方式所凸现的哲学的精神品格。它以人的现实生命存在为根基,后者构成了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以这种自觉理解为基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将真正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在“面向未来”和“面向现实”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维度中,使其得到充分彰显。
面向“未来”的维度,是指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将彻底抛弃对“永恒在场”的终极实在的迷恋,而体现为对“不在场”的未来希望的不懈追求。据考证,“乌托邦”(Utopia)一词源自古希腊,由“无”和“场所”两个词构成,即“不在场”(nonpresence)或“不站在对面”之意:(36)它不存在于时间中的某一瞬间和空间中的某一点。在这种古希腊思维的原始经验中,包含着对“乌托邦精神”的非形而上学理解。然而,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支配下,哲学把本应“不在场”的“乌托邦精神”“在场化”,结果使其失去了本应具有的面向未来的超越维度。而“未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就在于它的“不在场”性。真正意义上的“未来”,意味着“不站在对面”和永远向可能性敞开,意味着人们永远不可能把它实体化,并把它一劳永逸地收入囊中。一旦被“在场化”,也就表明“未来”维度的消失。破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是要拯救对“不在场”的未来希望的追求精神。
在哲学史上,康德曾通过“建构性理念”与“范导性理念”的区分,较早地对乌托邦精神的这一内涵进行了深入阐发。康德指出,“世界总体”、“上帝”、“灵魂不朽”等“先验理念”,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捕捉的“终极存在”“绝不具有建构性的应用,以至于某些对象的概念会由此被给予,而且如果人们这样来理解它们,它们就纯然是玄想的(辩证的)概念。与此相反,它们具有一种杰出的、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范导性应用”。(37)所谓“建构性应用”是指“先验理念”作为“在场”化的“无条件总体”,对“概念杂多”的“统一”作用,康德深刻地论证了,“先验理念”的“建构性应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欺骗性的“先验幻相”。而“范导性应用”则与此不同,它意味着,“先验理念”的功能不在于达到“无条件的绝对”,而在于使人们意识到自身之不足,不断超越自己,面向未来,去追求更高的知识和道德理想。在“范导性应用”的意义上,“先验理念”表征着永不可能被“在场化”的、但同时又不断引导人们自我超越的未来召唤。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哲学家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深入反省,对哲学乌托邦精神的这一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例如,布洛赫把乌托邦精神把握为“趋向美好未来的意向”,(38)哈贝马斯认为其“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初衷是要在“后形而上学”的地平线上“重建乌托邦”,(39)罗蒂则明确表达要以“后形而上学希望”取代“柏拉图主义”对“终极实在”的迷恋,认为“如果说实用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就在于它以更美好的人类未来观念取代了‘现实’、‘理性’和‘自然’之类的观念”,(40)詹姆逊强调乌托邦精神“来自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某种未来……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向我们发出关于未来的警示”。(41)其中德里达颇具代表性,他用“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见的可见性”来描述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特别是其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理想,认为它们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无限的范导性理想,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的终点,或是无限接近的极限”,而不能被理解为“现成的真理”与“永恒的原则”。作为“不在场”的存在,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作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更能显现和发挥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反之,把价值理想当成一种“实体性”的“在场”,其结果恰恰会导致“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42)从而陷入种种教条主义的僵化与独断。
真正的哲学所抱持的对未来希望和追求,不是脱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必然趋势的“空想”,相反,它是以对这种必然趋势的自觉理解为前提的关于“人的现实自由和解放何以可能”的不懈追问和探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43)“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代表着两种有着根本区别的历史观,“从人们所说、所设想、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对未来的设想必然是抽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而“从人间升到天国”,则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通过对以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运动的自觉揭示,回答人生存发展的现实根据,确立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前提。正是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才这样表达了对于人与社会的未来希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才在后来的著作中进一步这样描述人的自我解放进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5)“人的自由个性”作为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人和社会的未来希望,不是哲学家“世界之外”的空洞遐想,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并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等历史环节,因此,它在最深层体现了历史运动的根本趋向。
马克思哲学对未来希望的不懈追求精神,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与空洞玄想,恰恰相反,它是以对“现实”自觉而深入的理解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6)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把“现实”当作“实践”去理解,这表明:第一,“现实”不是静止的“现在”,而是在感性实践中不断生成并向未来敞开的历史性过程,“面向未来”是“现实”的重大特征;第二“现实”不是永恒的“现存”,而是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变和超越的对象,“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是“现实”的另一根本特征;第三,“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僵死“事实”,而是一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空间。马克思对“现实”的上述理解,既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直观性”,也克服了唯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抽象性”,深刻地体现了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哲学对未来希望的不懈追求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外在超越”而真正体现了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
同时,强调对未来希望的追求精神,也并不否定人类历史形成的积极文明成果,相反,对人类历史形成的积极文明成果予以切实的尊重和继承,是追求和创造未来希望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曾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7)这里所谓“现有前提”,既指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也指其历史成就。对未来共产主义美好希望的追求,不是基于所谓的纯粹的理性,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抽象的对立和否定关系,而是要充分吸收和发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和成果,对之采取“具体的否定”和“肯定”中的“否定”态度,未来希望正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根植于此。这表明,哲学对于未来希望的追求精神,又是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统一。哲学在这种统一中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面向未来的超越维度获得了坚实的根基。
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与对现存状态的批判难以分割。对阻碍人自由和解放的一切抽象力量进行彻底批判,这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另一重要内涵。
自哲学产生以来,批判和否定就始终是哲学的重要特质,也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重要体现。传统形而上学对终极实在的追求,已经蕴含着批判和否定现存世界的冲动和努力。但是,这种批判注定是不彻底的。这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要求从哲学所把握的终极存在、终极知识和终极价值为根据和标准来展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然而,批判的根据和标准本身却具有“绝对性”、“超历史性”和“无条件性”,因而享有免于批判的特权。在此意义上,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陷入独断和教条。
要把哲学的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关键在于自觉到,哲学的批判工作不是展示哲学话语霸权的场所,而是推动人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力量。哲学的批判本性源于对人生命特性的自觉理解和表达,它根植于人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生命本性,其根本旨趣在于破除一切与人生存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否定一切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妨碍人的生命自由的异化力量,以实现人不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
自觉到这一点,哲学将摆脱形而上学的独断和教条气息,体现出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曾围绕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对此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8)“不崇拜任何东西”意味着对一切“虚假偶像”的自觉揭露和拒斥。美国学者雅各比区分了“蓝图派”的乌托邦精神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精神。前者致力于在“绝对真理”的引导下,“纤毫毕现的描绘未来”;而后者的“本质性要素在于:它对此时此地的关注。它憧憬未来并珍视现在”,它相信:“与其为实现抽象的东西工作,不如为消除具体的罪恶而努力。”(49)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精神正体现了哲学的彻底批判本性。
哲学的“反偶像崇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以观念形态存在的虚假偶像进行批判,即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其职能在于祛除独断和教条的虚假意识和抽象观念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遮蔽,捍卫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性,通过人们的思想解放实现人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等,即是这种工作的典范。二是对支配和统治人们的抽象的现实力量进行批判,其职能在于揭露和解构宰制人们的现实生活、使人的生命存在陷入僵化的虚假偶像,从而捍卫人的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即是这种批判的范例,无论是抽象观念,还是支配和统治人们的抽象的现实力量,虽然表现不同,其共同点都是试图成为绝对的、无条件的主宰力量,束缚人们的头脑和生活,成为人走向自由解放的桎梏。通过对它们的批判,“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0)构成了哲学的“反偶像崇拜”的根本旨趣。
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用非历史的标准裁判现实的倾向不同,真正的哲学的这种“反偶像崇拜”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相反,它总是需要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获得具体内涵和主题的活动。无论是支配和统治人们的抽象的现实力量,还是独断和教条的抽象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哲学的批判活动总是针对人历史发展中具体的生存困境和矛盾而展开的,它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获得其现实的内容,离开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内在矛盾的领悟和理解,哲学的批判就会演变成堂吉诃德式的与臆想出来的幻影搏斗。在此意义上,哲学“反偶像崇拜”所体现的是一种既内在于历史和现实,同时又超越历史和现实的独特理论精神。
同时,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用先验的教条要求和规定现实生活,并以此证明哲学的绝对真理性与理论优越性不同,哲学“反偶像崇拜”的批判活动是推动现实生活跃迁的真实力量。马克思对此说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51)“教条式的预料未来”所表明的是哲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无根的独断和狂妄,而“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则是要推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去追求和创造一个与现存世界不一样的更为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在此意义上,哲学反抗虚假偶像的批判活动永远不会终结,只要地球上还存在贫困、不公与奴役,只要人类仍然在面向未来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人类就永远需要不断求助于哲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说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52)克服“教条式预料未来”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自觉地承担起“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任务,在永不终结的哲学批判活动中,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得到了充分彰显。
无论对“不在场”的未来希望的追求,还是对阻碍人自由发展的抽象力量的彻底批判,都是以对人现实的生命存在本性的自觉理解为基础,从不同维度对哲学乌托邦精神进行表达。它们表明,在抛弃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后,哲学并没有走向“终结”,而是以更加自觉和更彻底的方式彰显了哲学独有的精神品格。只要人类仍然需要自我理解,只要人仍在追求自由和解放,就需要哲学焕发其特有的乌托邦精神,哲学也将因此而体现其不可动摇的存在合法性。
注释:
①“合法性”(英文legitimacy,又译为“合理性”、“正当性”等),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意指政治制度系统得到人们认可和承认的程度。本文提出的“哲学合法性”,乃是要阐发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创造的一个特殊维度所具有的存在根据、意义和功能,论证哲学理应被人们认可和承认的、不可消解和终结的存在必要性和正当性。
②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③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第5页。
④彰显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为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可以从多个视角出发。本文从乌托邦精神的角度,为哲学合法性进行辩护,仅是针对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境而选取的其中一个视角,它并不排斥其他理解视角。
⑤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周纪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6、268页。
⑥布洛赫的相关思考集中体现在《乌托邦精神》、《希望原理》等著作中;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论解放》等书中,通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乌托邦精神”的重大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哈贝马斯明确把自己的哲学理想称为“交往乌托邦”;詹姆逊在《未来的城市》、《乌托邦的政治》、《未来的考古学》等一系列著述中,全面阐述了其对乌托邦和乌托邦精神的理解,并提出了“乌托邦的复兴”的主张;哈维在《希望的空间》等论著中,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其“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
⑦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⑧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页。
⑨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邦》,《哲学译丛》1991年第1期。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11)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邦》,《哲学译丛》1991年第1期。
(12)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95页。
(13)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
(14)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30页。
(15)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4页。
(16)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第2页。
(17)包利民:《现代性价值辩证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18)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附录”,第10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
(2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6页。
(2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2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0—321页。
(30)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34)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6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36)参见吉列斯比:《欧洲小说的演化》,胡家峦、冯国忠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37)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
(38)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Hope,vol.1,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6,p.7.
(39)参见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第105页。
(40)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页。
(41)詹姆逊:《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与政治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42)参见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与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4、46页。原译文“调节性理想”一词在引用时改为“范导性理想”。
(43)(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2、42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46)(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16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
(49)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页。
标签:哲学论文; 乌托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