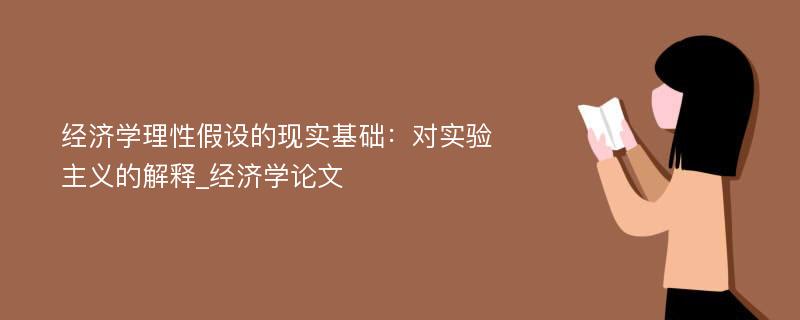
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现实基础———种实验主义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现实论文,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5)01-0001-07
一、前言
自从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之后,人们对市场经济及其机制的研究基本上遵循演绎推理的研究方式,即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之上,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一个模型化的理论结构,即阿罗—德布鲁分析范式,又叫“竞争—均衡”模型。
在“竞争—均衡”模型的一系列严格假设中,“理性假设”(准确地说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具有公理性和基础性的前提假设。根据希普(S.Hargreaves-Heap)对“理性经济人”的定义,所谓的“理性经济人”通常具有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选择那些能更好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1]。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只是站在工具主义的角度看待“理性经济人假设”,那么,它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的。正如希普所说:“这里的理性是一个手段一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待“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态度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置“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的局限性和现实性于不顾,把一个本该需要经验性认定的前提假设推向了绝对化的理论层面,并登峰造极地将其引至信仰的高度,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天然公理”,即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位置,都有着一致的“自利”性,不因个人差别、时空差别及社会环境差别而有任何变化;二是将奠基于“理性经济人”信仰或公理之上的纯逻辑推论或由此得出的形而上学结论,无限制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侵入到其他社会学科之中,用于重新解释政治、法律、社会日常生活和宗教关系等,掀起了一股重建其他学科理论基础甚至理论大厦的风潮,造就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盛名。
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论研究中严密的前提假设和抽象的逻辑推理代替不了活生生的现实,更不能满足人们探寻现实世界的需求。虽然经济学家们一贯标榜自己的学说是一种“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当人们满怀希望从经济学中寻找理解和认识现实世界的钥匙时,却发现经济学是多么的艰涩乏味,抽象而繁杂的方程式爬满了整个纸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平时容易犯错误、慷慨大方的男男女女到了经济学家的世界里,竟摇身一变成了冷酷抠门、理性十足和精于算计的“经济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具有多面性的。比如,人们常常愿意为了买衣服便宜5元钱而多走1公里的路,却根本没想过为了便宜2000元而去另一个城市购买轿车;有的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爱贪小便宜,时时寻找“搭便车”的机会,但对一些公共事务,如无偿献血、为陌生人提供信息、帮助老年人等[2],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例子都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远非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所能涵盖的。正如西蒙所说:“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了的世界。”[3]因此,人们为经济学的精炼和优美而陷入了“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泥潭,成为远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4]。
针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病”,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其病根在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缺乏现实基础。西蒙(Simon,H.A.)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作为决策人的“经济人”的计算能力和相应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表现在:(1)缺乏完整、统一的能够对可能的选择进行排序的效用函数;(2)人们只能找出所有备选方案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3)人们无法估计各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事件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这就决定了决策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佳决策,即所谓的“有限理性”说。西蒙还进一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决策时是基于某种常规或习俗,而并非理性计算的结果[5]。贝克尔(Becker,Gary S.)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因素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他将非经济因素引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的分析视角[6]。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Williamson,O.E.)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他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新制度主义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改更为宽泛,认为这个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和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总之,从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人们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和质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西蒙、贝克尔,他们对理性假设的批评主要是从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且他们的分析和论证过程往往容易陷入循环推理的陷阱之中。近些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科,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和分析则是非常深刻和富有成效的,它们从实证和科学实验的角度,对行为人自身特性的假设、决策环境的假设、行为的追求目标,甚至理性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等,都提出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挑战,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实验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近些年人们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二、行为经济学实验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实证检验与研究
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十年来才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美国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Kahneman,D.)和另一位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Vernon L.)共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及其理论观点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行为经济学试图运用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来检验有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努力,日益在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有人把这些实验所得出的结论看作是颠覆主流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有力工具。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决策主要是受物质利益激励和驱动的,即使是在存在某种风险的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者也能够准确地给有关的随机事件赋予概率,并选择使其最终效用期望值最大化的行为。因此,主流经济理论通常都是以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在1944年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来分析人们的理性决策。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决策者对各种被选对象间的偏好排列是固定和给定的,而这种给定的偏好主要是由人们偏好的完备性(或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决定的。因此,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偏好的这两大公理不成立,那么,“理性经济人假定”也就不成立。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A)在1974年和1979年共同发表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偏向》和《前景理论:一种风险决策分析方法》两篇文章。在这两篇行为经济学的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认为期望效用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在决策中的判断过程、决策程序以及决策对象或环境的描述本身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及其选择,如当事人决策时出现的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偏好逆转、后悔厌恶、过度信心、从众和攀比、炫耀、成瘾等非理性现象,都说明人们在决策时对其所选择对象的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
(一)决策者在决策时的直观判断行为会导致人的选择偏离理性轨道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往往是不确定、不完全和复杂的,在对它们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要达到最优化的合理性是困难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不能充分地分析所涉及经济行为及其概率的情境。这样,人们的判断依赖于某种捷径或具有启发性的因素,即以一些思维定式做出直观推断(heuristics),从而会造成系统性的偏差,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1.人们在实际决策时,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即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例如,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发现,如果被试者事先知道某一给定时间内在某大医院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他就会据此推断另外一家小医院内的情况也必定相同。但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是很弱的,仅仅根据大医院的数据是无法对小医院的情况做出正确判断的,这样的经验判断习惯实际上违背了统计学上的“大数定理”。所谓“大数定理”,是指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进等同于总体概率。“小数法则偏差”,是指由于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而产生的推测上的偏差。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1年指出,这种偏差实际上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夸大了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大样本代表性的低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小数法则偏差的例子。比如,当一个投资者观察一个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时,如果他发现该经理人连续两年的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就会推断该经理人具有超凡的能力,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统计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2.人们在决策时还要受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法则的影响和支配,从而导致系统性偏差。所谓相似性,是指人们总是会根据已有的经验来判断、考察事物,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依据仅仅是该事物与以前已经经历的事物相似。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利用1973年、1974年和1982年所进行的几个简洁实验,证明了这种直观的经验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区分推销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如果对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有较高比例或者销售人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斯基和卡尼曼还利用实验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的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的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3.人们在不确定下所做的推断存在某种偏差是由于信息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偏差所引起的。所谓可得性偏差,是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其结果是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从而导致在实际推断时出现偏差。例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实验中发现,如果被试者私下里听人提起生活中的某个人曾经被犯罪分子侵犯,尽管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全面、更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仍会高估其所在城市的暴力犯罪率。认知心理学的发现告诉我们,相对于一些不太熟悉的信息,熟悉的信息更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会被认为是更真实和更相关的。因此,信息的熟悉性或可得性往往会成为准确性和相关性的替代品。例如,某些信息被媒体多次重复地报道,使得这些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们获得,不管事实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人们都会错误地认为这些信息比其他信息更准确。
(二)人们在风险下的决策过程系统地偏离“理性经济人假设”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证据表明,风险之下,不仅判断过程,就连决策过程也会系统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早在1952年,莫里斯·阿莱(Allais,M)率先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指出风险下的决策偏离预期效用理论这一事实,即“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在实验中,他对上百个懂得概率的被试者做了如下实验: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注:具体而言,替换原理是指当决策者面临两个选择A和B时,如果决策者选择A而放弃B,则对任何选择C,决策者会选择概率组合pA+(1-p)C而放弃pB+(1-p)C。)
卡尼曼根据实验还发现,与结果的绝对数值相比,人们通常对结果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的偏离程度更敏感。这种侧重于变化而非绝对水平的倾向,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外界条件(如光和温度等)的绝对水平而言,人们对外界条件的变化更敏感。此外,人们对损失的痛恨程度往往大于收益所能带来的喜悦程度。换言之,一笔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等值的收益带来的快乐。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92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常需要两倍于损失的收益才能弥补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损失和收益对人心理的不对称影响,就是所谓的“损失规避”。人们通常不屑参与小数额的博彩,如以零成本和50%~50%的机率赢取12元或输掉10元,但大额的博彩却对很多人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对大数额赌博的风险追逐行为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因为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风险规避假设基础上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他们1979年的研究中发现,10个被试者中有7个人选择以25%的概率损失6000元,而不是以50%的概率同等地损失4000元或2000元(意即各25%)。这两种选择的期望值完全相同,而前者有更大的风险。如果说人们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规避,就不应该观察到上述结果。
行为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基础上,而且还对理性经济人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在传统经济学看来,人类行为的完美理性有三个特征: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对此,行为经济学指出,这三个特征都有待于进一步修正。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指出,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人们只是预期金钱收入但尚未收到它时,他们是能够相当理性地在花多少和储蓄多少的问题上做出规划的。在有限的刺激下,人们愿意储蓄和推迟开支,从而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莱布森认为,这一推理是有缺陷的。他认为,尽管人们的愿望是好的,符合理性选择,但是当真的得到钱时,人们的意志便崩溃了,钱往往立即被花掉,这一现象被称为“夸张贴现”。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时间偏好中,短期贴现率往往大于长期贴现率。夸张贴现函数正是抓住这一特征,认为人们并不是合乎理性地在一生中对开支和储蓄进行统筹安排,而是从年轻到老年都负债。因此,在实践中,虽然人们都知道何为最优解,但因为自我控制意志力方面的原因,人们是无法做出最优选择的,往往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做出选择,这就说明了人们在实际决策时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另外,大量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的品质和观念也是广泛存在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的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以及许多人的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也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这也说明人类的自私自利是有限的。
三、博弈论实验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实证检验
博弈论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是研究理性的当事人之间策略性行为的一门科学。博弈论的前提假设——“人是理性的”在整个博弈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作为十分苛刻的前提条件而存在的。
在博弈论中,不仅假定了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而且假定了“所有参与人是理性人”是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按照博弈论的原理推论,在许多情况下,理性的参与人在某些博弈中并不能使自己的得益最大,而且在博弈中,理性反而成为获得最大利益的障碍,最后导致“理性的”博弈参与人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境:每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结束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
囚徒博弈(Prisoners'dilemma)是一个著名的博弈困境,该博弈最早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塔克于1950年提出来的,其内容如下:两个囚徒被警察抓住后单独关押,警察给他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个囚徒均面临着两个策略选择——“招认”和“不招认”。如果一方“招认”,另外一方“不招认”,招认方无罪释放,不招认方将被重判(比如10年);如果双方均“招认”,因无立功表现,每人均被判刑(比如5年);如果双方均“不招认”,警察因拿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以前的罪行,只能对他们目前所犯的罪行进行惩戒(如判刑半年)。
显然,在这个博弈中,两个囚徒均会选择“招认”,因为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自己选择“招认”是占优策略。双方均选择占优策略“招认”所形成的策略组合点(招认,招认)是纳什均衡点。如果两个囚犯都选择“不招认”策略,虽然该结果是最理想的状态,即每个人会得到很轻的处罚,皆大欢喜,但这个理性的状态是达不到的,因为每个理性的囚徒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均会主动偏离这个状态。最后的博弈结果是一个非理性的双方都招认的策略,而且这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理性的囚徒难以摆脱的困境。
由于“囚犯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理论的经典例证,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广泛影响,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博弈论的实验研究大多围绕着“囚犯困境”的存在性及与由“不招认”可能产生的合作结果进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拉弗(Lave)、1965年拉伯帕特(Rapuport)和查姆(Chammab)进行的实验。拉弗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囚犯困境”的一次性实验(非重复性实验)中,存在一定程度合作的稳定性,而且这种合作稳定性的概率在大于0与小于100%之间。事实上,很多实验是被用来解析对合作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因素的。
其后,考尔曼(Coleman,A.)对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提出质疑,认为许多被人们当作一次性博弈来进行分析的实验,实际上都是各种类型的重复性博弈(非一次性博弈),但在具体分析时却被人们用一次性博弈的规则来解释有关问题。考尔曼曾于1983年列举了1500项实验,其结果是多数情况下证实了纳什均衡策略行为的存在,尤其是单一纳什均衡在单阶段标准型博弈中的解释力量。
与囚徒困境类似的是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博弈。公共地悲剧博弈是由美国生物学家哈定(Hardin,G.)在1968年提出的,其内容如下:假定一个牧场划出一块公共区域让牧民可以在其中随便放牧,这样,所有牧民都有购买牲畜的动机,因为能在公共区域免费放牧,其结果是每个牧民的占优策略是尽量多地放牛,因为购买牲畜的成本小于该牲畜长成后被卖出所得的收益。但是,当每个牧民均进行如此的理性思维与策略选择时,牧场将被过度放牧,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谁也不能放牧而使牧场荒芜。这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悲剧。公共地悲剧博弈提出后,引起了人们在各个领域里的讨论,比如人口问题、污染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均具有与此相同的结构——每个人均能够预先知道这些问题最后产生悲剧的必然性,因为这个必然性是每个人理性行为的结果,但每个人由于自己的理性,均不会约束自己的策略选择,因而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Gardner等人为讨论公共地悲剧问题设计了一种共享机制进行多时段(20~30时段)实验[7],其实验结果符合公共地悲剧博弈预测的结果,即随着各时段投资的持续增加,人们从投资中获取的收益(即租金)将远低于有效的水平,而且资源的过度使用呈现随经验的增加而恶化的趋势,平均租金由无经验局的41.5%下降到有经验局的30.5%,表明浪费的公共资源要比非合作行为所预期的更多。还有学者如道斯(Dawes,R.)对“公共地悲剧”和公共利益捐助问题进行了“N个人的囚犯难题”实验室模拟,也得到了与考尔曼类似的结果[8]。
不管是囚徒的困境,还是公共地的悲剧博弈,它们所反映的人的非理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这些博弈的实验及其结果也只是用来验证博弈均衡存在的证据。但是,在博弈论实验中,真正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并引起经济学界瞩目的是最后通牒博弈及其实验。我们先对这个博弈的内容做一简单介绍:假设该博弈有两个参与人,一个被称为提议者(Proposer,简称P),另一位被称为响应者(Responder,简称R)。这两个人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一定数量的钱,比如100元,具体的分配规则要求如下:提议者P会向响应者R提出一个分配建议,R可以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提议。如果R接受这个提议,那么,P和R可以按照该分配建议得到各自的份额;如果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则双方什么都得不到,此时,博弈结束。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博弈中,博弈参与双方不但完全知道要分配的金钱数额,而且也知道对方的效用函数,显然,这是一个两人参加的具有完美信息条件的一次性动态博弈。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博弈的均衡情况。在博弈第一阶段,先由P提出分配方案,此时,他知道R是理性人,即R的理性行为是可被P预测的。P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将提出一个较为极端的分配方案:把要分配的100元钱只给R留1分钱,而将其余的99.99元据为己有。到了博弈的第二阶段,R面临“同意”和“不同意”的选择:如果“同意”,他的所得为1分钱;如果他“不同意”,他将一无所得。理性的R将选择“同意”,因此,他只能得到1分钱。P正是利用R的“理性选择”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到了99.99元。当然,此时的均衡对于R来说,也是一种占优策略均衡。
虽然P所提出的分配方案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也是P的一个理性选择结果。当然,根据传统的博弈理论,最后通牒博弈或许存在着多重纳什均衡,如(99.99,0.01)或者(99.98,0.02)、(99.97,0.03)……,(0.01,99.99)等,但提议者P在预测到R也是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总会选择任何分配给R的钱数大于零的数额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在这种一次性博弈条件下,理性的R也只有接受P的这种分配方案。
从理论上看,上述的极端分配方案是最后通牒博弈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最优纳什均衡解。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近20年来,许多实验经济学家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了多种实验,并得出许多有趣而又出人意料的结论。第一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古思(Güth)等人于1982年进行的,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博弈论学者对理论上的最后通牒博弈均衡情况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也不能对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进行满意的预测。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大多数情况下提议者给响应者的分配比例不到70%,而且20%分配比例的提议会遭到拒绝[9]。
Roth等人于1991年在美国、以色列、日本和南斯拉夫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10]。他们让博弈双方共同分配1000元,并且要求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必须以1元为单位。为了让参与者发挥学习的效果,他们重复进行该实验,同时也进行严密的控制,以免成为参与者依赖过去经验而选择行动的一种重复性实验。最后的实验结果是,所有国家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各取一半钱。具体情况是:在美国和南斯拉夫各取50%,而在日本和以色列则是由首先提议的参与者分取60%,对方分取40%。
后来,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金额做了很多实验,结果显示,参与者的行为并不会因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或计算能力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奖金多寡对结果也没有多大影响。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实验中,参与者可以分享的金额是他们平均月收入的3倍,但当他们觉得对方提议给的钱实在太少时,仍忿忿不平地拒绝了。
上述有关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说明,理论上由理性选择所得出的结果与现实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如果我们用理论预测的结果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是极可能起误导作用的。事实上,世界各地的人,大多很看重公平待遇,而不是一味自私地追求最大利益。对此,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当参与者以一对一的谈判博弈分配一定数额的金钱时,对社会公平性这一概念的理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分配结果,人们心灵深处存在着某种公平性的观念,这种公平性的观念在人们的现实决策中发挥作用,从而使得以“理性选择”为出发点的行为最后导致一个“非理性”的现实结果。
四、评论与结论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仿佛是个“天然的”公理性假设,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不证自明的“天然性公理”却经不起科学实验的验证。大量实验结果显示,人们在实际的行动中有违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种种表现,如西蒙的“有限理性”、卡尼曼等人的“一致推断效应”和“偏好颠倒”以及“最后通牒博弈悖论”等,这些针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性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无疑对以期望效用理论为核心的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巨大冲击。更进一步地说,其对主流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命题、研究领域乃至整个现代经济学都是影响深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主流经济学也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试图改变目前不利的局面,如放松诸如个体决策与偏好等理论的有关公理化假定,试图在技术上对期望效用模型进行修正或改进;在研究方法上也引进实验研究方法,弥补以前仅仅依靠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数据验证经济模型现实性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主流经济学的这些修正和改进效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首先,主流经济学对某些公理化假定的放松或进行技术上的修补,只是让现象适应理论,而不能使理论解释现象。因为现实中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发生总有其合理的基础,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错误的现象,只有错误的理论。
其次,经过修正的理论模型在诸多实验面前往往顾此失彼和相互矛盾。比如,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诞生一个能够完全符合偏好颠倒现象的期望效用模型,而且这些模型本身在进一步的实验中也经不起验证,如Machina的扇型假设理论在Camerer和Conilsk等人的实验中就得不到证实[11]。
虽然主流经济学借鉴实验方法来改进其模型的努力并不十分见效,但这种方法论的融合和交流是值得肯定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尽管实验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两种方法在研究有关经济学问题上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并不否认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否认大多数传统经济学的假设。比如,理性的经济分析认为,人们会为将来打算,会为退休后的花费做好充足的储蓄准备。行为经济学模型也认为,人们会为将来打算,但允许人们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因此,可能出现储蓄不足、过度借贷的现象。这些就引出了与经济现实更为贴近的推论:对于流动性差的资产,人们会有较高的储蓄;而对流动性高的资产,人们会有较低的储蓄。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进行两个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一方面,以拉宾等人为代表,寻求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力求简化其分析模型,使之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传播方式,如以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来替代烦琐的心理学假定,就可以有效研究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另一方面,以史莱佛、格莱塞等人为代表,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同化行为经济学,如史莱佛通过有限套利问题来调和市场有效性的论争,而格莱塞则试图在行为经济学中安置一般均衡。
从经济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实验研究及其成果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改进或修正,而不是革命,其宗旨是让经济学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对现实的分析更具解释力。正如卡梅瑞(Camerer)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行为经济学并不全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建立了较完整的经济和非经济行为分析理论框架,并使这种分析能够得以实证,从而为实验研究提供了现成的实验对象和环境。
[收稿日期]2004-12-27
标签:经济学论文; 卡尼曼论文; 经济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行为经济学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博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