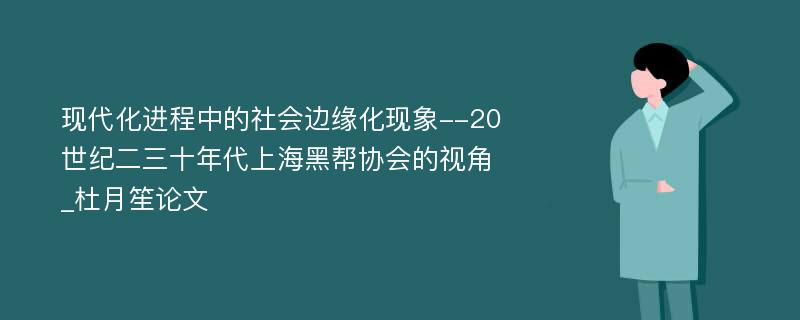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帮会论文,上海论文,二三论文,透视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58-06
近年来对帮会尤其是上海帮会的研究,颇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截止到2000年,已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周育民、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苏智良、陈丽菲合著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刘韦萍的《上海帮会与蒋介石政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夏斯云的《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恒社》(《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张莉的《论帮会产生的社会条件》(《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等多篇。此外,“帮会的历史、现状与当代黑社会学术讨论会”,也于1999年6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剖析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帮会大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其“适时而变”特点入手,进而揭示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
一 社会边缘化现象的理论透视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在这个时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分裂成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时,一些与旧秩序相关的社会群体,基于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与对现存地位和价值规范的不满,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要求维护或恢复传统秩序与传统价值的群体中去,形成一种社会边缘化现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则是这种边缘化现象的典型例子。
中国帮会是封建社会衰亡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民间下层秘密组织,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异化的产物。作为封建宗法家族制的畸变,无论其宗旨性质、组织与活动方式都显示了这是一种充斥着浓郁的封建气息的游民社会团体。所谓“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由封建家法延伸而来的行会制度的变异形态;“会”是以异性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关系的变异形态[1][p1]。帮会原是封建政权的对立物,但却未越出其阶级与文化的范畴。它在以特有的暴力掠夺和厮杀争斗的方式打击政权机构及其社会基础成为破坏旧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也以其极大的破坏力导致社会生产趋向衰败。这种最初由原始的均贫富意识引发的不事生产与建设、专为谋夺他人财富的破坏行为,严重悖逆了现代社会的准则,使其成为居于社会边缘又寄生于社会之上的赘生物。上海开埠后至20世纪20-30年代,帮会在上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种封建残余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城市社会中竟然如此恶性膨胀,充分凸现了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缩影的负面效应。
郭绪印认为,上海帮会因适应租界而立足发展,又因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而壮大,也因追求政党政治的道路而受阻[2][p108-109]。如果说前期是发展期,后期走下坡路,那么其鼎盛期则是20-30年代。这一时期上海帮会已渗入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极多,力量之大、能量之强、影响之广几达全国之冠,其表现手段、生存方式也以这一时期为典型,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大发展的原因
上海帮会在20世纪20-30年代大发展决非偶然,它是上海特殊社会条件的滋生物。
首先,新旧并存、多元异质的城市社会提供了帮会滋生发展的土壤。开埠至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大埠。新兴的工商企业迅速发展,市政建设、公用事业、文化娱乐各具特色,形成一种新兴的社会领域与发展取向,社会分化与整合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不断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与此同时,旧的产业、旧的人格、旧的意识依然存在。上海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不断上演着革命与改良、现代与传统的话剧,这种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消费与旧的生活于一体、汇各种社会力量与新旧意识于一市的多元异质的社会环境,使上海具备了能够接纳各种社会势力的能力,并为之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
其次,社会转型过速造成的过分城市化导致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上海的迅速发展与周边农村及传统市镇的不发展,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两极关系:即一极积累了贫困和双重自由的人口,另一极未相应积累对应的财富,未能创造出足以吸纳全部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容纳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过分城市化的趋势。过分城市化的涵义有二:一是指首位城市的人口远远超出第二大城市及其他城市人口。其测算的公式是:I=p1/p2。其比例差距越大,则表明过分城市化的趋向越明显[3](p217)。二是涌入城市的人口超出了城市经济可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研究者苏智良等由此认为,造成城市人口过剩,出现了一个持续存在无法消弥的庞大的失业者阶层[4](p13)。1930年-1936年间上海失业和无业人口约占上海职业人口的1/3和总人口1/5,面对利益分配与生存机会的不公,大批人投靠山门,义结金兰,以帮会为其求职谋生的靠山。许多在职职工也因生活艰难与环境险恶而大批加入帮会寻求帮助,帮会从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来源。李立三曾指出:“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5](p1)帮会在上海工人中的首席代表朱学范作了诠释:“从解放前全国来看,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5](p1)
第三,三国四界的多元格局与社会控制机制的有限度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是帮会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华界与租界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异质的文化、制度、意识、法律及政权范围,使各套社会控制机制都受到了局限。罪与非罪的标准各异,造成的间隙成为帮会生长的空间。华界罪犯逃入租界则相安无事。租界与帮会的互为依赖则是帮会膨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租界当局依靠能量巨大的帮会以发展与延伸其社会控制力,同时为烟、赌、娼这些帮会控制的“都市三鸟”披上“合法”的外衣,从中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帮会依赖租界而生存而发展,成为租界中强大的黑社会势力。事实上,20-30年代上海帮会闻人如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金九龄等都是在租界任过职并由此发迹的。高鑫宝、顾竹轩、徐采远、马祥生、叶焯山等也都是依靠租界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的。这种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关系使帮会这一传统的怪胎寄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社会的母腹中发育壮大。
三 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发展的特点
30年代上海帮会从早期散乱复杂、旋起旋仆的不振局面而发展到鼎盛时期,与上海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其原因固然与客观条件密不可分,更与其主观认识与应变谋略及实际措施相关。其要诀在于一个“变”字,即“适时而变”。张啸林已认识到大革命后的上海已非前清与北洋可比,“我敢保险,不出三年,黄浦滩要变成一个新世界,赌与土,恐怕要给他们连根铲除”。“连你连我,在新浪潮来了的时候,那是命中注定要被淘汰的。”[6](p74)杜月笙更因此悟出“以变应变”的道理,“民国以来时势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之快……我觉得他们像是钱塘涨潮一样,一冲过来便是万马奔腾,江里的大鱼小虾唯有跟着跑。这个力量太大,不是随便哪个可以抵挡得了的。所以我决定浪潮来了就要赶上去,既不能倒退,也无法不理不睬,袖手旁观”。“穷则变,变则通,天无绝人之路”。[6](p74-75)正由此出发,帮会在时代大潮冲来之后,经过一度观望选择了倒向国民党充当马前卒的“适时而变”,在“四一二”政变与以后的“清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政权初建后的国民党所接纳,从而奠定了双方默契合作的基础。随帮会三大亨被封为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成为“党国要人”后,“曲鳝修成龙”,帮会也终于由地下走上地面,为“以变应变”铺平了道路。从1927年到抗战前,上海帮会以此策略手段而得到了空前的恶性繁衍。不过,所“变”的乃是适应现代社会与商品经济大潮的手段与方式,而其社会寄生物的封建性却始终未变。尽管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但综观这10年,上海帮会的发展并未出现这种局面。
首先,因适应现代社会与商品经济发展而“变”。
第一,从生活方式到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传统帮会人物衣着打扮多以黑衫黑裤,翘起大拇指,手戴足金戒,横眉怒目,敞胸赤膊为典型。20-30年代揳入工商上流社会后,形象有所改观。杜月笙说:“衣食足,应当礼仪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害怕。”[5](p195)他衣着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学得文质彬彬,即使在炎夏,其衣领扣子也从不解开。他要求手下称他为“先生”,而不愿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手上那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4克拉半的钻戒也锁入保险箱中。在他倡导下,黑道人物纷纷改变形象,有人戏谚道:“黄浦滩上一下子脱掉了千万只钻戒。”[7](p222)杜自幼失学,发迹后重视文化,先后请了许多文化名人包括留洋博士、著名律师教其文化与法律,门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广结人缘,热衷社会事业,黑道所得用于白道,无论是各省天灾募损、社会慈善还是抗日捐款都不推却,从而获得社会声誉。这一时期帮会的组织形式与内部结构也有变化,其特点是趋简化松散,以实力地位为主。拜师礼已简化为只须具拜师红帖行磕头礼即可,不再墨守那种风高月黑夜于荒村野庙中举行由多重弟子执法司礼的庄重森严的开香堂陈规。黄金荣对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拜其为师时,已不开香堂,而仅由介绍人搭桥投帖,封一份贽金,向其磕三个头或三鞠躬即可。[8](p198)同时,辈份关系也已模糊混乱,多以实力而非帮内辈份论。四川袍哥大爷范绍曾与杜月笙的老师陈世昌是一辈的,但他却和杜月笙私交极好,往来甚密,称兄道弟,他自己也说,“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9](p64-69)。研究者周育民、邵雍由此认为:“帮会分子们趋炎附势不再顾及辈份的大小。上海青帮组织内部经过重新组合协调,按照各帮首的实力地位形成了新的格局”。[1](p552)这一方面是随形势发展出现了帮会内部的多元趋向,另一方面是在商业都市中采取承认现实的方法更能在宏观上予以控制。这是一个新特点。
同时,帮会的现代嬗变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神秘面纱,而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与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1932)、张仁奎的仁社(1935)、黄金荣的忠信社(1936)、朱学范的毅社(1935)以及杨虎的兴中学会、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义社、徐逸民的逸社、孙以乡的怡社、韦作民的文社、汪禹丞的民兴社、王知本的正诚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这些社团一般都标榜现代社会文明意识,以现代社团的合群、联谊、交友、互助为宗旨。如恒社宗旨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5](p293)。毅社更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口号相号召,倡导合作互助[5](p9)。其成员身份也有了较大改变,多为中上层人士,传统的下三流分子一律不准加入。从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的234名社员职业比例可见,商界人士占54%,警务为13%,政界12%,自由职业9%,军警5%,工界2%,学界2%,党务2%[10]。其中包括大批董事长、经理、厂长、校长、科长、管长、律师、记者、博士等现代科层制组织管理人员。忠信社、仁社中也有许多社会名流与军政商学界名人。[1](p551)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在形式上,即使在机制上,这种组织也确有现代社团机构之功能,如恒社理事会下设3科18组,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各自行使职能。仅1936年冬季即为21人介绍了职业,这在失业率高的当时确乎不易。[1](p549)帮会以现代形式装扮,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
第二,向工商界渗透,表现出某种资本主义色彩。杜月笙有一句名言:“花一文钱要收到十分钱的效果。”[11](p195)此时帮会已有投资——回报的意识与行动,不仅是社会效益,更重经济效益。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进入工商界,摄取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的利润。30年代帮会头目发迹后,多向上流社会靠拢,尤其向工商界渗透,不像其前辈那样仅仅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的走卒与爪牙。周育民、邵雍认为,其“高明之处在于已经成功地打入了上海的工商界,本身具有工商资本家的身份,对社会各界具有较大号召力和吸引力”[1](p544)。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许多人从早期的餐饮、娱乐业拓展到工商金融界,摇身一变成为致力于经济的实业家。如扎鞋底出身的金廷荪发迹后先后当上黄金大戏院经理、逍遥池浴室老板,至30年代他的身份已是冶茂冷气公司、大慎药记木行、宁波太丰面粉厂、上海华丰面粉厂、大运公司等多家现代企业的老板、总经理或大股东。杜月笙1929年在银行家钱新之帮助下创建中汇银行,1935年又揳入中国通商银行,取代傅筱庵任董事长,迅速在银行界发展,兼任中国、交通两行的常务董事与浦东、国信、亚东银行的董事长。同时,杜月笙又插足造船与船运业。1931年乘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之际收购大量股票而吞并之,于1938年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利用其在银行界的关系与势力,获得大量的以往该公司无法得到的银行贷款,制订了1600吨的新大达轮,在十六铺新建巨型货栈,使公司赢利大增,相继兼并了其他竞争对手,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船业,并于虞洽卿之后登上了上海船联公会理事长的宝座。杜月笙的手伸得很长,面粉、证券、纱布、食品、建材等行业都涉足其中,曾担任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等。及至1937年抗战前,他已当上了很多家现代工商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身兼200多个董事、理事与股东头衔,仅这些头衔的收入每月即达一二十万元[12](p320)。许多帮会头目也有类似倾向。这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上海帮会已从非正常的黑道掠夺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畴谋食,开始进行资本主义性的工商业正道经营。黄逸平认为,帮会首领们跻身工商业,意味着帮会分子的活动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侵蚀,使帮会也具有了若干资本主义性质”。[13]这种由黑道出身的帮会人物渗入并控制了工商界,又造成了工商界人士性质的某种畸变,即出现了一批如邵雍所说的“流氓企业家”、“白相生意人”,企业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低道德标准,“接纳以任何方式获得成功的新伙伴”[1](p514-546),从而在总体上将自身的素质层次放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这不能不说是企业界的悲哀,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二是除打入工商界外,还主动积极地拉笼工商界人士进入帮会。恒社1932年223名成员中工商界人士占120人,其中不乏社会著名的企业界人士,如陈光甫、钱新之、李桐村(大业公司总经理)、徐尔康(上海银行分行总经理)、陈香涛(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韦敬周(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黄金荣所收门徒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如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三星棉铁厂老板张子廉,江丰染织厂老板谢克明,泰康饼干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王云浦,上海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国信银行董事长郑筱丹,新华影业公司经理张善锟等[5](p278)。这样,帮会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入上海工商界,帮会成为一股新兴力量,很大程度上插足并控制了上海工商界,在改变工商企业家结构、成分、素质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黄逸平分析道:“帮会的经济收入由全部非正当收入转为有一部分正当的企业收入。其中虽不无有超经济的方式,但经营近代工商业必定要遵守一定的经济规律,这与从前单靠赌台、贩卖鸦片所得不同”,这一切,确也“促成了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化”[13]。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金钱在被帮会利用来瓦解社会肌体、侵蚀工商结构的同时,也同样无情无形地侵蚀着帮会自身。这是一条为史实所证实的客观规律。
第三,向现代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成为上海一大社会势力。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触角伸向社会各界,控制舆论,插足政界,操纵劳工运动,几乎无处不在。他们通过师生、朋友及各种社会关系,帮内帮外,三教九流,建立了一个宝塔式的关系网络,下层为职业流氓、白相人,中层为各种新式职业中人,如工商界、文化界的人士,上层为其帮会核心人物。黄金荣门下有名医王振川、方慎盦,鸳鸯蝴蝶派小说名家平襟亚,新闻记者沈菊隐,弹词名家吴玉逊等各种上流社会中人[5](p186)。杜月笙更是八面玲珑,无孔不入,身兼军委会少将参议与行政院参议,又曲意逢迎权要孔祥熙、宋子文,与杨虎、范绍曾拜把兄弟,将杨管北、吴开先收入门下,与史量才、王晓籁、虞洽卿交密,联络各方人士不遗余力,北洋才子杨度,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国民党中监委员杨千里,著名律师秦联奎、江一平,名报人唐世昌、姚苏风等都是其座上客,每年光这方面的交谊开支即达200万银元。但正是通过这种联系,使他逐渐集结起一支私人政治力量,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现代社会成员日益成为其借以自重的社会势力,使“杜门”成为一张盘根错节几乎无所不在、无事不能、无法无天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势力的非法组织”[4](p190)网络。也正因此,他常常能办到一些官方与其他社会中间组织无法办到的事。在历次工潮运动中,杜月笙“闲话一句”成为其信用担保,往往以“实力腰包”劝服双方予以调解,充分显示了社会能量。这支亦官亦匪、亦黑亦白的社会势力的迅速发展,填补了上海转型社会公共领域的某些空白,成为上海滩上一种多元异质的社会控制机制,是社会发展畸型化的表征之一。
其次,寄生社会之上、榨取社会财富与反现代社会的本质未变。
第一,帮会是一种不事生产专恃汲取社会生产力营养为生的社会群体。综观“三大亨”及其他大小头目,几乎无一不是依靠烟、赌、娼等见不得人的方式发财起家的。即便20-30年代组建现代社团或控制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后,仍带有极大的封建性。他们对现代企业的剥夺压榨行为,严重地干扰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30年代张啸林做棉纱股票巨额空头,孰料行情看好,天天上涨,张竟大耍流氓手段,派出打手到棉布交易所要求停止交易,导致行情下跌直至其捞足为止[6](p46)。杜月笙办的中汇银行,“正常的业务往来并不发达,其经营重点放在特殊业务上,即收、付烟赌两项的大量游资和押款,资本雄厚的大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费用即可保提、保运甚至保销烟土,这种生意是其他商营银行绝对无法染指的”[1](p546)。1933年上海银行业对其调查发现,“去年(1932年)除官利外,尚获纯利十几万元”[15],这些纯利主要靠非法经营而来。他兼任的多种现代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之职,不少是他人慑于其权势而双手奉送的,更多的是谋夺所得。他掌握这些企业后,虽然有时也要出面为之排难疏解,但毕竟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从事经济活动,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而非其他手段,全身心地投入这一通过生产、流通领域追求利润者才可得称为现代企业家。由此标准衡量,上海帮会各首领可以说无一人完成了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其巨大的收入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所得基本上是以非正常、非理性的方式从社会盘剥而来,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寄生虫与吸血鬼。
第二,帮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公共领域的真空,成为一种独特的畸型的社会控制机制。帮会这种崛起并俨然为租界和中国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不代表新兴社会生产力与现代社会法则的社会力量,其行动虽然比较复杂,但其宗旨与行动目标均围绕一己之私利。譬如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的同时,不少人也赞助革命掩护过共产党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有部分帮会成员参加。杜月笙邀已暗中加入共产党的杨度入幕予以保护,杨度寓所一度成为中共秘密高级接头点。他与潘汉年接头,赞助中共,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5]](p248),并收中共党员电影明星金山为关门徒弟[16](p31);而“苏北大亨”顾竹轩更是多次掩护过中共人士[5](p360)。但严格地说,这一切都是其“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传统、“狡兔三窟”的手法的再现,是非主流行为。就其主流行为而言,除剥夺榨取社会财富外,主要充当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阻力,是一种非现代非法理的社会控制机制。可以说20-30年代上海烟赌娼三业基本上由帮会控制,上海的乞丐、诈骗、抢劫、绑架、杀人、放火等社会犯罪也很少与之无关。当年几次轰动上海滩的大绑票案如绑架尹启忱之子及温宗尧、荣德生、魏廷芳、朱成章等案都是其精心策划之作,并都由此获得巨额赎金[17](p193)。此种暴力行为严重挫伤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经营的热情,造成恐怖的社会氛围。荣德生遭绑架勒索后,不仅经济上受巨大损失,心理上“也完全绝望了”。他们原先业已存在的弃商务农的职业回归心理加重加浓与此也密切相关。帮会在上海势力之大,连国民党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1935年11月,孔祥熙拉杜月笙进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时就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异议而解释道:“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体制造出骚乱来。”[18](p250)基于这种认识,国民党在这十年基本上持纵容、依靠与扶植利用的态度,导致这股畸型的社会黑势力日益坐大。这一点,连国民党情报人员也对此极为反感。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提到:“国府奠都南京,因欲利用安清帮首领消灭共产,流氓之势力于是日形扩大。迄至今日社会各阶层,均有流氓插足之地。流氓首领,竟亦身为国府高级参议者。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愤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1](p562)
作为封建社会的残余,帮会以对抗政权、破坏社会的面貌而出现,进入转型社会的上海后,这股“旧的社会力量也采取了新的形式”[2],适时而变。其在政治上勾结政府与租界当局,在经济上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的商品经济大潮,从而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作为一种传统人在现代社会的变体与寄生群,他们犹如一只“巨大的黑色章鱼”,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贪婪地吮吸城市社会的营养,又释放出大量的毒素,每日每时地抗衡与改造着周围的主体社会文化结构,损害着社会的健康[4](p265),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与包袱[19](p627)。
结论
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一般说来,在现代化历程中总会促使某些社会成员……作出原教旨主义的反抗。即企图以真实的或理想的形式回复到往日的大好时光。”[19](p627)在一个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的国度中搞现代化运动,来自传统的抵拒力必然是巨大的,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内外动力较强的新兴工商城市中,表现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行为取向中的传统因素仍然是较为明显的。他们一只脚跨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另一只脚却原地不动。他们同样也有着因外在要素激发而激活了内在要素的情况,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与客观环境实现共振而不得不回归传统。而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格局中,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个人、群体面对原有利益的丧失而在现存社会中难以立足的现状,愤怒与无奈的心理往往转变为社会抗拒行为。而当他们出于共同的感受而组织起来以畸型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与生存机会时,则形成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向冲击。作为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回流与暗潮,它们在上海时时涌现决非偶然。而社会边缘化现象及其社会病态行为,更显示了社会整合机制的不完善与整合力度的弱乏,成为二元社会生活中向新中的守旧、共谐中的异趋典型。不过,这种二元现象也体现于回归势力的抵触与抗拒过程之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异,它们试图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同时,自己首先被改造,“许多新的因素被引入了”,只是程度高低多寡之分。这表明,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生产不断的“连体婴儿”。它既是一种异趋,又是一种共谐:异趋既对抗共谐,又在共谐中实现;共谐既包容异趋,又明显有别于异趋。这种边界清晰却又模糊的关系,正构成了20-30年代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复杂壮观而又激荡的二元生活的理论模式与现实生活图景。
【收稿日期】2002-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