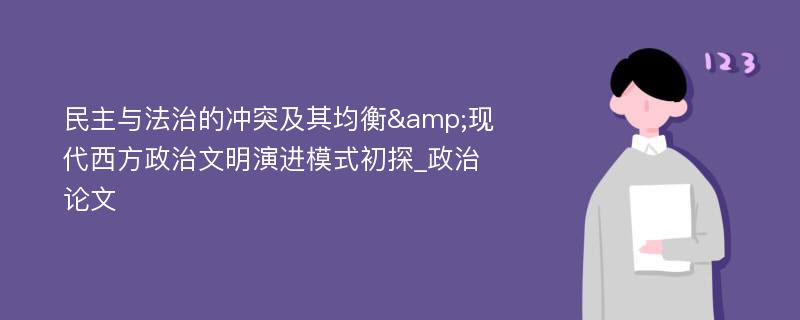
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及其均衡——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治论文,政治文明论文,民主论文,冲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术界对于民主、法治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对民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1]实事求是地说,严格意义的民主与法治观念更早地生长于西方,因此,对西方政治文明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与法治关系加以认真地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试图对现代[2]以来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做一全景式的观察以求教于学术界贤达。
一、对立: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形成
如果从宏观角度考虑现代西方政治实践及与其相应的理论,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民主与法治两种选择如影随形,不但指示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两条岔路,而且凝聚了政治思想的枝蔓向两个方向的伸展:一个方向是强调民主对政治权力的积极解放;一个方向是强调法治政治权力的消极约束。就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来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与均衡不但昭示了国家主权与法律至上性的要求的交叠,在议会主权与宪法至上、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张力,同时还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领域分离,在人民主权与人权、政治权利与个人权利、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要求应有的界限。总之,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倡明了现代以前西方社会始终模糊的权力与权利问题,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规定了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
就政治意识的形成来看,由于在不同程度上揉合了法治,现代西方民主观念形成了两个传统:“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3]与这两种政治意识相对应,就政治制度的安排来看,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明确地区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法治优位”模式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民主优位”模式。与之相适应,政治行为的模式亦区分为美国的宪政革命模式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模式。从美国的情况来看,革命胜利后,制宪会议从《独立宣言》的民主立场上退下来,选择了法治,有意地削弱了民主,成为一场缺少民主的宪政革命;与此相反,法国革命选择了民主,却没有形成民主的制度化,进行了一场没有宪政秩序的民主革命。总的看来,西方政治现代化早期以民主和法制的对立,从两个方向塑造了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雏形。[4]
诚然,如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ville)承认的那样,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5]但是在法国政治思想家勒庞(Gustave Le Bon)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摆脱纪律和法治的约束,勒庞指出:“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口号确定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而这些口号则成为人们为此辩护的托辞,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6]
与勒庞的描述看起来大相径庭的是,法国大革命给人的印象是追求法治。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无宪法,毋宁死”成为人们战斗的口号,人们相信立法的力量,总是希望通过新的法律给混乱的局面以秩序,走上前台的政治派别纷纷抛出自己的宪法,并试图通过它建立自己的统治。
这里面透视出的正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悖论:人们总是希望以法律来恢复秩序,但却不愿接受法治的约束。有“法兰西制宪之父”、“头号政治设计师”之称的西耶士(Sieyes)就认为,“国家通过其规章和宪法约束其代理人,因此,设想国民本身要受这些规章和宪法的制约,这是荒谬的。”[7]在“人民不受约束”的喧嚣声中,“法治”的原则被人们抛弃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视法国大革命为一场“公开的暴力叛乱”。[8]戴雪(Albert Venn Dicey)更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如谓法律主治的大义竟可废弃,此等现象惟可出现于大革命。”[9]
革命的动荡使得宪政的稳定性无从谈起。法国大革命前后,不但有1789年的《人权宣言》引人注目,人们还先后制订了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等,其变化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从1789年到1815年间,法国制定过7部宪法,平均不到4年就产生一部新宪法,法国成了宪法的“试验场”。然而,几乎没有一部宪法受到人们的尊重,1793年宪法未经实施即遭人抛弃;1795宪法通过时,雅各宾派已经日薄西山,更是很少有人问津。革命几起几落,革命的宪法随波逐流,成为革命派踢来踢去的皮球。法治秩序的建立一波三折,民主的制度化遥遥无期,这成为法国革命在一次又一次的复辟和起义中流产的重要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说它强大,是因为它是一场民主革命;说它脆弱,则是因为它是一场缺失了法治的民主革命。[10]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昭示的是没有法治的民主革命的失败,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没有法治的约束,民主是脆弱的,甚至会沦落为暴政的工具。
与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反,美国革命胜利后,保守派走上前台,推动了宪政秩序的建立。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阶级矛盾加深,1786年的谢司(Daniel Shays)起义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反民主的气氛日甚一日。哈特福德才子派[11]发动了所谓“把康涅狄格共同体从民主的污染中拯救出来”的运动,把“所有的动荡都算在了民主的账上,迫不及待地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熄灭民主之火”。[12]主张限制民主,恢复秩序的人们集结在联邦党人的周围,队伍不断壮大;相反,坚守大众民主的反联邦党人却四分五裂,起不了什么作用。[13]
在民主派人士缺席的情况下,1787年的制宪会议成了保守派的一场聚会。筹备者将各州的代表由5名削减到3名,而且,各州代表人数并不一致。[14]正像埃尔弗雷德·杨(Alfred Young)发现的那样,制宪会议的领袖都是些“和事佬”,他们为着保守的目的而出卖民主。[15]美国宪法的鼓吹者将制宪会议誉为“上帝的作坊”,而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却为人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5个凡夫俗子聚集在一起,炮制了这样一纸文书,而实际上参与签署这一文件的不过只有39个人,更不用说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奴隶主;13个州总共不到2000人投票通过了宪法”。[16]
在费城拉下窗帘的会议厅中,制宪者们坦率地表达了对民主的不满和谩骂。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一致认为,美国政治的危机滋生于民主过剩的危机。爱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认为,“如果追溯这些罪恶的源头的话,每个人都会发现,那正是起因于民主的骚乱与愚蠢。”[17]梅森(George Mason)则认为,“我们过去太民主了,但却不敢说出来,不小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应该注意人民中每个阶级的权利。”[18]格里(Elbridge Gerry)则指出,“我们经历的罪恶正是来自过度的民主。”[19]坦率地讲,他并不喜欢由人民进行的选举。[20]
在历时五个月的讨论中,制宪者当中仅有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梅森、格里、伦道夫等人在6天内7次提到民主,且一般都与“罪恶”、“暴政”、“过分”等词联系在一起。[21]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评论指出,“美国的宪法不是民主革命和反对英国体制的产物,而是民主强烈反作用的结果,并且倾向于母国的传统。”[22]
当时人们并没有像今天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欢迎1787年宪法。宪法在各州的通过是艰难的,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当南卡罗莱纳州偏远地区的农民听说他们的州已经批准了宪法时,他们将一口棺材涂黑,拉着它举行丧礼,并庄严地把它入土,以象征公共自由的寿终正寝。[23]
1787年宪法的通过使美国宪政制度的安排尘埃落定,它试图通过“宪政试验来制约绝对民主的危险”,[24]但却没能为民主与法治争论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对美国宪法的态度来看,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它的反对者,他们之间最能开诚布公地谈论的一件事就是,美国宪法不是民主的,至少主要不是民主的。人们抨击这一“最陈旧的教条”,是因为它不是民主的;人们信仰这一最古老的宪法,也是因为它不是民主的。
二、互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以民主和法治为框架的政治文明二元结构中,过分强调民主就会挤掉法治的空间,而过分强调法洽亦会扼杀民主的活力。由此看来,无论是“民主优位”还是“法治优位”,其极端形式都会使政治文明的发展畸形。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弥补革命时期两种模式存在的缺陷,造就民主与法治均衡的模式成为西方政治文明对其他政治文明的最为有益的启发。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制宪会议前,麦迪逊“强烈地认为,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国家的立法机关来实行”。然而,在制宪会议期间,他对这一立场的怀疑却“越来越强烈了”。[25]尽管麦迪逊宣称“在政府应该为社会提供安全、自由与幸福这一实质精神上”他“决不退缩”,[26]但无论是制订宪法,还是争取批准宪法,麦迪逊均站在了联邦党人的行列。如果说这一转变顺应了美国革命由民主转向法治的话,那么,麦迪逊在宪法通过后转而加入杰斐逊的阵营则引领了美国政治由“贵族共和”向“民主共和”过渡的潮流。[27]
麦迪逊的转变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微缩景观”。就美国情况来看,民主共和党人赢得了1800年的选举,杰斐逊当选总统,掀起了所谓的“1800年革命”。民主共和党人执政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联邦党时期的司法体系,增强了美国宪政的民主性。在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很快就“创造了一个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几乎立即改变了制宪者们原有创立的宪政体系。”[28]
我们看到,主张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自由主义是在同民主的结盟中受益的。美国学者巴伯(Benjamin Barber)指出:“1688年以来,自由主义在其不稳固但却常常是辉煌的政治史中,促进了许多联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革命与官僚、启蒙与浪漫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主义。结果,没有哪一个联盟能比它与民主的结盟更使它受益。”[29]
事实上,正如美国政治家克罗利(Herbert Croly)看到的那样,自由的“朋友”对民主常常并不友好,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甚至使人相信,“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依赖于对人民主权的否认和对选举的严格限制”。[30]以强调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逐渐地改造自身,在不断接受民主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这在自由放任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美国的“新政时期”,人们要求在集体自决中对自然权利的正当性进行辨论,把“高度的可信度”与“高度的协商”结合起来。孙斯坦在分析这一趋势时指出:“新政者期望有一种由公民和代表对公法的基本制度进行协商决策并通过反应迅速却很专业的机构进行运作的制度。摒弃不民主普通法秩序维持制度和通过法官确立的宪法体制,代之以服从公众政治意愿和贯彻公众指令的新的规范制度。”[31]
作为对这一观念的反动,在美国新政时期,人们发展了一种被派尔斯(Richard Pells)称为“民主集体主义”[32]的观念以弥补传统个人主义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克罗利认为,美国人民的希望在于“实现某种程度的纪律而不是经济自由的最大化;个人的服从和自制而不是个人难填的欲壑”。[33]杜威(John Dewey)亦认为,个性回归之路在“不再将社会合作和个体对立起来”,社会合作才是建设新的个体性的基础。[34]“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的经验之力量的信赖”成为民主的基础,[35]而“民主的共同体”则成为美国人的追求。[36]
与英国自由主义接受民主相反,欧洲大陆的思想界却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检讨“民主革命”之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场反思成为保守主义的源头活水。它串起一条自柏克(Edmund Burke)、德·迈斯特(De Maistre)及其追随者和盟友直到后来法国的勒庞、西班牙的奥尔特加(Jose Ortega)、英国的梅因(Henry Maine)等一系列保守主义思想家绵延不绝的线索。
不仅如此,“对暴民的恐惧,对无产者的恐惧”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题。[37]在民主问题上的一致性甚至模糊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边界。“对多数可能利用政府权力施行虐政的恐惧”显得“既真实又急切。”[38]民主带来的多数暴政成为托克维尔、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断咀嚼的主题,它划清了欧洲自由主义向消极自由退守的轨迹。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实现它所宣布的大部分目标,它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想体系的终结。”[39]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变得疑窦重重,博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就在此时,平等的原则却在毫无节制地疯长”。[40]在19世纪,人们很难在欧洲大陆找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家了。法国政治思想史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曾对此大惑不解,他无可奈何的指出,“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41]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迈斯特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任务就是毁灭18世纪曾经建立起来的一切。[42]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民主优位”和“法治优位”两种模式各自“进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一种反方向的思想运动。在时间不尽相同,但却基本类似的运动中,民主与法治不断地走向融合:在英美,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人们迫不及待地撕下“原子”个人主义(atomicindividualism)的冷漠面具,热情地拥抱民主;在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潮流却使欧洲思想界一片冷清,陷入了对法国大革命的长久反思,渴望着法治秩序的建立。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它所昭示的正是以冲突为动力,以“对立一互动”为特征的演进模式。
三、张力: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样式
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成就来看,民主与法治无疑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志。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制度样式,法治与民主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社会宪政民主制的基础。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使政治问题进一步复合化,就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和权力的结构性安排来看,它需要人们回答的是这样两个问题:权力与权利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起作用?
就政治意识来看,权力与权利的心理与思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观的基本特征,人们常常以“权力政治观”或“权利政治观”来描述现代西方政治现状。
就政治制度的形成来看,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渗透到了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当中,重构了另外两个问题,即民主与法治各自的界限是什么?
人们至今还是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主所及的范围亦进一步的扩大,它要求人们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内对民主的范围做更深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回答。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表面化:激进的民主派更进一步地主张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号召将民主程序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保守的自由派则坚持自由放任,主张通过宪法性的限定约束严格限制民主的范围。他们之间的冲突正是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表现。尽管民主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人们以整体为核心设计的权力结构更富有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要求的权利保障为民主权力设置的阻力亦是同样的强大,同样的富有合理性。
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取得巨大的成功后,达尔试图进一步提出一个“比美国人现有的体系更高的自由与平等的体系”。[43]为着这一目标,他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达尔试图将民主程序扩展到经济领域中。他指出,“如果民主在治国中是合理的,那么,在治理企业时,它同样也是合理的。”[44]这里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民主程序的假设是正当的,任何组织的成员都有权通过民主程序的方法来实现自治。”[45]
然而,面对民主派在民主与法治关系上的“矫枉过正”,自由派并不认账。他们重申传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法治精神,主张严格地对民主加以限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即对过于“民主”的宪法表示反感,并斥之为“坏宪法”。他指出,宪法的功能就在于它“既制约掌权者的意志又制约民主的‘人民的意志’”,而在当代社会中,“某些宪法如此‘民主’,以至于它们或者不再是宪法,或者它们使政府机器的运转太复杂以至于政府无法运转,或者两者兼而有之。”[46]
与萨托利呼吁回归到自由主义的限权宪法相对,拉米斯(Douglas Lummis)则“呼吁回归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力上去”。[47]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眼里,民主就是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的复合体,“‘民主’曾经是一个属于人民的词、一个批判的词、一个革命的词。它被那些统治人民的人所盗用,以给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是该收回它,并恢复客观存在的批判和激进力量的时候了,这样的复兴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48]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民主与法治之间可以产生矛盾的问题作为规范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而存在着”。[49]在民主与法治的争论中,尽管人们态度各异,但却都表达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认同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霍姆斯指出:“有些理论家担心宪法上的约束会窒息民主。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宪法之堤会被民主的洪流冲决。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都一致认为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和不可调和的张力。的确,他们接近于认为:‘立宪民主制’是对手之间的联姻,是一种矛盾修饰法。”[50]
就政治意识的发展来看,当代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还是“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继续。与之相对应,从政治制度的演进来看,西方政治文明越来越强调民主与法治的融合,进一步完成了“民主优位”模式和“法治优位”模式的调适。在人民主权与人权、民主与法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公域自治和私域自律之间,当代两方政治哲学展开了深入而又广泛地讨论。民主与法治关系的话题几乎吸引了所有的那些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潮。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重要的思潮之间,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带动了与之相关的自由与平等的政治价值、积极与消极政治态度、个人与集体的政治观念等主题而深入地研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指向标。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我们看到,西方政治文明就是在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演进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法国革命选择了民主,但却没有形成民主的制度化,是一种“民主优位”的革命;美国革命选择了法治,却相对弱化了民主的声音,是一种“法治优位”的革命。两种模式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向各自的反方向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实践了“民主融合法治”和“法治融合民主”的互动演进模式。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与均衡不仅是西方政治文明形成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它还决定了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
标签:政治论文; 法国大革命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明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