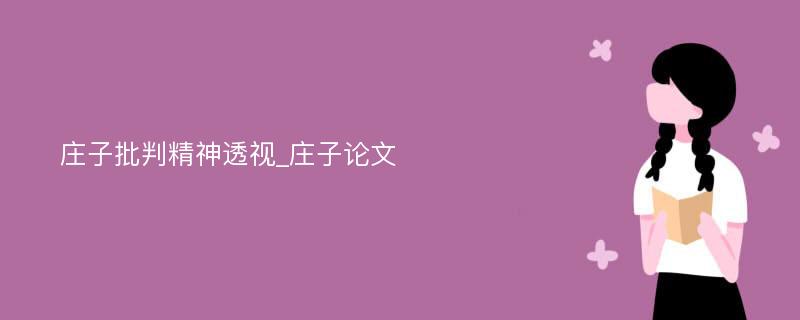
透视庄子的批判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透视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庄子》,那么这部书表明,庄子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联系到后现代主 义思潮,似乎可以说,庄子的批判,在总体上具有通过“解构”而导致虚无的“后现代性” 。但是,庄子的批判最终又不可归结为“后现代性”,而有其崇高的目标和追求。这是因为 ,其一,庄子的批判,主要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所造成的异化。其二,庄子“ 解构”“礼乐文化”,是为了追求和展现一种理想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批判“礼乐文化”的 异化,集中体现为庄子对于“待”的揭露和消解。
在庄子那里,“待”的基本内涵,就是有所依赖。由于有所依赖,就不能不受到所依赖者 的约束、局限,甚至受到统治和压迫。不过,这里必须区分“待”的两层不同的含义。人活 在世上,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不能不有所依赖和寄托。庄子对于“待”的这层含 义,是否也要加以消解呢?非也。但是,一旦从正常的依赖和寄托而变得受依赖者或寄托者 的束缚和压迫,就是说,出现了异化形态的“待”,那么,人的身心就失去了自由。显然, 庄子所要“解构”的,主要是这种异化形态的“待”。
异化形态的“待”,对于人在身心上的束缚和压迫,是很残酷的。庄子把这种束缚和压迫 表述为,人为“物役”、“物累”,甚至“殉物”。例如,在《齐物论》中庄子这样写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终身役 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哀邪!”就是说,人生而为“物役”,受“物役 ”的折磨几乎是一种不可变化、不能停止的悲剧。同时,这种终身为“物役”者,不仅不见 其成功,而且即使在疲惫无力支撑之时,仍是茫茫然,处于找不到归宿的哀境。
对于“待”,可以这样说,当庄子在批判中对之不加区别地“解构”时,他的批判就含有 与当今后现代主义相似的“后现代性”。不过,庄子往往是借“解构”而超越,即追求和展 现一种理想的自由境界。对于庄子批判的这种二重性,在《逍遥游》中有一则纲领性的表述 。庄子这样写道:“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难理解,庄子这里所说的“己”、“功”、“名”,
就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文化”。庄子的批判,就是把这种“ 礼乐文化”视为“待”,而以上述的“三无”加以“解构”或“消解”。
但是,从基本方面看,庄子的批判并不完全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构”或“消解”,也不 是没有目的和追求,以至像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那样陷入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庄子以上述“ 三无”所真正“解构”或“消解”的,主要是“己”、“功”、“名”的异化形态,也就是 “居己”、“居功”、“居名”。事实上,道家从老子到庄子,对于尚未异化的“功名”, 并非一概加以反对。然而,任何“功名”的取得,都潜伏着可能以“功名”自居的异化。因 此,他们才特别强调,真正的圣贤应当“功成身退”。例如,庄子对尧的“功成身退”是这 样描述的:“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 天下焉。”在这里,尧“窅然丧其天下焉”,即达到超越世俗功名的境界,正因为他已成 就功名“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在庄子看来,即使像尧这样的圣贤,在功成名就之后 ,也必须“功成身退”。
显然庄子所追求的,乃是通过上述“三无”这种“解构”而达到“无待”,即作为“游无 穷”的“逍遥游”。有些学者把庄子这种“无待”的追求,称为“绝对自由”的追求。我认 为,如其说“无待”是“绝对自由”,不如说是“理想自由”。或者说,“无待”是庄子设 定的理想目标。并且,正是由于设定了理想自由的追求和目标,才能在“解构”或“消解” “待”之后,避免陷入虚无主义的苍凉和恐惧。不仅如此,同时还使精神在对现实的超越中 提升到有如鲲鹏翱翔太空的自由境界。或者也像“功成身退”的圣贤一样,不仅没有任何失 落感,反而感到空前的轻松和自在。
当然,对于庄子的超越观是有争论的。不少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观,属于内在 的超越。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关于从此岸到彼岸的超越观,确乎不同。应当说,这样 的看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由此所作的某些引申,就不一定是合理的了。例如,“文 革”前某些极左派理论家认为,庄子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内在超越”,不仅没有积极价值 ,而且是属于应当被完全否定的阿Q主义。今天,我们再来看极左派理论家对庄子的批判, 那么,这种批判倒是一种没有任何积极价值的简单否定。因为,这种批判不仅没有任何创新 ,而且把庄子超越观的深刻合理内涵也简单否定掉了。
事实上,引导庄子提出追求精神自由这种超越的出发点,并不是精神问题,而恰恰是具体 的社会现实问题。庄子揭露的,人为“物役”、“物累”、乃至“殉物”这些残酷的现实, 完全是奴隶制和封建专制统治现实的写照。庄子这些批判的深刻,至今仍能醒世警人。例如 ,他对于当时官爵的透视,就极其发人深思。庄子拒绝高官的诱惑,并认为如其从官,那不 过是被拉入太庙祭献的牛,虽然披红挂彩,最终仍逃不脱被宰杀的命运。
勿庸讳言,庄子在批判中所“解构”或“消解”的,大多是属于精神的不自由。他最为用 力之处,也主要是获得属于所谓“内在超越”的精神解脱。而这种解脱的精神自由,主要是 回到人的本心(真宰),即归于对“道”的修炼和体悟。例如,庖丁解牛“官知止而神欲行” 的自由境界;女偊“朝彻”、“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的自由境界,都源于对 “道”的修炼和体悟。从这种修炼所获得的超越中,可以看到庄子批判的软弱性一面。他的 时代局限使他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精神不自由与社会现实不自由的内在联系。尽管如此,庄 子所树立的“无待”这种自由理想,确是悬挂在中国专制统治长夜的一盏明灯,并且一直凝 聚和引导着中国的有识之士,去为争取社会的现实自由而奋斗不息。庄子说过:“哀莫大于 心死”(《田子方》)。中国人的自由之心,始终没有死。显然,庄子对此是有莫大功绩的。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