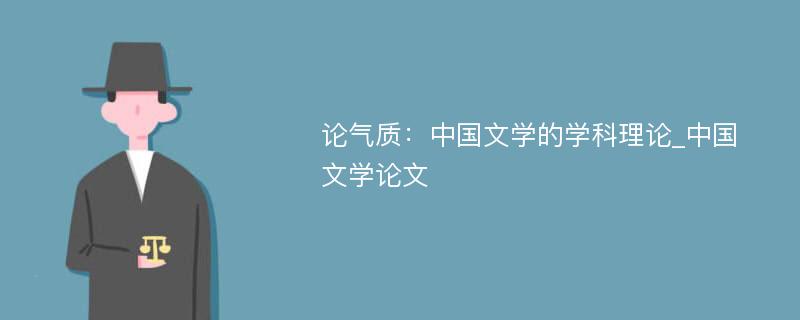
论性情——关于中国文学的主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情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情说,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精华。它不仅和灵气说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与此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和寄托,表达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换句话说,如果说灵气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那么性情就是它的灵魂;灵气来源于天地自然,而性情则是宇宙精华所聚,禀之灵气,散为文章,极尽“文学是人学”的艺术魅力。若无性情,灵气就无处寄托,而文章也就没有了生命活力,艺术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近年以来,关于文学主体论的学说众说纷纭,但我总觉得离哲学思辨太近,离美学和人学较远,这儿不妨探究一下中国文学中的性情之说,给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增添一份生气。
一、释“性情”
“性情”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双音词之一,其含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占据重要地位。《周易大传》曰:“利贞者,性情也,”把性情看作是天道原生,万物交合的精华所在。在《周易大传》中,所谓“元亨利贞”是天人合一的概念,不仅表达了万物资始,交合相聚的自然过程,而且也构成了人为君子的“四德”,后人释为仁、礼、义、事。不过,如何解释“利贞”之为性情,则有多种可能。如果把“元亨利贞”理解为一种生命过程的话,那么“元”为本,一生万物;“亨”为多,万物并盛;“利”为和,取万物之精华;“贞”为正,得生命之极致也。“利贞”在此表达了一种生命本原的最高境界,得之于天,而表现为人的性情。
然而,至少在战国时代,这种说法并不见得被很多人接受。因“性”和“情”那时和“利”与“贞”一样,还不可能粘合得那么紧,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隔阂和冲突。实际上,这种隔阂和冲突一直存在着,经过长时期的沟通和整合,才成为一种寓共同性与多样性为一炉的复合话语,其生命活力来自于丰厚的历史积累和意识发展中的反复构建。
谈性情,首先得释性。性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元话语,引起过王国维的高度重视。他的《论性》一文非常精彩,不仅对中国的“性”概念追根探源,而且以中西学理对照的方式探讨了古代各家学说的流变及其矛盾,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了性情之说。不过,这篇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性,尚未直接涉及文艺美学领域。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指出了自古至今纠缠于性善性恶一元论或二元论不能自拔的弊端,显示出了自己的卓见。其实,性从词源字形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象征和概括。性,“心”旁加一生命的“生”,按照古人“心之官则思”的看法,就是“能思维的生命”之意,可以说人的本性或者特点,但同时也是一种生命状态,问题在于从哪种角度进行解释。
人性来自于宇宙精气所聚,自然有其共同性的一面,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都是从共同性而言的,然而涉及到个性状态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在春秋战国时代,释性主要表现为二种角度,之一为从自然本源方面着眼,延伸出了人性的一元本质论或者共同性;之二为伦理判断的肇始,从具体经验角度探讨性之善恶;而这二者又经常互相交叉,形成难解难分的论辨僵局。
稍微能绕开这僵局的是老庄。不过《道德经》不曾谈到人性问题。但是从“道德自然”观点去推断,老子是推崇人性的本原状态的,所谓“圣人皆赤子”就是人性的理想境界。对此,庄子专门有《缮性》一文,其始就是“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和老子回归自然思想相通不悖。他认为古代人生活在混茫之中,处于自然状态,德无不容,道无不理,有知不用,是人性的佳境,但是后人则“去性而从于心”,“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在此,庄子还特别把性情与“志”联系起来,认为古人所谓得志,绝非“轩冕之谓”和“穷约趋俗”,而是保全自己的性情,“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庄子已经提出了艺术以性情为本的思想。而他之所以反对当时“礼乐偏行”,蔑视“轩冕”之志,是因为它们并非发之于性情,而且造成了自我与性情的失落。换言之,庄子并不反对言行礼乐,而是追求它们与性情的统一;若二者相悖,则宁取性情而去礼乐。所以他在《庄子·缮性第十六》中又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由此而推,庄子醉心于“疱丁解牛”、“庄周梦蝶”之类的神与物游境界,崇尚艺术而蔑视世俗权势,皆与其坚守性情有关。
可见,性情原本就是一种生命状态,其中自然包含着理、情、欲等各种因素;因为这是一种生命整体,其中必然包含着矛盾,在其运作中有生有死,有扬有抑。然而,人们一旦追逐于功利世俗生活中,一旦脱离了混沌为一的艺术状态,就不能不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规范和限制,按照外在的需要来剥离自己的性情。这也就是“性”“情”二字长期不能牢固粘连在一起的原因。其中道德和伦理判断的介入就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王国维在探讨中国哲学时曾对于古代“天人合一”与“仁”的观念给予过特别注意,并从中发现了古人处理天与人、性情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特殊思维方式。他指出:“天道流行而成人性,人性生仁义。仁义在客观则为法则,在主观则为吾性情。故情归于天,与理相合。天道即诚,生生不息,宇宙之本体也。至此儒教之天人合一观始大成。吾人从此可得见仁之观念矣(注: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8页。)。”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如何在普遍的社会之仁与具体的个人性情之间建造桥樑的。孔子学说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以追求“平等圆满绝对无差别之理想为终极之目的。”(王国维语)
也许正因为如此,调节普遍之“性”与个人之“情”之间关系,成为荀子(约前313-238)面对的一大难题。他认为性和情是有矛盾的,性来自于自然,“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而“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荀子·儒效》)然而荀子却又是把人的性、情、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探讨的一位学者,他指出:“生之所以然者为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而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又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同上)尤其可贵的是,荀子还专门谈到了“欲”的问题,认为人“天性有欲”,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节制,而且由此引申出了其“性恶论”观念,得出了“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的结论。在他看来,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所以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纵性情”,而且主张用礼仪法制“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
不难看出,荀子把“性情”引申到了更复杂的层面进行讨论,开始赋于这个概念更充分的生命要素,使它在痛苦和矛盾中站立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有“性善”与“性恶”之分,但是性情作为一个综合的有生命力的概念,具有多层次的含义,不但表达着中国人对善和美永久的追求,也包含着人生在自我追求中的痛苦体验;既是普遍的天人合一的自然造就,又无不活跃着个人情欲的自由意志。
二、性情的美学意味
于是,我们在荀子的学说中发现了这种僵局,即,性情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状态已经被确认,但是却得不到合理的存在理由;人们在无法摆脱和否认其存在的同时,却不能给它一个安居的美好家园。其实,这一困局一直在人的精神历史中存在,直到十九世纪,还使一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困惑不安,生命中的欲望给于他所意识到的自由意志实在是痛苦多于快乐。
问题是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和困局?换句话说,一种不可摆脱和消除的生命存在,是否也有完整存在和显示的理由和家园?
荀子无法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得给性情之欲留一点余地,于是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可见荀子的“性恶”其实是“欲恶”;无法“去欲”,就只好用礼来相抗,而如此又失去了礼之所本。最后还是王国维数千年后给他解了围:“考荀子之真意,宁认为(礼)生乎人情,故曰‘称情而立文’。又曰:‘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之极也。’荀子之礼论至此不得不与其性恶论相矛盾,其所谓‘称情而立文’者实预想善良之人情故也(注: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95页。)。”
尽管这场“情”与“性”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但是一种以性情为主的美学观却在自然生成,“性情”一时在政治和伦理道德范畴立足艰难,却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得到所有。中国最早就有“诗言志”一说,所谓志者,就是指一个人思想感情,并不受仁义道德的规范,所以庄子在《缮性》篇中就提到“乐全之谓得志”。这个“得志”就是能“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此可见,庄子美学同样具有“天人合一”的特点,其“天”就是宇宙自然,其“人”就是人的性情,而这二者从本原上来说是浑沌为一的。
在这里,性情不仅与天道自然同一,也更有其特殊的内涵——这就是真诚。在庄子看来,有无性情或者是否能保持性情,关键在于是否真诚。如果把性情看作是艺术家主体存在的话,那么真诚则是其有无艺术价值的关键因素。这里甚至可以说,无真诚者就无所谓性情,而无性情者更谈不上真诚;唯有从真诚中才能见性情,而在性情中才会有真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情与真诚是不可分的。庄子在《渔夫第三十一》中表达得非常精妙:
“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文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这也正是庄子反感礼义的地方,因为礼义是表面的,而性情是内在的,而他和孔子最大的不同在于重性情还是重功名;这不仅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更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人生状态,前者是艺术的,后者是世俗的。所以庄子在《渔父第三十一》中还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移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古代“真”的概念原本就与近代西方真实观念有差异,它所注重的是一种主观的真实和生命状态,本义就是指人的本原和本性。《庄子·秋水》中有“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里“反其真”也就是“渔父”中的“反其性情”,可见庄子所说的“真人”也就是性情中人,“真”和“性情”是可以互释的。这也就形成了中西文艺理论不同的范畴和思路。
重性情者,必然重人的自然本性,重人欲,重情趣,把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而并不在乎世俗功名的规范。这种思想在先秦已很流行。据《列子·杨朱第七》中所记言,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人生不必为世俗声名所累,而应该尽性尽情活着,理由是“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住,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而其中还提到一种“养生”观念就是“肆之而已”,这就是:
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阈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阈羶;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阈智;体之所遇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阈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阈往;凡此诸阈,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
——《列子·杨朱第七》
这种任情极性的人生态度显然与儒家礼教观念全然相左,这里引“礼记”开首后数句为对比:
敖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礼记·曲礼上第一》
可见《列子》中所推崇的纵情尽性的生活态度主要针对当时束缚人性的礼教规则和世俗功名,所追求的是不为钱财声名所累的“乐生”和“逸身”,也就是活着就是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其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郑国有公孙朝和公孙穆兄弟,好酒好色,不治身治家,引起子产等人担忧,去用礼仪之说劝诱,不想朝穆如此回答:“我早就对人生有所考虑才选择这样生活,人生珍贵,而且很容易失去,如果如此还要遵奉礼仪让别人夸奖,违背性情去获取声名,那还不如死了好!我生来就是要极尽生命万象之观,享受生命快乐,所以就怕胃不好不能享受美食之乐,身体不好不能肆情于色,并不怕自己名声不好,生命有危险。你如果用治国的道理来说服我,用礼仪言辞来扰乱我的心,用荣华富贵来诱惑我,难道不是很卑鄙而且很可怜吗?”朝穆还继续讲了一套“治内”与“治外”的道理,认为治国就要合乎人心人性,让人们生活得开心,使前来规劝他们的子产“无以应之”,后来朝穆被认为是“真人”。
当然,这是一种寓言的叙说方式。《列子》在各方面都承袭了庄子的思想,在性情方面更不例外。以上所说并不见得完全合乎生活真实,但是它们和庄子的“疱丁解牛”一样,无疑表达了一种生命方式和姿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生命方式和姿态本身就是艺术,因为只有这种生命方式和状态才能在一个有诸多规范和限制的社会生活中保持性情,体验生命的极致和“大方无隅”。
其实,老子和庄子都没有给艺术下过什么定义,甚至没有提出过“艺术和文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学说确实开创了中国文艺美学的先河。其中奥妙之一或许在于,在中国最古老的意识中,艺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技艺或者文本,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换句话说,只要人能够像疱丁解牛一般聚精会神,达到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境界,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是艺术。这种以人的状态来界定艺术与非艺术概念的思路,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独特性,而且与西方文艺美学重形式,重修辞的看法有明显差别。由此,从《列子》中可以看出,艺术不仅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人生,一种“从心而动”“从性而游”的生命状态。
既然艺术是一种生命状态,性情在此就无所遮蔽,无所束缚,能够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就不能受制于一个有限的世界,就得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这就是艺术。所以在《庄子》和《列子》,我们经常所触及的是一个幻化的寓言世界,因为只有这个世界中,人的性情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发挥,才能获得自己的完满存在,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一点在《列子·周穆王第三》中可以得到印证。周穆王自以为在世俗生活中享尽了富贵荣华,所能得到的满足已无以复加,但是在能“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亥”的化人面前自叹弗如,因为化人能自由创造一个“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的梦幻之境,而且能够在须臾之间完成,可谓“穷数达变”,无所不至。
这是性情的真正家园。而唯有重性情的人才能创造和拥有如此家园。在这里,我们或许会联想到弗洛依德对文学艺术的解释,他认为创作就是一种“白日梦”,是人的欲望,首先是性欲受到压抑后所产生的一种“幻想的补偿”。而在《列子》中同样有这种思考,其中“幻化”和“白日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周穆王第三》所讨论最多的就是梦幻,认为人就生活在“梦与不梦”之间,若能生活在美梦之中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对此列子有如此寓言为证: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伇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伇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有慰喻其勤者,伇者曰:“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
——《列子·周穆王第三》
三、性情文学与文学主体论
可见,把弗洛依德“白日梦”之说与列子梦幻之说进行对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所不同的是,弗氏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进行分析推论而得,而列子则表现了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着重于人内在的感悟和想象,把人的生命状态和外在宇宙自然融为一体,难分难解,自然也消解了“梦内梦外”的界线。子列子如此释梦:“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梦自俏,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可见在他看来,“真人”并无“梦与不梦”的区别,只有“神”和“形”的互相交通和转化,能够“神遇”和“物化”,生活在一个无差别的世界。而这正是“真人”和一般役夫之类的区别。
因此,人们经常把艺术家称为“狂人”“痴子”“呆子”以及神经病患者也是由来已久的,古今中外都有此说。因为他们经常处在幻想的世界里,以致于经常像“庄周梦蝶”一样,分不清物我的界线区别。老子所喜欢的状态就是“我独昏昏”“我独闷闷”的“愚人之心”。庄子也不例外。在《列子》中,列举了很多迷幻之人的事例,其中端木叔就是一个典型。他“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还把家里的财产都送给别人,连子孙都不顾及,到死的时候连葬埋的钱都没有。墨子的弟子禽骨釐听了以后说他是辱其祖先的狂人,而有人却认为他是“达人”。也许两千多年后俄国的托尔斯泰的性情可以与这位端木叔相比。托尔斯泰经历了早年的放荡生活,晚年却要把财产散给穷人,遭到全家人的反对,最终独自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有人说性格即命运,在此不如说性情决定艺术,艺术家主体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指认(Identity)。不过,这种主体的确认并非千篇一律。比较一下列子与弗洛依德学说就可看出,后者特别关注主体结构中的性欲因素,把生命中的性压抑看成是艺术冲动的主要来源,并由此提出了“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用来解析文学创作中的潜意识状态。而在列子的有关梦幻解说中,压抑和匮乏可能是多方面的,都可能成为梦幻的动因。而是在人们创造和进入一个梦幻的艺术世界过程中,性情始终是一种主动的情结,能够自觉地创造气质,使自己获得自由的展现和自在的生存。
这也就形成了性情与艺术创作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性情的极致就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作则无疑显示一种性情;所谓艺术主体的魅力也就是性情的魅力,它显示出艺术家独特的人格和气氛,以一种独有的艺术方式显示与众不同的生命状态。在这里,所谓艺术家的独立性以及艺术的独特价值,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荡漾在各种艺术创作中。由此性情文学或性情即艺术也成为中国重要的美学观念之一。
不过,这一观念的确立并非是通过理论体系的完善,而是源远流长的艺术实践所积淀和印证的。换句话说,性情文学作为一种有独特生命力的文学主体论,在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建构中并不显得突出,相反由于它不断受到了来自正统的理论观念的打压,只能处于“大美不言”的“次理论”(Sub-theory)状态。而真正占据意识形态高地,并成为主流的是“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这也许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动力之一,把一种原生态的美学积淀从“次理论”状态中解救出来,使现代文艺美学具有历史的魅力,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重写文学史原本不能从现代开始的,而不得不追溯到文学的源头。
在这里,我们首先获得的惊喜就是“个人性”的发现。这也是性情赋于文学并表现在文学中的最重要的特征。而文学是否是个人性的,正是中国自古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先秦时代,“道”原本是一个普遍的自然概念,但日后却产生了分化和差别。政治家用它来讲信条,规范和纪律,自然不喜欢文学搞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艺术家讲自然,崇尚性情,自然不愿意生活在樊笼之中,两者冲突不可开交,后来才产生了“和而不同”的观念,大家各让一步。不过,孔子修编“诗三百”和屈原汩罗江边“露才扬己”(班固语)已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人们对于孔子编修《诗经》历来众口一心给予肯定,但是对于屈原“露才扬己”却争议了上千年。原因是《诗经》原本就来自于民间和庙堂的集体之作,而《楚辞》则是在吸收民间文学基础上纯粹的个人创作。而孔子虽然也是性情之人,喜欢“春服既成”结伴而游,但毕竟以社会功名为重,用“思无邪”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屈原虽然也是庙堂中人,忠君爱国,但毕竟不能改移自己的狂狷性情,用文学来自我表现。
我认为从《诗经》到《离骚》表现了中国文学向个人化阶段的转变。《诗经》虽经文人修编,但基本上还属于原始的民间形态,而《楚辞》决不相同。司马迁称赞《离骚》“与日月争光”;王逸说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无不从尊崇个性,看重艺术作品的独创性。确实,屈原的创作无不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显示自己的性情。《桔颂》中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就是屈原独立人格的写照,所以明人汪瑗称《楚辞》为绝唱,因为“盖楚山川奇,草木奇,故原人奇,志奇又文奇,发乎辞章,敻立千古。”
明人焦竑在《梦辞集解序》中曾说:“余尝谓古书无所因袭,独由创造者有三:《庄子》、《离骚》、《史记》也。”就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文学观念的衍生来看,这三部书确实从自然、个性和历史等方面独步千古,贯通了灵气、性情和人物为一体的艺术品味。至此以后,性情在文学发展的观念形态上虽然并不占据上风,但是在创作实践中却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挥。到了魏晋时代,性情文学已如鱼水相依,深入人心,成为文学意识自觉的标志。陈寅恪先生曾在史学研究中开创“以诗证史”的方法,而我们从文学创作中更能看到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演变。中国传统美学意识的精华往往是显现在创作之中,并不一定形成理论,所以“以诗见论”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魏晋有二部奇书,是性情文学的绝唱,也最明显表现中国文学主体意识的自觉。一为《陶渊明集》(梁萧统(501-531)所编),一为刘义庆(403-444)所编著《世说新语》。陶渊明(365-427)是在功名和性情之间选择了诗酒人生,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了“我”的色彩。他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因为不能忍受与性情相违的生活,才回归自然“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他的《饮酒二十首》更表现了一种独特人生,田园养性,美酒陈情,因为在诗中他能找到自己:“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所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恐怕就是他最为迷醉的“酒中有深味”。
司空图言诗含蓄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名句,而刘义庆编著《世说新语》,虽不论说性情,但通篇尽显性情的风流魅力,把艺术家卓然标新的个性风采推向了极致。在《世说新语》中,文学和性情是统一的,而文学艺术欣赏的最高层次就是性情的把玩和把握。性情在这里是独特的,不同于圣人更不同于俗人,而多是“方外之人”的文采和风采,谁能“立异言于众异之外”,谁能“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谁“才藻奇拔”,才情秀逸,与众不同,谁就最能得艺术的神韵。
其实,性情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是一种艺术人生的特殊的“文本”,具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美学意味,因为这是艺术家在与世俗对抗中,用自己的生命所能坚守,并贡献于人们的最终价值。性情不但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更是人学与美学相交合的生命结晶,显示着自己不屈服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和追求。尽管日后人们对艺术有多种看法,但是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性情中人这一点逐渐成为共识。就连刘勰(约465—约532)写《文心雕龙》时都不忘这一点,他在《情采》中说:“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在《体性》中曰:“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而另一位理论家钟嵘则把“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看成是诗的本源,并且开始以品论诗,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至于在艺术创作中,日后文学大家无不崇尚黄老,放诞人生,以文学尽性情之魅力,以性情立文学之真缔。
正是在这种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艺术与世俗世界相互碰撞和交融中,性情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内涵。对艺术家来说,它既意味着一种人性的美学选择,同时又意味着用一种美学途径来维护、张扬和展现人性;既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家主体状态的独特表达,也可以看作是美学陶冶和艺术体验过程的自然结晶,最终向人们贡献出卓然出众的个性精神风采。当然,中国文学之所以重性情,也是对在专制统治条件下人性受到种种压抑和摧残的某种回应,因为艺术家自由写作和自由做人是永远连在一起的——这正如性和情本身就不可分离一样简单明了。王文公(1021-1086)论性情时批驳“性善情恶”论,坚持“性情一也”,也是一种对艺术家主体性的肯定。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人性论文; 列子论文; 读书论文; 楚辞论文; 世说新语论文; 国学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