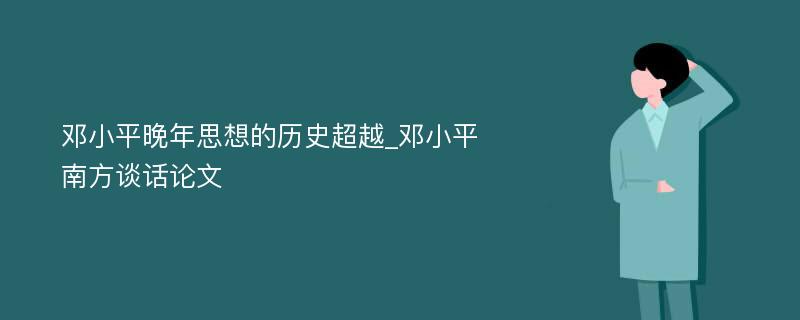
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历史性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晚年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思想到内容的全面继承,如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原则与按劳分配原则等;思想上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二是继承了原来的概念,更新了原来的内容,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跟原来一样,邓小平也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1](P165),但具体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新意;三是继承了原来的内容,更换了原来的概念与名词,如革命与建设的发展模式,从原来的“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如从“争取外援为辅”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正如邓小平同志自己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1](P300)
一、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一)在指导思想上,从参照别国模式到独辟蹊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探索自己道路的先驱者。他带领人民成功的探索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且还开始探索过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是指在革命的原则与大方向上走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走俄国革命“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毛泽东在成功地纠正了王明等照搬照抄的错误后,才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中国民主革命才走上正道并取得了胜利。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一开始毛泽东也遵循了这个思想。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谈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试图加以改革,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P261)原因是这次探索是在肯定苏联模式和维护斯大林形象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回旋余地很小。比如说在经济体制上,在充分肯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来发展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政治体制上,在充分肯定中央高度集权的基础上来搞民主化建设;在文化体制上,在充分肯定苏联式的“一种思想”,“一个声音”的基础上来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晚年毛泽东以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只是在一些比例关系上做文章,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层次矛盾,比如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分配制度、管理体制等认识不够。因而这种探索注定只能是对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在中苏论战中,为了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我党反其道而行之,重新维护斯大林,不但维护他的旗号,而且不恰当地把斯大林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否定这种模式,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在《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我们这样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3]这在理论上就堵塞了对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之门。60年代以后,在实践上,我们对50年代中叶开始的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积极成果也否定了,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改革,我们重新因袭“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向斯大林模式看齐,搞“一大二公”,取消一切非公有制经济,甚至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上仍然坚持平均主义,把轻微的贫富差别也看成是两极分化,甚至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都当成“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在市场上我们又限制商品交换与流通,甚至限制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搞“一平二调”;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我们一度更加封闭,把自力更生片面理解为“万事不求人”,搞完全的闭关锁国。所以,在毛泽东临终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是斯大林模式的翻版。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重新调整了思路。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3),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又确实走出了一条与苏联或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准确地说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一种体制的完全更新,尽管一开始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但大方向完全正确。首先是在计划经济的封闭房子里打开了市场调节的口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然后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在体制改革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最后才于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问题,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所以,在苏联模式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是方兴未艾。
(二)在手段上,从打破常规到打破僵化
毛泽东是我党最早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人,并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忠实地贯彻了这条思想路线。邓小平坦言,我读的马列的书不多,我就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在贯彻思想路线时,晚年的毛泽东偏向于打破常规。常规的东西有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有的则是陈规陋习。对于前者我们要尊重;对于后者,才是必须打破的。在毛泽东的早年,成功地破除了对苏联经验和马列教条的迷信,做到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晚年,却不恰当地破除了对客观规律的必要尊重,其结果必然是异想天开,偏离了实事求是。比如“大跃进”年代,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破除了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异想天开的东西都出来了;在贯彻实事求是过程中,邓小平则偏向于打破僵化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束缚,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并把它作为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改革初期他带头反对“两个凡是”,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擂响了战鼓;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反对抽象的“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引领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潮。正是他倡导的解放思想的推动,才使毛泽东一贯倡导而晚年又不自觉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与发展。
二、从“造反有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在思想上,从欣赏“天下大乱”到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毛泽东时代,曾经欣赏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时常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毛泽东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4](P688)因此,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连绵不断,其实这种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乱了自己。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国际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二是中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不能乱,不许乱,因为动乱的危害太大了。经济建设不能在动乱中进行。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十分贫穷,正是因为那里连绵不断的动荡给经济建设带来了灾难。江泽民进一步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唯有稳定才能搞好经济建设。国泰和民安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国泰就没有民安;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也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5](P210)
(二)在工作重心上,从“造反有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革命重心转移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完成了三大改造后,毛泽东也主张过“向自然界开战”,暗含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位置。但是,晚年的毛泽东却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之中。1966年8月24日,他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1939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讲过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4](P478)。这句话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重新走红,以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长期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邓小平同志反其道而行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后,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最得人心的口号。邓小平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P249)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有了邓小平的教导,我们党才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二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才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观点。
(三)在价值取向上,从欣赏“大民主”到崇尚法制
毛泽东虽然有的时候也重视过法制建设,比如亲自起草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而且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以“某某宪法”强调,如工业中的“鞍钢宪法”,农业中的“八字宪法”等。但总的说来对法制建设是忽视的,他曾经讲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都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4](P610-611)他非常欣赏大民主,充分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欣赏群众的自发性。邓小平同志则不然,他非常肯定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要法律化制度化。邓小平说:“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1](P276)比如,在反腐败问题上邓小平说,一靠教育,二靠法制,“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江泽民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法制的健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法制的完善;反过来,法制的完善,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制,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5](P330)
三、从“不断革命”到“可持续发展”
(一)在完成使命的方式上,从“不断革命”到“持续发展”
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因而认为革命运动也要不间断地开展下去,因此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当成了“不停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发动了一个又一个革命运动。常常是这个运动尚未结束,新的运动已经发动。以为这样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新的阶段。人们疲于奔命。而且每个运动,总要整一些人,中国的人才,不是被这样那样的运动所打倒,就是自身转入这样那样的运动而空耗时间与精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1](P251)邓小平则相反,提出革命是分阶段进行的,不能无限期的“革”下去,在完成了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以后,要始终注意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来考虑,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却必须“持续、快速、健康”地进行。
(二)在发展思路上,从“向自然界开战”到与自然界和谐共存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从本义上看是要结束革命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或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由政治革命向生产革命与技术革命转变。所以,后人对毛泽东的这句口号往往评价甚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这句口号是不科学的,很容易造成误导。因为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毛泽东是把自然界看成了人类的潜在敌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而不是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的朋友,善待大自然。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但开荒造田,而且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湖造田,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人定胜天”。现在,痛定思痛,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因此,我们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协调,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至少不再把大自然当成潜在的敌人去“开战”。所以,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其思路与过去开发“北大荒”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毁林开荒,毁草造田,围湖种粮,而是“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还渔”,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从争当“领头雁”到“决不当头”
(一)在国际形势判断上,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到“无中心论”
毛泽东也提出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当头的思想。但是,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十分欣赏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的评价,潜意识中对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充满信心。“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8](P544)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先是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说是“蛇无头不行”,同时承认世界革命的中心在苏联;后来,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展,我们又否认了苏联的中心地位,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论断。所以苏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党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建议。邓小平则不然,他公开否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中心,而是提出了“多中心论”或“无中心论”。所以特别强调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风云的变幻,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思路。
(二)在国际争端的处理上,从“战争解决问题”到“和平解决争端”
毛泽东也主张过和平共处。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亲自打开了中美与中日关系的大门。但是,总的观点仍然是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毛泽东认为,国际争端的最后解决,仍然需要依靠武力。客观原因是毛泽东时代“冷战”比较激烈,但是主观原因则是毛泽东的战争思维在和平年代仍然发挥作用,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比较强调“对立”而有所忽视“统一”。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潮流。邓小平改变了传统的看法,先是提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推迟,后又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防止,世界正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转化。所以我们把国民经济从战时轨道转移出来。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P49)解决国际矛盾与争端,最终都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三)在国家利益考虑上,从“无条件支援世界革命”到“把本国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时代,我国承担了太多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要支援世界革命,在自己还十分困难,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情况下,支援其他国家的力度是空前的,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主义者,只要是真心反帝,我们就支持。”他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是无偿的,“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4](P540)当时还大批了王稼祥提出的“三和一少”思想,把它与国内的“三自一包”合称为“修正主义”纲领。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提出国际主义要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支持,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发挥,才能吸引世界人民向往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4](P240)中国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江泽民也说:“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5](P89)
(四)在斗争目标上,从埋葬“帝修反”到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列宁最早提出的,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句口号,所以,在斗争目标上,我们确定了在全世界埋葬“帝修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宏伟目标。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道远。”[4](P666)那时,帝国主义也想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对我政治上封锁,经济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较量,现在大家都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将在一个地球上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一球两制”,斗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利。所以邓小平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5](P535)
五、从“保护生产力“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一)在理论上,从生产关系天然先进到生产关系不断革新
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我们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一时比我们快,但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却比他们先进得多,因此,党的“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观点。虽然毛泽东也承认生产关系仍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认为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不够纯,“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生产关系才是最完善的。邓小平则认为,我国社会的落后,不单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上,而且表现为生产关系的不成熟与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方面。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根据除了一般的生产力落后外,还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上层建筑的不健全,意识形态的不纯洁等。而这种“不完善”,主要是体现在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生产力发展程度,所以主张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在实践上,从保护生产力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P218)似乎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大功告成。但是,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艰巨的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为旧的体制、政策、观念都会成为生产力前进道路上的新障碍。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是相对的,是暂时的,因为生产力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的改革总是相对滞后,如果不及时更新,再先进的生产关系也会由先进变为落后。所以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P370)因此,邓小平指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与前一次革命一样,也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或者说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
(三)在思路上,从“抓革命、促生产”到“科教兴国”
毛泽东并非不重视生产力发展,恰恰相反,有的时候还是十分重视的。比如,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与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10](P144)并说如果我们不能快一点发展,“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大跃进”时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就是希望在生产力发展上能够来一个突飞猛进。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是方法不对头。毛泽东同志抓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抓革命,促生产”,即以政治鼓动与阶级斗争去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靠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力。对于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忽视、轻视乃至歧视的态度。他提出的口号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比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又比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崇尚“土法上马”。邓小平的思路正相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P40)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5](P231)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上,从“大兵团作战”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毛泽东也重视过客观规律,比如他提出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好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提出过按客观规律办事,“建议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4](P652)也强调过领导干部要学会管理,学习技术,“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4](P662)但总的说来毛泽东搞经济的主要办法是发动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三年“大跃进”是这样,治理大江大河是这样,“农业学大寨”也是这样。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马鞍山钢铁厂时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4](P613)。终观其一生,比较多地确实过分强调了人的意志的作用。他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在他倡导下我党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篇强调的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对于客观规律却不大尊重。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非常注意调动,曾经说过,六亿人民的积极性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如何加以正确的引导有时则重视不够,把调动积极性本身当成了目的。邓小平则不然,提出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他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1](P150)邓小平还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P146)江泽民进一步提出“领导经济工作,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积多年的经验,有些基本环节上不去,整个经济就上不去,经济结构不协调,速度也快不了。”[5](P99)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不搞唯心论。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强调调动,另一方面则重视如何引导。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里的“切实珍惜民力”确实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五)在发展生产力的外部环境上,从欣赏封锁到打破封锁
毛泽东也有过对外开放的思想。毛泽东时代,我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包围之中,想对外开放也难。邓小平也说到:“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P127)但是,在晚年的毛泽东同志看来,封锁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反而可能是好事,因为封锁有利于世界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封锁有利于我们自力更生,“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说法尽管对于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是有好处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好象封锁不但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本来应该反对的封锁,如今倒成了欣赏的对象。比如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现在不急于进联合国,等到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了,再让人家来请我们进联合国,那时他们后悔就晚了。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中说:“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4](P410-411)在邓小平的时代,我们也面临过西方国家的封锁,一方面我们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去打破封锁。所以,我们把对外开放当成基本国策,邓小平多次重申,“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标签: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斯大林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