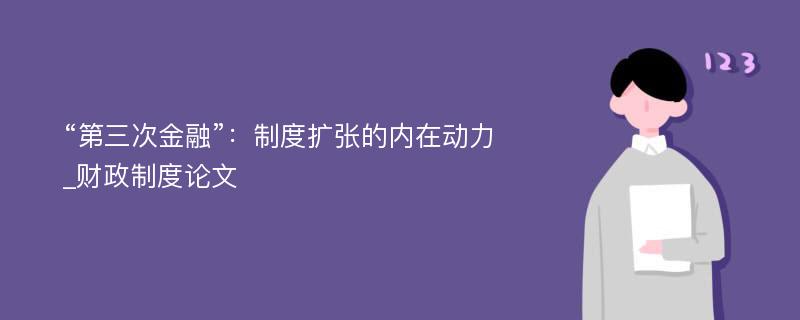
“第三财政”:机构膨胀的内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动力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机构膨胀的现状与趋势
十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机构体制改革。各级党政部门为精简机构,减裁冗员下发的文件可谓汗牛充栋,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多。然而时至今日,机构改革越改越膨胀,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就业的人数为1042万人,在事业单位中就业的人数为2534万人,合计为3576万人,占全国职工24%。仅仅1997年,我国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增员150万人。 此外,全国有4.8万个乡镇,803万个村,保守地算,每个乡镇按60个、每个村按5人“吃皇粮”的干部计算,那么仅此一项全国乡村有690万人吃“皇粮”。这样,两项合计为4266万人。与此同时,生产部门的下岗率不断提高。“八五”期间,国有企业下岗员工为1500万人;“九五”期间还将下岗1500——2000万人。直接创造国民财富的人越来越少,花费国民财富的人不仅绝对数增加,而且相对比例也不断增加,有识之士对此充满着忧患意识,有学者指出,如果任这种现状发展下去,国家迟早会支撑不住的。
推动机构膨胀的内在动力
为什么机构改革越改越膨胀?对此,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作出不少分析。我国人事制度上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机制;“吃皇粮”者收入稳定,失业风险小,等等,都是构成机构膨胀的基本原因。然而,很少有人将机构膨胀与制度外收入的膨胀联系起来考察。据笔者观察研究得出结论:制度外收入的形成和不断膨胀,为机构膨胀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财力支持,因而也就成为机构膨胀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何为制度外资金?这种资金主要来源于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和基金,是用政府的名义来强制征收的,本质上与税收毫无二致,属于广义的财政收入。但是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收支的格局中,它既不被划入预算内收入,也不被划入预算外收入的管理范围。如果把预算内资金称为第一财政,把预算外资金称为“第二财政”的话,那么,这种制度外资金则可以称为“第三财政”。那么,这种制度外资金有多大规模呢?目前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称,我国1995年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大致相当,可占GDP的10%, 制度外收入大约可占GDP的5%。另一些专家则从大量调查中引出结论:目前各级党政部门收取各种税外费之后,实际上交财政,由财政部门统一进行预算管理的“抵支收入”仅占所收费用1/4至1/2。其余的留作本部门自由支配。不少地方的财税大检查也证实这点。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制度外收入占全国GDP的5——10%是有可能的。如按1996年全国GDP达67795亿元计,则制度外收入可达3398亿至6779亿元之间。
庞大的制度外资金的收支运行,必然形成一个强大的内在机制,将那些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为宗旨的政策及其相关措施抵消,使其政策效应为零。具体地说,这种内在机制表现为4种驱动力:第一, 对制度外资金的征收,必须要有一支基本征收队伍。税外费征收权的获得,就意味着征收部门获得了这些制度外收入的支配权,从而也意味着这些部门获得相当一部分超出规范收入的部门收益。这种税外费征收越多,部门的收益也就越大,从而干部职工的福利收入也就越好。于是,原先已有收费项目的部门,会以各种“正当理由”,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收费的项目和范围;而尚未有收费项目的部门,也会不甘心落人之后,所以也会不断“创造条件”,推动种种收费文件的产生,于是形成如今差不多每一个政府部门和相当一批事业单位也都拥有了税外费的征收权。无怪老百性惊呼:除了5大税务局(国税、地税、海关、工商、 交通)以外,还有无数个小税务局!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自然而然的膨胀起来。征收权获取之后,仅靠原来编制内的人员已不足以实施征收的需要。于是争取编制、增加人员又成为其发展的必然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制度外收入的出现,是机构膨胀、吃“皇粮”人员剧增的最初的直接的动因。由征收税外费而引发的机关增加人员,是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这一体制安排的内在含义。第二,制度外资金转化为职工个人收入,从而吸引各方的从业者,推动了机构膨胀。由于各部门对制度外资金拥有自收自支的权力,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收入转为本单位职工的福利收入,所以这些部门福利好,收入较高。各方的从业者,必然为之所吸引。首先是本部门的某些掌握权力者设法将自己的子女亲属调进来;其次扩而大之本部门干部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照顾进来;再次就是“有门路”的各方人士也千方百计挤进来。于是就形成我国就业流向中的部门“家族化”“裙带化”的特有景观。第三,这些拥有制度外资金的部门有能力支付这些新增人员的工资,是“巩固”机构膨胀的关键因素。新增人员即使超编,但由于他们各有来头,这些部门仍以各种方式变通,如以工代干、借调干部、编外干部和等待指标调入等,让他们可以留下来。即使正式的财政拨款中没有他们的工资,这些部门也可以运用本部门收费中可自由支配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一俟上级对人员编制略有松动,这些人员摇身一变就成为本部门的正式工作人员。第四,制度外资金的收支特点,造成各个机构中人员能进不能出的特有机制。制度外资金开支的非规范性,对社会公众而言缺乏透明度,缺乏外在的制约监督。以严格的财经纪律来衡量,制度外资金开支违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违规现象,小则滥发奖金、公款旅游、狂吃海喝;重者公然化公为私、鲸吞巨款。而这些违规现象也常被本部门、本单位的少数人所知甚详,因为部门就业“家族化”“裙带化”的因素,这些“绝密”的信息经几番转辗传递,其他人也可以略知一二。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本部门、本单位职工可以从这些违规开支中,不同程度地获得好处,所以人人也能心照不宣,相安无事。一旦精简机构的文件下达,减裁冗员的计划还在机关首脑的案头时,有被减裁危险的人便四处活动,进而亮出“杀手锏”,扬言道:如果某人请我出这机关,我只要将本人所知全部抖出来,就可以让某人去蹲大狱。“精明”的单位领导,往往不会冒此风险。于是精简机构的文件照样宣读,但每每总是“光打雷不下雨”,难以动真格,机构仍沿旧轨道继续膨胀。
这4种因素,互为作用,相为表里,反复循环, 成为推动机构膨胀的内在力量。
机构消肿和消灭制度外资金:孰为先?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机构的设立,原本是为社会公众办事,说得堂皇一些,即为人民服务。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拥有税外收费权的部门中,一部分人的工作性质已出现异化。他们本质上不是为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能为社会公众服务,而是为本单位的小团体“谋福利”。我们在探讨机构膨胀过程中,如果仅围绕着——机关没事找事,有事增人,人增事繁,事繁增人——这样的怪圈来分析,就事论事,实际上是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尚未涉及其本质性的东西,因而也不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运用社会学的整体观原理透视这一社会问题,我们就不难看出,机构膨胀现象及多年来种种“消肿”的改革措施之所以收效甚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制度外资金作为其内在的原动力。没有制度外资金支撑,膨胀的机构一年也难以生存下去。这一结论,不仅完全符合于我国近年来机构膨胀的演化实际,完全吻合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因此,我们在进行机构“消肿”时,就不能仅在机构及其人员构成上做文章,而应结合消灭制度外资金来进行机构改革。我们认为改革思路应该是:首先要大刀阔斧地清理制度外资金,将大部分并入税收管理范围,小部分纳入规范化的规费管理,最终将政府收入全部纳入财政收入管理。这是从“原动力”上着手,对机构膨胀来个“釜底抽薪”,无疑比其他小打小闹、修修补补的改革有效得多。与此同时,严格核定党政机关和有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对于定编人员的工薪及所需经费,必须全部由财政按核定的标准予以及时拨款。当财政拨款不能满足其需要时,也只能学习国际上通用的做法,通过发行国债压缩开支和裁减冗员等办法来解决。决不能重蹈“不给拨款给政策”、“给收费权”等旧辙。唯有如此,机构“消肿”才有实现的希望。WW南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