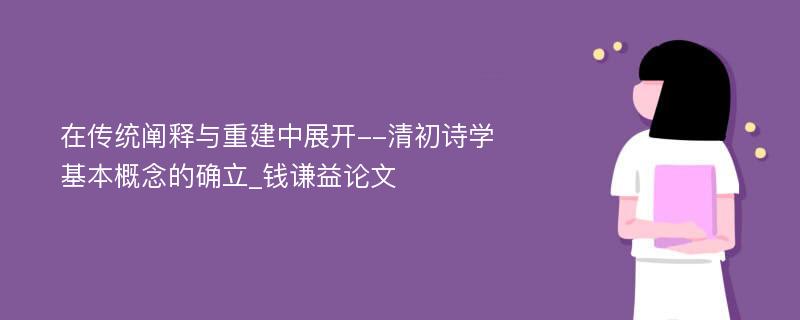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清初论文,重构论文,观念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诗学是在清算明代诗学流弊的同时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中确立自己的诗歌观念和诗歌理论的,在这一过程中,对诗歌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问题的核心。清初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风和学术的败坏,意味着明代无论在知还是行上首先是一个传统失坠的时代,为此清初文化救亡和建设的主要目标就被确定为修复和重整传统。
文化中的传统修复和重整,目标是单一而明确的,即张溥所揭应社的宗旨——“志于尊经复古”①,回归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以济世致用为基本宗旨的儒学传统。其核心是首先回到经学,以经学充实理学的知识基础,以实证性的考据方法重建经学和实学的方法论。而文学中的传统修复和重整,却要复杂得多,面临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就整个清初诗坛来看,对待诗歌传统的立场和态度是多样的,除了唐诗派和宋诗派,还有像裘琏那样否定唐诗而直溯《诗经》的,也有金圣叹那样“愿天下学古者,断以秦汉为法”的②,只不过流传范围不同,影响有大小而已。重要的派别和学说都需有待专门讨论,本文只就当时诗坛的几个热门话题略作分析。这些话题集中了诗歌观念和传统重整中最关键的问题。历来的研究虽也个别涉及这些问题,但缺乏通盘的考察,尤其是缺乏对其间内在关联的综合分析,以致不能对清初诗歌观念的建构形成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一、重倡诗教: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
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诗人来说,他们经历或记忆中的诗歌史就是一段诗歌走向堕落的历程,以致清初的批评家不得不再次站到一个类似唐初陈子昂的位置上,发出“诗道榛芜,宋元迄明,几五百年”的慨叹③。传统的失坠和风气的颓靡是如此不堪,甚至一般文人对扭转风气已感到绝望,而只能取洁身自好的态度,最低限度地维持一个读书人的操守。孙承泽《与梁玉立》云:“吾辈读书,即不能穷极理奥,决不可事禅悦以助颓澜;吾辈作诗文,即不能力追大雅,决不可戏噍声以堕恶道。”④话是这么说,但乱世总是豪杰之士挺生间出的时代,面对思想领域里的禅风流荡,文学领域里的恶习泛滥,有识之士不仅加以深刻的反思,还进行各种有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希望找到革除积弊之道。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古为理想和价值之源的国度,复古即回归传统永远是最有力的口号,同时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成功策略。清初的学人仍只能作此选择。如果说在思想领域他们是祭起经学的大旗,以振兴儒家正统思想来抑制异端的横行,那么在文学领域,他们就是以《诗经》的雅正传统为核心,回到儒家诗学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一种重整儒家诗学传统,以树立新的诗歌观念的共同意识。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基于诗歌的现实地位与儒家诗学政教传统的失落,将明清之际诗学的总趋向概括为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及审美上性情诗学、格调诗学的走向综合与统一⑤,最有见地,可以说抓准了问题的核心。不过“政教精神”这一概念,似还可以再作推敲。正像他自己指出的,诗歌的政教传统丧失已久,绝非在明代才失落;同时他将现实生活中诗歌地位的低落归结于科举的影响,又属于明清两代共同存在的文学生态问题⑥,不是诗歌自身可以解决的。由此谛审,政教精神失落与复兴的命题同清初诗学语境的关系显得稍为迂远,不如表述为诗学传统的失落和复归更能紧扣问题的实质。
当然,传统本身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就诗学而言,起码包括伦理的、审美的、知识的三个层面。对清初诗家来说,找回失落的传统,首先是要解决诗歌的伦理基础问题。为此他们重拾儒家传统诗论的种种言说,举凡“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修辞立其诚”、“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最古老的儒家诗学话语,都被他们作为诗学的核心命题,反复加以引据和论证,予以切合当下语境的阐说和发挥。当时,无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诗家,无论是正统文人,还是叛逆型文人,尽管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或师法策略各不相同,但在重建诗歌的伦理基础一点上却目标一致。连最有叛逆色彩的金圣叹,也强调“夫诗之为言诎也,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无邪,此则郑、卫不能全删,为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于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权,而使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言之所之亦必于无邪”⑦,则他人可想而知。清代诗歌的最初检阅——魏裔介编《清诗溯洄集》严沆序有云:“先生之论诗,一准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言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国风之不淫,小雅之不怨者乃始登之。”⑧两人在有限的文字中都堆砌了若干个儒家诗学的基本命题,而且都集中于伦理方面,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迫切态度。这正是现实的焦虑在诗学言说上的反映。
在伦理上对诗学传统的复归,首先表现为对已成为诗学根本概念的“性情”的重新解释。针对晚明以来,“性灵”逐渐取代“性情”成为诗学的核心概念,“性情”概念往往被解作“情”的偏义复词,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将“性情”离析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在肯定个人情感的同时,重申了道德情感的永恒性。这样,“主性情”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主张自我表现的命题,或重复“诗言志”的老调,而是通过“反其本”与传统诗歌理想联系起来,不只强调说什么,还要强调怎么说。为此,几乎已被忘却的“诗教”又被请回来,供奉于当前诗学的神龛。以“反本”为其诗学出发点的钱谦益,曾说:“诗人之志在救世,归本于温柔敦厚。”⑨朱彝尊则说,“凡可受诗人之目者,类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⑩诗人的天职,诗人的本质,忽然都与“诗教”联系起来,“诗教”一时成了清初诗学的焦点,成为当时最活跃的诗学话语之一。这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这一“诗教”虽被当代学者视为古代“论诗的最高圭臬”(11),但到清初却似已濒于灭绝,王夫之甚至认为它自唐代即已亡失(12)。这样,清初诗家重提“诗教”,客观上就形成一股诗学传统复兴的思潮。历史上的诗教,大体是从“主文而谲谏”的角度,作为艺术创作动机和艺术表现的规范而被接受的,即存心敦厚,措辞温柔,以婉曲含蓄、优游不迫为尚。毛先舒《诗辩坻》对诗教的阐释正因袭了这种传统观念,表面上看都是老生常谈,但背后却有着发掘和复兴诗教的动机。失落已久的古老诗教重新回到当代的诗学言说中,在名公巨卿的有关言论中呈现为诗学传统的复兴和发扬(13)。与此同时,不知是“诗教”二字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还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诗歌语境,人们有了新的理论要求,“诗教”不光是频繁地现身于清初诗论,还被加以多样的引申和发挥。
首先,“诗教”概念的外延得到扩展,在某些场合基本被视为诗道或诗歌传统的同义词。如胡世安《张坦公燕笺余引》云:“士无不能文而文心驳,亦无不能诗而诗教衰。”(14)钱澄之《白鹿山房诗集序》云:“吾乡诗素以才调胜,近得有怀诸子从事苦吟,绝去缘饰,独任本色,要皆情为之也。诗教其将兴乎。”(15)两人的说法虽褒贬不一,但扩展了“诗教”的外延,用以代指诗道,却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新的用法,意味着诗教作为概念,地位已经提升(16)。人们热衷于对诗教作种种申说,或与此有关。到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集》时,“温柔敦厚”四字已成为笼罩全书的唯一标准。
其次,与外延扩大相应的是“诗教”的内涵也不断被充实,虽然人们都在谈论同一个命题,但各自的解说和发挥却很不相同。除了张健指出的遗民诗群从贵“变”的角度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外(17),我们还发现,“温柔敦厚”四个字在众多诗论家的笔下,已呈现多方面的意蕴。黄宗羲《栗亭诗集序》首先从待人接物的厚道上来解释温柔敦厚(18),魏际瑞也从自我表达的角度肯定:“温柔敦厚可以嬉笑怒骂,得性情之正即可。”(19)这都属于将传统命题的内涵由辞令风格切换到性情上来,由表及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王弘撰《蒋处士诗序》,将《诗序》论创作冲动与道德规范的关系转换为写作动机的两种诉求,赋予《诗序》以新的涵义。让我们一方面看到经过明代性灵诗学的冲击后儒家正统诗歌观念的松动,一方面更看到当时扩展“诗教”的内涵,以重建诗歌伦理基础的努力(20)。
真正拓展诗教的内涵,将它提升为一个最具包容性的理论命题的是钱谦益。钱谦益晚年论诗文字中反复提到“诗教”,并作了多向度的引申。除了孙立指出的与元气联系起来外(21),最值得注意的是与性情、真诗等重要观念相沟通,暗示了这些观念内在的一致性及被整合的可能。陈玉瑾序曾灿所辑当代诗选《过日集》,也谈到诗教:
古人视经重,故视诗弥重。夫诗之所以为经者何哉?古人立言,皆思有益于天下后世,大而君父之大伦,细至昆虫草木,莫不旁引曲譬,使人观感有悟,足以为戒,足以师。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22)
很显然,这里是依托于《诗经》的经典性,将自己对诗歌社会价值的所有理解都灌注进传统的诗教命题中,包括与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相类似的观念。由此可见,这些诗论家虽所处地域不同,所承传统不一,所持话语各异,但其理论目标和精神实质却都是相通的。共同的理论意识使原本指向各异的传统诗学话语在“诗教”的范畴下得到整合,也使古老的“诗教”成为全面统摄当代诗学理想的重要范畴。而他们对诗教的种种阐释和开拓,更使诗歌观念日益趋向于丰富和多元化。
如果说清代诗学区别于前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观念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那么清初诗学即已显露这种倾向。前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给了诗人们多样的选择可能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只因处于反思明亡教训的历史语境,致使所有的选择和阐释都表现为对明代诗学的反拨和救赎。重倡诗教只能拯济性灵派末流的道德沉沦,决不足以肃清明代诗学的全部流弊。不立不破,不确立新的艺术理想,就无法破除明代诗学的痼疾。从根本上说,艺术理想的确立本身就是对明代诗学的反拨,矛头直接指向明人对传统的狭隘观念,并激发人们重新认识传统的意向。
二、重整诗统:拓展诗史视野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诗歌传统都一直在诗史上起着导向和楷模的作用,充当审美理想的旗帜。重倡诗教只是为诗歌创作奠定了伦理基础,它对诗歌创作的规范作用既很狭窄,也很抽象。诗论家们要全面阐明自己的艺术观念,表明自己在风格学或修辞学上的理想,还需要确立具体可感的艺术典范。这一典范不可能凭空雕塑出来,只能到过去的诗歌史中去寻找。一个对艺术理想的现实需求,最终演化为对诗歌传统的重新梳理和整合。
清初诗学的所有工作都从对明代的反思开始,在传统问题上也不例外。赵执信《谈龙录》在回顾历代对诗歌传统的态度时指出:
青莲推阮公、二谢,少陵亲陈王,称陶、谢、庾、鲍、阴、何,不薄杨、王、卢、骆,彼岂有门户声气之见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于前辈有过情之论,未若明人之动欲扫弃一切也。今则直汩没于俗情积习中,非有是非矣。后人复畏后人,将于何底乎?(23)
这里称赞唐人无门户声气之见,当然是针对明人的好立门户而言的;而当今俗情积习的无是非可言,又是承明人的流弊,总之归结于明人论诗的狭隘。此刻人们已看得很清楚,正是狭隘的艺术观念,导致明人论诗取径偏窄。在七子辈“诗必盛唐”的旗帜下,举世所讽习,不过开、宝几十年的诗篇,此前此后的诗歌全都排除在视野之外。万历后虽门户递起,各持一说,但是丹非素,所见益隘。诚如张缙彦所批评的,“今说诗者,每祖祢王李,既则訾之。旋效袁徐,渐为钟谭,后则又訾之。一以为正派,一以为新裁,如童子争日,不复相下。是以眼孔日窄……故诗道最广也,作者狭之,选者又狭之”(24)。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创作中的单调与雷同局面。要改变诗坛这整体贫血的状态,首先必须打破“诗必盛唐”以及其它的种种牢笼,将广阔的传统资源吸纳到自己的创作中来。
清初大量的诗文都告诉我们,破除明人对诗史的狭隘观念,将更广大的诗歌传统纳入自己的视野,乃是当时大多数诗家的共同意识。许多诗人都在有意识地作这种努力,差别只在于具体的取径路向以及论者处于什么位置、产生多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将不同时间、地域的诗人们的主张一一列举出来,但透过当时的文献记载,一个在激荡中扬弃,在沉思中建设的诗史时期还是约略可见其脉络。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时间最早同时影响也最深远的钱谦益鼓吹宋元诗。宋元诗自明初以来被束之高阁,直到公安派才突破格调派藩篱,稍加拂拭。在公安派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钱谦益,更因受程孟阳感染,推崇南宋、元诗,尤其是陆游诗。袁宏道还承认初、盛、中、晚各有其诗(25),钱谦益干脆釜底抽薪,用否定初盛中晚的分期彻底颠覆了格调派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天启、崇祯之际率先鼓荡起追慕宋元诗的风气。后辈谈到钱谦益的诗史贡献,都认为“虞山钱牧斋先生乃始排时代升降之论而悉去之,其指示学者,以少陵、香山、眉山、剑南、道园诸家为标准,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26)。显然,他对宋元诗的推崇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诗史视野。
但钱谦益鼓吹宋元诗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更没有波及所有的地域,就连江南一带也没都被宋诗风笼罩,如“云间几社及武林登楼诸子尚持时代升降之论,其徒相戒慎勿为开、宝以下人物”(27)。根据当时的文献,竟陵派和后七子派在清初都有复燃之势,在不同的地域各拥有一批追随者(28),而反竟陵者往往重归王、李旧垒,如徐增所说的,“近日学诗者,皆知竟陵为罪人之首,欲改弦易辙者,又不深谙唐贤之门庭堂室,复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乌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尘腐之冠裳,鲜不笑其败落者矣”(29)。云间派正是徐增说的唐人贤子孙,他们针对竟陵派的流弊,曾试图重振唐诗的理想,甚至重新整合古代诗歌的传统,但终因缺乏新颖而明确的艺术目标,仍不得不复蹈王、李故辙。其乡里后辈固然极肯定他们重振诗歌传统的功绩,然而他人未必这么看,未必承认其整顿诗学的功绩。
实际上在清初诗坛,大家都在突破“诗必盛唐”的藩篱,眺望广阔的诗歌传统。程孟阳、钱谦益是属于向后看的,更多的人则是向前看。明清之交的著名文学家薛所蕴,在《曹锡余诗序》中说:
今海内士大夫鼓吹休明,振起风雅,沨沨乎欲比隆唐人,而树帜登坛、执此道牛耳者,咸首推相国刘宪石先生。宪石与余共切劘者二十余年,论诗必先格调,通之性情,期于近法李唐,以远追《三百篇》遗音,务使言有尽而意无穷,斯非苟作者。常操是法以相海内人之诗,合焉者之谓正派,离焉者之谓时派。(30)
刘宪石名正宗,明末官至宰相,入清后在京师为龚鼎孳、吴伟业之外一巨擘(31)。他论诗主格调而兼重性情,应渊源于乡先辈李攀龙的格调派,至于论诗追溯到《三百篇》,则属于明清之交诗坛最一般的观念。周灿《刘介庵诗序》曾说:“今之为诗者,哓哓于李王钟谭之席,苦争胜负,独不思三唐而上有汉魏,汉魏而上有《三百篇》鼻祖之可寻乎?”(32)寻根寻到始祖即无余义可辩,遂流于一般而显不出特色。职是之故,刘正宗虽号称执诗坛牛耳,但当时诗学文献中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就像关中诗学的代表人物李因笃,同样主张学诗必本乎三百篇,“学三百而得苏李,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33),在诗坛也没什么影响。陈玉璂以古文家主张学《三百篇》,就更不用提了。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矫激立异者为世瞩目;平正通达的主张,则英雄所见略同,如康庄大道,人往来践行而不以为意,不以为奇。更何况学《三百篇》终究是个太学究气的主张,说说容易,真正付诸实践又如何措手?
云间派或刘正宗的实际成就及影响如何,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主张说明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唐诗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孙廷铨解释诗必学唐的理由说:“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善为诗者必不伧。”(34)既然确立了这一前提,唐诗就成为古代诗歌传统的不祧之宗,任何对诗歌史的重新解释都不能以否定、取代唐诗为前提和目的。这使清初所有对诗歌传统或艺术楷模的重构最终都成为一种出于策略的选择,而不是真正的趣味变异。钱谦益论诗以杜甫、韩愈、苏轼、陆游和元好问为宗,但指点方文,却说“近代思变杜者,以单薄肤浅为中唐,五言律中两联不对谓之近古,此求变而转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钱考功皆与杜老争胜毫芒,晚唐则陆鲁望、皮袭美,金元则元裕之,风指秾厚,皆能横截众流。足下论诗以杜、白为第宅,亦不妨以诸家为苑囿也”(35)。而他的弟子冯班也未传其衣钵,却由晚唐上溯汉魏六朝。这不都是出于师法策略吗?
按照格调派的观念,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像钱谦益、冯班这般取法乎中,岂非仅能得其下了吗?没办法,师法策略的选择基于诗人的才能及其自信程度,也受到师法对象本身提供的艺术资源的限制。盛唐诗毕竟被模仿得太多,可供开掘的艺术资源已很有限,而晚唐诗只在宋初和南宋末年一度风行,几百年过去已变得陌生,正好取作楷模。比晚唐更陌生的还有六朝,自中唐以后便鲜有人道及,因此也为一部分诗家所取资。康熙四年(1665)李因笃跋曹溶诗云:“天下无言《文选》者,诗日趋于敝,而五言为甚。近日始知羞称竟陵,更溯正始,然吾尝见其诗,考其原委,所为正始自大历已耳。无论风雅为几筵,汉魏为俎豆,即开府、参军,李杜常亟引之,而近人一涉六朝辄去之,若将凂焉。竭其生平之智力,区区从盛唐诸公庑下周旋,岂真以庾、谢风流反出其下邪?”他称曹溶“意取其厚,辞取其自然,所以复汉京也;调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选》体也。而雄浑悲壮,驰骤两唐者,反在所略”(36)。这是当时又一种师法路径,只因是个别人的实践,几乎是悄无声息的,不曾在诗坛引起反响。
无论宋元也好,晚唐也好,汉魏六朝也好,都意味着视野的扩大、传统的充盈。在这云谲波诡的激荡中,唯一不曾动摇的偶像是杜甫,只有杜甫保持了自宋代以来的典范地位。诗坛以杜甫为宗的普遍选择,曾引发清初杜诗学的兴盛。上至钱谦益、陈廷敬一辈诗坛巨子,贾开宗、仇兆鳌一流著名文士,下至朱鹤龄、黄生之类的乡曲老儒,众多的注家和注本对杜诗作了划时代的全面研究,一方面贯注了“诗史”意识,一方面融会了实证学风,使杜诗研究顿开生面。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多种专著(37),这里无须赘述。我想说明的是,在清初诗家的眼中,杜甫已不仅仅是一个供模仿和学习的偶像,像“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文统中一样,他成了诗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如贾开宗序侯朝宗诗云:“孔氏亡而诗亡,千余载而唐始有杜甫,甫亡七百年而明有李梦阳、何景明,何、李亡又百余年而有侯子。”这当然是格调派私修的诗统谱系,省略了太多的诗史细节,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同是不太可能的。果然,任源祥《与侯朝宗论诗书》针对贾开宗太过省略的诗统谱系,通过补充许多诗史细节,列举“自汉、魏以来,苏、李、曹、王、左、鲍、陶、谢之俦,皆杜甫所寤寐而羹墙之者”(38),再现了杜甫的集大成性和对前代诗歌的继承,这就使接受和学习杜甫成了附载杜甫以前整个诗歌传统的过程。到康熙中叶,集古今注杜大成的《仇注杜诗》行世,更清楚地展示了伟大诗人背后的诗歌传统,使人们的诗史视野愈加广阔,对诗歌传统的理解也愈益充实。
从现有文献来看,类似为诗歌传统“扩容”的工作,到康熙二十年前后基本已完成,其标志就是王士稹再度倡导宋元诗。门人汪懋麟说:“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梁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39)这说明王渔洋之提倡宋元诗,同样是出于拓展诗歌传统的视野和追求多样化的动机。尽管不数年间,宋元诗风就蒙受“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的批评(40),令王渔洋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改弦易辙,但“以扩曲士之见闻”(41),即揭示古典诗歌传统的丰富性,改变人们由盛唐诗获得的单一印象的目的却达到了。这场重新认识传统的论争还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那就是叶燮《原诗》对诗史的认识方法:“吾愿学诗者,必从先型以察其源流,识其升降。”(42)建立在这种态度上的诗史观是开放的、富有包容性的,它使每个诗人与以往的全部诗歌史联系起来。正像后来黄承吉说的,“士生今日,必穷乎源流正变,而后诗学乃全”(43),因此它也是有历史感的。这成为清人自觉区别于前人并引以为自豪的一种主体意识。
三、崇尚真诗:明确创作理念
周亮工《西江游草序》说:“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44)随着明代诗歌的核心理念——“以剿袭为复古”(45)在众多诗家的一片指斥声中灰溜溜地谢幕,格调和性情这两大诗学范畴发生了位移,从云间派到虞山派,诗学完成了从格调优先到性情优先的转变(46),性情中心观被重新树立起来。不过,性情和格调一样,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加以限定便留有理论缺陷。就像曾灿所说的,“诗以道性情,若性情失其真,即典雅骈丽,不过为优孟衣冠而已”(47)。这也正是明诗所有失误的根源,最终成为清初诗论家思考诗歌本质的逻辑起点。虽然经过改造的“诗教”奠定了诗学的伦理基础,被扩容的诗歌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师法范围、更多样的艺术楷模,但诗学仍需要一个响亮而有号召力的口号,来凝聚人们已然散落的信念。
正是在这一诗史语境下,“真诗”应运而出,成为回旋在当时的诗学言说中、统摄一切诗歌观念的最强音。只要是读过一些清初诗文的人,相信都会对当时人之执著于“真诗”留下深刻印象。这里姑举几条资料,以见不同社会阶层的诗人对真诗的推崇。
文坛盟主钱谦益:“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48)
名士余怀,“嗟乎,诗至今日,尚忍言哉?即不敢谓天下无诗,谓其无真诗也。”(49)
遗民诗人杜濬:“古今真诗皆露积于天地之间,无有遮蔽,不设典守也。然惟眼明者能见之,手敏者能举之,则其诗成而天姿弗饰,虽饰无以复加,以至于锤炼妥帖,只字莫易,无美不臻,而绝非人力所设施。诗至此至矣。”(50)
江南才子徐增:“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能于此等处会意,则《三百篇》可学,何况唐人也。”(51)
新朝达官李振裕:“夫诗所以贵真者,何也?曰:情也。诗以道性情,夫子称《关雎》以哀乐二端尽之,盖诗之真者能以其情移人之情。”(52)
封疆大吏宋荦:“自有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模唐,不必模古,亦不必模宋、元、明,而吾之真诗触境流出。”(53)
这些议论从批评明诗之失真,推原古代真诗的传统,到标举真诗的特征,说明如何创作真诗,包括了有关真诗的所有理论问题,暗示了诗人们对“真诗”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暗示了这是一个包含理论解释的一切可能性的时代命题。
“真”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本原,可以说是古今诗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有明一代诗歌观念的核心理念,自刘基、高启以降,直到归有光乃至王世贞,都认为真情是诗歌的生命。既然有这样的渊源,“真诗”理应成为诗坛的共同主张,为何到清初还说“真诗不见于世久矣?”(54)关键在于,明人虽然在观念上倡导“真诗”,但创作中实际并未处理好真与善、真与本色、真与风格等一系列关系,所以也就未创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真诗”,拟古而伪仍是人们对明代诗歌最一般的印象。在这种诗史语境下,“真诗”就成了清初反思明代诗学的逻辑起点。
因为“真诗”是清初诗坛最醒目的话题之一,很早就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近年的研究也有所阐发(55),这里我要根据自己接触的资料,对它作为当时诗学核心观念的意义作些补充性的论述。首先,我注意到“真诗”经常是反思明代诗学的起点。程可则《与施愚山论诗作》云:“晚近事鞶帨,无乃失其真。”(56)顾图河《与吕山浏论诗兼寄金介山》云:“真诗苦不多,众瓦一圭玦。”又云:“奈何百口吻,而但插一舌。”(57)这都是当时流行的说法。薛所蕴《刘蓼生诗序》细绎此意云:
古人学问醇备,故人品为真人品,事功为真事功,文章为真文章,即徵为声歌,发乎情。止乎则,范我驱驰,不失尺寸,绝无诡遇倖名之意,故心声于诗,而诗亦为真诗。后人学问浅驳,无论人品事业卑下不足观,即诗文一道,多假窃袭取而不知作者之意何居,乃至今日而更不可问矣。(58)
“真诗”在此成为划分古今诗歌的基准,古=真,今=伪,对当下文学的批评成了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凡“今”必与伪相联系,而“真”则成为救赎的金丹。正如关中理学家兼诗论家康乃心所说:“夫自十五国内外,人人言诗,亦人人为诗,而诗之存焉者寡,何也?曰伪也。有伪忠伪孝伪友伪廉伪仁让伪理学,即皆有伪诗。”“今之谬种流传者二,一在制举义,一在诗。制举义之谬,天下无学问;诗之谬,天下皆市谭。返本穷源,救之之法,不过一真而已矣。”(59)如果进一步反思,古之真何以沦为今之伪的呢?则仍不外是源于前文论及的明代应酬习气:
盖自王者采风而有《三百篇》,率多忠臣孝子、征夫思妇之什,皆能自道其性情而无所勉强。六朝三唐而下,渐失其真,应制有诗,登眺有诗,以及宴会赠答莫不有诗,人擅其名,家各有集。至于今日,举生平未识面之人,亦必以诗贻赠;卿士大夫寿言挽章,不论其人之能诗与否,必欲乞为诗歌。呜呼,不喜而笑,不悲而啼,而欲求为真诗,难矣。(60)
不必赠而赠,不必求而求,被赠者被求者均非其人,不喜而笑,不悲而啼,从写作到接受没有一个环节是真实的情感传递,诗要想不假都不可能。归根结柢就是诗中无人,无真性情,无真面目。而救赎之道,不外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诗中有人,有真性情和真面目。
我们知道,“诗中有人”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诗学主张,为吴乔、赵执信等人所标举。诗中有人的“人”就是作者的性情和特点,用当时流行的词叫“真面目”。朱釴论周铭诗云:“人生有真面目。自优孟之学叔敖而不真,自嫫母之傅脂粉而不真,浸假为净丑之涂抹、面具之神鬼,而竟疑假为真矣。诗亦然,以魏晋唐之字眼腔调为诗,而诗无真矣。今世具真面目不可以行世,则焉得有真诗可以传世?吴江勒山先生者,有真面目而更有真诗者也。”(61)他的“真面目”,最后落实到风格学意义的“字眼腔调”上,明显是针对格调派的模拟作风而言。尤侗则说:“诗无古今,惟其真尔。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62)他着眼的已不单单是风格,而是要表现真性情,从真性情出发创造本色的格律风调,形成自己的时代特点和个人特点。这不仅涉及字眼腔调的风格真实,更涉及性情表达的意义真实,即杜濬《与范仲闇》说的“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63)。篇无格套语是杜绝表面的风格模拟,而切人情则是要求表情达意的自然本色,这是清初诗家对明诗的一个更深刻的针砭。正像魏象枢所指出的:
古人之诗出于性情,故所居之地、所处之时、所与之人、所行之事、所历之境、所见之物,至今一展卷了然者,真诗也。若今人之诗,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颇多。即如极富而言贫,极壮而言老,极醒而言醉,极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发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饰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学者宜以真诗为法哉!(64)
这里指出的诗之失真,不只包括顾炎武所斥责的“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汙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的贰臣诗人(65),也包括为文造情、失其本色的矫情之作。所以他所持的“真诗”观念,实际上是要求诗歌作者、作品和世界所有层次的关系都是真实的。就诗所表达的内容而言,与其说是切人情,还不如说是切合身份。后人将这种由作者身份带来的规定性也视为文体学的一个部门(66),不能不说是清初对“真诗”加以深思而派生的理论成果。
魏象枢康熙间官至宰相,又以文学著称,“以真诗为法”相信代表了诗坛的共同主张。事实上,从钱谦益起,就将“真”作为诗歌的生命力来标举,真也成为诗歌最基本的价值前提,如申涵光《乔文衣诗引》所谓“诗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后可言美恶”(67);同时它也是诗歌的最高境界,甚至超过“佳诗”。杜濬《与范仲闇》有一段很不同寻常的议论:
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弟以为此佳诗,非真诗也。何也?人与物犹为二物故也。古来佳诗不少,然其人不可定于诗中。即诗至少陵,诗中之人亦仅有六七分可以想见;独陶渊明片语脱口便如自写小像,其人之岂弟风流,闲情旷远,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今真诗一人而已,可多得乎?(68)
按杜濬的理解,真诗乃是比佳诗更高的境界,属于彻底无碍的自我表现,故也可以说是人诗合一的境界。即便是大诗人杜甫,也只能到佳诗而已,古今能企及真诗境界的,惟有陶渊明一人。此言虽过于玄妙,但核心仍不外乎“诗中有人”四字。钱谦益《刘咸仲雪庵初稿序》说“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诗文”(69),尤珍《真意斋记》说“以其真意发而为诗,则诗为真诗”(70),曹可久说“吾为文止一字而已,曰我”(71),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论调,只不过不像他说得那么绝对。过于绝对地强调“真诗”,就像一味强调诗中有我,实际上存在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即它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真面目=好面目=好诗=真诗。问题是,表现了真面目的诗就一定美好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真面目一定就是美好的吗?“真面目”要想与美与好诗划等号,就必然要求伦理学或美学上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又在哪里呢?杜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奚苏岭诗序》里又指出:“夫诗至于真难矣。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疏游戏为真,而诗道遂亡。真岂如是之谓耶?夫真者必归于正,故曰正风正雅,又曰变而不失其正。诗至今日,不能不变,要在不失其正而已。”(72)引出“正”来作为真的价值依据,等于是赋予真以伦理学、美学的限定,这与顾炎武针对士大夫群体气节和道德的普遍沦丧,以“知耻”为“真诗”的伦理底线,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正”因其所附带的经学语义,无形中在“真诗”与诗教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这对于日益成为诗歌核心观念的“真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四、原本学问: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
清人对明诗的所有不满,可以归结为两点,那就是模仿带来的虚假,不学招致的空疏。钱谦益《王贻上诗序》有云:“诗道沦胥,浮伪并作,其大端有二:学古而赝者,影掠沧溟、弇山之剩语,尺寸比拟,此屈步之虫,寻条失枝者也;师心而妄者,惩创《品汇》、《诗归》之流弊,眩运掉举,此牛羊之眼,但见方隅者也。”(73)此序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多年过去,导源于格调派和性灵派的两种流弊依然泛滥。周灿《王茂衍轺香二集序》说:“每见近日诗人二病,恣肆者自谓独抒性灵,而同于野战;蹈袭者妄言规模先民,而貌若登场。”(74)所谓野战,就是刘克庄批评当时晚唐体说的“捐书以为诗,失之野”(75),意指空疏不学。相对来说,七子辈的“假盛唐”到清初已被鞭挞得体无完肤,但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灵诗学却应和着当时旺盛的自我表现欲求,渗透到遗民群体的诗歌创作中,形成流行一时的激切浅率之风。这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在反思、批判明代空疏学风的思潮中加入了对诗学的批判,使诗与学的关系成为清初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明代学风之肤廓而空疏,本朝焦竑已有“束书不观,游谈无根”(76)之叹。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论明代学风的堕落,说“一坏于洪武十七年定制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77)。阳明心学坐谈心性对明代学风的影响,论者已夥;科举以八股取士对整个文学生态的影响,我也有专文论述(78),这里只就李梦阳的提倡复古略作论说。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要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李梦阳引而申之,教人不读唐以后书。信奉其说者高谈汉魏,画地为牢,虽号为崇古,而终不免于鄙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曾指出“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他人就更桧以下无讥了。钱谦益说“末学之失,其病有二:一则蔽于俗学,一则误于自是”(79),缪荃孙说李梦阳之学失之俗,正本此而言。万历以后,风气稍变,如果说前此是蔽于俗学,那么此后就不免误于自是了。公安、竟陵都以反七子辈拟古之风的面目出现,但公安派以李贽“童心”说为理论根据,李贽说“学者既以多读书识礼义,障其童心”(80),袁宏道便推及诗学,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81)。而竟陵派针对拟古的虚矫,提倡“真诗”,其实质显然“也是一种妙悟说,而把它更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82)。因此,无论是明代的学风,还是明代诗学的主流意识,都不足以促使诗歌创作扎根于深厚的学问土壤中。到清初学人痛定思痛,反省亡国的教训时,便毫不客气地将账都算到明人的不学无术上,诗论中也充斥着对明诗空疏不学的抨击。
清初重要的诗论家几乎都对明人的空疏提出过批评,像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黄宗羲《破邪论》、《留别海昌同学序》、《范用宾诗序》、朱彝尊《胡永叔诗序》等。当时士大夫间研求学术的风气虽已形成,但诗学中似乎还没有确立起崇尚学问的观念,只有一部分兼为学者的诗人提倡诗歌创作必须原本学问,并进而提出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的区别。钱谦益《顾麟士诗集序》以“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对举,黄宗羲《后苇碧轩诗序》以“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对举,都是同样的意思。钱谦益在《定山堂诗序》中又将性情和学问对举:
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执性情而弃学问,采风谣而遗著作,舆讴巷謣,皆被管弦;《挂枝》、《打枣》,咸播郊庙,胥天下用妄失学,为有目无睹之徒者,必此言也。(83)
在这一点上,朱彝尊是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平日教训儿子辈即说:“凡学诗文,须根本经史,方能深入古人窍奥,未有空疏浅陋、剿袭陈言而可以称作者。”(84)他自己虽“能兼经学词章之长”(85),也自称“六经诸史百氏之说,惟诗材是资”(86)。另一位博学家方以智在《通雅·诗说》中则强调:“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吞吐始妙。”他的同里学人兼挚友钱澄之撰《文灯岩诗集序》,虽首先肯定“诗之为道,本诸性情,非学问之事也”,但接着又强调:
然非博学深思,穷理达变者,不可以语诗。当其意之所至,而蓄积不富,则词不足以给意;见解未彻,则语不能以入情。学诗者既已贯通经史,穷极天人之故,而于二氏百家之书无有不窥,其理无有不研,然后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为言。于斯时,不必饰词也,而词无有不给;不必缘情也,而情无有不达。是故博学穷理之事,乃所以辅吾之性情,而裕诗之源者也。(87)
还有一些诗家,虽不以学术著称,也提倡多读书。如李沂《秋星阁诗话》专立“勉读书”一条,立意近于方以智,欲学者博学养识力,“识见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诗之神理乃日益出,诗之精彩乃日益焕”。杜濬《交勉篇应蒋子》也说:“不读书,则不但率易无诗,即苦思力索亦无诗也。”方文《次韵题吴不官诗卷》则发挥前人以禅喻诗之说:“圆通由妙悟,积累在多年。岂许空疏辈,能耕卤莽田。”(88)钱仲联先生曾将清初有关为诗必须学问的主张概括为八点,最为精当:“一、学问原本六经;二、学问要致用;三、多读书则取精用宏;四、多读书增加才气;五、纠正空疏之敝;六、纠正偏重妙悟之敝;七、空灵也要从学问中来;八、多读书可以医俗。”(89)这显然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晚明以来格调、性灵两派的流弊而发。格调派流为俗学,欲惩其弊,只有济之以学问。因而邵长蘅《答贺天山》云:“诗文忌俗……然医俗无他法,惟平日多读书,则俗气自消。”而性灵派流于野战,欲救其失,也只有济之以学问。就像真面目与好诗没有必然联系,真性情也不能直接产生好诗。因此曾灿《龚琅霞诗序》说:“诗贵性情,然欲其朴至而文,则必有学问之事在焉。”(90)王尔纲《名家诗永·杂述》也说:“诗道性情,必资学问。学问所以道性情也。”(91)张希良《切庵诗钞序》更进而提出“以真性情为根柢,真学问为枝叶”的明确主张(92)。而许缵曾甚至将性情和学问两者的位置作了个颠倒,称“大雅元音,本之于学问,得之于性灵”(93)。这虽不无过激之处,但的确预示了有清一代诗歌主博综,重书卷,以经史考据为根基的主流倾向。
在清初人士的普遍意识中,明人的空疏不学是亡国的祸根。武装反抗失败后,汉文化救亡图存的希望全系于学术之一脉,一种博综的、求实的学问与人生最崇高的价值联系起来。我曾经指出,诗学在清代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即它是被当作学问来做的。无论是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史研究,还是王士稹、李因笃的诗歌声律学,都体现了这一点。诗学在走向学术化的同时,也要为诗歌安顿一个知识基础。以后二百年间的创作实践表明,清诗厚实的学问底子是在清初几十年就已打下的。
的确,清初诗歌观念的重建,不仅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清初诗学确立起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成为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清代中叶以后,无论是格调派、性灵派、肌理说还是宋诗派、同光体,莫不发挥其一脉而推广至极。二百七十年间的清诗虽波澜起伏,新变杂出,但这些核心观念却一直贯穿其中,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注释:
①张溥:《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卷2,明末刊本。
②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金圣叹全集》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40页。
③王嗣槐:《广陵韩子诗序》,《桂山堂文选》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康熙青筠阁刊本,第7辑第27册,第87页。
④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9,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⑤参看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明清之际: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参看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⑦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金圣叹全集》卷4,第34页。
⑧魏裔介:《清诗溯洄集》卷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康熙刊本。
⑨钱谦益:《施愚山诗集序》,《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年,第4册,第247页。
⑩朱彝尊:《高舍人诗序》,《曝书亭集》卷37,康熙刊本。
(11)徐复观:《释诗的温柔敦厚》,《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2)王夫之:《古诗评选》卷5江淹《效阮公诗八首》之二评语:“闻之者足悟,言之者无罪,此真诗教也。唐以后诗亡,亡此而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
(13)如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所举李光地《榕村语录》、徐乾学《十种唐诗选序》、朱彝尊《钱学士诗序》、王士禛《池北偶谈》等的言论,见《清代诗学研究》第34-35页。
(14)胡世安:《秀岩集》卷2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三十四年胡蔚先修补本,集部第196册,第614页。
(15)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16)这一点基本为后人所认同。同治间王轩序谢质卿《转蕙轩诗存》云:“志切者意必深,情至者词务尽,学古而不求形似,非深于诗教者不能也。”此“诗教”亦非温柔敦厚四字可尽。
(17)详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35-39页。
(18)见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2-383页。
(19)魏际瑞:《感兴诗序》,《魏伯子文集》卷1,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20)王弘撰《砥斋集》卷1下,康熙刊本。详蒋寅《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3年第2期)一文。
(21)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指出钱谦益晚年更多地提倡温柔敦厚之旨,与明亡后更多地接触遗民群体有关系,可备一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2-284页。
(22)陈玉璂:《过日集序》,曾灿辑《过日集》卷首,康熙间曾氏六松草堂刊本。
(23) 赵执信:《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537页。
(24)黄传祖辑《扶轮广集》张缙彦序,转引自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25)袁宏道:《与丘长孺》,《袁中郎全集》卷21,日本元禄九年京都刊本。
(26)李振裕:《善鸣集序》,《白石山房集》卷14,康熙间香雪堂刊本。
(27)李振裕:《善鸣集序》,《白石山房集》卷14。
(28)详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29)徐增:《与申勖庵比部》,《九诰堂全集》第11册,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30)薛所蕴:《澹友轩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顺治十六年刊本,集部第197册,第48-49页。
(31)韩诗《国门集初选》凡例:“近日辇下诸老,风雅翩翩,如芝麓、梅村而外,又有宪石、行坞,岩荦、犹龙诸先生,振藻扬芬,上嗣风雅,可为极盛矣。”见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第45页。
(32)周灿:《愿学堂文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9册,第319页。
(33)李因笃:《许伯子茁斋诗序》,《续刻受棋堂文集》卷1,道光十年刊本。
(34)孙廷铨:《梁苍岩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康熙刊本。
(35)钱谦益:《与方尔止》,《牧斋有学集》卷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下册,第1356页。
(36)曹溶:《静惕堂诗集》卷5,康熙刊本。
(37)有关研究有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
(38)任源祥:《鸣鹤堂文集》卷3,乾隆十一年家刊本。
(39)见《十种唐诗选》徐乾学跋,康熙刊本。
(40)施闰章:《佳山堂诗序》,《学源堂文集》卷7《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3年,第1册,第133页。
(41)顾复渊《海粟集》曹禾序,雍正八年刊本。
(42)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编《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9页。
(43)黄承吉:《梅蕴生诗序》,《梦陔堂文集》卷6,民国二十八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本。
(44)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刊本,中册,第771页。
(45)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语,《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2页。
(46)详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二章、第三章。
(47)曾灿:《复丁会公》,《六松堂文集》卷14,康熙刊本。
(48)钱谦益:《季沧苇诗序》,《牧斋有学集》卷17,中册,第759页。
(49)翁季霖:《胥毋山人诗集》余怀序,康熙刊本。
(50)杜濬:《程孚夏诗序》,《变雅堂文集》卷1,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刊本。
(51)徐增:《与同学论诗书》,樊维纲校注本《说唐诗》卷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2)李振裕:《善鸣集序》,《白石山房集》卷14,康熙间香雪堂刊本。
(53)宋荦:《漫堂说诗》,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第416页。
(54)王岱:《谢岳生诗序》,《了葊文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9册,第75页。
(55)参看入矢羲高:《真詩》,《吉川博士退休紀念中国文学論集》,築摩書房,1968年;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56页。
(56)程可则:《海日堂集》卷1,道光五年重刊本。
(57)顾图河:《雄雉斋选集》卷5,康熙刊本。
(58)薛所蕴:《澹友轩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7册,第45页。
(59)康乃心:《张采舒诗序》,《莘野文续集》卷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莘野先生遗书》。同卷《陆方山诗序》亦重申此意。
(60)曾灿:《依园七子诗序》,《六松堂文集》卷12。
(61)周铭:《华胥放言》戊集甬上诗话,太白山楼刊本。
(62)尤侗:《吴虞升诗序》,《西堂杂俎二集》卷3,康熙刊本。
(63)杜濬:《变雅堂文集》卷8,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刊本。
(64)魏象枢:《庸言》,《寒松堂集》卷12,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0-871页。
(65)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852页。
(66)如周镐《犊山类稿·鹿峰先生诗序》论馆阁体与山林体之别,即其例也。
(67)申涵光:《聪山集》卷2,康熙刊本。
(68)杜濬:《变雅堂文集》卷8。
(69)钱谦益:《初学集》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册,第910页。
(70)尤珍:《沧湄文稿》卷2,康熙刊本。
(71)裘琏:《曹可久文集叙》,《横山文集》卷2,民国三年宁波旅遁轩排印本。
(72)杜濬:《变雅堂文集》卷1,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刊本。
(7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7,中册,第765页。
(74)周灿:《愿学堂文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9册,第317页。
(75)刘克庄《韩隐君诗》批评晚唐体诗家“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6,四部丛刊本。
(76)焦竑:《笔乘》续集卷3,奥雅堂丛书本。
(77)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1,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9页。
(78)参看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79)钱谦益:《答徐巨源书》,《牧斋有学集》卷38,下册,第1313页。
(80)李贽:《童心说》,《李贽焚书》卷3,万历刊本。
(81)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袁中郎全集》卷1,明末钟惺增订本。
(82)钱仲联:《清代学风和诗风的关系》,《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84页。
(83)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首,光绪九年龚彦绪刊本。
(84)陈廷敬:《翰林院检讨朱公墓志铭》,《曝书亭集》附录,康熙刊本。
(85)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58页。
(86)朱彝尊:《高户部诗序》,《曝书亭集》卷38,康熙刊本。
(87)钱澄之:《田间文集》卷6,黄山书社,1998年,第256页。
(88)方文:《嵞山续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刊本,下册,第1126页。
(89)钱仲联:《清代学风和诗风的关系》,《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87页。
(90)曾灿:《六松堂文集》卷12,康熙刊本。
(91)王尔纲:《名家诗永》卷首,康熙间砌玉轩刊本。
(92)刘谦吉:《切庵诗钞》卷首,康熙刊本。
(93)许缵曾:《含晖堂诗序》,《宝纶堂稿》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