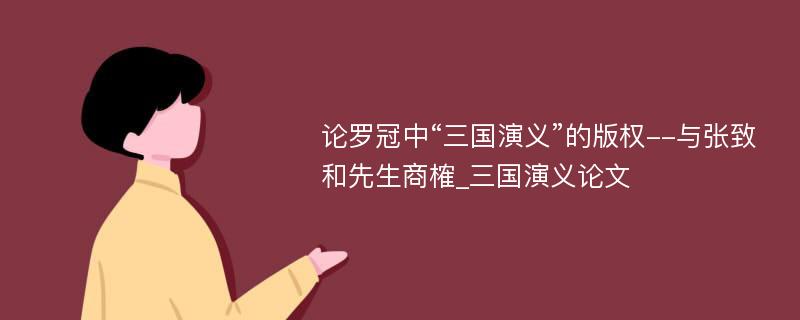
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问题——与张志和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演义论文,著作权论文,罗贯中论文,张志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大都有著作权归属问题,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作者为谁,长期以来都有过争论,有的至今还 时时升温为讨论的热点。唯《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明清以来从无人置疑。笔者尝以 之为幸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近来有张志和先生整理黄正甫本《三国演义》问世, 于该书《前言》中,又陆续发表系列文章(以下并《前言》总称“张文”)(注:笔者所见张先生有关论文包括其所整理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前言》,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1
月8日;《由周静轩诗看〈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年第6期;《〈三国演义〉的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载《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B),首倡“《三国 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其成书时间应当在明中叶”,“《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 南方人”等等,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问题便被提了出来,短时间内流传甚广。这说 不上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祸福,却一定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非有所讨论不可。
但是,据笔者所见公开发表的论著,学术界对张先生这一应可惊世的说法反响不多。最早 好像是徐朔方先生收入所著《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论〈三国演义 〉的成书》一文的《附记》,不赞成张文的某些看法,张先生著文作了答辩。除此之外,也 许还有笔者未见到的相关讨论文章发表,却总的说来显得冷清,甚或是寂寞。
《三国演义》流行天下,凡识汉字的,几乎没有人不读它;凡有它译本的国家和地区,也 都会有许多人读它;凡以各种形式接触到三国故事的人,无不受它影响。百年来各种文学史 、小说史著作和各种影印、排印的《三国演义》,以及电影、电视等各类作品,都把它归于 罗贯中名下。现在突然有人说这一切都错了,并出现了百年未见的不署“罗贯中著”的新版 《三国演义》,而学术界却基本上没有大的反映,这是正常的吗?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是学者们自愿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还是张文所考无可辨驳,还是张文持论不值一驳?我 想都不是,有的也最好不是。可能的原因,除了学者常有的谨慎之外,就是近年来古典文学 研究特别是《三国演义》研究缺乏商榷的气氛。这肯定对学术的发展不利,也是包括张文在 内一切认真的研究所不愿遭遇的寂寞。另外有实际的困难,是多数研究者一时不容易看到张 先生持论所主要依据的明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而不好下判断。至少这是笔者起意写作 本文之初所感到的。
但是,如果不是张文的发表,罗贯中《三国演义》著作权本不成问题,学者也就不一定重 视考察今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何以不署罗氏为作者等等的特点。实际上明刊本《三 国 演义》不署“罗贯中编次”一类字样的不止这一种,而从未有人因此质疑罗氏的著作权。所 以,张文从今存黄正甫刊本否定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读者所要关心的是:一、他 使用的资料是否可靠;二、他对资料的分析判断是否正确。从而决定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 。最好同时对张文做这两方面的检验。但在前一点一时不能完全做到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认 同张先生整理的黄正甫刊本及张文提供的资料是可靠的,而参照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学理 上看他的论证和结论是否正确。这应该是可行的。这样做的危险是,如果张文提供的资料有 误,我们就因为轻信而错上加错。但是,如果张文提供的资料可靠,而经由严格的分析论证 却也还得不出否定罗贯中《三国演义》著作权的结论,那应该就更能说明张文的结论有误。 笔者愿主要以新版黄正甫刊本和张文提供的资料为讨论的基础,对张文的结论提出质疑,以 此表示对张文探索精神的拥护。
一、今存黄正甫刊本不足为《三国演义》著作权论据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张志和先生整理出版之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问世是一件大好事, 肯定张志和先生对黄刊本“表里不一”等特点的发现有一定学术贡献。但是,我们对他就这 个版本所作进一步的考论却不敢苟同。张文介绍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说:
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 的 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 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分目录文 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书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 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刊 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6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 得注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个今所见最早刻本 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 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 的标签。
我们认为,从张文介绍黄正甫刊本的情况,结合它的论证,并不能得出《三国演义》非“ 罗贯中编次”的结论。理由有三:
1.诚如张文所说,这个今存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表里不一”,换句话它对于原黄正 甫刊本来说是个残本。残就残在“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 配的”,从而不是原黄正甫刊本“全书”。而传统上此书残缺部分的“封面、序言”一般会 题有作者姓名或有相关的说明,却可能连“天启三年补配”者也没有见到,从而原本是否标 有“罗贯中编次”一类字样,就应该是永远的谜。张文据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黄正甫刊 本,说“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云云,并不能得出原黄正甫刊本“ 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的结论。就今存黄正甫刊本而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是书补配 封面、序言、目录等部分和旧版正文部分均未标“罗贯中编次”之类题署,而原书是否标有 此类题署已不可考。
2.由此认定今存黄正甫刊本正文是早于嘉靖本的“旧版”,其“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 年以上”的根据也还不够坚强。张文的重要根据之一是《关云长水淹七军》一则中,黄正甫 刊本把“伍伯”误为官职,而嘉靖本“又误将‘伍伯’当作‘五百人’来理解,则是错上加 错了”。这里“又”字下得不妥。因为,这未必是先有黄正甫刊本“把‘伍伯’误为官职” ,然后嘉靖本进一步“误……当作‘五百人’来理解”的“错上加错”,而可能是各据旧本 校理不同处置的结果。这正如参加考试,试题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而考生的错误答案和致 误之由可能千奇百怪。张文说“由此亦可以证明,嘉靖本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会是最早 的刻本”,似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说明黄正甫刊本一定就早于嘉靖本。
其根据之二是嘉靖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则中“遂令扯碎其书烧之”语下小字注 有“旧本作‘板’”的话,而黄正甫刊本相应处正作“板”字,所以黄正甫刊本就是这样的 “旧有刊本”。这里的判断也小有失误,即由嘉靖本改“板”作“书”可定其“并非最早的 刻本”,却不能因黄正甫刊本未改这一“板”字就定它是“旧本”。这只是它可能为“旧本 ”的一个标志罢了,而是否旧本却要由全书来证明。这自然很难做到。不过博古生《序》已 称黄刊本“校阅不紊……庶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可知当时另有旧本,“校阅”的结果只是 “不失”原本的面目,却并不就是照原本刊刻的,所以“正文首行标作‘新刻考订……’” 云云,明说也不是“最早刻本”。
原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最早的刻本”,其“校阅”也非“不紊”,从中可以看到晚出的 痕迹。即嘉靖本卷之二十二至卷之二十四与黄正甫刊本卷之十八至卷之二十,《姜维大战牛 头山》等写姜维伐魏故事题下各依次小字标注有“一犯中原”、“二犯中原”、“三犯中原 ”,嘉靖本直至“九犯中原”;但黄正甫刊本至第四《邓艾段谷破姜维》题下改标为“四伐 中原”,第五《姜维长城战邓艾》缺标,第六《姜维祁山战邓艾》题标皆缺,第七《姜维弃 车大战》缺标,第八《姜维大战洮阳》下标“八伐中原”,第九《姜维避祸屯田计》下又缺 标。从上举两本小字注都有标“犯”字情况看,嘉靖本统一标“犯”字,“犯”表以邪侵正 、以下凌上之义,体现“按《鉴》”改编尊晋即帝魏的倾向;黄正甫刊本前标“犯”而后 改标“伐”,“伐”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伐”,表以正祛邪、以上临下之义,其前 后不一,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以此知黄正甫刊本小字注不是作者手笔,从而决不会是这个 刊本所具“草创初成的痕迹”,也不会是刻误,而应是“校阅”者根据两种本子简单拼凑的 结果。这两种本子一本作“犯”,一本作“伐”。其中必有一种晚出,从而黄正甫刊本整体 上是一个拼凑晚出的本子,而并非“旧本”,据以考论《三国演义》非罗贯中所作,不可能 有正确的结论。
3.由此认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 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理由并不充分,甚至完全 没有道理。根据有二:
一是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属志传系统本,嘉靖壬午本则是另外的系统。虽然它们一定 出 于同一祖本,但是中间经过了多少传钞、翻刻的转换,至今并不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原黄正甫刊本确实早于嘉靖壬午本,也不能认为所谓后出的嘉靖本标有“罗贯中编次”是 硬贴的“标签”。它应该有所根据。它的根据应当就是庸愚子《序》所说“士君子争相誊录 ”的钞本。如果那时已经有了黄正甫刊本,也不排除根据原黄正甫刊本原所残缺“封面、序 言”记载的可能,尽管原黄正甫刊本并不一定早于嘉靖本。
二是一般认为,嘉靖本刻工精致,当属官刻本,与一般书商的刻卖品有所不同。对这样一 个官坊精刻刊本的题署,似不宜如通常向“书商鬻书射利而贴…标签”上边去想。而据明清 间若存若亡的钞本《录鬼簿续编》所载戏曲作家罗贯中的一则资料可知,这位罗贯中并非当 时大名士之流,其微名未必就有招徕读者之效,从而果然“书商鬻书射利而贴……标签”的 话,应当用更合适的人,而不会是罗贯中。事实上明代不少《三国演义》刊本因为有了李卓 吾作招摇,而不再署“罗贯中编次”等字样,也说明因《水浒传》之累而被骂为“三世皆哑 ”的罗贯中,当时并没有多少招徕顾客的名家效应。而多数明刊本署“罗贯中编次”等字样 ,倒是因为相传如此,不得不然,并不出于更多“射利”的考虑。
总之,今存黄正甫刊本残缺有关著作权考证最有价值的部分,张文据此“全书”以考论《 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可能是上了“天启三年补配”者的当,而当时“补配”人却 未必有意骗人,特别是不可能想到蒙蔽三百多年后的学者。而此本正文也并非早于嘉靖本的 “旧本”,且有版本拼凑的痕迹,不足据为考论《三国演义》著作权的内证,尤其是不可单 凭这样一个本子下判断。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南方人”
张文由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而进一步提出“《三国演义》的最初写定者应是南 方人”。张文的理由是:
黄正甫刊本中“皇”、“王”不分或“黄”、“王”不分,“虽”、“须”通用的这些例 子,在北方话中都是完全不可能搞混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太原人,他如果是《三国演义 》的作者,决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而福建、广东、江浙一带,这些字的读音却几乎没有差 别。所以,黄正甫刊本的记录者必是据南方方音记录故事,才将这些字搞混了。而在嘉靖本 及其他刻本中,这种因音同而导致的用字错误基本上都被改正过来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的出现比该书明清时期的其他刻本要早得多,也足以说明黄正甫刊 本大有可能是一个根据说书艺人讲述的三国故事最初写定的本子,这个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 人。
这些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黄正甫本是刊刻本,张文所举是刻本讹误的例子。这讹误固然可能从南方人音读习 惯而来,却有两种情况:一是底本本就因音读而讹,刻本以讹传讹;二是底本不误,而刻工 听南人读字音而讹。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况,张文的判断就大致是对的。但是这不大可能。因 为黄氏刊刻此书应多多少少是“校阅”过的,即使粗略到“皇”、“王”不分未作校正(这 也是不可能的,详后),也不该容留他的族姓“黄”写作“王”,因而只能是底本并无音读 而讹的错误(这与正文有些卷标题有(“京本”的情况相合)黄氏校阅后下一道工序中刻工听 南人读字音而造成的讹误(这与黄正甫刊本出自建阳为闽本的情况相合)。总之,张文所举黄 正甫刊本“皇”、“王”或“黄”、“王”不分及“虽”、“须”通用的情况,是南方人读 ——刻北人所著书的结果,正好说明它不是“记录”本,而是晚出的翻刻本,不成其为考论 《三国演义》非罗贯中所作而由南方人写定的可靠根据。退一步说,这首先不是个读音的问 题,任何一位有“写定”《三国演义》水平的南方人或不免因音读习惯而误听,却决不会因 误听而把“秦始皇”之“皇”误书为“王”,那就表示他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而不够“写定 ”这样一部“杰作”的资格。黄正甫刊本仅一处“秦始皇”误作“秦始王”的例子,而其他 均不误,也说明这几处讹误不是由“记录”、“写定”发生的问题,而是闽人刻书致误。
其次,也不能从《关云长五关斩将》中叙事的地理知识错误判定《三国演义》的作者非北 方人,而是南方人。对此,笔者曾有《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一文有所讨论,摘录相 关部分如下:
同类的错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还可举出一些。典型的如卷六第四则《关云长五关斩 将》,故事在今见史书、话本和元杂剧中均无踪影,当是罗贯中的创造。但是,这一处叙事 地理方位可说是错得一塌糊涂。当时关云长弃曹操投奔刘备,应是自许昌出发北上赴黄河渡 口白马津。但是,小说写他经过的五关:第一关“东岭关”,是虚构的;第二关洛阳,越嵩 山绕到西北去了;第三关沂水关,“沂水”在山东临沂,《水浒传》所写李逵的家乡;第四 关滑州,又回到河南去了。依“寿张”错为“寿阳”的推论,罗贯中又该是山东沂水人了。 然而,这仍是一个钞误:洛阳东有汜水县,正在去荥阳的方向上,“沂水”定是“汜水”之 误。盖“沂”、“汜”形近而讹,把“沂水”改为“汜水”,方位就对了。这里,研究者可 以奇怪作品把地理搞错了,多方面去找原因,而不可以只从作者是哪里人,于所描写的地理 环境是否熟悉方面去深求。
笔者当时所据是嘉靖本,而今存黄正甫本正作“汜水关”。只是张文又奇怪他为何不走直 路,却“绕了个大弯子去过关斩将”。这只有从《三国演义》为小说和它受“说三分”的影 响去考虑了,却不一定只有南方人才会胡诌为绕“大弯子”。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写北方事的 多,也很有些地理知识的错误,依张文的逻辑,凡小说写北方事而有这类错误的,作者就该 是南方人了。这样的考据就太省力气了。而退一步说,即使是南方人写北方事容易有地理知 识的错误,那就很可能不止一处;而北方人写北方事不会出现地理知识的错误,却不能保证 写北方事而有地理错误的书不是一个早年流寓南方的北方人所作,因为它叙及地理之处毕竟 大部分正确。总之,对于一部有几百年说话和戏曲艺术背景成书的古代小说,以其叙事中地 理 方位的个别不合判断作者籍贯,纵然不是全无用处,也应该十分谨慎才是。
第三.张文说“黄正甫刊本大有可能是一个根据说书艺人讲述的三国故事最初写定的本子” 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分说如下:
一是张文说“明代的长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艺人在书场上‘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下来时, 他的写定者往往连这样的话也抄录下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的写定者当成作者来看待的 ”。结合张文的其他论述,换句话说,这样的“写定者”主要是一个“记录”的人,而“黄 正甫刊本的记录者必是根据南方方音记录故事”。这个说法颇新颖,却殊难理解。即短篇的 宋元话本一般也被认为是说话人的底本,而非听者的“记录”本;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 资料可以证明宋元时代有过说话人一边说一边被人“记录”下来而形成小说的事情发生。至 于小说家把说话人“卖关子”的套语也用在所写作品里,一面可能是编入了某些话本旧文, 一面主要是承袭话本的风格以“通俗”。如果从它用了说话人“卖关子”的几句套语就断定 其为“记录”,则不仅全部明代小说,连《红楼梦》等清代章回小说也会背上“记录”成书 的嫌疑。而章回小说这个形式上的显著的民族特点,就成了它全部为说话“记录”本的证据 ,岂不是荒唐。
二是张文说从多方面看,“元末明初罗贯中生活的那个年代,三国故事还不够成熟,许多 故事还没有定型,凭罗贯中一个人的智慧,无论如何也编写不出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来”。笔 者 不能清楚张先生有何具体的根据,但这至多可以是一个疑问,而不能由此得出《三国演义》 非罗贯中所作的结论。因为中外历史上可以提出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更大的疑问,能有很多 。近世欧洲就有人鼓吹莎士比亚写不出那么好的戏剧,其作者应该是同时代的培根。但学者 仅报之一笑而已。如果可以这样置疑于古人,历史上许多伟人的作为就几乎都不可解,所以 好像也有人说埃及金字塔是外星人建的。即以中国论,唐人的诗尚且一般很短,而屈原在他 的时代为什么能写出长篇的《离骚》?汉大赋也不过三二千字的规模,何以在那个时代司马 迁能写出历史巨著《史记》?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地提出问题。近年来李学勤等学者提出 “走出疑古主义”,也应该适用于古代小说研究。事实上,罗贯中在汲取史书、“说三分” 和三国戏曲资料的基础上“按《鉴》改编”,完全可能把他写三国故事的原稿提高到接近今 存嘉 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水平。而从罗氏原稿到嘉靖本与志传本之间,又有人做过某些进 一步的加工,使之能有今天读到的“那么多精彩”。
总之,从《三国演义》的文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是,大胆的疑问和推测更应该有 坚强的证据,否则将无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张文否定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援引胡 适的说法指它“不是一个人做的”,并进一步说它的“最初写定人是南方人”等等,立论可 谓大胆,而证据却薄弱到拿了凡章回小说都有的“卖关子”套语作“记录”成书的根据,就 不免使人失望。顺便说到,张文一面称引胡适《三国演义考证》中贬低“《三国演义》的作 者 、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等语 ,说明《三国演义》的写定者“对该书的创作并无多大贡献”,却同时又赞扬《三国演义》 为“不朽的巨著”、“不朽的杰作”,有些不合逻辑,也是可以斟酌的。
三、《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张文说《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不是新鲜的意见,也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就判定“其 成书时间实在罗贯中之后”,以使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失去最后依靠。这是一个错 误,虽然这并不是张文中最先出现的,却是关系罗氏《三国演义》著作权的大问题,也不可 以不辩。
所谓《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实际是说明中叶以前还没有《三国演义》这部书。在这 一问题上,持论者忽略了适用于这一考证的基本规律是说“有”容易,说“无”难。说“有 ”,只要举出一个证据就是“有”;而说“无”,则必须遍索明中叶以前至少是整个元代的 一切文献加以证明。而当时产生的文献至今已十不存一,所以这遍索之事已根本不可能。但 是,今之持成书明中叶论者,只从今见本《三国演义》中有明人尹直、周静轩等人的诗和明 代的地名及其他迹象,就断言其晚于何时何时;或者从庸愚子弘治甲寅序以前未见有人称道 《三国演义》,推论其不早于明中叶云云。殊不知文献有阙或已经改窜,是很难得实据下结 论的。反倒论其“有”,看似“难于上青天”,却可以偶然得之。
笔者曾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改定年代小考》[1]一文,举元末明初载籍中《三 国 志通俗演义》一则佚文和一条独与《演义》记载相合的资料,证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 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这一则佚文是: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释宋人陈刚 中《白门诗》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吕布骂语不见于《三国 志》等正史、《三国志平话》及今存元代三国戏以及他书的记载,独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等多种版本《三国演义》所写相合,可视为早期《三国演义》的佚文,证明此书早在瞿佑(1 341——1427)生活的元末明初就产生了。
但文献有阙,这一佚文也是一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说“有”容易,而在他书中说“无” 难的材料,并且是孤证,尚难据以结论。却是又从《吊白门》顺藤摸瓜,找到元末张宪《玉 笥集》咏三国史诗《南飞乌》一首,题下注“曹操”,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 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 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 ,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 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却又独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各本《三国演义》相合。 从而可以认为元末张宪《南飞乌》诗“白门东楼追赤兔”句典出《三国演义》,成为元末已 有《三国演义》的另一证据。
这两个证据从不同方面表明,在元至治(1321—1323)年间的《三国志平话》之后至明初一 段时期,《三国演义》已经产生和流行,其影响在张宪的诗歌的创作中已经有了表现。
而张宪字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则即使其《南飞乌 》诗作于入明以后,他所根据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当产生于元末。而考虑到一部书流传 到它的如“布骂曰”一类话语播于众口,“白门东楼”之说能夺正史记载之席,成为诗料, 需要较长的时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下限还应有较大提前。则参照各家研究的成果 ,定其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学术固然要求证据越多越好。但是,有了这两条资料的相互印证,关于《三国演义》成书 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立论就有了相当的基础。而发表至今两年有余,寂寞中又听到张 文重复“明中叶成书”说的老调——区区拙文并不重要,但是,难道今天做研究的人可以对 新 出现的材料也不屑一顾吗?
四、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不容否定
张文以今存经过补配的黄正甫刊本不署作者姓名而否定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却 忽略了明代多种版本《三国演义》明署罗贯中为作者的事实。英人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 表列《三国演义》现存明清版本共35种,其中明刊28种,题署作者简况表列如下(有庸愚子 序 视为题署罗贯中为作者):
序次版本简称题 署
1
上海残叶 无(存一叶)
2· 嘉靖本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3· 夏振宇刊本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辑)
4· 周曰校刊本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5· 郑以桢刊本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卓吾李贽评注,闽瑞我郑以桢绣梓
6· 夷白堂刊本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编次,武林夷白堂刊
7· 英雄谱本 晋平阳陈寿史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
8· 李卓吾评本
绣像古本,李卓吾原评《三国志》(有庸愚子序)
9
宝翰楼刊本
李卓吾先生评《新刊三国志》
11 钟伯敬评本
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校阅
12·叶逢春本 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绣像
13·双峰堂刊本
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等等
14 评林本
晋平阳陈寿史传,闽文台余象斗校梓
15·种德堂刊本
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冲宇熊成冶梓行,等
16 杨闽斋刊本
晋平阳陈寿史传,明闽斋杨春元校梓
17·联辉堂刊本
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少垣联辉堂梓行
18·汤宾尹本 平阳陈寿史传,东原罗贯中编次,江夏汤宾尹校正
19 黄正甫刊本
书林黄正甫梓行
20·诚德堂刊本
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诚德堂熊清波锲行
21 乔山堂刊本
书林乔山堂梓(行),等
22 忠正堂刊本
李九我校正,东涧熊佛贵刊行(残缺两卷或序目不详)
23 天理藏本 无(序目不详)
24·藜光堂刊本
晋平阳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明富沙刘荣吾梓行
25·杨美生刊本
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
26·魏氏刊本 晋平阳侯陈□志传,元东原罗贯□□□,□□林魏□□□□
27 魏玛藏本 无(残存卷6-10)
28 北京藏本 无(残存卷5-7)
从本表可知,现存28种明刊本《三国演义》中,序次后标有.号的15种版本题罗贯中.“编 次”、“编辑”或“演义”等;其他未署罗氏姓名者,或残,或为评点本,其中黄正甫刊本 为补配本,却绝无题为他人所作者。古人好奇,标新立异决不下于我辈,而对《三国演义》 作者除说到罗氏外绝无异辞,岂不是说明罗贯中《三国演义》著作权铁案如山,后人已无可 置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15种版本包括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 系统各主要版本。也就是说,这两个系统《三国演义》的各主要版本的题署相互印证,可以 确定罗氏为是书作者。同时,今能确知刊刻年代版本中最早的嘉靖本,题署及所载明弘治甲 寅庸愚子序也相互印证罗氏为是书作者。即如黄正甫刊本虽因补配而不知其本来有无罗氏为 作 者的题署,但黄正甫为建阳书林人,明代建阳书林梓行各本《三国演义》,多题“罗贯中编 次”等,以此类推,原黄正甫刊本今已残去的部分也未必就没有“罗贯中编次”或类似 的题署。总之,这是据直接材料的证明或推定,比较从一字一句的猜谜似考校,孰为可信, 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张文从庸愚子序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 ”与“实际上该书叙事是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不合,而置疑序称罗贯中 为《三国演义》作者,已有徐朔方先生的《附记》辩驳。徐先生的看法是,“如果不是刻板 地考虑问题的话,始于汉灵帝戊申岁即建宁元年(168)同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也可以并 不矛盾……两者虽然相差十几年,其间叙事不到一千字。张文以此贬低蒋大器序,或进而贬 低《三国志通俗演义》,根据不足”,可备一说。然而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即蒋大器所序之 《三国演义》本就从“却说中平元年”开篇,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第一则“却说中 平元年”前的文字是嘉靖壬午刊刻时增加的。理由有二:
一是作于弘治甲寅的蒋大器《序》中说: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 权柄日窃,渐侵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
这段话正是“却说中平元年”前一段文字大义,不过多了一些灾异天谴的描写而已。如果 《三国志通俗演义》早就有这前一段文字,蒋大器的话就成了多余。所以很可能是《三国志 通俗演义》本无此段文字,而嘉靖壬午刊刻时,因了蒋序而增写置于开篇,以便读者“求其 所以”。
二是从文字风格看,这前一段与“却说中平元年”以后文字风格不类。前者不过千余字, 而两引奏章,拉杂成文;后者由“却说”领起,才是真正小说家声口。所以,这前后的文字 大有不出于同一人之手的可能,而今本前段文字是嘉靖本增补的。
但是,嘉靖本增加了这一段文字,却没有顾及或者觉得不便改动前人所作序,遂有了张文 所指出的这一矛盾,也实在是学者应该知道的,却不可因此更横生疑忌,连庸愚子序说“东 原罗贯中”云云都不敢相信了。至于张文说蒋序“将罗贯中的籍贯‘太原’误写为‘东原’ ”,专家都会知道这其实是很长时间以来的一面之辞,另一面有说《录鬼簿续编》把“东原 ”误钞为“太原”的,甚至有说戏曲家的罗贯中可能为另一人的[2],张文也还应该有所 注意的好。
总之,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不足据为推翻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定论,罗贯中 《三国演义》的著作权不可动摇。罗贯中是元末“东原”即今山东泰安西南东平、宁阳、汶 上一带人,是他在正史和各种前代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大约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创作了 伟大的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属罗贯中的创作,也与包括张先生在内许 多学者意见相左,笔者将另文说明。这里,笔者要再一次强调张先生整理黄正甫刊本和某些 发现的学术贡献,而企盼本文的献疑能有助于张先生把他观点说明得更加周全。至于论述难 免有不当之处,盼能得到张先生及有关专家的批评。
标签:三国演义论文; 罗贯中论文; 张文论文; 三国论文; 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三国志论文; 张志和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南方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