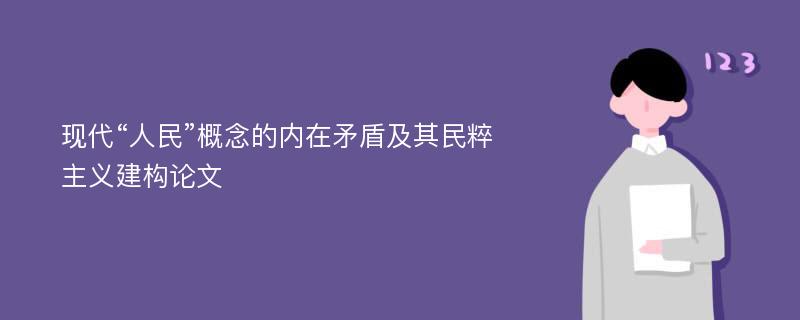
现代“人民”概念的内在矛盾及其民粹主义建构
孙经纬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 现代“人民”概念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含义。民粹主义与民主一样,依靠“人民”、诉诸“人民”,其首要任务就是建构出具有特定意义的“人民”。“人民”概念在“质”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和在“量”上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的紧张关系,为民粹主义建构“人民”提供了可能,也为民粹主义赢得政治话语权创造了空间。民主只有把“人民”拉回到政治话语的中心,化解“人民”概念的内在矛盾,才能消除民粹主义造成的民主危机。
[关键词] 人民;民主;民粹主义;理想性;排他性
“人民”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复杂概念。自现代“人民”概念产生至今,人们对“人民”的含义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人民”似乎变化无常,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指涉的内容不尽相同。古往今来,政治思想家们试图将“人民”内涵阐释清楚的尝试都是有限的,“人民”的概念几乎成为民主理论中最为困难的问题。近几年,欧美民主陷入困境、出现危机,民粹主义对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论战,将民粹主义研究的核心指向了民粹主义对“人民”概念的重构,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1) 拉克劳在《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中讨论了“民众阵营的符号统一体的建构”问题。认为人民是必须建构出来的抽象概念,人民从来都不是一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建构。他提出了异质性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民粹主义“人民”的产生过程。而齐泽克在《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中将民粹主义“人民”概念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一系列“民主性”要求(如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反战等)与某些同类事件的结合。See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4, 2006, pp. 646-680. Slavoj Žiž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3, 2006, pp. 551-574. 。民粹主义呼唤人民、迎合人民、动员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人民”是民粹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民粹主义的首要也是核心任务就是建构出具有特定意义的“人民”概念。在民主与民粹的话语中,“人民”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二者都将“人民”作为其理念内核。那么,两种话语中的“人民”有何联系?民粹主义的“人民”建构何以可能?这是认识民粹主义本质也是解决民主困局的关键所在。本文以“人民”概念为切入点,旨在分析“人民”概念在“质”与“量”上的双重矛盾,进而解释民粹主义“人民”建构的政治逻辑。
一、“人民”概念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下,人民被视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人民的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承认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所有民主国家的普遍共识。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孕育了“人民主权”原则,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阐释人民主权思想,对君主专制进行清算。在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笔下,“人民”是一个体现公意的抽象整体,具有道德人格,是最高主权的所有者(2)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都明确宣告,主权的本源在于人民(3)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三条写道: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人民主权”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人民”以主权者的身份出现,成为最受关注和尊敬的政治主体。
我们风尘仆仆辗转沿海城市,荣幸拜访多家企业,也深深难忘此次经历。多想时光再慢些,珍惜共处时光,又多想未来快快到来,因为那将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中国的未来。
然而,在民主政治的叙事中,“人民”却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人民”是一个神圣崇高、完美无缺的形象,它是智慧与正义的化身,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人民的选择意味着绝对正确。尤其是在推翻君主统治的政治运动期间,对“人民”的赞赏之词更是不绝于耳。欧洲革命浪潮爆发的两年前,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就写了《人民(Le Peuple)》一书来讴歌“人民”,在他的描绘中,“人民”慷慨大方、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和人性的光辉(4) Marco D' Eramo, “Populism and the new oligarchy”, New Left Review, Vol. 82, No. 4, 2013, pp. 5-28. 。另一方面,则对“人民”充满了贬斥甚至是蔑视。我们可以找到一连串形容“人民”的负面词汇:愚蠢、粗野、冲动、无序、肆意妄为、麻木不仁、没有受过教育、易受人煽动,等等。黑格尔(G. W. F. Hegel)曾直言:“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62-363页。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6-367页。 。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词能像“人民”一样,对它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极端对立的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集于一身。“人民”仿佛是上帝与恶魔的双重附体,一面是神圣的、具有创造性的,一面是低劣的、具有毁灭性的。上帝般的“人民”寄托了民主的理想,恶魔般的“人民”表现出了人民力量的可怕。
对“人民”呈现的两种不同态度直接导致了在民主政体中人民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权力——既要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又要对人民保持警惕,极力抑制人民对政治产生的影响。由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立法权自然应归属于人民,“唯有人民才可以立法,这是民主政体的又一条基本法”(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页。 因此,人民以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在立法时刻。同时,基于“人民”的种种消极特征,“人民”被认为缺乏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无法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于是人民的出场时间受到了限制。当立法完成后,人民随即退场,在现实政治中保持静默。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提醒可能是对限制“人民”权力最好的解释:“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都是罪恶。”(8)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这反映出,目睹了革命是如何摧毁旧制度整个过程的人们对“人民”力量的忌惮与恐惧。
(1)配料 考虑到成本问题不做调整,试块铁液熔炼主材采用40%~60%的废钢加40%~60%的浇冒口返回料。
随着文明的进步与政治的更迭,“人民”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人民”所涵盖范围越来越广,西方政治的发展过程就是“人民”形象逐渐丰满的过程。麦克利兰就曾称:“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政治史,可以用‘人民’的观念逐渐扩张,卒至包含每个男女的过程为主轴来写。”(19) 麦克利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在现世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等都不作为“人民”的限定标准。在法理上“人民”即使不包括一切人,也至少包含享有政治权利的全体成年人。甚至有人认为,“人民”的含义包括了“全体有政治权利者(公民)”“全体国民”“目前的全部人口,而且包括过去和未来的世世代代”(20) 沃尔夫冈·曼托(Wolfgang Mantl)认为,凡是与法律秩序有积极关系,以任何方式参与法律规范订定者均可称为人民,或者更为广泛的因为年龄,或因精神与道德健康问题,或因其他理由而未能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但并不包含住在境内的外国人。甚至是囊括了现在活着、已经死亡与尚未出生的人口。参见沃尔夫冈·曼托:《代表理论的沿革》,应奇编:《代表理论与代议民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2—14页。 。上述的“人民”以及我们日常话语中的“人民”就是指共同体内部的所有人。这里,“人民”毫无疑问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它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人纳入到“人民”这个统一体当中。可以说,“人民”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集合整体。
基于先前的讨论,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现代“人民”概念在“质”和“量”两个维度上都充满了矛盾之处。在过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和掩盖了“人民”的内在分裂,因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构成“人民”的每一个个体相一致的目标。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政治权利的诉求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使得“人民”的困境又一次显现出来,民粹主义在欧美世界的强劲“复兴”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若“人民”概念像此前分析的那样,民粹主义建构“人民”的政治逻辑便好理解了,其在今天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只是“人民”在“质”和“量”上的抵牾所积累而成的爆发。“人民”概念的内在矛盾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温床,正是由于“人民”概念先天性的不足,才使得民粹主义进行“人民”建构成为可能。
“人民”概念的这种包容性,为更多的人争取政治权利打下了根基,但同时也造成了认识和实践上的模糊与困难。第一,“人民”的规模越是庞大,越需要从整体的视角看待人民,越要强调它的整体性特征,因为在庞大整体的面前,渺小的个人或者“人民”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民”的这种整体论调存在重大缺陷,就如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讲,“它对民主毫无用处,或者说它无论如何都可以用来为任何政体辩护”(21)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民主政体可以,极权主义政体同样可以,而作为个体的人民就极有可能成为作为整体的人民的牺牲品。第二,无论共同体中的成员自身身份如何切换,“人民”这一标签永远都不会变,一个人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是“人民”。“人民”就会变成一个无所谓确切含义的概念,这也就是在今天人们全然不知何谓人民,却对自己就是人民当中的一员深信不疑的原因。第三,当进行政治运动时,为了明确动员对象,就需要解决哪些人是“人民”的问题,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就失去了价值,因为如果将“人民”用来描述那些站在“人民”反面的人,“人民”一词将失去光彩,变得毫无意义。
二、“人民”概念的包容性与排他性
事实上,在主权确立以后,“人民”经历的两次出场(立法时刻与选举时刻)和两次退场,体现了“人民”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巨大落差。人们开始怀疑,建国精英之前对人民的欣赏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借口罢了,他们为了赢得统治,不得不表明为“人民”而战的鲜明立场,传播一种“人民”的美好形象。不可否认,代议制政体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民”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依托人民的代表,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给予了回应。但这仍然难以解决如何把权力实实在在地、持续性地掌握在“人民”手中的问题。“人民”概念所内含的理想意味,是民主赢得人心、取得成功的动机和重要条件,而“人民”的现实状况却导致了其对民主的失望和不满,这成了现代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人民”在虚妄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持续摇摆、无所适从,他们缺少足够的存在感与参与感,大部分时间里隐而不现,以一种近乎虚幻的方式来实行统治。结果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民主使自己的两难处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人民”的两难。
(2)监督盲区诱发“道德风险”。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活动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是确定服务承接者的主要方式。我国社会组织培育较晚且发展不成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宏观性较强。因此,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同时,服务供给者有可能在生产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向政府只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更为吊诡的是,现代“人民”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建国者与理论家们界定“人民”时像在做一道选择题,通过排除法来获得答案。“民族”是划分“人民”与“非人民”的首要标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熏陶、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目标愿景等因素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这些具有同质性的人们组成了民族,非本民族的人排除在了“人民”范围以外,“人民”首先获得了民族属性。18世纪中后期,“民族”与“人民”两个词几乎相伴而生,携手进入到现代政治领域,这两个术语也一度被看作是同义词。民族“将人民描述成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它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特性,具有政治存在的意志……当人民并非作为民族而存在时,它就只是一个在种族或文化上息息相关的联合人群,而不一定是一个政治地存在着的联合人群。”(22) 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人民”通过“民族”来获得政治主体的身份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在民族中找到了归属感,民族性特征深深地烙在了“人民”的概念里,“人民”变成了“民族”。民族(nation)概念因此也从18世纪以后“断绝了与古代希腊罗马的natio,gen和ethnos等诸概念的关系,并且获得了其现代意义,指的是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的成员资格,是作为希腊罗马时代所使用的politai和cives的近代版本的‘国民’概念”(23) 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直到现在,民族也被看作是最恰当的政治单位,世界由若干个民族国家构成是基本事实。民族国家的产生制造出这样的现象:有纳入到“人民”之内的人,就必然有其他的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持续地灌输民族意识,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使“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是取得民族独立的最重要手段。“在整个欧洲,民族主义精英需要在‘人民’中做大量的文化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解放和国有化这些‘人民’”(24)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vernacular mobilisation in Europe”, Nations & Nationalism, Vol. 17, No. 2, 2011, pp. 223-256. 。这些民族精英随后进行的便是不断地纯化“人民”,把一些他们认为有损“人民”同质性的人从“人民”中排除出去。通过减少“人民”的数量来圈定“人民”的范围,成了一项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最终发展到以“种族”来标定“人民”,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清洗就是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
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民”有时专指平民,并非包括所有人。由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人民”概念的含义就呈现出了平民转向的特征。在欧洲革命的话语中,“人民”是指穷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受压迫的人,他们是那些不为人知、不被重视、生活凄惨的劳苦大众。法国大革命时,“平民”与“人民”合二为一,以“第三等级”的称呼出现,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西耶斯(Sieyes)的呐喊是“人民”抗争的简洁表达:“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25) 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页。 确切地说,第三等级包括了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与贵族阶级对立的群体。当时国民议会的成员都宣称自己是平民的代表,革命的领导者对于平民的同情与理解,也成为最高的政治美德。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称:“人民(le peuple)”在法国大革命中“破天荒第一次,这个词涵括了参与政府事务人员以外的人,不是指公民而是指下层人民。”(26)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换言之,与平民相对的统治者、政治精英、社会上层、有权势的人被排除“人民”之列。
集成电路产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电子、通信和测控等领域发展的基石.集成电路设计人才的培养也是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根据“新工科”的发展要求,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目标,针对目前集成电路设计专业课程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课程体系、实践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集成电路设计课程进行了改革,并对课程内容等多方面进行了优化.为学校工科的发展,以及创新型和应用型的设计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但是,仅仅在立法时刻出场,还远远不能说明“人民”的统治地位。代议制的出现为人民在退场之后如何安顿的难题找出了解决办法——人民以选举产生代表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于代议制中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的论证最为有力。他指出:在代议制政体下“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利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掌握有这个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不需要由宪法本身给他们以这种控制权。”(9)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 也就是说,“人民”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代表,“人民”的代表作为中介使得人民与国家产生联系。代表原则融入了民主政体,“民主”与“代表”原本两种不同的理念实现合流,“人民”从而变为“选民”。在选举时刻,“人民”可以再度出场,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代表原则的运用在美国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10)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3页。 ,人民代表比人民自己发出的声音更加符合公共利益(11)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7页。 。联邦党人为了更加清晰阐释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甚至用“共和”一词与“民主”区别开来。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及美国民主时也称,“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而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也微乎其微,并且薄弱得很,何况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服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1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1页。 这样的解释,看似是恰如其分的,但在民主理想的坚定崇尚者看来,建国精英们实则是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把“人民”排除在政府之外,使“人民”无法进入到实际的政治领域,以至于“人民”不能亲自行使权力。可以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也可以说,“人民”已经完全退出了政府(13) J.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17. 。在本质上,“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的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14) 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页。 这样一来,人民统治的理想设定大打折扣,政治权力依然是被政治精英把控着,而“人民”的权力被架空,“人民”只是在名义上掌权而已。或许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点到了民主的实质:“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15)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5页。 其实,基佐(Fran?ois Guizot)很早就对代议制产生了质疑:代议制与人民主权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人民拥有主权却不统治,而进行统治的政府却没有主权(16) Fran?ois Guizot,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Europ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2, p. 61. 。这样的逻辑着实令人费解。正如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德蒙·摩根(Edmund S. Morgan)分析的那样,人民同时具有两个身体,即主权者与臣民(17) E.S.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8, p. 61. 孟德斯鸠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民主政体中,人民在某些方面是君主,在另一些方面是臣民。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页。 。民主亲手将“人民”分裂成在政治上对立的两种不同形态。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民”是一个缺少实在基础的虚构概念,因为政治权力的核心由君主转变为人民,君主权力有具体的某个人负载,而人民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指代,故而出现了权力的空位(18) Claude Lefort,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 17. 。
三、民粹主义“人民”建构的逻辑
1) 在生物量方面,在黏土中,从移栽到DAP30,3个处理间地上部生物量没有显著差异,DAP30到DAP60,甘薯地上部茎叶生物量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加,而到了生育后期(DAP118),T2处理高于T3,说明适宜的外源压力有助于甘薯茎叶在中后期的生长.在黏土和砂土中,各生育期甘薯地下部生物量均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由此可见,“人民”概念兼具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定义“人民”时加法和减法的同时使用,再一次使“人民”概念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人民”陷入了一种悖论,其自我实现要依靠自我否定的方式,即用排他性的“人民”否定包容性的“人民”。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将既指代所有人的“人民”,又指代底层平民的“人民”,分别看成是“大写的人民”(the People)与“小写的人民”(the people)。他认为,“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是“人民”概念原始结构的断裂,只有这两者在内涵上达成统一,“人民”的内部战争才可能停止(27)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31. 。也正是这种原始结构的断裂,大大增加了“人民”的不确定性,“人民”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建构的可塑性概念。只要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就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诉诸新的辩护手法,任意划定“人民”的所指范围。因此,“人民”合法化新进程的代表往往同时积极参与摧毁关于“人民”的传统知识(28) Jean-Fran?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30. 。任何一股政治势力,在进行政治动员时,为了表明“人民”真实存在着,必须制造出“人民”的对立面来拆解“人民”本身,以确定被贴上某种标签的“人民”的一部分,来否定包括了全部人的“人民”整体。这样就造成了,“人民”原本是“同一性的纯粹源泉,却不得不根据排外主义、语言、血缘和领土来重新定义自身,纯化自身。其本质不在自身而在其对立面上,因而,‘人民’自身缺乏本质;也因此,它的实现与自我放弃也将同时发生;为了存在,它必须经由对立面来否定自身。”(29)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31.
一方面,民粹主义把“人民”概念的理想性强化到极致,为建构“人民”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与民主相同,民粹主义同样把“人民主权”的理念奉为圭臬,其主张与民主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民粹主义者呼吁把主权交还给“人民”,突出“人民”善良、纯洁、高尚的一面,通过神化“人民”为自己套上一层华丽甲胄,将“人民”作为其坚固的外壳。德国戏剧家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这样描写激进民主的“人民”概念:“我们的‘民众’概念是指那些不仅全力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占据历史,加快它的前进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的人民。在我们心目中,人民谱写了历史,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他们自己。在我们心目中,存在着战斗的人民,因而也存在着一个进取的‘民众’概念。”(30) 转引自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可见,在民粹主义话语中,预设了“人民”的正义性,这也为民粹主义开展运动、夺取政权的道德正当性寻找到了依据。另外,民粹主义者捕捉到了在现实中“人民”对政府产生的疏离感,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表现出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反抗。民粹主义者声称自己才是“人民”真正的代言人,将人民的代表视为障碍,反对将“人民”弱化成“选民”,拒绝经由中介机构来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强调“人民”直接参与政治、行使权力。因此,民粹主义者常常表现出反精英、反建制的特征。实质上,民粹主义夸大了“人民”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下流的和道德的,非理性的和体现一个国家真正价值的,及对民主的威胁和主权的持有者,这种相互竞争并且经常对立的图景决定了民粹主义与其敌人斗争的政治形式,定义并且重新定义谁是‘人民’及其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是什么。”(31) 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2005, p.16. 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实则是建构了一个“人民”的乌托邦,那些仍怀揣民主理想、对现存政治失望的人就会主动走到民粹这一边。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利用“人民”概念的排他性,划分出特定的“人民”范围。民粹主义者将自认为可以团结的人纳入进“人民”范围之内,号召所谓的“人民”加入其中形成对政治的狂热参与。同时将其他人排除在“人民”范围之外,确定与之对抗的关系。从而在政治上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构成了“人民”与“其他人”的分界,构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区别。著名的民粹主义研究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提出了两种民粹主义者构建“人民”概念的方式:一种是界定“谁不是人民”,即划分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人为地塑造对立;另一种则是界定“人民在哪里”,即标示出“人民”的特点,强调通过这些特点来回归一种人民的生活(32)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8页。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在民主那里找到印记,民粹主义几乎采用了与民主建构“人民”时同样的手法。如前所述,民主政治以民族为标准将本族人与外族人分割开来,以识别谁是“人民”。民粹主义者也经常利用人们的排外心理挑起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感。“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宣扬的‘人民’,与民族主义者宣扬的‘民族’,其最初含义出自同一谱系。”(33) Guy Hermet, “From Nation-State Populism to National-populism”, in Alain Dieckhoff (ed.), “Revisiting Nationalism Theories and Process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92. 尽管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划等号,但由于“人民”与“民族”二者的紧密联系,高举“人民”大旗的民粹主义与高举“民族”大旗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混乱。带有民族属性的“人民”天然是民粹主义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工具,正是现代“人民”概念的民族性基因,为民粹主义覆盖上了一层民族主义的色彩,也为民粹主义赢得话语权提供了强劲的支持,民粹主义者也因此往往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大声疾呼“人民”忠诚于自己的民族,是最容易也是最能激起人们热情的一件事了。同时,民粹主义也通常将“平民”等同于“人民”,这只不过是沿袭了民主的“人民”含义,“继承了人民重心下移的历史惯性”(34) 丛日云:《从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到民粹化民主——论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趋向》,《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第12页。 ,与“人民”的民主式建构如出一辙。简单地说,“人民的存在来自于其在组织构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对立面,来自于敌人被外化为实际的侵入者、障碍。”(35) 斯拉沃热·齐泽克:《抵御民粹主义诱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72页。 而划分在人民对立面的人就是民粹主义的“构成性外在”(36) 这一概念最初由亨利·斯塔顿(Henry Staten)提出,之后被墨菲(Chantal Mouffe)应用。墨菲指出,“构成性外在”观念的目的是要突显“一种认同的缔造包含着差异的确立,而这种差异通常基于一种等级而被建构”“一旦我们理解到每一认同都是关系性的,并且,对差异的肯定乃是任何认同之存在的前提,即认识到某种‘他者’构成了它的‘外部’”。参见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民粹主义的“人民”建构将“人民”割裂成相互对抗的两个群体,抛出了一个似乎没有选择的问题:是站在人民这边,还是做人民的敌人?
德国宪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曾说过:“人民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它不是一个拥有受限定的权限、按规定程序履行公务的固定主管机关。只要人民拥有政治存在的意志,它就高高在上,不受任何形态化和规范化的影响。作为一个无组织的实体,人民不能被消解。只要人民存在着,并且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活力,始终能够找到新的政治存在形式。人民的弱点在于,它本身并无固定形态或组织,却要决定有关其政治形式和组织的根本问题。因此,人民的意志表达很容易遭到误解、曲解或篡改。”(37) 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第126页。 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建构充分说明了“人民”概念的弱点。作为民粹主义话语构造的“中心地区”(heartland)(38) 保罗·塔格特开创性地将“人民”的概念提到民粹主义话语建构中心地区的位置,指出民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与“人民”在一起,居于权力合法性之源的中心地区,而此中心地区是一种永久的话语构造。参见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28—133页。 ,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还是左翼民粹主义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并无同一的内涵,也无统一的标准与尺度,而是依附于意识形态随意进行政治叙事。实际上,在民粹主义建构“人民”概念之前,“人民”本身就已经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分离。人民在现代民主产生之初便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其涵义的原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民”概念的可塑性与灵活性。“人民”在“质”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和在“量”上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的紧张关系,为民粹主义划分敌友、制造出虚构的政治合法性、赢得政治话语权留下了空间。民粹主义通过建构自身需要的“人民”概念,一边填补空隙,一边制造分裂,在解构与重构“人民”的过程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人民”动员,激发了“人民”潜在的巨大话语能量。与其说民粹主义利用了人民概念的漏洞,毋宁说“人民”概念的内在矛盾使民粹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民粹与民主共享人民主权的话语体系,而自由主义民主下的“人民”概念的含糊与矛盾是民粹主义可以肆意建构“人民”的重要原因。“人民”概念自身困境的形成和进一步恶化,与民主没有认真对待“人民”有极大的关系。民粹主义的发展“与‘人民’一词的废弃程度成正比:在政治话语中,人民越是处于边缘,民粹主义就越成为中心”(39) Marco D' Eramo, “Populism and the new oligarchy”, New Left Review, Vol. 82, No. 4, 2013, pp. 5-28. 。在西方国家中,“人民”已经逐步淡出政治家们的视野,正在走向政治话语的边缘,甚至遭到了抛弃。在实践过程中,主流民主对人民概念避而不谈,“人民”偶尔被提出只是用来充当政治的工具,人民成为选举意义上的多数人或是被组织起来的少数人。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而利用和透支民意,甚至刺激民粹,“人民”的意义渐渐被消耗殆尽。主流民主忽视了人民的内部差异,高估了人民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掩盖了人民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讲,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泛滥是主流民主弊端的折射。民粹主义产生根源在于,自由主义民主中“人民”不同面向之间的张力,其本质是“人民”概念内在断裂的极端选择。因此,民主产生之时便埋下了民粹的种子,只要民主没有解决“人民”概念内含的冲突,民粹主义的幽灵便会如影随行,一直跟随在民主左右。
四、结 语
民粹主义以民主的方式挑战民主,其对民主所形成的冲击为民主敲响了警钟。民粹与民主相互纠缠、难解难分的关系起于“人民”,也应止于“人民”。要想攻破民粹之“民”的堡垒,必须廓清民主之“民”的概念。赋予“人民”新的内涵,恢复“人民”的名誉,确定“人民”权力的合理边界,阻塞民粹主义随意建构“人民”的通路,抵制利用人民特殊地位实现恶的企图,从源头上抑制民粹主义的泛滥,于民主而言是一项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现在为“人民”正名的时刻已经到来。对“人民”的错误认识,终将导致“人民”的悲剧。真正的“人民”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并非抽象的遥不可及的“人民”和少数特殊的“人民”,也并非虚幻的政治统一体。“人民”并不是算术意义上简单的单个人的相加,而是具有个体意识和人格的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权利的聚合。只有将“人民”权力转化为每一个人的切实权利,从而有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人民”才能获得现代政治中应有的尊重,民主才能从民粹主义的泥潭中走出。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People ”and Its Populist Construction
SUN Jing-we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 Behi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people” exists an extremely complex meaning. Populism, like democracy, relies on and appeals to the “people”, and its primary task is to construct the “people” with specific significance.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 in “quality”, along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inclusiveness and exclusiveness in “quantity”,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populism to construct “people” and create space for populism to win political voice.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caused by populism can be eliminated only when the democracy brings “people” back to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esolv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
Key words : people; democracy; populism; ideality; exclusiveness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6-0093-08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孙经纬(1992-),男,河北张家口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
[责任编辑:张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