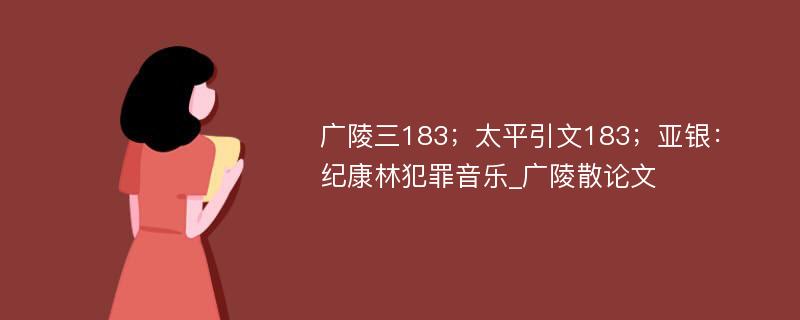
广陵散#183;太平引#183;雅音:嵇康临刑奏曲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广陵散论文,奏曲考论文,雅音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6)02~0136~09 一、《广陵散》《太平引》、“雅音”辨 关于嵇康临刑奏曲故事,除为人熟知的《广陵散》外,还有另外两个版本。 一为“《太平引》版本”。《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曰:“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①《文选》李善注亦引此,而脱“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句,多“就死,命也”四字。②《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七所引略同。③ 二是“雅音版本”。《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④这个记载与上两个版本相比不同之处有二:首先,未言明所奏何曲;其次,“于是绝”的对象是泛指(即雅音)。 关于三种记录之抵牾,前人早已注意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嵇康别传》所记《广陵散》事与《魏氏春秋》对举,言“与盛所记不同。”陈耀文于《天中记》卷四十二《琴》中广徵史料,指出“《太平引》、《广陵散》、‘雅音’之说互有不同。”⑤《晋书斠注》卷四十九引各家说辞而未辨其得失。⑥此外,多有学者注意到了“《太平引》版本”而加以辩正。总结起来共有四种观点,撮述要旨如下: 一是认为《太平引》是《广陵散》的别称。如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据《文士传》而言:“《广陵散》本名《太平引》。”⑦沈叔埏《颐彩堂文集》卷三亦据此云:“则是《广陵散》似即《太平引》。”⑧这种说法仅据此孤证而言二者系一曲,无论于史料还是于情理上都是缺乏支撑的。故戴氏批评持此观点的《选学胶言》云:“张云璈《选学胶言》据《文士传》之说,因疑《广陵散》别名《太平引》,则更属臆度矣。”⑨ 二是相信《广陵散》说而否定《太平引》说。如徐昂《畏垒笔记》卷四云:“临命而作《太平引》,恐无是理,当以干令升《晋纪》作《广陵散》为正。”⑩此说较前说为合理。一是以情理度之,《广陵散》较《太平引》更符合当时场景。王德埙说:“焉有在黑暗政治的屠刀下的颇具斗争性的嵇康,偏要援琴为当局粉饰太平之理呢?”(11)《太平引》早佚,难明其究竟为何种曲目。王氏以曲名而度意,虽不免臆测之嫌,但亦可备一说。二以干宝《晋纪》的可靠性作为依据,唐修《晋书》本传对其高度评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刘知几赞其:“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12)干宝《晋纪》早佚,《黄氏逸书考》、汤球《晋纪辑本》、陶栋《辑佚丛刊》、《众家编年体晋史》皆有辑。关于《晋纪》对此事的记述后有详论,此不赘。这种说法虽似可靠,但仍属推测,证据略显不足。 三是一并承认两种史料的可靠性,试图作出调和矛盾的解释。如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并据《嵇康别传》与《文士传》云:“《太平引》、《广陵散》当系二曲。康临刑所弹者《太平引》,而又忆及《广陵散》也。”(13)戴明扬对洪说的态度较为暧昧:“洪氏分二曲为所弹所忆,固未必得之;而二曲之非一事,则似可无疑。”戴氏所谓“二曲之非一事”实是对于第一种观点的否定,但并未表明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洪说乍看合理,却经不起推敲。洪氏的立论点在于其所见到的(此定语极为重要)《嵇康别传》载嵇康临刑之语云:“《广陵散》于今绝矣。”(14)而未言嵇康弹奏《广陵散》一事,《文士传》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太平引》,曲成”,洪氏于是将两首曲目合为一,分为“所弹所忆”,这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嵇康别传》全文已佚,洪氏所见引书为残句,此句之前很可能有嵇康奏《广陵散》的记载。从文意上看,洪说不符合行文惯例,亦殊于人情常理。第二,对比《文士传》之“《太平引》于今绝也”及《嵇康别传》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可以很明显看出二者的“亲缘”关系。宁稼雨的看法很准确,此为“一事两传”,(15)绝非同一事之两个部分。另外,不同的史料于同一件事分而载之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此为嵇康临终之语,何有断开成句,各记一半的道理?故而此种说法并不能成立。 四是否定《广陵散》说而取《太平引》说。由于《广陵散》说史料丰富且影响极大,故推翻此说极为不易。刘鹗《十一弦馆琴谱》据“唐以前各家琴书俱载有广陵散”而证《广陵散》之未绝,由此驳《广陵散》说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进而否定《广陵散》说。又把《太平引》之“《太平引》于今绝也”作为“此绝传者是《太平引》,非《广陵散》”的又一证据,最后得出“袁孝尼从中散学琴为一事、中散临刑鼓太平引为又一事。史书误合为一耳”的结论。(16)按,《广陵散》未绝之原因前人论之已详,详参戴明扬《广陵散考》、王德埙《琴曲〈广陵散〉流变初考》(17);余嘉锡之释“《广陵散》于今绝矣”句亦可明刘说之误:“不过康时感叹之言,《广陵散》实未尝绝”,“盖康自以为妙绝时人,不同凡响,平生过自珍贵,不肯教人。及将死之时,遂发此叹,以为从此以后,无复能继己者耳。”(18)故不能以《广陵散》未绝一事证《广陵散》说非,刘说难立。 综上,在没有将“雅音”说纳入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只有第二种观点有成立的可能。但还需要更多切实的证据。下文拟从史源入手,对三说再作钩考。 二、史料溯源与探幽 现存最早关于嵇康临刑奏曲的记载为向秀《思旧赋》,序中云:“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19)此并未言所奏何曲,亦未有临终感叹。这是西晋时可检之惟一文献。时至东晋,可察者较多。干宝《晋纪》虽佚,然《文选》六臣本《思旧赋》李善注中保留嵇康临刑残句,曰:“广陵散于今绝矣!”(20)《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竹林七贤传》曰: 嵇康临死,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惜固不与。《广陵散》于是绝矣。”(21) 按,史无《竹林七贤传》一书,别题《竹林七贤传》者有二。一为袁宏《竹林名士传》,二为戴逵《竹林七贤论》。袁书早佚,各书见录,或题“竹林七贤传”,或作“正始名士传”,或曰“名士传”,或作“七贤序”,吴士鉴《晋书斠注》卷九十二有考。(22)戴书亦有此别名。(23)由于袁书与戴书时代较近(后文有论),对本文论证结果几无影响,故不辨,俟另考。(24) 据王尽忠考证,干宝生于公元280~289年间,卒于351~361间,此处采取较为保守的说法。(25)故《晋纪》成书时间最迟不过公元361年。程章灿将袁宏卒年系于公元376~377年。(26)依张可札说,戴逵卒于公元395年。(27)由上推知,《广陵散》说最迟于361年前已经出现。但并没有成为定论。证据是孙盛《魏氏春秋》所载的“雅音”说。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将孙盛卒年系于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28)据《晋书》本传“年七十二岁卒的说法,则孙盛生于公元302年。尽管生卒年各有所差,但可知干宝、孙盛、戴逵、袁宏大体属于同一时代人,没有证据可以确定其成书次序的先后以及互相之间是否有影响。但孙盛“雅音”说的出现,则能证明在东晋时期,嵇康临终奏曲之事已有两传,然故事之基本要素则为一致:(1)临刑援琴;(2)感叹琴曲从此绝传。“雅音”说与《广陵散》说差异处有二:一是感叹绝传的对象不同,前者是泛指,后者具体到曲名;二是后者多了对绝传原因的解释,即袁孝尼学琴一事。 尽管事有两传,但很明显《广陵散》说的影响力于时已经盖过“雅音”说。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七所引《灵鬼志》: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着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蹔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29) 这个故事固然出于时人的附会,但嵇康习得《广陵散》之神秘性以及“不得教人”的誓言,显然非常具有针对性。即至少于《灵鬼志》成书(晋末)之前,《广陵散》说已极为盛行。 此后,突然出现另一种说法,即《文士传》之《太平引》说。据朱迎平考,《文士传》成书不能早于公元373年,下限则推到公元429年。(30)《文士传》虽佚,然据辑本,则知以上诸人中,至少孙盛有传。(31)虽不能由此断定《文士传》曾直接受上述文献影响,但《文士传》较上列文献晚出则为定论。为便论述,兹重引《太平引》说于下: 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 此处记载并没有脱离已经定型的嵇康临刑奏曲故事的基本框架。上文所述的两个基本要素皆在。但很容易看出它对于原型故事细节的敷衍与删窜。首先增加“兄弟亲族咸与共别”一事,为引出其兄携琴而来,其后嵇康奏曲便显得顺理成章。《文士传》作者虽使细节更为丰富,但不禁使人疑其小说笔法。裴注《三国志》对《文士传》真实性的评价很低,其考《文士传》所载王粲说刘琮事之虚妄,末云:“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32)又引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驳《文士传》载阮瑀事,斥云:“愈知甚妄”,“了不成语”,“瑀之吐属,必不如此”。(33)周勋初先生对于《文士传》的态度很谨慎:“文士传中的记载每与史实有出入,后人援用时当郑重对待。”(34)笔者认为,《太平引》说很可能出于对前说的敷衍与虚构,并不符合史实。 时至刘宋,成书于元嘉六年(429)的《三国志》裴注同引《魏氏春秋》“雅音”说与《嵇康别传》之《广陵散》说,而云:“与盛所记不同”。这里传递出两个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在裴松之时,《广陵散》说还未成定论,“雅音”说仍具有一定地位。第二,此处提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即《嵇康别传》。这是现存史料中《嵇康别传》首次见引: 康临终之言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条材料与《太平御览》所引《竹林七贤传》几乎相同,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成书于元嘉十六年(439)到元嘉十七年(440)的《世说新语》(从杨勇、范子烨说)(35)几乎一字不落地收录此条。按,《嵇康别传》早佚,此为残句,在此之前当有对嵇康临刑奏曲的描写。今检《世说新语》刘注,刘注多引《嵇康别传》,然于此条下不引,盖《别传》与《世说》所录略同,或《世说》径承于此,或与《别传》所据材料同源。 对于“雅音”说与《广陵散》说之是非,实在难辨。二者出现时间略同,行文一致,虽然记载“雅音”说之现存文献仅《魏氏春秋》一条,但如果简单地用“孤证不立”来否定前者,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由于史料有限,难以进行严密的、实证性的考证,下面仅提供个人的一点猜测。 《三国志》卷二十二裴松之注对《魏氏春秋》所记陈泰事的批语极有启发性,其云: 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36) 据裴氏所言,孙盛对于“记言之体”,“率更自以意制”,致“使辞胜而违实”。以此推“雅音”之说,只见于孙书而别无他见,盖亦属孙氏“意制”“改易”之类乎?至于改易的原因,窃以为即是“《广陵散》从此绝矣”的遗言与《广陵散》实未绝传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对于此点前文已有论述。古人多不明其理,而试图找到某种解释。如《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四引《幽明录》曰: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着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 又有袁孝尼窃听而记之说,(37)皆出于对“《广陵散》从此绝矣”的牵合。盖记述者因《广陵散》未绝而改作“雅音”也未可知。(38) 三、《嵇康别传》辑考 上文提到《嵇康别传》对于《广陵散》说有奠基之功,然此文献早佚,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同时后人多将其与嵇喜所作《嵇康传》混为一谈,兹作辑考,以是为辨。今从《三国志》裴注辑得二条,《世说新语》刘注辑得三条,《文选》李注辑得二条,《初学记》辑得一条,去其重复,共得五条佚文如下: 1.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说新语·容止篇》注) 按,《文选》卷第二十一《五君咏》注作“美音气,好容色”,无“而”字。(39)徐坚《初学记》卷十九亦作“好容色”,“土木形骸”前有“虽”字,“不加饰厉”作“不自饰”。(40) 2.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41)(《世说新语·德行篇》注) 3.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42) 4.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 按,此句有“称康临终之言”云云。“称”字殊不合理,若以之入正文,则为孙登述嵇康林中之余,与理不合。此盖裴转述之言,即《别传》称康临终之言云云。以此字明二句非联句也。故删“称”字。 5.临终曰:袁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就死,命也。(《文选》卷十六《思旧赋》李善注) 按,《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作“称康临终之言曰”,上已辨,称裴为转述之字,则“临终之言”亦为裴语,不从。“靳固”作“固”。 《嵇康别传》(以下简称《别传》),作者不详。嵇喜作《嵇康传》见《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所引《嵇氏谱》“喜为康传曰”云云。严可均《全晋文》所辑嵇喜《嵇康传》即袭于此。(43)遍检史料,嵇作从未有过《别传》之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注《别传》作者为嵇喜,(44)实误。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题作“嵇喜为《嵇康传》”,并列《别传》,明二者非一,(45)此当为定论。 《文选理学权舆》录《别传》于“人物别传”后。《晋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未见收。高似孙《纬略》录于“刘孝标《世说》”后,(46)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沈家本《古书目四种》亦有录。(47)以上各书除收抄录题名外未有片语。 《嵇康别传》最早被征引于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成书于元嘉六年(429),故《别传》完成时间最迟不过公元429年。六朝时,见诸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至唐,李善《文选》注、徐坚《初学记》皆有引。然考李、徐所引,皆不出裴、刘引句范围之外,故疑《别传》于唐时,甚至于隋时既已亡佚。宋代类书别出,更不见引录。比较稳妥的说法是,《别传》至迟亡于宋。 值得一提的是,《别传》与《魏氏春秋》有着某种“亲缘性”。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对比佚文3,我们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尤其是“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一句,近乎全同。“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是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化出,并非故有成句,此下再接“大将军”云云,遣词排句如此相同,绝不是偶然之巧合,可以断定,两个文本具有某种内在关联。再如《魏氏春秋》:“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由于缺乏实证,我们无法判断此种因袭是如何产生的。即便有材料证明二者出现时间的先后关系,我们也不能说后者一定袭自前者,因为存在二者史料来源相近之可能。 从内容上看,《别传》文辞雅丽,骈散相宜。尤其是“七尺八寸”“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材料。《世说新语》即沿用了“七尺八寸”的说法,(48)而唐修《晋书》,所取者更多。佚文1、2、4、5皆见取录。(49) 如果唐时《别传》未佚,《晋书》所见者为原文,非间接引录,则有理由相信,《晋书》中还保存着《别传》已佚之其他部分。 四、结论 经过上文考述,关于嵇康临刑奏曲之记载的源流与嗣承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当我们把三家所记各异的嵇中散临终情景之共同性从纷杂的史料中提取出来,重新置于整条文献嗣承的脉络中,甚至置于中古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此问题所指内涵绝不仅仅是嵇康临终情景之是与否,更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向度。从东晋时《广陵散》说、“雅音”说的出现,意味着嵇康临刑奏曲故事的基本定型,到《太平引》说对此事的敷衍,再至“广陵散”说为后世广泛接受直至成为定论,此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即是后人对嵇康临刑奏曲一事所保有的热度与情结。尽管三种书写的具体记载不一,但其透漏出的历史心态则为一致: 一为痛惜与哀婉之情。如《魏氏春秋》于“雅音”说后续云:“时人莫不哀之。”《晋书》本传云:“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即直观地传递出当时人的痛缅之情。 二则是崇敬向往之心。无论是《晋书》所记的“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还是《世说新语》描绘的“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都可以看出后人对嵇康当时风采的追慕与倾想。这种推崇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对其个体人格气度的肯定。《春渚纪闻》卷八云:“此真所谓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婴怀者。若彼中无所养,则赴市之时,神魂荒扰,呼天请命之不暇,岂能愉心和气,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时耶?”(50)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指出:“嵇康悲剧还纠结着当时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的种种复杂因素。”(51)故嵇康临刑的从容在一定程度上则代表了“道”在面对“势”的压迫时的坚守以及隐在的诗化反抗。其次,它更多地代表了人们对一种生命意识与价值向度的神往。当面对无法左右的外部力量给予的悲剧命运时转而回归内心,在对“雅量”(52)的保持与借助弹琴获得的“对现实的超越感,自由感”(53)中消解着死亡所带来的悲剧意识,完成着对于有限个体生命超越之期冀与努力。临刑而不失风度,不仅仅是个体之行为,而是中古名士玄化士风的一种集体表现。(54)《三国志》卷九记夏侯玄临刑之景:“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55)《晋书》卷八十四《王恭传》云其:“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56)《世说新语》引《晋阳秋》云:“嵩事佛,临刑犹诵经。”(57)《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苻朗曰:“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58)(注意,苻诗有“远同嵇叔子”句,则可明嵇康之死已为时人“经典化”,甚至成为效法的对象。(59))而临刑哭泣悲伤,神色有异,则被看作有失士人风范。《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载其临刑“悲涕流涟”,遭到外甥谢综的嘲讽:“舅殊不同夏侯色”,而“晔收泪而止。”(60)故而嵇康临刑自若,顾日影而弹琴,其所映射的不仅是独立个体对生死的达观态度,更蕴含了一个时代价值向度的投影。而嵇康之死显然参与到对此价值向度的构建与强化之中,并凭借其不凡的人格魅力与临终奏曲一事所蕴含的独特美学意味,(61)最终成为一种典范、高度仪式化、带有鲜明标识的文化印记。而上文所探讨的繁多不一的史料记载则是此种印记最好的明证,它们饱含了那个时代对嵇康影像的亲切记忆与理解,承载了对广陵余响悲情的哀悼与敬意。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核检与梳理,大致勾勒出三种关于嵇康临刑奏曲不同记载的出现与流传过程,最终认为唐修《晋书》所取的《广陵散》说相较其他两说更为可靠。对此问题作考,其所关乎的不仅仅是三种说法的是非,更可藉此一窥中古史料之流传线索,定伪辑佚,以供研究探讨的继续深入。 中古文献散佚较为严重,而在有限的史料中,对同一件事的记述常常存在多样的书写与表达,一些研究假定了某种记录的可靠性而径直采用,似乎它拥有被追问的豁免权,事实上,探求多种不同叙述的出现为什么成为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由不同的历史书写交汇形成的历史事件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角度与丰富的阐释图景,而生动的历史正凝结于多种可能的面向交错之间。同时,关于本文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与必要。如对《世说新语》、唐修《晋书》有关嵇康史料来源的辨析,《嵇康别传》的出现时间、可信程度以及重要性的探讨(对嵇康容貌的夸饰很可能源于此文献),对嵇康形象建构过程的追踪等等。这对魏晋时期许多问题的研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与启示。 (致谢:本文系笔者本科三年级学年论文删节而成,原由童岭师指导,谨志于此,以申谢悃) 注释: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7页。 ②《文选》本无“邪”字,“以”作“已”,“叹”作“叹息”,“也”作“矣”。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20页。 ③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06页。 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6页。《文选》所引略同,无“自若”,“援”作“自援”,无“叹”字,句尾多“时人莫不哀之”。 ⑤陈耀文:《天中记》,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394页。 ⑥吴士鉴:《晋书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20~903页。 ⑦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⑧沈叔埏:《颐彩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 ⑨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48页。 ⑩徐昂发:《畏垒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11)王德埙:《十八拍〈广陵散〉确系嵇康所作——答家浚同志》,《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02~105页。 (12)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13)洪亮吉:《北江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 (14)《嵇康别传》早佚,此句可见于《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 (15)宁稼雨《〈世说新语〉成书的社会氛围》,收于王杰主编《东方丛刊》2000年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16)刘鹗:《十一弦馆琴谱》,刘鹗:《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21~623页。 (17)王德埙:《琴曲〈广陵散〉流变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18~24页。 (1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11页。 (19)李善注所引曹嘉之《晋纪》对此记载也较为简略:“康刑于东市,顾日影,缘琴而弹。” (20)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6页。 (21)李昉等:《太平御览》,第2614页。 (22)参《晋书斠注》,第1517~1518页。 (23)熊明:《〈名士传〉〈竹林七贤论〉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81~685页。 (24)严可均《全晋文》有《竹林七贤论》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韩格平亦有《〈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原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亦收,增益七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28~634页。严氏未收此条,而韩文收。今考《太平御览》凡引戴书处,皆作原名(《竹林七贤论》),故疑《竹林七贤传》者当为袁书。然《太平御览》所引《竹林七贤传》亦有源于戴书者,如《太平御览》卷第三百六十六《目》引《竹林七贤传》曰:“王戎眸子洞彻,视日而眼照不亏。”而《艺文类聚》卷十七《目》则引作《竹林七贤论》。待考。 (25)王尽忠:《干宝研究全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6页。王氏最终考证结果为公元283~351年间。 (26)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生年可依张可札公元328年说,据程卒年考则推至328~329年,见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27)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第146页。 (28)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9页。 (29)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09~2510页。标点略有改动。《灵鬼志》早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据李建国考,此书成于晋末。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30)详见朱迎平《第一部文人传记,〈文士传〉辑考》,原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6期,又收于《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31)除朱迎平辑本外,周勋初亦有辑。见周勋初《张骘〈文士传〉辑本》,收于《周勋初文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3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599页。 (3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600~601页。 (34)周勋初:《张骘〈文士传〉辑本》,见氏著《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35)参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收于《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38~476页;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87页。 (3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642页。 (37)朱长文:《琴史(外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38)李昉等:《太平广记》,第2615页。标点略有改动。《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卷八百八十四引作《世说》,今本《世说》无此条。 (39)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1009页。 (40)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54页。 (4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2~23页。 (4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67页。 (43)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71~672页。 (44)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29页。 (45)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续修四库全书》第1581册,第22页。 (46)高似孙:《纬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页。 (47)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95页。 (48)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嵇康身长七尺八寸”条,第716页。 (49)参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9、1370、1374页。以上四条,《晋书》或全录,或半取。第5条由于亦有它见,故《晋书》未必录于《别传》,然1、2、4皆为《别传》所独有,故可断定。 (50)何远:《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 (5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52)范子晔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对“雅量”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直面生死,无忧无惧”即为其中之一。参氏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53)徐国荣在《玄学与诗学》中探讨了“琴”在“嵇康之死”中所代表的独特文化内涵,详见氏著《玄学和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148页。 (54)李根亮:《死亡是一面镜子: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死亡现象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3~196页。 (5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299页。 (56)房玄龄等:《晋书》,第2186页。《世说新语·方正》篇所记略同。 (5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65页。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附周嵩传》所记略同,见《晋书》第1662页。 (58)房玄龄等:《晋书》,第2937页。 (59)参郑伟《论嵇康与六朝临终文学现象》,收于胡晓明编《中国文论的思想与情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221页. (60)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8页。 (61)嵇康临终场景具有众多审美元素,充满了“旷延又凝重,残酷又优雅的悲剧美”。参康石佳《嵇康与〈广陵散〉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年。李建中《〈世说新语〉:魏晋名士心态录》文末亦言及此,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怎样读文学古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1页。标签:广陵散论文; 嵇康论文; 晋书斠注论文; 太平御览论文; 世说新语论文; 初学记论文; 思旧赋论文; 竹林七贤论文; 三国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