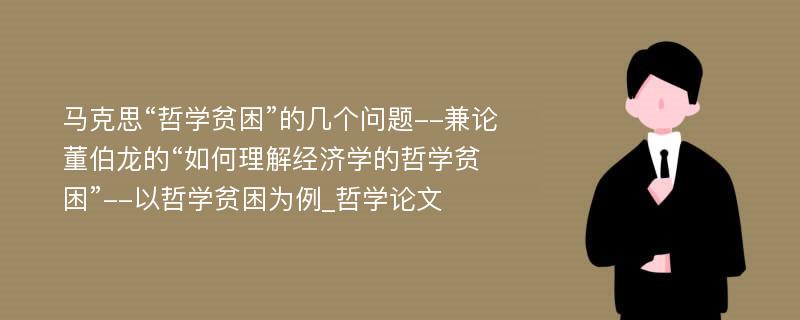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几个问题——兼评董必荣《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贫困论文,哲学论文,为例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3-0004-11
马克思十分重视写于1847年上半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过了三十三年之后,他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指出“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①该书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该书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哲学动态》2011年第5期刊登了董必荣的《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以下简称董文,凡引自该文的不再注明)一文,试图“解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表述的经济哲学思想”,令人注目。但是拜读之后却发现董文对《哲学的贫困》的理解存在不少问题,下面就其中的三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应该如何正确解读《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论战性著作。要正确解读该部著作,除了要了解写作该书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有关黑格尔哲学的知识外,还要了解以下三个材料:
首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该书分上、下两卷,出版于1846年,中译本由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该书的全称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但是后来人们都习惯以副标题“贫困的哲学”作为其书名。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他的批判。例如,为什么蒲鲁东要把他的书称之为“贫困的哲学”?董文认为,“对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蒲鲁东认为其中包含着某种‘财富的哲学’;同时,他跟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看来,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困。因此,他要研究‘贫困的哲学’。”其实,关于书名,蒲鲁东自己有一个说明:现代文明人贫困的唯一原因在于缺乏秩序。只要有了良好的组织状态,不仅可以延缓贫困的到来,还可以在人口与生产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均衡。“这个假定的证实对人类将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这样一个假定成为事实,那么,不论是人类的怠惰所造成的贫困,还是工业组织的弊病所造成的贫困,都可以无限期地避免;而我们的命运问题,世界命运的问题,将会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其实,这个重大的证明,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作出了,其副题《贫困的哲学》,本身就充分地表示了这个意思。”③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④,我们仅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再比如,《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标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董文说,“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其实是‘哲学’的代名词(下文均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那么,这一章的标题所说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这是望文生义,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在欧洲沿用了二千多年,但含意几经变迁,而且各个哲学家对它理解也不一样。黑格尔对他之前的形而上学都不满意,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⑤,强调“每一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⑥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第一章“经济学”一开头就提到了形而上学,“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渊博、最纯洁和最适于实践的科学。这个新的论点,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对我说来,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因此,谁要是研究劳动与交换的规律,谁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⑦综合黑格尔和蒲鲁东的论述,我认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标题“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和第一章的标题“科学的发现”一样,是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位自诩为发现了政治经济学“伟大规律”的“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的批判和嘲弄!
其次是马克思有关蒲鲁东的重要论述。一是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写给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长信,明确宣布要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这本“很坏的书”进行批判,阐述了即将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揭示了蒲鲁东思想怪胎的阶级根源:“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种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⑧二是《论蒲鲁东》,这是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当时蒲鲁东刚去世。这是一篇简要而全面评论蒲鲁东的文章,特别是对蒲鲁东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包括《贫困的哲学》进行了深刻的评析。这时的马克思已完成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看看他对十八年前同蒲鲁东论战的回顾,对于深入理解《哲学的贫困》是很有帮助的。三是《关于〈哲学的贫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帮助正在筹备成立的法国工人政党掌握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需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该文是马克思应法文报纸《平等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作为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的引言。在这篇简短的“引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对《哲学的贫困》和蒲鲁东作出了评价。在马克思一生的论敌中,多年以后还能继续回顾的不多,蒲鲁东就是其中一个。
再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关蒲鲁东的通信,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真实动机和主要目的。但是,董文对这极为重要的一点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经济哲学”的“确立”:“我们知道,要确立一门科学,既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还要为这种研究对象确立专门的研究方法。蒲鲁东恰恰未能做到这点。马克思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或经济学的哲学,应当从对象和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且不说在董文所作的有关经济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论述中,把一些不是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如“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生活,经济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不过是经济的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而已”;等等),其根本错误在于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说成是马克思为“确立”“经济哲学”这“一门科学”而同蒲鲁东展开的学术争论,这实在是偏离马克思太远了!我们看看恩格斯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1846.9.16)⑨“而这里的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1846.9.18)⑩“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1846.10.23)(11)而马克思的回应则是:“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12)即使在晚年,马克思也坚持认为:“为了给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13)
二、马克思如何批判蒲鲁东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说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14),后来在正式出版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时,把书名定为《哲学的贫困》,其用意是很清楚的。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蒲鲁东哲学的贫困呢?
董文的论证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系的观点,应当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进行研究,而不是满足于研究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是满足于研究几个方面之间的机械联系。二是发展的观点,应当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自身矛盾,从代表不同经济关系的阶级对抗中,而不是通过清除对立面的办法去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在这两方面,蒲鲁东同马克思的看法都是相反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董文从《哲学的贫困》中摘引了很多论述。表面看来这似乎不无道理,但细读之后,发现有三个不妥:其一是竟然对唯物史观只字不提。大家知道,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自己新的历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马克思1859年1月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著名“序言”中,曾回顾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强调唯物史观“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15),还特别指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6)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既区别于黑格尔又超越蒲鲁东的根本所在,离开了唯物史观,一切将无从谈起!其二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持非历史观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同他的经济理论一样,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同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应用和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精辟地阐述了其构建哲学体系所运用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但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该如何扬弃、如何将其“合理内核”应用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还在进行探索。这项重要工作的完成是在十年后的《资本论》第一稿、即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直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在董文中,1847年的马克思似乎是以一个成熟的辩证法大家的面目出现了,这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其三是又落入了“原理加例子”的窠臼。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著作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习惯于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引用若干个原理,然后从马克思著作中找一些段落来加以说明。例如,在我所看到的有关《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大量论著中,这种情况俯拾即是。这种“原理加例子”的方法是很省力气的,但对真正的马克思研究来说,毫无用处!不幸的是,董文又重犯了这个毛病。
马克思对蒲鲁东哲学贫困的批判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给了蒲鲁东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都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17)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以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制造了相关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8)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方法”所作的“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中,第二个说明最为重要,因为它阐述了唯物史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而“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19)
其次,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想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蒲鲁东接触黑格尔哲学的时间不长,而且是1844年在巴黎同马克思的争论中,多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但由于“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20)蒲鲁东就这么一点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可怜的本钱,居然想在法国人面前卖弄一番,“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21)但结果却是:作为黑格尔哲学糟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他全盘接受过来了,而作为黑格尔哲学中精华的辩证法,却被他歪曲甚至是阉割了。蒲鲁东以黑格尔的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为前提,套用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公式,企图推演出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22)不仅如此,蒲鲁东最后还搬出天命来,用天命作为火车头,拖着他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他在《贫困的哲学》的第八章,全部用来写天命,题目就叫“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问题的解答”,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更可笑的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发挥”,把每个经济范畴都分为好坏两个方面,这就构成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23)十八年后马克思在评论这件事时还说:“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24)
再次,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含糊不清的”,(25)远在他所批判的经济学家之下。蒲鲁东自称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但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他一个也看不上眼,在《贫困的哲学》第一章“经济学”中他写道:“我应该现在就指出,我并不把近百年来人们正式名之日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自相矛盾的理论视为科学。……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让·巴·萨伊所留传给我们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遭到否定,而且半个世纪来我们亲眼看到它停滞不前。这是本书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26)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贫困(这也许是其著作名称的另一层含意),结果使政治经济学这片辽阔的空地上到处堆积着准备施工的材料。工人们急于动手干活,但却无所适从,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建筑师不见了,也没有留下图样”,“这样一来,建筑社会大厦的事也就无人过问了”,工地一片混乱,那些经济学家“历史的和叙述的方法尽管在当初认识事物时颇为有效,可是以后就毫无益处了。”(27)于是,蒲鲁东也就以政治经济学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首先在哲学方法上实行大胆的“革新”。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哲学方法一点也不比他的前辈高明,实际上是十分的贫困:第一,严重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坑。“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又“把这些范畴看作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28)第二,缺乏历史知识,又不做深入研究,当他无法解释历史发展时,就开始胡编乱造。蒲鲁东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马克思列举大量的史实予以揭露,如:他不懂得分工问题,既没有提到在德国从9-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谈世界市场;不懂得机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尤其荒谬的是把机器当成和分工、竞争、信贷等并列的经济范畴。……总之,“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助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29)第三,蒲鲁东企图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来构筑政治经济学大厦,却是破绽百出,以失败告终。黑格尔哲学体系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是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而在蒲鲁东那里,经济范畴的排列居然成了一种拼凑起来的脚手架。“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30)他那两卷本的著作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31)第四,蒲鲁东的哲学实际上是典型的二元论。蒲鲁东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不想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变社会现实的基础。他一心想调和矛盾,企图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各种社会对立平衡起来。“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32)这是蒲鲁东哲学贫困的深层原因,也是他政治和学术生涯悲剧的秘密所在。
三、如何实现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
使经济学和哲学内在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已逐渐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识。董文以《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需要既懂经济学,又懂哲学,这要求研究者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决不能浅尝辄止,满足经济学和哲学的表面词句的‘结合’;更不可抱投机心理,一方面拿半生不熟的经济学吓唬哲学家,另一方面拿半生不熟的哲学吓唬经济学家。”遗憾的是,笔者发现,董文正是犯了其所批评的这种毛病。
先看董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错误理解:
其一,不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并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马克思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久,还是个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异议者。《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折,他已赞同并高度评价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1857-1858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转折,不仅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变革,而且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初步构建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体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马克思继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自己的著作定名为《资本论》,出版了第一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逝世,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理论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所以,当我们具体分析马克思某一经济思想时,一定要有历史的观点。董文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在谈到《哲学的贫困》中劳动的“抽象”时,居然引证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有关论述,时光跳跃了二十年,这是很不合适的。又如,董文谈到,“马克思不仅从总体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发展过程和灭亡条件,而且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贯穿了辩证法。以‘价值’问题为例。”如果讲到“价值问题”的细节,那么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到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再到1873年的第二版,马克思都作了很多修改,即使在他晚年,还对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价值问题”作出重要评述。董文用了很多篇幅,批判蒲鲁东“无法理解价值实体”,而马克思则要“确立价值实体即抽象劳动的地位”,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对蒲鲁东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即使马克思当时也未意识到这一点。劳动的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建立起来的。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33)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引用和评价应持此科学态度。
其二,不了解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董文说,“劳动价值论其实并不是马克思创立的,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并不把‘价值’看作永恒的现象,而将之与交换价值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交换价值的历史发展又与劳动的抽象化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正是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入手,才真正弄清了价值的主体本质”。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但也存在重大缺陷。他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的性质和价值的性质,因此不能完整而科学地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说在他们那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是很不严谨的。第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一是从“经济的具体物”——商品中分析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二是劳动二重性是首先由马克思批判地证明了的,它成了理解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三是第一次对价值形式作了全面阐述,揭示了货币的产生和本质;四是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五是实现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无缝对接”,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成为一个具有逻辑一贯性的严密的有机整体。董文对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所作的重大贡献的概括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至于“马克思正是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入手,才真正弄清了价值的主体本质”,令人不知所云。此外,董文还提到,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理论“这仅仅是马克思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层次”,说明其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还是一知半解的。
再看董文对马克思哲学的错误理解:
其一,董文说:“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辩证法,二是逻辑辩证法。后者是前者在思想中的抽象表现。”请问:马克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表述?马克思论述辩证法最详细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明确宣布《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4)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应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还论述了辩证法的精髓和批判的革命的本质。董文这里所说的历史辩证法和逻辑辩证法,实际上是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一个原理,即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问题,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其二,董文认为,“马克思承认辩证法是生命力的体现,但并不认为它仅仅表现为理性的生命力,或绝对精神的生命力,而认为它是‘现实的个人’的生命力”。请问:马克思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承认”?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现实的个人’的生命力”,那它与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和蒲鲁东所发明的“新理性”又有什么区别?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的论述吧:“我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进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5)
其三,董文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层次。”这暴露出董文既不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不了解马克思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应用的辨证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36)相对于商品或价值来说,资本是个具体得多的范畴,按照马克思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资本”只有在第一卷的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时才出现,然后逐步展开。针对那种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而产生的误解,马克思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37)至于剩余价值理论,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总称,恩格斯把它与唯物史观并称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怎么在董文那里就成了“马克思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层次”呢?
其实,如何实现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结合,我们从《哲学的贫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明确结合的目的,不仅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从经济学和哲学两方面批判蒲鲁东,就是为了揭穿他的伪科学面目,清除其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为正在组织为政党、开展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提供新的理论武器。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其次,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之所以能把蒲鲁东批驳得体无完肤,之所以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就是因为马克思掌握了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38)
再次,“结合”要以对经济学和哲学的优秀遗产的科学批判和继承为前提。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始于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以后,他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并作了摘录和笔记(遗留至今的有《巴黎笔记》共九册)。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继续政治经济学研究,研读了大量经济学文献,其中包括历史上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包括同时代各派经济学家的著作,同样做了摘录和笔记。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打算写一部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出版,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利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劳动价值论上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为马克思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能够娴熟地运用辩证方法,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复次,“结合”要和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中不断地汲取养料,保持理论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马克思在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就投身于工人阶级的火热斗争中去,他深入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马克思曾这样热情地写道:“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39)在布鲁塞尔期间,为了实地考察英国的经济状况,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实际资料和文献资料,并与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马克思还于1845年夏天,在恩格斯陪同下,到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作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对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预见,既是他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结果,也是他亲身参加生产和革命实践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马克思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40)
最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是个不断创新、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开始了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结合,其重要成果是虽不成熟但已潜在地具备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基本要素的异化劳动理论。1845-1846年的“结合”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产生;1847年的“结合”产生了不朽名著《哲学的贫困》及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堪称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共产党宣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结合”产生了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规律。在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中,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境地。马克思不无自豪地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41)列宁非常重视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和哲学的有机结合,《哲学笔记》中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还强调要组织“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因为“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的非常成功”(42)。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教导,并努力躬行之。
注释:
①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8页。
③(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中译本,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3页。
④(20)(24)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616、618页。
⑤(德)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9页。
⑥(德)黑格尔:《自然哲学》,中译本,薛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⑦(26)(27)(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中译本,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38-39、60-6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页。
⑨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9.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版,第9页。
⑩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9.1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11)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10.2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13页。
(12)(17)(29)(32)马克思:《致帕·瓦·安年柯夫(1846.12.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531、536、541页。
(13)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8页。
(1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533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4页。
(18)(21)(22)(23)(25)(28)(30)(3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137、144、141、144-145、137、146、145页。
(33)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7页。
(34)(35)(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4、8页。
(37)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38)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7页。
(40)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4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7.3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42)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短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标签:哲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哲学家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资本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蒲鲁东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