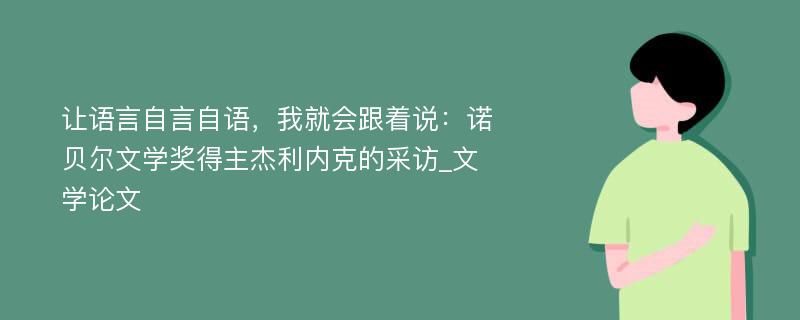
让语言自己说话,我紧随其后——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奖得主论文,说话论文,语言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根本上来说,语言的挑战就像用羽绒枕来击打水泥墙。如果人们感到无法用语言来做什么,出现失语状态,那就该停笔,如果我输了这场战斗,如果语言最终离我而去,那我当然就会封笔。
2004年10月7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次日,这位极度敏感、患有人群恐惧症的作家即宣布,由于健康原因她将不会亲赴斯德哥尔摩出席12月10日的颁奖仪式。代她领取诺贝尔奖的,是柏林出版社资深编辑施密特先生。
施密特先生作为编辑,从1970年代起就一直陪伴鼓舞着耶利内克的文学创作,是她深为信赖的挚友。几年前,当施密特从罗沃尔特出版社易职到柏林出版社时,耶利内克也随他改换门庭,成为柏林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我的老师、汉堡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克里本先生与施密特30年前师出同门,共同攻读日耳曼文学博士学位。通过克里本教授的穿针引线,施密特先生于2月底为我们联系上在维也纳深居简出的耶利内克女士。
获奖后的她继续埋头于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新小说将更侧重于语言实验。当时她还在修改一个新剧本,因为城堡剧院打算于3月进行首演。虽然如此,她仍然答应给中文版《逐爱的女人》作序。但考虑到她时间和工作上的压力,我们建议不如采用对话的形式,这样能有的放矢,或许也更直接生动。
耶利内克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采访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准备后如期进行。3月14日,我们把9个详细的问题提交给施密特先生。3月18日清早,打开电脑,邮箱里躺着一份来自维也纳的邮件,是耶利内克对我们问题的逐一详尽回答。匆匆一遍读下来,仿佛她就坐在你的对面,没有任何的掩饰。感情激越时大小写的颠倒和单词的遗漏,平和时行文的工整和缜密,字里行间流露着她的情绪。
施密特先生告诉我们,耶利内克女士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放下其他一切工作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甚至置她即将首演的新剧于不顾。事后,她对施密特先生说,以后她不再接受任何此类形式的深度访谈,因为不由自主的投入和用心让她精疲力尽。
一场穿行于维也纳、柏林、汉堡和南京的采访,传递其中的是信念和友爱,就像耶利内克女士不懈地在她的书中做着抗争,而在写给我们信中却低调承认:“世上有如此多的苦难,我们所能做的极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也正是诺贝尔精神的一部分?
●您于1946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属于战后一代,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战后重建、经济恢复,六十年代的冷战、青年学生运动和女权运动,还有当时的越战,这样的成长经历与您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正义感有一定的联系吗?
耶利内克:我父亲的家庭是犹太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小就赋予我一种责任,与所有的权威和我所见的法西斯倾向,特别是种族主义倾向做抗争。这样的责任感使得我以后一直关心政治。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家族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交给我了,可能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不懂其真正含义。但我始终知道,我必须这样做。
●1975年的《逐爱的女人》使您一举成名,这部早期作品的基调和语言风格让我想起德国二三十年代的一位女作家可因和她的《纺丝女孩》,在冷峻尖刻和嘲讽后面是一种深深的忧伤和对人的关怀。您曾在1980年的纪念文章中对这位几被遗忘的女作家表示了深切的敬意,并赞扬了她面对当时横扫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来的毫不妥协的心灵和彻底的勇气。您自己一直在和人类的历史遗忘症做着不懈的斗争,她对您来说是否是一种鼓励?您能告诉我们哪些作家对您产生过影响吗?
耶利内克:可因关注的是1920年代城市贫民中的职业女性,比如小打字员,她们梦想着终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于是她们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为自己找一个所谓条件好的男人,目标是拥有他,从而拥有好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年轻的职员小姐还是非常自主的,她们有自己的头脑。在《逐爱的女人》中我描写的是农村和城里的贫民。她们不是职员、秘书,而是农民的女儿和工厂女工。我有意识创造一种封闭的环境,没有出路,这一点很重要。我大部分的小说都以农村为背景,因为人不那么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在那儿人不得不生活在现成的固定的社会关系中,直到悲惨收场。两部小说里的女孩都试图通过婚姻来获得好一点的生活,可是什么是“好一点的生活”,本身还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就像自然科学通过实验来证明一个道理,我想借此表明的是,如果女人不自己来掌握自己,而把自己的命放在男人手里,那一切就像是六合彩,全凭运气了。
可因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经受了考验,而且非常出色。由于历史原因,我没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作家是1950年代的维也纳派作家,他们致力于语言实验,并重拾被纳粹时代割断的“后达达主义”传统。但也有女作家像玛丽路易丝·弗莱斯纳,或者罗伯特·瓦尔泽。当然还有卡夫卡,他把内容和美学形式的结合发挥到极致,千变万化。我从来没有对只有内容,却没有相应的美学形式的东西产生过兴趣。
●您一再强调您不是想和男性作斗争,而是要和有形无形的压迫女性的社会制度与理念做斗争。那是否这就是在您的笔下,就像在《逐爱的女人》中,不仅男性多为负面形象,女性形象也同样灰暗丑陋的原因?有些女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惰性,害怕,意志薄弱等等而去适应甚至客观上强化这种社会,您觉得她们自身要为她们的艰难处境负责吗?
耶利内克:我想打破的是父权文化和它的男性崇拜。我们所拥有的美学标准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必须服从它,我也如此。我以写作来反对这种不公平。没有可以让我依靠的女性价值体系。女性必须屈服于男人的评判,不管是她的身体(女人必须年轻漂亮,必要的话,通过整容手术来改善外形,所谓战胜自然),还是她的智力成果和艺术创造。女人还没有形成她们的标准体系,即使一半多的读者是女性,但女性创作的评论员仍然是由男性来充当。总有一天,女性不得不听命于这样的评判,她们无路可走。
在我的作品中我一直谴责女人的同流合污。如果女人之间的团结,结果对男人比对其他女人更有利,如果女人利用她们的结盟来毁灭其他女人,让她们心灵死亡,那么在我的眼里,这种女人就是魔鬼,是可鄙可恶的。不惜手段巴结讨好男人就是我想批评的,只要我看到,如此的巴结讨好!
●您说过,您写的是色情文学的相反,您的文字是用来戳破欲望。人们在您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丑陋的性、残酷的恶、虚伪的美和愚蠢的麻木。那么可以把您对世界的阐释模式归纳为“性、强权、暴力”吗?
耶利内克:我原本想尝试写女性色情文学,就是与巴塔耶《眼睛的故事》相似的东西。但最后我却发现世上只有用男性语言写的色情文学。女人展露自己,男人驻足观看。在这个过程中,女人不再拥有个性,千人一面。而男人在色情文学中总是主体,女人却失去主体地位。在由女人创作的色情文学中(我所指的仅是纯艺术色情文学,而非商业性的!),几乎没有成功的,除了保利娜·雷阿日(笔名)的《O娘的故事》,她把女性的虐恋作为天生的来写。小说是写给她的情人的,她想取悦于他。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把色情作为暴力的实现来解构。《欲望》就是把人们最私密的,也就是性,作为男女之间的权利结构来分析,即黑格尔的主仆关系。
●您一直强调,语言是您艺术创作最有效的工具,是您作品的主角、灵魂,语言本身的力量比情节更具说服力。但在您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您传达的是一种对语言的绝望和否认。您是否一直处于这种对语言的矛盾情结中?失语状态将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耶利内克:可能我这场和语言的角斗是持久的。我依赖于它,可是它还没到我笔下,就已被蹂躏,被弯曲,被扭曲成庸俗笑话。而我最看中的恰好是庸俗笑话,也就是最廉价的笑话和文字游戏,它们允许我采取一种悲悯,热烈的,而非冷淡的(因为冷淡的悲悯很容易僵化为廉价媚俗的东西),必须是一种投入的悲悯,政治上也如此。在这场角斗中,有时语言占上风,有时是我,就在我把它变为我的工具的时候。正如所说的,对语言的怀疑使得奥地利的文学传统和德国的有着根本的区别(和以前的民主德国区别更大,他们特别关注的是内容)。为了能承载生活中实质的东西,语言必须一直处于发展中,作为计划或忍受。从根本上来说,语言的挑战就像用羽绒枕来击打水泥墙。如果人们感到无法用语言来做什么,出现失语状态,那就该停笔,如果我输了这场战斗,如果语言最终离我而去,那我当然就会封笔。
●您曾在访谈中谈到翻译您作品的难度和作品的不可翻译性。您甚至认为最好的翻译也许出自于作家之手,也就是说,您欢迎他们在译作中添加自己的东西甚至某些新的创作。那么您不担心在转换过程中,您原本所要表达的东西被稀释或改头换面吗?
耶利内克:这种稀释或改变一直都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如果想减少由于翻译带来的损失,那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尽可能地少保留。因为我发展了我自己的语言,它不单单是内容的载体,那我必须得一开始就预料到它的不可翻译性。通常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奥地利人(以奥地利德语为母语,因为我经常使用维也纳地方方言)为主译,然后由母语为目标语言国的人来作修改,这样的配合最可能取得成功。我非常困惑我的作品能在国际上获得种种承认,我经常会问自己:读者到底读到了什么?如果他们只读到我作品的翻译,那他们根本不会看到我写的是什么。这一切让我作品的译者很沮丧,他们常常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绝望。
●《美好的、美好的时光》成书于1980年。您当时是在何种心态下去写这本书的?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耶利内克:《美好的、美好的时光》的故事本身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发生于1960年代中期。我把发生的时间前移到1950年代末,因为我想展现的是年轻人的典型境遇和他们的社会阶层状况。就是在1960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登台,青年学生运动开始,消费主义也逐渐抬头(虽然在1950年代已初见端倪,或者说是在二战后),我写这本小说也来自于我对德国“赤军旅”的政治恐怖主义的经验。我想对恐怖主义刨根问底,找出其根源,最后在小说中一直追溯写到了这个青年团伙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出生于大资产阶级的索菲拥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对她来说,以政治理由为借口的犯罪行为是一项娱乐,一种刺激。工人子弟汉斯遗失了他的阶级立场,他没有团结的能力。安娜和赖纳是小市民家庭的孩子,他们悬在真空中,所处的危险最大,因为他们无人可靠,无处生根。他们听命于他们的自私和个人无政府主义,完全的施蒂纳准则:惟一者(自我)和所有物,最后导致的是灾难。
●您认为您的创作有时段性吗?随着岁月的变迁,您的创作在题材上或者手法上有侧重点的转移和改变吗?
耶利内克:我想这么说,首先在我对这个世界了解还不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现在有多么多的了解),我写的是通俗神话、杂志小说、电视上的家庭剧系列等等。这以后,特别是在《逐爱的女人》中我开始解析现实,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展开,然后是两部比较“现实主义”的小说:《美好的、美好的时光》和《钢琴教师》,两部相比而言最容易翻译的作品,它们都有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故事情节。从这以后我又破坏了这一切,在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所谓的不可翻译性正源于此。现在我让语言自己说话,而我紧随其后,就像上面说过的。
●中国读者很高兴能有机会读到您的作品。您是否担心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妨碍您作品的接受程度?或者您认为您的作品是以我们人类的基本矛盾为中心,因而使得文化差异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耶利内克: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中国文学甚至影响过我(我所了解的很少,而且主要是关于“文革”的)。可惜我无法讲出作者的姓名,因为我记不住任何姓名,不管是什么语言的。但我甚至在我的《死者的孩子》中偷偷地引用了一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话。我很喜欢这样,所谓偷一个句子来,就像人们为一座大厦奠基,我就把这般那般的句子砌进去。在《死者的孩子》一书中,我就把那个作家的两三句话砌了进去,虽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但他所写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