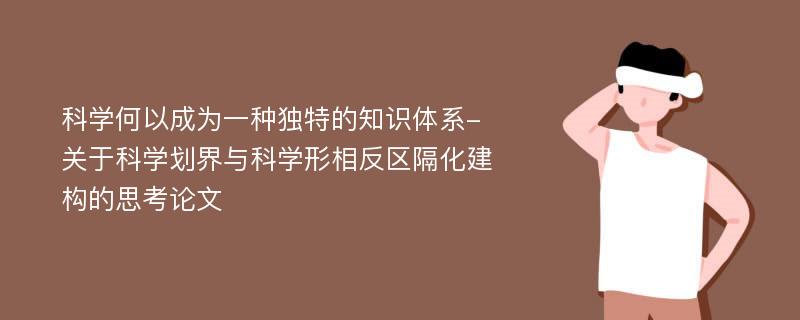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科学何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
——关于科学划界与科学形相反区隔化建构的思考
刘翠霞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对科学是如何与其他事物区隔开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相的知识体系这一问题的解答,与划界问题及其争论密切相关。从科学史发展历程来看,认识论上的“真理”诉求、分工建制上的“公正”配置、主体地位上的“精英”身份、伦理品性上的“美德”精神、功能效用上的“福音”力量构成了正统标准科学的基本形相。由于划界标准中存在一元还是多元、刚性还是弹性的巨大争议,划界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相对主义者因此主张通过否认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而取消划界问题来消解这一难题。这种相对主义的处理方式以极端化的形式瓦解了划界问题的意义价值。边界运作理论通过回归实践以及对研究科学形相建构过程必要性的强调,打破了标准论与消解论两种方案之间的对立。从边界运作理论的角度看,经由对自我的正当化、对异己的污名化、对问题的免疫化、对知识的科普化、对他者的涵摄化等一系列边界运作策略的运用,科学的标准形相得以被建构;这五种策略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统一性的整体运作机制,在区隔与反区隔的张力空间中共同建构和维系着标准科学的基本形相,其中既有通过边界区隔对这些形相的正向塑造与逆向确证,也有通过边界防御对形相偏差的反驳与辩护,更有通过边界跨越对其良好公众形象的谋划与强化。
关键词: 科学标准; 科学划界; 科学边界运作; 科学公众形象
近代科学作为人类知识观念更新与社会格局变迁的产物,其含义与指称的界定确立以及范畴意象在生活世界中的表征呈现,是诸多学者关注思考的重要议题。围绕“科学是什么”(注重定义)或“什么是科学”(注重说明)的问题,从科学本质的分析入手,以某种标准为依据,区隔出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界限,从而“锁住”科学的领地并保持其纯净性,是大多数研究就此议题采取的主要思路,其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即是“划界问题”的分析进路。这种探讨着眼于理想的“规范科学”,其旨趣建立在对理念世界中的科学的先验判定基础之上,意欲寻求隐藏在深处的撬动科学诞生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旦宣称找到支点,确定了区隔标志,划界问题便迎刃而解。然而,现实的科学在运行中总是衍生出比拥有完美逻辑连贯性与统一性本质的科学更复杂生动的形相,其对“本质支点”的偏离、反叛、甚至破坏无处不在。理想科学对支点的依赖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使其对科学的理解日益走向僵化封闭。从表面上看,对科学的探究从本质转向“本质直观”的形相似乎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退步”;然而,从理念世界回归到生活世界,解释科学形相的建构过程及其动力学机制,不仅能够打破本质思维的固化困局,洞悉明见科学的流变性与社会性,而且对于辨析批判日益“高级”的伪科学,捍卫真正科学的尊严和地位,能够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论据。近年来随着边界运作理论的兴起,将划界问题从本质标准的探寻引向对标准的创造建构等具体实践的剖析,通过对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区隔标准的社会建构性与流动性的揭示,为我们重新解读和反思科学的本质及其形相的建构过程开辟了一条极富想象力的路径。
一、标准科学的性质及其基本形相:从“科学”到“科学的”
科学的性质是科学元勘的起点和基础,科学哲学史以及科学学的相关研究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科学性质的理解辩护史。几乎每一位以科学作为分析对象的学者都会首先就科学的性质展开审慎的思考,或遵从某些不言自明的默会性的预设,以此作为立论出发点构造阐释自己的观点或理论体系。尽管关于科学的性质,有“知识系统说”“人类活动说”“社会建制说”“研究方法说”“精神气质说”“生产力说”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大都将“客观真实准确”视为科学性质的正统原型,以此为依托对传统科学观进行批判或辩护。虽然当今社会风险与利益的嵌入使得科学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准确性屡受质疑,但由于经验图式的前见惯性与路径依赖的认知经济性,科学的“客观真实准确”性质已经以本质直观的方式深深扎根于人类的思维秩序中,这些性质最终被统合在一起,便成了具有价值评判功能的作为形容词的“科学的”,这一语词以更为简洁的形式替代了科学具有的“客观真实准确”性,也使科学实现了从专名到摹状词的跃迁,“科学的”或“科学性”便成为衡量几乎一切事物好坏的重要指标。于是,在先验的逻辑推理与心智联结的助推衍射下,认识论上的“真理”诉求,分工建制上的“公正”配置,主体地位上的“精英”身份,伦理品性上的“美德”精神,功能效用上的“福音”力量,便成了科学在生活世界中的基本形相。
具体说来,科学作为一种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客观反映实在本身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其主要的目标就是生产普适性的“真理”,这些真理产品有别于一般常识、宗教信仰或其他形而上学观念,是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威标志,拥有认识论的优先性。而要确保科学的真理面相,科学共同体在相关资源的分配以及评价体系的设计上则需保持公平中立的立场,摆脱政治经济利益及情感倾向的限制,使科学建制内的合作竞争能够均衡有序地进行,这也便造就出科学如同法律一般的公正形相。同时,科学作为知识权威,其持有者必须是经过长期严格的专业教育训练并获得了从事科学研究资格的人,其职业地位身份不同于普通大众,在知识文化技术领域以及某些重大决策面前拥有更高的话语权,是公众认可并遵从的社会精英。而这些精英必须具备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无私宽容、理性怀疑等基本的科学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现代公民意识,这样的集体精神肖像使科学(家)超越了纯粹知识的范畴,具有了伦理道德上的典范榜样意味,成为“美德”的化身,在此意义上,“美德即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命题之一。不仅如此,科学凭借其强大的经世致用性,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因而也被誉为人类社会的“福音”,实现了人类诞生以来的诸多梦想,突破了自然给予人类身上的诸般局限,创造了种种神话般的奇迹,科学也因此被颂扬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成为公众心目中“美好”与“希望”的代名词。
而刘德平教授研发的“桑叶苦瓜糖果压片”优选天然桑叶、苦瓜、枸杞、菊苣、乌梢蛇等,从中成功分离出高能生物活性降糖生物素,并添加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经过科学配伍后加工而成。该产品通过滋补肾阴、滋养五脏,恢复失调的脏腑功能,使机体内五脏平衡、气血平衡、阴阳平衡、元素平衡,并使植物中的活性多肽及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直接激活胰岛受体细胞,从而激活和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使胰岛素分泌增多,使各种糖、蛋白质、水、电解质紊乱得到全面改善,使五脏器官能够正常吸收利用摄入的糖分,血糖从而自主下降至正常,逐渐摆脱服用降糖药的恶性循环,将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并发症自然消除。
当然,上述科学的基本形相——真理、公正、精英、美德、福音——并非科学全貌的摹刻写真,它是关于科学的理想期待与现实表征、应然规范与实然描述之间若即若离、混同作用的产物,是认知上的“自我实现预言”在“本该如此”与“就是如此”之间来回滑动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科学合法性的依据与表现,同时也打造出主流科学、标准科学、正统科学的形相原型。
1.划界问题何以成为难题?
二、科学与非科学的区隔:划界问题的提出及其标准的争议
鉴于某些非科学、不科学以及伪科学(1) 关于非科学(non-science)、不科学(unscientific)、伪科学(pseudoscience)的区别,斯坦福哲学辞典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非科学的外延最广,是指不属于科学的,系偏中性的术语;不科学,是形容词性的,侧重指某些失误或错漏;伪科学则是带有是非善恶判定夹杂其中的贬义词,是带有欺骗性的假科学。有学者强调在解决划界问题时应该注意理清解决的究竟是科学与三种中的哪一种的划界。本文着眼于一般性的分析,使用周延性较广的“非科学”一词,将不科学、伪科学等也涵盖其中。 的危害及其对科学形相与名誉权的侵犯,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划清界限,为科学正名进而确保科学知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维护科学的“真理、公正、精英、美德、福音”的美好形相,成为科学家及相关研究者首先必须应对的难题。因此,当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提出“划界问题”之时,便立即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也使得划界问题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四大哲学问题之一。
划界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其“具有重大的健康、安全、教育、政策与正义后果”(2) David B. Resnik,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1(2), 2000, pp.249-267.。它一方面是公众日常生活实践明智化的需要,通过清晰的划界标准的区隔,公众将会获得更加审慎地判别科学与伪科学差异的能力,比如在健康养生或疾病治疗的过程中,能够辨别区分何为可靠有效并值得信任的知识,何为妄言可疑与哗众取宠的花招辞令,从而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采取有效的行动确保个体生活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治、经济、教育、非营利组织和机构实现决策科学化与管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划界标准的确立使相关部门能够在科学的方法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的辅助下,在合理地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过程中,整合优化各种资源,对可能面临的风险做出准确评估,排除伪科学或打着科学旗号的伪专家的干扰,避免决策错误,降低重大决策失误发生的可能,以达成组织的目标并完成相应的社会使命。此外,划界问题对于捍卫科学的独立自主性及其知识权威的身份地位也是必需的,只有摆脱常识、形而上学、神学以及原始思维的影响,拒绝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介入,坚持自身对客观真实准确的知识的追求,严守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明确界限,科学方能在与“他者”的区隔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获得傲视其他一切知识信念的资本。
本研究通过可控的大棚盆栽试验,采集了2种典型土壤(黏土和砂土),研究了不同土壤外源压力条件对甘薯不同生育期生理生态形态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结果:
然而,由于科学起源的模糊性和发展谱系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观照视角的差异,关于科学的划界标准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区隔界限存在诸多争议。早期研究大都坚持一元标准,但这些一元标准的严格性并不同,考虑到一元标准容易陷入绝对武断的困境,后期研究大都力主多元标准,当然多元标准的稳健性和弹性也有诸多区别。概括而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划界标准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严格的一元标准,宽松的一元标准,刚性多元标准,弹性多元标准。
1.严格的一元标准
正是在基瑞恩边界运作理论的启发下,诸多学者开始使用这一范式策略分析相关研究领域的问题。比如,借用基瑞恩的观点和方法,Ramírez-i-Ollé对2009年“气候门”事件中科学家及其共同体为确保科学权威性而运用的修辞谋略进行了细致的探讨。面对公众对气候科学的质疑,气候科学家们运用排除、保护、扩展等不同的边界运作形式向公众揭示气候科学的共识性、非社会性、开放性等特征或诉求。比如将持异议者视为“盲目的拒绝主义者”或“异教徒”(排除),诉诸共识性知识与尚未达成共识的知识之间的分工使气候科学的某些领域免于受指责(保护),以此维护气候科学的共识性诉求;利用独立于社会的声称保证自身对研究议程与资金的控制权与自主权(保护),控诉非科学家的批评和干预是出于政治偏见和既得利益的考虑(排除),以此确证气候科学的非社会性;基于开放科学具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增加科学公共资源因此有了正当的理由(扩展),科学的自我纠错能力及其公有主义观使其能够免于外部的干预(保护),所以气候科学的开放性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29) Meritxell Ramírez-i-Ollé, “Rhetorical Strategies for Scientific Authority: A Boundary-Work Analysis of ‘Climategate’, ”Science as Culture ,24(4),2015, pp.384-411.而刘思达则引入社会学的互动论和过程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基瑞恩的边界运作思想,将边界运作的形式概括为边界制造(boundary making)、边界模糊(boundary blurring)、边界维系(boundary maintenance)三种,并指出边界并不仅仅是由处于争议两端的两个行动者相互作用建构出来的,诸多外在的行动者和力量也会干预建构的过程,从而强调了边界运作中“交换”的重要性,并借用边界运作与交换理论对中国30年来法律职业的产生、分化和碎片化进行了阐释说明。(30) Sida Liu, “Boundary Work and Exchange: The Formation of a Professional Service Market, ”Symbolic Interaction ,38(1), 2015, pp.1-21.
当然,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意识到,由于时空的广延性与无限性带来的归纳难题的存在,经验证实是渐进积累的过程,完全的证实是不可能的,因而将划界标准调整为“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强调一个命题并不需要即时彻底明确地被证实,其只要具有在逻辑上得到经验证实的可能性,就是科学的。而为了进一步回避归纳问题,应对科学命题检验中的经验窘迫性难题,后来的支持者(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者)又用“可确证性(confirmability)”或“可检验性(testability)”,甚至用“概率确认”代替“可证实性”标准,强调不可能有绝对的证实,只可能有逐渐的确证,认为至少潜在地能够借由特定的观察或实验方法,用经验证据来检验(而非证实)的,才是科学的。(4) 参见卡尔那普:《可检验性和意义》,《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9-81页。
而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则认为,逻辑实证/经验主义尽管想尽各种方法修补经验证实原则面临的归纳困局,但事实上这一困局在逻辑上是无解的,科学作为全称命题,对其的经验证实相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总是暂时的、微乎其微的,而且很多非科学的信仰以及伪科学都可以获得一定意义上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要摆脱归纳难题,就要反转思维,依托演绎逻辑(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用“证伪”替代“证实”作为划界标准,因为根据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其“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是能够和单称陈述相矛盾。……从单称陈述之真论证全称陈述之伪是可能的”。(5) 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16页。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单称陈述出现的个别经验事实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科学的全称命题,但是却可以否证它。因此波普尔主张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标准,承认科学的可错性以及科学史发展的冲突性与革命性。尽管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两种划界标准截然对立,但它们其实都是建立在还原论与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知识与逻辑真空”中探究科学的性质,否认科学的社会性和价值负荷性,而将它们视为非科学的显著特征,意在以此为科学的核心形相“真理性”构筑起坚实牢固的防御堡垒。
2.宽松的一元标准
与严格的一元强标准不同,这种类型的划界标准更柔韧灵活,回归到作为人类活动的科学研究的日常世界中,不再完全遵从抽离于人之外的经验性原则,而是着眼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特征,加入了对某些社会性因素的考量,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隔界限留下了些许转圜的余地和商讨的空间。比如库恩将划界标准归之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心理信念和认可,指出波普尔过分夸大了证伪的作用,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不完美的,如果一出现反例证伪就拒斥它,那么所有的理论都该被拒斥”。(6) Asis Kumar Chaudhuri,“On Science, Pseudoscience and String Theory, ”http://arxiv.org/pdf/1606.04266.pdf, 访问时间:2018年9月10日。 因而证伪标准只适用于革命科学而非常规科学。处于革命时期的科学,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相互批判竞争,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十分模糊。而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形成了共同接受的“范式”并在其指导下从事着类似解谜的活动,所以“真正能够将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的只能是常规科学”(7)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9、270、313页。 ,亦即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选择接纳。但拉卡托斯则批评库恩的主观主义倾向,认为其过分强调社会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在划界中的作用,容易滑向相对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既不是经验的证实或证伪,也不是作为科学家共同体信念的范式,而应当是对新的经验事实的预见性,亦即科学家可以通过调整作为一个结构整体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辅助性假设来应付经验中的反常现象,使经验内容获得增值,这样能够不断针对新事实产生更多预见性的理论就是科学的,是进化的研究纲领,反之就是退化的非科学的研究纲领。
此外,科学社会学家齐曼的“理性共识”标准、默顿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的规范标准,还有认知心理学倡导的“开放理性的人格特征”标准(8) David B. Resnik,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1(2), 2000, pp. 249-267.,等等,都试图以源于科学家群体的信念、认知、性格、行为等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尽管严格说来,经验事实在划界问题中仍是决定科学与否的关键依据,但其已不是完全独立外在于人类主观意识并自成一体的客观事实,而是打上了深刻的人为烙印的经验现象。依托于科学家个体或共同体的分析评判、行动旨趣与人格魅力,利用科学的具身性表现,以“社会人”而非“抽象物”作为区隔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出发点,这样科学的基本形相便更加立体丰满起来。纵使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依然分明森严,但科学圈层内外由于共处于广阔的社会场域中却有了交汇融通的可能。当然,尽管宽松的一元标准从对“铁证”的苛刻性依赖中解放了出来,但其归根结底仍然坚持一劳永逸的唯一的划界方案,通过判决性的区隔,坚决维护科学作为真理、美德、福音的必然性及其建制的公正性与职业身份的精英性。
3.刚性多元标准
前述独断性的一元标准动用奥卡姆剃刀,过度简化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难免有一叶障目的片面之嫌。科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知识体系,是诸多事件、偶然、规律以及数学、逻辑等共同编织的人造网,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动态整体。其随着影响力的扩散,已深深嵌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与其他知识、文化、制度融汇在一起,试图用一刀切的标准区隔科学与非科学,必然会忽略两者的粘连性和通约性,产生诸多逻辑漏洞,极易被驳斥否证。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倡通过收缩划界问题的关注视阈,增加标准的数量和维度,用多元标准划界,以应对一元标准的逻辑软弱性与经验匮乏性。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一位叫张蹇的人手持旌节率队出了长安西城门。见惯了冠盖云集的喧闹长安城,也许并没太注意到这队人马,更没料到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将从这队人马的脚下开始,以丝绸搭桥直抵罗马。
界限的区隔是边界运作理论兴起的认识论前提,而划界问题的“标准”与“终结”两种解决思路的无力则是其得以提出并被广泛应用的动因。从这个角度而言,科学的形相既不是依设定标准机械地模拓刻画出来的,也不是附庸于其他知识信念的翻版替身,而是科学实践的结果,是边界运作的产物,其随着实践运作过程的推进拓展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而前述关于已有的边界运作策略和形式的介绍,充分展示了边界运作理论的解释效力,其对于边界内外能量的分割、归属、冲撞、交换、对接等的分析,为我们剖解科学形相的边界运作逻辑机制提供了运思依托的空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些刚性的多元标准,运用认知逻辑与共识权威等武器,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以期甄别肃清科学队伍中的伪科学,捍卫科学的正面积极的形相。但这种多元标准显然缩小了划界问题的范围,聚焦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别,只关注科学的“真”与“假”,仅仅适用于现实中的一小部分现象,忽略了知识领域中更广泛的分类归属问题,而从科学的演进史来看,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同样也很重要,它是科学独立自主并获得合法性地位的根基。
4.弹性多元标准
前述三种类型的划界标准或者过于粗略武断,无视科学的异质性与复杂性,或者过于具体狭窄,缺乏充足的适用性与延展性。这些建立在二元论思维基础上的逻辑疏漏进一步固化了标准科学的形相,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科学的“标准化”或“正统化”过程,遮蔽了从“不是科学”到“成为科学”的历程中的诸多可能性以及科学内部不同学科或理论体系的特殊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很多学者提出了更具弹性的多元标准,将科学的边界柔化,承认科学性存在程度上的高低差异以及表征上的侧重点的区别,从而弱化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之间的等级区分,而代之以一种光谱式连续统思维理解科学的划界问题。比如曼纳受到生物学的物种划分思想的启发,提出使用“聚类集簇法”来解决划界问题,也就是在综合考虑科学的起源、性质、方法、应用等基础上,构建一整套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科学指标,列出符合科学形相特征的一系列清单,合理规定出满足最低条件的数量,给出诸多属性变元簇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依据,比如说有10个指标,规定要满足7个以上的指标才能称之为科学,这样也就有176种变元簇可以帮助我们划界,同时也以量化的方式展示了科学的多样性。(13) Martin Mahner,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How to Demarcate after the (Alleged)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 (eds.),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 29-43.而皮格里乌斯则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依据理论理解和经验知识两个维度,按照科学性的强弱有无,区分出伪科学、原型科学(或准科学)、软科学、公认确定的科学四种科学形式,其中占星术、智慧设计论、HIV拒斥论等属于伪科学,历史科学、进化心理学、弦物理学、外星人研究等属于准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属于软科学,粒子物理学、气候科学、进化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属于真正的硬科学。皮格里乌斯指出,四种形式之间既相互连通又有显著差异,借助模糊逻辑的方法理解划界问题将会更加有益。(14) Massimo Pigliucci,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A (Belated) Response to Laudan,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eds.),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 9-28.而瑞斯尼克则主张采取实用性方法探究划界问题,他认为被称为科学的人类活动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和实践意涵,我们不应该指望用一个关于科学的非政治的理论或定义去解决划界问题,而应通过分析科学在公众教育、医学、工程学、研究资助、法庭上的科学、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作用表现等,情境性地权宜性地判定其究竟是否是科学。(15) David B. Resnik,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1(2), 2000, pp. 249-267.尽管弹性多元标准经常面临将划界问题复杂化的指责,过于重视划界标准的穷尽性而无法满足区隔的互斥性原则,但这种试图走出二元论困境的弹性思维,对于重新审视科学的形相以及划界问题的实质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之,学术界关于科学划界的具体标准存在诸多争议,无论是一元标准还是多元标准,无论是严格的划界还是宽松的划界,其主要目标都是将科学与非科学区隔开来,为标准科学正名,清除其中的污染性要素,维护科学的纯净意象与天使形相。因此,虽然划界标准的选择多种多样,但在选择之前却大都预设了“标准科学”作为统一的参考框架,以此为默会性的基础展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区隔。而且,尽管每种标准划界区隔的着眼点不同,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但都从特定视角揭示了科学的一种或多重面相,它们组合在一起,大体上可以拼接勾勒出一幅科学的基本形相图。
三、从标准到实践:划界问题的“终结”与边界运作理论的兴起
不难发现,前述有关划界问题的处理都是围绕“标准”展开的,大多力求通过简明确定的标准来区隔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省略了对标准选择背后的预设、前提、信念、语境、惯习、偏好等背景知识的检视,以简化关联因素的复杂性,清除界限边缘的模糊性,从而描绘出科学与非科学形相的差异。这种以“标准”作为区隔依据的划界方法,重点关注的是划界的结果,回避了划界过程中可能牵扯到的诸多不确定性,或者说其聚焦于“界”的存在,而非“划”的活动,着力解答的是静态的“定界问题”而非动态的“划界问题”。
尽管“标准定界”是解决划界问题最常用的方案,能够方便快捷地对某些现象事件给出有效的决断,但由于标准选择的争议,几乎每种标准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反例而被否定,标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得划界问题只能在理想的理念世界中加以化解,而在实在世界中,划界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境。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划界问题是个伪问题,甚至直接取消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强调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们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相对主义的处理方案以极端化的方式瓦解了划界问题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虚无主义与不可知论的深渊。边界运作理论的出现,则打破了两种方案之间的对立,试图通过回归实践,调和平衡划界问题中的标准规范论与本质建构论之间的冲突。
这些形相的魅力促使科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张拓殖,科学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科学的公信力也愈渐增强,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格局,也开启了科学“泛化”之门。诸多非科学纷纷效仿科学,借鉴科学的方法、建制及其话语体系,确立并夯实自身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尽管其中某些知识或学科在“科学化”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比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在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分析更加理性,研究范式也有了新的突破。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一些人假借科学之名,行“欺诈诱骗”“谋取私利”之实,成为“伪科学”“垃圾科学”“不科学”的代言者。这些“科学”常常误导公众的行为选择,影响某些组织机构的管理决策,甚至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它们侵蚀着科学的合法性根基,摧残着科学的正面形相,也因此削弱着科学的公信力。如何将科学与非科学或者伪科学区分开来,避免前者成为后者的“替罪羔羊”,将伪科学清除出科学的队伍,还科学以清明之相,因而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情境下,科学的划界问题得以提出并引发诸多讨论。
自从划界问题提出以来,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判定标准就成为相关领域学者探究的重点主题。但由于科学本身的异质性及对其理解向度的差异,划界的标准也呈现出纷杂多样化的特征。各种标准之间的相似性、殊异性、矛盾性、不可通约性并存,关于科学的界限也缺乏统一的共识,致使划界问题掉入永无休止的争论漩涡中,成为一个斯芬克斯式的难题。
“田同志,水给你送来了,只有这么多,将就着用吧。”田志芳看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拎只铁皮桶立在地面上,她让他送进来,小伙子犹豫了一下,风一样下来,又风一样上去。田志芳认出,就是他帮着把行李搬下车送进地窝子,想说声谢谢,但小伙子早走远了。
“免疫化”是生命政治学的一种重要分析范式,是政治学与生物学耦合的产物。由于“免疫化是一种依赖于将异自体引入自体的自我消解过程,是一种识别区分何为自体何为异自体的过程,通过确认与清除自体中的退化物,免疫化能够对生命的演化进行产生优生学效果”,借用这一隐喻,在生命政治学中,免疫性被称为现代统治权力制度化的基本原则。(37) Casey Riffel, “The Paradigm of Immunization, ”Discourse ,33(3), 2011, pp. 409-412. 笔者在此借用这一术语探究科学形相的建构机制。
这些意在消解或终结而非解决划界问题的处置策略,通过对科学本身内在异质性与外在社会性的剖析,直接撤销了划界的可能与必要,抹除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将研究者思考的重心从对科学自相标准的勘定转移到对知识共相的挖掘,是现代社会民主平等理念在知识论领域的贯彻体现。它们的确暴露了“标准”思路在划界问题分析中具有的过于理想化、规整化、格式化等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落入二元论思维的“易攻难守”陷阱,但“消解”思路着眼于批判反驳,以最极端的“无解”之道断绝了与划界问题的关联,对“科学何以是科学”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形相何以可能”并未给出详细具体的解答,而是交付于“参考其他如艺术、哲学、宗教、政治、常识等的形成及其运作方略即可”。在此意义上,科学只是一个方便人类沟通交流某些事物的指称而已,其指称和内涵完全可以通过与前述艺术、宗教等的类比加以理解,尽管这拓展了阐释科学的想象力空间,但也增加了科学丧失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风险,为伪科学、坏科学、垃圾科学的盛行打开了通路,不仅不利于科学自身的进步,也妨碍了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的发挥,破坏了人类未来美好前景的可能性。
本次学术论坛是以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主要承办单位举办的图书馆年度学术论坛,从2014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论坛通过发布选题并征文的形式,搭建交流平台,汇聚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业界同仁,引导馆员参与学术研究,辅助馆员撰写并发表科研成果。论坛通过专家通讯评审、论文作者现场交流、专家现场点评、优秀论文推荐发表等形式,旨在图书馆业界营造科研氛围,涵育学术成果,扶持学界新人。
2.难题的“终结”及其风险
如何攻克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划界难题?继续寄望于标准的寻求只会进一步加剧科学形相区隔中的矛盾和纷争,划界标准与种类的增加不断地考验着研究者的耐心和勇气,历史上的科学以及现实中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又时时冲击着各种标准,一再地驳斥着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机械性区隔。这样看来,划界难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妄图以某种标准化解这一难题将会使研究者陷入西西弗式的永无休止的苦役中。因此,要彻底摆脱这种苦役,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走出问题圈定的领域,以壮士断腕的决绝直接取消划界问题,无论是劳丹的“伪问题说”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消界论抑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等,都采用这种途径“终结”了划界难题。
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征信行业尚处在市场化起步阶段,潜在市场容量相对较大,但行业内产品质量信用评估标准的统一性、实用性,产品质量信用数据的准确性、孤立性,产品质量监管政策的滞后性、针对性等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在劳丹看来,划界问题建立在科学具有某种恒常本质的预设基础之上,只要找到这一本性,划界便轻而易举,但“通常被视为科学的活动或信念具有明显的认知异质性”,用所谓的本性去代替这种异质性是片面武断的,而这也“提醒我们欲意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寻求一个认识论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或者说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程度是有差异的:“有些科学理论已经被充分地验证了,能够成功地对意外现象进行预测,而有些则指通过了为数不多的检验,无法对未来做出有效预测,有的科学分支发展得非常成熟,而有些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被波普尔称为认识论核心问题的划界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劳丹认为,“‘伪科学’与‘不科学的’仅仅是一些具有煽情意味的空洞词语,只适用于擅长修辞话语的政客和苏格兰的知识社会学家们”,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理性的一边,那么就应该放弃使用‘伪科学’与‘不科学的’这些字眼”。(18) Larry Laudan,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 R. S. Cohen & L. Laudan,Physics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Essays in Honor of Adolf Gr ünbaum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111-127.鲍尔对劳丹的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释剖析,强调并没有普适客观公平的标准可以区分“好/坏”或“真/伪”科学,所谓的异端学说都是主流科学定义的结果,并指出伪科学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并非是一种知识类别,其不过是主流科学为捍卫自身权威而给出的某种贬义性的断言。(19) Henry H. Bauer, “ Anomalistics, Pseudo-Science, Junk Science, Denialism: Corollaries of the Role of Science in Society, ”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28(1), 2014, pp. 95-111.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用“科学性程度的差异”取代“划界标准的选择”的思路,是将界限量化为无数连续性的点,而现实中使用的与科学具有质性区别的“伪科学”等语词是人为贴标签或修辞化的结果。
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则更为激进地使用对称性与相对主义原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毫无区别,认为它们都是“各种偶然、机会、社会传统、文化惯例等巧合”(20) Robert Evans, “Introduction: Demarcation Socialized: Constructing Boundaries and Recognizing Difference, ” Science ,Technology , & Human Values ,30(1), 2005, pp. 3-16.的产物,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划界问题。一方面,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诸多利益、权力、信念等因素冲撞博弈的结果,其同样依赖于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认知习惯和直觉思维,甚至可以说“科学只不过是日常推理的高度精细化与复杂化的扩展而已”(21) Maarten Boudry, “Loki’s Wager and Laudan’s Error,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eds.), 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 79-98.。另一方面,科学与形而上学、艺术、宗教、神话、文学等一样,都只是文化样式中的一种,并不具备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人为地将科学与非科学分离开来,这种粗暴懒惰的二元对立的划界思维带来的麻烦困难比其解决的要更多,其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因为“知识并不是趋向于某个理想观念的一系列没有矛盾的理论,也不是逐步接近真理,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海洋,充满了各种互不相容的、甚至不可通约的理论和信念,每一个理论,每一个童话,每一个神话,都是这个海洋中的海水,都迫使其他部分更加完善”。(22) 朱志方:《再论科学划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这样看来,恰如提倡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的费耶阿本德所言,“如果我们要理解自然,要掌控我们生活的物理环境,就必须使用一切观念,一切方法,而不仅仅是从中选择的一小部分(即科学)”。(23) F.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p. 306.此外,科学在当代社会俨然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其作为“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24)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因而它与某些非科学、伪科学或不科学的事物一样,具有诸多不合理的甚至是独裁垄断式的诉求。这条思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决了划界的必要性,将科学拉下知识教主的神坛,解构科学背后的种种不堪,揭露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所以,科学并不比其他知识更值得令人刮目相看,它是其他知识、观念、制度等相互作用、协力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与其他事物一起共同构筑并再生产着现代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因此要将它们区隔开来并无多大意义。
上述八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划界困难或者说划界争议的原因,基本上与划界范畴及单位的多样性、科学本身的异质性、参照对象设定的任意性以及区隔标准确证的情境性等有关。而从劳丹所谓的“元哲学”角度来看,关于划界问题的争论其实主要源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不同理解:(1)划界标准的提出应当满足何种充适性条件,足以解释将科学与非科学分离开来的通常路径,从而展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差异?(2)划界标准为科学身份地位的确定或者说“科学的”与“不科学的”之间界限的确立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吗?(3)关于特定信仰或活动是否科学的断言中隐含着何种意图或判断,使得划界成为价值负荷的贴标签行为,从而带来影响深远的道德、社会和经济后果?(17) Larry Laudan,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R. S. Cohen & L. Laudan,Physics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Essays in Honor of Adolf Gr ünbaum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111-127.目前已有的划界标准无力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答,大多都通过委婉的修辞或迂回掩饰的方式躲避自身在逻辑上的漏洞和现实中的寡淡,在最终标准的择定中也充满了无奈和将就,划界问题也因此成为困扰科学家与相关研究者的重大难题之一。
总之,在消解方案中,科学就像“洛基的赌注”,其居无定所、形无定式,没有明确公认的定义,因此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界注定无功而返,遵循“思维经济”与“认知效用最大化”原则,消除标准争议中的种种噪音,直接取消麻烦棘手的划界问题,是一种最为省时省力的做法,但这一做法的代价就是科学日益增长的“躲避崇高”的平庸化,以及以科学之名作恶为过的常态化。
3.回归实践:“边界运作”理论的兴起及其启示
尽管划界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研究者,在理论上很难概括抽象出一种可行又可靠的方法或标准解决这一难题,因而才有了终结划界问题的消解方案的出现;但殊为悖谬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自然地”或“本能地”辨识出哪些东西是科学的,哪些不是科学的,这种默会性的直觉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对某一事务现象的科学与否做出合适的判定。
日常世界中划界的轻而易举与学理场域中划界的举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这种依赖于常识的粗糙划界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日常决策和行为,使科学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切实落实了为人类谋福利的职责。所以,无论是就科学这一特定语词本身具有的内涵指称来看,还是就科学所担负的荣耀使命来看,科学与非科学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也应该是有界限的,“我们今天区分不出这条界限或‘带’,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或‘带’”(25) 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毕竟“边界是科学共同体维持自身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屏障,也是与外界发生联系、沟通和交互的场所”(26) 马乐:《STS中的边界研究——从科学划界到边界组织》,《哲学动态》2013年第11期。 。但是这一界限并非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流动多变的,因此划界问题的重心不是在“界”的锚定,而是在“划”的过程。正如基瑞恩所指出的,科学划界并不仅仅是由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探讨的理论分析性问题,也不只是给出“谁能做科学”的依据的学术性问题,而是在大量具体现实和日常的环境下,由科学家不断例行地完成着的实践性的问题。(27) Tomas Gieryn,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1983, pp.781-795.这就意味着,划界并非是单纯的范畴界定问题,也不依赖于某一万能的标准判据,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奔走跳跃于边界间的行动。因此,划界应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的边界是如何被划分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怎样的实践运作被生产出来的。正是基于对划界本身的“实践性”的反思,基瑞恩率先系统地提出了一种介于“标准”与“终结”之间的新的理解应对划界问题的方案——“边界运作(boundary work)”。
在基瑞恩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是科学家建构出来的,边界的存在对于科学家获取知识权威身份和职业地位机会、揭露拒斥伪科学家的权谋心机、保护科研远离政治干预的自主性,等等,既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因而,科学家会努力通过一系列边界运作的实践确保科学与非科学的区隔界限,使之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真正承担起其应负的使命,但“科学并非是单向度的,其边界是被灵活地、历史与境性地、有时是模棱两可地划定的”。概括而言,科学家在科学的边界运作中一般会运用三种策略:第一是扩展(expansion)策略,科学家往往会使用对比手段揭示那些诸如宗教、机械论等传统的非科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以此彰显并拓展建立在客观真实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的权威性;第二是排除(expulsion)或垄断(monopolization)策略,科学家常常通过排斥异己,给它们贴上“假冒的”“离经叛道的”“业余的”等标签,实现职业权威资源垄断的目的;第三是保护(protection)策略,为了维护科学的自主性或自治性,科学家会使用“替罪羊”免除自身工作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责任,或者说在科学家看来,假如没有外部的干预,科学工作根本不会造成严重后果。(28) Tomas Gieryn,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1983, pp.781-795.基瑞恩用三个案例分别详细论证了科学家边界运作的三种策略,这为后来相关研究者理解分析科学与其他知识、事务、组织、系统等的关系打开了一条新的实践审视理路。
这一类型对划界问题的处理以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为代表,强调科学与非科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只要按照唯一的划界标准,就可以准确地辨识出非科学的知识,将其踢出科学的阵营,维护科学的纯净形相。其中,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就是将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的经验事实加以逻辑系统化而构成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而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则取决于该命题是否表述经验内容,只有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3) 郑可圃:《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几个流派的科学划界标准》,《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 因此经验证实便成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亦即凡是能被经验事实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就是科学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非科学的。
总而言之,边界运作理论的兴起,将科学划界问题从“标准”难题中解放了出来,其实践转向发现了科学边界的弹性,并“盘活”了科学与非科学间的“交易”市场,从对“物之边界”的研判转移到对“边界之事”(31) Andrew Abbott, “Things of Boundaries, ”Social Research ,62(4), 1995, pp.857-882.的重视,使边界这一地理学隐喻逃离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跟随时间与人的能动性翩翩起舞。因此,边界并非是具体固定的,而是处于不稳定的腾挪转移状态之中的,是一个充满协商与修辞的灰色模糊地带。考虑到将边界具体化或物化可能带来的强制独断危险,将边界运作的焦点集中于“运作”而非“边界”上是更明智的选择。(32) Sally Eden, Andrew Donaldson & Gordon Walker, “Green Groups and Grey Areas: Scientific Boundary-Work,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 2006, pp.1061-1076.这对于重新思考科学形相的建构过程,理解“科学形相何以可能”的问题,从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隔作为目标到全面考量区隔的动力学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区隔与反区隔之间的张力:科学形相的边界运作逻辑及其机制
如前所述,从划界问题到边界运作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是对科学的理解从标准化迈向实践化的体现。当然,后者并非是与前者的彻底决裂,它们在逻辑上的渊源以及现实中的关联,或者说二者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在边界运作理论的核心观点与基本预设中得到了印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是有区别的,是存在界限的;界限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滑移流动的;滑移流动是实践运作的结果,而实践运作是滑移流动的表征。
主张刚性多元划界标准的学者大都将划界问题定位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别,至于科学与哲学、历史、形而上学、神学、艺术、日常推理等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并非真正的划界问题,它们属于知识领域的划界,涉及的是知识的分类或不同学科间的劳动分工,它们之间的依赖性和连续性使得区分它们变得无多大意义。因此,这些学者致力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隔,提出了两者间的诸多划界标准。比如,萨加德认为划界标准需要考虑三个要素——理论、共同体、历史场域,而以“科学的”作为旨趣的一种理论或学科是伪科学的,当且仅当“(1)与其他可替换的备选理论相比,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的进步更少,而且面临许多未解决的问题;(2)但是,这种理论或学科共同体成员却很少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去发展理论,对这一理论相较于其他理论的优劣评价也漠不关心,而是精心选择性地对待证实与否证问题”。(9) Paul R. Thagard, “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 1978, pp. 223-234.邦格则系统地提出了划界的12个标准,他指出科学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应满足E=(C,S,D,G,F,B,P,K,A,M)。其中E为特定的知识领域,同时它又是更广阔的认知领域的一个构成要素;C为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认知共同体,S为鼓励至少允许C之活动的社会,D为E的真正实在的论域,G为C的世界观或研究伦理,F为E的形式背景(逻辑和数学工具),B为特定背景或从E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借调的有关D的一系列假设,P为E要处理的一系列问题的组合,K为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的储备,A为C对完善提升E所抱的目的或目标,M为运用于E的方法论体系。他还特别增加了一个动态时间标准,即E的每一个构成要素都处于不断变化中。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知识领域才是科学,而“任何不能满足上面所说的所有十二个条件的知识领域都将被称为非科学。……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作伪科学”。(10) Mario Bunge, “What is Pseudoscience? ”The Skeptical Inquirer ,9, 1984, pp. 36-46.汉森通过深入的逻辑论证与推理,给出了伪科学判定的三个著名的标准,他指出,某个陈述是伪科学的,当且仅当“(1)所涉议题是在科学领域范畴内的;(2)缺乏认识论上的正当理由根据;(3)发挥了教条式的作用,其主要支持者都努力营造‘它在认识论上有正当理由’的印象”。(11) Sven Ove Hansson, “Cutting the Gordian Knot of Demar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3(3), 2009, pp. 237-243.此外,德克森也曾借助知识的可靠性与人类的可错性两个尺度区分了科学与伪科学,并详细论述了伪科学的七宗罪。(12) A. A. Derksen, “The Seven Sins of Pseudo-Science,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4, 1993, pp.17-42.
正是在此启发之下,笔者将科学形相的边界运作逻辑概括为五种相互关联的实践:一是对自我的正当化,以此“修养自身”的区隔方式确立科学形相(真理、公正、精英、美德、福音)的标准基调;二是对异己的污名化,以此“批判异己”的区隔方式揭露伪科学的消极形相(谬误、偏见、妄人、庸俗、灾祸);三是对问题的免疫化,在面临偏离标准科学形相的现象时,以“防御区隔”的方式自我辩护并豁免自身责任;四是对知识的科普化,通过向公众宣传普及研究成果,展示科学形相的魅力,以“开放性的反区隔”方式或者说是科学知识常识化的途径来拓展科学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五是对他者的涵摄化,尊重并虚心谨慎地悦纳民间科学和其他非科学(不包括伪科学)知识,以“包容性的反区隔”方式提升科学的公信力和支持度。这样的边界运作机制充分利用了区隔与反区隔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区隔的前提是无区隔空间的存在,而且无论区隔得多么严密,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边界本身总是需要也是必然留有一定缝隙的,界限之间的渗透联通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反区隔预设了区隔的在场,欲求通过对边界的跨越,打破界限的阻隔,以实现空间的自由解放,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运作策略既是现代社会民主平等价值观在知识领域的体现,也是对更行之有效的区隔的再认,为更高级稳健的区隔奠定了基础;同时,介于区隔与反区隔之间的防御区隔,是面对批评质疑指责时,尽力消除边界模糊性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对界限的坚守维护边界的清晰性。具体说来,科学形相的边界运作实践机制可表述如下:
1.对自我的正当化
这是科学从人类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中独立出来,获得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过程,也是标准科学形相基调确立和浮现的过程。通过本体论的设定、认识论的承诺、方法论的规范,科学形成了具有一致性与融贯性的特定严格的整体性系统,在知识的坐标格局中赢得了重要的席位。在本体论的层面,科学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客观实在的自然界,而且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是有秩序和规律的,其秩序是广泛的,其规律是一以贯之的。在认识论的层面,科学坚信人类能够运用天赋的理性、先验逻辑和先天知识发现自然的本质、结构与规律,并对其进行准确可靠的解释说明,最终用普适性的理论表征自然运转的基本秩序与原理。在方法论的层面,科学规定了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确定了研究应遵循的基本流程,强调综合运用实验、数学、假设检验、归纳推理、经验证据等客观真实的工具手段,实现解蔽自然奥秘、揭示真理的目标。正是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践努力,科学逐渐将与之相关与不相关的东西,或者对它而言内在和外在的东西分离开来(33) 达德利·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28页。 ,从而与常识、神学、形而上学、文学、艺术等其他知识信念区分了开来,成为人类认识、解放、改造世界的一种新形式。
这些数据说明, 在一定的水活度下, 随温度升高, 平衡含水率值下降, 金银花的吸水性下降。 这种趋势是由于温度引起物质内部的化学、 物理变化而导致水的亲合活性点减少的结果[4]。Pali pane KB和Driscoll RH提出温度升高, 水分子的活性能提高, 使得食物中的亲水力破坏, 变的不稳定, 因而平衡含水率降低。随着温度的变化, 分子的激发态、分子之间的距离会变化, 因而分子间的引力也会变化, 导致在一定水活度下, 随着温度的变化吸收的水分子数量也会发生变化[5]。
这种新的理念方法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奇迹,实现了人类的诸多梦想,大大提高了人类生存生活的质量,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科学因而成为福音的代名词,其对自然神奇性的揭秘以及带来的强大实用价值为它赢取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支持,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也越来越高,成为教育体制、职业分工与文化建制中越来越权威的要素,成为评判其他事务合理性与可信性的依据。科学的基本形相——真理、公正、精英、美德、福音——也在这样的正当化区隔中日益牢固地被创造出来。
2.对异己的污名化
为了更好地与其他知识区隔开来,除了从自身的定位规划努力做起,科学也经常会通过展示对立面的种种不足,为“不科学”的对方贴上“坏”的标签,以之作为参照对比,彰显科学自身的真善美形相。当然,由于“非科学”的异质性,科学在对异己的污名化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于宗教神学、形而上学、文学、艺术等,科学首先会承认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会指出他们的虚幻性、玄思性和情感性,因而是一种弱污名化的区隔。
而对于借助科学之名行诳骗之实的垃圾科学、巫毒科学或者统称的伪科学,科学则会进行强烈的抵制和严厉的批判,通过对伪科学的强污名化摒弃伪科学的安身立命根基。这些伪科学大都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背道而驰,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被很多人接受,是由于“其契合了人类长久以来的认知演化机制,用直觉吸引力牺牲了知识的健全完整性与客观准确性”(34) Maarten Boudry, Stefaan Blancke & Massimo Pigliucci, “What Makes Weird Beliefs Thrive? The Epidemiology of Pseudoscien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8(8),2015, pp.1177-1198.,带有与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原始思维印记。比如,德克森曾分析指出伪科学的七宗罪——合理得体证据的匮乏、通常毫无根据地排除不受欢迎的数据、沉迷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奇迹般巧合的诱惑、自诩拥有神奇魔力般的方法、神化初创者并视之为先知、声称拥有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缺乏批判性的过度自负。(35) A. A. Derksen, “The Seven Sins of Pseudo-Science,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4, 1993, pp.17-42.帕克也曾对伪科学的七种病症进行了诊断——竭力直接向媒体推销叫卖科学新发现(营销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或有权势背景的科学共同体压制它们的新发现(阴谋论者);效果很难经得起多次检验(牵强附会者);新发现的证据是坊间传闻性的(道听途说者);某一信念可信是因为它已持续了几个世纪(诉诸传统者);重要发现是在与世隔绝情况下孤立地被完成的(遁世奇才/世外高人);不可思议的新发现必须要提出全新的自然法则来解释(狂妄诡辩者)。(36) Robert L. Park, “The Seven Warning Signs of Voodoo Science, ”Think ,Spring, 2003, pp. 33-42.正是通过对伪科学中充斥的各种谬误、偏见、无知、危害等的揭露,科学的正当性及其标准形相得到了有力的反证。
采用Excel 2007和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多重比较(Duncan氏新复极差法)分析。
3.对问题的免疫化
为什么划界如此困难?曼纳尔详细地总结了八个原因:第一涉及区分对象的复杂性,究竟是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非科学(比如常识、艺术、人文等)的划界?第二是牵涉好科学与坏科学的区别,比如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完美而忽略少数不和谐的数据的人,是坏科学家还是伪科学家?第三是面临如何判定原型科学与非正统科学的问题,比如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由于并不具备成熟正统科学的所有特征,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说是一种原型科学而非伪科学,一种替代性理论在何时会被视为一种伪科学,何时又会被看作仅仅是一种非正统的观点?第四是与科学本身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争论有关,那些赞同科学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连贯性与统一性知识的学者更热衷于划界问题。第五是受到划界单位选择的影响,也就是着眼于科学的哪个方面和层次进行划界的问题,这些单位包括陈述、问题、方法、理论、实践、理论和(或)实践的历史发展序列、知识领域等。第六是由于划界时只依托于单一标准或少量标准,忽略了划界单位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第七涉及划界标准应当是非历史性的还是时间依赖性的问题,或者说是选择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标准还是考虑历史发展的灵活性标准的问题。第八是要考虑到划界逻辑的恰切性问题,亦即划界的标准在逻辑上应当满足必要性和充分性的条件,而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标准很难找到,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放松标准或直接放弃划界问题可能是更好的出路?(16) Martin Mahner,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How to Demarcate after the (Alleged)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Massimo Pigliucci and Maarten Boudry (eds.),Philosophy of Pseudosci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 29-43.
尽管科学的确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但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自然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科学必然也是不完美的,同样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局限,这成为学者们争相抨击与批判的对象。不过,科学具有特定的结构弹性和自我修复力,在面对各种反面证据和批评时,能够运用有效的免疫策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38) Maarten Boudry & Johan Braeckman, “How Convenient! The Epistemic Rationale of Self-Validating Belief System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5(3), 2012, pp.341-364.在具体现实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的标准形相的确常常发生扭曲变形:其生产的并不一定是真理,而是威权性和可错性的知识;在资源的分配竞争与评议体系中带有门户之见和圈子意识,“马太效应”随处可见;科学界的分层并不必然比其他领域更合理,人才等级的金字塔甚至更加明显;科学研究者并非都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也会屈从于权力利益的诱惑支配,出现造假、欺骗、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科学带给人类的不只是福音,还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及其导致的本体安全感的日益流失。无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对上述科学的社会建构性和意识形态霸权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比如“科学的教条主义、科学知识与既得利益的关联性及对外行知识的驱逐”(39) Jaron Harambam & Stef Aupers, “Contesting Epistemic Authority: Conspiracy Theories on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4(4), 2015, pp.466-480.,成为科学美好形相的威胁。
面临这些问题和挑战,科学启动了自身强大的免疫力,或者通过预防接种,或者通过目标转移,或者通过“概念的紧缩修正”(40) Maarten Boudry & Johan Braeckman, “Immunizing Strategies and Epistemic Defense Mechanisms, ”Philosophia ,39, 2011, pp. 146-161.,或者通过无应答等边界运作方式,维持机体自身的健康协调运行,确保科学的真善美形相。具体而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其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道德与行为的奖惩规范,以发挥激励与震慑作用,一旦研究中出现越轨失范等行为,可以及时加以惩戒。因此,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不端和腐败问题仅仅是个别人的过失,并非科学整体中的普遍性现象。事实上,社会建构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是误将伪科学当成了科学,那些加诸科学之上的消极负面形相其实是伪科学的特征,并非真正的科学,通过紧缩科学的所指区间,可以成功地排除和转移各种强加的质疑。与此同时,科学也会动用“阴谋论”思维,将对科学的不信任和指责归因于对方的利益或权力动机,或者受到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的蛊惑,转而强调由于人类在认知与生理上的局限性,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很多灾难事故的发生并非科学本身造成的,而是人为疏忽导致的。而对伴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某些显而易见的威胁和危害,科学会采取某种“避而不谈”的躲闪态度,以漫不经心、不闻不问或“反向守护”的方式“封存”某些事实,“让某些特定的观察资料和数据沉默不语”(41) Babette Babich, “Calling Science Pseudoscience: Fleck’s Archaeologies of Fact and Latour’s ‘Biography of an Investigation’ in AIDS Denialism and Homeopathy,”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1), 2015, pp. 1-39.,如受了诅咒般被人遗忘,以此捍卫科学的正面合法形相。
不经常出现的问题称为“例外”问题,例如,在工程施工中遇到的材料价格突然或连续猛涨的情况.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应对市场随时变化的行情进行分析研究;在材料价格暴涨之前,或已在上涨途中,预计材料价格在高位会维持较长时间时,将所需材料尽可能多进一些,以免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而在价格连续下跌时,则不应保持过多的库存量.
4.对知识的科普化
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尤其是在大科学、后学院科学时代,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社会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科学要赢得更多的支持和资助,必须要争取公众与其他机构组织的认可和信任,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树立起科学的可靠形相。因此,科学必须走出“实验室”和“职业舒适区”,跳出自身的“势力范围”和“学术地盘”,跨越科学与公众或专家与外行之间的边界,向公众宣传普及科学知识,通过“开放边界”这一“反区隔化”的手段,使公众真正接触了解科学,更理性地看待理解科学,从而更有利于科学正能量形相在公众心目中的塑造。
通过对资源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及时转变人员观念;高效使用预算资金;实现财税科学管理,希望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土资源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从而促进我国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其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概括来说,反区隔化的科普方式主要包括博物馆的建设、各类科普协会组织的成立、科普图书的撰写出版、“科学素养”教育的开展、基本健康急救安全知识讲座、科普知识手册的发放、线上线下科普活动的举行等。比如,世界各地科技博物馆的纷纷建立,为青少年和普通公众更直观地了解科学技术提供了便利。在博物馆中,科技被打造成神奇的令人惊叹的景观,激发了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很多博物馆甚至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使游客在休闲娱乐中学习到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科普与旅游资源的结合,极大地展示了科学的魅力。
(1) 废旧橡/塑制品再生利用,可变废为宝,缓解环境压力,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应用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总之,各种科普化举措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科学的客观真理形相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鸿沟”,使公众成为科学中的“一员”,从而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科学家的立场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生产的价值,由此,科学的公信力大大提升,影响范围日益扩展,产出效益也实现递增。
5.对他者的涵摄化
科学的诞生发展是不同主体与各种力量或隐或显地斗争博弈的结果,除了对敌对异己者的污名化之外,科学在建构自身的正面形相之时,也积极地寻求与近似的他者协商合作,跨越与他者的界限,虚心接纳善意他者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他者的研究权利,运用“包容性的反区隔”路径描画自身宽容民主的肖像。
(4)输出重建信号和残差信号。通常情况下,重建信号为原输入信号中的低频分量,残差信号为原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分量。
这些他者包括民间科学、公民科学等,它们是相对于官方的、正统的、专业的科学而言的他者,属于未经过长期严格的现代专业科学教育培训的业余者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其中,民间科学更多的与传统的技艺、习俗、生存经验、生活智慧有关,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色彩,它们并非是与科学呈对立分裂关系,而是连续统一体关系。(42) Gregory Schrempp, “Folklore and Science: Inflections of ‘Folk’ in Cognitive Research,”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33(3), 1996, pp.191-206.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民间科学的滋养作用,比如民间科学中关于植物分类和功能的朴素认识对现代食物学与药物学的贡献,关于居住地理空间的常识对理解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历史的帮助,关于天文气候的经验判断给气象学带来的洞见,等等。(43) Weston La Barre, “ Folk Medicine and Folk Sci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55(218), 1942, pp.197-203.公民科学则是指普通公众以其智识努力或持有的相关知识,或利用他们手头的工具和资源,自愿花费时间精力与专业科学家一起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以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44) European Commission,Green Paper on Citizen Science ,2013.
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所需要的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单靠科学家群体的力量很难完成,采用众包形式吸引普通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中便成了一种最佳的选择,“搞科学”对于这些自愿参与其中的公众而言是“一项严肃的休闲娱乐活动”(45) Morgan Meyer, “On the Boundaries and Par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Museum and Society ,6(1),2008, pp.38-53.。正是由于对业余科学爱好者以及民间智慧的涵化与濡化,科学增加了自身边界的弹性和韧性,赢得了更广阔的创新性空间,获得了更高的发展潜力,既扩展了自身的张力,也保持了自身与外界的平衡,科学的积极开放民主的形相也因此进一步稳固。
随着汽车的产量和保有量日渐提高,汽车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为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油耗及污染等问题.
上述五种边界运作的逻辑过程并非是各自孤立进行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统一性的整体,在区隔与反区隔的张力空间中共同建构维系着正统标准科学的基本形相,既有通过边界区隔对这些形相的正向塑造与逆向确证,也有通过边界防御对形相偏差的反驳与辩护,更有通过边界跨越对其良好公众形象的谋划与强化。
科学作为现代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其诞生发展以及与政治、经济、宗教、习俗、文化等的关系是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那么,科学是如何与其他事物区隔开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相的知识体系的呢?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答。而这些解答究其实都与划界问题及其争论密切相关,无论是关于划界标准的争议还是划界问题的终结,以及实践转向后边界运作理论的兴起,都为理解科学的形相特征及其建构过程提供了启发和依据。因此,从对划界问题的分析出发,沿着这一线索探究“科学形相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条有效可行的思路。以此为基础,笔者通过对划界问题及其争议的梳理反思,强调研究科学形相建构过程的必要性,并运用边界运作理论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科学形相的建构逻辑与实践机制。
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主要关注的是科学家群体的边界运作策略,或者说是科学家心目中的标准科学形相的建构机制,而对公众、艺术家、人文学者等心目中的科学形相及其建构逻辑涉及较少,尽管科学家的边界运作会影响其他群体对科学形相的理解判断,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科学形相总是社会与境性的,充满了种种权变的可能,而且由于知识背景、社会地位、生活情境、利益诉求的不同,科学形相及其生成逻辑的主体间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第二,论证前提建立在科学形相的统一性基础之上,忽略了科学共同体内部不同专业对科学形相的认知的差异,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科学摩擦”(46) Paul N. Edwards, Matthew S. Mayernik, etc., “Science Friction: Data, Metadata, and Collaborat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1(5),2011, pp.667-690.对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形相的影响如何,这同样也是理解科学形相建构过程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三,偏重于抽象的理论阐释,缺乏相应的质性或量化研究资料和数据的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论点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结合具体案例和事件,利用扎根理论开展科学形相建构过程的质性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概括分析科学的基本形相,将是未来笔者着手进行的工作。第四,近年来,边界运作理论在公共政策、经济管理、组织创新、教育改革等其他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涌现出了新的边界体概念以及边界组织理论,这些概念理论对省思科学的形相及其建构机制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意义,文中尚未提及,科学形相是否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边界体”,处于科学与其他社会世界之间的边界组织在科学形相的塑造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对它们的思考将有利于对科学形相及其社会运行机理的深入理解,这将是笔者后续研究中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SH002);江苏省中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计划项目
(责任编辑 王浩斌)
标签:科学标准论文; 科学划界论文; 科学边界运作论文; 科学公众形象论文;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