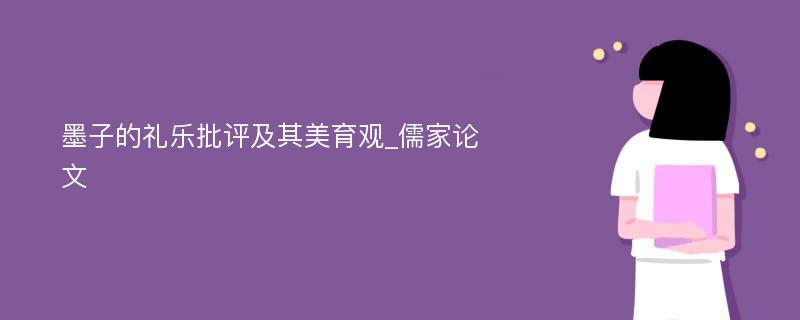
墨子的礼乐批判及其美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美育论文,礼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
《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这是墨子“非乐”论的总纲。从中可以看出:一,墨子之所谓“为乐非也”之“乐”并非限于音乐,它不仅包括“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而且包括“刻镂华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大体涵盖了诗歌、音乐、舞蹈、建筑、雕刻等审美和艺术活动。因而,墨子“非乐”也就是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否定;二,对于音乐、雕刻、美味、建筑等,墨子是“耳知其乐”、“目知其美”、“口知其甘”、“身知其安”的,也就是说他承认美和艺术的存在,也认识到美和艺术具有给人以审美愉悦的价值,墨子“非乐”并非是因为美和艺术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而否定之;三,墨子之“非乐”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原则的,是以是否“利人”为标准的,他之所以“非乐”,是因为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将会“亏夺民衣食之财”。可见,墨子的“非乐”论的关键主要集中在审美和艺术与现实的社会功利的关系上。《公孟》篇载:“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很显然,在墨子看来,做任何事情都有其目的,就象盖房子是为了避寒暑、别男女一样,而任何事情的目的、价值都只能用是否“利人”、是否“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标准来衡量。而“乐”在墨子看来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因而被认为是无用、无益甚至有害的。这是墨子美学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非乐”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墨子美学观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就是将事物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对立起来,用事物的实用价值否定其审美价值,用基本的物质需要否定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这种观点,突出地体现出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审美观。
当然,墨子的“非乐”主要是针对“当今之主”、“王公大人”对于审美与艺术的极端奢侈的享乐追求的,他批判“当今之主”宫室必求“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衣服必求“锦绣文采靡曼之衣”,还要“美食刍豢蒸炙鱼鳖”、“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衣食住行极尽其美,极尽奢华,并为此“暴夺民衣食之财”、“厚作敛于百姓”,从而导致物质生活上的极度的不平等,使“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在《非乐》篇,墨子从几个方面对当时社会礼乐文化进行了全面抨击:
首先,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况下,“王公大人”为享受“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而“造为乐器”,一味追求“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将必厚敛乎万民”,“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治与?”因此,“王公大人”之“为乐”“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其次,“王公大人”要欣赏音乐,必将“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又要有壮年之人“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以撞钟、击鼓、奏乐。这就不仅要“亏夺民衣食之财”,而且必然会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絍之事”。
再次,音乐的欣赏“頞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因而“王公大人”一定要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这就肯定会影响到“听治”与“从事”,“与君听之,废君之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
复次,那些为“王公大人”演奏乐器、表演乐舞的人是“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的,因为“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这些人“不从事乎衣食之财”,反而要用很多费用来供养,不能不变本加厉地“亏夺民衣食之财”。
最后,“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上至“王公大人”、“士君子”,下至“农夫”、“妇人”等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共同付出艰苦的劳动,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说乐而听之”,就将使他们都废弃各自的“分事”,“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墨子从乐器的制作、音乐的演奏、音乐的欣赏、乐人的供养以及音乐欣赏的结果等几个方面对当时上层社会的音乐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性的批判。墨子始终以是否“利人”、“兴天下之利”、“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来衡量、判断审美和艺术的价值的,直接的现实功利成为礼乐批判的唯一标准,审美和艺术因为不能使“国家治”、“财用足”而遭到墨子的否定甚至禁绝。“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从“非乐”走向了“禁乐”,这是墨子礼乐批判的最后结论。
墨子的“非乐”论与其对礼乐传统及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墨子的礼乐教化观念随着墨学之成为“显学”而以其激烈的反传统和社会批判精神以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战国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点通过《墨子》一书所记载的墨子与儒者及时人关于礼乐问题的众多论辩以及后来孟子的“辟杨墨”表现得非常明显。墨子的礼乐批判由于反映了下层社会劳动者的利益和正义的呼声,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并且由于它突出地显露出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对立、苦乐不均以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社会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因而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正因为墨子比较自觉地从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出发观察、思考和判断问题,限于小生产劳动者包括其思想代表的社会地位、知识、眼界以及文化教养,这种功利主义又不能不表现得非常狭隘,从而使其对审美与艺术包括礼乐教化问题的看法带有颇为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由对当时上层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活动与社会功利活动、审美价值与实际功用之间的尖锐矛盾无情揭露而走向了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彻底否定。
荀子曾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这一批评是切合实际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所说的“文”主要并不是指广义上的审美和艺术,这种意义上的“文”墨子是肯定其存在的,并且认识到其审美价值的。荀子说墨子“不知文”主要应该是指出墨子不懂得审美和艺术的政治、道德教化的功能、作为人的内在政治、道德修养的审美表现的功能以及陶情冶性的美育功能,这种意义上的“文”就是孔子所说的“文之以礼乐”的“文”,是荀子的“文理隆盛”的“文理”。墨子确实认识到审美和艺术具有可以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价值,但是他是把“目知其美”、“耳知其乐”完全等同于“身知其安”、“口知其甘”,说明他所说的“美”与“乐”仅限于直接的感官愉悦,其中并不包括超越性的精神愉悦。墨子对上层社会礼乐活动的批判显然是把音乐的欣赏仅仅视为一种享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极力反对上层社会沉溺于极端奢靡的审美和艺术的享乐,也反对甚至禁止下层劳动者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后去从事审美和艺术活动,这也说明墨子不懂得人所具有的超越直接物质需要的对精神愉悦的审美追求。因此,墨子从来都没有超越直接的实用功利去思考审美与艺术所可能具有的精神价值,当然也不可能意识到礼乐的审美教育价值。墨子的礼乐批判是把礼乐作为享乐的工具来批判的,而不是把礼乐作为教化的手段来批判的。他对礼乐传统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否定以及对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完全是从直接的现实的实用功利出发的,完全没有涉及到礼乐在政治、道德教化方面的美育价值。因此,严格说来,墨子并未真正了解西周以来的礼乐教化的历史传统和儒家的礼乐教化观念,他的礼乐批判从理论上看既狭隘又浮浅,在先秦美育思想发展上的贡献完全不能和儒家及道家相比。而且由于在审美和艺术包括礼乐教化问题上的极端狭隘的功利主义,墨子思想虽然作为“显学”在战国时代曾盛极一时,但对美育思想的发展却绝少影响,成为名符其实的“绝学”。
然而,从先秦美育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墨子的礼乐批判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墨子的思想是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周以来传统礼乐传统的美育观的巨大裂变中,墨子的礼乐批判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教化观念激烈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对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触及到了儒家所一直漠视的审美与社会功利问题,也显示出儒家注重社会政治、道德教化和个体心性修养而对如何促进国家富强、如何解决民生疾苦缺乏关注的片面性。尽管墨子对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理解得过于片面和极端,但是他对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的矛盾对立的突出强调,尤其是对当时上层社会极端奢靡的音乐享乐与国家昏乱、黎民困苦不堪等社会现实的尖锐对立的无情揭露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从一个方面表明,随着春秋末期以来愈演愈烈的“礼坏乐崩”,一直承担着政治、道德教化功能的西周礼乐已经越来越形式化,完全成为上层社会奢侈享乐的工具,礼乐的政治、道德包括宗教功能逐渐消解、淡化而其审美愉悦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
墨子以“非乐”论为中心的美育思想也是先秦美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墨子的礼乐批判曾引起当时的思想界的强烈关注,作为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直接对立面,墨子的“非乐”论对于促进儒家美育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孟子是以“辟杨墨”著称的,但我们从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中似乎也可以看到墨子“非乐”论的影子。墨子曾指出,“当世之主”、“王公大人”欣赏音乐“頞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因而一定要与“君子”、“贱人”共同欣赏音乐。墨子是将这种“与民同乐”作为“非乐”的理由之一来看待的,因为“与君子听之,废君子之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而孟子则反其意而用之,他也指出王者“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并进而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指出“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孟子是把“与民同乐”视为王者“得民心”并进而“得天下”的手段来看待的,是从积极方面对“与民同乐”的肯定,而他的这一思想固然是其“仁政”、“王道”学说的体现,但也不排除曾受到墨子的启发。至于墨子对荀子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荀子的《乐论》就是直接以墨子的“非乐”论为批评对象的,该篇每阐述一个重要观点之后都要说一句“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美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他对审美和功利问题非常重视,这也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墨子思想的影响,虽然两者对待审美与功利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可以说,正是墨子的礼乐批判促使荀子全面地思考礼乐教化问题,从而完成了先秦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系统化和体系化。而先秦法家尤其是韩非的礼乐批判及美育观也与墨子有相当强的思想联系。此后,《吕氏春秋·大乐》篇论“乐”也曾提到“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这里的“非乐者”无疑是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