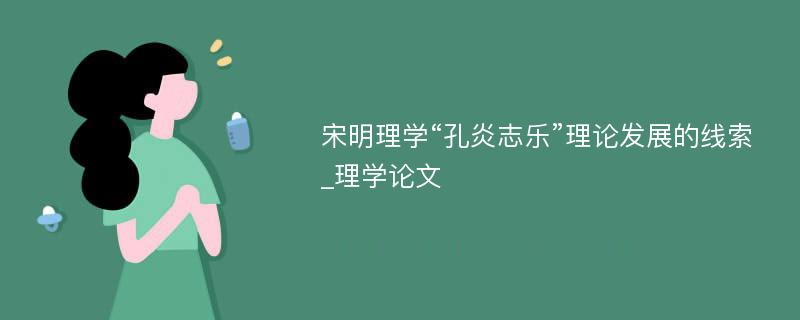
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线索论文,之乐论文,理论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6)04—0039—06
“孔颜之乐”问题自从周敦颐明确提出后,几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有关“乐”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孔颜之乐”论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线索:由注重外在规律、规范到注重个体内心自适;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从精英意识到平民心态;由理想追求到现实现成;从“无我”到“有我”等线索。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和从“无我”到“有我”这两条线索,下面我们就这两点进行阐述。
一 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
大致地说,宋代、明初“孔颜之乐”论更侧重于道德理性,而明中后期“孔颜之乐”论则着重于生活感性。前者更注重道德与理性,给人的往往是崇高感;后者则更注重自然与自适,让人感觉到生活的轻松、愉悦。
在周敦颐看来,颜子乐是因为“化而能齐”即与“纯粹至善”的“圣人之本”齐一,与“天道”齐一,也就是与“诚”一体。① 程颢心中的“大快活”则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乐,真正感觉到自身与天地及天地万物都是浑然一体的自然境界。② 可见,“孔颜之乐”论在提出之初虽然主要侧重于遵循“天道”与“自然”,但是,由于他们心中的“自然”、“天道”并非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天道”,而是包括了“人道”在内的。故此“乐”既有自然活泼的一面,又有道德理性的一面。
如果说周敦颐与程颢心中的“乐”也有与自然“天道”合一的成份,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吟风弄月”,“望花随柳”的乐趣,那么程颐、朱熹等“纯粹天理”之“乐”则完全把“孔颜之乐”看做是“德盛仁熟”之后的事,只是一心“纯粹天理”境界之时的“乐”。③ 程颐、朱熹眼中的“孔颜之乐”主要是与规律、规范一体之后所自然而然具有的“乐”,并不是追求的对象,所以他们把眼光放在“道”的工夫上,而不是放在作为结果的“乐”上。因而当道德规范的绝对性与权威性确立之后,“孔颜之乐”论中遵循自然、“天道”的一面便逐渐被淡化,而道德理性的一面日益凸显。
程颐、朱熹及其后学,以及张载、叶适等都认为“孔颜之乐”是与“理”合一的境界。他们的“理”既有自然规律的成份又有社会规范的内容,身心与“理”完全合一的“乐”也就成为:人的所有思想言行无不与外在的规律、规范相一致,从而达到完全道德、完全理性。张载说:“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然后能无方无体,然后无我,先后天而不违,顺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④ 这便是一个有着完全道德、完全理性的圣人所达能到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实际,圣人只是“从心所欲”而谈不上“逾矩”不“逾矩”,因为圣人已经与“理”完全一体了,圣人本身就是道德的化身,就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达到此“乐”的地步就是想要“逾矩”,想要不道德、不理性都不能,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欲罢不能”。
虽说程朱之“乐”中的“自然”、“天道”的内容已经逐渐减少,淡化,但毕竟还是存在的,而“自然”、“天道”内容的存在就有可能导致自然活泼的非德性的“乐”。因此,到明初,“孔颜之乐”论中的“自然”与“天道”的成份便被进一步地清除了出去,“乐”也几乎成了完全的道德与理性之“乐”。为此,曹端、薛瑄、胡居仁等虽然都认为“乐”也是“心”与“理”合一的境界,但是他们此时的“理”更加倾向于道德的理性即他们所说的“当然之理”。同时,他们在方法上则变得更为严谨清苦,左绳右规,“时时刻刻不忘于操存省察”,⑤ 其目的便在于提高自己道德修养,增加言行思虑的理性成份。
然而,这种纯粹道德、纯粹理性的生活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现实的生活中还有众多非道德的内容,感性的成份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原本多姿多彩,纯粹道德与纯粹理性的生活则是单调的。“物极必反”,当纯粹道德与理性走到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时,自然、感性之乐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乐”思想便在纯粹道德理性统治下打开了一个缺口。陈献章说,学者应该“以自然为宗”,要“使心在无物处”,“不可滞在一处”。而应该顺心之自然,亦即他所说的“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的“自得”境界。他这种“乐”已经开始反对那种纯粹的道德理性了,把目光集中于个体自然、感性与自由之上。从他的一些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⑥
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⑦
风清月朗此何溪,几个神仙被酒迷。云水此身聊起倒,乾坤入眼漫高低。⑧
悠然得趣于山水之中,超然用意于簿书之外。⑨
为何要“放浪形骸”?为何“被酒迷”?正是因为陈献章要打破纯粹道德理性的统治,而寻找新的人生道路。然而,陈献章并没有建立起“自然自得”之“乐”的理论根基,他更多的只是“从静中悟出个端倪”。既没有从“格物致知”的“解悟”中入手,也很少从现实生活的“练习”中入手,只是追求个体的“自然自得”之诗意,所以对于自己冲出道德理性藩篱也是时有惶惑、孤独与不安之感。陈献章在给李德孚的信中便流露出他的这种惶惑与不安,他说:“大抵吾人所学,正欲事事点检。今处一家之中,尊卑咸在,才点检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义则拂和好之情。于此处之,必欲事理至当而又无所忤逆,亦甚难矣。”⑩ 陈献章这一肯定自然、感性自由之“乐”的思想为后来王艮、罗汝芳所发扬。
王艮肯定自由感性之“乐”建立在王守仁“本体”之“乐”的理论基础上,由于他们认为“心即理”,从而找到了作为其理论的根基——“良知”,所以王艮便不再有陈献章那样的不安与困惑。王艮肯定感性之“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肯定道德所带来的感性之“乐”,并以“乐”作为自己的追求。这一点在他的《学乐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他认为不能给人带来“乐”的便不是圣贤之学。二是肯定日常生活中感性之“乐”。“百姓日用即是道”,(11)“乐”是“心”与“道”的一体,而“道”也就是百姓平常的生活,百姓生活中虽有理性之“乐”,但更多的是感性之“乐”,而这也应该是圣人之“乐”亦即“孔颜之乐”。
后来王艮的儿子王襞则进一步把“乐”看做是“现现成成,自自在在”的状态,根本无须经理性思索,如同饥食困眠一般。(12) 在他看来,须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才“乐”,那是“有所倚”的“乐”,并非真“乐”,真乐“无所倚”,“触处皆乐”。如果说王艮之“乐”还是“百姓日用之道”中的“乐”,还是没有完全走出道德理性,只是由纯粹的道德理性而转入到日常的生活基本道德理性。而王襞的“饥食渴饮”式之“乐”则企图通过“良知”把日常基本的道德理性都变成自然与感性。
而罗汝芳则直接把“孔颜之乐”看做是“赤子之心”在一定情形下的自然反应的感性之“乐”。他说:“孔颜之乐”是顺适自然、天机活泼的状态,无需经过理性思考,亦不要“计较寻觅”,要做到如同赤子一般想哭就哭,想笑便笑,“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将来,任他宽洪活泼”。为此他说“乐只是快活二字,岂快活之外还别有乐哉!”(13) 而实际上,“快活”与“乐”还是有所区别的,“快活”这一提法更侧重于生活中的感性之“乐”的一面,而“乐”则涵盖面广得多,罗汝芳把“快活”当做是“乐”也可以看出他的“孔颜之乐”中自然感性的一面。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中“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有一个从重视客观道德理性到提倡主观现成、自在的感性,再到肯定感官、人欲的线索。
二 从“无我”到“有我”
这里所谓的“我”就是指主体与众不同的个性,“无我”也就是不重视主体的个性,而把个体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共性提高到极至,以致把个性的“我”消融在共性之中。“有我”是指实现个体的潜在本质,展示自我的个性。如果说宋代“孔颜之乐”思想更注重的是“无我”,那么明中后期“孔颜之乐”思想则更侧重于个性之“我”的存在。
周敦颐心中的“孔颜之乐”是个体与“诚”一体之“乐”,程颢的“仁者”之“乐”是个体与天地与万物一体之“乐”。按说既然个体与天地万物一体,个体与“天道”之“诚”合一,应该既包括个体的个性与天地万物的共性,不应该是“无我”而应该是“我”与“非我”的统一。但是,在他们看来,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标准是天地万物,是以人去符合外在的标准。这样,有着不同个性的“我”也就消失在外在的标准中。所以,周敦颐说,要获得此“乐”也就只能“思诚”、“反身而诚”,通过“主静”、“无欲”使自己符合“天道”(14),从而把“我”特性排除了出去;程颢“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之“乐”,虽然并不是道家个体自我“玄冥”于万物之“乐”,而是“我”体万物,“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我”境界。但是这种“大我”的境界并不是有着各自个性的“有我”境界,相反也是一个“无我”的境界。(15) 要成为“仁者”就得“除去昔日习心”,直至“与物浑然同体”,使万物成为“我”的组成部分。于是,万物之性也都成了“我”之性,表面看是“我”变大了,然而实际也是“我”消失在万物之中,正如程颢所说:“放这身来,在万物中一例看”,物我之间的差别没了,“我”也就消失了。可见,周敦颐与程颢心中的“孔颜之乐”都是“无我”之“乐”,其获得“乐”的方法实际是一步步地消除“自我”的过程。
“纯粹天理”的“道中之乐”是个体除去与“理”不相符的特性从而完全遵循“理”之后所具有的“乐”。虽然他们也并不完全否认自我个体的特性与自由,他们心中的“孔颜之乐”也有“从心所欲”的一面,可是,他们这种“从心所欲”所表现的自我特性并不是眼前的,而是几乎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的。可见,在此“乐”中,个体的自我仍然消融在外在的“理”之中,此“乐”也是“无我”的境界。正因为他们心中的“乐”是“无我”之“乐”,所以他们大都赞成:喜怒哀乐都是因物之当喜怒哀乐,与我无关。
程朱为代表的“纯粹天理”之“乐”承认在“天理烂熟”之后还是可以获得“从心所欲”的自我自由与个性的,虽然这个“自我”是被外在的“天理”消解之后的,几乎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的“自我”。然而,到了明代,曹端、胡居仁、薛瑄等认为要获得与“所当然之理”合一之“乐”,就应该时刻做到“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就是圣人也一样要时时敬畏,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16)。这样个性“自我”就完全消融于外在的道德规范之中了,就连虚幻的、仅存在于理想之中的个性自我与自由也最后消失了,从而走向彻底的“无我”。
当“乐”走到诚惶诚恐、无限苦楚的地步时,也就与“乐”背道而驰了,与个性自我彻底相脱离,这时就预示着那种“无我”之“乐”已经走到了极点了。在“孔颜之乐”中原本包含着“有我”与“无我”两个方面:“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当“无我”走向极端时,“有我”的思想也就一定会凸显出来。
“孔颜之乐”的标准逐渐地由外在的“理”(和“事”)或“天地”“万物”转向内在自我个体,由“无我”之“乐”转向“有我”之“乐”。这个转向从陈献章开始,他认为,只要自我自自然然、自得其乐便是“孔颜之乐”,从而打破了“理”的藩篱开始朝个体“自我”转向。而后到王守仁提出“乐是心之本体”标志着“孔颜之乐”的标准已经由外在的“事”“理”转变成内在的“心”,从“无我”之“乐”变成“有我”之“乐”。
王守仁提出:“孔颜之乐”是每个人心中原有的状态,虽然他的“良知”之“乐”并没有完全摆脱“理”的影响。他的“心即理”正体现了从“无我”到“有我”转型时期的二面性:如果“乐”是以我的“心”为标准,那就是“有我”的“乐”;如果以“理”为标准,那就是“无我”的“乐”。为此,在获得“乐”的方法上体现出“无我”与“有我”的两面性:“本体功夫”与“格物”“正心”的修治。“正心”也就是不断地做“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可是“正心”以什么作为标准呢?当然不能又以“心”为标准,若以“心”为标准那“正”也就无从谈起,可见,这时实际的标准仍然还是外在的“理”。故而王守仁所侧重的“正心”方法依然是“无我”的方法,是以“理”来检验“我”的方法。而“本体功夫”的方法则立时就体悟到自己的“本心”无限光明,当下便可体会“孔颜之乐”,并不须要用“理”来裁剪自我个性,是“有我”的方法。
后来,王艮、王襞、罗汝芳把“孔颜之乐”发展为充满个性、自由、活泼的“有我”之“乐”。此“乐”的标准是个体自然、直觉之“心”,从而突出了“乐”中的“我”。
王艮的“乐”还是提倡“学”“百姓日用”之“道”,使我“心”循此“日用之道”。而王襞则认为真正获得“乐”的工夫是“不犯手”的,甚至认为王艮的“学”也是多余的,也是对自我个性的破坏,因为现成、自然的生活就是“乐”,故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什么。一旦要存心地去学什么,那就是“私心”,也就不可能真正“率性而为”,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乐”。(17) 可见,王襞在获得“孔颜之乐”的方法上已经顺适我心,率性而为了。
如果说在王艮那里获得“孔颜之乐”的方法还得循“百姓日用”之“矩”,“我”还是受到限制的,那么到了罗汝芳那里就连这个“百姓日用”的“矩”也可以不要。“工夫难到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在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18) 罗汝芳认为:只要顺着自己的“赤子之心”而行,有些工夫做不到,若没办做到,那就干脆不做,免得没有做到一直放在心里不踏实;或有些要求、规矩、规范本来就是错的,或难以做到的,“有大识见”的人就可以根本不去做。如果不遵循这些规范时感到一时还有些不踏实,那不踏实就不踏实,在他看来,这时的不踏实,没有依归感,也就是一种现实的状态,就顺着它去,做不到时能不去做本身也就是一种工夫。此方法已经达到当时可能的极至了,不仅突出了“孔颜之乐”中“从心所欲”的一面即自我个性与自由的一面,并且还进一步对消融自我个性的“矩”提出了质疑。
三“孔颜之乐”理论发展的内在原因
从上面对于宋明理学中“孔颜之乐”理论发展线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中“孔颜之乐”理论发展是由强调人的责任、义务、伦理、道德等群体“利他性”到侧重于人的自由、快乐、自然、感性等个体的“利己性”。那么,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呢?我们认为,“孔颜之乐”理论如此发展并非偶然,实有其深刻内在原因:
其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果。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个体之意识觉醒与逐渐扩大。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导致了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这种范式所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注重道德修养,强调整体观念和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特别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作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巅峰的宋代在理论上即“程朱理学”中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特征,同样,作为“程朱理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理学”精髓之一的“孔颜之乐”理论,当然也逃不出这些整体的特征。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即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开始对传统农耕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腐蚀和瓦解,那时,传统的自给性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的结合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从而使得个体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这种经济地位的独立性必然要反映在思想上,这就是体现个体自由、快乐、自然、感性的“孔颜之乐”理论的产生。
其二,“孔颜之乐”理论内部固有矛盾的运动的结果。理论是人所创造的,但是当理论被人们创造出来之后就成了客观的存在,也就有了客观的运动变化规律,这种变化根本上决定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论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同样,“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也是其内部固有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孔颜之乐”理论中主要有这几组矛盾:自由与约束即“从心所欲”与“矩”,社会与个体,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性,道德与情感,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当群体的责任感、道德感与义务感等“利他性”的精英理性走向极端,变得惶恐不安,“不敢越雷池一步”时,与群体“利他性”之“乐”思想同时产生但却遭受压制的现实、自然、感性的个体“利己性”之“乐”思想只能以非主流的形式存在着。然而,“物极必反”,当作为矛盾的一方即个体“利己性”之“乐”被压制到极点时,便自然要浮出水面。正因为矛盾运动的方向必然是向着对立面转化的,所以,可以说“孔颜之乐”理论的这种发展变化也是其内部固有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其三,人们认识的深化的结果。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也是当时人们对“孔颜之乐”认识由外而内的深化过程。
如果说作为开端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乐”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但同时又是比较模糊的、浅层的;那么,到程朱理学时期,对“乐”的认识主要是对外在规律、规范的认识,处于“格物穷理”的阶段,属于“外向性”认识阶段;陆王心学包括后来王艮父子及罗汝芳等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开始把眼光投向自身。此时,他们对“乐”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对外在规律、规范的认识了而是变为对外在规律、规范内化成为主体自我组成部分的认识,属于“内向性”认识阶段,带有一定反思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外在规律、规范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从认识的逻辑上看,应该还有个“乐”总结阶段,属于逻辑地回到原点,可是,宋明理学的总结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其四,修养方法转变的结果。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也是由于修养方法由重“解悟”到重“体悟”的结果。
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应该回归到实践之中,其具体体现为修养方法由重“解悟”转变成重“体悟”的过程。程朱理学中对“乐”的认识主要是处于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如何诠释“孔颜之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强调社会性与理想性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到明中后期,对“乐”的认识进入到实践阶段,这时,人们发现原来的认识难以在实践中取得效果,“理”与“心”“难凑泊”,按照原来的方法对追求“乐”所得到的却是一种苦楚,于是抛弃原先的“解悟”与理想,转而重视个体与现实的“体悟”与实践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注释:
①(14) 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1~38页;第38页。
②(15)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第16~17页;第33页。
③ 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1,第114页。
④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85,第80页。
⑤ 薛瑄:《读书续录》,《读书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卷四。
⑥⑦⑧⑨⑩ 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第275页;第276页;第449页;第138页;第240页。
(11)(12)(13)(17)(18)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卷三十二;卷三十二;卷三十四;卷三十四;卷三十二。
(16) 薛瑄:《读书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