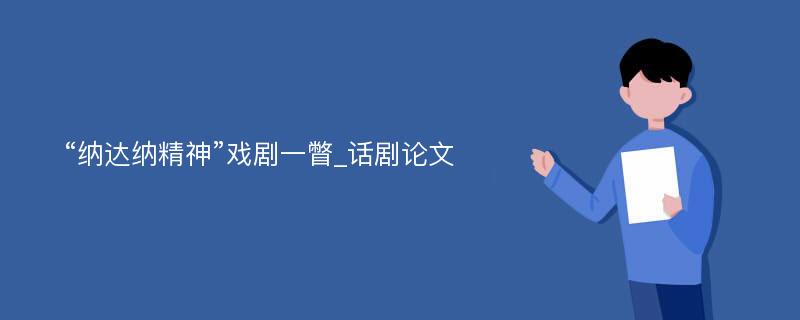
一瞥话剧《娜当娜的灵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光论文,话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对《娜当娜的灵光》的兴趣,首先在于它是一部由国外百老汇戏剧作家阿瑟·柯比特创作的当红戏剧。这部戏到了北京,由北京的戏剧团体改编演出,由影视、戏剧演员史可导演并演出,究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惨遭夭折的命运,还是会因为其鲜明的异域色彩,给北京的话剧市场带来一线灵光?
故事其实很简单,说的是一个男人如何因为金钱与社会认同的刺激,在咄咄逼人的劝诱之下,而不惜以阉割自己为代价,换取搞不清真假的一纸合同。尽管有些悲剧色彩,有些荒诞之处,但整出戏并不声嘶力竭,既不去刻意展现生命在金钱与权势面前的脆弱,也不把那种荒诞不经演绎为嘲讽或批判。在戏剧的表层,它最起码做到的,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离奇而别致的故事。但百老汇的戏剧,自然有着百老汇的固有传统。这一传统,表现在《娜当娜的灵光》中,是其在情节意义的层面下,流淌着饱满的个人表达的意味:是其在讲述故事的前提下,刻意雕琢语言的多义与丰富;是其在戏剧形式感的要求下,追求表演中个人才华的充分展现等等。其实这些因素,只是一部优秀话剧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东西;但在近些年的北京话剧市场,这些使话剧充溢生命力的元素,却似乎让我们觉得陌生了。当然,只要能感觉到了陌生感就毕竟是件好事。不同的风格只要能带来某种冲撞,就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希望;这也是一次启迪,展现给我们话剧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展现在北京观众面前的,并不仅仅是阉割所象征的男性尊严的失落(当然,话剧表达男性尊严的失落,对女权也不忘嘲讽),而且是在表演过程中不断从演员的表演中蹦出的粗俗字眼。作为一种修辞手段,阉割在艺术样式中已经不足为奇;但在这种共享共同空间的戏剧观赏中,既不像坐在家中看VCD一样具有强烈的私人性, 甚或也不像看电影——那毕竟是一种在胶片上演绎的真假难辨的表演,从而也具有了遮蔽的保护色。当你置身于百人以上的剧场,听着如此赤裸的粗俗词汇:这些词汇本来只在男性群体中以一种秘密方式的流通,似乎绝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在本应高雅的话剧舞台上出现,我想人们被包裹紧密的神经,也会被触痛的。
毕竟语言这样一种形式,本来就极端具有穿透力的: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那我们就来颠覆语言秩序吧!语言,也是一种直指中产阶级虚伪道德价值准则的利器,在《娜当娜的灵光》中,语言以自己的暴力旅行,通过把一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在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阴暗的欲望释放出来,从而完成其调侃、戏弄这个社会虚假道德准则的使命。这种释放,也许会带来一种难以表述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我想对中国的大多数观众来说,只能停留在引而不发之中;为了维护自我道德水准的尊严,很难流露出欣赏的自然快感:因为那不啻是在向众人袒露内心。
看《娜当娜的灵光》,让我最先想到的是库布里克的《大开眼界》。尽管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但那种对欲望、色情的残酷展现,却有着美国人的共通之处。关于欲望与色情,我想对美国人而言,可能因为其太过致命,也许反而成了太过平常的话题。思考并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对一个导演或一个剧作家来说,不过是份内的事情。但这种东西,到了中国,又会遭逢什么样的命运呢?当话剧演员在现场直接地做出具有性象征的表演,说出猥亵性的语言,对中国的话剧观众来说,却也是一种挑战。
但有了挑战,也就会有回击。我倒希望它刺痛了软绵绵的中国话剧市场,给它注射一剂强心针,在惊耸之后,会有着鲜活的力量。
